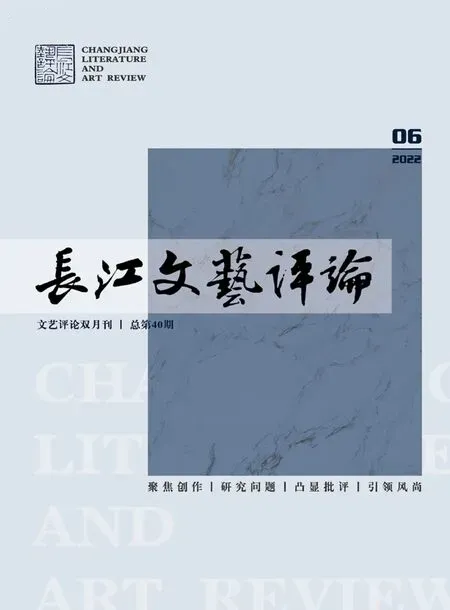刘守华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建构
——以“类型”为中心的讨论
◆林继富 马培红
中国故事学体系建设离不开众多学人的砥砺奋进,刘守华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成绩卓著,先人一着[1]、可点石成金[2],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建构作出了奠基性贡献[3]。自1956年他在《长江文艺》发表《论民间讽刺故事》,就开始对民间故事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学术研究,聚焦艺术世界、梳理民间故事史,走向故事诗学等在他的民间故事学体系中熠熠生辉,而这些探索离不开对类型的理解、借鉴、融入与深化。不管是勾勒故事生活史、展现故事艺术光彩还是探求民族、宗教与故事关系,他的民间故事的类型思维贯穿始终,成就“最突出”[4]。“类型”是刘守华故事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在多年研究中已如毛细血管一样融于他的民间故事研究中,上升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析思维,并将他从事的民间故事研究引向诗学叙事。目前对其类型研究的讨论往往是分散的[5],并没有系统的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类型研究成果。因此,系统理解以“类型”为中心的刘守华故事学理论建构,不仅可以呈现他与众多学人交往中,与时代同频共振中的类型研究脉络,更重要的是可以丰富刘守华故事学研究体系。
一、“一组”民间故事: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意识
在西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特别是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纂与研究理论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部分学者开始了类型研究。虽然比较研究与钟敬文民间故事“型式”研究业已关涉到民间故事“类型”问题,但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意识并不明显。刘守华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民间故事研究,却并未有民间故事类型的分析。刘守华对民间故事有“类型”意识,并从“类型”视角进行研究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的。“一组”“近似形态”等话语表达蕴含了刘守华故事集合性质的“类型”研究,这也构成了他关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起步阶段。
(一)“一组”民间故事:集合式“类型”观念的叙事
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刘守华常将民间故事分组归类,建立同类故事集群,而跨国比较研究,让其一开始就具备了国际性民间故事组集合意识。1979年刘守华对德国《格林童话全集》中“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似曾相识”[6],后查找发现与中国的《三根金头发》“多么相似”,在发现其并不是模仿格林兄弟的文本时“喜出望外”,在发现十几个文本后感觉“更加令人惊异”,于是将中国和德国的相似故事列为“一组”。随后,刘守华发现在德国《格林童话全集》中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中国民间故事选》中的《三根金头发》《日卡孤儿故事》《穷人寨》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富玛耳科和倒运的华西利的故事》里,距离遥远的三个国家在“三根金头发”故事上的艺术构思和情节结构方面却是“相似”,是使人“不胜惊异”的“奇特现象”。特别是在中日民间故事中,“模样相似的姐妹篇随处可见”[7],“构思相同”“形态相似”“艺术构思十分相近”“情节结构大致相同”[8]。他惊叹于不同国家故事的相似之处,并将它们作为“一组”故事进行比较,然而这时对作为民间故事学术概念的“类型”他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晰。
虽然他“当时没有类型学知识,只是把若干篇情节结构大同小异的文本进行比较,发表粗浅议论”[9],但是却在“大同小异”比较中丰富了对民间故事类型的认识。事实上,潜在的类型概念,以及以类型为切口的民间故事研究已经在摸索中逐步展开。《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刘守华以“代表作”的方式将童话分类归纳为20类并列出每个类型的具体故事,如表现人民道德观念的《仙女故事》有《螺顿变人》《天牛郎配夫妻》《蒲妹》,表现生产斗争的《开山造河故事》有《盘三哥》《三个儿子》。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归纳新的分组,他将找到的“古今中外大同小异”的《木鸟》《鲁般做木鸢》《金翅鸟》《乌木马的故事》等十个木鸟故事[10]归纳为科学幻想故事等。
从国际学术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民间故事领域的AT分类法,1937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78年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均已出现,但因没有中译本而尚未进入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范畴。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这也恰好说明这一时期他的民间故事“类型”意识是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学术传统。
(二)“大同小异”:民间故事溯源与关系建构
刘守华关于“民间故事组”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比较寻找民间故事之间的异中之同,阐释民间故事的相似点,寻找故事相似的原因以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故事的联系性。
在他看来,这种“同”,一方面可以建立完整的故事脉络。为了对钟敬文的《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中孟姜女故事两阶段划分进行补充,他结合大量故事资料,在比较中寻找故事的主干,进而发现孟姜女故事演变分为杞梁妻善哭和哭倒城墙的原始形态,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情节的基本形态以及她和秦始皇面对面展开斗智斗勇投海而死三个阶段[11];另一方面,这种“同”揭示了中国与不同国家如印度、日本、阿拉伯等的民间交流。刘守华沿着印度《五卷书》[12]中记载的民间故事脉络发现,它们以翻译佛教经典或对印度故事的改编等多种形式流向中国并加入中国文化色彩,展现了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的交往交流。他还将经济、地理等因素结合起来寻找民间故事源流,在充分分析《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与《苏遏》相似原因后他推断,它们“应是从同一故事演化而出。从它在中国扎根之深、流传之广乃与中国民族生活、心理之紧密联系来看,它很可能是在唐代,同古都长安的辉煌形象一道传入阿拉伯地区的”[13]。同样地,刘守华针对“三根金头发型”故事,将中国、德国、俄罗斯相关故事比较后认为,“中国的《淌来儿》形态最为古老,似乎最先在中国形成”[14]。他这种“找来源”的老做法[15],虽然看似新意不足,但是对于理解同一类型民间故事源流与演进则大有裨益。
刘守华对民间故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跨国比较,并深入分析民间故事源流关系,与后来引进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在分析思路和寻找民间故事生命史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他的类型意识在日本学者饭仓照平看来并不完善,他结合日本翻译的刘守华的《略谈中日民间故事交流——读〈日本民间故事〉》[16]一文,认为“仅就这些故事来看,如果能参考艾伯哈德和丁乃通的故事类型索引等研究书籍,可能会指出更多的彼此相类似的情况”。不过也正是因为没有参照西方类型研究,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意识的形成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
(三)学术关系:类型意识的多重来源
刘守华的类型意识隐含在对民间故事资料、方法、对象的把握上。这一点与其过往的资料搜集习惯、国内学术传统以及学者之间的交往有密切关系。刘守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间故事搜集奠定了类型意识的资料基础。他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去搜集洪湖革命歌谣及相关的故事传说”[17]到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搜集当时出版的各种民间故事、民间童话小册子,便成了自己的课余爱好”[18],为其了解不同地方的民间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遵循故事“型式”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始于1928年钟敬文、杨成志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发展于1931年钟敬文撰写的《中国民谭型式》,他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归纳为45型51式。在民间故事研究中,钟敬文“将众多故事辨析异同,定型归类,再作深入解剖”[19],形成天鹅处女型、蛇郎型、老獭稚型等故事类型研究成果。钟敬文的故事研究思路也直接影响了刘守华。因此,刘守华是沿着以往中国民间故事的学术传统进行故事研究。同时,对比较方法的坚持让他具备比较的思维和视野,将民间故事作为“一组”的类型意识就是在比较方法加持下得以展开。钟敬文、季羡林等学者“多次鼓励我进行故事的比较研究”[20]。这些都坚定了刘守华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多侧面开掘民间故事的信心。“比较研究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21],尤其是跨国比较,使他一开始的类型意识就具有了国际性,可以从国际层面建立更为宏大的故事交往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比较方法是他从事民间故事学研究的学术支点[22],撬起了他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方向。
二、把故事作为类型[23]:刘守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成熟实践
民间故事学中的“类型”,源自1910年芬兰学者安蒂·阿马图斯·阿尔奈在《民间故事类型》使用的type一词。故事学家通过比较其异同,将这些文本归并在一起,称之为同一“类型”[24]。刘守华努力吸收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类型研究成果,眼界大开。同时,刘守华收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25]跨国邮寄的英文类型索引著作,接受丁乃通的指导,在他们具体帮助下,他深刻地领会并掌握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方法,并从资料、内容、方法层面扩展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宏观与微观:呈现民间故事风貌的整体特质
一个民间故事类型是众多异文的集合体,既有宏观的故事整体性又有单个故事的个性色彩,这种宏观与微观层次为刘守华提供更多学术研究空间。刘守华认为,一个故事类型是一个故事,单篇异文有缺点,或“完美”或“粗俗”或“缺胳膊断腿”,若是研究者“随意抓住某些异文给予评说,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这一个故事的思想与艺术特征”[26],也就是说,只有从类型入手才能够清晰地理解民间故事主题、思想特征与艺术魅力。在具体研究中,就要“集聚众多异文,注意吸取学界对相关类型的研究成果,将类型整体和多样化变异联系起来,更深入和更完整地把握这些故事的思想与艺术特质”[27]。其中体现的“多”与“一”的关系对应了宏观与微观民间故事层次表达。
刘守华在研究中不断结合大量民间故事资料深化对类型的认识。类型索引极易受资料所限,难免有疏漏之处。特别是中国成百上千万的故事体量,而列入索引的仅仅是其中的小部分,这样来看,索引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了。在蛇郎故事研究中,AT分类法将神奇故事433型《蛇王子》分为433A、433B和433C、433D四个亚型。刘守华结合搜集到的蛇郎故事还发现了两个类型,“我把它们列为433E和433F。其中433F型为蛇民族的始祖传说,形态最为古老,到433E型出现,蛇郎形象起了大转变,由人们尊崇的始祖,变成了‘怪人妻女’,罪孽深重的妖精”[28]。通过对这一故事类型的补充和精细研究,刘守华指出,就整体而言,印度、缅甸的433A、433B、433C和中国的433D、433E、433F是两个不同故事系统,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分别开放的两朵奇异花朵[29]。他以民间故事的具体案例解释了中印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驳斥了历史地理学派的一元论,深入讨论民间故事的多元播化。
类型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揭示民间故事特质的有效方法。刘守华通过类型研究,希望“对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文化特质及其珍贵价值,它的精美之作和整体风貌,求得一个切实的认识”[30]。具体来说,就是服务于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探索,从微观上揭示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从点到面,进而在“宏观上揭示出中国民间故事所建构的优美艺术世界的特征”[31]。
(二)结构关系:建立民间故事类型“家谱”
类型研究开辟了深入民间故事内部肌理解读故事的路径。刘守华认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是,“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求异文,并对其异同之处作精细比较,解析出它的母题和类型;然后把它们置于一定历史地理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中构拟出故事原型,从横向的地理传播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再依据原型回头考察有关异文,便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由此勾勒出该类型完整的‘生活史’了”[32]。进一步来说,就是从广泛搜集故事、解构同类故事、追寻故事最初时空、构拟故事原型,在历史地理中建立故事的原型和祖籍,形成对民间故事类型的完整结构关系的解读。
对此,刘守华积极利用历史地理学派方法探索民间故事生活史,建立民间故事传承演变“家谱”。“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实际上也和人类一样,有自己的家族”[33]。刘守华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就从文献角度尝试勾勒了白水素女、田螺姑娘、叶限、田章等十几个贯通古今的故事类型的家谱。以天鹅处女型故事为例[34],刘守华将天鹅处女型故事追溯至《毛衣女》,并脱胎出三个亚型:一是在鸟姑娘找到自己的羽衣飞走后,接下来着重叙述其子上天寻母、母子团聚的经过,可称作“鸟仔寻母型”,如《田章》,汉族的《七星仙女》、壮族的《鸟眼田》、瑶族《坚美仔斗玉皇》、傈僳族的《花牛牛和天鹅姑娘》等;二是故事中在鸟姑娘飞走后,着力表现丈夫追寻妻子、直至夫妻团圆的经过,可称为“丈夫寻妻型”,如苗族的《天鹅姑娘》、瑶族的《五彩带》和汉族的《天牛郎配夫妻》等;三是将鸟姑娘的爱情故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上,同民族战争、宗教冲突等结合起来展开叙述,赋予作品以更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如傣族的《召树屯》、藏族的《普兰飞天的故事》、蒙古族的《格拉斯青》。由此,他将不同民族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纳入其中并建立了从源流—亚型—各民族故事的庞大家谱关系网。在这个过程中,类型对于民间故事风貌的整体呈现,庞大资料异同的处理、母题对于梳理故事演变脉络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样本解析:重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模式
刘守华不拘泥于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在吸收和融入历史地理学派、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研究理论之上,结合自己多年对于民间故事研究,试图建立更具操作性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模式。他认为类型解析时,“可以从‘大同’之中看出它们共有的母题、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情趣等等,展现出故事的原型;也可以从‘小异’之处看出不同文本的民族地域色彩以及讲述人的个性风格等等”[35],才能获得对故事的完整印象。为此,他努力结合自己的学术旨趣建立民间故事类型分析模式,不仅包含故事梗概和母题构成情况,还包含“流传分布情况及其亚型,文化内涵及其叙事美学特色,历史演变和跨国、跨民族比较,以及本类型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等等”[36]。他并不是一味寻找原型,而是从结构上解析母题,从范围上弄清区域,从文化上阐述内涵,从研究上了解动态,相比于西方类型研究重形式和情节结构的特点,刘守华的分析模式增添了对民间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的关注,注重开掘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之美。
重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模式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刘守华从浩如烟海的故事中选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蜈蚣报恩”故事解析》《怪异儿的英雄传奇——“怪异儿”故事解析》等60个故事类型进行富有操作性的集中尝试。如对《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解析中,首先丰富《宝船》的异文并作出故事梗概,然后,找出其源头——佛经中的“本生故事”如《阿难现变经》的《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命》,并将中印故事进行比较,推断中国故事脱胎于印度故事,进而详细阐述该故事在中国不同地方经历的各种演变与再创造。这种民间故事类型解析一方面建立了丰富的类型研究样本,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倾向。
(四)学术导向:探寻民间故事类型中的文化意蕴
针对历史地理学派较少涉及“故事文本所涵盖的生活思想内容、叙事美学特征,以及同传承者之间的联系等”[37]问题,他在既有的结构分析基础上,注意对民间故事文化思想意蕴的透视。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繁复多样的背后“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38]。对此,刘守华立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本土特质和历史文化实际,建构自己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特色。
刘守华努力探寻类型故事背后的文化意蕴和古老的文化因子。民间故事主题的文化特色是他探寻的要点。“狗耕田”故事从兄弟分家开始,以弟弟分得的狗能耕田创造奇迹为核心母题,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在中、日、韩分布广泛的故事群。刘守华在分析中日韩三国社会历史环境后指出,“关于兄弟间均分家产这一制度、习俗是它构成和流行的社会文化基础”[39],这一习俗是中国所独有的,日本、韩国均没有兄弟均分家产的文化渊源,因此,“狗耕田”故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他还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生活现实中探究故事类型长盛不衰的文化根基。刘守华发现晋代陶潜《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台湾的《田螺的故事》和福建流行的《螺女江》属同一类型,他认为这些民间故事展现了两岸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在海峡两岸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中,表明了中华文化根基的强固有力”[40]。虽然他是按照类型、母题解析故事,但“都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41]。因此,在类型研究中,他广泛运用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将故事放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注重故事文化意蕴的根源性分析和社会习俗分析。这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努力在类型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通过引进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丰富对故事类型的文化认识,建立民间故事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从民间故事类型家谱到建立民间故事整体分析框架,并深入探究民间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根源,这是其对国外类型研究的中国化,代表了他的学术旨趣和观照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民间故事类型分析模式已经融入到民间故事史、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以及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阐释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守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道路上,丁乃通是不能忽视的引路人,他夯实了刘守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在两人的交往中,刘守华一方面通过书信往来接受指导,丁乃通鼓励刘守华用历史地理方法探索“求好运”的生活史,并在1983年5月的信中写道,“AT460和461是一个故事圈或集团……假如我是你的话,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42];另一方面,刘守华参阅丁乃通寄来的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在1985年9月份,邀请丁乃通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主要讲述汤普森的著作讲授西方民间故事学类型学,介绍芬兰历史地理学派方法,这些使刘守华能够更为系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理解和熟悉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母题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使自己的以类型为中心的民间故事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
三、回归“口头语言艺术”[43]:刘守华民间故事类型的诗学阐释
如果说刘守华将民间故事与宗教、民族、生活结合挖掘民间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以扩宽民间艺术世界的广度,那么对民间故事的深化则是以更超拔的眼光赏析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间故事,以此提升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高度。他在一贯追求的民间故事的“核心或本质是其艺术世界”[44]的基础上提炼出共同的价值内核和美学特质,将对民间故事类型更深层次的生命力推向诗学层面,进而散发富有史诗魅力的学术光彩,彰显其学术追求和社会关怀。
(一)艺术价值:文化基因融古通今的关联表达
立足于世界民间故事生活圈,成千上万的民间故事异文化约而成的类型无疑是异中有同,而这个“同”所建构起来的故事生活圈,则内涵了不同民众和地区古老的文化基因,包含把世界连接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以AT461型“求好运”为例,主要讲主人公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小伙子,他们累世受穷,便要出门找原因,不管是问事还是寻宝,他都努力与命运抗争,改变自己贫困不幸的命运。“求好运”故事超越时空构成故事流变的“世界性故事圈”,刘守华认为,这个故事折射了人类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寻求幸福的美好意愿,蕴含史诗般的魅力。
置于世界民间故事圈的中国,求好运自然在普适性价值中意涵中国民间故事的价值表达。这在刘守华看来是中国文化根基的表现,是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时代生活紧密关联,且古今贯通。刘守华将这些不同地区、民族的民间故事异文联结成为口头叙事作品的整体,再结合中国大地为“求好运”而涌动的民工潮来看,其史诗魅力与诗学价值得到彰显。他认为,“求好运”的史诗魅力在于主人公积极进取、奋力向命运抗争的精神和“代人问事获好报”的突出主旨[45]。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主人公代人问事的这种先人后己的精神与墨家的兼爱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将当下的价值表达与中国文化根脉、传统基因建立了联系,凸显了民间故事贯通古今的价值联系和文化基因的复制和创新。
刘守华从历史与现实维度拓展民间故事类型共同价值的广度和深度,探索更为宏大的深层价值意蕴所展示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46]。这种美揭示了文化基因的魅力,使得文化基因在传承演变中根深蒂固,融入社会发展不断散发枝桠而又历久弥新。
(二)艺术塑造:民间故事类型的美学表达
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注重叙事艺术,力图回归“口头语言艺术”,并将文艺学、美学融入其中进行民间故事类型解读。从表达方式来看,他主要从语言艺术、形象塑造方面探讨民间故事类型。
民间故事类型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异文的个性色彩上。刘守华在采集梁祝传说的时候提到结尾处关于马秀才扒坟的描述:“马秀才气哭了。他咋不气呢?马家接,马家抬,马家只落得一只鞋!方圆几十里,名誉难听。当下他就用手扒。他气得不吃饭,不喝水,一个劲地扒。肚子饿了,他就紧紧腰带。扒呀,紧呀,腰越紧越细,头和屁股越来越大,终于晕倒在地上,变成了蚂蚁。所以,蚁蚂的腰至今还那么细”[47]。故事用朴实的话语将马秀才变成蚂蚁的情景描述得活灵活现,叙述风格摇曳多姿。
叙事形象的塑造在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而象征是民间故事的重要表达手段。正是通过象征手法的张力,将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活与民间把故事世界的生活进行了转化叠合。“叙事艺术的奥秘则在于将大量神话中的神奇幻想转化成了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理想意愿的象征性表达”[48]。刘守华认为,“巧妙编织而成富于象征意义的故事,较之直接叙说人类社会生活中同一主题的真实故事,更具有概括意义,更耐人深思体味”[49]。民间故事中的形象不计其数,但是在类型性质的民间故事中,就保留着一些民间故事形象塑造的共同性。这一点,在以人和动物为角色的故事类型中表现明显,如“神蛙丈夫”“龙女”“虎妻”等都以象征手法增加民间故事的趣味性。在《蛇郎》故事中,人蛇婚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民间故事中就可以用蛇象征某类男性,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民间故事中俯拾皆是,这些都是为了增加民间故事的趣味性,也包含了某种古老的信仰要素。当然,刘守华还将象征性表达放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如中国神奇幻想故事中断尾龙子类型,塑造的断尾孽龙形象是“一个既古老怪异而又极具现实性和人情味的独特艺术形象”[50],这种矛盾的艺术形象,在他看来就是象征一个激烈社会动荡中的“社会叛逆者”[51]。
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类型分析中,不管是语言艺术还是形象塑造,他都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展现民间故事类型富有感染力的美学特色,并善于将民间故事关联到社会历史与现实,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时空中建立对民间故事类型的深刻把握。
(三)艺术构思:聚焦母题的附会与衔接
对于民间故事类型而言,因其具有跨国、跨地区、跨民族的异文而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重点在于“解读或剖析贯穿于同一类型众多异文中的母题,由母题及其组合情况来考察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特色”[52]。聚焦母题的附着与衔接所形成的艺术构思就展现了故事的奇思妙趣。
围绕母题的艺术构思表现的是不同讲述者对故事的加工。黄鹤楼传说中,刘守华看到了仙人驾鹤的核心母题“神仙情结”[53],他解读黄鹤楼传说时提到,“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至霄汉,俄顷已至,乃黄鹤之宾也”,他从飘然、俄顷等细节描述中发现黄鹤楼传说的神仙情结,并强调虽然黄鹤楼传说几经变迁,仙人也在荀環、子安等角色间飘忽不定,但是神仙情结依然稳稳地在黄鹤楼传说中流传,饱含了道教文化色彩的艺术光芒。
民间故事中既有单一母题的不断丰富,也有多个母题的相互衔接。母题之间的联结也是故事魅力的意味所在。在刘守华看来,流传在湖北省西部地区的《樵哥》“是义虎型故事中最富有诗意的一篇”[54],主要表现在人虎情缘母题的魅力。刘守华认为,它“是一个由多个母题巧妙串接而成、情节曲折动人的复合型故事”。针对母题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本故事中三个母题的串接就是情节的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而其间的人物对话、情境描绘和细节设计,虽均系朴素的口语点染,却富有匠心”[55]。对母题的精巧构思使得故事可以波澜起伏,在生动有趣中又延续了民间故事的艺术生命力。
作为故事类型的精神基因与文化价值追求是故事诗学的生命力之根本,象征表达和艺术技巧构思是让民间故事绽放奇光异彩的诗学方式。刘守华的诗学探索正是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生活之美和精神之美”[56]讨论的凝练与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故事诗学是刘守华学术研究的一贯特点,他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对民间故事诗歌的节奏,语言的夸张、形象的比喻等修辞富有诗意的强调[57],到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向故事诗学》,这是对以类型为中心的民间故事研究新的跨越。
结论与讨论
刘守华紧跟国际国内民间故事发展潮流,在充分吸收不同学者民间故事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着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民间故事学体系。类型研究就是其汇入世界学术网络,展开学术对话和研讨,并深入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略。从有意识的“一组”民间故事的比较、民间故事类型分析模式建构以及娴熟运用民间故事类型再到理所当然的故事类型的诗学分析,构成了刘守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脉络。虽然他不满足于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母题解析这一套[58],但也从未离开对于“类型”“母题”的创造性运用,并由此建构了属于刘守华的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
刘守华以类型为中心的故事学体系,基于他持续性对于民间故事资料收集所形成的庞大资料体系,这是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民间故事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追寻,从而系统、深入呈现并丰富了他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解。由表及里、从微观到宏观的共同价值挖掘与艺术呈现使类型学的故事研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类型出发,他对故事圈史诗般魅力的理解正好与“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的价值联结在诗学层面相契合。
类型作为一种模式化分析思维已经融入并像树根一样稳稳地扎根于刘守华的故事学体系,促使其故事学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透过类型,刘守华研究民间故事这块“多棱宝石”[59]显得更加耀眼。只是基于民间故事文本的类型分析难免缺乏故事类型转化为生活中具体故事讲述的诗学情感,这也为后学者留下了故事诗学研究广阔的空间。
注释:
[1]刘守华:《刘守华故事学文集(第3卷)·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前言页。金荣华写给刘守华教授的信件提及“您在故事研究方面常有先人一着的卓见,成果又丰硕”。
[2]黄永林:《刘守华:把中国民间故事“点石成金”》,《光明日报》,2019年1月21日第11版。
[3]张锐,夏静:《刘守华:深潜于民间故事,沉醉于泥土芬芳》,《光明日报》,2022年4月13日第13版。
[4]施爱东:《故事学30年点将录》,《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5]黄永林:《追踪民间故事建构故事学体系——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评述》,《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刘晓春:《增强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话力量——以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6]刘守华:《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新华文摘》,1979年第11期。
[7][16]刘守华:《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读〈日本民间故事〉》,《比较故事学论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186页。
[8][25]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的中日之旅——为日本“中国民话之会”的落幕而作》,《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5期。
[9][27]刘守华:《关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一些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0]刘守华:《“木鸟”——一个影响深远的民间科学幻想故事》,《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11]刘守华:《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对〈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的补充》,《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12]刘守华:《印度〈五卷书〉与中国民间故事》,《比较故事学论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13]刘守华:《〈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故事札记》,《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14]刘守华:《民间童话之谜——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之二》,《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
[15]《金克木先生来信》,1983年3月26日;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3页。
[17]刘守华,孙正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18]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后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19]刘守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20]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后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21]刘守华编:《民间文学概论十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22]林继富,马培红:《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论建构——刘守华故事学思想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4期。
[23][41]被访谈人:刘守华;访谈人:漆凌云;访谈地点: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812室;访谈时间:2015年5月8日。漆凌云:《他山之石与本土之根:故事类型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24][30][31][32][35][36][37][49][52][59]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导论,第 2页,30页,29页,25页,23页,28页,25页,32页,23页,733页。
[26]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思想战线》,2003年第 5期。
[28][29]刘守华:《蛇郎故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2期。
[33]刘守华:《孔雀公主故事的流传与演变》,《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34][50]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288页,170页。
[38]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论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39]刘守华:《兄弟分家与“狗耕田”——一个中国民间流行故事类型的文化解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0]刘守华:《闽台蛇郎故事的民俗文化根基》,《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4期。
[42]《丁乃通先生来信》,1984年5月8日;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4页。
[43]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4]刘守华:《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刘守华自选集》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5]参见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6][56]林继富,马培红:《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论建构——刘守华故事学思想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4期。
[47]刘守华:《湖北“故事村”里传承的梁祝传说》,《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48]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1][58]刘守华:《叛逆的异类——秃尾巴故事解读》,《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3]刘守华:《黄鹤楼传说的“神仙情结”》,《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54][55]刘守华:《人虎情缘的诗意书写》,《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