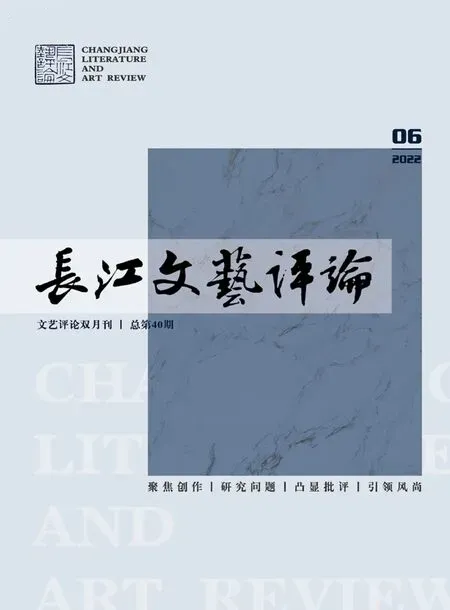村居记忆、民族立场与体验叙事
——评李鲁平诗集《桩号73》
◆赵亚琪 庄桂成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新诗界的诗学建构与诗歌批评经历了体式与内核的重构、方法与路径的更新、学理与领域总结几个阶段。新世纪以来,诗歌谱系研究方法以“代际划分”为主流,而成长于“镰刀”的光影和“麦子”的锋芒的“60后”诗人群作为诗歌代际划分谱系中的兼具历史意识和实验精神的“洪流”,诗风整体性呈现出以“进场”与“还乡”为关键词的体验叙事风格。《桩号73》就是“60后”诗人李鲁平2017年以来行走荆江的部分记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荆江世界就是依赖桩号和水位获得解释的世界”[1],上百里洲的大堤与沙市观音矶的水位即是诗人村居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呈现出浓厚的土地依恋与乡土情结。
一、村居记忆:“精神游子”的复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具备村居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在贫穷而落寞的乡村,很多青年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和崇拜产生了图腾式的信仰。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商品价值体系的确立,搭乘“恢复高考”的春风进城的“知识青年”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坚力量。物质文明逐渐吞噬精神理想,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却在撕扯着中国大地上奔流了千年的淳朴情思,这批在思想上仍旧游弋不出“乡土情结”的“精神游子”即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还乡”态势。
首先,“村居记忆”体现在对故乡山水的“精神复归”。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精神游子”,有学者认为诗人在《桩号73》的创作中深度介入了“极其强烈的记忆标识成分以及相应的空间遭际和地方性知识”[2],这些记忆标识的烙印源自诗人的荆江村居记忆,更准确地说,来源于“清澈的溪水”“溪水边的稻田”以及稻田里的童年。诗人热爱那方洋溢着泥土气息与麦穗香气的村庄,“布谷鸟叫的是‘播种割谷’/它是队长/一遍又一遍下达出工的通知”(《桩号73+003》),存在于诗人的村居记忆中的“播种割谷”是贴近大地最灵动的方式,城市文明的发展始终不能填补诗人内心的稻穗谷麦情怀,还加重了城市“异乡人”漂泊零落的情感体认。当灵与肉注定分离,灵魂只能依附于空旷的城市,精神便依托诗歌回到故乡的大堤,回到本源之地。
其次,“村居记忆”体现在对淳朴情结的留守皈依。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外来者入城,精神文明的虚无感在物质文明的横冲直撞下显得异常孤独,都市的生存压力和无根浮萍式的精神世界让诗人产生了对城市文明的抵抗,“城里人不需要知道如何辨别蛇洞与黄鳝洞/在你们看来黄鳝与蛇可能是兄弟/韭菜和麦子可能是姐妹/你们需要用尽心思/辨别不同楼栋”(《桩号73+013》),“楼栋”作为象征着“城市文明”的符号价值与“麦子”象征着的乡村文明产生着现实冲击波,城里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对大自然的生息状态与体貌样式一无所知,被城市异化的人们将自己圈存在巴黎“拱廊街”[3]上享受着邻里不识的“惊颤”,诗人以“村居记忆”来抵制物欲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入侵,随之批判城市文明中的声色犬马对人的本质的摧残,也传递出“异乡人”居于城市的精神孤独。物质的丰盈并没有改变诗人对精神充裕的追求,在诗作的表达上,诗人极力抵制城市的物欲横流,企望能够留住自己作为“农村人”的淳朴情结。
灵魂盘旋在故乡的上空,肉体穿梭于城市的霓虹街景,灵与肉的剥离使诗人成为徘徊在城市与村庄的“精神游子”。“左边有沟渠/渠上有一座小桥/桥下有三个蛇洞/桥中间嵌一颗五角星”(《桩号73+007》),故乡的原始记忆是难以磨灭的,“村庄记忆”作为“60后诗群”的集体无意识存在绝非大地之上的农人聚集地,而是承载着一代人成长的“精神故乡”。因此,“村庄”在诗人笔下绝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名词,而是思想生发的源泉与着力点,是诗人感怀精神桃源的寄托之地。这批来自乡村的诗人表现出浓厚的土地意识与乡土情结,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4]。忙碌的城市文明川流不息无法安放灵魂,诗人在精神和情感上对乡土有强烈的皈依感,既定的村庄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判断在疏离与缥缈的物质文明中遭遇了心理上的挫败,肉体无法还乡与故土接壤,“收割机把河滩的布谷声/运回家乡/我也回到了南河”(《桩号73+054》),精神的游移复归村庄,一定程度上能够慰藉城市文明进程中诗人心灵的孤独与空虚,因此,“村庄”和“河流”成为他诗情和诗思的生长点。
二、民族立场:“文化阵地”的坚守
90年代末,京郊盘峰宾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诗界论争,由此分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不同理论和创作倾向的文化价值立场。一派是以西川、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群体,其具备较强理论自觉,延续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诗风历史;另一派是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主张“民间写作”的诗人群体,其更多沿袭了“第三代”诗人对诗歌的“日常化”和“口语化”的艺术追求,一反朦胧诗的晦涩、沉重,用诗歌的语言解构了政治权利和人生。民间写作阵营对知识分子写作倾向相当不满,认为其“唯西方诗歌为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西方大师们鹦鹉学舌的殖民地垃圾文本”[5]。而王家新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置身于更大文化语境而又始终关心中国、关心我们自身现实和命运的写作,也是一种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显示出深刻历史意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写作”[6]。但正如学者魏天无所言:“我们虽然不应该低估知识分子写作对当代诗坛的贡献,但是也要正视其写作中存在的普遍借重西方资源的问题。”[7]
文联作协语境成长起来的李鲁平兼具诗人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具备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理路。其诗歌既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表现方法,以此形成知识分子写作的沿袭,又融合“民间写作”结合时代、联系群众、扎根生活的典型特征,形成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两相勾连的民族立场话语蕴藉模式。
首先,《桩号73》在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方面坚守民族立场。诗中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展现出诗人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与进取的入世情怀,“这些朴实的刀听得见孩子的热泪/滴落在草丛/照得见老人的/清汤寡水和单薄的冬天/那时/很多沾满水泥和砂浆的刀/就劈出上学的路/也砌出故乡温暖的灶膛”(《桩号73+006》),诗人规避了高屋建瓴式的“高阁”写作,转而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诗人将社会问题与现实状况结合来谈,真正亲近大地,将温暖的目光投注在弱势群体身上,揭露城乡文明发展进程中仍旧存在的物质生活匮乏与精神文明缺失的现象。但“往后不会有比过去更糟糕的天/乾下坎上/利涉大川”(《桩号 73+001》),诗人选用《易经》中的“乾下坎上”卦象来言明志向,传达出自身顺应天道、静待花开的澄明心境,但静待时机并非无所作为,“只有隼上天入地/刚健而不陷”(《桩号73+001》),化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凸显出诗人的进取精神与“诗言志”的文化价值功用。诗人还引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入诗,“一条河也有疑难杂症/医生赖晓平肯定有过如此的推理”(《桩号 73+097》),“赖晓平”是湖北监利县的乡村医生,为了保护地方民歌,他踏遍田间地头,成为保护“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代表。直接将民间非遗保护人引进诗歌,既凸显了诗歌的传统文化特色,同时更增强了诗作本身的文化包容性。
其次,《桩号73》在地域文化方面坚守民族立场。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8]引言中,把地理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诗歌的创作离不开诗人世代生活的自然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构成李鲁平诗歌的自然意象,而“水”成为《桩号73》诗集中独特的地理符号与诗歌文本结合。“东荆河从黄家口到新滩口一百公里/河床平均宽三四公里/最宽七公里”(《桩号73+060》),“西陵峡以下/无大山挺立/无猿猴哀鸣/也不生长石头”(《桩号73+069》),“往事留在荆山以北/一条河跟随楚人走到了长江边”(《桩号 73+072》),“十五条河流都看得见 /汉水/襄河/涢水/汉北河/泵站河/南支河/北支河/庙五河/军垦河/还有躲避人类/潜藏不露的义水 / 汊水”(《桩号 73+083》),“东荆河”位于长江中游下荆江以北、“西陵峡”位于楚之西塞和夷陵(宜昌古称)的西边、“荆山”位于湖北南漳县、“汉水”自西向东流入湖北省后在武汉注入长江等等,李鲁平将独属于故乡风土的水域地名作为对话与书写的客体对象,而诗人“我”作为主体,二者是分离状态,这种分离感是诗人“外来者”入城与家乡分离产生的乡愁带来的。深度进入诗人故乡之水的文化肌理,这些地域水名主要具备三种用处:一为“凌晨三点的长江,夜航的水手见过没有”(《桩号73+008》)的交通运输之用;二为“通顺河没有峡谷、峭壁、瀑布……稻子、鱼虾、油菜、棉花都在它的流程内”(《桩号73+020》)的农业灌溉之用;三为“我把河流写成了坏人,我该告诉你如果它不能作为坏人,我还能写谁”(《桩号73+048》)的创作意象之用。诗人故乡之水融通四海,且诗所涵盖的空间遭际暗含厚重的历史意识,既囊括了地理区域本身的人文历史,也是诗人自身生命体验的诠释与见证,是地域文化与文学的深度结合,展示出荆楚文化极具特色的艺术张力。
总体来说,《桩号73》的“知识分子写作”既未落入西方资源的文化附庸的窠臼,也未落入平庸的日常生活情绪的宣泄陷阱,而是在坚守本民族文化阵地的立场中,实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文化突围。诗人试图以个人存在经验运用知识考古学,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观照,对居住地的地域文化进行融合,试图打破“知识分子写作”对西方文化汲取与运筹的壁垒,改变原先“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从而形成平行与互文的关系,以此坚定民族文化的独立精神并重建民族精神的时代信仰,这也体现出诗人李鲁平探求如何将“地方经验书写”最终形成“中国经验书写”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
三、体验叙事:“中年写作”的突围
近年来,对诗歌叙事性的讨论日益增多,有学者认为,叙事使诗歌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变成了对现实的描摹。“……人生活的世界上,面对着吃喝拉撒睡,面对着美与丑、爱与恶、生与死,经验当然是庞杂的。而庞杂兼有活力和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叙事”的选择实际上迎接了更大的挑战,包括对甄别能力和指责的挑战。”[9]叙事性的形成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改革主导下的九十年代的商业语境高压密不可分,诗歌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语症”,诗人面临三种境况:要么孤立写作跃入“无人之境”,再也不出现于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要么直接放弃写作另谋他路,或者重建新式诗语言说方式,恢复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因此诗歌的叙事性应运而生。诗人在创作中采用体验叙事的策略,以此来实现对“中年写作”情感表达的突围。
首先,诗人在《桩号73》中尝试口语化的日常叙事表达策略。“爷爷驾船我驾船/父亲打鱼我打鱼……我比他们走得远/下荆江有我的码头”(《桩号73+037》),诗人改变原本诗歌洪流倾泻式的情感直抒,将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寓于诗歌当中,展现出浓厚的宗族意识与细腻情感,隐藏着传统文化中“子承父业”的技术传承与血脉延续的愿望。“上学经过排灌站/我一定要认墙上的字/农业学大寨/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少生孩子多种树/……每天都读一遍/这面墙/就是一面挂在天空下的黑板/用最少的字告诉坝洲/南河与大海其实连在一起”(《桩号 73+011》),“这面墙”见证了诗人的成长过程,也见证了国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农业发展与人口基数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挂在天空下的黑板”告诉诗人答案:百川东到海,莫说行路难。诗人将自身的读书体验、思想精神融入社会问题、民生苦难的当代语境阐释中,表明科学的理论能够解决国家的大问题,知识的精进也能解决个人的小问题。为适应时代变迁,诗人尝试新型诗的言说方式,反省个人化写作经验,在诗歌现实语境锤炼下,诗人逐渐进入“中年写作”,笔法愈趋成熟稳重、冷静克制,扭结生活阅历与现实态度,形成“进场写作”的独特体验叙事。
其次,诗人在《桩号73》的创作中力图进行克制式的亲历写作。当叙事性上升为一种诗学观念,突破“亚叙事”的藩篱,诗人则被要求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从现实中遴选材料,使语言与具体事物相联系。诗人选取不同类型的河流来阐释自身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思索,“我见过横不讲理的大河/见过世事洞明的细流/有的河粗犷/裹一身泥沙/有的河曼妙/沿途抖袖/云手/有的河不走直路/有的从不拐弯……但只有一条河无法穿渡/只有一条河看得见生死沉浮/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命本如何”(《桩号73+24》),诗人在现实语境中选择不同类型的“河流”意象来对应不同的人生经历,凭借人生阅历来洞察每一种类型的“河流”(人)会经历怎样的状态(人生),阐释了不同河流(人)的生命状态与自然规律。在谈到河流穿渡的问题时,诗人坦白每一种河流的自然生命状态自己都是热爱的,但只有一条看得见“生死沉浮”的河流无法穿渡,这也是流向“死亡”的“宿命之河”。“不是心甘情愿”体现出诗人对“生”的强烈愿望,“命本如此”则呈现出诗人坦然面对生死的豁达心境,也透露出对生死的无力之感。诗人希望在诗作中以亲历写作的独特视角呈现出诗情本身的张力,但语言表达上更多倾向克制与隐喻,这与诗人的创作基准进入“中年写作”有莫大联系。
“正如新诗本身承担着传承时代命题的重任,诗人的成长往往有其特有的时代印记。”[10]《桩号73》里众多诗歌采用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进场写作,以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与个人化情感的表达来铺陈个人生命的历史浮沉以此建构自我诗学体系,这既避开了强烈直泄式的主观情感偏执,又规避了抒情过滥,从而凸显如艾略特所说的“新情感”[11]范式,即与中年写作观念相对应的“中年情感”,一种成熟了的情感,少了冲动、宣泄、直截了当,多了克制、舒缓、气定神闲。“中年写作”自此在诗人笔下实现诗学建构的突围,即“中年写作”并非“年龄写作”,进入中年并不等于老态龙钟,而是一种“心态写作”,以此导引诗人的笔风自青春、跳脱走向成熟、稳健。正如诗人与周新民对谈中所提到阅读“赵红梅、戴茂堂《文艺伦理论纲》里谈到道德,涉及到卢梭‘回归自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12],从自我的成长与他人的遗憾里来感知一切“逝去”的情怀,从“过年——团聚——离世——追忆”来自我反思归乡与反哺的诗性自然精神,以此达到超脱于世、回归自然的审美理趣。
《桩号73》以“60后”诗人群的“村居记忆”为书写底色,力图塑造工业时代背景下“精神游子”渴望复归的“乡村晚景”,以此来抵制物欲文明肆虐而导致的精神荒芜、心灵漂浮之感。《桩号73》以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特色地域文化为创作旨归,重塑民族诗学的文化自信,形成地域文学书写经验,建构起既具备阳春白雪式的“牧歌之诗”,也具备下里巴人式的“现实之叹”,打破传统“知识分子写作”崇尚西方经验的思维桎梏,实现了以民族立场为根基的“文化阵地”的坚守。下沉乡土大地,俯身人民群众,以进场写作的方式体验人间冷暖,是“中年写作”之体验叙事的一次战略性尝试,诗人关注到个人与国家的发展、生命进程的方式流向、死亡意识的豁达与无奈等问题,既为诗歌叙事性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视化的试验文本,也发挥了诗歌反思现实的功用。
注释:
[1]李鲁平:《桩号73·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2]霍俊明:《“上百里洲”,精神“桩号”与命运标识物》,《长江丛刊》,2022年3月。
[3]【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0页。
[4]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著:《人,诗意地栖居》,郜元宝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
[5]沈奇:《秋后算帐——中国诗坛备忘录》,《诗探索》,1999年第1辑,第24页。
[6]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诗探索》,1999年第4期。
[7]参见魏天无:《九十年代诗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版。
[8]Hippolyte Adolphe Taine: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THE GEBBIE PUBLISHING/CHATTO&WINDUS,1897.
[9]孙文波:《我理解的九十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 2期。
[10]肖敏:《日常化写作的纵深与“风景的发现”——论李强诗歌的抒情构成》,《江汉学术》2017年,第57—61页。
[11]【英】T·S·艾略特:《叶芝》,王思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66页。
[12]周新民,李鲁平:《并非专业的职业生活——李鲁平访谈录》,《文学界(专辑版)》,2013年,第 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