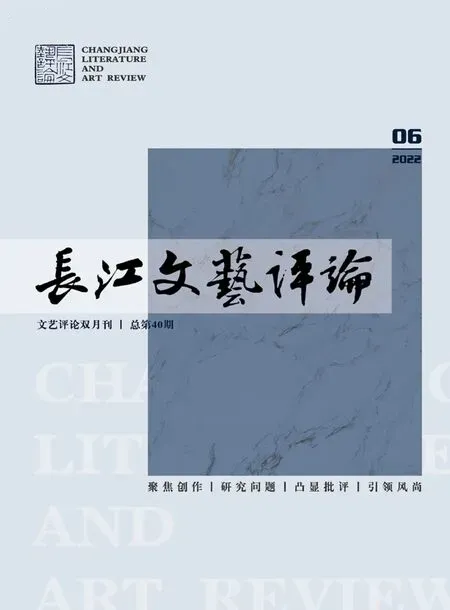“三生三世”的凝望
——读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
◆肖博瑶
早于国内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沈从文热”,1972年,纽约传文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将之纳入“世界作家系列”的一种,详细介绍了沈从文的生平和作品。聂华苓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以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文学语言的深刻领悟与深深共鸣,试图解读沈从文作品中的深层意蕴与审美价值,“旨在帮助西方读者了解这位现代中国文学大师”。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沈从文的评传,有着与其他传记不同的文学视野和不一样的艺术魅力。时隔五十年后的2022年,恰逢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刘玉杰翻译的《沈从文评传》中译本,意义十分特别。
一、创作理念和阅读期待的投射
作为一名小说家,在《沈从文评传》中,聂华苓试图从现代小说家创作的角度去理解沈从文,她从“为什么沈从文的作品是艺术品”的角度出发,运用象征主义理论,对沈作从现代化主题、风格和意象上进行分析。
在《沈从文评传》前言中,聂华苓对沈从文甚为欣赏,认为沈从文的写作是“通过描述中国的男女老幼,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在中国曾有和一直将有的生存状态”,是“切身而真实”“抒情而又生动”的描写,这也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独特的贡献”。在聂华苓看来,“真实”“抒情”“生动”是沈从文小说具有现代文学价值的关键词,正是这些贡献将沈从文推向了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前沿。同为作家,在聂华苓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对以上特征的追求,和沈从文相似的文学理念、创作旨趣使她在评传中不由得代入更多自身创作的经验和情感,表露出她对沈从文的崇拜和惺惺相惜之情。
如她所说,台湾时期的“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1]。在一次她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中,比德·乃才瑞士提到《珊珊,你在哪儿?》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她补充道:“也是一篇浪漫的小说。”[2]这一时期聂华苓在艺术表现上基本是从个人经历出发,真实地再现生活。在美国定居后不久出版的《桑青与桃红》中大量采用了现代派的创作手法,试图“融合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戏剧手法、诗的手法和寓言手法”来追求“客观的真实”,不甘于只作外部世界的再现,而力求写出她主观感知的“真实”——世界、国家直至个人内心的“分裂”。结合两个时期的创作可见,聂华苓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创作经验,以及追求真实的生动、意向的表达的文学思考都潜移默化体现在《沈从文评传》中,作为阅读期待投射在她评价的“抒情又生动”的沈从文身上。
不同于其他沈从文传记侧重传主的生平以及作品创作记录,《沈从文评传》拒绝简单停留在分析沈从文的小说故事表层,而是着力挖掘沈从文小说的象征层面,旨在阐发沈从文的“言外之意”。聂华苓重点关注了沈从文小说中运用的意象和象征手法,视沈为一位有敏锐洞察力的“象征主义者”。王德威也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有“抽象的抒情价值”[3],这与聂华苓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总能散发出一种象征性的五光十色的效果”相似,他们都强调了沈作的象征性和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是“一位意象派、讽刺的结构主义者”,聂华苓则更加重视沈的现代性小说家身份。聂华苓和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都企图用“两个世界”的塑造来展开对人性的表现和探索,评传中评价沈作“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达象征的意义”也鲜明显示了聂华苓的创作倾向和自身阅读期待的投射。当带着自己的阅读期待去解读自己喜爱的作家时,自然就更易于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特别是对于文学的多重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理解投射到作家身上,不同的期待视野,也就导致了作者不同的阅读选择、重点和效果。
《沈从文评传》中聂华苓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带有鲜明的创作旨趣偏好。如聂华苓高度评价了沈从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认为这是他“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它有好几个方面高超绝伦:紧凑的结构、成功的人物塑造、内在有机的象征和不可侵犯的主题”,这同时也对应了聂华苓创作中所追求的理想小说样式。可见,聂华苓作为小说家的创作理念与她对沈从文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不无关系。沈从文在《短篇小说》中谈到他认为的小说“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4]。同为小说家,聂华苓从沈作中读到了创作旨趣上的深深共鸣和阅读期待上的契合,也正因此,聂华苓对沈从文才有“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之一”这样的高度评价。
二、“边缘人”和“旁边者”的共鸣
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在城乡之间矛盾徘徊着的边缘人、旁观者[5]。“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是沈从文对自身文学以及思想的边缘地位的确认,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五四”以降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思想文化而言的。一个处于现代知识分子边缘的、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边缘的位置和对此的自觉意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观照现代文学,使他从结构、环境、抒情、意象各个方面对现代文学进行“乡下人”式的独特审视。
虽然沈从文一再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但他在精神上与真正的乡下人是无法融合的,就如《沈从文评传》中聂华苓所说到的,“乡下人是文明发展产物下的孤独的杂种,夹在进步和被动的文化枷锁之间。”不同于夏志清从文化伦理的保守主义解读,或金介甫以历史学和人类社会学的方式力图廓清“乡下人”的内蕴,也不同于凌宇试图从个性情感心理、气质的角度深入“乡下人”角色之中,聂华苓在《沈从文评传》中从象征主义角度,聚焦于沈从文的“乡下人”书写,以期寻找“乡下人”背后的暗示和神秘性,这样的理解与她自身的边缘人经历和旁观者角度无不关系。聂华苓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作家的代表,她的一生离不开一个“外”字,在其自传《三生影像》的自序中写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6]。在她自己看来,她有三辈子,三辈子都在逃亡。在《个人创作与世界文学》这篇文章里,她说:“我流亡了三辈子。军阀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7]可见,“三辈子”的流亡使聂华苓深刻体会身在边缘的无奈,但无论处在哪个时期她都坚持着关注个体生命和捍卫文学尊严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这也使她的评传中对沈从文其人终其一生自称“乡下人”、其作“背后隐伏的悲痛”,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上的认同与共鸣。
聂华苓在《沈从文评传》中把“乡下人”理解为“孤独”而“荒谬”的“边缘人”,并将沈从文的“乡下人”与加缪笔下的“陌生人”进行对读,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归根结底都是“荒谬”的,“都是被疏远者,对生活都无多求——除了死亡”。并且聂在自由主义文学观和象征主义文学观的视野之下,认为沈作更近于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而非现实主义,进而判断沈作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便在于其揭示出这些“乡下人”的蒙昧不觉与荒谬不经,能充分认识到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也是《沈从文评传》的价值所在。
沈从文把自己称为“人性的治疗者”[8],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主张重视艺术、着重于文艺本身的探讨,做与社会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旁观者”。40年代之后,沈从文的政治怀疑论和文学自由主义倾向,终于将他推到一种孤立的境地。“乡下人”形象的根源是作家本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渴求,从成年后独在异乡毫无依靠的“异己感”“陌生感”和“一切与己无关”[9]的感受,到成名后又因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不同而与挚友、与文学决裂的痛苦,其文字“背后的隐痛”都是现实中的压抑和痛苦的心理记忆转化而成,是心灵受伤后的痛楚和坚守文学自由的孤独交织而成。
同样,聂华苓的自由主义文学主张——从人性出发,认为自由是人性最根本的需求,从她在台湾做《自由中国》主编时就有所表露。文学主张和生命体验相类似,由此产生的精神渴求与文学创作也有相通之处。在文学立场上,聂华苓始终保持着对主流叙事的疏离性、对政治中心的疏离性及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追求,始终站在边缘话语的一端,以边缘视角审视中心,表现出追寻自由的终极性美学目标。
作为“边缘人”和“旁观者”的共鸣,聂华苓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有着与沈从文相似的边缘人物和情感。在沈的文字中,他一直在都市与乡村,原始与文明的矛盾之间游走着,多以水手、船夫、火夫、杂役、妓女等平凡人为他作品中的主角,聂华苓将其概括为“贴地的人和水上的人”,认为沈作的独特视野和他独有的天分完美地匹配,展现出了“乡下人”所具有的人类心灵的原始无辜、淳朴善良,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例如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柏子》,在沈从文的妙笔之下,“闪耀出他包罗万象的人道主义光芒”。聂华苓在评传中指出沈从文从来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乡下人”进行评判,而是作为一个受过文明洗礼的局外人对自然与人性有一种怜悯和思索。与沈作类似,聂华苓的边缘化写作并不立足于指责道德破产者,而是有意将这些边缘人物从道德责任的框架中释放,把人作为高于一切衡量标准的标准,通过创作中的“边缘人”来体现她对“人”“女性”“自由”命题的思考,对国家、战争、文化、民族道德的质疑与反思。如《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等作品中,聂华苓刻画了婚外情、乱伦的禁忌之爱、冷淡的母女关系、现代人道德滑坡的救赎,这都体现出作者对传统伦理规范的思考和反抗以及人道主义关怀的旨归。
沈从文的边缘人物多以“贴地的人和水上的人”为主,聂华苓的边缘人物多以政治避难者或是开除国籍者、流放国外者、移民等等少数族裔为主,但他们都试图通过对这些边缘人物的意象化书写,营造一个现实之外的“寓言”世界,用“两个世界”来展现人性、探索人性。正是采取立足边缘的自由主义文学视角,在《沈从文评传》中,聂华苓才能关注到沈从文小说中简单对称面的意义深度,判断沈所创造的“乡下人”形象预示着文学中现代异化人的出现,言近而旨远。
三、小结
《沈从文评论》不仅介绍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还从文学与创作的角度论述了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沈从文是聂华苓最佩服的小说家,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都是她仰望的天空,所以该著中时常流露出:她自己作为作家,对沈从文的生命孤独体验的知己之感,对沈作的阅读期待视野的潜意识投射。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在《中国时报》上评价沈从文:“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从40年代因文学创作与主流不符合而受到排挤后,接下来的近40年时间里,敏感的沈从文小心规避着跟文学之间的任何联系,以至“站在文学消亡的边缘”销声匿迹。对此,聂华苓痛惜地说“他的自我克制证实了鲁迅的话:‘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想不到也可以指挥文人’”,流露出对沈从文“后半生精神上过着流亡的孤独生活”的怅然之情。
临终前,沈从文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10]但他年轻时在“窄而霉”斋里,一边擦着鼻血,一边不分昼夜地奋力书写对世界无尽的喜爱,忧伤的文字在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文字“凝聚成为源潭,平铺成为湖泊”,为无数后辈小说家提供养分和启发,亦如聂华苓。
这本五十年前发行的英文版的《沈从文评传》,在时空的转迁里,恰逢沈从文诞辰120周年时在国内翻译出版,堪作告慰。
注释:
[1]参见聂华苓:《台湾轶事·序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李恺玲,谌宗恕主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3]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8页。
[4]沈从文:《文学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页。
[5]张森:《沈从文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31页。
[6]聂华苓:《三生影像·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7]参见聂华苓:《三生影像(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78页。
[8]沈从文:《给某教授》,载《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9]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10]丁东,谢泳:《文化十日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