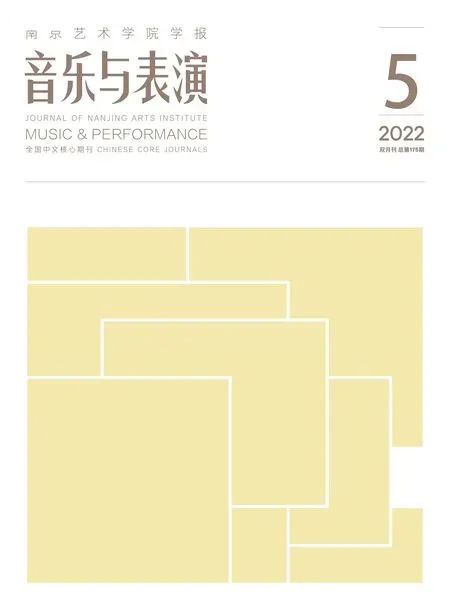舞蹈影像创作中的“隐秀”之美①
许 薇(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夏 静(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1]6,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刘勰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隐秀”特征。至此之后,“隐秀”这一范畴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黄侃认为:“故知妙合自然,则隐秀之美易致。”[2]傅庚生觉得:“‘水光潋滟’是秀美的模样,‘山色空蒙’是隐美的模样。”[3]当代的叶朗把“隐秀”作为刘勰提出的最具特色的美学范畴之一进行分析:“刘勰对审美意象的分析,首先表现在他提出的‘隐秀’这一组范畴。”[4]作为一个蕴含多重审美内涵的理论资源,“隐秀”中涉及到“意”“象”关系的多个话题,因此它虽源自文论,但同样也适用于其它艺术领域。并且因为时代与文化语境的变化,隐秀一词的理解与含义指涉也在不断地丰富与革新。
近年来,随着视觉文化的崛起以及占据热点的跨界创作意识的影响,舞蹈影像作为舞蹈艺术与影像数字媒体跨界融合的创生性产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作为特定语境催生下逐步选择的结果,当代中国舞蹈影像的创作在舞蹈语言的选择使用和视觉画面的建构呈现方面,相比传统舞蹈,更加关注“情感表现性”中的“观念性情感表达”,在扬弃了时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基础上,以“情在词外”和“状溢目前”的诗性表达,呈现出时空写意与形态写实、精微之舞与广大之势相辅相成的隐秀之美。本文以传统美学中的“隐秀”讨论当代新兴的舞蹈影像创作,分析以“隐秀”为中心的“复意”“卓绝”“共生”等艺术问题,这既是一次跨界视域下针对实践问题的理论阐释,也是一次在现代语境下重温中国艺术的美学诉求、寻找当代艺术民族精神基点的思想旅程。
一、隐美:以复意为工,写意现实
关于“隐”,刘勰给出的定义是“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5]387,并且“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5]387。可见,“隐”的特征产生于文辞之外,是审美意象所蕴涵的深层思想感情内容,而非依靠逻辑判断的形式。之后钟嵘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6]唐代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7]也是这个意思。在文学语境中,“情”和“义”是“隐”的内容,即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意向;“词”与“文”是“隐”的载体,即作品所呈现出的语言形式,包括艺术形象。作者的思想情感应存在于复杂的、丰富的审美意象之中,需要读者在品读的过程中细细体味,不断琢磨。刘勰笔下的“隐”不仅意在说明文章需要有含蓄内敛的深意,其深意更需要有“文外之重旨”,即“义生言外”。这种“义生言外”不仅仅只有文章语言本身之外的含义,更以复意为工。
在创作方面,舞蹈影像与文学有着相似的“基因”,通过创造“意象”表达情思,促发观者或读者的想象,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于舞蹈影像而言,“隐”的内容是创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意识;“隐”的载体主要包括舞者的身体语言以及人、物、山、水、事、景等情景性语言。身体语言与情景性语言共同构成了舞蹈影像的视觉形象。有别于传统舞蹈对于“动作”的过分依赖,舞蹈影像的艺术语言存在于新媒体技术对于时空环境的深度挖掘。这个时空环境既包含自然环境,也涵盖了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场境,还包括了意象时空。这种包含了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专属的质感和气息,以及特定人物生活经历、心灵感悟和思想意识等多重组合因素的特定意象的时空环境,不仅构成了舞蹈影像的呈现方式,也是舞蹈影像艺术语言存在和生发的一种方式。《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5]249刘勰把“意象”看作是“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是情思与形象的交融,意象的存在为艺术家营造一个丰姿多彩的艺术世界提供了可能。当舞蹈影像中的身体语言与时空环境建立起“形象—意象”的融合转换关系时,“自然之象”融入人的心意和情绪转化为“人为之形”,意象时空便可作为思维中介物,对作品中的人、事、物、景、动作等各种符号系统结构与形态进行整体完形,从而将内心过程转化为可观、可感、可知的具体影像作品形式。
意象不同于影像,也不同于形象。影像和形象作为具体的动态图像,具有“现成性”的特点,是舞蹈影像的结果性呈现;而意象是象外之象,是内在心象,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具有“非现成性”的特点。“意象是决定影像和形象的意义和深度的美的本体。由意象驱动而生成的动态影像,可以突破有限的‘象’,超越现实生活的‘实’,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然。”[8]因此,对于舞蹈影像创作而言,作为表现载体的影像呈现,并非舞蹈与影像的机械组接,也不是镜头和画面在蒙太奇技术层面上的拼接和凑合,而是舞蹈影像的核心意象在审美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结果,是艺术创作中诗性直觉中的灿然呈现。
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5]387这些是说审美意象的多义性特征。“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9]唐代刘禹锡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由于意象本身不是知觉刺激的直接效应,而是在知觉基础之上经由记忆等机制而唤起的内心形象,因此“意象比图形具有更多的可塑性”[10]。例如舞蹈影像作品《颂》的一个片段。深夜,两位朝圣的僧人陷入沉睡。黑暗中两个如鬼面般的物体在他们的头部升起、漂浮,似乎在寻找什么。一簇熊熊燃烧着的篝火变得忽大忽小,火苗渐渐地越来越弱,越来越小,最终完全熄灭。紧接着在天亮的画面中,只有一位僧人继续前行,而另一位僧人的面容以虚幻穿插的方式如影随形。对于影像的欣赏者而言,创作者只是为他理解作品所包含的言外之意提供了一定的线索。鬼面与篝火、黑暗与光明、死神与生命、虚境与实境,创作者在状物叙事的同时留出充分自由的遐想空间,将超出言内之意的生命感悟包含于“人逝灯灭”的舞蹈意象之中。作品之“隐”,意味着表层语言的所指(言内之意)——“灯火熄灭,生命在悲凉、痛苦与执着的复杂情感中终结”也变成了能指——成为另一层次所指(言外之意)——“于虔诚而淳朴的朝圣者而言,朝圣无关时光、无关生死,是通往心灵的道路,亦是对信仰绝对的尊重与膜拜”的载体。复义性特征赋予了作品含蓄深沉的审美内涵。
“隐”中所包含的含蓄和深沉,使得舞蹈影像的艺术语言类似诗歌,更多地会以创作者“自我化”的写意方式来表达对于复杂世界的独白式或内在化的回应。它凝聚了创作主体对于现象的本质性把握,注重的是心灵和情感的体验。传统舞蹈一直以同一空间和连续时间的表达作为主要表现手法,以线性模式为基础,强调作品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舞蹈影像的创造思维依托的是数字化、影像化的全媒体时代环境以及后现代的艺术思潮,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由动态意象组成多元时空的造境活动。创作者通过蒙太奇的电影拍摄手法和意象碎片的拼贴与重组,以主体的视界为出发点,超越时空局限,让情感意象以点状散射的方式委婉地流动在每一个画面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5]390深刻的作品包含着内在的美,味外之味要在曲折迂回中体现,潜藏的文采要在无影无形中生发。在一部舞蹈影像作品中,不断流动变化的意象作为多元时空建构的某个角度或某个层次,在服从整体意境营造的同时,作为虚线进行整合串联,若隐若现,若虚若实,正如清末刘熙载所言:“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11]意象的变动特性使得它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流动状态。舞蹈影像作品《唐宫夜宴》中,博物馆中的国宝文物勾勒神秘玄妙的氛围、仕女穿行嬉戏的动作场景展现乐俑活化的想象;水边整装弄姿的场景配合中国水墨的肃穆;金鱼飞空装饰下的皇宫与仕女呈现恢宏大气的盛唐景象,四个意象场景通过创作者的主体性选择和裁剪,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逻辑性进行游移转换,以此建构符合特定情感、意义和观念的艺术表达语境。《唐宫夜宴》用短短5分多钟,从文物、画卷、汉唐舞姿等多种文化符号,在完成传统文化当代重塑的同时,通过多条意象为线索触动欣赏者的主体经验产生审美共情,进而建构跨越标签的民族记忆和国家认同。
“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12]意象的暗示取代了一目了然的叙说和抒发,意象的流动与派生取代了平面拼凑的说明和证实,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同一性因主体“自我化”的时空重构,进入“自由化”和“个性化”的意境范畴。舞蹈影像的余味也因“曲包”而更加隽永蕴藉、令人寻味。
二、秀美:以卓绝为巧,雕饰天然
关于“秀”,刘勰说:“状溢目前曰秀。”[1]6又说:“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5]387之后,清代的冯班《钝吟杂录》又做了补充:“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13]较“隐”而言,“秀”是具体且外露的,是对作品外在形式的一种规定。刘勰提倡象之“秀”,是因为意象之“象”承担了帮助审美主体把握、感知、体验和接受艺术存在的重任,是意境之表征。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些不容易描写的景象,而且还要使人产生耳闻目见、亲临其境之感。所谓“秀以卓绝为巧”[5]387。如果说“隐”拥有的是含蓄深沉、委婉隐曲的特征,那么“秀”呈现的则是卓绝独拔、状溢目前的气质。它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超越常音的气象。
《为摄像机编舞的研究》是美国艺术家玛雅·德伦的一部经典之作,被称为“舞蹈影像创作最初的教科书范例”。在这部舞蹈影像作品中,德伦巧妙地利用摄像机的移动和后期剪辑以及回放、慢放和快进等镜头语言技术,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连接起来,充分传递舞者的动作质感和作品的审美意蕴。整部作品传递出一种诗意朦胧的美感。树木随着舞者舞动,舞者本身又融入树木枝叶中。透过摄影机可以看到舞台剧场难以看到的效果:特显镜头将微小的细节无限放大并且清晰地呈现,舞者的手、脸、脚部的细节延展了身体语言的表现张力;长镜头中舞者含胸弯腰,再次伸展的同时将左腿慢慢抬起,脚尖从左向右在空中划出弧线。当他开始落下动力腿时,镜头保持流畅和平稳,紧接其后的全景镜头表现大范围的身体运动和宽广的自然空间,有效地实现了夸大角色身体和周围环境的对比。除此之外,创作者还使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当镜头再次切换为近景特写时,舞者原本在树林环境中缓慢降落的左腿突然转换到在一个室内空间中完成。结尾部分,舞者在美术馆中旋转、起跳,双腿腾跃跨过天空,最终在树林中落地。两次剪辑完成的空间转换使作品画面获得了跨越时空的艺术效果。最后的跳跨动作被玛雅·德伦分解为包括身体特写、局部中景和全景成像在内的六个分镜头。作品在身体语言和镜头语言的对话中结束。
同样是使用摄影机,与通常所见歌舞片的视觉奇观和娱乐精神不同,舞蹈影像解构了舞蹈和镜头语言,是编舞家和电影技术之间真正的合作。摄像机不仅是拍摄者也是表演者,编舞家以镜头语言思维进行艺术创作。在时空观念、剪辑节奏和动作节点等多种手段的助力之下,舞蹈影像相比传统舞蹈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能量,包括更丰富的表现手段、更繁复的制作流程和更多元的媒介构成。这些都为实现“状溢目前”的独特之象、出众之象奠定了基础。
刘勰所言的“秀”是文学中的作品形式,既对应“句”的概念,也指向“篇”的范畴。就前者而言,体现在“篇章秀句”的“独拔”之美。让人“动心惊耳”的词句是一篇文章获得“逸响笙匏”审美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舞蹈影像作品中,与文学之“句”相应地是指镜头的概念,即镜头画面的鲜明生动性。舞蹈影像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将舞台编排好的舞蹈照搬上屏幕,也不是档案意义上将摄影作为全景式记录舞蹈的技术手段,它不仅需要考虑屏幕的大小、图像的质量、特效的运用、场景的变化、镜头的拉伸和摄影机的位置,还需要考虑摄影机的运动和剪辑所产生的效果。它是身体与镜头共同展开的“双重书写”,意味着所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镜头与身体、身体与环境、镜头与环境的视觉景观。拍摄近景和特写镜头,摄影机离演员很近,能够表现身体细节动作。当整个画面被一只手、一个臂膀或者一副后背运动产生的身体语言所占有时,肢体细节的表达张力在音乐、置景和色彩的渲染下被放大被强化。全景、远景镜头,摄影机离演员很远,适合表现身体大幅度的运动。画面中渺小的身体与宽广的环境能够产生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凸显肢体的整体运动与环境的关系。此外,慢动作的效果强化了动作质感和画面纹理,可以使舞蹈达到浪漫化的效果;而加速的剪辑能产生较强的节奏感,形成高速运动的感觉,通常用于象征时间的流逝。无生命的物体也可以通过这种放慢或者加速的手法达成任何期望值的运动速度。影像作品中,舞蹈语言中的形态、速度、运动路线和表达意图通过镜头和剪辑的处理完成表现形式的转换,最终形成生活动作、舞蹈动作与画面节奏动感契合无间的复合型视觉效果。需要确定的是,通过镜头处理的身体语言既不是动作的“现实”,也不是动作的“图像”,而是动作的“形象”。一般来说,自然物一旦转化为艺术形象,便意味着已融入艺术家的情感、经验和思想。这种打碎视觉现象既有的序列,构成特有的形象话语的处理方式,不但可以提升动作的视觉质感,而且可以作为情感媒介诱发联想的刺激,充分激发观看者自身的思维与情感活动,产生亲临其境之感。例如:现场表演中舞者只用一两秒即能完成的“大跳”,通过影像剪辑,可对舞者起跳双腿前后打开至180度的瞬间进行放慢处理,延长整个跳跃的过程,并且给予特写,从而引导观众记住这个震撼的瞬间。再如:通过运镜和剪接大量转切画格(frame),舞者肢体大胆而突然地扭开,然后放掉,交给重力,或仰头后坠,或俯身坠臂,再来,重复再来,以近乎无情的回环往复,流露真情。
关于“篇”的范畴,“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5]388是刘勰在《隐秀》篇的补文中所做的阐释。和前面所说的“秀句”不同,这是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秀”的审美理想。具有“秀”的特征的文章应整体表现出秀丽婉转的气象和鲜活生动的审美意象,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词句。在舞蹈影像的制作过程中,蒙太奇技术能够发挥出单个镜头所不具备的意境魅力,因此由“镜头组”所产生的意境相比单个镜头所产生的意象,更加具有丰富性和艺术张力。正如爱森斯坦所认为的:“一系列蒙太奇片段的蒙太奇组合,在意识中不是被解读为某一连串顺序的细节,而是被解读为一连串顺序的完整场景。而这些场景不是描绘出来的,而是在意识中形象地产生的。因为局部代表整体也是促使在意识中产生形象的手段。”[14]表面而言,描绘局部场景的单个镜头并不存在连续性或整体性,相互之间甚至缺乏必要的时空逻辑。但是当它们被置于特定的上下文中,通过蒙太奇手段进行巧妙组合和特殊拼贴,却可以构建出一系列关于整体的意象群,经过相互间的信息转换与传递,促使观众调动自己的内在想象去补足或者充实整体,从而更加生动、立体和个性化地展现作品意图。舞蹈影像作品《姜公》中,旋梯的挣扎、楼顶的争斗、原野的追逐、山坡的攀登、海浪的自由,五组镜头用一只纸飞机和一根钓鱼竿串联在一起,不是连续,而是以并列的方式作为意象的方法和元素,协同构建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表达意境。五组镜头单个来看并不具有特别含义,但当它们以相互平等的关系聚合在一起时,便可以形成一个充满意义的表述。空间、典故本身只是个引子,创作者的意图也不在叙事,而是着眼于一种思想表达或认知模式。创作者用现代化的表演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将镜头与镜头,镜头与其内部各个表现元素(造型、音响、构图等)加以强化、类比和凝练,借助意象与意象间的力场关系,强调意象的不断变动性和无限可能性,作品主旨的阐释权通过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交给观众。蒙太奇的运用使观众不仅能看到作品中的表现元素,更能体验到意象出现和集合所具有的活力的过程。
“摄影机的移动性以及动作的打断与继续,并不是在破坏戏剧的完整性,在此创造了一种跟戏剧同样引人入胜的完整性,但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完整性。”[15]镜头语言和蒙太奇思维的运用使舞蹈影像的艺术表达创造出完全不同于剧场舞蹈的完整性。身体的细节、局部的结构,抑或非舞蹈的视觉画面,被巧妙地排比、分解、并置,以全新的线索重新聚合成一个超越部分之合,且血脉流通的整体艺术形象。舞蹈影像因此拥有更加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量,内在的、虚幻的、抽象的主题,得以获得最生动的语言形式和最准确的媒介构成实现情感外化。舞蹈影像之“秀”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自然一时之中寓目同感”,舞蹈影像的表现意义因此将超越传统的局限而走向更广阔、更深层的境界。
三、隐秀之美:以互文为介,“意”“象”共生
《隐秀》开篇即言: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5]387在刘勰看来,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主体的思维与情感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它可能关联到久远的社会生活,独特的文化印记,甚至关联到人的潜意识。它所关联的内容越丰富,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越复杂,文本的创造性就会越突出,越充满活力。优秀的文本就像植物一样,只有潜藏地下的根扎得深,如枝叶般的文辞才能茂盛,而这个根就是深隐的情感。传统文本如此,作为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像亦是。为了建构“隐”“秀”并进,“意”“象”共生的艺术表达场域,舞蹈影像的创作者竭力在寻找独特的方式,开辟全新的视角,使自己的作品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以及情感生活产生呼应,为舞蹈语言的表达拓展更多的维度,为视觉影像的审美内涵开放更多的层次。2021年由河南卫视与B站合作的《舞千年》系列舞蹈影像在全国范围掀起前所未有的国风热潮。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影像作品原生于成熟的舞台经典剧目,舞蹈本体的编创与表演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另一方面在进行影像化再创造的过程中,创作主体选择从历史文化的记忆中提取影像叙事的载体,以文本间的互文性延伸、扩展和深化作品内涵,使其意义的生产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的容量。在《舞千年》系列作品中,例如《踏歌》对少女成年笄礼的呈现,《火》对原始生命起源的追溯,《相和歌》对七星盘鼓爱情故事的讲述,这些刻意加入的情节画面,为原作中抒情性的动作语言寻找到形象且准确的叙事基点。再如《秦王点兵》中引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简》中引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作为文化经典记忆的古诗词,为原作中抽象的表达内容提炼出较为具体的表意指向。影像的创作者根据自己的逻辑,将历史的文本与当代的表述进行嫁接与重构,在制造出全新视觉景观的同时,用饱含主体精神的反思性视角引发对于民族文化记忆的关联性体验。由此,舞蹈影像的意义生产被置入与它自身不可分割的更宽广更深入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
舞蹈影像产生的时代语境,以及自身视觉性、运动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属性特征,注定了它的意义生产必然呈现于一个诸种因素彼此并立的互文结构中。这种彼此并立的互文结构除了作品中出现的具体的人、事、物或景,还包括了主体经验、影像媒介、镜头语言、蒙太奇技术等。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把各种形式关系聚集在一个更加统一的式样之内,使这些关系在有意图的组合中,通过生发、变形、互补、置换等方式,从而产生“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5]387的艺术效果。通过含而不露的艺术表征,表达深广丰富的内容,即用卓绝独拔之“象”,去隐喻含蓄深沉之“意”,从而获得“意”“象”共生,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意”“象”之间的隐喻关系,是舞蹈影像完成表意实践的有效机制,也是舞蹈影像突破传统舞蹈时空,真正回归“情感关照”与“现实关照”,实现“隐秀”之美的最好表达。
舞蹈影像中隐喻表达的形成建立在互文结构的基础之上,它以两个及以上不同形象或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通过组合和聚合的方式完成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开拓影像文本之外的意义空间,形成多义、婉曲、含蓄的审美意趣。传统舞蹈中的隐喻通常是借助其他文本中的意义来挖掘舞蹈的本体导向,而舞蹈影像作为舞蹈艺术与影像技术的集合体,从身体到环境、从景深到蒙太奇,从叙事到风格,从细节到整个文本都是其隐喻表达赖以呈现的重要表现形式。使用隐喻手法能够促进对影像本体在内容与形式、文本与表达的关系上进行更多维度的创新思考。《舞千年》舞蹈影像系列中的《鱼戏》选自张继刚创作的舞蹈诗《侗寨人家》中的一个段落。原作以七名男舞者的手臂配合和身体连串动作的起起落落展现鱼儿在水中的灵动,并以此致敬侗族文化中的图腾美学。同名改编的舞蹈影像作品在保留了原作舞蹈本体形式的基础上,借助镜头语言的变化应用以及蒙太奇技术所产生的时空重组,彻底地将影像表达从原本舞台舞蹈的印象中抽离了出来,成为更加饱满和独立的存在。影像中,舞台环境被公交车厢、海边沙滩、现代建筑和海底幻境等实景或虚境所替代,创作者对组成影像空间的部分进行串联从而完成特殊喻意的传递;舞蹈语言的关注焦点由原先舞蹈形象的形成转变为舞蹈意象的构建,在打破时空的效果镜头中,肢体脉动的精微把握加之“意识流”的风格引入,使得身体语言最终成为推动隐喻含义传递的意象符号。场景、人物、动作及隐喻性动画这些反复出现的具有特殊含义暗示的具体表象经过整合,构成了超越影像本身的意境联想,为抽象的隐喻思维与现实所指之间搭建桥梁,从而完成意义的指代和隐喻内涵的传递。在多重媒介的协作与重构之下,舞蹈影像《鱼戏》以强烈的诗意感、空间感和置身感指向了《庄子·秋水》里的那句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创作者借助影像,隐喻着个人与社会、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暗含着对于当下生活的审视与反思。
舞蹈影像的创作因为隐喻手法的运用,表达效果更具“视觉和感知”的双重审美。在魔幻般的视觉景观下,它的镜头进入到被我们忽视的细节,使不可视变为可视,以有形的“秀”包揽无形的“隐”,在“意”“象”共生中让我们所处的现实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与更复杂的内涵。
结 语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足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6]梅尧臣的命题清楚地显示出“隐”“秀”这对范畴和“意”“象”的关系。可见,一切外在形式的组织和把握,为的是创造出一个个有着恒久的精神体验和生命体验的意象世界,也正是这种追求令舞蹈影像如愿以偿地成就了自己作为艺术语言的存在。舞蹈影像是技术和艺术携手,更是舞蹈创造走进精神境界的又一探索。影像的加入给舞蹈增加了一双打量现实的镜头的眼睛。以蒙太奇构建的影像语言系统,其真正的价值除了外在形式,更在于其中影像画面和身体语言所展开的对话,是否真正触及并整体性地把握到足以呈现本质真实的核心力量。中国艺术向来不重视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制和对表象的简单记录和模仿,它不用逻辑科学之眼,而是以诗性生命之眼观察世界。将中国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舞蹈影像的研究视阈,可以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助推动中国舞蹈影像的本土化建构的良性循环机制。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与媒介,舞蹈影像的创作更需立足于从中国民族文化和艺术中汲取养分,以自己独特的创作体系和美学话语在全球化时代担当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