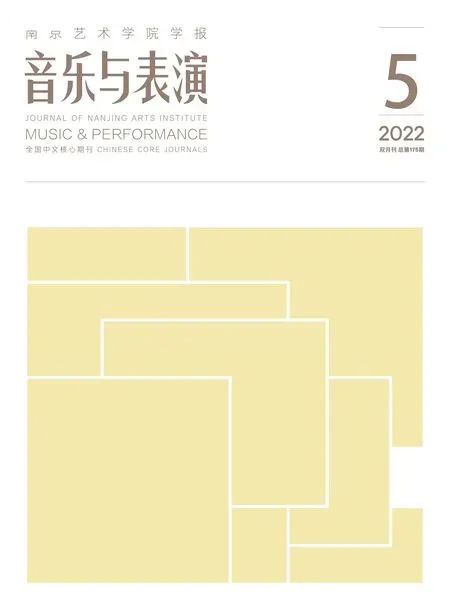民族音乐学“双视角”
—— 局内—局外、主位—客位
李纬霖(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袁海娇(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双视角”贯穿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每一个学术环节。纵观学术界以往研究文献,已有较多学者对“双视角”研究方法的介绍、运用、历史溯源、理论剖析、多学科视角等方面进行论述,鲜有学者将“双视角”理论方法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脉络进行论述,并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志(包括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实践进行分析。本文建立在学术界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研读,并结合民族音乐学中国实践的学科视角,以“双视角”“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为关键词,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第一,对“双视角”理论溯源进行论述;第二,对“双视角”国内外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第三,对“双视角”的中国实践进行论述;第四,对“双视角”的中国实践进行反思。
一、“双视角”理论溯源
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理论方法来自语言学领域,语言人类学学家派克(Pike Kenneth,1912—2000)在书写人类学民族志过程中,提出“局内—局外”理论方法,并在此理论基础上,研究语言现象与人的行为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主位—客位”理论方法。此后,两对研究理论方法广泛运用到人类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领域。
20世纪50年代,语言人类学家派克在描写人类民族志过程中,受思维方式、描写立场等学科理念影响,提出“局内—局外”(insider-outsider)理论方法[1],派克认为“局内人”指某种文化的内部持有者;“局外人”指该文化外部的观察者或研究者两种不同概念视角。可知,局内人与局外人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关系。
与此同时,派克在“局内—局外”理论基础上,借鉴语言学术语“phonemic”(音位学)和“phonetic”(语音学)提出主位—客位(emic-etic)理论方法。在语言学领域,语音学者(etic)研究发声和听觉系统的构造以及说话时如何作出反应,音位学者(emic)则研究哪些音差会影响交流的问题。所以,派克认为“主位”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承担者内部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它是内部的描写,亦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而“客位”则代表着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scientific observers),它代表着一种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认为“双视角”是指“局内—局外”文化身份和“主位—客位”学术立场;另一部分学者单指“局内—局外”文化身份或“主位—客位”学术立场。笔者认为,“双视角”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对关系以及各自持有的不同身份和观念立场。
除上述外,中国学者往往惯于将上述源于语言学的“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两对理论方法统称为“双视角”理论,而西方学术界并未有学者提及“双视角”一词。纵观中国学术界, 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在具体实践运用时,提出“双视角”一词。其中,沈恰指出“双视角”研究法全称是“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研究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应当从该音乐所处之文化的“内部”和“外部”这样两个视角去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对象,把握住对象的本质。杨民康描述“双视角”是民族学民族志暨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进入田野作业现场及其后进行案头分析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考察研究方法[2]。此外,王丹、王萍等学者的研究中也涉及“双视角”一词。[3]
综上可知,“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研究方法来源于语言学(“双视角”一词源于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其中“主位”是站在“局内人”文化身份视角对文化现象持有的观念立场,“客位”是站在“局外人”文化身份视角对文化现象持有的观念立场。此后,“双视角”研究理论在不同学科领域被广泛运用。
二、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研究发展历程
纵观学术界,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局内—局外”(insider-outsider)、“主位—客位”(emic-etic)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分别论述:第一,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学者以研究非欧“异文化”音乐为主,呈现“局外—客位”的研究特点。第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学者受两对方法论的影响,提出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理论观点,并运用于音乐记谱分析,呈现从“局外—客位”转向“局内—主位”的研究特点。第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者探讨两对方法论互为主体的平衡性研究,以及对两个处于对立关系的问题进行反思,呈现“局内—主位”与“局外—客位”相互融合,互为主体的研究特点。
(一)西方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研究发展历程
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为“比较音乐学”时期,此时民族音乐学以欧洲学者为主要学术阵营,以非欧“异文化”的音乐研究为主,以达到宏观认识的研究目的。这时期的民族音乐学体现出“局外—客位”的研究特点。例如,霍恩博斯特尔(E.M.Vonhornbostel,1877—1935)、 萨 克 斯(Curt Sachs,1881—1959)《乐器分类法》一文对世界乐器进行分类研究。埃利斯(A.J.Ellis,1814—1890)在《论各民族的音阶》[4]一文创造“音分标记法”对世界各国的不同音阶体系进行测试比较。上述研究呈现出“局外—客位”的研究视角特点,对民族音乐学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受人类学功能主义、整体论等理论影响,开始关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此时,西方民族音乐学呈现以“局内—主位”或以 “局内—主位”至“局外—客位”方法交相并行。通过研读文献,可知此阶段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双视角”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具体分析方法运用。如阿—佩莱耶尔(F.Alvarez-Pereyre)和阿罗姆(Simha Arom)从“客位”转向“主位”对记谱法进行探讨[5]。纳蒂埃(Nattier)继承阿罗姆记谱分析法提倡用耳朵作“客位”记录,来找出各类音程的分布[6]。梅里亚姆(Merriam,1923—1980)在实验室分析工作中,对怎样运用“局内—局外”观念提出“民间评价与分析评价”两种判断标准[7]。第二,学科理论建设。胡德(Hood,1918—2005)从“主位”学术立场对田野考察进行思考,提倡在田野考察现场,从耳、眼、手、嗓音等方面培养“双重音乐能力”[8]。同时,梅里亚姆在探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倡从“局内”视角对其研究对象的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并在不同时期提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音乐就是文化,音乐家的所作所为就是社会文化”[9]“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10]的学术观点,促使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的第一次转型,即宏观“客位”研究转向微观“主位”研究。
20世纪80年代至今,民族音乐学逐渐发展成熟,学科形成分层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向。学界对“局内—局外”“主位—客位”进行互为主体研究,同时进行学术反思和批评,呈现多元化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记谱的思考。埃林森(Ellingson,1992)探讨音乐记谱时提道:“对于许多民族音乐学家phonetic-phonemic进行的细节区分来说,他所用的‘宽’(broad)、‘狭’(narrow)的记谱概念是一种比较精确的标签。”[11]C.西格(Seeger,1886—1979)将不同的记谱方式归为“规定性”记谱和“描述性”记谱[12],内特尔(Nettl)将埃林森和C.西格的记谱方式以“主位”与“客位”进行了区分[13]。第二,从“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两极对立的关系走向相互转化、互为主体的平行系统研究。派克提出“局内—局外”理论后,指出应从局内至局外视角进行研究,并主张一个局外人应该去学习像一个局内人去行动。涅特尔把“主位—客位”形象比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可称作“人们的分析和人类学家的分析”[14]。玛丽娅·赫恩顿(Herndon,1941—1997)对“局内—局外”身份的关系描述是:“概念化的主位—客位二分,或完全局内人—完全局外人的连续体,都行不通,提出‘部分insiders’(部分outsider)的观点。”[15]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指出局内人与局外人并非简单的角色划分,而是体现着文化理解方式的不同,是从文化内部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还是从文化外部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其结论完全不同。对“主位—客位”研究体验时,山口修认为体验作为对象的音乐时,可以有Etic-Emic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6]。而对主位—客位持有的观念立场赖斯(Rice)则提出反思:“etic-emic”是“二元性”的还是“连续性”的?[17]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研究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通过山口修《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 等日本民族音乐学学者相关文献的介绍和引荐,中国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关注“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研究方法,并进行讨论、运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便直接翻译西方研究观念和方法的相关文献,介绍西方学界 “主位—客位”“局内—局外”的相关研究方法,使中国民族音乐学对此理论方法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以刘勇翻译的《音乐民族学和Emic-Etic问题》、戴薇翻译的《Etics和Emic——它们的起源和运用》[18]等文章较具代表性。
可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学者对“双视角”理论方法的初识和实践阶段。其中,沈恰是最早关注“双视角”理论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对中国云南省基诺族音乐进行实地考察时,就针对“局内”与“局外”辨识的标准,他指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此处尤指某种音乐文化)二者所处之人文系统(圈子)的关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人文“圈子”,那么,这个研究者就是所谓“局内人”;如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所属的人文“圈子”不同,那么,这个研究者就是“局外人”[19]。此外,韦慈朋(J.Law rence)从多个层面对“双视角”进行阐释,认为每一个研究者在某些方面是insider,在另一些方面是outsider:一个“文化的insider”存在于多种不同的层次(种族、语言、方言、国家、宗教、村落或其早期的近邻)[20]。洛秦对“主位—客位”理论的阐释,指出“客位”立场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或参照系来对某一或诸社会文化体系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涉及对分析者所建立的廷论体系的应用和发展。相反,“主位”的观念表达和阐述是“本地人”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模式,这种方式所强调的主观意识是被他所在的社会集团所分享的,并且所摘讨的文化上的特定模式是被这一集团的成员们所共同经历的[21]。可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对“双视角”的概念、理论已经做了充分、详细的论述与阐释,为后来的个案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21世纪初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学科多视角融合。越来越多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关注“双视角”研究方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学术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双视角”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沈恰《“融入”与“跳出”:民族音乐学之“道”——由“局内人”和“局外人”问题引出的思考》《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22]等文章提出“音乐文化的双视角关照看作民族音乐学基本方法学原理,对田野考察中局内人跳出和局外人融入的技巧提出方法论指导”。杨民康《民族音乐学“双视角”和“异文化”研究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意义》《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向》[23]等文献对“双视角”理论国内外发展进行详细阐述,认为Etic(或“远经验”)与本地人持有的Emic(或“近经验”)两者都不可能仅涉及单向的或一般的角色互补问题;而是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形成“螺旋形反馈”的和彼此平行、互为参照的双向(两极)考察系统。第二,学者进行具体研究个案,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仪式音乐研究、跨区域音乐研究、音乐民族志研究、教育教学工作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第三,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双视角”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其中,俞人豪结合自身研究体会,通过梳理中国传统音乐学者周吉先生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intersider”(局际人)的研究理念 。汤亚汀反思“主位”得来的知识应怎样赋予“客位”生命。张振涛提出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过程中怎样进行适度干预等问题。
可见,中国民族音乐学者从翻译日本学者文献开始引入“双视角”研究方法——直接翻译西方学术界“双视角”相关文献进行个案研究、理论阐释与反思,凸显出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在中国学术实践上,对“双视角”理论方法的积极探索和运用,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学者的“双视角”范式特色。
三、“双视角”研究的中国实践
“双视角”研究方法起源于西方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对该方法论进行翻译、讨论、阐释,并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在理论学习阶段,“双视角”理论方法是作为学习的重点内容,且需要运用到实际田野考察及案头写作中。若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历程来看,可用“双视角”的理论方法去观察和论述不同时期研究者身份特点及观念立场,从而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进行多维阐释,一方面,从“双视角”的角度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一)理论研究
沈恰是中国最早关注“双视角”方法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一文,从“双视角”本身全面阐述“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定位、区别,以及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应用及实践意义。之后,在《“融入”与“跳出”:民族音乐学之“道”——由“局内人”和“局外人”问题引出的思考》一文中,具体对研究者在实践中提出“融入”现场作用和“跳出”现场作比较的体验和技巧进行论述。同时,作者对“双视角”研究法运用到本学科进行深度思考与反思。
此后,学界对“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探讨成为热点,学者们不只是单纯研讨“局内—局外”文化身份的区别、“主位—客位”看法的差异,更是从不同层面探讨研究者考察过程中自觉转换的文化身份、观念立场、学科发展等方面进行反思。汤亚汀在《民族音乐学主位—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一文表述:“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获得主位以及客位(跨文化)知识。”[24]张伯瑜论述“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研究有三个层面,前者是人与音乐的关系、人与音乐的距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研究者作为客位;研究者作为主位—客位的结合;研究者作为自己。张振涛在《中国学人的身份定位与“局内、局外”观》[25]一文对研究者身兼的双重身份基础上,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是否要进行适度干预展开深度反思。
上述学者从共时层面对“双视角”本身属性进行研究和思考,杨民康《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向》和《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从共时性和历时性对“双视角”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综上,中国民族音乐学者从理论角度积极探讨“双视角”理论方法,体现出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中国学者对“双视角”理论概念的论述,呈现从对自身具有文化身份、观念立场的“点”研究到多重身份、身份转换、两者互补关系、互为主体、文化阐释等“多面”研究的特点。
(二)个案研究
除上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对“双视角”理论研究的中国实践进行论述外。可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学者的个案研究中,窥探出“双视角”的研究特点。笔者将文献进整理、归纳、研读,并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局外—客位”研究。第二,“局内—主位”。第三,“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研究。
1.“局外—客位”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汉族民间音乐研究主要呈现“局外—客位”视角。一方面,学者将中国和西方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如王光祈留学德国期间,撰写《东西乐制之研究》一文对中西乐制、调式、乐谱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为国内音乐的研究引入西方的研究方法,预达到振兴民族音乐,以振兴中华的目的。赴日留学的萧友梅撰写《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一文对中西乐谱、乐器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他将西方音乐研究的技术理论来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创新,开拓了国内音乐理论的研究范围,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变革进程。另一方面,学者致力于国内各地汉族民歌、器乐、民间音乐等进行收集研究。如冼星海撰写《民歌与新音乐》一文,广泛收集国内各地民歌,并把收集到的民歌资料分类研究,为建立中国新音乐的音乐创作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吕骥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首次将中国民间音乐进行整体“八大”分类,为此后《民族民间音乐概论》等文献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吕骥特别重视对民族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主持中国音乐家协会与文化部合作,收集中国各地民歌并编辑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一文,之后开展《中国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等一系列文献编辑工作。
2.“局内—主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学者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他们返回家乡对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这类学者的研究,具有“局内—主位”的研究特点,但在研究成果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研究特点。如和云峰利用自身文化身份的优势,对纳西族音乐进行多年实地调查、专题研究,广泛吸收纳音乐、历史、语言等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撰写成《纳西族音乐史》。格桑曲杰致力于西藏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他走遍西藏70多个县的乡村、牧场、寺院,收集了大量西藏民族民间歌曲、器乐、戏曲、说唱音乐的音响、文字、图片乐谱等一手资料,并撰写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等。包爱军在《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等文献对本民族音乐进行全面的研究,促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
3.“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民族音乐学理论的传入,人们逐渐接受“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等理论概念。此时,学者们往往带有“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的研究方法,对“异文化”的音乐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研究、阐释和论述。如伍国栋在田野考察基础上,以纪实为主,研究白族民间音乐的渊源流变、历史沿革及现状,撰写成《白族音乐志》。赵塔里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地区的蒙古族额鲁特民歌进行长期田野考察,并阐述额鲁特民歌的分类、音乐特征、歌词特点等方面,认为曲式为简朴的二句体和四句体构成的单乐段的特点。此外,何晓兵关于白马藏人民歌的研究,周耘关于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杨晓鲁、和云峰关于纳西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吴鹏飞关于达斡尔族鲁日格勒音乐的研究等,取得较令人瞩目的成绩。
除上述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起先在香港、台湾等地展开,随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多所音乐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同类研究也陆续发展起来。此类研究,往往要求研究者要进行田野考察,并根据考察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论述。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研究视角,才能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其中,曹本冶通过分析不同属性的民间音乐仪式个案,以“仪式中音声”为切入点,以他们在该领域研究实践中所获之领悟和体验为基础,提炼出一套相对完备和清晰的理论框架。为学界在仪式音乐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具启发性的思路和可扩展的空间。杨民康、杨晓勋对瑶族道教仪式中的音乐、乐器以及音乐符号所负载的文化内容进行详细研究。薛艺兵着眼于中国民俗中与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仪式音乐,把“民间祭祀仪式”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的大背景之中做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并提出“信仰—仪式—音乐三重认知”等研究方法,构建祭祀仪式与音乐的关系的具体分析和文化阐释的一套方法体系。杨民康以局外视角研究傣族南传佛教仪式音乐风格和音乐形态,把节庆仪式分为核心层次、中介层次、外围层次,同时,又分别从基本模式、形态特征、风格变异几方面加以细致解析[26]。赵书峰对瑶族婚俗仪式音乐“涵化”发展现象,对婚俗仪式音乐的族性歌腔(“纳发调”)、曲牌等进行分析,并认为瑶族人民对自身音乐文化的族群认同是保护与传承瑶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内在驱动力。[27]
近年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一方面,此类学者研究具有“局外—客位”视角。洛秦从局外人视角对美国城市街头音乐进行考察和研究,探讨作为“局外人”的中国学者怎样看美国街头音乐现象以及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视角中的美国街头音乐现象分析。这是中国音乐人类学家在“域外田野实践”中的“中国经验”的典型案例,填补了音乐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8]。汤亚汀研究上海犹太难民在不同场合表演的音乐类型来维持社群音乐生活,以局外人视角对外来者群体融入中国的音乐文化变迁进行研究。现居美国的中国学者郑苏以华裔学者的文化身份视角,研究美国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传统音乐,论述中国传统音乐有关的族群、族性、文化变迁等问题[29]。另一方面,学者前往跨界研究对象音乐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身兼“局内—局外”双重身份视角。如李纬霖对云南与周边国家(老挝、泰国、缅甸)共有傣仂赞哈音乐表演现象,作者通过多次田野考察和学习赞哈找到赞哈表演前的模式,并分析中、老、泰、缅赞哈音乐的族性特征[30]。董宸对中—泰两国泼水节仪式音乐进行个案比较研究,从国家、城市、族群三个维度对仪式音乐中南传佛教圣俗对接的方式及融合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后世俗化”阶段中宗教(音乐)文化的基本发展规律。[31]
综上,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窥视出学者们沿着一条“局外—客位”“局内—主位”或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交互研究的中国实践路线。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研究视角,都具备研究的可能性和研究意义,关键要看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选择和位于的文化身份,以及为达到目的选择的研究观念视角。此外,“双视角”研究方法,贯穿于不同的研究环节中。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的不同时间、不同环节、不同目的,具备“双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而达到研究目的。
四、“双视角”理论方法中国实践的反思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身份的学者登上学术舞台,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同身份的研究者,往往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田野考察及案头工作等各个研究环节,运用“双视角”理论方法,从而达成研究目的。本节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对“双视角”理论方法的中国实践进行反思。一方面,能够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相关学术界关于“双视角”的研究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可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双视角”研究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第一,纵观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界,关于“双视角”研究,大多学者关注理论溯源、理论的概念阐释、跨学科视阈下的相互影响等论题。在个案研究中,也只是在论文的某个部分提到“双视角”研究,较少学者以个案的研究实践,对“双视角”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及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等进行综合论述。这就导致初学者虽明白理论概念,但具体操作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示,往往需要自己在实践中进行尝试和领悟。
第二,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志的相关课题研究,“双视角”贯穿理论学习、田野工作、案头工作等不同的研究阶段。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如何更好地运用“双视角”理论方法来指导课题研究,还需今后学者进行论述。
第三,如今,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研究身份呈现多元化趋势。针对多元化研究者身份,缺乏相对应的文献,只是针对“双视角”理论方法的实践运用进行分析与论述。例如,笔者带的硕士研究生往往来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具备少数民族身份,会说本民族语言,会唱本民族歌曲,会演奏本民族乐器。但是,学生们就算在理论阶段理解掌握了“双视角”相关理论方法,一旦走入田野,也会产生迷茫、不知所措,从而导致田野考察出现“误差”,案头工作时对研究对象造成“误读”等现象。
第四,随着学科的发展,“双视角”理论方法,从“局外—客位”发展到“局内—主位”。如今,学术界对“双视角”理论方法的运用与实践,主张建立双视角“螺旋形反馈”的考察系统,彼此平行和互为参照的双向(两极)考察系统。但是,从音乐民族志书写角度来看,上述考察系统如何建立,平衡点如何掌握,还需结合大量的个案研究进行分析和论述。
第五,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研究方法,来源于语言学。那么,擅长于“异文化”研究的民族音乐学。从学科研究实践层面,怎样助力跨学科的“双视角”研究,尚待研究和分析。
结 语
通过对“双视角”研究方法的理论溯源、国内外发展历程、中国学术实践、中国学术实践反思的论述,可知:第一,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研究方法来源于语言学,“双视角”一词为中国学者提出,并运用到相关研究中。第二,从国内外“双视角”发展脉络看,西方沿着从局外—客位到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交互研究。中国“双视角”理论方法,源于对日本学者的相关文献翻译,随后对相关理论进行论述,并运用到个案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学者的“双视角”范式特色。第三,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遵循着局外—客位到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交互研究的学术实践。第四,学术界对“双视角”研究方法应该进行更积极的学术反思,从不同研究者文化身份,观念立场及结合整个学科发展进行体察。学者应该从学理上理解双视角的概念意义,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能够自觉地随着研究环节的变化,进行转换文化身份和观念视角,从而更好实现其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