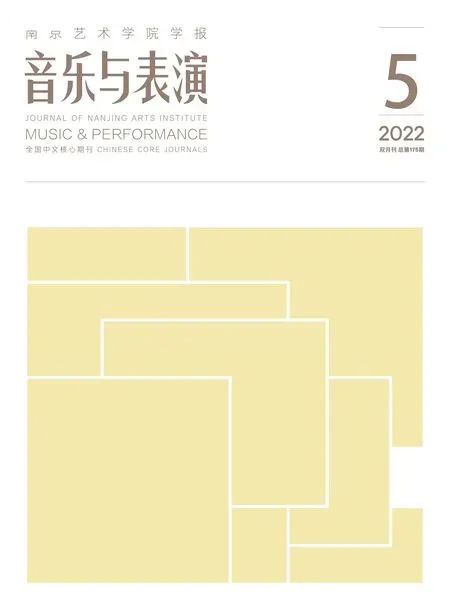语 境①
欧阳平方(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北京 100007)(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语境(Context)历来是科学哲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学等学科备受关注的论题,各领域立足从本体论立场、认识论路径、方法论视角等维度对语境问题进行了纵深探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亦称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境”日渐成为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关键词,以音乐(文本)或文化(语境)为研究主旨的学术论争贯穿了学科的发展进程,并由此形成在理论视域与方法上长期对峙的局面,即民族音乐学学科中的“音乐学派”与“人类学派”两大阵营并立同行。[1]179-184纵观两派之论争,实则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一种音乐现象均涵盖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两个方面,且均承认“文化(语境)”对于理解与阐释音乐现象之意义的重要性。
那么,何为民族音乐学的语境?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有何关系?相关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议题有哪些?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语境研究有何特点?对此,追溯语境的历史流变并对其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予以释义,厘清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有关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剖析与反思其在当下存在的问题,梳析其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实践经验等问题,即从“关键词”或“概念史”的研究视角②关于“关键词”研究与“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参见李春青.谈谈关键词研究的方法与视角[J].中国图书评论,2022(09):55-61.方维规.关键词方法的意涵和局限——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重估[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116-133+206.对民族音乐学之语境进行阐述则显得十分必要。
一、语境概念释义
语境③“Context”在各种汉语翻译中,又做“背景”“参照系”“情境”“环境”“景境”“场景”“情景”“上下文”“关系域”“内涵”“脉络”“场域”“语意场”“氛围”“人文叙事”等不同的解释。概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涉及众多研究领域和使用场合。或可说,但凡存在说明或解释的场合,即会存在与之相应的语境。
关于语境,在我国古代传统语文学中对其即有关注与相关认识,其时虽未有语境概念之名,却有对语境认识之实。例如,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提到的“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句”即为“一字”的“语言上下文”,即狭义的语境。再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提及的“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当中已从“字、句、章、篇”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一个语言形式在“语言上下文”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此外,在我国传统语文学中还存在大量的“微言”中蕴有“大义”,其“大义”已超出语言“上下文”之范围,属于“情景上下文”,即广义的语境。换言之,语言形式同它在语言环境中的功能运用紧密相关,语言环境包括“语言上下文”和“情景上下文”,虽说后者非为语言之本身,但研究语言却离不开语言的“情景”,这两种“上下文”指向语言的“内在”和“外在”被统称为语境[2]。
从词源学角度来说,语境概念是由英文词汇“Context”翻译而来,该词产生于拉丁文动词“Texere”(即编织),与之相关的“Contexere”则带有编织、交织、结合在一起或构成之意[3],并由此引申为“会话双方之间的相关性和连贯性”[4]。另从原文构词角度来看,语境(Context)是由词根“文本”(text)加上前缀(Con)构成,可知语境概念是指与“文本”直接相关的环境或领域。
在《社会科学新辞典》中,语境被解释为“语言成分出现的环境”,且分为“局部的上下文环境”“话语的微观使用环境”“话语的宏观使用环境”[5];《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中的背景(语境)被解释为“个体与他人互动之中,之前和之后运用的环境”[6];《后现代主义辞典》中的语境译为“上下文”“语意场”“氛围”,强调“当我们诠释某一词语时的一切有关事情,都是该词语全部使用历史所留下的痕迹”[7];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语境被释义为“使用语言的环境”,并分“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前者是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后者即指“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8]等。可见,语境概念的界定与解释是丰富多元的。
然而,就一般意义而言,语境概念有两种含义为人们所公认:一是特定语词、话语或段落的上下文的形式关联;二是特定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所映射的某种对象世界的特征[9],即表明“言语和文字符号所表现的说话人与周围世界的方式,可拓展为事物的前后关系、境况,或者扩展到一个特定‘文本’、一种理论范式以及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10]。可以说,这两种含义从“内在”和“外在”的结合上体现了语境的结构性及其对意义的规定性。
二、语境理论的相关学科面向
语境概念内涵丰富多元,具有不同的学科面向,理论来源亦复杂多样,且各学科领域的语境理论相互渗透与融合。特别是在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有关语境问题的讨论已成为一个较有学术创新性的论域。以下,笔者将以语言学、民俗学的语境理论为例,聚焦呈现语境理论的经验动态与学科面向。
(一)语言学之语境观
语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系统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20世纪20年代初,马氏在特罗布兰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原始文化做田野调查时,发现语言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紧密关联。1923年,他在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中附录了《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一文,率先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概念,认为“语言本质上植根于文化现实、部落生活和民族习俗,不经常参照这些宽泛的话语语境,语言就无法解释”,它主要指围绕话语的“即时环境”[11]。此观点在他1935年的《珊瑚园及其巫术》(Coral Garden sand Their Magic)一书中再次被表露,即“语境不但包括说出来的话,且还包括脸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所有参与交谈的人和他们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12]23。同时,马氏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跟语词相关的物质设备、活动、兴趣、道德或美学价值等)的概念,认为在“情景语境”之外,“语词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语境”[12]58。可以说,马氏提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概念形成了一个“三元论”的语境观,即“语言上下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13],亦即从“言语语境”扩展到“非言语语境”[14]。
马氏的语境理论深刻影响了他的好友——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的语言理论,弗斯全面阐发了马氏的“情景语境”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境的三个范畴,即言语活动参与者的相关特征(包括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语言的非语言性、非人格性实践;语言行为的效果[15]。其实,马氏及弗斯的“情景语境”理论,与英国哲学家、现代语用学奠基人之一奥斯汀(J.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言语本身”“言语效力”“言语影响”三个方面均是不谋而合,即分别与之对应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16]76。
此外,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A.K.Halliday)在《语言、语境和文本》(Language,Context and Text)一书中,将由马氏提出、弗斯完善的“情景语境”具体落实到语言本身的语义之中,提出了“语域”(Register)概念,它由“场景”(field)、“方式”(mode)、“交际者”(tenor)三部分组成[17]。同时,英国语用学家斯波伯(D.Sperber)和威尔逊(D.Wilson)在《相关: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提出了“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的概念,指“用于话语解释中的一系列前提(Premises)”[18]。有学者把这种“前提”认为是人类迄今积累的既有经验知识和集体认识水平[19],是对“文化语境”的一种提炼与解读[16]79。另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指出,语境是指一种由时间、地点、主题、身份等因素组成的社会情境[20],而海姆斯(Hymes)则认为语境是由文本的形式与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媒介、风格等因素组成[21]等。
国内语言学界,在充分借鉴与吸收国外语境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语境理论的中国经验进行了积极探索,它集“语形、语义、语用”分析于一体。如陈望道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提出了“题旨情境说”,“情境”即为“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为语境的具体化奠定了基础[22]。王德春是国内最早提出“语境学”概念的学者,并将语境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认为语境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23]。何兆熊将语境的构成因素归纳为“语言的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前者是指所使用的语言的知识和对语言的上下文的理解,后者则包含情景知识(交际活动的时间、地点、话题、正式程度、参与者的相互关系等)和背景知识(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关于客观世界的一般知识、参与者的相互了解等)[24]。
熊学亮则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认知语境”进行了阐述,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一门语境学”,而语境主要是指“认知语境”,即“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它包括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语用范畴: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是“社会”中的人所共享的东西[25];同时,“认知语境”还具有“集体意识”的特征,并在个人的知识结构里以“社会表征”的方式来协调人际间的行为和语言使用,使之适合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26]。
上述关于语言学的语境理论阐述,充分映射了语言学革命中一个重要的哲学观念转向,即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文本”(Text),置于其相关的环境——“语境”(Context)之中,而不再局限于将其视为孤立的“存在”[27]。
(二)民俗学之语境观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国外民俗学界“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理论的兴起,语境日渐成为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
美国学者邓迪斯(Alan Dundes)在《亚文本、文本和语境》(Texture,Text and Context)一文中强调民俗学研究不能仅关注文本,也要关注民俗事件依存的语境[28]。而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则指出“语境并非仅为一种附属性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文本与语境在现实中是水乳交融的”[29],并在继承马林诺夫斯基“语境观”的基础上区分了“场景的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的语境”(Context of Culture)[30]。由帕里(Milman.Parry)和洛德(Albert.Bates.Lord)创立的“口头程式理论”旨在从史诗艺人的表演语境中进行研究,即聚焦于“表演中的创作”,将口头史诗从过去注重“以文本为中心”(textcentered)的研究还原至其依存的活态表演语境中进行研究[31]。虽说帕里和洛德注意到了语境因素对口头史诗表演中创作的影响,但他们“终究没有走向对动态的表演过程的分析,而是最终回到了史诗唱词的文本形式研究”[32],而此问题直至在“口头程式理论”影响下出现的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中才得到解决。
表演理论的核心是“以表演为中心”,在表演语境中研究口头传统,强调文本和语境之间互动共生的关系[33]189,关注民俗事象的交流功能及其发生的互动语境与实际过程[34]。美国学者、表演理论代表人物鲍曼(Richard Bauman)强调研究“语境中的民俗”,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Context Culture)和“社会语境”(Social Culture)两大类,并进一步 细 分 为“意 义 语 境”(Context of Meaning)“风俗制度语境”(Institutional Context)、“交流系统语境”(Context of Communicative System)、“社会基础”(Social Base)、“个人语境”(Individual Context)、“情境性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还指出“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也应包括在内[35]。此后,鲍曼又将“语境”归纳为“文化意义的语境”(Context of Cultural Meaning)“功 能 语 境”(Functional 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 Context)[36]。鲍曼的“语境观”彻底颠覆了民俗学以往注重“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进而强调民俗表演的语境[37],关注民俗语境中的表演过程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行动与实践[38]。
此外,民俗学家托尔肯(Barre Toelken)在他的歌谣研究中界定出“物理语境”(Physical Context)、“时间语境”(Time Context)、“文化—心理语境”(Cultural-Psychological Context)、“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表演的即时人类语境”(Immediate human Context of Performance)[39]。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认为语境是多元的、建构的,并将语境分为“当下语境”(Present Context)和“遥远语境”(Remote Context),二者均可划分出“时间语境”(Spatial Context)与“空间语境”(Tempora Context)[40]。布瑞格吉(A.Kaivola-Bregenhj)在民间叙事研究中提出了“情景语境”(Situation Context)、“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类型语境”(Generic Context)[41]等。
梳析上述国外民俗学的语境概念及其理论,可知民俗学家们似乎在努力寻觅所有那些关乎民俗现象的“语境性”因素,但事实上,特定民俗现象的语境是不可能被研究者给穷尽的[33]190。鲍曼指出,研究“语境中的民俗”并非为简单地停留在罗列民俗现象的“语境性”因素,而是需要研究者深入明晰“语境与文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而关注“语境中文本的呈现”(Emergence of Texts in Context)及其形式的实际应用问题[42],并采取“以行动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在社会互动中寻找“语境化的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36],关注民俗表演文本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43]等问题。
反观国内民俗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主要研究范式是“超越民俗传承的具体时空、以民俗事象为中心(item-centered)”,但这种研究取向“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人群在具体的时空坐标中对民间文化的创造与享用”[44]。此后,中国学者便开始反思过去注重“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从文本到文本)的范式,继而转向“以表演中的、过程中的民俗为中心”,主张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45],其中的“生活”“情境”“人际互动”“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等均是民俗学语境的重要构成因素。对于语境,朝戈金曾将其分为“广义的语境”和“田野意义上的语境”,前者涵括了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后者是指“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至少包括以下六个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46],从中可知语境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然而,正是语境问题的引入,使得中国当代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从历时研究转向“历时+共时”的研究,从静态考察转向具体、动态的民俗生活考察,并与民俗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整体研究取向[45]。
概言之,语言学、民俗学领域有关语境的研究经验动态与学科面向表明,语境不仅是作为一个研究的议题或对象,而更渐进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理解社会文化议题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一种文化事象的存在,只要我们承认其存在“意义”,便会对其予以追问,即“意义”从何而来?然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与文化事象相关的语境即随之而来,它不仅存在“层次”与“阶序”,更是一种关系性、动态性、过程性、建构性的“存在”,并有助于人们客观地去认识某一文化事象及其内蕴的文化意涵,而这些理念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有关语境问题的理解与阐释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国外民族音乐学的语境研究
民族音乐学对于语境问题的讨论,必然要论及与之相关的音乐(文本)及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纵观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可知将文化(语境)视为音乐(文本)的生成过程或参照系,并从二者相互依存、互动共生的关系中进行整体研究,即“研究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民族音乐学学者广泛采纳和始终坚持的学术传统。
(一)音乐(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论争
民族音乐学作为脱胎和起源于音乐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47]3,决定了它注重对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同时,这也直接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何为音乐”的相关问题,即是音乐现象本身?还是一种人类文化?究竟要把哪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与出发点?是优先关注和探讨其中的音乐(文本)因素,同时也兼顾其他文化(语境)因素?还是一开始就以文化(语境)之眼光,将音乐(文本)因素置于音乐(文本)与人的关系以及文化(语境)中去考察音乐(文本)在整体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态?[48]3-8因此,研究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则形成了分别注重以音乐(文本)或文化(语境)为研究主旨的两大论争阵营,即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派”和“人类学派”。
其中,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派”沿袭了“比较音乐学”时期的欧洲音乐学研究传统,强调以音乐(文本)为研究主旨。此派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胡德(Mantle Hood)认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一个旨在从生理、心理、美学和文化现象等方面去考察音乐艺术的知识领域,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作为研究者应以获取有关音乐的知识为主要目的”[49],提出“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any music)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音乐周围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50],强调“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主题是音乐。但是与这个主题基本上不同而又相互依存的不妨包括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如历史、人种史、民俗学、文学、舞蹈、宗教、戏剧、考古学、词源学、肖像学和其他与文化表现有关的领域——这种对于似是而非的方法、目的和运用的研究事实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的还是音乐”[51]等。可见,在“音乐学派”看来,对音乐(文本)的研究是可从与其相关的文化(语境)中“析离”出来单纯进行的或可分先后的。
而民族音乐学中的“人类学派”因受“整体论”和“功能主义”的影响,则强调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融性,主张将音乐(文本)置于其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此派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于1960年在《民族音乐学讨论与范畴之界定》一文中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music in culture)”[52],并于1964年在《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一书中进一步对其加以阐释,即不仅关注音乐本身,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研究[47]7。此后,梅氏还提出“音乐就是文化(music is culture),音乐家的所作所为就是社会文化”[53],以及“音乐作为文化(music as culture)的研究”[54]等,以此来区分“音乐学派”获取音乐知识的研究。
关于民族音乐学界的“音乐学、人类学”之争,美国学者内特尔(Bruno Nettl)认为,梅氏于20世纪60年代主张“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是一种历史和民族志研究的常规方法,在70年代提出“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专门研究,但以胡德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却是一种“作为音乐的研究”[55]。同时,美国学者李斯特(George List)还就此对北美民族音乐学界出现的重“过程”而轻“音乐”以及对文化术语概念的故弄玄虚等现象提出了批评[56]。而荷兰裔美国学者林格(Alexander Ringer)则认为两派的论争实则对学科发展毫无意义,二者在“一统音乐学”的语境中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57]。其实,回顾两派争论双方各自的观点及过程会发现,两派于20世纪60年代的论争是聚焦在研究方法层面,即民族音乐学究竟是聚焦以音乐(文本)为主旨的学科,还是一种将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但到了70年代,论争则上升到了研究主旨层面,即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58]38,亦即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作为音乐的研究”?还是“作为文化的研究”?
(二)音乐(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融合
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一统”的学科,它对音乐(文本)和文化(语境)的双向关注历来就是学科思想史中的互补组合[59],亦即“音乐学派”和“人类学派”均承认文化(语境)对于人们理解与阐释音乐现象的价值和意义[60],都关注到了音乐是什么(what)及怎么样(how)的一般性问题。但较之而言,“人类学派”还是多了一层“音乐之为什么(why)”的意味,即在“音乐(文本)”(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之外,搭建了一个可进入音乐语义学乃至语用学(语境学)研究层面的平台与入口[48]19。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两大阵营则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均日渐走向融合之态势,诸如以下相关经验尝试。
譬如,英国学者布莱金(John Blacking)于1973年在《人的音乐性》(How Musical is Man?)著作中着眼于“社会和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社会和文化”,认为音响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而人类亦是“音响组织起来的人类”,通过音乐去研究文化,最终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不同的人”的研究[61]36-74,亦即“研究音乐就是研究人”。他在梅氏“音乐就是文化”“音乐作为文化”的意义上走得更深远,进一步确认了“文化中的音乐”之“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对音乐现象阐释的重要性[61]48。此外,他还指出在文化语境中研究音乐不能忽略音乐的生物属性(即生理语境),因为人类在制造音乐的基本生理与感知过程中存在先天的普遍生物性本能[61]23-26。对此,芬兰学者莫伊萨拉(Pirkko Moisala)亦提出,人类制造音乐的程度是由其先天性的生理心理机制决定的,而要对音乐的后天性的社会文化程度进行定义,则只能通过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音乐显现进行比较研究[62]。
内特尔于1983年在继承梅氏“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观点上,将其改为“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中的音乐的研究”[55],并将梅氏定义中的“文化”概念予以具体化与特定化,显现出“文本与语境”的文化符号学与阐释人类学的分析思维[58]36。同年9月,胡德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讲座时亦阐述了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主旨的新观念,即“民族音乐学就是用音乐本身的语汇来解释音乐与它周围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他对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存在相互共生、不易分割之关系的认同,亦传递了他对梅氏理论的部分认同之意[48]27。
再如,美国学者西格尔(Anthony Seeger)于1987年在《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中对“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和“音乐的人类学”(musical anthropology)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注重将音乐视为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从“整体论”的角度去研究音乐,后者则主张通过对音乐表演(performance,即呈现过程)的透视来观察社会[63],即“通过音乐来研究文化、研究人”。而这也体现在菲尔德(Steven Feld)对卡路利人(Kaluli)的音乐研究[64],以及内特尔在Blackfoot相关音乐思维模式的研究[65]之中,均体现了对音乐与其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考察。
此外,加纳学者恩克蒂亚(J.H.Kwabena NKetia)在以往民族音乐学之“音乐学、人类学”的论争基础上,提出“通过音乐(through music)去研究文化”[66]的观点。认为音乐的“文本”(texts)只存在于表演者和那些对其有所体验的人的记忆里,且是在他们具体的表演中生成的,而要对这样的音乐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就必须且只能是在其各种表演情境中去观察和记录,因为只有在这些情境中,特定的音乐文本才能在生活于这种文化传统的人的回忆或讲述过程中被我们所获得[67]84-91。其实,恩克蒂亚在此明确提出了一种“文本—表演—记忆—语境”的研究模式,并强调了语境对音乐文本(形态学)分析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指出,“语境”或“语境化”只是一种在对音乐意义进行描述性分析的过程中的探索工具或“方法”(means)而并非“目的”(end)[67]81。
另需提及的是,美国学者赖斯(Timothy Rice)在《重建民族音乐学》(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一文中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四层阐释模式”[68]469-488。该模式是在梅氏“三元模式”(概念—行为—音声)基础上,受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运用”[69]模式启发,并结合以往民族音乐学界的“音乐学、人类学”论争,且按照研究者面临的研究实际而提出。其中,第一层(分析程序):把“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与经验”分别视为独立的组成部分,再将梅氏“三元模式”分别置入其中予以综合分析;第二层(生成过程):对“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体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第三层(音乐学的目标):人类如何制造音乐;第四层(人文科学的目标):阐释音乐行为同人类其他行为的异同,亦即对“人”研究[68]474。在赖斯的研究模式中,体现了他对梅氏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如他认为在梅氏“三元模式”中,音声直接与行为和概念相联系,而人为地将音乐和语境分离,且各分析层次间的关系是单向的[68]481。而通过对格尔茨“历史、社会、个体”模式的借鉴,他不仅充实了梅氏模式的文化(语境)条件,还增添了“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创造、体验与使用的“主体”——“人”的因素,并将其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即对“人类性”的阐释。
(三)民族音乐学的语境及其指向
诚如前述,我们可充分认识到语境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其实,梅氏在1964年提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的定义中,“文化”即是一个语境[70]27,但在梅氏“音乐就是文化”“音乐作为文化”的定义中又表明“文化”并非仅是指某种“文化语境”(context)[48]34。那么,究竟何为民族音乐学的语境呢?
我们从恩克蒂亚的“文本—表演—记忆—语境”研究思路中可知,民族音乐学的语境概念实则与前述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中的定义之间存有共通之处,即均指研究“事象”得以发生的“具体情境”与“生成过程”。恩氏指出,在语境不加修饰词单独使用时,意为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或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但却“并非人们广泛设想的那样,语境仅仅意味着社会语境或文化语境,因为可以通过好几个参照框架对音乐进行观照”[67]85,而其中的“参照框架”即指语境,亦即民族音乐学的语境是存在“层次”和“类型”的。
譬如,赫尔顿(Marcia Herndon)和麦克雷奥德(Norma McLeod)在《语境与表演》(Context and Performance)一文中提出,语境是指音乐得以生成的过程,它围绕着音乐,并解释着音乐,孤立的声音并非音乐,只有“在语境的整体中音乐才能存在”,即语境对于音乐而言就是指一些包括“谁”(who)、“何地”(where)、“何时”(when)、“什么”(what)、“为何”(why)、“如何”(how)等方面的顺序(orders)或因素,语境的相关内容则是由研究者自身来决定的,进而将语境分为生理的语境、社会语境、语言的语境、场合语境、个体语境、身势学的语境含义等六个层面[70]32-41。此外,美国学者辛格(Milton Singer)在其出版的关于印度传统音乐的著作《传统印度:结构与变革》(Traditional India: Structure and Change)中首次提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概念,指出其核心即为“情境”(Situation Context),是指由诸如“表演的时间、地点、长度、内容及表演者和观众”等一系列结构性要素构成,而表演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结构化的情境中得以被传递与表达[71]。
日本学者山口修则认为民族音乐学“不仅要阐明其中心对象的内部结构(音乐结构),还要阐明其受到各自的社会、文化制约的外部结构(脉络结构),并进而把握其内外两种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而将围绕音乐的“脉络(语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72]。在山口修看来,民族音乐学的语境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前者是指音乐的形态语境,后者是指音乐的社会语境。此外,美国学者洛马克斯(Alan Lomax)在《民歌的风格与文化》(Folksong Style and Culture)一书中认为特定的民歌风格、声音类型与质量只会存在于那些展示着某种特征的文化中存在[73],布莱金亦提出“音乐的意义不但依靠作品的语境,还依靠某一时代的音乐习俗”[61]59等。
综上可知,民族音乐学的语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信仰的、个人的、语言的、习俗的等方面,是某一文化族群所共享的物质的、文化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规则,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并为具体的音乐表演提供一个文化的限定与制约;二是中观层面的音乐表演情境(场域),包括表演的时间、地点、场合、内容,表演者与观众的生理、身体行为以及表演的互动关系等,是一种具体的音乐表演场景,具有即时性、过程性特征;三是微观层面的音乐形态语境,它会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和音乐表演情境而引起音乐文本结构的自身变化。
事实上,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所面对的是“作为文化的表演中的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演情境中得以生成的,且存在于上述“宏观、中观、微观”语境的“双向互动脉络”之中。然而,当研究者将较单纯的“音乐研究”置入上下文语境时,首先指向中观层面的音乐表演情境(场域),然后才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语境[1]181。因此,在这个“双向互动脉络”中,研究者需要“以表演为中心”,通过对音乐表演的动态性、过程性与生成性予以音乐民族志式的田野观察,以此去切入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是因何而乐、如何作乐及如何用乐的问题。应当说,语境对于任何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而言可能均不陌生,在民族音乐学从比较音乐学时期注重的“音乐研究”转向“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研究”再转向“多点(线索)式的音乐民族志研究”的进路中,语境概念已然渗透到了其众多研究方向。语境概念的出现,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域引至到了“为什么”的层面,进而促使研究者置身心于音乐的田野作业现场,并将目光聚焦于对音乐表演动态过程的观察。
四、民族音乐学语境研究在中国
自20世纪80年代(“南京会议”①“南京会议”是指1980年由南京艺术学院高厚永等前辈学者发起和举办的“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后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便以此作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确立的标志。)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40余年间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经历了学术的“认知期”“实践期”“发展期”“繁荣期”四个发展阶段[74]。在这个学术进路中,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和意图有所取舍与改造”[75]之后,积极构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式方案”,而语境即是其中重要的学术论域。当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众多研究方向,均在各自维度就语境问题展开了多向度探讨。本部分将以“南京会议”为界,以此前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萌动时期”[48]66-83的“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两个阶段,及此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确立发展时期的语境研究为例,集中呈现民族音乐学的语境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发展动态。
(一)“南京会议”以前的中国民族音乐学语境研究
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沈洽将其分为“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四个时期,但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认识,其中论争焦点在于“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否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本文赞同将这两个时期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确立与发展的前期阶段[75]。纵观两个阶段的已有研究,虽说未有语境之名,却存有与语境问题相关的认识和实践。
20世纪40年代,吕骥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同时强调“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应当从它本身出发,分析它自身所具有的规律,然后根据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其发展的历史,予以合乎实际的解释”,并将民间音乐的研究内容设定为“一般理论的问题”和“专门的技术问题”[76]。其中,“一般理论的问题”多属于音乐的外部关系问题,即文化语境,而“专门的技术问题”则属于音乐的内部结构,即文本形态,并强调先从音乐本身出发,再对其得以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背景进行阐释。
从吕骥的研究提纲可以发现,他对民间音乐的研究目的并非仅是局限于胡德式的“获取音乐艺术的知识”,而是已经具有将民间音乐作为文化知识来进行研究的意味。应当指出的是,吕氏于1941年②该研究提纲写于1941年秋,是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而写。参见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J].音乐研究,1982(2):34.提出的这种学术主张实则并未受国外民族音乐学之影响,若从这个角度类比而言,吕氏要比梅里亚姆在1977年提出“音乐作为文化”[54]的观点早了将近40年。
事实上,研究“音乐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问题,并非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专属”,因为尚有其他学科亦关注这一问题。对此,美国学者西格尔曾有类似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联盟,虽然对某些人类说是合理的,但过于局限,因为也有其他同样与音乐学相关的“上下文语境”学科存在[77]。譬如,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抗日战争的国内高校南迁而使大批高水平研究学者迁至贵州③如当年闻一多等人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考察,大夏大学期间以吴泽霖、陈国钧等人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部”等。,在这期间的社会调查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黔东南苗族音乐的研究[78]。其中,跟随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考察团的心理学家刘兆吉在《西南采风录》中注意到了苗族情歌与苗族民俗语境的关联,并从音乐的角度探讨了苗汉之间的文化融合问题[79];民族学家梁瓯第在《摇马郎》一文中对苗家人的歌唱行为与“摇马郎”的社会风俗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进行了多向度描述与分析[80]等。这些研究成果均体现了将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进而对音乐与社会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进行考察的理念。
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系列社会考察工作的开展,部分音乐艺术院校的音乐学者亦参与其中,而这种情形亦使此阶段的音乐调查研究添增了不少社会历史文化之意味,即在搜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对音乐与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的关系予以考察,代表性成果有《苗族民歌》《苗族芦笙》等。
譬如,在《苗族民歌》中,作者充分结合苗族民歌的音乐形式(文本)和用乐场景(语境)对其予以分类,如“牯藏歌”“‘游方’生活及其情歌”“苗族的酒歌”[81]5-6等,将苗族民歌归还到苗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此外,关于苗家人的“游方”活动,作者从其歌唱场景、社会功能以及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语境层面进行考察[81]13-49。这些均体现出作者并非单纯地研究苗族民歌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知识和苗家人的生活方式去考察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让人们“对苗族民歌的了解也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对其生活全貌的了解出发,对民歌创造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得到较深的认识”[82]。而作为同一时期的成果,《苗族芦笙》[83]的研究范式亦是如此,即不局限于对音乐本身的研究,更注重对音乐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考察。《苗族民歌》和《苗族芦笙》不仅拉开了现代性音乐学科层面的苗族音乐研究之序幕,同时更是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将“文革”前夕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78]。
另外,“南京会议”以前有关语境问题的研究,还体现在“音乐形态语境”层面。如于会泳提出的“综合研究”(又称“横向研究”),将普遍存在的音乐形态规律加以理性地抽象归纳,进而挖掘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整体规律[84],其《腔词关系研究》对传统声乐的腔词关系(如腔词音调、唱腔与字调、腔词节奏等)结合语言学的知识进行了探索总结[85]。又如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讲稿》从“音韵”和“句逗”的维度对汉族语言(语境)与汉族音乐(文本)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纵深分析[86]等。
综上,无论是将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知识,继而对其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还是有关传统音乐形态语境的研究,均为“南京会议”以后的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换言之,1980年传入的国外民族音乐学,对中国音乐学界而言不应为一个全然陌生的学科。
(二)“南京会议”以后的中国民族音乐学语境研究
自“南京会议”以后,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得以正式确立并得到真正发展,有关语境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日渐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热点论域,并主要呈现为以下维度。
1.国外民族音乐学经典文献译介工作
中国音乐学界接触国外民族音乐学的路径,多是在对国外民族音乐学文献译介中开始的,且译介工作一直贯穿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进程。既编译出版了诸多论文集①如《民族音乐学译文集》(1985)、《音乐词典词条汇集——民族音乐学》(1988)、《音乐民族学译文集》(1992)、《民族音乐学译丛:EML理论·方法·应用》(1992)、《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2010)、《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2011)、《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007)、《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2019)等。,亦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民族音乐学经典著作②如《非洲音乐》(1982)、《歌唱测定体系》(1986)、《出自积淤的水中》(1999)、《人的音乐性》(2007)、《音乐人类学》(2010)、《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2011)、《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12)、《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2017)等。。这些译介的经典文献系统地反映了国外民族音乐学的学科面向与发展状貌,而其中有关“音乐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问题则构筑了这些研究成果的主线,这不仅为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传播夯实了基础,也加快了中国学者探索与构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进程。
2.区域音乐文化研究
区域音乐研究旨在研究特定自然、文化空间的音乐现象与该空间的自然环境、古代文化状貌、方言语言、民俗民风等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多维共生关系[87]。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的“民歌色彩区划”研究,在不同侧面对音乐与地理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究[88];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广泛吸收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成果,对传统音乐的形成与区域风格进行了多向度研究,积极探索“中国音乐地理学”[89]的研究范式。如乔建中从文化地理学与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传统音乐与其特定地理历史文化背景(语境)的互动关系[90]。同时,亦有学者从学理层面对区域音乐研究进行探讨,如樊祖荫对乐种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剖析[91],赵书峰提出了开展基于“文化圈背景”甚至是“同一区域音乐文化语境下的跨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92]等。
近年来,音乐学界涌现出一种注重以“文化遗产廊道”和“山水通道”为载体的“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景观)”研究热潮,主张将特定自然文化空间的音乐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整体性”“流动性”“历史性”“关系性”的客观文化存在,强调从以往定点、个案式的田野考察转向一种多点、线索式的田野追踪,即在一种“流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音乐与线性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立体式研究,如张应华、赵书峰、胡晓东等学者的系列研究[93]。
3.(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
面对作为口头传统的活态音乐,研究者不得不回归到人类组织的声音呈现过程,即关注特定表演语境中的音乐生成与建构。在民俗学表演理论的影响下,音乐表演民族志日益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关注的学术热点。如杨民康指出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书写中的“音乐符号文本”与“仪式表演文化活动”之间,本质上存在并体现了某种“文本与上下文语境”的关系[94];萧梅对以“体验”(身体感知语境)为核心的音乐表演民族志文本的表述方式进行了探讨[95];赵书峰则从语境、身体、互文、权力的角度对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进行了再思考[96],并主张结合民族志“深描”视角去关注特定语境中音乐表演的“新生性”研究,即从表演的“去语境化”“再语境化”去关注音乐表演文本的建构与生成③引自赵书峰2022年6月23日在第三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发言《音乐表演文本的建构与生成研究》。;博特乐图从表演、文本、语境、传承的角度对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97];以及李亚对上海地区江南丝竹乐种的表演民族志研究[98],朱腾蛟从表述、认知、语境的角度对“语境化”的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的研究[99],凌晨、李纬霖等学者对跨界族群的仪式音乐表演研究[100]等。
4.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
针对以往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缺乏对音乐生成的“历时性文化语境”关注的现象,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历史人类学影响下,一种注重以“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历史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应运而生[101]。如伍国栋强调以“音乐历史本来面目”去理解与阐释音乐文化的活态存在及其形塑过程[102];项阳注重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相结合,将活态的音乐事象与其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接通”[103];杨民康主张将音乐作品、音乐事件和音乐人物还原其依存的上下文语境中予以整体描写,进而探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多样性书写范式[104];齐琨提出将音乐放置在时间的过程中解读,并将这个过程作为文化给予阐释,即在“共时与历时”和“空间(文化)和时间(历史)”相结合的语境中理解音乐[105];赵书峰指出不但要关注音乐的活态呈现,并要将在场的音乐文本置于其历史文献的“书写语境”中予以观照和审视[106]等。
5.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
认知民族音乐学的核心任务是阐释人们如何制造和接受音乐的问题,即通过音乐来获取对“人性”的理解,而语境是研究音乐文化认知模式的重要因素。如张伯瑜认为“声音的建构和社会语境的建构必然会存在着某种建构模式”[107],并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中国作曲家创作个性所隐含的“集体性认知模式”[108]进行了分析,以及倡导从声音与表演的“结构语境”去审视用乐主体的文化认知模式[109];萧梅则主张“回到声音”和“从感觉出发”,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中“境域式”地实现“我”“在场”的认知经验[110];赵卓群指出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研究音乐本体和表演程式进而聚焦音乐创造者的思维是认知民族音乐学提倡的音乐认知分析方式[111];朱腾蛟立足以“体验”(身体感知语境)为基础对少数民族民间歌唱认知模式的研究[112];欧阳平方提出进入用乐主体的特定生活场景(即“用乐认知语境”)去参与、观察他们的观念(分类、事件)和表述(身体、言语),是理解某一族群音乐文化认知模式的重要路径[113]等。
6.仪式音乐研究
仪式音乐研究意在将仪式音声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而对仪式音声和信仰体系(即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114]。而它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繁荣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及其博士团队的学术研究之驱动。不仅产生了诸多专门探讨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方法论成果,如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2003)、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2003)等,更催生出系列仪式音乐的案例研究,如赵书峰将湘中民间仪式音乐与“在地化”的互动关系置于其“在地化”现象的移民文化语境中予以整体研究,强调了社会文化语境对仪式音乐现象进行理解与阐释的作用[115]等。
7.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目光的投向问题
有关音乐本体形态和“音乐作为文化”之间孰轻孰重、孰是孰非的讨论是民族音乐学界长期存在的话题,而这与郭乃安提出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紧密相关。究其本质,在于一些学者狭隘地将其中的“人”等同于“外部诸条件”(即民族学、人类学层面的文化),然郭文实则强调的是:音乐中存在“人”的因素,并涵盖“音乐本身的研究”和“音乐与其外部诸条件的联系的研究”两种类型[116],二者并存且均存在“人”的因素,亦即“人的音乐性”和“音乐的人性”。
音乐作为“人”的行为结果,定然会受与之相关的语境影响,但其根本语境则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使用它们的“人”[27]18,而这亦是“民族音乐学为何要研究人”[117]的重要逻辑起点。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即文化语境因素对音乐本身的影响,既有显性的,亦有隐形而一时无法寻得的;此外,“音乐形式还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历史继承性的一面,故而不一定都要或都能够与音乐内容及生成背景(语境)相联系”[118]。
除上述以外,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有关语境问题的讨论还体现在音乐与认同、跨界族群音乐、音乐民族志、音乐教育与传承以及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研究领域。
总之,透视语境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在对语境问题的不断讨论、实践、反思、否思、探索与建构过程中,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文化意涵,但同时我们亦发现其中一些存在的问题:譬如,一些年轻学者由于对语境概念的不清晰,而一般简单化地将之等同于“文化”,致使出现“为文化而文化,为语境而语境”以及“音乐与文化”之“两张皮”的现象。又如,民族音乐学因强调语境的重要性,而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于音乐现象的田野现场,在肯定这一举措的同时仍需指出,走进“田野”并不意味着就把握了音乐的相关语境,如若缺乏“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理论视野、调查方法和问题意识等学科知识素养,那么从田野中得到的田野资料仍可能是“风干的标本”[119]。再如,民族音乐学论文写作的模式化问题,一般常见为先大篇幅地介绍所谓的音乐社会文化语境(包括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模式、宗教信仰、民俗、语言等),再定性分析音乐的本体艺术特点,然二者实则往往互不关联。此外,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有关语境的方法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具体的实际田野个案研究却仍有待加强等。诸如此类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与思考。
结 语
音乐是一种文化,它的生成受到各族群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由此而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语言、宗教等诸多(社会文化语境)方面的综合影响[120],继而在不同的维度显示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不同的文化“符号”表征[121]。作为一个指向“意义”的学科领域,民族音乐学和语境之间密切关联。纵然“研究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作为学科范式的关键词,语境的意涵并非仅是名词性的context,而更是指向一种过程性、关系性、生成性、建构性和多样性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实践。
语境不仅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亦是作为一种理解“音乐与文化”之互动关系议题的重要认识论路径与方法论视角。国外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确立与发展,其本质原因是在于它将音乐置于其依存的“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整体考察,并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整体阐释,继而使人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成为他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以及对不同文化理解的一个途径[122]。于此可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已然形成了“本土化”的语境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同时,我们亦可预见,语境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未来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存在更大的拓展空间和可能性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