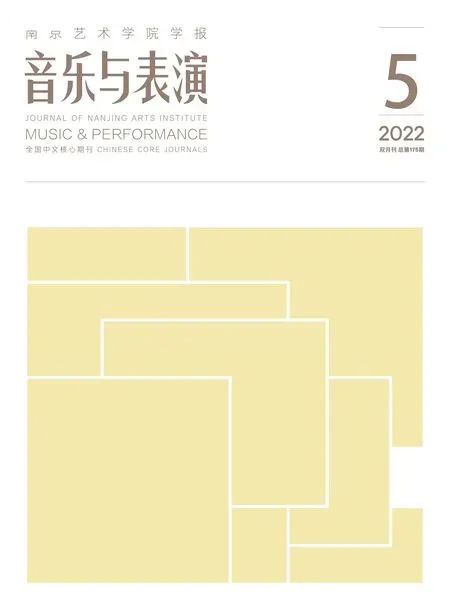语言音乐学①
苏毅苗(云南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
陈海韵(云南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
“语言音乐学”是一门综合运用语言学和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交叉学科,它以各地音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记录、描述与分析,从而研究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该学科概念的提出肇始于杨荫浏先生于1963年为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音韵学课程所编撰的《语言音乐学讲稿》[1],而后十余年,杨荫浏先生及其学生孙玄龄将旧稿重新整理修订并改名为《语言音乐学初探》,后被收入1983年出版的戏曲音乐研究丛书《语言与音乐》[2]中。语言音乐学的提出迄今已近60年,本文通过整合不同时期学者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成果,分析语言音乐学学科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的变化,厘清其学术发展脉络,从而了解关于中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音乐中词曲关系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来路,对当下语言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反思。
一、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音乐学与语言学本是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学者关注到这两门学科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关系,为准确表达本“语言音乐学”一文之旨义,避免相关词汇多义性的误解,在此必须将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的一些语素或问题提前加以释义与说明。
(一)本文中关于“语言”定义
“语言”广泛的科学定义为“语言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3],是人类的交际工具。由于目前语言音乐学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研究中国各民族语言和音乐的关系,故本文提及的“语言”主要是狭义的专指释义为“中国民族语言”,即中国各民族语言的总称。
从纵向看,古代的“语言”以华夏各地方言为主。1949年后,经中央政府调查统计正式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涵盖了中国通用语言(普通话)和各地区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从横向看,各民族、各地域语言具有特殊性,其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关于“语言文字”可得。中国56个民族,其语系涵盖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其中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二)语言学和音乐学
“语言音乐学”是由语言学和音乐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一门学科。语言学下有语音学、语义学、形态学等诸多分支学科,“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领域”[4]。本文提到的语言音乐学研究方法涵盖音乐学、语言学及其下所有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
(三)本文研究旨归
综上所述,本文所指的语言即为中国民族语言,语言音乐学是以各地音乐为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学和音乐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族语言中关于音乐的若干问题,寻找中国民族语言中的音乐元素,从而探究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二、语言音乐学之溯源
语言音乐学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迄今历时近60年,回顾语言音乐学发展历程,笔者将其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三个阶段。
(一)语言音乐学的萌芽期——20世纪60年代之前
“语言音乐学”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但关于语言与音乐的关系阐述,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涵义为诗是人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歌曲是咏唱诗的语言;声音要和咏唱的语言相配合,乐律用来调和声音。从《击壤歌》到《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或是从瞽矇说唱到宫廷俳优、唐代变文和参军戏、宋代唱赚、诸宫调和鼓子词、明清的弹词与鼓词;抑或是从宫廷俳优到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和南戏、元代的杂剧以及清代地方戏曲和京剧等,纵观中国5000年历史,不论是诗歌、曲艺还是戏曲,其音乐与语言血脉相承,采用以词待曲或倚声填词的形式相伴而生,随之产生了所谓“以字行腔”“字正腔圆”的说法。到了近代,吴梅在《顾曲麈谈》[5]中较早地对传统音乐(戏曲)中声调和曲调的关系进行研究,赵元任“开创汉语声调的记调方法,创制五度制的声调符号”[6]58-59,并在《中文的声调、语调、吟唱、吟诵、朗诵、按声调谱曲的作品和不按声调谱曲的作品》[7]中探讨中文语音语调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他的诸多成果极大影响了语言学界和音乐学界,也奠定了语言音乐学的产生基础。
(二)语言音乐学的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
1963年,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关于音韵学的课程,邀请杨荫浏先生讲授并撰写《语言音乐学讲稿》,“语言音乐学”就此诞生,也为语言音乐学提供中国式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而后十余年杨荫浏继续深入探究语言和音乐的关系,与其学生孙玄龄重新整理修订旧稿,并改名为《语言音乐学初探》,该文与孙从音《戏曲唱腔和语言的关系》、武俊达《谈京剧唱腔的旋律和字调》一齐收入1983年正式出版的戏曲音乐研究丛书《语言与音乐》中。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的学者逐步开始涉足语言音乐学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汉民族音乐和汉语言之间的关系,即关于中国传统音乐中腔词关系、词曲关系、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的研究,如李西安《汉语声调与汉族旋律》[8]、沈洽《音腔论》[9]、周青青《汉语语音的声、韵因素在汉族民间歌唱中的作用》[10]、章鸣《语言音乐学纲要》[11]、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12]等。这一时期关于音乐和语言的关系的著述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音乐学或语言学的理论角度阐述二者关系;第二,概述性、基础性或集成性的论著较多;第三,从戏曲民歌表演的视角阐述二者关系;第四,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的思考的相关著述。
(三)语言音乐学的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民族民间集成的推进,以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使得学界逐渐重视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21世纪初钱茸提出“民族语言音乐学”,语言音乐学的学科定位由“民族音乐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是以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手段,并结合我国传统声韵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有关诗词格律的知识来研讨、阐明我国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包括民歌、说唱、戏曲和歌曲)中语言与音乐的密切关系”[11]1,扩展到“借鉴现代语言学方法(包括记音方法、分析方法、思辨方法、数字科技手段等),结合音乐学方法,以地域性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界系统学科”[13]113,研究范畴也由中国传统音乐扩展到少数民族音乐。这一时期民族音乐学领域关于少数民族音乐与其本族群语言之间关系的成果逐渐丰富,如高贺杰《因“韵”而“声”——鄂伦春人的歌唱世界》[14],潘永华《论侗族大歌音乐形态特征及其形成的思维基础》[15]等。虽各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其研究成果对于语言音乐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国外有关“语言和音乐”研究成果
关于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便有学者探究。“柏拉图声称某些音乐模式提升精神的力量源于它们与高尚语言的声音相似(Neubauer,1986)。”[16]3-4中世纪 song-school“刻意地将音乐表达与语言表达结合起来,不仅仅是因为‘语法与旋律’代表了基础研究的两个主题,而且共享了相同的基本材料:声音”[17]。同样,自古印度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确定清晰表达的语言和我们称为音乐的声音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18]。如今,哲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和音乐学等多个领域皆从不同视角对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
1.音乐领域研究成果
关于音乐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首先从音乐符号学视域下探讨语言和音乐的关系。音乐符号学从最初借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逐步脱离语言学逐步转向“认知符号体系”[19],但还是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如凯塞尔斯《从音乐意义的分析来看,音乐是情感的语言吗》[20]“将音乐与语言的比较作为其对象,并置于符号学的框架中展开研究。”[21]9费尔德、福克斯《音乐与语言》[22]从作为语言的音乐、音乐中的语言、语言中的音乐和关于音乐的语言四个方面梳理语言和音乐思想的历史轨迹,并通过符号学和音乐学来整合这四个方面,其后逐渐发展“声乐人类学”[23],这“也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整合语言和音乐的研究,从而探索在音乐和语言艺术中语言的诗意和声音象征方面”[24]。其次是音乐语言学中涉及语言和音乐。《音乐语言学:从新词到公认的领域》谈到,音乐语言学是“音乐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试图用语言学的方法来描述音乐感知现象”[25]。此外,2007年发表的Iwaidja Jurtbirrk Songs: Bringing Language and Music Together[26]一文,作者在对“Iwaidja Jurtbirrk Songs”的生态、社会背景,整体内容(歌集)介绍的基础上,对其音乐、语言(其中包含文本的音节结构、语法、特殊的亲密词汇)进行分析,探究在这项表演中语言和音乐的关系,文章对本文所提语言音乐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另外,国外成果方面不乏涉及中国语言和音乐关系的成果,如Esther Mang在《中文语音—歌曲界面》[27]一文中探究汉语语音与歌曲表演的界面。同样对中文语言和音乐研究的还有John Hazedel Levis的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28]等。
最后,还有一部分为大陆学者或港澳台地区学者发表于外网的文献,如卞赵如兰《(字)调与(乐)调:在中国字上加各种音乐成分的举例》[29]在其父赵元任关于声调、语调和音乐的关系研究基础之上,列举戏曲音乐的例子补充说明个人关于语气、语调、吟诵、咏诵和有调性作曲和无调性作曲等方面的观点。从音乐领域成果来看,由于西方国家语言主要以非声调语言为主,研究成果较少涉及语音本体和旋律形态的关系,对研究中国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借鉴意义较小。
2.其他领域研究成果
生物学领域有《语言与音乐的比较》[30],从进化和认知的角度,通过实验比较大脑对语言和音乐处理的异同。心理学领域有《在大脑中唱歌:歌词和曲调的独立性》[31],通过实验分析证实歌词和曲调的独立性并寻找语言和音乐处理之间的异同。《音乐和语音引发的语言:共享处理机制的证据》[32]通过实验,研究测试音乐和语言感知的速度差异如何影响后续的言语产生,解释音乐和语言之间的一些联系并提出了一种通用域速率处理的共享机制。神经科学领域有《韵律和音乐模式的处理:一项神经心理学调查》[33],通过实验比较探索语音和音乐中旋律和节奏模式的处理之间的关系。《成人和儿童的韵律和旋律处理:行为学和电生理学方法》[34]比较分析语言中的韵律处理水平与音乐中的旋律处理水平,以及《音乐,语言与大脑》[16]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对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探讨等。音乐和语言之间从根源(生理)上看息息相关,以上领域关于音乐与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扩大了音乐学、语言学领域学者的视野,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
三、语言音乐学之实践
语言音乐学迄今尚未建立普适性的标准或分析方法,而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音乐学不同领域的一系列范式,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实践。音乐研究学者在借鉴语言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目前主要采用以下几种采音、记音手段,描述手段和分析方法。
(一)采音、记音手段
语言音乐学早期研究对象以戏曲音乐为主,采音手段常用《方言调查字表》[35]。记音手段主要依靠汉语拼音以及随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的国际音标,如杨荫浏在《语言与音乐》中记音手段为汉语拼音,章鸣《语言音乐学纲要》则使用国际音标记音。张明霞《赣南信丰县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36]进行信丰县客家方言声调实验中选择的发音字是从《方言调查字表》而来。后期语言音乐学研究对象扩展至各民族音乐,主要依靠国际音标记音。如以戏曲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单刀会〉双调【新水令】字调腔格初探——基于语言音乐学视角的元杂剧旋律风格考辨之一》[37]和以少数民族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符号的隐喻:语言音乐学视阈下的海南黎族音乐》[38]皆使用国际音标记音。
(二)语音和音乐的描述手段
1.音符类描述手段
除了常规的五线谱、简谱外,语言音乐学使用的音符类描述手段还有——双音唱谱。此为钱茸提出的一种新式记谱法:“即兼有为唱腔标示音高、节奏的乐谱与为唱词注音的国际音标。唱词的上方既有音符,又有音标,故称‘双音唱谱’。”[13]68如苏毅苗《“呗耄腔调”经文唱词特征与词曲逻辑关系研究》[39]对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呗耄腔调进行描述中不仅使用五线谱和国际音标记录音乐旋律和唱词,更加入该音乐唱词的彝文、彝文直译和译义,使得描述更全面具体。
2.非音符类描述手段
(1)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
“通用旋律动态模拟器”是1995年沈洽与邵力源研发出的一款计算机软件,“可用来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旋律的动态(音高与时值的互动关系)和人的听觉对旋律的感应(心理量)作出精确描写,描写数据(是为‘DEAM乐谱’)可立即转化为模拟演奏和直接用于旋律风格特征(形态特征)的定性、定量分析”[9]148。这是学界非音符类描述手段一次质的突破。
(2)字调与腔调音高对照图
苏毅苗在《“呗耄腔调”经文唱词特征与词曲逻辑关系研究》中“以字位为横坐标,以音高为纵坐标,实线表示调值,虚线表示腔调音高,形成字调与腔调音高对照图”[39]99-100,通过对照图描述呗耄诵唱腔调的字调与腔调音高之间的关系。另外,钱茸《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40]中也提及类似的描述手段,即“调腔音高对比图”①钱茸于2009年首见黄妙秋的《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研究》关于词曲关系的对比图,其后经霍亚新改良,钱茸将其称为“调腔音高对比图”。。字调与腔调音高对照图使得腔词关系跃然于纸上更便于理解。
(3)实验语音学“声调测绘”
语言音乐学中,通过Praat软件对音乐进行测试,得出基频率数据和声调T字图、声调格局图等,清楚准确地呈现音乐的音高、音长等数据,从而代替传统的语言学家、音乐学家根据器官来模拟语音语调,并使用音标其语音进行描述和记录。应用此描述手段的文章有张明霞《赣南信丰县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钱茸《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等。
(三)分析方法
1.声韵调分析法
杨荫浏在《语言与音乐》中最早使用音韵学方法分析戏曲唱腔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后这种方法被普遍用于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与汉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种对语音语调的传统分析法为音韵学上的声韵调分析法,“就是把语言里的音节一分为二:前一部分叫‘声’或‘声母’,后一部分叫‘韵’或‘韵母’,附在整个音节上的音高叫‘调’或‘声调’”[41]27。后此方法与音位学分析法结合,使原本只能分析汉语语言可运用于分析汉藏语系语言。
在语言音乐学中,中国学者通过对传统音乐中汉字声母、韵母、声调的分析,探究其语音变化的规律和结构特点等,再结合音乐学研究方法,从而达到总结字调和旋律的关系、归纳地方方言音乐共同属性等研究目的。如杨荫浏先生在《语言音乐学初探》中通过昆曲在音乐上适应字调的经验,总结南北曲字调配音规律,从而探究南北曲的音乐风格与语言的关系。章鸣《语言音乐学》则在“方言与音乐举隅”中用此方法阐述八个地方方言及其音乐的关系。除此之外,使用声韵调分析法对语言音乐学视域下的音乐进行研究的还有薛雷《“拉魂腔”渊源及形成考辨》[42]、黄建荣《浅论方言对抚州采茶戏腔调、唱词、韵白的影响》[43]等。
2.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
历史语言学于19世纪广泛应用于印欧语系研究中,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是人们建立语言史的唯一方法,它有助于人们确定所比较语言间的亲属关系进而构拟出它们的原始共同语”[44]。语言音乐学中借鉴了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对音乐(含乐器名称)进行研究。如罗艺峰在《口弦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将不同语族的民间音乐进行比较,他认为:“先将一语系或语族的同源词 (指口弦名称)列出,然后在不同语系或语族间寻找读音相同或基本相同或有某些音节相同的词(指口弦名称),其中可能的联系如语音转换关系、古音今音对应关系是我们企图实现同族或不同族语言‘时空转换’的关键。”[45]罗艺峰在《石峁初音——音乐学、考古学与语言学结出的奇葩》[46]中同样使用此分析法。曹量在《符号的隐喻:语言音乐学视阈下的海南黎族音乐》中也使用历史语言学比较法对黎语与同语族间的音乐学进行比较研究。
3.“双六选点”分析法
“双六选点”作为语言音乐学学科发展中一种较为新颖的分析方法,是钱茸在语言学方法和音乐学方法基础上,吸收融合并创新的一种方法。钱茸提到:“唱词音声本体所具有的音乐性,它们自身的存在就具有音乐价值,它们中的某些部分,又产生了对腔的‘影响’。”[47]“双六选点”主要包括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选点与唱词的隐性音乐符号选点两个大类。其中,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六选点涵盖了特殊音色、色彩对立、衬字、认同回归和谐、地域声乐品种、导引特色声乐发声六个点;唱词的隐性音乐符号六选点涵盖了唱词的字调走向、习惯性语调、字量变化、语言音色、声音长短、习惯性重音六个元素对唱腔旋律的影响。胡晓东《巴渝民歌的语音学初探》通过分析巴渝民歌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和隐性音乐符号,探究“巴渝民歌唱词音声本体特性中有可能会对民歌的音乐形态特征发生内在影响的因素”[48],总结巴渝民歌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地方风味。另外,花文《语言音乐学视角下的河阳花鼓戏》[49],高彩荣《语言音乐学视域下的陕州梆子地域风格探究——兼谈陕州梆子的“本土”身份》[50],冯凌燕《语言音乐学视角下长沙、岳阳花鼓戏唱词音声本体及地域性艺术特征对比分析》[51],皆使用“双六选点”分析法进行研究。
4.实验语音学方法
实验语音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使用各种实验仪器来研究并分析语音。语音音乐学中,它既是一种描述手段,又是一种分析方法。学者使用Praat软件对唱词语音和歌唱旋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音乐和语言的关系。钱茸在《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论证》[52]中提到,实验语音学能通过近代以来可用于研究言语生理状况的医学器械,以及测量、分析言语声的物理仪器等科学技术手段,来研究、分析语音,并借助这种数字化手段量化展示音乐中的“中国元素”。如张明霞在《赣南信丰县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中对信丰县方言采录,通过运用实验语音学研究单、双字调的声调实验方法,使用实验语音学软件Praat分析,从而得到信丰县客家方言调值,在此基础上分析信丰县民间音乐腔词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变更。音位学分析法弥补了传统声韵调分析法的不足,但其研究对象多适用于汉族音乐。“双六选点”分析法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地域性音乐,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亦具有可行性。历史语言学比较法总结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地域下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及其亲疏远近,推出各语言之间音乐文化融流的历史,为语言音乐学历时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验语音学方法不仅准确分析唱词语音语调,更精准捕捉唱词中的中国音乐元素。
四、语言音乐学实践经验之反思
自杨荫浏先生1963年提出语言音乐学的概念,迄今已近60年。在这60年间,学界前辈杨荫浏、于会泳先生对语言与音乐关系的关注,为语言音乐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洽教授、钱茸教授等学者为语言音乐学的基础理论完善和实验方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研究实践上,描述手段从音符类描述走向了非音符类描述,对音乐的描述更为客观,视觉上更为直观。在分析方法上,声韵调分析法、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双六选点分析法、实验语音学方法等,为语言音乐学乃至音乐学的分析研究扩展了视野。但是,“学科发展中势必经历试验、实践和反思阶段”[53],特别是对于年轻的语言音乐学来说,交叉学科的属性使得它的发展更为复杂。对语言音乐学的总结反思,能够找出制约因素和薄弱环节,进而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语言音乐学学科理论缺乏体系化的构建
虽然语言音乐学从提出至今已有近60年历史,不少学者对其理论和实践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但是,我们在梳理语言音乐学的发展轨迹时可以发现,语言音乐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戏曲声腔。从研究戏曲声腔的成果中析出方法,并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展为汉藏语系音乐,再到民族音乐。这种发展轨迹,更类似于在各种研究对象中验证已有的方法和理论,提炼出相关结果以丰富基础理论。实际上,目前所能采集的语言音乐学相关成果,个案研究较多,对该学科系统性阐述的专著较少,对该学科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系统性阐述的专著成果尚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和总结提炼。
此外,语言音乐学属于语言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在理论内涵与外延方面的界定,基本分析手段的固定,研究成果的定位与应用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总体来说,语言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缺乏体系化的构建,如何完善学科体系、形成学科研究范式是中国音乐学界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建设、构建学术话语权较为重要的一步,也是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发展,深化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必要举措。
(二)研究范畴、研究内容有待多元化
研究范畴方面,目前语言音乐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具体音乐事项以及某一地区或某一族群的音乐,研究成果中个案研究居多。但是,研究对象涉及的范围还远远不够,得出结论的普适性还需进一步增强,族群、民族、流域、走廊、文化圈的音乐本体刻画和属性揭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其研究范畴不应仅限于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还应逐步扩大至国外民间音乐,用他者的音乐与国内民间音乐相比较,验证语言音乐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性。
其次,语言音乐学研究的范畴,“显性”的形态分析个案比较多,而“隐性”的分析比较少。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戏曲声腔,以及有腔音化特点的民族音乐题材。这些题材的音乐,由于自身就带有明显的语言即音乐的特色,可以称为音乐的“显性”特征,而不具有此种特点的音乐,在开展语言音乐学分析时,就需要拓展研究范畴。譬如,管建华《语言学转向与重识国乐》[54]中谈到中国音乐与语音、语法、句法、语义、语言中的哲学的关系,这些语言学涉及的方面,也应该纳入语言音乐学研究的范畴。由于不具有腔音化的特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隐性”特征。
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唱腔与唱词语音语调关系的研究,未来学界应扩展语言音乐学研究内容,如关于唱腔的节奏和唱词句读的关系、用于配乐的器乐与唱词语义的关系等,将研究范畴从音乐本体进一步扩充至音乐生态方面。
(三)研究方法待规范化
语言音乐学具有语言学和音乐学双重学科属性,目前语言音乐学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借用或者移植语言学和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已有成果证明以上几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近现代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将两学科研究方法完美融合,但是,借用的方法总是带有原生的局限性和偏向性,这些方法在分析某一具体对象时有效,在更换研究对象,或者将研究对象扩展为某一文化区或文化层时,这些研究方法的普适性还无法产生让人信服的结果。同时,借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同一音乐事项开展研究,其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这都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问题,也是该学科研究方法待规范化的方面。
另外,语言音乐学在中国形成,总结提炼的研究方法更适用于开展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音乐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语言音乐学必然与国际接轨,因此,语言音乐学在向外输出的同时,需要考量研究方法能否适用于国外音乐研究。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把语言音乐学的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从《尚书·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中提及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再到近代赵元任开创五度标调法的萌芽时期;从杨荫浏在《语言音乐学讲稿》中提出“语言音乐学”学科概念,到此后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沈洽《音腔论》中主要关注语言与音乐关系的语言音乐学形成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的语言音乐学多元发展期,钱茸提出“民族语言音乐学”的学科构想,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也逐步开始涉足语言音乐学研究。从语言音乐学学术发展脉络来看,第一,目前汉语言音乐研究成果斐然,和汉语相关的音乐研究,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均为我国语言音乐研究的主流。其中,现代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无不融合了与音乐的诸多关系。另外,各方言区语言音乐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多民族语言音乐的研究尚需深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语言与音乐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有效倡导,促成了一大批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均为前沿的研究成果。
纵观语言音乐学发展近60年,其研究方法从最初音韵学的声韵调分析法到其与音位学分析法有机结合,再发展到“双六选点”,研究范畴也从单一走向多元。语言音乐学虽发展较为滞后,但仍有一代代学者在漫漫长路上砥砺前行。亟待解决的是,语言音乐学的发展仍缺乏体系化的构建,研究范畴、研究视角有待多元,研究方法有待规范。笔者提出对于语言音乐学实践经验的反思以供学界诸友参考,同时亦可看出:语言音乐学的研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深耕,研究空间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