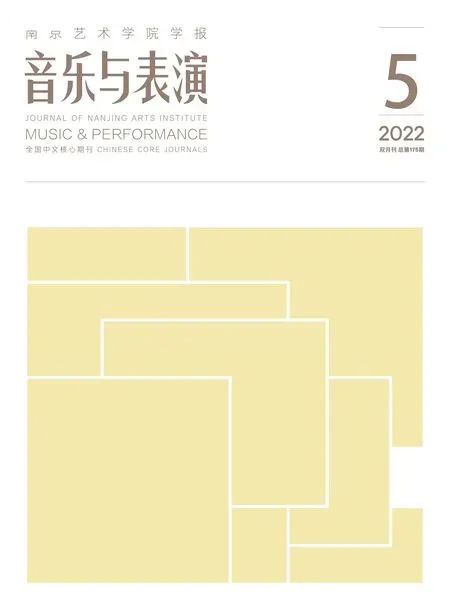中国现代声乐艺术发展述论(1919—1949)①
张 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210038)
冯效刚(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725000)
中国歌唱艺术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先哲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歌唱艺术高度重视,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典籍还是传说中,均不乏对歌唱艺术的描述,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韩娥)、“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秦青),都是对先秦时期演唱翘楚的记述。在中国歌唱艺术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朝历代均人才倍出[1]②如有文记载,我国盛唐时期的著名歌唱家有许和子、张红红、刘采春、周德华、李龟年等。,优秀的代表人物不胜枚举。中国历代艺术家注重演唱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演唱技巧和表演观念,如蕴涵在中国传统《唱论》中的“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等,均代表着中国声乐歌唱艺术的追求。然而在近代以前,中国歌唱艺术主要是以戏曲(京—昆)和蕴藏在民间的传统说唱艺术为主。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歌唱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走进了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里程。
中国音乐文化向来注重内在的风格与神韵。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根深叶茂,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则更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艺术都属于时代的艺术,任何艺术也都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印记和时代特征。[2]现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新趋向是“中西融合”观念的产物,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之路,体现出融汇中西、兼收并蓄的特质,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方法和表演艺术风格。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是百年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诚然,“凡是音乐表演,总是有某种理论观念和美学意识在起作用的”[3]。作为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其在经过自身探索与成型、积累与繁荣、成熟与高峰的历程之后,更是有着其独具魅力的审美特征。因此,对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纵向”梳理与总结,归纳与反思,将会使当代学者更清楚地了解我国丰富的历史音乐文化,力求对当下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自20世纪初在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表演艺术的形式,另一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在其表现形式和相关审美理念上,继承保存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美学的重要成分,又融入了西方戏剧表演美学的一些新元素。从而在满足中国当代“受众”审美取向的同时,又不断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为此,笔者将这些产生于20世纪初、借鉴来自欧洲的“新生”演唱界定为“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因为在这种新唱法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歌唱艺术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里程,今天已成为中国音乐表演舞台上声乐艺术的主流。如西洋歌剧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嬗变出中国民族歌剧唱法,中国艺术歌曲产生了独特的演唱方式(如中国古诗词歌曲、戏歌及城市小调)等,这些都对现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早期美声唱法融汇中西的努力
20世纪的现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运用舶来自西方歌剧的“美声唱法”(意大利文:Bell canto)演唱中国艺术歌曲和中国民族歌剧,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广泛吸收中国音乐元素,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声乐演唱风格。
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缘起自20世纪初,伴随着沿海“口岸”的开放以及“租界”的建立,一批批欧洲艺术家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歌剧和艺术歌曲等声乐表演艺术。在欧洲声乐艺术刚刚走进中华大地之时,由于西方美声唱法在中国“涉世尚浅”,有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弊端”[2],遭到不少非议。然而我们也看到,第一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在借鉴和学习美声唱法时,已经关注到了大众接受的问题。
第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掌握了欧洲歌唱方法的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活跃在大江南北的音乐舞台上,形成了中国声乐艺术领域第一代表演艺术群体。其中,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可谓“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地位以及对中国当代声乐艺术发展的历史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他们在演唱中“融汇中西”的努力。
周淑安①周淑安(1894年5月4日—1974年1月5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后来的喻宜萱、郎毓秀、张权均曾受教于她。是我国最早留美学习声乐表演艺术的音乐家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研究欧洲传统声乐表演艺术的音乐教育家之一。周淑安在舞台艺术实践中发现,演唱中国歌曲时“吐音咬字”有不同于外国歌曲的地方,因此在声乐教学中十分强调这一点。廖辅叔先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周淑安教的学生普遍“吐字”十分清楚,“吐音咬字一丝不苟”已然成为她的学生的一个共同优点。[4]可见,“以字行腔”已成为周淑安坚持的一个声乐教学原则。
应尚能②应尚能(1902年2月25日—1973年11月22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1930年代初即开始在上海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其演唱曲目以中外艺术歌曲为主。是中国最早研究与介绍欧洲传统声乐表演艺术的歌唱家之一。他的演唱风格严谨朴实,声音丰满柔韧,富于抒情性。在他总结其一生演唱经验所得的《我的声乐经验》[5]《以字行腔》[6]等论著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歌曲演唱中的“字—声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他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赵梅伯③赵梅伯(1905年—1999年11月19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声乐史”。1932年,他被比利时全国无线电台广播音乐会聘请为长期独唱演员,中国歌曲第一次随着比利时无线电台播到欧洲各国,欧洲报评言及:广大听众很意外惊喜地发现了中国民歌,尤其是认识了可爱的中国,艺术美的中国。他1936年回国,受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校长之聘,任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主任,郎毓秀、葛朝祉、魏秀娥、黄钟鸣、伍芙蓉等都是他的首期学生。早年曾就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是第一个在西方世界演唱欧洲古典、浪漫歌曲与中国近代歌曲的中国人,第一个在欧洲歌坛上为中国人夺得歌唱头奖的声乐表演艺术家。1930年代,赵梅伯在美国演唱了中国民歌《老渔翁》《凤阳花鼓》,成为第一个将中国民歌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声乐艺术家。[7]当时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报评论道:赵梅伯的演唱“有美丽的歌声,东方清幽的音色,表情细致,技术卓越,这是一位突出的学人歌者,将我们带到神秘雅静的世界,没有我们的瘴气、庸俗与沉重。”[8]他曾出版《唱歌的艺术》等相关声乐著述。[9]
从对以上三位第一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歌唱(或教学)追求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演唱和教学观念凸显出对“字”“声”关系的关注,体现出当时声乐表演艺术中“融汇中西”的理念。
早期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号称“四大名旦”的黄友葵、管夫人(喻宜萱)、周小燕和郎毓秀。
黄友葵④黄友葵(1908年4月3日—1990年9月1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包括著名歌唱家魏启贤、臧玉琰、孙家馨,以及方应暄、王萃年、汤爱民等。作为我国首批留学国外学习声乐的音乐家之一,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亨廷顿大学音乐系。同年9月踏上归国之途,在东吴大学任教。1937年,黄友葵在中国古装歌剧《柳娘》⑤《柳娘》以《聊斋志异》为题材创作,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该剧的男主角由著名歌唱家斯义桂担任。中担任女主角,演出圆满成功,获得“中国第一女高音”的赞誉。黄友葵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她的代表作包括《远望姐妮下田来》等。从1938年起,黄友葵专心教书,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演出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声乐教育事业中,成为我国近现代声乐教育的开拓者之一⑥1945年,国立音乐学院迁址南京,黄友葵担任声乐系主任,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兼教声乐课。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黄友葵先生任音乐系教授兼声乐教研室主任。。黄友葵作为美声学派的声乐家,却在不断研究中国民族歌曲的演唱方法,探索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结合的路子。[10]
喻宜萱⑦喻宜萱(1909年9月6日—2008年1月8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从1961年起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她在声乐专业教学中,将《翻身道情》《纺绵花》《新疆好》等民歌和创作歌曲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努力吸取民族、民间声乐艺术的营养,先后组织完成了《中国独唱歌曲集》《中国声乐教学曲选》《外国歌曲选》等十余部声乐教材。作为20世纪著名的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不仅是美声唱法在中国的传播者之一,还是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发展的推动者。她的演唱风格热情奔放、朴素严谨,声音圆润洪亮,色彩浓郁。喻宜萱注重恰切且又能够表现不同声乐作品的艺术风格,她所演唱的声乐作品曲目中外兼蓄,尤其是对现代创作歌曲和民间艺术歌曲的演绎,这也正是她能够把《虹彩妹妹》《小黄鹂鸟》《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牧羊姑娘》等经典的中国歌曲尤其是民歌唱红中华大地的原因。喻宜萱认为:“一个中国声乐演员,应当提倡唱中国歌曲,尤其是民歌。”[11]
周小燕①周小燕(1917年8月17日—2016年3月4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早在1930年代就运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如《长城谣》《红豆词》《美酒美人》《春晓》《饮酒歌》等,被誉为“中国的夜莺”。她的演唱不仅展示了高超娴熟的歌唱技巧,而且使中国声乐演唱的方向更加明晰。周小燕的声乐艺术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更是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内部各体系发展路径的研究方向。[12]
郎毓秀②郎毓秀(1918年11月4日—2012年7月7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撰写与翻译的学术著作有《卡鲁索的发声方法——嗓音的科学培育》《伊丽莎白·舒曼的教学》《西洋艺术歌曲二十首》《歌唱学习手册》《美声学派的原理和实践》等。因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被声乐界誉为“中国四大女高音”之一。她演唱的代表性中国曲目包括《满园春色》《乡愁》《早行乐》《天伦》《鸾凤和鸣》《飘零的落花》《蝶恋花》《杯酒高歌》《雪花》《大军进行曲》《月佬佬》《教我如何不想他》《太阳之光》等。郎毓秀在1930年代陆陆续续为“百代”唱片公司录下了《飘零的落花》《杯酒高歌》《满园春色》《乡愁》《早行乐》等二三十张唱片,曾风行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地区。她曾经提出:学美声的也应该扎根民族唱法,向民间学习。郎毓秀一生坚持这种演唱理念。喻宜萱曾在1980年代撰文赞赏道:“她的演唱仍不失音色的优美纯净,音质的柔和饱满。她声音运用自如、上下统一,处理作品细致、深刻,表达情感发自肺腑,形之于色却并不流于造作,她的演唱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13]
在以上第一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们的努力下,源自西方的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在1949年前已经有了一些发展,这种新声乐表演艺术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光彩绽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文化进程中发挥了有目共睹的巨大作用。
早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还有不少,其中一部分一方面系统学习美声唱法,同时注重演唱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声乐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蔡绍序和朱崇懋。
蔡绍序③蔡绍序(1909年1月19日—1974年2月26日),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在中国声乐界男高音领域颇有影响。嗓音圆润清亮,演唱时感情质朴亲切。他的演唱始终坚持科学的发声方法,强调磨平声区间的界限,将流畅的中声区和漂亮的高音有机统一起来,认为这是关系到声乐艺术成败的关键之一。他认为中国歌唱家必须唱好富有民族特色的声乐作品,他对四川风味歌曲的处理尤有独到之处。他演唱的川、贵民歌《槐花几时开》《太阳出来喜洋洋》《葫豆花开》《好久没到这方来》《想亲娘》《李友松》等堪称一绝,被评论为“声情并茂,色彩鲜明,洋溢着泥土的朴实、芳香” ;“在艺术上有所提高而不失原来风格、特点,是一种创造”。[14]早在1930年代,他的演唱就被灌制成唱片发行。
朱崇懋④朱崇懋(1922年—2000年10月11日),著名歌唱家,20岁就举行了首次独唱音乐会。以学习西欧传统声乐唱法为基础,同时向我国民族民间传统声乐艺术学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抒情男高音声乐演唱艺术风格。他的演唱吐字清晰,含蓄内在、音色甜美,细腻深情,特别是在高声区的“弱音控制”和“延长”等方面的处理分外动人。由他演唱的《金瓶似的小山上》《草原之夜》等多首优美抒情的声乐艺术歌曲风靡几代人,至今仍广为人们学唱。
美声唱法作为一种西方演唱体系,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进程中,虽然历经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期,但它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声乐表演艺术亦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首先,抗战结束仅仅数年,转移到“大后方”的文化艺术机构尚处于“回迁”之中,还未安定下来就遇上解放战争。动荡之下,大城市中的艺术音乐活动寥寥,许多崭露头角的歌唱家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高芝兰、张权是其中的代表。其次,在延安成长起来的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家在“延安保卫战”中分散到各地(以东北为多),此时也谈不上继续提高。
二、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乡土化”进程
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璀璨音乐文化的基石,它渊源流长、久唱不衰,一直“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它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受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提炼,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臻完美”[15]。中国民歌对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影响巨大,在其发展里程中,民歌演唱艺术的影响不容小觑,“乡土化”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发展的一个亮点。
(一)中国民歌演唱艺术的影响
作为以历史文化、社会观念、生活方式及民俗风情等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民歌,其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一定社会个体、群体与相关音乐行为等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其中的特质与变化维度,恰恰亦是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切实性、动态性源流与生存样式和传播和发展规律的重要条件之一。[16]20世纪以来,中国民歌犹如一朵“乡野之花”流变至今,不少在今天称之为“原生态”的民歌演唱者活跃在中华大地的各个地方,他们对中国民歌演唱艺术的贡献可以、并应当彪炳史册。
冀东民歌演唱家曹玉俭①曹玉俭(1901—1977),民歌手。他参加过大蒲河村的民间文艺组织“海乐班”“同乐班”的演出活动,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演唱二人转和乐亭大鼓。他对民歌的卷舌音、嘟噜音、颤喉音、喉鼻音、控制音、补字音、滑音、装饰音、重尾音等环节的演唱技巧运用自如,尤以准确把握、巧妙利用卷舌音、嘟噜音、颤喉音见长。在19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慕名来请曹玉俭去教冀东民歌,他先后在天津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上海音乐学院、杭州歌舞团、兰州歌舞团、河北歌舞团等专业院校、团体传授冀东民歌。,据笔者所知,是目前我国20世纪见诸文字记录、出生最早的一位民歌手。他从13岁起开始学习扭秧歌和演唱民歌,从大蒲河的常平、薛家营的张成等民歌老艺人那里学会了不少传唱下来的民歌,他根据自己的嗓音对这些民歌的演唱进行再创作,最终形成了抒情味极足的独特演唱风格而享誉乡里。他在演唱民歌的过程中,擅长根据语言特点对歌词进行体味、理解,经过不断磨练,渐渐掌握了很高的民歌演唱技巧,曹玉俭的演唱炉火纯青,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演唱冀东民歌近50年,演唱的民歌字正腔圆,咬字行腔非常讲究,被其学生形容为:吐字如吐钉,行腔如行云;快有字儿,慢有味儿,悲伤挂叹气;短腔亮字,长腔亮声等。他的演唱不仅感情充沛、细致入微,而且地方风味极足,并做到了:情引歌声出,气送歌声走;喜怒悲欢传双目,五体皆表口中词。这使得他的演唱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他独特的声乐演唱艺术风格概括总结起来说,就是字正腔圆、节奏准确,声音嘹亮婉转、感情充沛。其鲜明的艺术表演形象赢得了较多赞誉,强烈的歌唱艺术感染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如他演唱的《茉莉花》《绣灯笼》《正对花》《反对花》《拣棉花》等20多首昌黎民歌独具一格,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他演唱的主要民歌代表作还有《红月娥》《铺地锦》《十女夸夫》《货郎标》等。曹玉俭视冀东民歌为自己的生命,一直唱民歌、学民歌、编民歌、教民歌。[17]
中国民歌演唱艺术实质性的发展是从陕北起步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对民歌演唱艺术的贡献人所共知。来自陕北的农民歌手李有源②李有源(1903年2月23日—1955年5月10日),农民歌手。1952年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代表会议,获得了奖旗、奖章和奖金。出身贫寒,幼年曾利用去县城高小打工的机会,取得旁听的资格。他主动给学校的教师唱民歌、唱秧歌,深得大家的喜爱。1942年冬,他采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唱出《东方红》,被誉为“人民歌手”。
1940年代,陕北有一个天才的民歌演唱者张天恩③张天恩(1910—1969),陕北民歌手,民间艺术家(秧歌、快板高手)。1955年,张天恩随陕北民间艺术团到北京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的接见,文化部授予他“民间文艺天才”称号。很可惜,张天恩这位中国民歌歌坛上的“天才”过早离世,一颗光辉闪耀的明星陨落了。,他被吕骥誉之为“陕北民歌大师”。张天恩的青少年时期以运货(驮盐、送炭)为生,赶着牲口走三边、下柳林,沿路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激发了他的灵感,编唱、创作了许多民歌。如《赶牲灵》《白面馍馍虱点点》《十劝劝的人儿》等。特别是《赶牲灵》曾被誉为“中国民歌之首”。张天恩也是秧歌能手,每年边区春节“闹社火”都少不了他,他的演唱和表演独树一帜,《跑旱船》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作品。张天恩是陕北民歌的无私推广者和热心传播者。后来对陕北民歌创作和研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白秉权④白秉权(1930年12月—2010年5月),女,陕西省歌舞团独唱演员。说,她就是在1951年向张天恩学了《赶牲灵》和《跑旱船》这两首民歌。[18]
这些陕北农民歌手的表演可谓是积极的艺术创作,对当时延安的秧歌剧和新秧歌运动影响巨大。陕北民歌无论体裁、曲调,还是唱法,均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1938年至1947年间,延安“鲁艺”师生深入民间,先后整理出版了《绥远民歌集》(吕骥整理)、《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二集》(李焕之、李元庆、杜矢甲、马可等编)、《秧歌曲选》(李焕之、刘炽、张鲁等编)、《陕北民歌选》(鲁艺师生集体编)、《陕北民歌选》(何其芳、张松如编)等民歌曲集[19]。陕北民歌的演唱也直接影响到民族歌剧的演唱,我国第一代民族歌剧演唱家李波、王大化、王昆等都是在陕北民歌滋润下成长起来的。
20世纪40年代,一部分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歌唱家汇聚到延安,她们将美声唱法带到那里,一批演唱“新歌剧”的声乐表演艺术家也受到影响。如在延安“鲁艺”颇有声誉的唐荣枚⑤唐荣枚(1918年1月3日—2014年1月20日),湖南长沙人。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曾被誉为“延安夜莺”。,曾在国立音乐院受过系统的美声唱法训练。孟于,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学唱的也是西洋唱法。在“秧歌运动中”,她在原来唱法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了陕北民歌、眉鄠、秦腔等民歌、戏曲的演唱特点,在唱法上有所改变。[20]
唐荣枚到了延安以后决心转变歌风,学习民间唱法。此后,她演唱的《翻身道情》《三十里铺》《歌唱毛泽东》《信天游》《种瓜人李宏泰》《掐蒜苔》等民歌风格浓郁,令人耳目一新。[21]
李波⑥李波,1918年出生于河北曲阳县南下关,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演唱过《翻身道情》《妇女自由歌》等歌曲。1941年进入延安鲁艺学习声乐,1943年与王大化⑦王大化(1919年5月16日—1946年12月21日)又名端木炎,山东潍坊市人,中国话剧演员(曾在苏联名剧《马门教授》里扮演老科学家马门洛克医生)、木刻家,年青的人民艺术家。一起演出《拥军花鼓》受到欢迎。但李波的演唱艺术多为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唱法,唱、白相间,唱腔显得极为朴实真挚。
这一时期在解放区产生的著名歌唱家中,王昆①王昆(1925年—2014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唐县,歌剧表演艺术家。1945年,出演共产党领导下创作的第一部歌剧《白毛女》中的女主角喜儿。1982年,任东方歌舞团艺委会主任、东方歌舞团团长。1989年,荣获巴基斯坦总统授予的“卓越明星”勋章。的演唱可谓出类拔萃。她虽然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但她在延安时期的表演根植于民族民间传统的“真声”演唱方法,同时又吸收了系列科学的演唱和发声方法,具有音域宽广、声音辽阔、深情并茂的艺术品质,再加上她的舞台表演和身段肢体语言的传达等“二度创作”,均与传统的民族民间艺人的艺术表现,形成了强烈对比。
(二)“山歌社”的民歌推广活动
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时中国民歌就开始受到关注,但中国民歌的演唱艺术尚未引起“新文化人”的重视。直到1940年代,“山歌社”(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音乐社团)在重庆为推动中国民歌演唱艺术进行了积极的活动②华中师范大学戴俊超在硕士学位论文《国立音乐院“山歌社”音乐活动述论》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22],他们不仅倡导、策划、组织、参与了多次丰富多彩的民歌演唱会,部分山歌社成员在声乐表演理论方面的新颖思索也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据载,从1945年4月23日起,至1947年2月4日,“山歌社”在当时的重庆举办的较为正式的“民歌演唱会”有8次;在他们的推动下,“把民歌搬上音乐会的舞台,一时蔚然成风”。[23]“在演唱会的后续几次排练以及表演过程中所出现的拥挤场面,在音乐院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民间野乐,走进了庄严而又Classic的音乐院里,自然算是奇迹了。可是它是民间的,人们都偏爱它。几次的试唱演唱会中,都告客满,六七百听众,一定可以找到好几位百十里外的远地来客。”[22]并且,“山歌社”应邀为中央广播电台录制“民歌广播节目”(持续六周,一共播放近百首民歌)。不仅如此,“山歌社”还在各地开展民歌演唱活动,仅1946年7月间,社员潘名挥、郭乃安、郭杰、张文纲、黄克等在贵州的遵义和盘县,香港、广西的合浦、甘肃的油矿局组织过一系列类似活动。[22]
“山歌社”的努力得到积极响应,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也纷纷将民歌演唱融入自己的音乐会,斯义桂(男低音歌唱家)、胡然和伍正谦(男高音歌唱家)、黄友葵和喻宜萱(女高音歌唱家)先后登台演唱民歌。“黄友葵教授在民歌演唱会之后,热情地辅导她的学生黄凛演唱民歌,使得其演唱在后来地民歌演唱会上得到好评。”[22]其后,学生毕业音乐会必唱民歌成为“不成文的约定”,如何陵、叶理平的毕业演唱会(1947年4月27日)上,“听众拥满会堂,情况空前热烈,节目均甚精彩,民歌大受欢迎”[22]。谢功成在回忆国立音乐院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时的民歌成了斗争的武器,有的民歌在这种场合演唱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如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叶理平参加的每一个晚会都唱,都收到热烈的欢迎,因为这时“遥远的地方”己变成人们对解放区的向往了。”[22]叶理平在演唱时“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咬字准确,在吐字上需要夸大一些;一是感情方面,目前我们不可能身历其境去体验,我是从曲调里去体会的,更多地了解词意会更好一些”[22]。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山歌社”成员重视探讨“用什么声音、什么方法来演唱民歌”的问题。储声虹③储声虹(1920—2012),出生于贵阳,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社会活动家。在《山歌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谈民歌演唱》的文章(署名“小粗”),总结了这几次民歌演唱会的经验,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民歌演唱的几点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首先是“口语化”;其次,演唱民歌要注意“真、假声的运用”;第三,根据中文的“声韵”需要借助“滑音”的演唱方法;第四,要注意民歌里的“衬字与衬腔”;第五,呼吸问题。文章最后指出:“民歌演唱……要想感动听众”,“首先……你要他们听得清你的吐字”,“我们演唱民歌,不是老百姓唱民歌,但是,我们是为老百姓唱民歌。尽管我们采用西洋发声方法去演唱,但我们一定得使他们听得懂、感到民歌的亲切、使他们乐于接受。”“我们还不能清高,还得向老百姓学习,研究他们演唱民歌中声音的运用、表现手法。民歌演唱的道路……我们要一边演唱、一边研究,从不断的实践中找出其理论来。”[24]
综合起来看,这篇文章强调了当时“山歌社”成员对民歌演唱的一致看法,认为只有在咬字吐字上花功夫,从表现民歌的情感出发体会作品的风格,才能产生打动人的演唱。这些关于民歌表演理论的探讨,直接推动了民歌的传播,使得他们的民歌演唱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范例[22],如:伍正谦1946年5月间在上海的演唱会上,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24];在南京的音乐会上又首演了江定仙根据四川康定地区民歌改编的《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喻宜萱将其“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出了国门。然后又由上海的大中华唱片厂将此歌灌制成唱片广为流传”[25]。《康定情歌》的广泛传播更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例。[22]
结 语
诚然,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共时性,造就了植根于这种文化土壤中所产生的文化文本的复杂状态。1919—1949的30年间,虽然中国的新声乐表演艺术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尚未形成气候,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突飞猛进是在1949—1977年间,且从分庭抗礼走向了融合,针对中国声乐表演艺术这一时期相关内容的研究,将是笔者接下来所关注的重点。
当前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更应该向本体回归,要充分吸收中国多民族民歌、传统戏曲、说唱等表演艺术之优长,强化改革;科学借鉴古今中外演剧艺术中的一切有利因素,融合创新;以满足广大“受众”的审美情趣,这也理应是当下中国声乐表演艺术构思及总体把握的美学原则。因此,对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历史传统,同时也离不开对全球范围内世界文化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