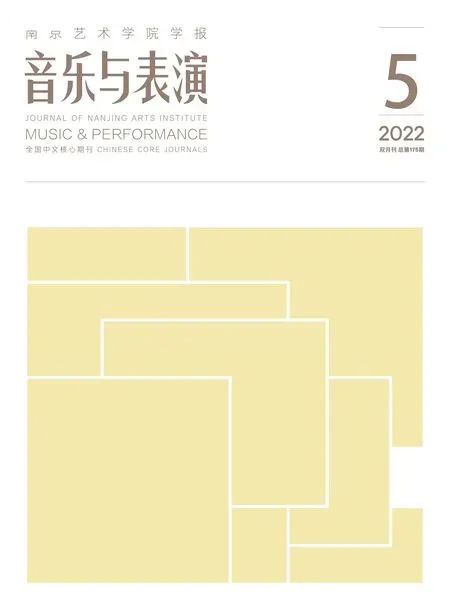音乐表演焦虑的成因及其干预①
张 洋(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王勇慧(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人的“焦虑”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是伴随着人的生理、心理及其精神意识变化而出现的心理情绪现象。在艺术表演领域(特别是音乐表演领域),对于“焦虑”的研究似乎从未中断过。受苏联心理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往研究中常把处在音乐学习和表演中的“焦虑”状态看作“紧张”或“怯场”的表现,以易感性的临场表现作为观察问题产生的切入点,较少关注“焦虑心理”形成的现象本质,以及人与外物关系相互影响的、较为复杂的综合性因素。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从人的“焦虑”产生及其影响等层面进行了大量实验分析,得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结论,本文借此研究成果及其相关理论,就音乐学习与表演中的“焦虑”问题,再做探讨。
音乐表演焦虑(Music performance anxiety,简称为MPA),是指与音乐表演相关的显著和持续的心理焦虑或忧虑体验,一般通过音乐学习或表演者的情感、认知、躯体症状和行为症状的组合表现出来。[1]
音乐表演焦虑在音乐学习或表演者的身上不同程度地都会有所体现。不同的是,有人会因此而影响学习或表演进程,甚至导致事业走向失败,而有人则不会受太多的影响,有人通过学习或表演实践锻炼,基本上可以把控MPA的出现或影响,而有人终其一生都很难克服其对自己的深刻影响,极端者甚至因此而放弃继续学习或者由此而改变职业道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从事音乐学习和表演者中的MPA的发生率并不十分确定,有研究认为其比率介于15%至25%之间。[2]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比率了,意味着在从事音乐学习和表演的人群中有15%—25%的人不断遭受MPA的影响,反映出对其进行干预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音乐表演焦虑的特征
心理学研究中的“焦虑(anxiety)”概念是指个体在感受到潜在胁迫时, 在主观上出现的紧张、忧虑、烦恼等情绪,同时出现自主神经系统活动亢进的现象。[3]认识这一问题出现的前提是要确定焦虑因何而来。过于羞怯、能力不足、不习惯暴露在众人面前等有可能是其产生焦虑的前因。但针对音乐表演行为,无论是学习或实践展示过程中,则可能因其“作业”准备不足或心理预期过高而出现被“胁迫”,从而导致心理焦虑出现,其结果会对音乐学习或表演行为产生不良影响。Wesner, Noyes和Davis[4]认为,无论演出者的音乐能力、教育程度和准备情况如何,音乐表演焦虑者都会担心在观众面前表演失败。越担心问题就越多,过分的MPA影响会把正常的音乐表演行为引向毁灭。即使成熟的音乐家,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这样的错误。近年来,音乐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音乐表演焦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实际表演过程中。有研究表明,参与音乐活动的人可能会在人群面前表现出对表演和成功的焦虑。[5]音乐表演焦虑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演者认为他们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必须“完美”,否则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为此他们表现出焦虑不安的情绪状态。[6]
2.表演期间出现呼吸困难、颤抖或心悸等躯体焦虑症状。[7]
3.表演者希望能够推迟、取消或者避免参加表演活动。[8]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与之对应的是当事者过高的心理期待造成的心理胁迫;第二个方面的情况是当事者因表演时的高度紧张产生心理胁迫后的直接生理反应;第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当事者难于面对表演现场而出现的完全消极的心理躲避暗示。事实上,这三种情况对于高焦虑者而言并非孤立存在的,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并存的,只不过不同的人在某一方面表现的比较突出而已。
二、音乐表演焦虑的成因
音乐表演焦虑的成因主要涉及遗传、认知和社交障碍三个方面。
(一)遗传因素
有关遗传因素作用于焦虑产生的影响,有学者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9]其中,所谓“状态焦虑”是指目前环境诱发或引起的暂时性的焦虑水平上升。这种焦虑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当事者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不能迅速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而引发。而“特质焦虑”则是指由于个体的气质性差异(即某些个体原先就具备焦虑气质,有些个体缺少或没有焦虑气质),造成其在焦虑易感性方面的不同。Domschke和Dannlowski[10]认为,对于特质焦虑的个体而言,其基因和神经生理指标是可以追溯的。
除特质焦虑个体说明了遗传因素对于MPA的作用外,还有相关研究证实了MPA病因中存在遗传成分。有研究考察了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基因与个体儿童时期的感受压抑、羞怯以及尴尬经历之间有关。[11]
(二)认知因素
相比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往往是由个体的认知因素而引起的。我们知道,焦虑并非总是产生负能量,适度的焦虑对于个体的生存进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它可带来学习的紧迫感,可促进积极心态的自我提升要求等。但不当的、过度的、错误的焦虑,则会严重破坏个体的生活状态,这些焦虑往往由个体偏狭、固执的认知因素所引发。过高估量自己的认识,容易丧失客观;偏狭的认识理解,容易规避善意的合理建议等。由于认知因素的缺陷和不足,使得焦虑障碍患者在对社交信息的加工和社会感知方面表现出能力不够。[12]这种不够往往是隐形的、自己很难感知到的,而与之交流者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与陌生人进行交流时,其动机强度和焦虑水平之间呈负相关,[13][14]换言之,因焦虑水平的上升导致了动机强度的减弱。他们也不能与交谈对象进行善意的眼神交流,在语言沟通上容易自持己见、不愿相互理解、且越行越远,最终使之相互交流的语境变得支离破碎、无法沟通。
状态焦虑意味着通常的MPA水平和自我感知的表现质量之间的联系可能仅仅依赖于情境因素,例如是否有观众或者是否需要在公众面前表演。[15]状态焦虑者往往表现出难以化解情境因素方面的困难,而非状态焦虑者并不会因情境因素的改变而弱化自我感知的表现质量。
(三)社交障碍
音乐表演焦虑者常常表现出在社交技能方面的障碍和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焦虑者在与他人交往时容易缺失信心, 低估自己的社交表现,倾向于预期负面结果(例如声乐演唱时某个困难高音的处理,器乐表演时某个快速段落的演奏等)的发生[16]。与之相反,非焦虑者与他人交往不会缺失信心,能够把个人认知和意愿较好地表达出来,倾向于预期正面结果。即使出现不好的结果,他们也会很快寻找原因并做出自我安慰和调适。
Leary和Downs认为,高焦虑者逃避社会交际是为了防止自尊受到伤害或发生潜在的人际冲突。[17]高焦虑者在对人际交往进行信息加工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高焦虑者往往自信心不足,更容易听从外界信息(如权威信息或他人意见)的影响,表现出更多的权力依从或依从他人;[18]2.高焦虑者往往由于低自尊以及负面的自我形象,导致其社会竞争动机较弱;[19]3.高焦虑者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差。[20]
音乐表演焦虑被一些研究者归为“亚型社交焦虑障碍”[8][11],并且认为社交焦虑障碍是MPA的重要预测因素,[21]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和MPA特征显著的音乐家的认知加工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加工在认知、注意力和记忆力水平上的干扰起着重要作用,促成MPA的持续和恶化。[22][23]
MPA特征显著的音乐家在公共场合进行表演时,常常伴随着持久和强烈的焦虑。[11]有人会将这种焦虑贯穿到表演活动的始终,以高度的紧张状态伴随演出的整个过程,直到结束才能够释然。但也有人一旦进入演奏状态,因其音乐情绪的感染而瞬间忘却焦虑。有经验的音乐家规避焦虑的最有效办法,一般是选择安静的一角,通过调整气息、摒弃杂念、进入表演状态来应对;而另一些音乐家则刻意转移注意力,尽量使自己松弛下来,以轻松的姿态进入表演过程。
在阿普尔鲍姆撰写的《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家谈演奏》中,介绍19世纪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古别列克(Kubelik),他焦急不安地对我说‘帮帮我的忙吧!今天晚上我有一场音乐会,我已经练了十二个小时,手指都练出血来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他那天晚上的演出技术是完美的,然而,在音乐上却是一张白纸!”[24]
联系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克莱斯勒的这段回忆,意在强调音乐练习与音乐思考谁显得更重要一些。无疑,在天才的音乐家克莱斯勒眼里,后者的位置更为突出。他认为:“技巧实际上是一种脑力活动。……从目前大家所谓的‘练习’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练习过。我只有在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才练习。你思考一段音乐,并且明确怎样去演奏它,这是最重要的。”[24]
但对于古别列克来说却完全不是一回事,他需要通过长时间的、不间断的练习才能达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以增加自信心并克服焦躁的心理。在这些著名艺术家中虽为个例,但并非鲜见。而对于一些最初走上艺术舞台的实践者来说,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艺术实践课程的设置,并不仅仅是使学习者在实践中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其具备音乐家所达到艺术心理的健全与成熟。
三、音乐表演焦虑的干预
(一)PER模型
Fehm,Schneider和Hoyer的研究发现,社交情境比其他恐惧情境更容易被负面的反省所影响。[25]其研究结果表明,事后反省(post-eventrumination,简称PER)①PER是指个体对近期社交活动行为进行思考和反省的过程,包括自我评价和与活动行为相关的其他因素的思考和反省。[26]是引发MPA的一个重要方面,关注PER的过程能够对MPA起到干预作用。“事后反省”是对近期的事情的不断回顾,这个回顾带有自我评价意味,往往包含正面的肯定和负面的检讨,甚至有人为此陷入深深的后悔或自我谴责中。
Abbott和Rapee重点分析了社交恐惧症患者和健康参与者,在发表演讲任务一周后的正负性PER表现。他们发现两组负性PER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正性PER之间没有显著差异。[27]Kocovski等人发现社交焦虑低的人,在面对社交任务时(如一周后将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比社交焦虑高的人表现出更积极的想法。[28]由于正负性PER可能共存,所以在研究PER和MPA之间的关系时应考虑两种形式的PER(正、负性)。
这两组认识的切入点存在一定差异,前者观察的是事后的易焦虑者与非焦虑者的反思情景,在负性指标上差异明显,说明易焦虑者不仅在事前受焦虑心理影响,事后同样更容易陷入对行为过去式的思考,而非焦虑者的心理情形则完全相反。而后者着重于对事前的心理观察,通过比对发现非焦虑者或者社交焦虑低的人,有着遇事比较乐观、向上的趋向,正是由于其遇事善于往好的、积极的一面思考的行为,反而激发了面对事物向上努力的正性能量的堆积,从而获得身心的全面放松和积极的身心间的协调配合。
Nielsen等人认为,高焦虑的音乐专业学生在独奏表演10分钟后比低焦虑的音乐专业学生表现出更加负面和较少正面的PER。[15]这样的结论,即使在经验的层面,也很容易在日常的音乐学习和演出实践中观察到:往往低焦虑者更愿意模糊掉实际演奏中出现的小错误,而急于在事后放松、庆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肯定);而高焦虑者短时间内总是习惯把凝重聚于心头,不放过对自己出现错误的内省和谴责,也更关乎别人的评价态度。这一现象支持了Clark和Wells以及Rapee和Heimberg的社交焦虑模型:在紧张的社交事件后,与比较低或没有社交焦虑的个体相比较,社交焦虑的人往往会进行更消极的反思。[22][23]
由于主观表现评价在正负性PER机制中均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较高的主观表现评价与较低的负性PER相关,另一方面较高的主观表现评价也与较高的正性PER相关。
Blackie和Kocovski在一项演讲任务后对参与者的PER进行了评估,并将他们随机分为三组:反省、分心和控制组。[29]他们发现,演讲任务后的“分心”任务通过PER在第二次演讲任务前可以帮助减少预期焦虑。即在事后有效的时间段里,采用转移注意力、引发别的兴趣点等方法,可以降低事后反省的自我关注度。另一种降低负性PER的方法是使用建设性的自我指导技巧。正如Hildebrandt和Nübling所做的那样,他们为音乐演奏者及其指导教师开设了专门课程。[30][31]例如,直接面对解决MPA的策略,而不是过多地分析演奏、演唱时出现的专业问题。这种具有建设性的课程是有效的。它可以使学习者打开胸襟,活跃思维,通过一些有效的锻炼途径降低自己MPA强度。
MPA、主观表现评价与正负性PER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于表演、练习、排练等过程中。因此,在对音乐专业学生MPA进行干预时,在练习和排练时就应随时关注表演者的正负性PER与主观表现评价,使其能够涌现较高的正性PER或降低负性PER,形成较好的主观表现评价意识,从而降低MPA的发生概率。
(二)FER模型
FER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即面部情绪识别,通俗讲就是“察言观色”,这一点在社会行为和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要。“察言观色”往往决定着行为方向和对自我的评价。有大量来自焦虑障碍和FER之间关系调查的证据表明,焦虑症患者往往会更加关注带有威胁的、不赞同的面部表情以及消极的面部情绪。[32-35]导致出现FER的缺陷,是由于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准确或被扭曲所致,由此引发焦虑。[35-37]有关MPA的研究表明,与没有MPA的音乐家相比,存在FER缺陷的音乐家,具有更多的负面认知和悲观思维。[38][39]FER缺陷的音乐家在音乐实践活动中的期待值往往较高,但又怀疑自己的能力,需要从自身之外的他人态度中予以确认、肯定,并且常常误读或扭曲他人的面部信息,喜欢揣度别人面部表情后边是否隐含着不同的东西,从而加深了负面认知。Sabino等人的研究认为[40],一般来说,高MPA的音乐家具有较低的FER准确度,特别是对于高兴或欣喜的识别;高MPA者对恐惧面孔的错误认识比MPA低的音乐家更频繁。Brosschot,Pieper和Thayer[41]进一步认为,持久的不良认知(如担忧)可能会延长对压力源的生理反应,并导致个体的心身障碍(如躯体疾病、心血管疾病、睡眠质量差)。
FER作为个体社会行为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针对MPA的治疗中应充分考虑FER的相关因素。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原发的,比如天生性格上存在缺陷(性格内向、不喜欢与人交往);也可能是后天养成的,如成长经历中的精神压迫、精神损伤(长期寄人篱下、某次重大失误)以及不良的、习惯于负面的思维习惯等;也可能是先天、后天并存,如内向性的拘谨性格又遭遇不好的生存环境与条件等。
(三)CF模型
CF模型即条件恐惧模型,是用于考察各类焦虑和恐惧情绪的一种基本的实验研究模型。该模型可以用来解释音乐表演焦虑、考试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焦虑等多种焦虑情绪障碍。
条件恐惧(Conditioned fear),是指一个原本不具备引发个体情绪功能的中性刺激(此中性刺激称为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简称CS,如音乐会演出或者专业考试时的演奏、演唱等),常常伴随一个特定的厌恶或者恐惧刺激(无条件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简称US,如心跳加快、忘词、出汗、脸红、腿颤抖等)的出现,个体就在不知不觉中习得了对这个中性刺激的条件恐惧反应(表演时会出现心跳加快、忘词、出汗、脸红、腿颤抖等焦虑反应)。该模型表明,当条件刺激继续出现而恐怖或者厌恶刺激不再出现时(即表演时个体不再出现心跳加快、忘词、出汗、脸红、腿颤抖等焦虑反应),习得的条件恐惧反应就会逐渐消退或消失。“消退”代表着个体主动降低了CS-US间关系的强度,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这种适应性的变化因人而异。
有些研究者提出,个体之所以对CS产生厌恶或者恐惧情绪,是由于个体认为CS是US将要出现的信号,即个体者会根据以往经验,预感到表演时可能出现心跳加快、忘词、出汗、脸红、腿颤抖等焦虑反应。US会导致表演行为发生变形,轻者如情绪、速度上的张力异常;重者如瞬间的失忆、记忆阻断而不能持续进行表演。[42][43]
为了考察条件恐惧模型的干预效果,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辨别条件反应范式:在条件反应任务中设计两个CS(即CS+和CS-)。跟随US出现的,是CS+。CS+代表的是兴奋性条件作用(excitatory conditioning);不跟随US出现的,是CS- 。CS-代表的是抑制性条件作用(inhibitory conditioning)。这样,辨别条件反应就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对CS+和CS-所产生的条件反应的差异。[44]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对于音乐表演而言,在经历了同样的演出后,为什么有些个体产生了适应性的情绪反应,而另外一些人却形成了焦虑情绪障碍?Orr 等人认为:和正常个体相比,焦虑个体在习得阶段和消退阶段对CS+和CS-表现出更强的辨别条件恐惧反应。[45][46]该观点被称为条件恐惧增强理论。该理论认为,CS+代表着危险和恐怖情境,CS-代表着相对安全的情境。为了适应环境,个体会表现出应对适当恐惧的能力,以此来调动机体的资源应对CS+带来的刺激和威胁;同时,个体会加强CS-的抑制作用。在音乐表演时,演出者为了达到良好的演出效果,会调动自身的各种资源来抵制和应对CS+的出现。
在此列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予以佐证。某音乐学院招生中,有位考生因为临场紧张,导致把乐曲的再现段演奏错了。好在担任伴奏的老师有经验,随机应变配合着完成了演奏。该考生的成绩因此被扣了相应的分数。幸运的是,该考生进入了三试,由于现场考官人数减少,演奏曲目又是该考生最拿手的,结果他以非常出色的发挥完成了考试。该考生的整个考试过程呈现出典型的CS-自我干预的特征,其中不同考试场次的考官人数变动是影响CS+朝着弱向发展的原因,而考试次数的累加及不断适应则是该考生CS-作用上升的条件,由此构成了考生在三试演奏中以最佳的心态对CS+影响形成了较好的自我抑制力。
(四)发展可塑性理论
Moczek等人(2011)在研究中认为,发展可塑性是指个体本身就具有的、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发展以应对变化着的环境和条件的能力。这种发展的可塑性因人而异。[47]Belsky在研究中将个体发展可塑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不同的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敏感性不同,因而导致个体发展结果的不同。[48]这种对外围环境的敏感性不仅存在差异,并且在接受干预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这就引发了发展可塑性理论倾向于关注积极环境的讨论,也就是可干预的研究层面。基于发展可塑性理论,Belsky等人提出了:差别易感性(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模型;[48]Pluess、Manuck等人提出了:优势敏感性(vantage sensitivity)模型。[49][50]一般情况下,心理干预属于关注积极环境的应对方式。发展可塑性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具备某些特征的特定当事人更容易从心理干预中获益。
“差别易感性模型”是指有一些个体在积极环境中能够更获益,在消极环境中则更加容易受损。个体在积极环境中更获益的某些特征代表了差别易感性的“光明面(light side)”,个体在消极环境中更受损的某些特征标示了差别易感性的“黑暗面(dark side)”;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个体在积极环境中不能够更获益,在消极环境中也不容易受损。[51]差别易感性模型可以揭示个体所处的环境与其发展结果的相互关系。[51-53]
例如,在温暖家庭中成长或具有和睦师生关系的高差别易感性音乐学习与表演者,相对于同等条件下的低差别易感性音乐学习与表演者,可能发展出更高水平的表演技能和社交技能,从而较少出现音乐表演焦虑;如果高差别易感性音乐表演者成长于暴力家庭或师生关系紧张,相对于同等条件下的低差别易感性音乐表演者,可能导致表演技能和社交技能上的不足,从而产生更多的音乐表演焦虑。
世界著名钢琴家郎朗在回忆儿时的学琴情景时说过,其父亲对他的学琴管理基本上是“残酷的”甚至“暴力的”,甚至在过大年时都不允许他停止练琴休息一天。这种高压学习环境很难判定是积极或消极的,尤其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但却适应于天才音乐家郎朗这种性格的孩子,越是有压力越是往上抗争,并且在学习中和父亲的管教形成了一种正向的相互驱动力。换言之,差别易感性在郎朗那里总是趋向于“光明的一面”,而不是“黑暗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郎朗与生俱来的较为外向的、刚毅不服输的性格所决定。
“优势敏感性模型”是指有一些个体对其所处的积极环境能够给予更为敏感、积极的反应;其即使处在消极环境中也不容易受损。[53]例如,一个优秀的表演者,其在良好的场所(如音乐厅)能够自如地演出,其在不良场所(如混乱的餐厅)同样能够表现出优异的技能。日常音乐活动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演奏家不会过于在乎时间或场地的安排,也有一些音乐家在时间和场地的安排上不太愿意做出迁就和退让,严格坚守自己的习惯,才可能保证演出的质量。
除此之外,在对音乐表演焦虑进行干预时,还应避免“优势抵抗”(vantage resistance)现象的发生。所谓“优势抵抗”是指某些个体不能从积极的影响(事件、事例)中获益的倾向。例如,当看到成功者的表演时,不能认真或以咨询的态度分析其表演成功的原因,而是习惯于专注自己的失误或者失败。他们对问题的态度几乎全部是向内的,而不是建立在内外关联的基础上分析和认识,很容易就形成了“优势抵抗”的自我偏狭认知习惯。
结 语
“焦虑”是音乐学习与表演行为中的重要障碍之一,有其典型的特征与发生机理,并在音乐学习与表演者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克服并进行有效的干预,本文引介了西方心理学界近年来提出的四种重要模型,重点分析了各模型不同的认识侧重点,对于我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对焦虑心理的进一步观察和印证不无帮助意义。
事后反省、面部情绪识别、条件恐惧模型、发展可塑性四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音乐表演焦虑(MPA)进行有效干预。这些干预不仅只对音乐表演焦虑有效,同样适用于诸如体育竞技、演讲等带有表演性质的焦虑缓解。“事后反省”强调了MPA患者的自我负面评价,“面部表情识别”反映出MPA患者对他人态度的依赖和揣度,“条件恐惧模型”表明了MPA患者在面临“中性刺激”时的态度及反应,“发展可塑性理论”则强调了MPA患者应变环境和条件的能力上的差异存在。这四种干预方式涵盖了MPA患者行为表现的几个主要方面,但缺少相互的关联性。现实生活中,MPA表现的每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不过不同的个体在表现上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针对音乐表演焦虑的干预,应将每个表演者都看作是一个生命的“宇宙整体”,从整体的层面考虑辨证施治。只有这样,针对音乐表演焦虑的干预研究才会取得更加有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