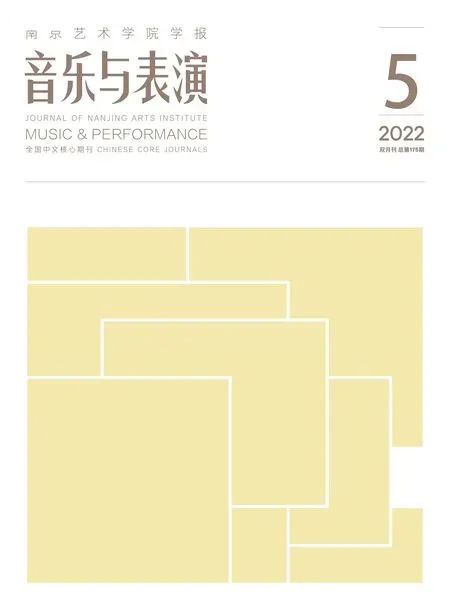当代西方学者视角下的“古琴音乐与自然观”研究
李美燕(屏东大学 中文系,台湾 屏东 900391)
中国的古琴艺术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孕育而生,也在传统的天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其音乐美学的观点。在古代的琴学文献中,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举凡古琴的材质、形制结构与象征意义、琴谱的指法手势图、琴曲的曲目、弹奏古琴的环境等,随处皆可见古琴音乐取法大自然的思维。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古人很重视弹琴的环境与人的心境结合为一,以达到物我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嵇康的《琴赋》与徐谼的《溪山琴况》皆有植根于道家修养工夫的基础上,提出在“天人合一”的思维下体现人与大自然宇宙契合的最高境界,反映出古代中国人透过古琴音乐达到与大自然沟通的理想。而当代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古琴的论述也关注到这个课题,因此,本文对高罗佩及其后的西方学者如何来解读“古琴音乐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古琴音乐与自然”的关联简述
(一)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
古琴作为一项中国音乐的瑰宝,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只是在于音乐本身,更在于中国人赋予它崇高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的文献史料中,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可以发现不少有关古琴与天地万物和大自然相关联的文献记载,见于有关古琴的材质、琴谱的指法手势图、琴曲的曲目与弹琴的环境等资料中。
以古琴的材质来看,在古代中国人的观点里,古琴是一项具有崇高文化意义的乐器,因此,古琴材质的选用不仅攸关音色的好坏,更要优先选取那些在宇宙大自然的精华之气酝酿下所生长之树木。如在魏晋时期的嵇康(223—262)《琴赋》中即提出古琴的材质是得自天地精华孕育之宝地,经过避世隐居之得道至人的斫制,方可成就一张高雅的古琴。[1]1
以琴谱的指法手势图来看,古琴谱的指法手势图具有不同于西洋五线谱的特色,乃在于不记音高与节奏,让演奏者可以保留有弹性的发挥空间。此外,透过指法手势图可将每一个指法的动作以图文并缀的方式展现出来,让弹琴者从文字、图片的导引,想象这个指法动作所要表现的音色效果。弹琴者可以从每一幅指法手势图找出音色之美的解密关键。因此,古琴的指法手势图其实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意义的记谱方式,它除了保留古代中国人对古琴音乐在审美感知上的体认外,也让听觉之声透过视觉之画的想象与联想而呈现。
古琴的指法手势图借由图像来比喻音色的特质,其中的图像大部分来自天地万物(包括:大自然的景观、动物、植物)与神话传说等,传递出弹琴的指法技巧与音声特质,甚至是古琴音乐的文化意义与审美观。因此,当弹琴者透过其中的图像与大自然之间的天地万物做联想与想象,既可贴切地体会到古人对古琴音乐的审美认知。同时,古琴的指法手势也让后人了解,古人是如何去诠释这首琴曲,应该如何去掌握每一个指法下的琴音所具有的鲜活特质与细腻的情感。
以琴曲的曲目与弹琴的环境而言,目前所能见的古琴曲目,据查阜西先生编纂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来看:“在谱集方面,包括印本、稿本和转钞本已达一百四十四种之多。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中略去重复,共得三千三百六十五个不同的传谱;六百五十八个不同的传曲;一千七百七十一条琴曲解题和后记(说明琴曲的历史、表现内容、演奏效果等的总称);三百三十六篇琴曲歌词。”[2]5在如此大量的古琴曲目中,随处可见以“大自然”为母题的曲目,如:石上流泉、四大景、白雪、松下观涛、松风引、幽涧泉、风入松歌、风雷引、流水、高山、万壑松涛、梅花三弄、渔歌、渔樵问答、碧涧流泉、平沙落雁、樵歌、潇湘水云……或以四季为题之琴曲,如春雨、春思、春怨、春景、春晓吟;秋山木落、秋水、秋月照毛亭、秋江夜泊、秋江送别、秋江晚钓、秋夜吟、秋夜长、秋思、秋风、秋风词、秋怨、秋塞吟、秋闺怨、秋宵步月、秋鸿、秋声赋、秋蕊香……这些以“自然”为母题的古琴曲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将情感生命寄托于大自然的心境。
此外,古代中国人对于弹奏古琴的环境相当讲究,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琴谱中常可见对弹琴环境的要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明代杨表正(约1520—1590)《弹琴杂说》中的论述。弹琴除了室内要选择清净的正室厅堂或高层楼阁外,在户外要选择山林之中、山巅或水边,或在道观中,在阴阳二气和谐的氛围下,迎着清风赏明月,静坐弹琴。如果能遇到知音,固然可喜;如果遇不到知音,大自然中的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颠猿老鹤都是琴友。[3]270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始终非常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因此,古琴的材质、琴谱的指法手势图、琴曲的曲目、弹奏古琴的环境等皆与自然有关。
(二)从精神修养的层面来看
中国历代留下有关于古琴音乐审美观的文献中最重要的作品主要有二:一是魏晋时期嵇康的《琴赋》,二是明末清初徐谼的《溪山琴况》。这两篇琴论作品都有写到弹琴与大自然的关联。
首先,嵇康的《琴赋》,除了前述谈及古琴的材质取自高山峻岭中的秀丽之地,汲取天地日月之精华的梧桐木以外,文中也有取大自然的景观来比喻琴乐中的意境,描写琴音之美可以带给人们联想到大自然的景色与动植物(如流星、高山、流水、繁花、鸡鸣声、鸿雁飞、鸾凤和鸣、百花盛开等)。[1]2-3嵇康将其对琴乐之美的感受,透过大自然的景象来比拟,使存在于人心的乐象与大自然相关联。
其次,明末清初徐谼的《溪山琴况》是中国古琴音乐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篇巨著。徐谼透过二十四况(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釆、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提出一套深入而缜密的演奏美学与美感意境论。其与前人的古琴美学最大的不同是,徐谼选用一个字,以简驭繁地评述古琴的音乐之美,这一个品评的字眼涵括无穷的美感意境。值得留意的是,徐谼在每一况中或多或少透过“一段文学性的景象描述,引领学琴者从技巧理论的层次,转而领略琴韵意境的美感,甚至体认到琴声以外的生命境界”[4]45。如和、静、清、远、古、淡、恬、逸、迟诸况的景语,几乎都是借诸“大自然”的化境开显琴韵的意境。这些景语,让人们体认到人与大自然之默契妙合,而可展衍出心灵宽广的无限延伸的境界。
审言之,徐谼所使用的文学性景语是借由一种充满诗意的情致来呈现其心中的画面,以表达言语所难以形容的心境。而这些景语绝大部分都是取自大自然的景象,由此可见徐谼所体会的琴乐之美感意境并非人间之世俗情感(喜怒哀乐等)的寄托,而是倾向于精神层面的超脱意境。所以,其借诸大自然的景物来比喻其内心的体认,唯有当人心能从世俗红尘中洒脱地走出,去迎契大自然的无限宽广,才能体会弹琴之妙趣,存乎自我心灵的升华与大自然的相感应而呈现。
以上简述古琴音乐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后,接着,本文即拟探讨当代的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琴学中的这个课题。
二、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省思
目前从西方研究中国古琴音乐的情况来看,19世纪以前,有极少数的西方汉学家从事中国古琴或古琴音乐的研究,包括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英 国 传 教 士 李 太 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英国音乐学家赫尔曼·史密斯(Hermann Smith,1824—1910),[5]51但几乎无人从事中国古代的琴学文献翻译与解读的工作,直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才开始从事此工作。即使在今日,西方汉学界与音乐学界对中国琴学的解读仍不多见。因此,高罗佩《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 一书即是提供西方人了解古琴和古琴音乐知识,及中国古代琴学文献的英文翻译与解读的先驱之作。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系统地将中国古琴引入西方世界的学者,其《琴道》一书也带给当代西方的汉学家、音乐学者与艺术史学者一定程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琴的认知尽管有深浅不同,但大体上,他们都将古琴视为一种儒家教化所用的乐器,[6]113[7]168没有人注意到古琴与道家之间有重要关联。直到高罗佩《琴道》一书才独具慧眼地提出古琴与道家之间的关联。此著引述了《列子》《庄子》的话来说明“与道为一”,从世俗羁绊中解脱的意义,[8]46也提出“古琴思想体系的基础与道家相当一致”[8]46、“道家的理念支配了古琴思想体系的发展”[8]49的观点,而成为西方文献中最早提出“古琴思想体系”与道家思想有关联的论述。这与他在此前的西方文献中有关古琴的观点几乎皆是以儒家理想作为古琴思想体系的依归相区别。[5]66-68
尔后,当代的西方学者也多半参考高罗佩的《琴道》一书,以了解中国琴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当代的西方学者都关注到古琴音乐与自然的关联。因此,本文试图探索在高罗佩之后的这些西方学者随着时代的演进及学术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如何来解读中国的古琴音乐与自然的关联。他们是否开展出新的研究视域,他们的论述观点与高罗佩有何差异呢?以下即以当代西方学者来作为考察的对象,包括美国汉学家杜志豪(Kenneth J.DeWoskin)与史蒂芬·阿迪斯(Stephen Addiss),荷兰的音乐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英国的艺术史学者尼克·皮尔斯(Nick Pearce),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对他们论述“古琴音乐与自然”的观点加以省思,以探讨在东西文化的视域融合下,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琴学中的自然观如何解读,他们的认知理念究竟为何。①本文仅选择非华裔的西方学者用英语和瑞典语撰写有关琴学的作品来讨论,讨论的作品中又仅就他们的论著中有“古琴音乐与自然”这个课题者为主。因此,尽管其他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Georges Goormaghtigh 与美国的Fred Lieberman也对中国古琴的研究有所贡献,但他们目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杜志豪《中国古琴》 [9]21-26
美国汉学家杜志豪 (1943— ),是一位汉语文学教授,1999年自密歇根大学荣退,其研究的兴趣和专长包括中国的散文文学、哲学、美学、音乐和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他曾经根据中国的文本与考古证据来撰写专著(书名为A Song for One or Two:Music and the Concept of Art in Early China),这本书所采用的材料来源包括神话、美学哲学、音乐知识和符号系统,从宇宙论和道德哲学的背景来看中国音乐和艺术理论的演变。
而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古琴》一文中,深入浅出地运用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素材来介绍中国的古琴文化。可见其也注意到古琴曲和自然的关联,他提出“古琴美学的语言就是自然的语言”,[9]24并以古琴曲的曲目名称为证,如:《高山》《流水》等都是与大自然有关,且指出“琴乐不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是人为的”[9]24,换句话说,琴乐有超乎人为艺术上的意义,古琴音乐与自然有关。
同时,《中国古琴》一文也提到弹琴的手势与技巧的描述、弹琴的环境、弹琴者与听众的心境以及古琴在其他艺术与文学中被描述的方式等,也都与自然有关。他又举古琴谱中的弹奏技巧之名为例,如“飞龙挐云”“螳螂捕蝉”“神龟出水”[9]25等也是取自于大自然。最后,他的结论是,古琴指法的每一个指法动作都能唤起对大自然景物的联想,换言之,古琴音乐和大自然有强烈的关联,如此的现象反映出古琴的音声特质与品味恰与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与不确定性相对立。[9]26此外,杜志豪还提到“琴道” 乃是在成就个人之道(a Way, or Dao),也指出遗音(余韵)乃是得自庄子“得鱼忘筌”的启发。[9]25
(二)史蒂芬·阿迪斯 《从汉代迄今的中国古琴》 [10]27-34
史蒂芬·阿迪斯(1935—2022)在1977年曾在美国的堪萨斯大学教书; 1992年他转任里士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Virginia),担任人文艺术学教授。他早年是一位音乐家,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旅行,也是一位在中日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很好成就的东方学者。他在诗歌、音乐、绘画、书法和陶瓷的学习和实践上受到中国文人艺术的启发,将从东方文化中学习到的东西与他本身的传统和价值观互动,从而创造出一些大胆而新颖的作品。他的体会是,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二者是分不开的。
阿迪斯在身为一个东方学者的背景下,对文人艺术抱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文章中也谈到古琴在古代中国的多重功能,包括作为娱乐、祭孔乐及文人乐器。[10]27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位主要的人物创造出中国的“琴道”的观念。其一是嵇康,其《琴赋》一文有谈及琴德,也提出与大自然有关的作品。同时,阿迪斯也强调古琴曲《流水》与《高山》的纯洁与高尚的象征意义。其二是陶渊明,阿迪斯有一段话值得重视,他说陶渊明的“无弦琴”的观念,让他联想到西方有一位Henry David Thoreau也有类似的说法:“所有的声音几乎都类似无声”,[10]27-28并且他也引萧统的名言“何需丝与竹,山水有清音”[10]28来说明古代中国人对大自然的体认。
此外,阿迪斯有略微谈到弹琴的环境要在户外的月下,还有指法手势图亦与大自然有关。同时,他也提到了法国神父钱德明的观点,[10]32这些观点在高罗佩的书中也曾经被引用。[8]3阿迪斯还提到一个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弹古琴作为一种让心灵和谐的方法,是否仍能保留在21世纪中?最后,他引用高罗佩《琴道》一书的话语作结[10]33-34:“古琴及其音乐的内在美是如此这般地使我有信心,往后必定会有其他人继续弥补我所留下的空白。”[8]169[10]33-34
事实上,杜志豪和阿迪斯显然都是在高罗佩的基础上引用更多中国文人的典故与作品来加以阐述,两者的作品都有提到古代中国人对古琴音乐与大自然关联的看法,但阿迪斯和杜志豪一样,缺少对古代中国人如何透过修养工夫而体认古琴音乐中的自然观做进一步的省思。
(三)高文厚《意义与结构:以古琴音乐为例》 [11]39-62
高文厚目前是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的负责人。
这篇论文先谈到传统中国的古琴之道,如谦虚与傲慢的对比。高文厚引用了西方汉学家杜志豪(Kenneth J.DeWoskin) 、郭茂基( Georges Goormaghtigh) 、高罗佩(R.H.van Gulik) 、与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的话,提出古琴对演奏者和听众来说,主要是作为启迪心灵和自我教化之道,而古琴音乐的内容也具体地呈现许多故事。同时,高文厚也发现“古琴从未摆脱作为一种悲乐的乐器,并且作为传达演奏者与听者之间心灵交流的媒介,唤起一种深度的平和之感”[11]40。
高文厚还指出下述中国琴学的核心观念:“在古琴音乐中,据说,凡是能以清净的心、开阔的胸怀去探索琴声,并且能够认知和接受这项乐器的‘神秘’的人,才能达到心境平和与宇宙和谐的境界。”[11]41总之,古琴音乐是人和大自然沟通的重要媒介。
高文厚多次强调古琴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琴是作为通向非人文的世界以达到不朽的境界、永远的平和与超越的圆满的一座桥梁。同时,他引述杜志豪的话:“琴是作为一种‘能引起共鸣的共鸣器’,一种提供接收更深层的自然之‘声音’的媒介——即存在的形而上的真理。”[11]4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高文厚也引用杜志豪①高文厚引杜志豪之语出自以下论著:De Woskin, Kenneth J.(1982) A Song for one or two; music and the concept of art in early Chin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138.的话:“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助听器’,一种与宇宙力量交流的工具。……琴的音乐不是由演奏者创造的:它是从大自然接收到的信息组成。”[11]42并且高文厚指出琴乐中的“无声之乐”,乃是“在正常人的耳朵听觉能够感知的范围之外的声音,声音的想象和延宕随着手指在琴面上摩娑,而在任何可听见的声音消失之后,仍然有深沉的、心灵的声音持续在进行”[11]42。
但是很遗憾,高文厚只是客观在描述中国古琴音乐的特质,却没有谈到如何可能。这也反映出中西方因文化背景上的不同,而有认知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的眼里古琴不只是一种乐器,还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道器。因此,古代的中国人在弹琴的演奏实践与心性修养上有一定的要求,但西方的琴学研究者显然较少重视弹琴对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此外,高文厚还引用古琴指法图来说明自然的意涵存在于其中,也谈到琴在形制上与“自然”有关的象征,如琴乐有直接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如流水、飞鸟等),又如弹琴的指法也与大自然的动植物的模仿有关,而产生一些诗意的描述性字眼。[11]45事实上,这些说法也见于高罗佩的《琴道》一书。
同时,高文厚也承袭前人对古琴在心灵价值方面的说法,如弹古琴可让演奏者自由地发挥,而不受限于乐谱的形式。而不同于前人者是,高文厚的文中提到中西音乐相通的地方,从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篇中提出音乐被视为宇宙的范例,谈到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中禁止浪漫的感性等。[11]41高文厚也从中西音乐可以做弹性演奏的地方来做比较。如18世纪法国的大键琴及吉卜赛小提琴调、法国的鲁特琴前奏曲 (lute preludes)或法国大键琴前奏曲(French harpsichord preludes)也是给予演奏者自由弹性的空间,让演奏者自己去发现他们的步伐而自行去划分他们的节奏。[11]47
但本文以为,西方的自由节奏与中国古琴的弹性节奏还是不一样。从形式上而言,中国古琴在演奏上的特色是速度较自由而随兴。古琴音乐的弹性节奏,如“跌宕”,在形式上“有如西洋音乐的弹性速度(Rubato),不同的是,Rubato 在西洋音乐中是由作曲者在乐曲中让一段旋律即兴发挥,但后来依然要回归到原来的速度,因此,Rubato绝少放在结尾,结尾处多半是渐慢(Rit);而古琴音乐的‘跌宕’却没有如此限制,它赋予琴人演奏时即兴发挥的最大空间”[12]280。
(四)尼克·皮尔斯《超乎声音之上的视域:琴的另类音乐性质》 [13]40-46
尼克·皮尔斯是目前仍任职于苏格兰哥拉斯哥大学美术系的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在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摄影师在中国所拍摄的照片,以及从中国的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来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摄影这件事。同时,他也是一位东西方艺术作品的收藏者,他关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
因此,皮尔斯从艺术史的角度切入了绘画中的古琴研究,他的文章谈到绘画与思想之间的关联性。皮尔斯提出古琴音乐有超越声音之上的意义,此即古琴与文人画的关联。而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并没有立于西方本位去看待中国的山水画,而是着眼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与世界的关怀。他也谈到古琴减字谱的特质乃是一种描述性的乐谱,利用中国文字去指导演奏者的指法、装饰音、形式和节奏等,并且指出中国古琴的指法谱允许人们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弹性空间。[12]41皮尔斯还注意到中国山水画中的古琴深深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联,音乐中的次序就与自然中的秩序一致。[12]42
(五)林西莉《林西莉古琴的故事》[14]
林西莉(1932—2021)是一位瑞典汉学家,也曾经是一位教授、作家和摄影家。她师事瑞典知名的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 ,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留学北京大学,之后多次造访中国。林西莉的《古琴》一书原本是用瑞典语写成的著作,于2006年出版,而在2009年被翻译成中文版。
她透过在20世纪60年代穿梭于北京学琴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展开这本书,深入浅出对古琴的知识做一番介绍。林西莉对于她所曾遇到和学习过的琴家给予其个人的评论,并向当时重要的古琴大师们致敬,对于一个在她来到中国之前完全超乎她想象的精神世界表示敬意。通过这本自述性的作品,林西莉展现她对琴的主题的基本尊重,因此,她的这本书引起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
然而,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冬教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文《导读——从“孔子古琴的故事”说起》中,曾经提出如下的评论:“本书设定的读者是外国人,由这层意义来看,本书的写作是成功的。……符合了西方读者对于繁华缤纷的中国的想象。这些架构的铺陈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但我也必须指出,正因如此,本书取材的富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讨论的深入。例如本书再三提及琴音如何取法大自然的天籁、弹琴的手势如何模拟禽鸟的姿态,其实背后更深层的含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经由琴的弹奏以追求契合于自然,所谓‘与万化冥合’的境界。”[14]13
换句话说,林西莉的这本论著的预设读者是西方人,她必须考虑如何将中国的古琴导入西方世界,让西方人能够认识与接受中国的古琴文化。所以,其写作的方式是以感性的散文做介绍,而不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本位来写作,其内容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
此外,这本书不免有疏于考证之处。例如在其书中有提及“琴道”一词,她指出“竹林七贤均生活在三世纪,这出自江苏的浮雕上所展示给我们的画面后来逐渐被人称为琴道”,[14]134事实上,中国的“琴道”一词早在东汉时期桓谭《新论》一书就已经正式提出其定义,[15]8林西莉的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知其论点所据为何。
而在其书中有提及老子的“道”“是一种接近大自然并与其合而为一的尝试”。[14]136同时,她和高罗佩一样,也提及“道教” “与控制自然力量的需要有关。这把他们带入了学习炼金术的阶段……尝试着各种养生之道,以求长生不老。透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可以使人心境开阔,达到‘静心’——一个清澈和平的高远境界”,[14]136“道教对于各种呼吸的技巧以及其他影响生活节奏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与超自然的力量沟通的兴趣”。[14]136显然,林西莉的这些说法与高罗佩之说如出一辙。
此外,林西莉在其书中也提到了部分的指法手势图,但她对中国人的指法手势图为什么可以展现古琴音乐与大自然的关联,显然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事实上,古代的中国人以古琴作为体现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乐器,乃是借由古琴的指法的音色与天地万物(包括大自然的景观、动物、植物)与神化传说形象等联结,然后让弹琴者产生想象与联想,以掌握这个指法音色的审美要求。同时,古琴的指法手势图之所以与天地万物(包括大自然的景观、动物、植物)产生联结,也是因为古琴音乐所追求的声音之美是与大自然宇宙的生命合而为一。[16]31-32
结 语
中国古琴音乐美学中的自然观,可以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举凡古琴的材质、琴谱的指法手势图、琴曲的曲目、弹奏古琴的环境等,随处可见古琴音乐与自然的关联。这些以大自然为法的记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追求与大自然和谐为一的价值观;而从精神方面来看,古人很重视弹琴的环境与人的心境内外结合为一,以达到物我合一的最高境界。凡此皆植根于道家修养工夫的基础之上,才有所谓抚琴操缦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
今本文特就几位当代的西方学者在论述古琴音乐美学的作品中来看,他们在跨文化的情境下,愿意投注时间和精力将中国琴学介绍到西方世界,并站在中西视域融合的角度上,让中国的琴学能够符合西方的思维逻辑、走入西方的学界。他们的贡献值得肯定。他们大都能掌握中国琴学中的自然观的意义,并且指出其与道家思想的关联,但遗憾者是,他们几乎皆未省思到古琴音乐与大自然的关联如何可能。
事实上,古琴音乐与大自然之间的关联并不是通过知识逻辑的思辨可得,而是要透过抚琴操缦的修养去体证。审言之,古琴音乐可以传达人对大自然景观的感受,但见诸嵇康《琴赋》与徐谼《溪山琴况》对大自然的观照,不仅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灵空间。这种心灵空间的开拓得之于人的自我修养,当人能从世俗的纷扰中放下执着,让自我从现实的环境中解脱,而拥有包容世界的宽广心灵,弹琴才能达到与大自然和谐融入的境界。然而,这却是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高明面。
观其缘由,原因之一即是他们的写作虽然都注意到中国琴学中的自然观,但很明显的一个共同的情况是,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古琴文化主要是得自几本(篇)西方汉学家的论著,尤其是取自高罗佩和杜志豪的观点,有些则是在中国大陆做实地考察与访谈,而得出其认知观点,但他们极少,甚至根本没有参考中国人的琴学研究成果。
今日,不管当代音乐如何与时俱进,古琴对今天的演奏者和观众来说依然很重要。古琴音乐绝不仅仅是一些想象中的遥远过去的遗迹,而是可以活在每个人心中的音乐,关键就在于其背后所具的文化内涵是根植于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古琴音乐美学中的自然观,是中国古代琴人的情感寄托与生命归宿。虽然,本文所引用与讨论的西方汉学家、音乐学者和艺术史学家等人的文论中也都有充分的强调,但如果他们能与中国人的琴学研究对话,进一步研究古琴的形而上意义,或弹琴的修养工夫与道家及道教的关联,相信中西观点的交流又可能会开启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