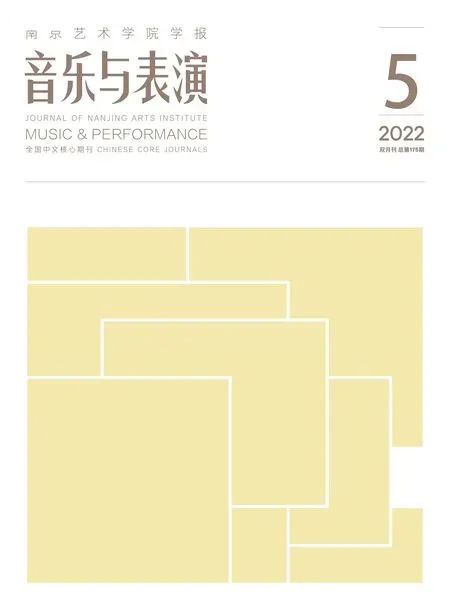武俊达:“三位一体”的戏曲音乐人生
薛 雷(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武俊达(1916—1997),生于南京,祖籍山西交城。1937年,他初中毕业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南昌参加了青年服务团。1939年,他进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直至1943年,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和作曲理论。
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音乐理论家,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出版和发表了《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戏曲音乐概论》《谈戏曲音乐的特点》《戏曲艺术美论二题》和《中国戏曲和西方歌剧》等系列专著与论文。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他执教数十年,编撰了戏曲音乐理论教材数十种,内容涉及昆、京、扬、锡、淮等剧种音乐的基础理论,还为外国留学生讲授传统戏曲课程。作为一位编者,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1982)特约编审,《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1982)主编,《中国戏曲志·江苏卷》(1982)编委。编选精当、成绩卓著,于1988年获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大集成”“志书省卷”编纂工作突出贡献荣誉奖。
一、勇于开拓,著述等身的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俊达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投身戏曲改革工作。他潜入民间音乐艺术的海洋,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演员艺人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昆曲,他曾与昆曲艺人同吃同住。他这种精诚所至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戏曲艺人们,同时学得了大量、直接的戏曲艺术感性知识,并挖掘出许多戏曲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后来的戏曲音乐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早年武俊达先生系统地学习过西方音乐理论,他在戏曲音乐研究中,能够较好地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对中西音乐进行比照分析,从而对我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有着更加深入与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其代表作《昆曲唱腔研究》[1]便是明证。在该著作中,他依据中国传统音乐构成规律,并融会西方音乐理论和方法,对昆曲唱腔音乐进行了更加合理与系统地解析。他不仅从乐句的结构、落音规律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入手,剖析昆曲曲牌的曲体结构和调式结构,还把昆曲唱腔曲牌腔型归纳为“直线型”“鞍桥型”“环绕型”和“音型移动型”四大类,进而对“环绕型”和“音型移动型”两种类型做深入讨论,“在曲调构成上与前两种截然不同,特别是第四类音型移动型,是以典型的音乐模进变化手法而构成,其有明显的西方音乐的思维特点”[2]。显然,他的这一认识,与他学贯中西的音乐文化积淀密不可分。
武俊达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总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与艺术实践。他经常不顾年高体弱,即使是偏僻道远,都尽可能赶赴现场进行音乐事项的实地考察与分析研究,以探索求真的精神,力图揭示我国戏曲音乐的基本规律。他也由此成为我国当代戏曲音乐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戏曲艺术改革与振兴以及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卓越的开创性贡献。正如其同窗学友杨琦所说:“虽然他在进入戏曲研究领域之前从未接触过扬剧、锡剧、昆曲、京剧等剧种,但是他经过踏踏实实的钻研,却写出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著述,而且有不少是开拓性的研究成果。”[3]譬如,他对扬剧曲牌【梳妆台】的系列研究,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出其右。甚至可以说,他对戏曲的微观研究,不仅为我国戏曲音乐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生面,也构建了他个人学术研究的重要一面。1957年,他发表了《从曲牌演变看戏曲音乐的曲调发展法——从扬剧【梳妆台】曲牌谈起》[4]一文,对【梳妆台】曲牌从清曲到登上扬剧舞台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做了较为翔实而全面地阐述。尤为重要的是,他发现,流行于江苏民间的“春调”即《孟姜女》调,乃是扬剧曲牌【梳妆台】的母体。从此,他在扬剧曲牌【梳妆台】的研究上,可谓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以扬剧曲牌【梳妆台】为例》[5]和《吕剧四平腔与扬剧梳妆台》[6]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从音乐形态上具体分析了【梳妆台】曲牌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而对【四平腔】与【梳妆台】这两个唱腔曲调的密切关系展开剖析、论证。这一系列研究对我国戏曲音乐应如何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起到了倡导与示范作用,并在扬剧音乐编创领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为后学研究扬剧曲牌音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和模板。正如《音乐研究》后记所言:“武俊达的《从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是从扬剧的一个基本曲牌【梳妆台】的发生、发展与其各种变化来说明戏曲唱腔形成的过程,同时,对照其他剧种有关这一曲牌的唱腔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渊源。这种做法是值得戏曲音乐工作者加以注意的。”[7]
除此之外,武俊达先生还对扬剧【大陆板】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不仅厘清了【大陆板】是江苏两大地方戏曲剧种锡剧和扬剧的主要唱腔之一,乃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被扬剧艺人所引入,而且还明晰了扬剧【大陆板】的基本曲式。即该曲牌虽然是上下两个乐句的乐段结构,但其上下对句式的乐段也可以以乐段为单位进行变化重复,构成排比型的多句式唱段,有时其结构形式也可以以“正、反、合、结”的四句式乐段形式存在。[8]扬剧【大陆板】的结构形式既深受苏北地域方言、文化的影响,又在实际运用中遵循“统一中的变化”和“变化中的统一”的规律。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扬剧【大陆板】是扬剧音乐构成中最具鲜明特色、也是最能营造艺术气氛与艺术效果的唱腔曲调。
武俊达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可谓成果宏富、著述等身。其著作主要有《扬剧音乐概述》(1962)、《昆曲唱腔研究》(1987)、《京剧唱腔研究》(1995)、《戏曲音乐概论》(1999)等。他的代表性戏曲音乐论文主要有《从曲牌演变看戏曲音乐曲调发展法——从扬剧“梳妆台”曲牌谈起》(《戏曲研究》,1957)、《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以扬剧曲牌【梳妆台】为例》(《音乐研究》,1958)、《从【梳妆台】在其它剧种的变化和发展》(《音乐研究》,1958)、《吕剧四平腔与扬剧梳妆台》(《音乐研究》,1958)、《再谈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美学问题》(《音乐研究》,1959)、《剧院楼台繁弦急 滩簧一曲江南音》(《人民音乐》,1960)、《扬剧现代戏的音乐设计经验与问题——从〈夺印〉到〈东风解冻〉的音乐设计看扬剧音乐的推陈出新》(《人民音乐》,1964)、《谈昆曲唱腔的推陈出新——〈十五贯〉唱腔分析》(《人民音乐》,1978)、《谈旋律节奏与语言节奏的关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79)、《【大陆板】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谈旋律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中国音乐》,1981)、《紧慢转调法的理论与应用——中国古代曲调作法研究之一》(《音乐艺术》,1981)、《扬剧〈鸿雁传书〉与堆字【大陆板】》(《江苏戏曲》,1982)、《多情一阕扬州曲 百岁新征日月新》(《人民音乐》,1982)、《从傩舞、傩戏到扬剧》(《戏曲研究》,1982)、《扬剧与扬剧音乐》(《人民音乐》,1982)、《谈京剧唱腔的旋律和字调》(《音乐与语言论文集》,1983)、《戏曲艺术美论二题》(《江苏美学学会论文》,1983)、《昆曲音乐浅谈》(《江苏戏曲论文集》,1983)、《从旋律对比看徽京剧唱腔的发展》(《皮黄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戏曲唱腔曲式发展三组曲例浅析》(《沈阳民族音乐学会论文》,1984)、《昆曲音乐改革的历史经验》(《江苏戏曲》,1985)、《迎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科研工作黄金时代的到来》(《中国音乐学》,1985)、《戏曲唱腔中的音乐因素和语言因素》(《中国音乐》,1985)、《昆曲唱腔的装饰音及记谱法》(《音乐艺术》,1987)、《吴梅南北词简谱在曲学上的贡献》(《艺术研究》,1989)、《谈江苏省语言区的划分与剧种分布》(《江苏省戏校学报》,1990)、《谈江苏省的戏曲声腔与剧种》(《江苏省戏校学报》,1991),等等。这些都是武俊达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为我们留下的一笔丰硕的学术财富。
武俊达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之特色是立足江苏、放眼全国,高屋建瓴地抓纲挈目、寻根探源,并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戏曲音乐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戏曲音乐研究中就倡导运用“基腔对比法”对戏曲音乐进行探究。这一戏曲音乐分析方法中的“基腔”,是指唱腔的核心音调,它集中体现了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三原则即“整体性”“层次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9],也是最能说明戏曲“唱腔家族”的风格特征,因为戏曲唱腔的一切变化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生发而完成。显然,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真正触及了戏曲唱腔之根本。随后,武俊达先生又在20世纪80年代,将“老三论”①这里是指“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三种学科理论。和“新三论”②这里是指“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三种学科理论。借鉴、运用到戏曲音乐研究之中,从而大大推进了他学术研究深度。另外,他还将“黑箱方法”①也称“ 黑箱系统辨识法”,是通过观测外部输入黑箱的信息和黑箱输出的信息的变化关系,来探索黑箱的内部构造和机理的方法。“黑箱”指内部构造和机理不能直接观察的事物或系统。黑箱方法注重整体和功能,兼有抽象方法和模型方法的特征。引入戏曲音乐研究,以揭示创作心理方面个人的和社会的“信息输入”与作为创作结果的“信息输出”之间的奥秘。1992年,武俊达先生在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所宣读的《论中国戏曲音乐功能状态的亚稳态》论文,对戏曲音乐“亚稳态”②源自原子物理学和材料学中的概念,是指体系高于平衡态时自由能的状态的一种非平衡。这里是借用。的分析,无疑为我国戏曲音乐形态学研究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研究思路及课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师者
武俊达先生自1956年调入江苏省戏曲训练班(江苏省戏剧学校前身)任教,就与戏曲音乐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坚守于戏曲音乐教育及其研究领域,为我国的戏曲音乐创作、教育和理论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还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昆曲、京剧入手,探根求源,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江苏地方剧种扬剧、锡剧、淮剧等声腔音乐,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丰厚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他先后编写了《戏曲音乐基础理论》《戏曲作曲专业教材》《演员唱练教材》《戏曲音乐分析》《戏曲多声部处理》《戏曲唱功训练》等教材20余种。20世纪70年代,他又完成了长达30余万字的《民族旋律和戏曲唱腔写作方法初探》教材,对民族旋律与戏曲唱腔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宏观上看,该教材在民族曲调的丰富写作经验中,提炼出其本质性的东西,以揭示其客观规律;从微观上看,该教材把复杂的创作现象区分为许多“单因子”,透过现象对个别单因子进行对比、分析和归纳,而且这种剖析、归纳又是在紧密联系着我国整个民族音乐的大背景、大系统下所进行的。他所编写的诸多戏曲音乐教材条理明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浅出,对学习戏曲音乐专业的学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武俊达先生在戏曲音乐教学中,不仅承担江苏省戏剧学校京剧专业的京剧音乐分析课程、为南京艺术学院作曲专业的学生讲授戏曲音乐课,而且还为天津戏曲音乐进修班开设《京剧音乐研究》讲座、为日本研修生有泽晶子讲授昆曲音乐研究课程、为美国留学生魏莉莎讲授戏曲理论课程,等等。特别是他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女士通力合作,硬是将一位初学汉语的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戏剧学的“洋贵妃”魏莉莎教授培养成了一位“戏曲通”。
另外,他在戏曲音乐研究上对后辈的帮助与提携,更是彰显出他的学者风范与高尚师德。武俊达先生的学生冯石明《忆恩师》一文写道:“1965年下半年,我(冯石明,笔者注)想把手上搜集的一些唱段以《锡剧基本曲调介绍》的形式出版,由于我对此事心中没有底,便请武先生(武俊达,笔者注)对这件事的可行性谈谈看法。武先生首先肯定了我的想法,并当即同意与我合作。结果不仅使该书增添了必要的大量材料,更是在基本曲调的形成、调式调性的变化及板式的发展,都做了极为详细又有高度的阐述,一本有着较高理论水准的编著便问世了。可是,武先生却不愿在此编著上署名。”[10]不仅如此,据原江苏省戏剧学校校长何华平介绍,武俊达先生曾对他说:“小何(何华平,笔者注),你经过了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系统学习,有着比较好的基础。但是,从事戏曲音乐是许多音乐人不想干或坚持不下去的,往往要凭着一种精神和一股毅力。你要想在音乐(戏曲音乐,笔者注)方面学有所成,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第一,要放得下架子,沉得下去;第二,要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第三,要经得起挫折,甚至不怕受委屈。”[11]100虽然只是武俊达先生当年对学生的一番肺腑之言,但这番话放在今天,依然能够对致力于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后辈学人带来警示及启迪。还有张林雨在其《武师论治学》一文中的回忆。1992年11月,张林雨在中国戏曲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论转转腔》,武俊达先生听后,颇感兴趣,随即开导张林雨:“在四目失明的艺人家庭中,居然培养出了能创立转转腔的梅花奖演员宋转转,在中国艺人中是罕见的,你可以为此写成一部学术专著。”[12]于是,张林雨在宋转转的故乡深入生活年余,最终写出了《宋转转与转转腔》一书。更让张林雨终生难忘的是,武俊达先生为他审定《晋昆考》书稿时,从书名到书的框架结构乃至“宫调理论”及其运用的阐述等方面,都逐一加以指教。戏剧家王易风在《晋昆考》一书出版之时发自肺腑地说道:“它(《晋昆考》一书,笔者注)是索于民间,求诸文献,名师指点,奋笔成篇。”显然,这番评价总结中所说的“名师”主要是指武俊达先生。
三、一丝不苟,默默耕耘的编者
武俊达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等编审工作中认真负责、成绩斐然,于1988年荣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大集成”“志书省卷”编纂工作突出贡献荣誉奖。
据黄叶绿在《默默耕耘 潜心研究》[13]一文中回忆,1983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编辑委员会集中部分同志在北京东方饭店审定书稿。当时,武俊达先生不幸摔伤了腿,行动十分不便,但他仍然坚持出席了此次审稿会议。他对每一个条目都做到句句推敲、字字斟酌。特别是,他为了把当代胡琴怪杰赵济羹先生写进大百科全书,竟然不怕麻烦、历尽波折,不辞辛劳地去拜访赵济羹先生的再传弟子梅允华先生,最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赵济羹”条目在撰写上尽可能地做到精确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武俊达先生的治学精神,就此也赢得了学界同仁的敬重与称赞。武俊达先生为《中国音乐词典》撰写条目42条,共计一万六千多字。他不仅交稿及时、书写清楚,而且内容准确、一丝不苟,令编写单位十分满意。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以下简称《戏曲音乐集成》)是武俊达先生在晚年全力以赴的又一项工作。《戏曲音乐集成》的圆满完成不仅是全体编撰人员共同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武俊达先生学术思想的集中呈现。可以说,武俊达先生把积累多年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和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融入“戏曲音乐集成”的编辑之中。在编排上,他对于入卷的戏曲声腔不是简单地采取一般性的平均铺排,而是更加强调了江苏地方戏曲及其艺术特点,做到了重点突出、繁简得当。丛书给予昆曲以大量篇幅,对保存昆曲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武俊达先生在浩瀚如烟的资料基础上,凭借对我国戏曲尤其是对江苏地方戏曲声腔音乐多年研究的深刻认知,就江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戏曲声腔剧种做出极为清晰、透彻的阐述。在每次编辑工作会议上,他都能紧紧抓住学术性的研究议题予以讨论解决。在他的带动下,各位编撰人员团结奋进、脚踏实地,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在3年内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编撰任务,由此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
结 语
对武俊达先生“三位一体”的戏曲音乐人生的回顾与梳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武俊达先生对戏曲音乐研究之深、范围之广、观点之新。作为学者,他研究涉猎之广以及所具有的敏锐的音乐感知力和洞察力,令人敬重。作为师者,他甘为人梯,诲人不倦的师德是后学敬仰的楷模。作为编者,他呕心沥血,尽职尽责的工作作风深得学界的称颂。尤其是他在戏曲音乐研究中闪耀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继承。譬如,他在戏曲音乐研究中的“亚稳态”研究理念,就值得后学们进一步接续性地探究。武俊达先生所从事的研究,从未仅仅浮在表面、简单武断地照搬西方音乐理论,强行诠释我国的戏曲音乐。而是从我国民族传统音乐的实际出发,结合西方的音乐理论,认真探索我国戏曲音乐的特殊规律。他还从美学的角度深入探索我国优秀传统戏曲瑰宝的艺术规律,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总结。正如武俊达先生的同事厉声所说:“我们不仅学到他对戏曲音乐规律所做出的探索和论述,而且也从他的研究方法、研究道路方面受到教益。他的工作对于我们从事民族音乐遗产的继承、发展工作,对于培养民族音乐理论人才,也是一种启迪。”[11]102故此,我们重温武俊达先生治学、育人及工作之精神,并以“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为座右铭,以期在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研究道路上更加努力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