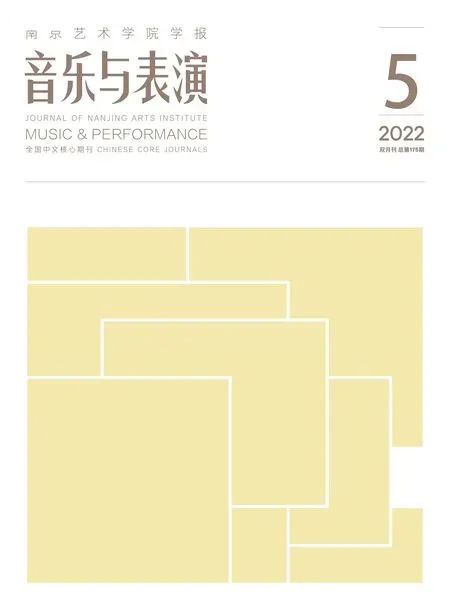宋代江苏地区琴人琴事述略①
施 咏(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宋代具有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也造就了较为庞大的文人群体。由于宋代君王重文轻武的思想,长期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古琴被视为音乐“正统”,上至皇帝将相、下至文人僧侣均好鼓琴。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分别集中在京师开封及南方的两浙、江西等地,因而出现了江西、京师、浙等较大的古琴流派。宋太宗时宫廷中设有琴院,有琴待诏专伺鼓琴,宋徽宗设“万琴堂”广搜天下名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琴艺术的发展。皇室爱琴之风也影响了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对古琴的关注,并且直接或间接使得另一琴人群体——琴僧的发展壮大。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也推动了琴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如朱长文《琴史》等重要的史论专著。琴人、琴曲、琴论发展突出,琴学发展态势繁荣,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琴文化发展历史中十分重要的时期,并对古代古琴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宋时期,江苏分属江南东路、两浙路、淮南东路、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南宋时江苏据有江南和淮南。因而,两宋时期吴地的琴乐也得到了自上而下全面的推广与发展。
有关宋代琴乐的研究成果丰富,涉及琴人、琴史、琴诗、琴派等诸多方面,但目前未见专事于江苏琴乐研究的成果。相关研究中古代文献多散见于《苏州府志》《松江府志》等地方志书及各类笔记、见闻录中。现代的学术成果亦较为丰硕,章华英《宋代古琴音乐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戴微《宋代女性琴人史料初考》(《音乐艺术》2019年第4期)、章瑜《宋代古琴音乐文化整体历史发展思考——编年史体例与宋代古琴音乐文化研究》(《音乐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年)、张斌《宋代的古琴文化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以及施吟云《吴地琴史探微》(《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学生音乐学写作文选》2013内部刊行)等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都对江苏地区琴乐有所涉及,但多较为零散、未成体系。本文拟在上述前人之研究基础上,聚焦考述与江苏地区或与之相关的琴人、琴事。
一、琴 人
鉴于两宋时期琴人身份多样,涉及琴待诏、士大夫、江湖文人隐士、僧侣等多种类型。本文拟以此基本分类分述。
(一)宫廷琴师
宋代宫廷中设有琴院,出现了一批琴学造诣深厚的宫廷琴师。江苏籍的宫廷琴师中以朱文济最具代表。
朱文济(976—983),江宁(今南京)人,北宋初年宫廷琴待诏,著有《琴杂调谱》十二卷,现已佚。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中称其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3)“鼓琴为天下第一”[1]。任琴待诏时,他曾极力反对宋太宗改古琴七弦为九弦之举,谏称“帝方作九弦之琴,五弦之阮,裔以为宜增,文济以为不可”[2]。与他同为琴待诏的赵裔因附和宋太宗的做法而授“赐绯”(相当于五品官职),获饷甚厚。然而朱文济不为所动,仍坚持自己观点。后宋太宗命其用新制九弦琴演奏,他仍只用其中七弦演奏《风入松》,众人无不称赞。其后,宋太宗也因朱文济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对他予以褒奖,“上不以其不达为遣,而嘉其有守,亦命赐绯”[2]。
朱文济“性冲澹,不好荣利,唯以丝桐自娱,而风骨清秀若神仙中人”[3],他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也与自唐代发展起来的琴僧系统不谋而合。
(二)民间琴僧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琴僧的历史由来已久。如唐代诗人张籍曾在五言律诗《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中云:“书客多呈贴,琴僧与合弦。”到了宋代,琴僧群体的地位愈发重要,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形成了具有师承渊源关系的琴僧传承体系,其中最为重要且特殊的即为宫廷琴待诏朱文济所传一脉。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载:“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1]从中可以看出,宋代琴僧的琴技多出自宫廷琴侍诏朱文济,京师的慧日大师夷中得其真传,后将琴技再传越僧义海,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琴僧师承关系,义海之后又传有释元志、释惠崇、释则全、释梵如、释祖可、释元肇、释普度、释从信等人,成为琴僧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脉。众僧鼓琴修禅、以琴说法,形成了一支独特的琴人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琴僧之琴技源于宫廷琴师,而交游于文人之间。如无锡祥符寺天封塔琴僧释演化曾在北宋诗人苏舜钦(1008—1048)家中抚其所藏名琴不忍释手,苏为此赋诗一首:“双塔老师古突兀,索我瑶琴一挥拂。风吹仙籁下虚空,满坐沈沈竦毛骨。按抑不知声在指,指自不知心所起。节奏可尽韵可收,时于疏澹之中寄深意。意深味薄我独知,陶然直到羲皇世。曲终瞑目师不言,忽言昔常奉至尊。……幸逢宝器惬心手,因声感旧涕洒胸。顾我踟蹰不忍去,将行更欲留悲风。”[4]由诗可见释演化的琴乐意味之深远、韵味之高妙。
而关于释良玉与梅尧臣之间的交游也被文(琴)坛传为佳话:“良玉,字蕴之。昆山慧聚寺僧。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学,又善书,工琴棋,因游京师,梅圣俞见而喜,以姓名闻于朝,赐以紫衣,其东归也。”[5]梅圣尧臣还作诗相送良玉。此外,在《清江三孔集》卷17“杂著”中,还载有孔武仲的诗文《说琴僧元志》,诗中记载元志为其鼓《越溪》《履霜》二操,而此越溪则位于苏州城区之西南部,亦当属吴地之琴事。
(三)文人琴家
思想意识上的重文轻武,使得宋代文人阶层在相对宽松环境中造就了平和、淡泊、超然的心境。他们往往兼有政治家、艺术家等多重身份,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同时又精通音乐、绘画、书法。宋代诸多文人与琴人的交往,也被传为琴史佳话,如范仲淹与王镐、林逋,苏轼与陈季常、欧阳修与李景仙,无不是把屡遭贬谪的失意付之瑶琴。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元丰二年(1079),同毕仲孙、舒焕、冠昌朝等人游江徐州铜山县桓山、登石室,并使道士戴日祥鼓苏轼所藏雷氏琴。
这一时期的文人琴家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扬州与苏州两地。
1.扬州琴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亦是“江西琴派”的代表琴家之一,曾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任扬州太守,常于扬州蜀岭上的平山堂住所弦歌雅乐、切磋琴艺,并作有“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唤新声”[6]的诗句。此外,《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北宋扬州高邮的琴人桑景舒,曾以“吴音”制琴曲《虞美人操》的轶事。
南宋时期扬州最知名的琴家,当属与浙派缘起渊源颇深的张岩(1132—1215)。张岩,字肖(晓)翁,大梁人,后迁居扬州,曾任扬州知府。郭楚望为其门下清客,二人常切磋琴技、往来密切。张岩平素好曲律,因善鼓琴而闻名,对琴谱亦颇有研究,辑有《琴操补》十五卷、《调谱》四卷,因故未及刻印,“后(杨瓒)悉得广陵张氏谱而加校焉”[7],汇编入《紫霞洞谱》,为浙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此外,“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曾任南宋真州(今扬州)司户参军,亦善古琴、通音律,并著有论著《琴原》。
张侃(1189—1259),张岩之子,字直夫,号拙轩,扬州人。嘉定十六年(1223)任上虞丞。理宗宝庆二年(1226)任句容知县。端平二年(1235)为镇江签判。郭楚望任张岩门客时与他颇有交往,张侃在其《拙轩集》中曾载:“《高山》《流水》,钟子期所作;《箜篌引》,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今《流水》有《公无渡河》声。《公无渡河》,因渡河溺水,援箜篌而歌之。士友郭沔相与笑,‘后人穿凿’云。”[8]记录了郭楚望对所谓古人琴曲附会之说的态度。
宋元之际,金兵南侵,扬州因战争陷入萧条。至元时,可见于记载的琴人有甘泉县善琴者王有恒,常鼓琴自娱,后因战祸迁于东吴居住。九皋声公所作的《王有恒听雨篷》一诗,表现了王有恒流亡中以琴自遣的生活:“江南雨多春漠漠,蘧篨中宽可淹泊。坐听萧瑟复瑶琤,若在洞庭张广乐。木兰之楫青翰舟,斜风细雨不须忧。笔床茶灶便终日,知我独有沧浪鸥。廿年携书去乡国,芜城草深归未得。援琴时作《广陵散》,鱼龙出听天吴泣。江湖适意无前期,身如行云随所之。平山堂上看春色,还忆江南听雨时。”[9]
2.苏州琴家
苏州的琴家中则以江苏吴县人氏,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范仲淹较具代表。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升为秘阁校理,其间结识当时的宫廷乐师崔遵度并随其学琴。崔遵度去世后,范仲淹又随浙江杭州处士唐异学琴,不仅崇仰唐异琴艺,更崇仰他“厌入市廛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10]的高洁品格。朱长文曾在《琴史》中评价范仲淹的琴艺:“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11]可见,范仲淹虽所弹琴曲不多,但琴趣颇深,能够透过琴声表其心性。
范仲淹在陈州任地方官时,曾于仲秋之夜听闻一高僧真上人弹琴,并作《听真上任琴歌》以表达对古琴演奏的感悟。他还主张“琴不以艺观”与“中和”的琴乐思想,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其《与唐处士书》一文中:
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东宫故谕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思而释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疲乏欤![12]
范仲淹在文中开篇从儒家的角度指出琴人、琴乐与天下之道的关系,表述其“琴不以艺观”的音乐思想,反对将古琴作“艺”来对待。他又通过解读崔遵度的琴学思想,进一步提出“弗躁弗佞”“中和之道”的观点。可见,范仲淹的琴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也因其与隐士、僧人的交往而受到佛、道的影响,而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也无不体现其中。
此外,宋代著名词人、苏州长洲人叶梦得(1077—1148)也是屡见史载的苏州琴人之一,据《琴史续》中所载:“少时从信州道士吴自然学琴,能为一两弄……庐州崔闲……每坐玻璃泉上使弹终日不倦……闲所弹更三十余首,有指法而无其谱,乃略用平侧四声,分均为句,以授梦得曰‘公能为,我为辞,他日辞归庐山,倚琴而歌,亦足为千古盛事。’梦得许之而未有应也,旋从徐度处得江外招隐一曲,以王琚旧辞增损足成者,于是倚此为辞,以终闲志焉。”[13]由此文可见,叶梦得曾向多位琴人习琴,练琴刻苦,且具有一定的曲目积累。
二、琴 派
南宋时期,临安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带动了两浙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众多琴家纷纷聚集于此,他们的演奏风格、指法编订、琴曲创作等方面与之前的“江西派”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派”。其中代表琴家除了两浙地区的郭沔、刘志方、杨缵等人外,亦有扬州人张岩、张侃父子。张岩因随郭楚望习得《乌夜啼》一曲,而以“张乌夜”闻名一时。
浙派古琴继承前代琴学的成就,广泛吸取各家所长而发展成为自南宋以来一大琴派,到明代时以浙江四明(今宁波)琴家徐和仲为代表,并且直接影响到明代江苏常熟虞山、扬州广陵诸派的形成。首先,“浙派徐门”在元明之际影响很大,虞山派琴人多受到浙派的直接影响;其次,虞山琴派的代表琴谱与“浙派徐门”曲谱多有相同,虞山派代表人物严天池编订的《松弦馆琴谱》和徐上瀛传谱、夏溥编订的《大还阁琴谱》中《渔歌》《樵歌》《潇湘》《乌夜啼》等曲均为浙派传统琴曲;再次,两者在琴学观上也都提倡纯器乐曲。宋代浙派注重左手轻重疾徐、吟猱绰注的指法应用,虞山派继承这一传统,十分重视左手的运用。由此可见南宋浙派在古琴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江苏诸琴派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琴 论
宋代古琴除了涌现出一批琴人、琴曲,在琴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出现了朱长文的《琴史》、袁桷《琴述》、崔宪度《琴笺》、刘籍《琴议》、陈敏子《琴律发微》等著述,也分别涉及了琴史、美学、律学、演奏理论等方面。
而与江苏地区最具关联的则以朱长文的《琴史》最具代表。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潜溪隐夫,苏州吴县人。北宋乐学家、文学家。朱长文出身于古琴世家,其家族中尤以朱亿、朱亿姊广慧夫人、舅惠玉等精于琴艺。其中,祖父朱亿还曾因入宫鼓琴受到宋太宗的赞赏,任刑部尚书。朱长文19岁中进士,嘉祐四年(1059)授其许州司户参军,因坠马伤足成疾,不肯出仕。便在其祖母吴氏于苏州城内凤凰乡集祥里所购的金谷园故址(后改名为“乐圃”)隐居著述长达二十余年。元祐元年(1086)受苏轼、邓伯温等人举荐为苏州州学教授,与楚州徐积、福州陈烈并称“三先生”。元祐八年(1093)被诏为太学博士。绍圣四年(1097)迁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文字。
朱长文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著有《墨池编》《吴郡图经续记》《琴台志》等,其中所著《琴史》是现存最早的琴史专著。《琴史》成书于1084年,由其侄孙朱正大后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付梓刊印、为最早的刻本。书中材料来自《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南史》《魏书》《晋书》等史书,以及《琴操》《琴清英》《琴道》等前代琴学专著,同时也加入上古神话、野史、杂记等内容。全书共有六卷,内容可分为琴人传记和琴论两大部分。前五卷按通史时序收录自先秦到宋初琴人156人,第六卷为琴论。
作为第一部独立的古琴专门史,《琴史》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宋初古琴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了前人有关琴史和琴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后世认识、了解古琴提供了重要史料;且在搜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史论结合,亦阐明其琴学见解及审美观点,而具有较大的史学价值与学术意义。而近世后人周庆云补编的《琴史续》《琴史补》,亦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完善。
结 语
综上,两宋时期江苏地区的琴乐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琴人身份的三大类型中,民间琴僧之技艺源于宫廷,游于文人。琴僧与文人的交游在吴地无锡、苏州留下诗乐佳话。两宋吴地的文人琴家辈出,多借瑶琴排遣贬谪失意,尤在南宋之特殊时代以抒其“国破山河在”之爱国情怀,也是导致这一时期吴地诸多文人琴家活跃的重要原因。两宋时期吴地虽尚未产生独立且具有较大影响的琴派,但在“浙派”代表琴家中亦有扬州张岩、张侃父子等,可见,两宋之“浙派”对后世江苏常熟虞山、扬州广陵派的形成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诚然,两宋时期吴地、抑或是江苏地区的琴人、琴事绝非本文所涉及之范围可囊全,定尚有诸多遗漏之处。如吴地的女性琴家中,目前可见有载的宋理宗时期,知军张仲之妹张女郎(江苏海陵人)抚弹《长相思》,另据《历代琴人传》中所载,吴地的文人隐士琴家还有许扬、颜直之、陈郢、张炳炎、邓道枢、江参等。但亦多为只言片语之零散文献。若冀对此论题进一步完善,还有待各位琴学专家在此断代史、地域史、专门史的交叉研究中共同耕耘,以求共进。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提供些许框架线索,以待方家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