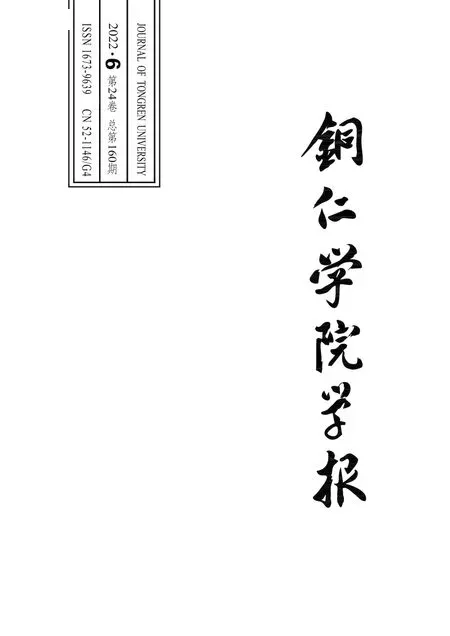“昌邑不终,天之去就”:从《汉书·五行志》看刘贺的“天意验证”
吕宗力
【梵净古典学】
“昌邑不终,天之去就”:从《汉书·五行志》看刘贺的“天意验证”
吕宗力1,2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
视天体异动、气候反常、山崩川竭等灾异现象为上天对人间君主的警诫,见诸先秦、秦、西汉初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汉书·五行志》在《洪范五行》天谴灾异的论述框架中,列举草妖、服妖、犬祸、血污、青蝇矢、久阴不雨、天狗夹汉等涉及刘贺的负面“天意验证”,论述废黜刘贺、继立宣帝的正当性,应该有其史事基础,而非后世史家刻意制造的后设性论述。在汉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和灾异论述中,刘贺即位前后这些灾异征兆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符合“天意”的。
刘贺; 夏侯始昌; 《汉书·五行志》; 《洪范五行》观
一、西汉政治文化中的灾异论述体系
西汉成帝统治后期,“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刘向感慨“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屡上封事谏诤,成帝不能用其议。元延年间,刘向再上奏论灾异,历数秦、西汉政局转折之际种种异象,慨叹:“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1]卷36-1964
视天体异动、气候反常、山崩川竭等灾异现象为上天对人间君主的警诫,见诸先秦、秦、西汉初文献,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管子》《墨子》《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乃至战国秦汉简牍。其中强调天人感应的星占理论,在西汉的灾异论述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汉书·天文志》: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卷26-1273
更系统地引入阴阳、五行理论,构建天、地、人互感的论述框架,将自然界和人间的各种“灾异”现象解释为天意的启示,应该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策问贤良文学“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之时。[1]卷56-2496董仲舒回应策问,首“推阴阳言灾异”,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先后被任命为江都王相、胶西王相。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1]卷56-2524虽然《春秋繁露》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等篇,但他的灾异论述,主要基于阴阳学和《公羊春秋》。其弟子吕步舒,再传弟子眭弘等也都善言《春秋》灾异。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毫社灾。两观、桓、釐庙、毫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出。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时田蚡已死,不及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1]卷27上-1333
董仲舒死后,夏侯始昌成为西汉灾异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夏侯始昌,鲁人,“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1]卷75-3154孙筱曾评论说,“西汉经师多攻一经。若申公兼通《诗》《春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了,夏侯始昌‘通五经’更是绝无仅有。”[1]“绝无仅有”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①但在西汉经师中确属凤毛麟角。
夏侯始昌身兼《齐诗》《尚书》两经宗师,在当时的经学界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西汉的《尚书》学,传自伏生。伏生,济南人,秦博士,入汉,在齐鲁一带教授《尚书》,受业者众。传其学者,济南张生、欧阳生,于是汉初《尚书》学有张、欧阳两支。夏侯都尉从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夏侯始昌。始昌推衍《尚书·洪范》经义,撰《洪范五传》,依据五行架构梳理灾异的分类和诠释体系,论述灾异与政治、人事的关系,是西汉灾异学说最重要的论述体系。②齐《诗》也以律历阴阳五行占候吉凶著称。武帝天汉四年,封宠姬李夫人之子刘髆为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夏侯)始昌为太傅。”[1]卷75-3154任职昌邑王太傅期间,夏侯始昌所擅长的《诗》《书》灾异学说对昌邑王室和昌邑地区的经学风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始昌以《尚书》及《洪范五行传》传族子夏侯胜,胜传从兄子建。由是今文《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夏侯胜的再传弟子长安人许商,撰《洪范五行传记》。夏侯始昌所传齐《诗》,据律历阴阳五行占候吉凶。焦延寿、京房等也用灾异说研究《易》,分六十四卦更递值日,以风雨寒温占验善恶。
宗室刘向习《易》《谷梁春秋》,而兼综齐、鲁、韩、毛《诗》,《左传》《公羊春秋》[3];于成帝河平三年领校中秘书后,参照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的分类和诠释框架,“集合上古以来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1]卷36-1950,撰成《洪范五行传论》。其子刘歆兼通今、古文经学,所撰《五行传说》,则对其父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作出学理化的修正。[4]
夏侯始昌和刘向父子所构建的《洪范五行》灾异论述,成为西汉最重要的灾异论述体系。班固撰《汉书·五行志》,就是以这一体系为分类和诠释框架,兼采董仲舒《公羊春秋》和京房《易》学。在《汉书·五行志》中,378个春秋六国至秦汉、新莽的符瑞、灾异征兆,参照《洪范五行传》的分类,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以著其占验,比类相从。[5]每类首引《经》(《尚书·洪范》);次引《传》(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再次引“说”(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五行传说》)等;再次举例证,引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夏侯始昌、谷永、眭弘、李寻、夏侯胜、杜邺、杜钦等论述为解说,集《春秋》《尚书》《易》诸家灾异学说之大成。
拙文《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曾讨论天意验证在西汉帝位继承正当性论证中的重要性。那么,《汉书·五行志》是如何在天谴灾异的框架中,论述刘贺被废黜的正当性的呢?
二、枯树复生,是为草妖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昭帝富于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诛之。后昭帝崩,无子,征昌邑王贺嗣位,狂乱失道,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1]卷27中之下-1412
《汉书·眭孟传》记载同一事件而更详细一些: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1]卷75-3154
眭孟即眭弘,董仲舒的再传弟子,鲁国蕃县人。少年任侠,斗鸡走马,年长学《春秋》公羊传,弟子达百人以上。因通晓经书任议郎,官至符节令。“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不详其义所出。但眭弘对该征兆所代表天意的解读很明确:“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这种解读,应该源自《公羊春秋》的师法。《焦氏易林·大过之第二十八·蒙》:“阳失其纪,枯木复起”,也以枯木为阳不当位之征。[6]京房《易传》则以“枯木复生”为“人君亡子”的征兆。
昭帝崩,无嗣,霍光主持朝议,推选昌邑王刘贺入嗣昭帝,昌邑枯木复生似已成为刘贺继体的天意验证。然而刘贺即位不久被废黜,被废为庶人的武帝曾孙刘病已如枯木逢春,应谶而起。究竟枯木复生代表着什么样的天意呢?
在《洪范五行》灾异论述框架中,枯木复生属于“草妖”之象,对应洪范“五事”之“视”。《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引《洪范五行传》:“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恒奥,厥极疾。时则有草妖”。“说”:
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匀,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奥也。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故有草妖。
《洪范》五事,貌、言、视、听、思心,视指君主的视野、观察力、判断力。恒奥属庶征中的咎征,即天谴的征兆:“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不哲即不智。据《洪范五行》论述,在上位者视不明,就容易受到阴暗面的蒙蔽,善恶不分,察人不明,赏罚失度,施政弛缓,因而引发四季紊乱,③植物生长异常,即“草妖”。而枯木复生,就是“草妖”的一种。
在上位者视不明,则善恶不分,察人不明,赏罚失度,除了引发气候的异常,还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呢?《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列举例证如下: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先是,连兵邻国,三战而再败也,内失百姓,外失诸侯,不敢行诛罚,郑伯突篡兄而立,公与相亲,长养同类,不明善恶之罚也。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不正,阴失节也。
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方有宣公之丧,君臣无悲哀之心,而炕阳,作丘甲。刘向以为时公幼弱,政舒缓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刘向以为先是公作三军,有侵陵用武之意,于是邻国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余年,因之以饥馑,百姓怨望,臣下心离,公惧而弛缓,不敢行诛罚,楚有夷狄行,公有从楚心,不明善恶之应。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灾,寒暑之变,天下皆同,故曰“无冰”,天下异也。桓公杀兄弑君,外成宋乱,与郑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时,楚横行中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晋败天子之师于贸戎,天子皆不能讨。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善恶不明,诛罚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岁,秦灭亡奥年。
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绝大幕,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还,大行庆赏。乃闵海内勤劳,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天下咸喜。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时上年九岁,大将军霍光秉政,始行宽缓,欲以说下。
据董仲舒、刘向等的论述,除了“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之孤例,一般都会出现内忧外患、主弱臣强的局势。
枯木复生之“草妖”,又对应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现象呢?眭弘师从的《公羊春秋》,“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以为“人君亡子”。《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亦引例证如下: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歆以为草妖也。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君位,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是时,公子遂颛权,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后,将皆为乱矣。文公不寤,其后遂杀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传》曰:“臣有缓兹谓不顺,厥异霜不杀也。”
《书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传》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凉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穀之异见。桑犹丧也,穀犹生也,杀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朝将为虚之应也。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是时僖公死,公子遂颛权,文公不寤,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臧,则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支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须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摎结,大如弹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据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的解说,也都象征着王德已衰,臣下专权,政权面临危机。昭帝元凤元年,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上官桀、桑弘羊等因密谋政变被诛灭,霍光权倾朝野,实际掌控西汉政权,主弱臣强之势已成。昭帝亦无后嗣。元凤三年昌邑王社枯木复生,是否预兆“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即昌邑王刘贺?后来的事态发展是,刘贺被征嗣位,二十七日后以“狂乱失道”,被霍光联合上官太后和部分朝廷重臣废黜,更立平民身份的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是为宣帝。所以,《汉书·五行志》编纂者对昌邑王社枯木复生的解读,认为这是刘贺的恶兆,宣帝的吉兆。
“草妖”被视为吉兆,在《汉书·五行志》中还有一例: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墓门梓柱,是砍伐后已使用的木料,居然再生枝叶,当然也属枯木复生的“妖征”。刘向和王莽却视为“受命而王之符”“将代汉家之象”。
三、上失威仪,故有服妖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说”曰: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轨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貌”居《洪范》五事之首。君主的体貌仪容仪态,形之于外,投射的却是内在的人品心态、礼仪修养和精神面貌。“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君主待人接物怠慢骄蹇,仪容仪态不能展现谦逊有礼的风度和适合其身份的威仪,则“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对应的社会、政治迹象,如“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以及“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所谓“服妖”,是指有违礼制或常制的奇装异服。凡服饰(包括质地、色彩、样式)与身份不合、场所不当,都可被视为“服妖”。[7]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所举例证:
《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以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弗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君有心矣。”后四年,申生以谗自杀。近服妖也。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后晋文伐郑,几亡国。
晋太子申生偏衣帅师,见《左传·闵公二年》: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慝,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期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8]269-272
晋献公令太子申生代己领军出征,却让他穿“偏衣”,即从背部中分,左右异色(其中一色与公服同)。上军右将先友安慰申生,偏衣的半身与晋献公同色,表示晋献公认可太子为其分身。上军主将狐突却认为,服色代表身份,戎服本贵纯色,今以杂色衣之,申生的前景不妙。下军主将梁余子养提醒申生,受命于君,领军出征,礼制本有规定的服饰,却被赐以杂色服饰,国君显然不怀好意,不如逃亡。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8]426-427古知天文者戴鹬羽冠。郑子臧不知天文,而好收集鹬冠,终遭杀身之祸。在古人的观念中,服饰与身份不相称,是一种灾祸。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将这种违制的服饰行为定义为“服妖”: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辠,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适,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仄注冠”,颜师古注:“应劭曰:‘今法冠是也。’謂之仄注冠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法冠也称“獬豸冠”,是监察、执法官员的首服。但据刘向《新序》:“昌邑王治侧铸冠十枚,以冠赐师友儒者。后以冠冠奴。龚遂免冠归之,曰:‘王赐儒者冠,下至臣。今以余冠冠奴,是大王奴虏畜臣也。’”。④仄注冠显然是儒者的首服。《后汉书·舆服志下》:“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筩,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9]则仄注冠应该是高山冠。在《汉书》的叙述中,刘贺在昌邑国时,性情佻脱,蔑视礼法,常“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正属《洪范五行》论述中的“貌不恭”类型。“冠者尊服”,刘贺令人制作了一批仄注冠,以冠大臣或师友儒者,郎中令龚遂即其中之一。但刘贺却将剩余的冠给地位卑下的奴婢服用,因而引起龚遂的抗议:“今以余冠冠奴,是大王奴虏畜臣也。”再联系到刘贺即位皇帝之后,“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墨绶、黄绶,与左右佩之。龚遂谏曰:‘高皇帝造花绶五等,陛下取之而与贱人。臣以为不可,愿陛下收之。’”⑤这都属于“服妖”的征兆。
“大白狗冠方山冠”情节,亦见于《汉书·武五子传》:“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1]卷63-2766刘贺为此咨询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⑥京房《易传》以为“妖狗冠出朝门”预兆的是“君不正,臣欲篡”的政治形势。
据《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引刘向“说”,“服妖”于五行属木,“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而“水鸟色青,青祥也。”所以“昭帝时有鹈鶦或曰秃鹙,集昌邑王殿下”,在《洪范五行》论述中,与“服妖”征兆是呼应的。京房《易传》对宫殿出现野生水鸟的解释是:“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寤,卒以亡。”王充《论衡·遭虎篇》:“昌邑王时,夷鸪鸟集宫殿下,王射杀之,以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曰:‘夷鸪野鸟,入宫,亡之应也。’其后昌邑王竟亡。”[10]龚遂所对,正与京房《易传》合。
四、言之不从,遂有犬祸
《汉书·武五子传》:
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遂为言其故,语在《五行志》。王卬天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1]卷63-2766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以为,“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
昭帝时,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
野熊闯宫,《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也归类为“犬祸”。《洪范》五事,言列第二: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
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
“言”即言论,指君主口头或书面发布的信息。据《洪范五行》论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从”,顺也,顺从天意、大势、民心也。“艾”,颜师古注:“艾读曰乂。”“乂”,治也,安定和谐也。为什么在上位者“言之不从”,天下就会不治呢?《洪范五行》“说”引孔子之说为理据,原文出《易·系辞上》: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11]
所以,君主当慎言谨行。如果在上位者刚愎自用,出言不善,“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并受到“恒阳”的惩罚,即大旱不雨。对应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⑦对应的灾异征兆,则是“犬祸”。
他如“《左氏传》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国人逐狾狗,狾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橶高后掖,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作崇。遂病掖伤而崩”;“文帝后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齐悼惠王亡后,帝分齐地,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兄弟并强,有炕阳心,故犬祸见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乡者也”;“景帝三年二月,邯郸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也。是时,赵王遂悖乱,与吴、楚谋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这些都是《汉书·五行志》列举的论证。
为什么“言之不从”会伴之以犬祸呢?《汉书·五行志》引述的解释是“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旤”。另一种解释是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
草妖、服妖、犬祸之外,刘贺在昌邑国,还见到其他的奇怪征兆。例如曾见血污坐席。咨询龚遂,龚遂告诫说:“宫空不久,祅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1]卷63-2766刘贺至长安即位后,有如下情形:
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1]卷63-2766
血污、青蝇矢之类的灾异征兆,未见《汉书·五行志》记载。龚遂为刘贺所作解说,可能参照了齐《诗》等汉儒的灾异论述。
五、久阴不雨,有篡弑之祸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此下“说”曰: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
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疴。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疴云。皇极之常阴,刘向以为,《春秋》亡其应。一曰,久阴不雨是也。刘歆以为,自属常阴。
“皇极”是《洪范》九畴第五畴。《尚书·洪范》: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2]1163
“皇极”是《洪范》的核心,九畴的精髓。是人间的君主遵照天帝的训诲所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准则,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2]1207在《洪范五行传》论述中,“皇极”也据有核心地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人间与宇宙的秩序与失序,取决于君主的言行和修养。《洪范》五事,君主在任何一事有过失,都会引发程度不等的天谴灾异;而在皇极方面有过失,则“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彻底丧失上天的信任。对应的灾异,刘向认为是久阴不雨,刘歆认为是常阴。对应的政治效应,诸家说法是:“下强盛而蔽君明”;“《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下人伐上,天诛已成”。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此常阴之明效也。
刘贺继嗣皇位后,因急切试图以昌邑旧臣分割霍光集团的权力,引起霍光的警惕,因而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立。事极机密,外间无有知者。刘贺毫无警觉,照常出宫游玩。时任光禄大夫的夏侯胜拦在乘舆前劝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1]卷75-1459
夏侯胜是西汉今文《尚书》《齐诗》学名家夏侯始昌的族子及弟子,“后事蕑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久阴而不雨”,按照《汉书·五行志》引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的论述,是上天针对“皇之不极,是谓不建”降下的天谴征兆。夏侯胜对刘贺的劝谏及其对政治形势的预言,依据的应该就是夏侯始昌之说。⑧夏侯胜之劝谏,固然出于其侍从顾问的职责,但也可能是看在其师夏侯始昌与前代昌邑王的师生情分,对刘贺的政治前途分外关注。然而刘贺不仅不领情,而且大发雷霆,说夏侯胜所言“为祅言”,缚以属吏。主审官吏向霍光报告有关案情后,霍光非常紧张,以为同谋废立的张安世泄露机密,但经询问,安世不曾外泄。霍光于是召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说:“《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1]卷75-1460霍光、张安世大惊,从此不敢轻视经术之士窥测天意的能力,非但不治夏侯胜“为祅言”之罪,而且在废黜刘贺、改立宣帝后,推荐夏侯胜教授上官皇太后《尚书》学,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⑨
刘贺面对“皇极”之谴,不知悔悟,臣下犯上之祸于是成真。
六、天狗夹汉而西行,昌邑不终之兆
本文开篇,曾引刘向于成帝元延三年上奏论灾异。荀悦《汉纪》也收录了这篇上奏:
四月,光禄大夫刘向上奏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蚀,山陵沦亡,星辰出于四孟,大白再经天,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㜸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大人见临洮,长星孛于大角,秦氏以亡。及项籍之败,亦孛于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蚀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也,天狗夹汉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兆也。”[13]
《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
(元平元年)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乙酉,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众星随之,众皆随从也。天文以东行为顺,西行为逆,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
汉代的灾异论述,于《洪范五行》之外,星占学也是重要的一支,其传承源流比《洪范五行》更久远。昭帝驾崩前,西汉的天文家观察到大星西行、众星随行、牂云如狗的天象。占辞认为,该天象预兆着“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汉书》的编纂者在叙述这则故事之后,根据历史进程的轨迹,写下了验辞:“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以霍光对应占辞中“运柄”“行权”的大臣,刘贺对应“乱君”。
李鹏为、安瑞军《昌邑王登基前的一次天象》指出,这一天象的突出特征是大星西行和天狗出现。用今天的天文学知识来分析,这是一次流星陨落事件,但是对于西汉中期的天文官们来讲,它发生的时间和所表现出的特征却极不正常。[14]
所谓“大星”,即太白星。《汉书·天文志》:“太白,兵象也。”《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天官占》:“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将军之象也。”纬书《龙鱼河图》:“(天)太白星主兵,凶。”[15]1153在秦汉的星占论述中,太白星即金星,主兵、主凶,所居之国象征着兵灾、人民流散和改朝换代。
“太白”在夜空中亮度仅次于月球,清晨出现在东方天空,被称为“启明”;傍晚处于天空的西侧,被称为“长庚”。昭帝元平元年二月甲申清晨,太白星大如月西行,有众星相随。在西汉的天文学认知中,日月五星皆右旋(东行),西行为逆。[14]《汉书·天文志》:“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夫历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众星随太白西行,显然是异象。
次日(乙酉)有三枚形似天狗的赤云,拖着长尾,沿着银河西行。[14]“天狗”指流星或彗星,当时被视为大凶之兆。《史记·天官书》: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汉书·天文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后秦遂以兵内兼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
(孝文帝后元六年)八月,天狗下梁野,是岁诛反者周殷长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孝景帝前元三年)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七国反。吴、楚兵先至攻梁,胶西、胶东、淄川三国攻围齐。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吴楚之敝,遂败之。吴王亡走粤,粤攻而杀之。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咸伏其辜,齐王自杀。汉兵以水攻赵城,城坏,王自杀。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为王,王胶西、中山、楚。徙济北为淄川王,淮阳为鲁王,汝南为江都王。七月,兵罢。天狗下,占为:“破军杀将。狗又守御类也,天狗所降,以戒守御。”吴、楚攻梁,梁坚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有著天白气,广如一匹布,长十余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传曰:“言之不从,则有犬祸诗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
纬书《春秋·文曜钩》:“彗为不吉之星,其见无期,其出行无度。遇圣主则伏而不见,遇暴君则出而助虐,故又名天贼,亦名天狗。”[15]707《河图·帝览嬉》:“流星夜见光,望之有尾,离离如贯珠,名曰天狗。从所下,兵大起,王者徙都邑,期三年。”[15]1163
如此凶恶的征兆,从何而起?《汉书·天文志》录元平元年占辞:“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此亦有说。《河图稽耀钩》:“太白散为天狗、主候兵”;“太白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15]1110、1111当时的星占术士以卒起、天狗等为妖星是由太白等五星散发精气而成。
所以刘向在给成帝的上奏中,以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而众星随之为宣帝兴起之兆,而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为昌邑不终之异。
小结
自秦始皇建立独裁专制的皇帝制度以来,如非遇上民不聊生、群怨沸腾、统治体系失效的皇朝末期,自下而上废黜在位皇帝,始终是惊世骇俗的高风险行为,在西汉发生过两起。霍光废黜刘贺的过程,虽有暗涌微澜,总算是完美掌控,政局迅速稳定,并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霍光也赢得后世“废昏立明,前代令范”的认可。继立的宣帝,政绩显著,被史家誉为西汉的中兴之主。他自己也非常重视统治正当性的建构和舆论的引导,在位期间祥瑞迭传。经过西汉中后期灾异学者的积极论证,政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汉书》编纂者的精致论述,刘贺荒淫昏庸、不为上天所喜(“天之去就”)的形象,深入人心。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16]东汉初,已平定河北的刘秀与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各引图谶,展开舆论战。公孙述引述当时流传的《西狩获麟谶》,宣称谶语中的“乙子卯金”“立子公孙”都能证明他获得了上天的认可。刘秀写信反驳道:“《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以)〔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17]身为刘氏宗室的刘秀,视外戚霍光废黜刘贺为理所当然之举。
当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东汉政论家王符,就指斥霍光“专相幼主,诛灭同僚,废帝立帝,莫之敢违”,其奸诈与篡汉的王莽如出一辙。霍光和王莽“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从上鉴其奸,神明白幽照其态,岂有误哉!”[18]针对霍光集团指斥刘贺在位二十余天,干了一千一百多件错事,明代史评家张燧质疑:“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19]吕思勉直截了当地说:“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20]笔者以为《汉书》中有关刘贺失德的种种叙述,虽然未必全如吕思勉所说“皆不足信”,但夸饰、失实、以讹传讹处必不可少。那么,《汉书·五行志》中围绕刘贺的种种灾异,是否也都是以讹传讹,甚至只不过是刘向、刘歆、班固等论证废黜刘贺、继立宣帝符合天意而刻意制造的后设性论述?
《汉书·五行志》所记涉及刘贺的灾异,昌邑王社“枯木复生”,发生于昭帝元凤三年,不止见于《五行志》,也见于《眭孟传》。眭弘依据《公羊春秋》灾异学作出的“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谶言,并非为刘贺上位制造舆论,却是警告刘汉皇室,因而激怒了霍光,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久阴不雨”和“太白西行”“天狗夹汉而西行”皆属众目睽睽下的天象,不仅见于《汉书·五行志》《天文志》的记载,也见于《刘向传》《夏侯胜传》,卷入事件的除了直接当事人刘贺、夏侯胜,还涉及霍光、张安世等重要朝臣。《汉书》的编纂者不至于无中生有,应该依据了相关的官方记录和档案。
至于“服妖”“犬祸”“血污”“青蝇矢”等灾异意象,均出现在昌邑王宫或未央宫等私密场所。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作为昌邑王的大臣,曾就这些意象所象征的“天谴”意涵,诤谏刘贺。刘贺被废黜后,他从昌邑国带到长安的旧臣两百余人,都被霍光集团拘捕审讯。其中只有龚遂和王吉以屡谏免死,其他人最后都被判死刑。龚遂虽然免死,仍受牵累,髡为城旦,至宣帝朝始获起用为渤海太守,治绩斐然,后征为水衡都尉。涉及刘贺的灾异意象,会不会是龚遂为了脱罪,对刘贺的诬陷呢?从昌邑国入京旧臣几乎全被处死的刑罚来看,他们涉及的是危害皇权的重罪。西汉的诉讼审理(鞫狱)体系完整,重视取证和核实(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口供等)。[21]龚遂能够以“屡谏”逃脱死罪,必定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谏诤的实质性证据,例如书面的谏诤记录或宫廷侍从的旁证。《五行志》和《武五子传》记录的“服妖”“犬祸”“血污”“青蝇矢”等灾异意象,和龚遂对其天谴意涵的即时解说,很可能就采自当时的审讯档案。田家溧审视《汉书》所叙昌邑王“服妖”事件,认为《五行志》所引龚遂、刘向、京房的相关论述,应该是“儒生建构自己理论的意义大于实际史事的书写”。[22]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汉书·五行志》关于刘贺的负面“天意验证”的“书写”,应该也是有其史事基础的。同时,至少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和灾异论述中,刘贺即位前后这些灾异征兆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符合天意的。
①史称“通五经”的西汉经师,还包括董仲舒及其弟子兰陵人褚大(《汉书·倪宽传》)、琅邪人王吉(《汉书·儒林传》)、楚人龚舍(《汉书·龚舍传》)等。
②《洪范五行传》作者,有伏生、刘向、夏侯始昌等诸说,笔者采信夏侯始昌说。参见缪风林《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转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9页;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第156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290页。丁四新认为,《洪范五行传》是否为夏侯始昌本人所创,尚值得讨论,后儒及今人多认为《五行傅》出自伏生之手。不管怎样,夏侯始昌很可能对于西汉中后期诸家所传定本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灾异说和新德运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6期,第112页,注2)
③例如暖冬。《春秋》记“无冰”凡三次,包括桓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八年、成公元年,皆在二月。因二月行“藏冰”礼,遇暖冬,无冰可藏,故史官书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谷梁春秋·桓公十四年》:“无冰,时燠也。”(《春秋谷梁经传补注》,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7页)《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庶征之恒奥,刘向以为《春秋》亡冰也。小奥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引京房《易传》:“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奥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奥,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征,其咎当寒而奥六日也。”
④刘向《新序》佚文,《太平御览》(宋李昉等编,夏剑钦、王巽斋校点,中华书局2000年版)卷500引,第2288页。
⑤同④,卷682引,第3047页。《汉书》卷68《霍光传》:“(刘贺)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⑥龚遂是山阳本地人,以经学入仕。所习何经、所从何师不详。但在政治实践中“引经义,陈祸福”,可知他在经学上受过良好训练。从《汉书·五行志》《武五子传》《龚遂传》的叙述可知,刘贺遇妖怪灾异之兆常咨询龚遂,龚遂也屡以《诗》和《洪范五行传》的经义劝谏刘贺,推测龚遂的经学背景与夏侯始昌的《齐诗》《尚书》学有交集。
⑦有关妖言、谶谣、诗妖的讨论,详见拙著《汉代的谣言》,此不赘。
⑧《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刘向以为,《春秋》亡其应。”可知此说源出夏侯始昌《尚书》学。
⑨参阅拙著《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1] 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95.
[3] 徐兴无.刘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99-100.
[4] 陈侃理.刘向、刘歆的灾异论[J].中国史研究,2014(4).
[5] Wang Aih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136-137, 155.
[6] 尚秉和,注.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279.
[7] 刘露.“服妖”由来考——汉代服饰统一下的服饰怪异[J].科教文汇,2016:(2月中).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9] 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66.
[10] 黄晖.论衡校释: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90:711-712.
[11]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7[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79.
[12]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63.
[13] 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卷27[M].北京:中华书局,2002:471.
[14] 李鹏为,安瑞军.昌邑王登基前的一次天象[J].文史知识,2016(11).
[15]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1153.
[16] 吕宗力.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J].史学集刊,2017(1).
[17]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1.
[18] 王符,撰.汪继培,笺校.潜夫论笺校正: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7.
[19] 张燧,撰.贺天新,校点.千百年眼[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4.
[20]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54.
[21]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5-490,620-629.
[22] 田家溧.汉代冠服体系的发展演变及意义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6(4).
"If Monarchs Misbehave, Anomalies will Appear, Indicating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Analysis on Verification of Liu He's Destiny by Anomalies from the
LYU Zongli1,2
( 1.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2.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The disasters and anomalies such as celestial body changes, abnormal climate, landslides and dried-up rivers, etc.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warnings of heaven to human monarchs,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the pre-Qin, Qin and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ies and unearthed bamboo slips. In the discussion framework of the wrath of heaven and abnormal disasters described by,lists the negative "verification of Liu He's destiny by anomalies", such as grass demon, strange dress, dog disaster, blood stain, green flies' excrement, long-lasting rainy days, and Heavenly Hound taking the Milky Way to the west, etc., and discusses the legitimacy of deposing Liu He and electing Emperor Xuan, which shall have its historical basis, rather than the postmortem discussion deliberately made by later historians.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discussion of disas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signs of disasters before and after Liu He'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is reasonable and in line with the will of Heaven.
Liu He, Xiahou Shichang,, opinions on
I206.2
A
1673-9639 (2022) 06-0001-13
2022-07-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纬书文献的综合整理与研究”(20&ZD226)。
吕宗力(1950-),男,广西陆川人,博士,南京大学特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制度史,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史,古典文献,民间信仰,谶纬。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
——《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