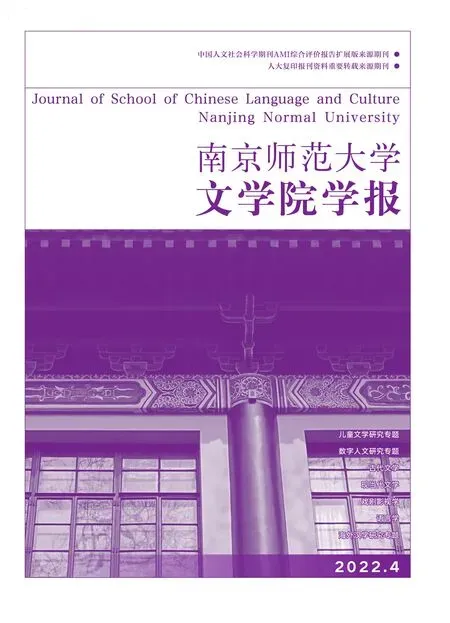“一片”辨
方 均
(江苏畜产进出口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2)
诗圣杜甫的七律《曲江二首》中第一首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在杜甫的诗作中它不能算是最好的,但从古到今,在各种杜诗和唐诗的选本中,它的入选率却相当高,看来颇受诗评家和鉴赏家的青睐。这首诗除了颔联“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句法有点奇特外,其余的都很明白易懂,应该不会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然而,近日翻书,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诗的第一句“一片花飞减却春”中的“一片”这个词语却居然一直被误读着。
初看,这只是对小小的一个词语的误读,似乎无伤大雅,但细一考究,却是事关对语言规范的准确掌握和维护,事关对诗歌审美意象的精微认知和体验,甚至还可能牵涉到对诗作品格的高下优劣的评判。所以,我认为把“一片”这个词语提出来作一番辨析,从而让这个可能几近千年的误读得到纠正应该不但不是多余,而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先从近的说起,在《莫砺锋诗话》中题为《春》的一文中谈及杜甫的这首诗时,有这样一段话:
杜甫在曲江头看到繁花似锦的枝头忽有一朵花瓣飘然落下,不禁惊呼“一片花飞减却春”,及至风雨交加落红成阵,敏感的诗人又当如何感慨?(1)莫砺锋.莫砺锋诗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在这里,把“一片花飞”解释为“一朵花瓣飘然落下”,而且又用了“及至……又当……”的句子表达式将之与“落红成阵”(也就是第二句中的“风飘万点”)看做是一种数量上的对比递进关系。无独有偶,在叶嘉莹教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的第一篇讲演《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关于这首诗,则有这样的说法:
杜甫《曲江》诗说“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写得很好,具有诗人敏锐的心灵……他看到一片花飞就感到春光不完整和破碎了,所以说“一片花飞减却春”。接着又说“风飘万点正愁人”何况等到狂风把万点繁红都吹落,当然更使人忧伤。(2)叶嘉莹.古典诗词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3页。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把“一片花飞”解释为“一朵花瓣落下”,不过,从后面那句“何况……当然更……”的句子表达式来看,显然也还是把“一片花飞”与“风飘万点”理解为一种数量上的对比递进关系。
再如,《唐诗鉴赏辞典》中收有霍松林教授撰写的对《曲江二首》的鉴赏文章。关于这句诗他就十分明确地解释为:“‘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还有,已故陈贻火欣教授在他的《杜甫评传》中,提到《曲江二首》时也有如下的说法:
花飞一片便觉春减,极言之以衬托风飘万点之愁,也含有知微见几的哲理意味。
“‘极言之’和‘知微见几’强调的仍然是一种数量上的对比递进关系。”根据以上的这些说法,不难看出,四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一片”这个词语理解为是数词“一”加量词“片”的数量词。
不错,“片”和汉语中的大部分量词一样,是一个从名词演化而来的量词。它本来的意思是“判木也”(许慎:《说文解字》);木被剖开后“左为爿,右为片”(《辞海》引《九经字样》)。后来就演变为表示“物之单薄而面积相形见广者”(《辞海》)或“物之薄而平者”(《辞源》)的单位的量词了。例如:
一片面包 两片火腿 三片西瓜 四片树叶 五片羽毛 等等
在固定的成语中,则有:
片言只语 吉光片羽 片甲不留 等等
应该说,《辞海》和《辞源》对“片”这个量词作出的是用在“物之单薄而面积相形见广者”和“物之薄而平者”上的概括性定义还是比较正确的。(窃以为如果再能加上一句:“从某一整体中分割下来或从数目众多的族群中分离出来的”那就更加准确。)
诗人徐志摩在其著名的《再别康桥》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云”为何物,而用“一片”,合适吗?合适的。你细想一下,这“一片云彩”不是可以理解为从整体的云团或云层中分离出来的相对而言的较为单薄者吗? 这样看来,专家们把“一片花飞减却春”中的“一片”认为是数词“一”加量词“片”的数量词,把“一片花”解释为“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似乎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首先,从我们的语言使用习惯来看,“片”这个量词我们一般并不与“花”这个名词连用。花作为整体,它并不能被视为“物之薄而平者”,所以,对于花我们不论“片”,而是论“朵”,论“枝”,论“束”,论“簇”,甚至论“树”等等,我们习惯说“一朵茉莉”“九十九朵玫瑰”“一枝梅”“一束康乃馨”“一簇郁金香”“一树梨花” 等等,在诗句里则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不过,一朵花总是由若干花瓣组成的,而花瓣才是从花朵这个整体上分离出来的“薄而平者”,所以花瓣才可以论“片”。这也就是为什么莫教授在同一本书的另一 篇题为《花》的文章中提到杜甫的同一首诗的同一句时会说:“春色正浓之时,诗人忽然看到一片花瓣随风飘落”,这就把在《春》一文中那个“一朵花瓣”的不甚规范的说法改正过来了。其实,“瓣”这个名词也已经经过演化,可以作为量词来用。“一片花瓣”可以说成“一瓣花”,如果“一片花飞”所表示的真的是为了突出“一片花瓣随风飘落”,那是完全可以说成“一瓣花飞减却春”的。
其次,“一片”这个词语在其使用的历史演化中并不安分,似乎决非只是一个作为数量词的功能可以限制得住的。且看下面的例子:
一片苦心 一片孝心 一片丹心
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一片闲愁,芳草萋萋(辛弃疾《一剪梅》)
一片春愁待酒浇(蒋捷《一剪梅》
这里的“心”和这里的“愁”还可以说是“从某个整体中分割下来或从数目众多的族群中分离出来的”“物之单薄而面积相形见广者”吗?显然不能。这里的“一片”所限定的“心”(或“愁”)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心脏或某个具体的物,而是向某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心情”“感情”“情怀”“情绪”等发生了转移。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指出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个“一片”中的数词“一”已经不再能用其它的数词来换用了。它只能是“一片”,而决不能说什么“二片冰心”“三片苦心”“五片春愁”等等,原来,这里“一片”这个词的使用在语法的形态和功能上都已经稍稍地偏离和逸出了“数量词”的范畴。(3)有关语法学的形态与功能问题,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和2009年出版的徐思益著《语言研究探索》中的相关文章。与此相类似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片”这个词在对“声、光、色”的描述时的使用频率很高的例子:
声:一片哭声 一片骂声 一片掌声 一片欢呼声
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
一片神鸦社鼓(辛弃疾《永遇乐》)
光: 一片阳光 一片火光 一片金光 一片霞光
色: 一片金黄 一片漆黑 一片白茫茫 一片绿油油 全国山河一片红
长安一片月(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对古来一片伤心月(辛弃疾《贺新郎》) ( 这里的‘月’当然指的不是月球那个具体的物,而是‘月色’。)
一片丹青(辛弃疾《临江仙》)
在这些例子中,“一片”中的“一”同样不能换用其它的数词。上面我们说它只是“稍稍地偏离和逸出了数量词的范畴”,那是因为虽然它所限定的已经不是那个“从某一整体中分割下来或从数目众多的族群中分离出来的物之单薄而面积相形见广者”,其表示“数量”的意味也相对地有所减弱和淡化,但它所限定的毕竟还是一些名词概念,即便是比较抽象的(如声、光、色)或十分抽象的(如苦心、孝心、闲愁、春愁)概念也好。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是“一片”这个词还有下面的这样一些用法:
一片狼籍 一片模糊 一片苍茫 一片沉寂 一片惊慌 一片混乱
形势一片大好 前景一片光明
显而易见,这些“一片”的用法与数量词的范畴已经不是稍稍地偏离和逸出,而是相去胡越了。因为,从语法形态上看,除了这个“一片”的“一”决不能用其它数词替换外,它所限定的也已经不是表示某种“物”(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的名词概念,而是表示某种“动态”或“情状”的动词或形容词的概念,因而它的语法功能也就变成为一种副词和状语的功能。
辨析至此,我们自然就可以肯定地给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片”这个词除了表示“物之单薄而面积相形见广者”的数量词用法外,还存在着一种副词的用法,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短语用来描述某种或散布、或充塞、或笼罩、或弥漫在某个具体的或相对抽象的空间中的状况,这个状况可以是动态的(一片唏嘘、一片惊慌、一片混乱等),也可以是静态的(一片沉寂、一片狼籍、一片光明等)。 让我们再回到杜甫的诗句上来。“一片花飞减却春”这句诗中的“一片”是哪一种用法呢?无疑应该是后一种用法。因为,与其说杜甫在这句诗中关注的是花瓣的数量,不如说他更为关注的是“花飞”这一散布弥漫在曲江畔这一特定空间内的动态的状况,这样说难道不是更为自然合理,更为说得通吗?
以上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一片”这个词语所进行的辨析,也许有人会说,诗圣杜甫这句“一片花飞减却春”是诗的语言,是不能与一般的日常语言同日而语的。那好,我们下面就再从诗学的角度来进行辨析。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杜甫这首诗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请问,他当时“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而使他产生了创作这首诗的“情”呢?我们无妨来进行一番想象。
那是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的春天,杜甫踽踽漫步在长安曲江头(也可能是独坐在曲江畔的某座酒楼中),举目望去,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什么?按照上面所引的专家们的说法,他看到的应该是只有“一片花瓣”飘然落下,于是,具有“敏锐的心灵”(应该再加上“极好的视力”)的诗人“就感到春光不完整和破碎了”,接着,他就想象起将来“风飘万点”的景象(也就是“及至……又当……”“何况等到……当然更……”的语句表达式的含义),并用它来和眼前落下的“一片花瓣”对比,从而伤从中来感慨万千。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杜甫当时看到的是“风飘万点”“落红成阵”的景象(这应该是更为可能的情况,因为诗的第二句明明是“风飘万点正愁人”,大家知道,“正”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表达的就是当下即时的意思。还有第三句“且看欲尽花经眼”,且不说“且看”“经眼”也含有当下眼前意思,就说那“欲尽花”则该是“飘零殆尽”的花,怎么能和仅仅“一片花瓣”扯上什么关系呢?)那么,表达“一片花瓣飘然落下”的“一片花飞减却春”就只能是一种通过极为理智的逻辑推理思维再用之来和“风飘万点”比较的对以往景象的回忆?
两者必居其一。然而,不论是对将来的想象也好,对以往的回忆也罢,就都把诗圣创作的审美观照和审美意象从好端端的“现量”生生地推向“比量”去了。什么是“现量”和“比量”?这是明末清初的古典哲学家和诗学家王夫之从古代印度因明学中移植过来的诗学范畴,对之他有这样的解释: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比量”,“比”者以种种事比度种种理。(4)王夫之.船山全书[M].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美学家叶朗认为王夫之的“现量”指的是“瞬间的直觉而获得的知识,不需要比较、推理等抽象思维活动的参与。……是真实的知识,……是把客观对象作为一个生动的、完整的存在来加以把握的知识,不是虚妄的知识,也不是仅仅显示对象某一特征的抽象的知识”,王夫之“强调诗的审美意象必须从直接审美观照中产生。……这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谁也不能违背”(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这也就是说,“现量”实际上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本质性的特性,是诗之为诗的关键所在。所以,在王夫之众多诗评中,对诗的品格高下优劣的评判,往往也就以他的“现量”说作为根据:
不以当时片心一语入诗,而千古以还,非陵、武离别之际,谁足以当此凄心热魄者?
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
情感须臾,取之在己,不因追忆。若援昔而悲今,则如妇人泣矣,此其免夫!
就当境一直写出,而远近正旁情无不届。
寓目吟成,不知悲凉之何以生。诗歌之妙,原在取景遣韵,不在刻意也。
心理所诣,景自与逢,即目成吟,无非然者,正此以见深人之致。
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睽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
祗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俗目不知,见其有叶落、日沉、独鹤、昏鸦,辄妄臆其有国削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六义中唯比体不可妄,自非古体长篇及七言绝句而滥用之,则必湊泊迂窒。(6)王夫之.船山全书[M].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所以,如果我们在解读杜甫的诗句时把“现量”解读成了“比量”可不是件小事,那无异于降低了诗圣诗作的品位。其实,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对词语“一片”的辨析,能够正确解读“一片”的含义,我们就会意识到,诗圣在他的诗句中吟咏的都是他当时“触”到的景,既没有想象也用不着回忆,那是完完全全的“现量”。因为“一片花飞”和“风飘万点”实际上就是同样的审美意象,都是诗圣同时“触”到的“景”,“一片花飞”并不是只有一片花瓣飘然落下,而是当时散布弥漫在曲江头这个特定的空间内的一个动态的状况:花瓣儿一片、两片、三片……许多片地不断飘落下来,纷纷扬扬地在空中飞舞着、飞舞着、飞舞成了一大片!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由此感到,春天在渐渐地远去了。
或许又有人会说,如果“一片花飞”和“风飘万点”说的是同样的审美意象,那岂不犯了语义重复的毛病?不然。这里倒毋宁说正是表现了诗圣在诗歌语言运用上的游刃有余和多姿多彩。他驾轻就熟地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反复传达出同一个审美意象,以此来加深加强给人的印象,使之更鲜明、更生动。第一句先是突出了自然现象的客观效果,第二句就顺势引出了主观上的感伤情绪。更何况,杜甫本来就是一个并不避忌重复的诗家圣手。不用到别处去找例子,就是这首《曲江》诗,有一个版本的第二句的“风飘万点”是‘花飘万点’,一个‘花’字竟重复了三遍!为此有人还惊叹道:“……三句连用三‘花’字,一句深一句,律诗至此,神化不测,千古那有第二人。”(7)查慎行.初白庵诗评[M].张载华辑.清乾隆42年(1777)刻本。
写到这里,对“一片”的辨析就可告一段落。但这时我们心中却不禁会生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专家们又会如此不约而同地出现误读呢?开始,这确实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后来,再多翻了些古书才发现,原来他们这是受了古人们的误导。其中第一个古人叫方回。他是宋末元初人,五十七岁(公元1283年)时写成了一部唐宋间律诗的选评集《瀛奎律髓》,书中在评论杜甫这首诗时就说:“第一句、第二句绝妙。一片花飞且不可,况于万点乎?”这应该就是把“一片”和‘万点’解读为数量对比递进关系的滥觞。后来,以讹传讹, 明代的王嗣奭便说:“起句语甚奇,意甚远,花飞则春残,谁不知之?不知飞一片而春便减,语之奇也。以比君心一念之差,便亏全德,朝政一事之失,便亏全盛,……盖花既飘未有不尽者,以比君骄政乱,未有不亡者,故欲尽花更进一步,危斯极矣,愁更甚矣。……前六句皆比也。”(8)王嗣奭.杜臆[M].北京:中华书局,1963。发挥得淋漓尽致,真可谓极尽比附之能事。到了清代,注杜大家仇兆鳌也说“一片花飞至于万点欲尽,此触目之堪愁者。”(9)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还有个金圣叹则说:“本为万点齐飘,故作此诗,却以曲笔倒追至一片初飞时说起。……看他接连三句飞花,第一句是初飞,第二句是乱飞,第三句是飞将尽。裁诗从未有如此奇事。”(10)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 [M].周锡山编校,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9。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即我们的古人在评注诗作时所下的评语往往都是些即兴的印象式的直觉感悟领会。你并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系统的,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思辨,更无法苛求他们有什么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学知识了。不过,他们这种“灵魂在杰作中寻幽访胜”(法朗士语)式的评语又常常是说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从而一不留神就被他们误导的事,也就不足为奇。
于是,对杜甫的这句“一片花飞减却春”就有了几近千年的误读,(即使从公元1283年算起,至今也已有七百余年,而1283年以前,虽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但也很可能是早已被误读着的。)而现在通过以上的辨析是否就可以说是已经把它纠正过来了呢?那也未必,因为在对诗歌艺术的评赏和对诗歌语言的解读上向来就是见仁见智,很难有绝对的是非标准,所谓“诗无达诂”,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过,把问题提出来,辨析明白,对后来的读者作为一个提醒,应该还是有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