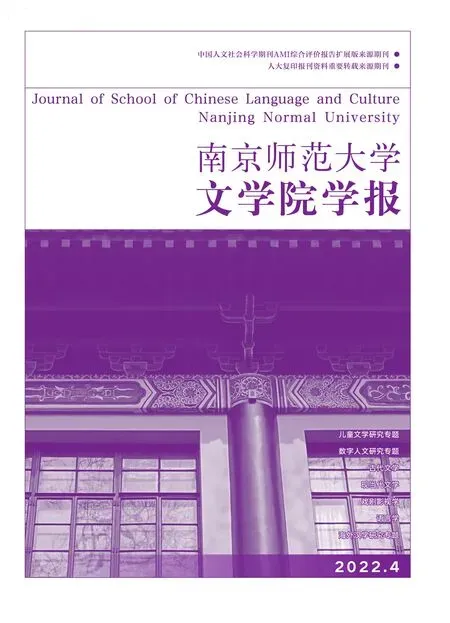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政治
吴翔宇 任 超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身体是一种“两面性的存在物”,既负载着对最高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1)汪民安主编.生产(第2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22页。。循着身体的标记,可以“指示着身体进入文字领域、进入文学的途径”(2)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8页。。论及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需要正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从身体政治的切点中寻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特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历史化的整体,现代儿童观的发现、出场与拓展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线,这契合了现代中国发展的演变进程。在国家文学体制的框架内,新中国儿童文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体化”的关系,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政治的副本,其“主体性”依然存在,身体书写则以具象化的文本形式反映了这种深微的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为中国儿童文学指明了方向,“儿童本位”思想中被注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涵。问题在于,返归元概念,儿童文学是由“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内外两面构成的。在获得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时,新中国儿童文学也不能丧失自身的本体特征。“一体化”与“主体性”的“矛盾与统一”贯穿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脉络。简论之,新中国儿童文学中的身体书写集结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体现为一种专属于儿童文学的身体政治。
一、出场及性质:儿童本位与身体意识的重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批评陷入了“模式化”的惯性思维,有代表性的看法是,1930年代革命儿童文学和延安解放区儿童文学是其知识范式的源头(3)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第213页。。相对而言,忽视了其与“五四”儿童文学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新中国儿童文学是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以及战争年代“革命—救亡”主题的左翼儿童文学延展的结果。研究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首先要回到现代儿童观的发生场域,从儿童文学的理论原点中透析“五四”精神对其发展的推力作用。在此基础上,考察新中国儿童文学对“纯化”与“泛化”儿童观的继承及超越。其次,从身体书写的内容与形式来看,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并未脱离由左翼儿童文学开创的“革命范式”(4)吴翔宇.左翼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范型”的重构[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第111页。。同时,为了适应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构建,“左翼范式”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的内涵。在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被纳入国家体制,成为了一种“国家文学”(5)吴翔宇.国家文学体制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第44页。。
从身体书写发出,不难窥见新中国儿童文学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具有“体制化”与“反体制化”的多质性。一方面,在一体化的文学机制中,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需要合乎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为了获取国家文学制度的助力,儿童文学确立了与新中国政治合辙的原则,利用“体制化”的身体书写自觉承担了传达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使命。另一方面,新中国儿童文学又需要维持其作为儿童文学的独立品格,在文学与政治交互的裂隙中,以“反体制化”的身体书写彰显“为儿童”与“为文学”的本体意涵。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并非受到政治或文学单向度的牵引,“体制化”与“反体制化”也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缠绕、相互融合的新格局,即蔡翔所谓“体制的反体制性,反体制的体制性”(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页。。因之,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视域中,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内隐了五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本体诉求,依托左翼文学“革命—救亡”语境中的范式,以“多质性”的文学样态编织于一体化的文学系统中。
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董之林指出研究“十七年文学”容易忽略其复杂性,“十七年文学”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断裂,是一个不成功也不紧要的阶段”(7)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页。。同样的际遇,新中国儿童文学与五四儿童文学的关联也常常遭到忽视。从元概念出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确立,得益于现代知识分子对儿童身体观的重新认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人深切地意识到人的解放是民族复兴的前提。病态与失语的传统儿童形象遭到了认同危机,人的发现以及儿童的发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为五四知识分子重建中国形象、想象未来国民提供了现实路径。作为“意义给予行为的前提条件和机体”(8)[美]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梅洛—庞蒂[M].关群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20页。,身体成为了区隔成人进而发现儿童的“始发点”。
在现代研究视域中,“身体”概念不仅涉及肉体(flesh)层面,而且渗透至精神(mental)层面,是混合了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含混的存在(9)[法]梅洛·庞蒂.哲学赞词[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48页。。扩而言之,取消了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为身心一体的复合物。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就将身体视为“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他认为对待儿童“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10)毛泽东.体育之研究[J].新青年,1917(2)。,并主张利用儿童躯体的成长带动其精神成长。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基于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鲁迅重申了现代儿童身体的“非成人性”:“所以这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有感于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通过将儿童与成人直接对比,鲁迅将儿童定义为“即我非我”的人,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当“同时解放”(1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37-141页。。通过承认儿童在身体维度的独立价值,儿童的发现楔入了“人”的发现的体系中,进而使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具有了“身心合一”的现代品格。
基于儿童的发现,儿童身体的特殊性催生了儿童文学本体建构的内在诉求。在“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上,有学者将儿童与原始人类比,借用原人的文学来创构儿童的文学。在《儿童世界宣言》中,陈伯吹指出:“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12)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A].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65-66页。显然,这与周作人等人所提倡的“复演论”颇为类似。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13)周作人.儿童的文学[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第274页。张梓生也有类似的表达:“人在孩提的时候,在知识发达上讲起来,与原始人类同在一阶级;他所能了解,所最喜欢的,就是类似神话的童话了。”(14)张梓生.论童话[J].妇女杂志,1921(7)。童话、神话、儿歌纳入儿童文学成为了先驱者的共识,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构建。然而,即便认为儿童与原人相近,周、张二人也不否认两者的差异性。周氏认为,“儿童心理既然与原人相似,供给他们普通的童话,本来没有生命不可,只是他们的环境不同了,须得在二十年经过一番人文进化的路程,不能象原人的从小到老优游于一个世界里,因此在普通童话上边不得不加以斟酌”(15)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一[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第586-587页。。周作人认为儿童亦是不等同于原人的独立个体,因此儿童文学应该有区别于“成人文学”“原人文学”的独立品格。
儿童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身体与成人不同,更体现在儿童作为精神的主体存在着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随着儿童年龄的成长,其生理与心理均会发生改变。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为其提供相适应的文学,构成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儿童有没有文学的需要》中,魏寿镛、周侯予利用儿童肉身的成长推演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身体变化的层面指出了儿童成长的特点,“这是儿童生活,他一路转变生长;我们对付的方法,也一路转变。肉体如此,精神也是一样”(16)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有没有文学的需要[M].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75-81页。。从儿童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郭沫若提出了认识身体的必要性,“儿童身体决不是成人的缩影,成人心理也决不是儿童之放大。创作儿童文学者,必先体会儿童心理,犹之绘画雕塑家必先研究美术的解剖学”(17)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M].郭沫若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77-229页。。戴渭清将社会因素注入儿童本位观,提出儿童身心与文学思潮存在呼应关系,“适应现代文学思潮的儿童文学,是儿童普遍心理的文学;适应儿童心理的儿童文学,是仿佛儿童真情之流的文学”(18)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M].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93页。。凡此等等,都能看出现代知识分子将儿童的身体视为区隔成人的显在标记,发现儿童可从发现儿童身体入手。
秉持“身心合一”的身体观,新中国儿童文学基本接续了新文化人对身体的理解,同时又注入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与使命。《人民日报》刊载的《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明确提出新中国儿童文学应承担培育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责任义务:“我们必须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把他们培养成为体质健壮,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知识、生产基础知识及文化教养的新人,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就可以继承长辈的事业,把艰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任务担当起来。”(19)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N].人民日报,1955-09-16。由上可知,被纳入国家文学的儿童文学是确证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载体,在培育儿童身心发展的层面上发挥着其独特的价值。
不过,在对待五四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新中国儿童文学并未采取全盘接纳的态度。相反,过度纯化、窄化儿童及儿童文学的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却遭到了批评与否弃。在中央高度重视儿童读物的背景下,郭沫若呼吁儿童文学应具有革命现实性,他批判部分旧有的儿童故事或寓言是出于“纯粹的空想”,有许多同今天的要求是不合适的(20)郭沫若.请为少年儿童写作[N].人民日报,1955-09-16。。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在此时受到广泛关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牵引下具有了明晰的方向性。这种方向性就体现在儿童身体的描摹与书写之中,它也成为窥测政治意识形态的视窗。同时,社会性、政治性注入中国的儿童文学观,也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的新变,在新中国文学的“一体化”格局中丰富了“儿童本位”的内涵。
二、他属与自属:“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身体辩证法
为了适应新中国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话语体系,儿童文学的艺术性需要服从于思想性与政治性。儿童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受到了国家文学的整体体制的驱导,政治对儿童文学的规制“集中在身体上并通过身体得以表现”(21)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第1页。。身体是反映文学与政治交互关系的窗口,对儿童身体的描摹也铭刻了时代的烙印。概而言之,新中国儿童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存在福柯所说的两种“主体”(22)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3,p212。性质。首先,是权力造就的“他属”的身体。阿甘本认为,现代国家同古代社会区分的标志之一,是将身体作为政治保护以及其权利赋予的对象:“成为新的政治主体的不是自由人(及其法律和特权),甚至不是绝对的人,而毋宁说是身体”(23)甘本.生命的政治化[M].汪民安主编.生产(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22页。。在政治的指挥棒下,新中国儿童文学积极主动地承担传达国家话语、建立文学规范、教育和引导儿童读者的责任使命。同成人文学一致,儿童文学也会受到“党性”“政治性”的引导和重构,儿童的身体成为了隶属于国家政治话语所想象和认可的“他属”的身体。显然,这种“早熟”的身体容易造成儿童的成人化倾向,遮蔽了儿童身体的“私人性”与“自然性”。在这里,儿童文学对“一体化”的反映与其“主体性”的诉求形成了一种显隐的张力结构。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新中国儿童文学在左翼文学构建的“革命范式”中被重塑。个人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语境中,身体的出场变得朦胧,儿童成为了“缺席的在场者(an absent presence)”(24)Cris Shilling:The Body in Cultur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5,p16。。《永路和他的小叫驴》《没有路条,不能通过》《芦苇里响起了枪声》《竹娃》《篝火燃烧的时候》《保卫红领巾》《小兵张嘎》《杨司令的少先队》《小游击队员》《闪闪的红星》《雨来没有死》《鸡毛信》《野妹子》《红色小哨兵》《黎族少年刘信文》《英雄的儿童团长谢荣策》等作品都对儿童的身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夸张与美化,具体表现为:将其塑造成能够勇敢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的英雄的身体。这样一来,儿童身体的公共性被强化,个体性则被淹没在这种集体的政治指向中。在《没有路条,不能通过》中,苏苏用极简的文字描写了一群革命时期把守寨口的“娃娃们”,他们有着与年龄极不相仿的特征:“一个拿着大刀的男孩子,看样子有十四五岁了,他带着他老爹的皮帽子,那么不相称,走上前来,态度很好,说话也和气。”同时,儿童自身的特殊性通常被革命话语所掩盖,留下了表意革命的身体语言:“那个拿大刀的儿童团员”“我们就在大刀、红梭枪中一起进了牛家寨子”“大刀、梭枪,在雪花团团转的天空中摇动起来”。在叙述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民族国家需要的是如刀一般坚忍和锋利的身体。这些作品弱化了男孩身体的“肉身性”,而是用“大刀”突出表现了战争语境中对理想身体的迫切渴望。李心田创作儿童小说的初衷是要让青少年不忘记“辛酸的童年”,并要把它告诉当今的青少年”(25)李心田.我和儿童文学[J].儿童文学研究,1992(2)。。他还说:“我不回避我的作品要对青少年进行某种教育,如果不这样做,我会遗憾的”(26)李心田.不要讳言教育[J].儿童文学研究,1992(1)。。新中国初期,小英雄刘文学的故事流传后,就出现了多种文体书写同一人物的现象:袁鹰创作了叙事长诗《刘文学》、贺宜撰写了儿童小说《刘文学》、中国儿童剧院创作了话剧《少年英雄刘文学》、儿童艺术剧院集体创作的儿童剧《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与“刘文学”故事跨文体书写相似,《闪闪的红星》从儿童小说到电影的版本变迁也是跨学科和艺术门类的。不过,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多种文体的集体书写属于“合鸣”式的,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提升等方面趋于一致,而后者的改编则受制于新中国70年代时期诸多原则的规约,出现了并不趋同的差异。总体而言,修改后的电影剧本更突出在典型环境下来塑造潘冬子这一英雄形象,通过简化了其身体的自然属性来强化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象征功能,由此赋予潘冬子成长的“高起点”(27)王尧.《闪闪的红星》:电影对小说的修改[J].小说评论,2011(3),第66页。。
为了表现阶级矛盾,身体往往被赋予了阶级对立的指向性。在儿童文学中,儿童的身体也归入了阶级政治的轨道。《打狼要打死》《野葡萄》《双筒猎枪》《小仆人》《琴声响叮咚》《神笔马良》《奇异的红星》《上学》均描写了一种“去身体化的符号式”(28)韩雄飞.身体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1917-2020[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第116页。的儿童形象。《奇异的红星》借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身体受到了民族国家情感的驱动而被赋予了阶级对立的色彩。作为无产阶级的后代,阿力拥有一个年轻而健壮的身体:“这个儿子气力很大,胆子也很壮。他今年才十五岁,可是在村里,没有一样重的东西他扛不动,也没有一个高的山头他爬不上。”作者刻意强调了阿力“力气大”“胆子大”等身体的功能性,而没有用多余的笔墨描写这位十五岁儿童身上的儿童特质。在与恶魔斗争时,阿力拥护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家通过身体书写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意志,“他的脚板破了又结茧,结了茧又破了,血和汗交替地浸渍着他的双脚”。在一系列的身体书写中,儿童身体层面的阶级性被放大,争夺身体也就意味着阶级性的博弈。在共产党人的启发下,阿力转而领悟到只有走群众的路线才能获得更多的人的力量,只有“红星”的真理才能完成阶级斗争。在这里,阿力的身体超越了个人性,而是萨特所言的“他人的身体”(29)[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432页。,与人民的身体达至了某种“同一的结构”。相反,在塑造指代地主阶级的人物形象时,反派角色的身体通常是丑陋的、被贬损的,且与劳动人民相对立。譬如,《奇异的红星》中“脸色苍白,用针来刺也刺不出一点血”的恶魔、《双筒猎枪》中“面露狰狞,不蓄胡髭”的地主田雨叔公、《鸡毛信》中“鼻子跟蒜头一样大,嘴唇又黑,又厚,真是又凶又丑”的日本鬼子即可作为显在例证。
其次,新中国儿童文学中也存在儿童“私人身体”的展现。同成人文学一样,儿童文学在反映政治的过程中依然会保留自身的独特性,有“规训”所不能规训的东西(30)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8页。。从尼采对“身体与力本身”的关系出发,汪民安发现民族国家身体与个人身体是一种二重力的强化:民族国家身体需要借助个人之力才能强化自身,它是个人之力的聚集、表达和再现,只有个人身体得到强化,国家身体才能得到强化,这二者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吸引(31)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37页。。换言之,国家身体既要控制个人的身体,使其不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但同时又要允许其自在的、自然的发展,展现个体的内在生命力。这种“自属”的身体是儿童文学“儿童性”的自然流露,使其在同一化语境中保留了自身的主体特征。
在革命与历史的叙述中,新中国儿童文学存在某种“溢出”同一化语境的倾向,即在承认、遵从宏大的社会框架前提下展现儿童真实的写照(32)吴其南.从仪式到狂欢——20世纪少年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19页。。身体书写虽然受到一体化话语体系的限制,但是它常常能通过各种隐秘的方式表达自身,这里一方面存在和意识形态的某种妥协,另一方面也存在“身体”乔装打扮后的“出场”(33)李蓉.从身体“悖论”出发[J].文艺争鸣,2012(9),第69页。。质言之,儿童文学对本体性的体现,并未使其脱逸出国家文学的整体结构,两者在矛盾和统一中共构了新中国革命范式的新传统。
在新中国儿童文学中,“红色儿童”的成长故事并不鲜见,难能可贵的是,儿童的身体在革命历史的成长历程中也处处流露出属于“儿童”的特性,如《小兵张嘎》中嘎子与胖墩打赌进行摔跤比赛,在套间关紧闭时又抓起了家雀儿;《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将“皇军”谑称“黄军”、对潘行义的感情超越了革命信物“红星”;又如《鸡毛信》中海娃面对鬼子的质问故意歪起脑袋,张开大嘴巴装傻等。这种一出场并非英雄人物的设置,与红色革命历史叙事原则有着偏离,因而所书写的不过是“革命英雄前传”(34)张楠,重读《闪闪的红星》[J].小说评论,2013(2),第139页。。事实上,这种跨越年龄的遐想套用班马的话说即是“儿童反儿童化”(35)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第34页。。“儿童化”曾被视为一种反对“成人化”倾向的、致力于达到儿童状态的追求。然而,在特定的情境下儿童并非固化于“儿童化”的状态下,儿童想要摆脱童年而向往成年的冲动被调动起来。班马曾列举《小兵张嘎》为例来分析儿童处处模仿成年人物的特色。张嘎不甘做留守在村里的儿童,其遐想本源于革命与成长的双重召唤:沉溺于童年不谙世事的幻境势必不贴合革命的正当原则,同时张嘎也受到走出“不成熟”状态的成长原则的牵引。与以往的类似小说相比,《小兵张嘎》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简化嘎子身上的独居特色的“嘎气”,也没有以先入为主的革命信仰、思想来牵引主人公的成长选择。
应该说,儿童身体的“自属性”仍然源自于革命与抗战的现实背景,并非“存在或源自于一个社会真空状态”(36)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228页。。儿童文学对本体特征的书写并非意味着可以脱逸“一体化”文学的框架,也不是要完全将儿童身体隐匿在逃避战争与无视历史的乌托邦中。有感于“儿童成人化”的倾向,王泉根曾提出儿童的“不知情权”(37)王泉根.“成人化”剥夺了童年的滋味[N].文汇报,2004-2-16。的观点。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小说中,这种“不知情权”显然是对儿童革命信仰及成长隐喻的阉割,对战争、政治、革命等宏大话语的“不知情权”无异于抽空了此类儿童小说“回述”历史、确证新中国合法性的条件。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主体性”与党性、人民性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相反,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改善新中国儿童文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的文化生态。在《双筒猎枪》中,任大星有意展现儿童身体的私人性,但却巧妙地将其置于阶级斗争年代的时代主题当中。主人公月华的出场具有闲适的乡村生活气息:“她整天赤着脚,在泥地上跑来跑去,帮助妈妈搬柴草、打水、喂鸡鸭什么的,光脚板老是发出噼拍噼拍的声音”。从开朗的少女“好像一下子变大了几岁”,月华的突然长大不是自然性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战争的牵引。在塑造人物的立体形象时,任大星并未剥夺儿童对时代与社会的“知情权”。在作品中,“我”与月华的情感是复杂而微妙的,并以“局外人”的身份目击了月华的一生。一方面,在革命政治的场域中,两个同龄儿童间的情感慰藉弥补了家庭破碎、物质匮乏带来的精神伤害;另一方面,作者并未遮蔽少男少女之间的朦胧情感,而是将其若隐若现地融于主题叙事中。第一次面对月华时,“我”因害羞而脸红,十七年后重回旧地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急急想知道月华的消息”。作者用白描手法描写了月华死亡时的身体,加深了个体面对战争时的无力感。“解放前,她被地主用双筒猎枪打伤了大腿,没钱医治,后来变成了疮,烂了几个月,发热病死的。”通过对月华死亡的追问,个体的命运悲剧在时间的纵深处具有了某种普遍性,蔓延至历史革命的洪流深处。关于这一点,刘绪源认为任大星在处理少年情感与战争生活时把握了恰好的“分寸感”,“让人丰富沉入一种少年的心理的深渊,得到非常充实的审美享受”(38)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第130-131页。。正因对儿童私人性的描摹,使得新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反公式化、反体制化的新范式。
在“他属”与“自属”交织而成的身体话语背后,其实质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写儿童”与“为儿童”两种创作观念的矛盾与统一。深受左翼革命文学的影响,新中国儿童文学在进行主题叙事时往往通过身体书写强化革命年代的思想性与阶级性。依循“写儿童”而非“为儿童”的创作观念,将“儿童”作为方法来反映国家文学的思想意识,儿童的私人性被搁置在主题叙事的框架之外,因而造就了身体的“他属”性质。相反,本着中国儿童文学“为儿童”的本体理念,“自属”的身体的出场在文学一体化的话语体系中弥补了个体性、艺术性的缺失。事实上,在新中国儿童文学中,具有普遍性的是“他属”的身体,身体的“自属性”仅是偶然地出现在体制化、透明化之外的文本裂隙中。但正是这种“偶然的出现”,使新中国儿童文学从根本上拯救了“人”的失落,“自我”的失落以及文学本体的失落(39)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57页。。
三、功能与审美:“教育性”与“社会性”的身体协商
新中国儿童文学广泛再现了“革命斗争、工业建设和农村土改”等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现场,并通过书写符合民族国家想象的“新人”身体在新中国“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中获得某种“合法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历史传统的惯性和政治化的“思维定势”(40)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第8页。中,文学向政治的偏转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儿童身体的“自然性”,造成了身体书写的体制化、模式化。然而,儿童文学的本体特征并未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完全受遮蔽。相反,新中国儿童文学中也存在彰明文学独立性和特殊性的身体,它们以潜隐的方式处于文本的边缘和裂隙中,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反抗”。身体在这里超越了表层意义的生理学概念,成为了新中国儿童文学表征“一体化”思想、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符号”。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在表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要反映“社会的解放”。同成人文学一致,儿童文学也需要书写合乎新中国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继承五四儿童文学与左翼儿童文学的基础上,新中国儿童文学建构的新人不仅要抛弃旧式的观念与身份,而且要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下从个人走向集体。为了明确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方向,“教育”概念的介入无疑会削弱了儿童的私人性。教育性连同思想性都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管控,然而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通常情况下,儿童文学因其特殊性被认为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绝缘的“净土”。彼得·亨特指出,相关研究认为儿童文学难以接受意识形态的渲染,“因为大家仍普遍假设,儿童文学应该“纯真”得不必关心性别、种族、权力等——或者应该只去传达被设计得很透明的信息”(41)彼得·亨特.理解儿童文学[M].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第56页。。在《关于儿童的书》中,周作人也曾反对将政治意识形态等“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混杂在儿童文学中:“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42)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第194-197页。。然而,周氏实则陷入了某种逻辑悖论,他一方面主张“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另一方面又反对将政治因素注入儿童文学,实际上是忽略了儿童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将儿童文学悬置于脱离现实的“真空地带”。
事实上,儿童文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作为语言的艺术,儿童文学的语言实践并体现了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43)Clare Bradford.Unsettling Narratives: Postcolonial reading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M].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7,p6。。没有超逸语言的思想,也没有脱离思想本体的语言形式,这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本体性”(44)吴翔宇.中国儿童文学语言本体论:问题、畛域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4),第2页。。新中国儿童文学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教育性与社会性被彻底激活,共同助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伟大工程。《罗文应的故事》《长长的流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蟋蟀》《刚满十四岁》《海滨的孩子》《妹妹入学》《采蘑菇》《省城来的新同学》《晓英入队》《宝葫芦的秘密》等文本都或多或少带有教育的意味,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对于儿童的某种期待和塑造。在《长长的流水》中,刘真描写了一个接受“整风”的革命女孩。虽然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我”却是一个处处“不懂事”的姑娘。在“我”与大姐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战争与历史的书写浓缩成为回忆,“我”的私人生活成为了小说的主体。“整风”实质上就是对儿童的教育与规训,大姐严厉地要求“我”进行学习,“我”的行为以及心理活动全然符合孩子的思想逻辑。“看!我还没有长大,就有了一个婆婆。”在身体书写方面,刘真重视细节描写,并未遮蔽“我”的天性。在转变对大姐的态度后,“我”仍然怀有不成熟的逆反情绪,想要逃离成人的管控。在私人空间中,刘真借助身体来展现儿童的游戏天性与自然性:“跑到小河边,我脱了鞋,坐在一块明光光的大石头上,把两只脚丫二伸进清清的水里泡着,两手打着拍子,唱起歌来。”然而,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与历史的联系,儿童的成长也需要时空的过渡。“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45)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232-233页。。换言之,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儿童的私人性受到教育性、公共性的挤压,开始接受社会群体所赋予的新的主体身份。从儿童文学的生成机制来看,儿童文学主要表征成人对童年的看法,而非“儿童自身的看法”(46)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徐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53页。。因此,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成人文化社会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长长的流水》中的大姐、《蟋蟀》中的振根叔、《晓英入队》中的辅导员、《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中的杨老师均充当了传达教育思想的角色。
由于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不对位”,使儿童文学中的代际矛盾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种“代际”包含一种将特定的历史想象加以符号化的姿态。真正构成“同一性”的不仅在于年龄和经历,更在于“所选择站立的位置,以及建构、表述时代体验的方式”(47)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统合,儿童身体的成人化、模式化成为了文学与政治的协商载体,冲破了这种代际关系的阻塞。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构成“成人—儿童”同一性的合法场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儿童文学本身的逻辑裂隙。以《闪闪的红星》为例,在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成长过程中,“革命”置换了一般意义上的“家”体制下的儿童教育,“家长”功能被传统家庭伦理之外的“革命”力量所取代,而成为“被替换的父母”(48)谢芳群.革命儿童叙事中“家长”功能的消解与转换——以《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为例[J].南方文坛,2013(2),第65页。。为了给“革命”话语预留空间,小说设置了潘冬子“无家庭”的情节:父亲潘行义参加长征走了,母亲被胡汉三烧死。这种“无父”的状态既是潘冬子寻父的精神根由,也为革命话语替代家庭话语提供了可能。然而,这种置换、取代并非生硬地消解。尽管父亲潘行义没有陪伴冬子走上红军战士的道路,但其少有几次的影响却是冬子的人生启蒙课。潘行义腿上中了弹,在取子弹的场景中,冬子见证了父亲的坚毅与英勇:“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中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49)李心田.闪闪的红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8页。。在与潘行义的对话中,冬子明白了“血债血偿”的道理:“也用枪来打,叫他们也淌血”。而潘行义也为冬子接续革命火种进行了进一步的革命启蒙:“记住,等你长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子”。在留给潘冬子一本列宁小学课本、一颗子弹头和一个红五星后,潘行义离家投入了革命队伍,父子的告别意味着传统家庭体制的破裂,也为冬子投身革命、在革命中成长提供了空间。而当母亲牺牲后,冬子真正变成了“无家”的儿童,也预示着其向“革命的战士”转变跨进了一步:“自从妈妈死后,修竹哥就是我的亲人,游击队就是我的家,我怎么能再舍得离开呢!”此后,修竹哥、陈钧叔叔、吴书记等游击队员正式成为冬子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导师。然而,冬子毕竟是个孩子,在战争年代不能独立地打“白狗子”,他还需要成人的庇佑。此后,宋大爹“接管”和“承担”了冬子父亲的角色。然而,不幸的是胡汉三却把宋大爹抓起来了,冬子再次失去了世俗意义上“家”的护佑。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胡汉三杀害,十三岁的冬子没有丧失斗志,他遐想自己快点长大:“我要快点长啊,长到了十五岁,我就来找游击队,那时我能扛得动枪了,跑得动路了,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打白狗子,打那些叫‘皇军’的日本鬼子”。1974年10月,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被改编成电影。作为视觉的艺术,电影《闪闪的红星》通过镜头语言书写革命年代对于物质身体的渴望,集中地呈现了潘冬子的“红色”成长历程。为了突出和深化主题,电影《闪闪的红星》集中呈现潘冬子与胡汉三及米店沈老板的斗争中的集体色调,通过潘冬子与儿童群像的同一化行为传达明确的阶级斗争思想,借此表现个体内在的某种“政治共约性”(50)叶志良,林可.国家的仪式:新中国儿童电影主题的身体建构[J].当代电影,2009(6),第116页。。
经过电影改编,“革命英雄前传”编织于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成长”的宏大议题中。电影改编后好评如潮。姚青新指出:“再一次宣告那些攻击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不适用于电影艺术谬论的破产。”(51)姚青新.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试谈彩色影片《闪闪的红星》对同名小说的改编成就[N].解放日报,1974-10-25。谢佐、殿烈也认为影片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为现实斗争服务方面取得了成功,“突出了潘冬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用生动的形象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52)谢佐,殿烈.歌颂小英雄 表现大主题——谈谈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J].红小兵通讯,1975,(第1、2期合刊)。。在观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当时的观众和影评人的反响热烈,出现了诸多评论该影片的研究成果。从儿童小说到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更为集中,但是表征儿童性的身体语言却随之弱化,“童心”“童趣”的成分几乎被坚硬的政治话语所遮蔽,这是思想性对于艺术性抑制的结果,也是我们反思新中国儿童文学不容忽视的重要角度和切口。
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儿童文学是左翼儿童文学的深化与具体化。借助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土壤,新中国儿童文学与五四儿童文学拉开了距离,摆脱了五四儿童文学在“儿童本位”与“社会本位”间游移的暧昧状态,明确了自身作为“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价值取向,自觉承担构建“社会主义新人”的责任使命。这在身体的描摹及折射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就能洞见其差异,关涉身体的知识范式的革新预示着儿童文学观念的转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分强化必然会抑制儿童文学艺术审美特性的自然生长,受到束缚的艺术性又会反过来制约思想性与革命性的传达。整体来看,新中国儿童文学创构了文学与政治相互融通的文学新范式,利用身体话语的混杂寻求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平衡。结合整体的历史语境,新中国儿童文学在一体化的机制中既有显在的顺应又有潜隐的反抗,这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先锋探索与本体的追索提供了前史。由是,新中国文学的整体视域中,儿童文学的价值与局限需要被重新评定。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