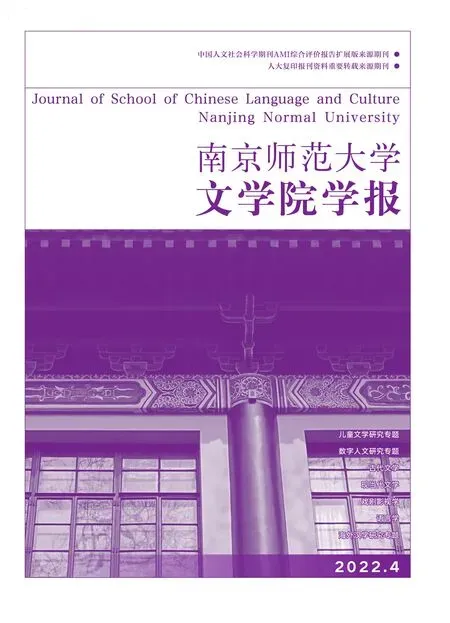从文人案头到勾栏瓦肆:《聊斋志异》传播的平民化趋向
——试论《聊斋志异》的说唱改编
刘总总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清中叶是讲唱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在历经了唐代变文、宋代陶真、金元诸宫调以及明代宝卷等艺术形式后,无论是表演风格还是文本创作都日臻完善。《聊斋志异》作为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尽管早期接受群体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但不可避免地出现受众群下沉的情况,其表现之一就是聊斋说唱的兴起,出现这一情况首先是大环境使然,其次,作者本身也起到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聊斋说唱形式逐渐形成聊斋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与弹词等四种。
一、聊斋俚曲
蒲松龄在世时并不满足于《聊斋志异》只作为案头读物在文人雅士间传播,他有着更为远大的济世之志,据其子蒲箬记载,他在创作间隙“摘其中之果报不爽者演为通俗之曲,无不脍炙人口”(1)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280页。,而此举的目的也极为明确,“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2)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283页。,于是,肩负着劝世救人之功的聊斋俚曲便应运而生了。
关于俚曲的篇目统计,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张元所撰的墓表,上面列有俚曲十四种,分别为《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丑俊巴》《快曲》《禳妒咒》《磨难曲》《幸云曲》。其中改编自《聊斋志异》的有六种:《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禳妒咒》《磨难曲》。从改编作品的选择上来看,蒲松龄所选的故事多以女性为主要角色,内容上多以家长里短为主要情节,《姑妇曲》(改编自《珊瑚》)反映了婆媳间关系,《翻魇殃》(改编自《仇大娘》)塑造了一个善于持家的女性形象,《禳妒咒》(改编自《江城》)讲述了一个善妒妻子的故事。这些女性形象有正面有反面,有忠肝义胆的侠女,也有搬弄是非的泼妇,但故事主线都围绕闺阁宅院、孝悌人伦,而《聊斋志异》中常见的以妖鬼狐神、刺贪刺虐、科场弊端为主题的经典故事反而相对较少。由此可以大胆推测,蒲松龄改编的聊斋故事俚曲主要面向的受众从一开始就以闺阁女儿、宅院妇孺为主,这是《聊斋志异》从文人案头向内闱深宅传播的一个可靠证据。
其实,聊斋故事在女性中传播记载很少,但并非毫无端倪,在蒲松龄的交游研究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蒲松龄曾撰写过一篇《祭时夫人》文,时夫人乃淄川知县时惟豫的妻子,《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周生》据考证就是影射这夫妻二人,蒲松龄不仅与这位时县令过从甚密,与其妻也应当有过往来,这一点从其特意为时夫人写悼文就可以看出,甚至在后来与唐梦赉的信件中还透露时夫人向蒲松龄借过书(3)蒲松龄有《上唐太史济武梦赉先生文》,其中有云“所呈司内之书,无有副本,不讨之,恐归乌有耳”。据此袁世硕在《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中认为这是蒲松龄在向时夫人讨要借去的《聊斋志异》书稿,笔者以为从其后“暇时留心,不在一日也”来看,是小说的可能性很小,但从“其诗一首,视可投则投之”可以看到蒲氏与时夫人的交情颇深,《聊斋》盛名在外,时夫人感到好奇向其借阅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缺少文字佐证,只能作一推测。,而《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的看家之作,很大可能也被时夫人借阅过,甚至在时家妇人间乃至更大范围的内闱群体有过传播犹未可知。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落实到文字上的记载十分匮乏,只能作一大胆推测。
除了被动性的传播,《聊斋志异》也曾有向内闱主动传播的过程,《姑妇曲》开头有诗曰:
二十余年老友人,买来矇婢乐萱亲。 惟编姑妇一般曲,借尔弦歌劝内宾。(4)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60页。
从诗的内容来看,应当是友人买了伶人来给老夫人娱乐,蒲松龄为此特意编写了《姑妇曲》来助兴,从尾联“借尔弦歌劝内宾”可以看到,蒲松龄此次创作的主要受众还是宅院内闺的女眷们,所以在故事的选择上也有意向她们感兴趣的方向靠拢。
虽然传播方向上发生了偏移,但这并不影响聊斋故事在从案头向口头的演变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具体来说有以下表现:
首先,从人物塑造上来看,小说受篇幅所限,有很多关键人物塑造过于扁平,例如《姑妇曲》中的丈夫大成,这个角色在婆媳矛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小说中着墨甚少,在珊瑚和母亲的冲突中,完全化身强者帮凶,脸谱化的形象、程式化的行为,导致这个丈夫角色仿佛丝毫没有个人情感,完全为置女主人公于险地而存在。在俚曲中,蒲松龄加强了这一角色的塑造,将丈夫大成这一角色由情感单一的扁平人物转变为思想矛盾、举止复杂的圆形人物。例如在母亲于氏想要状告收留珊瑚的沈大姨,让大成写状纸,大成心里矛盾,一方面不愿将妻子逼上绝路,一方面又怕母亲生气,于是先满口答应,等第二日母亲气消,才劝母亲不必理会,且劝词极能展现安大成性格特征:
为儿今夜细思量,妯娌相处是寻常,官府不肯处治他,惹的那泼势更猖狂;更猖狂,面不光,那倒越发气着娘;气着娘,不必忙,咱找法儿把他降;把他降,他休慌,咱定着珊瑚离了庄。(5)路大荒. 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71页。以下相关内容皆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标注。
安大成心里并不同意母亲的做法但内心又怕母亲生气,于是劝词处处从母亲的角度出发,先等一夜让母亲稍稍消气,又说官府未必肯理会妯娌琐事,反而助长他人气焰,令母亲面上无光,最后再给母亲吃上一粒定心丸,只说“咱从容找法治他”。由此,既给了珊瑚去处,又消了母亲的气,这样一个惯受“夹板气”的丈夫形象栩栩如生。这一段在小说《珊瑚》中是没有的,蒲松龄特意在《姑妇曲》中加入这一笔,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故事情节也更为通顺、合理,不能不说是在文字小说向口头文学过度中的一大进步。
其次,由于说唱形式的需要,蒲松龄在原有的戏剧冲突中加入了一些更有冲击力的刺激性场景。例如《寒森曲》中的“吴孝咬心”一节,在小说《商三官》中商三官手刃仇人之后自尽而亡,并没有过多渲染气氛的描写,而《寒森曲》中则极尽夸张之能事,商三官不仅投缳自尽,且口咬仇人心脏,赵豹要求留下心脏,三官却是怎么都不开口:
二相公使手掏,大相公把头招,一行又使筷子拗;拗来拗去不开口,上下咬的甚坚牢。
取出心后,三官的两个哥哥更是分食了仇人心脏,这段唱词却是恐怖至极,血腥至极:
割去了老贼头,剜出心狗也羞,闻一闻一片腥臊臭。拿来一刀分两断,兄弟嚼来血水流,只因原是仇人肉。咯吱吱一齐嚼响,骨碌碌咽下重楼。
从《聊斋志异》中的篇目来看,蒲松龄虽然热衷写鬼怪妖狐故事,但并不耽于其中恐怖、刺激的元素,更多的是偏重故事本身,所以《聊斋》中恐怖血腥的篇目并不多,也少有过度渲染。此处加入如此有爆发力的场景无非是为了使案头文学更加适应说唱这种艺术形式,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再如《姑妇曲》中的“珊瑚泣血”一节,珊瑚从普通流泪改为“腮边滚滚落红珠”的血泪,一则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二者激化矛盾,使小说中平铺直叙的冲突变得更有爆发力,如山崩海啸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另外,为了使聊斋俚曲更符合内闺妇孺及普通百姓的审美需求,蒲松龄还在故事中加入了很多鲜明生动的民间生活场景、情节。例如《姑妇曲》中于氏与何大娘对骂的桥段,可谓是泼辣有趣、妙语连珠,为压住于氏气焰,何大娘几乎句句歇后语:
“耶耶好奇呀!驼垛子的老驴上山——你捱霎着,又济着喘嘎粗气哩”
“裤裆里钻出个丑鬼来,——你唬着我这腚垂子哩”
接着又让围观的乡邻评理,乡邻不接话,又诅咒谁谁昧着良心便托生珊瑚,直把于氏骂到哑口无言才罢。虽然用词较为粗俗但极符合二人的身份,将一场“泼妇骂街”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从这点可以看出蒲松龄平时应当对日常生活中的类似场景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此时描摹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惟妙惟肖,这也是在小说版《聊斋》中不曾展现的,可以说蒲松龄很好地把握了口头文学的长处所在,没有像案头文学那样过于“雅化”,反而注意到接受群体的趣味,使讲唱文学的优势也在这里得以印证。
二、子弟书
子弟书是清代特有的讲唱文学形式,现在唱法已经失传,只留下一些曲词记载。根据车王府、百本张等存世资料,单《聊斋》曲目就有二十多种,其中不乏一些优秀之作。总体来讲,子弟书有以下特点:
(一)疏于叙事,长于抒情
疏于叙事。由于演绎形式比较单一,多是以第三人称平铺直叙,导致在故事主体的转化上存在劣势,直接表现情节过于简略。例如《陈云棲》《侠女传》,这两篇作品在原作中人物经历都非常曲折,情节上也是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蒲松龄为人称道的以传奇手法写志怪在这两篇有很明显的表现。但是在改编为子弟书后,这种传奇性明显降低了,在情节上只是粗陈梗概,人物上则是尽量减省,《陈云棲》中其母为了阻止儿子娶道士为妻,曾几番阻挠,这在子弟书的文本中都被一笔带过,《侠女传》中侠女杀妖以及与崔生的关系转变都是原文中的重头戏,也是极能展现侠女性格、传奇经历的部分,在此也叙述极为简略,仿佛只是为听众展现了一个故事大纲。究其原因,一是篇幅短,二是第三人称叙事,角色分工不明确。
长于抒情。第三人称叙事除了故事情节转化困难以外,也有它难以取代的优势,即长于抒情和人物描摹。
吟诗抒情。子弟书的每回开头都有诗篇,诗篇或长或短都对仗工整,并加以衬字,不管是阅读还是吟唱都朗朗上口,从内容上看除简要介绍、引起下文外,主要还是以抒情性的描景、议论为主。其作用,首先在于给观众一个进入情节的缓冲,由于说唱形式的需要,帮助观众收敛心神,集中注意力,其次为全篇定下一个情感基调,将观众快速置于营造的氛围中来。例如,《绿衣女》讲述了一只蜂化身少女与一书生短暂的相遇故事,情感基调清新梦幻,没有太多纠葛,结局少女化身而去,如周庄梦蝶。所以在开头的诗篇中,也极力渲染清新爽朗的氛围,描景则“杏花初放柳条青”“竹窗春暖无一事”,“柳条”“竹窗”皆青绿色,“杏花”“春暖”皆盎然之景;议论则“多把春风添笑脸”“少将愁锁挂眉峰”,寓及时行乐之意;结尾处“千般世态千般幻,一场热闹一场空”,点明人生如梦的主题。与之相反的《大力将军》则表现出不同的意趣,为凸显将军孔武有力的气概,开篇以“身如山岳气如虹,自笑途穷志不穷。积雪堆中埋壮士,卑田院内识英雄”四句来定场,没有《绿衣女》如梦似幻的氛围,显得更加气势如虹。
借景抒情。子弟书的抒情性除了在诗篇中有所表达外,在正式的唱段中也处处可见。首先,在叙事的唱句中会插入大段景色描写,这些描写往往与所叙之事相互映衬,起到烘托气氛作用,主要目的也是表达情感:
这书生,掩卷出门阶前立,见苔痕满地露泠泠。静悄悄,几簇花阴一天月色;乱纷纷,一墙竹影四壁蛰声。门掩白云寺院,山空残夜冷春风。月明人静钟声远,露重花香蝶梦轻。暗想道:如此良宵,那里来的女子?一回头,见一个灯影儿窗前,有个人影儿行。(《绿衣女》)(6)关德栋,李万鹏. 聊斋志异说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页。文中相关原文皆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标注。
这一段唱词中涉及故事情节的只有开头和结尾两句,分别交代了书生掩卷出门和回头看见窗前人影,但是这样一句话可以交代清楚的内容中间却插入了大段景色描写。“静悄悄”“乱纷纷”映衬了人物夜来相会的心绪不宁,“一天月色”“露重花香”又烘托了春色旖旎的情绪氛围。不仅是第三人称叙述中如此,在人物对白中也有大量描景抒情的唱词出现,这其实是人物情感的含蓄表达。
(二)长于人物形象的描摹。
虽然子弟书在情节叙事上是提纲挈领式的,但在人物塑造上却不吝惜文字,现存的子弟书篇目出自不同人之手,却无一例外都分别从外貌、心理、语言、神态动作等诸多方面对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角形象予以强化和补充。外貌上主要是对女性的美感进行详细描写,这部分内容良莠不齐,有些恰到好处地对原作中人物形象进行了补充,贴合了人物的性格行为,《侠女传》中描写侠女外貌则是“凛如霜雪”“冷如秋”“匕首寒光射斗牛”,在侠女的美丽中加入了其特有的豪侠气,突出了其性格中冷酷的一面。如同样是女性美,《凤仙》《秋容》则是用“翠黛弯长”“秋水含情”“浅浅淡罗衣”等词语突出了女儿家柔美的一面。对男性角色的外貌描写较少,主要为突出角色个性而勾勒,这一点与对女性的描摹有所不同,《大力将军》里为突出壮士的勇武有力,用了很长的唱词从体型、声音、肤色、服装甚至吃饭的姿态全方位展现,这些在原文中都是没有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外貌描写都是如此,有些则拖沓庸长过于迎合低俗趣味。好的作品应当详略得当,过多对美女的描述则显得累赘,影响了作品的完整性。例如《葛巾传》对花妖的描写以及《绿衣女》对蜂妖的描写都用词过艳,内容过长。但总体来说对完整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仍可谓基于原作的一大进步。
对于人物心理的描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原作中基本没有对这方面的阐述,仅以行动来推进情节,子弟书的唱词在补充上人物心理活动后,使整个人物形象更丰满,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原作中缺失的信息,使情节逻辑更合理。这类描写有些是直接将心理语言表述出来,衔接上下文中的人物活动;有些是侧重心理活动后产生的情绪。前者如《绿衣女》中的书生听到女子扣门声后心想“哪里来的女子”,下文自然过渡到回头看见“有个人影儿行”;后者如《胭脂传》中胭脂偶遇书生后的心理活动,心中所想是鄂秀士,每夜梦里相会“觉后单”,表现的情绪是“挨过五更就像一年”。在语言上子弟书对原作的转换策略和心理描写一样,也是进行内容上的丰富,补充缺失信息,并在语言上予以修饰。由于短篇受限于篇幅,这一点在长篇多回目的子弟书中表现比较明显。《绿衣女》中蜂妖在与书生两情相悦的过程中有过反复的试探,语言上的推拉,非常符合热恋中男女青年的表现,在原文中则以“于心好之,遂与寝处”一笔带过。从这里看,子弟书的妖显得更具有人情味,如寻常男女一般。至于语言上的修饰,则多在人物对话中加入对仗的句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
除了以上两点外,子弟书还在人物的神态动作上加以润色,使原作中比较干瘪的形象生动饱满起来,在《莲香》中原本在朋友间夸下海口的桑生在面对朋友找来扮作狐妖的女子,吓得方寸大乱:
吓得他,蒙头伏衾无一语,身摇床戰像呆人。直等到,门外声音来去杳,方才敢,掀衾出被汗淋身。
原作中描写比较简略,只说“生大惧”,而在神态举止上只用了“齿震震有声”,子弟书中则在神态动作上描写更为具体。
三、单弦牌子曲
单弦牌子曲作为牌子曲的一种多流行于北方,尤其京津地区。相较于子弟书其流行时间更晚,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篇幅更长,艺术上也愈成熟。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唱腔至今流传,如名篇《王六郎》至今有艺人演唱。由于时间较近,各牌子曲的唱腔都有保留,所以单弦牌子曲种所保留的聊斋篇幅较鼓词、子弟书也更多,这些因素都使得单弦牌子曲成为聊斋志目改编中更受重视的一部分。
(一)承袭蒲公言志传统。
虽然聊斋故事中的大多数篇目是作者发乎情,生乎趣的产物,但长期受困科场壮志难酬的困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和官场中的黑暗,人世间的不平让作者不能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7)李贽.杂说[A].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二明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8。,同时由于长期受到文以载道传统思想浸润,以及“史补”“教化”等小说观念的影响,使得蒲松龄在创作聊斋故事时难免落入“传道”的窠臼、“教化”的俗套。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常以“异史氏”之名进行点评,这些点评中往往蕴含着作者之“志”,《续黄粱》中的“福善祸淫,天之常道”,《促织》中的“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叶生》中的“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处处皆疵”,以及《阿宝》中的“性痴,则其志凝”,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说唱艺术受功能所限在这方面并不偏重,子弟书中几乎将“志”的部分都去掉了,只侧重其中情与奇的元素,连蒲松龄自己改的俚曲也多挑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篇目,就连之后的鼓词弹词也亦然。虽然从小说观念上讲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小说理念,但作为长期活跃在市民中的艺术形式往往会走向过度“谄媚”的另一极端,大大影响了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在子弟书等均表现明显。但这一点在单弦中有极大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时代环境影响,单弦流行于清末民国时期,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将这种热情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这些说唱的民间艺人也是如此,其次观众的口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小情小爱已经不再能满足人们的观赏意愿,长期浸润民间市场,以经济为导向的说唱艺术对此则非常敏感,进而影响了大批的从业者。最后从地域上来看,单弦的流传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平,当时各种各样的革命事件都与之息息相关,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这些说唱艺人都与这些国事有更近的距离,所以即便是民间的娱乐说唱也充斥革新的时代气息。
单弦牌子曲唱词中“言志”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开篇的“曲头”“数唱”部分,创作者多在这两部分表明唱段的主题,一般多教化世人、感叹世事的劝世良言。聊斋单弦牌子曲也是如此,有些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原作相近,例如《画皮》里劝人不要贪恋美色,《王六郎》里劝人多结良缘,《田七郎》里劝人不要滥交损友等等。另一部分则是“旧瓶装新酒”借古讽今,融合了时事,当时社会上掀起了各种革新运动,其中破除迷信的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市面上出现过很多反迷信的小说,《聊斋志异》原作就曾成为这方面的首选,吴绮缘的《反聊斋》就是其中的翘楚,这股反迷信热潮也影响到了说唱系统中的聊斋故事,不少单弦作品就是借聊斋之体行反迷信之事,例如《驱怪》原作中讲的是明朝徐远公驱怪的故事,在德寿山的单弦改编中则是劝年轻人不要沉迷玄学,要“实学定家邦”,并列举了庚子年义和团之事,论证偏学无用,这就将原作中意思完全翻转过来,也可视为聊斋翻演作品中的一种;另一个反迷信作品是隋世傑的《易嫁》,这个作品改编自蒲松龄的《姊妹易嫁》,原作中并无太多鬼神迷信的元素,作者改编时却借用此题反对当时婚姻选择仰赖于求签问卦合八字的陋习。还有一些是反映旧社会官场黑暗的,如《续黄粱》,原作多为表述人生如梦、想亦非真的思想,对所谓官场黑暗,此篇表现不甚明显,改编作品则将其主旨改为“唱一段贪官迷梦,写尽了旧社会官场的形状”。除了反迷信、反旧官僚的主题还有一类是意在倡导男女平等思想的,例如《杜小雷》《马介甫》两个曲子,皆是讲普通人娶了悍妻,改编者一改原作中对女子不守妇道的指责,而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导致的,在立意上较其他同期作品有所进步。
聊斋故事单弦牌子曲的改编承袭了蒲松龄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尤其是传播了新时代新思想,这在整个聊斋故事说唱传播系统中都是值得称道的佼佼者,但是受限于改编者的创作能力,以及说唱艺术的受众多集中在下层群体,使得其所传之道并不能很好地与原作融合起来,例如《杜小雷》,只在曲头、数唱中对男女平权有发人深省的议论,其后正文故事里只将原作照搬演绎了一遍,完全没有相应的改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马介甫》曲词有缺,不能断言,但从所存部分来看也是如此。这样子的改动造成了立意与故事的分离,令听众难免有一种脱节感,其所宣扬的理念也很难深入人心。虽然也有部分作品是在故事中有所改动的,但其改动也是小修小补,流于表面,故事的主体还是换汤不换药,例如《易嫁》中的大小姐为了不嫁给穷小子,有一段剖白,里面尽是新潮主张,“这买卖式的婚姻不能作,父母主张办不得”“必须得两情相悦,奴家我得认可”最后,“我法院起诉,妨害自由,连父母都有了罪过”。这些剖白咋听十分有道理,但大小姐在故事中是以反面角色出现,改编者将这些新式思想加在反面人物的对话中,实在不清楚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读者迷惑,听众必有同感。以上这些是单弦牌子曲在改编聊斋故事传播新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即立意与内容脱节,翻演流于表面,故事主体换汤不换药,这也是其在文本上很难与吴绮缘、破迷等人的翻演之作相媲美的重要原因。
(二)艺术上臻于成熟。
同聊斋说唱改编的其他曲种相比,单弦牌子曲在艺术上表现更为成熟,首先它在改编题材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化,俚曲的改编选择偏向于家长里短、孝悌人伦的故事类型,因其传播受众偏向于内闺深宅的妇孺,子弟书曲目短小精炼,偏重于才子佳人、游侠奇遇,很少选择情节比较复杂的故事,鼓词则多仙境神异,奇幻色彩浓郁。单弦牌子曲所选择的篇目类型更为广泛多样,有极富神异色彩的仙游法术类故事,如《劳山道士》《驱怪》《续黄粱》等,也有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题材,如《青凤》《阿宝》《凤仙》等等,还有涉及断狱官场类的故事,如《胭脂判》《田七郎》《侠女》等,以及一些描写悍妇的故事,如《马介甫》《杜小雷》《易嫁》等等。这些多元素的故事题材丰富了《聊斋志异》说唱改编的内容,也促进了聊斋故事在市民阶层中的传播。
其次,在内容细节上充斥着时代气息和讽刺意味。《聊斋志异》文本故事在改编成口语化的单弦后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很多新时代特有的句子及生活场景,如,《恒娘》里恒娘劝朱氏不要理会丈夫时说“你来个报馆歇工暂时停板”,《褚遂良》里赵不屑劝女郎与自己保持距离言“应当避嫌疑,不看报纸上净登新闻儿”。此外,具有时代性的语汇更是不胜枚举,“洋白面”“飞机头”“高跟鞋”“跑火车”等等这些时代元素不仅增加了故事诙谐调侃的趣味性,也使聊斋故事更好地满足了新时代传播的需要。更难得的是一些时代元素暗含了针砭时弊讽刺现实的特性,例如将《申氏》里的王八精类比侵华的列强,“帝国主义侵略性,八大王的凶横早传名”,表面写王八精为非作歹为害乡里,实际暗讽列强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最后对申生怒打王八精场景刻画细致生动,“直打得,四肢瘫软不能动,直打得,脑浆迸裂冒鲜红”,赢得观众一片叫好声。这实际上是对旧有故事的一种新的突破,从传播的角度上讲也更符合时代的特性。
聊斋单弦曲目在艺术上的成熟性不仅表现在加入了不少时代元素上,也在于改编者对人物的塑造、细节上的刻画以及故事情节的掌控上。在人物的外貌上,不再拘泥于美女的描摹,对于一些贩夫走卒的小人物也不吝笔墨,如《王六郎》里对打渔人许翁外貌的详细刻画,没有塞子的酒壶、掉了扣子的褂子、光着的脚丫等都侧面暗示了主人公的拮据,但是绾得整齐的白发、遮阳的草帽又显出人物的整洁干练。除了外貌,一些原本不重要的细节在单弦曲子中也成了着重强调的对象,例如《褚遂良》里对一盆剩菜的细致描述,读之令人作呕,但结合赵不屑之后滑稽的行为举止又充满了戏谑的意味,在美女的温柔乡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这种灰色幽默夹杂在大团圆明亮的色彩中更突显了小人物现实中的辛酸。
改编后的聊斋单弦志目在情节把控上也更符合传播的需求,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戏剧冲突更加激烈,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作为消费型的艺术形式,单弦牌子曲要求改编者更注重观众的感同身受,故事情节必须更加扣人心弦,不能有平淡寡味的地方。在《杜小雷》的剧情里为了激化婆婆与媳妇之间的矛盾,改编者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原本包饺子这段全剧情节中的主干,在志目中变成了情节的支线,更多内容放在了三人的情感纠葛上,例如婆婆为儿子婚事愁瞎眼,又因为眼瞎为儿子选错了儿媳,儿媳的不孝也是通过很多细节一步步表现出来,先要分家,后进谗言,最后虐待婆婆,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三者之间的情感、矛盾也逐一铺垫,使得原本普通的矛盾成为更激烈的对抗,剧情也更吊人胃口。
四、鼓词及弹词
聊斋鼓词留存下来的志目较其他说唱类型还是比较多的,《中国鼓词总目》记载了两个合集,分别为马立勋所编的《聊斋白话韵文鼓词集》和求石斋编的《聊斋志异鼓词》(8)李豫等.中国鼓词总目[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第217页。,后者翻印次数比较多,其中部分志目经关德栋、李万鹏整理收入了《聊斋志异说唱集》中。从整体来看,这些志目的改编水平不高,大多沿用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和大纲,很少作有质量的改动,基本上是根据韵文形式对聊斋故事进行白话改写,没有大的新意,但是从鼓曲演唱的角度讲,它又不如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那样扣人心弦,说唱艺术的传播对象文化水平一般比较低,这就要求艺人在改编底本时需要加入足够多的笑料、俗语甚至是荤段子,情节也要更加高潮迭起,这一点聊斋鼓词甚至不如蒲氏自己改编的俚曲,改编者似乎未能掌握讲唱文学的基本特性。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和当时的鼓词小说热有关系,晚清以及民国时期有不少出版商开始印刷鼓曲唱词供读者阅读,这些鼓词有些是根据艺人演唱底本印制,有些则直接是文人编写,上文中的聊斋鼓词应该就是后一种,所以呈现出无论是文学上还是艺术上都难以与聊斋其他说唱作品相媲美的情况。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鼓词小说的大量印刷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还是大有裨益的,它改变了文言小说阅读困难,受众狭窄的状况,推动了聊斋故事的下沉传播。
但是从《申报》等民国报刊来看,这几种聊斋鼓词小说并没有引起太大热度,与《聊斋志异》原本、绘图本、仿续本的热度难以抗衡,反倒是当时有本署名为蒲松龄的《聊斋鼓词集》值得单独评说,该书因署名蒲松龄,加之有周作人挂名序言大受欢迎。此书出版有周作人挂名的序言,内容包括了问天词、戒睹(原文如此,疑为“赌”)词、东郭词等等,上文提到的《聊斋白话韵文鼓词集》就收入了这几种,并增加了逃学传、学究自嘲、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等,共计七篇。根据刘阶平1933年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记载,这几篇鼓词是当时淄川马立勋从亲戚家收得,原有九篇,内容遗落不少,后来其中的《东郭词》翻印了很多版本。不过对这些词的作者归属问题当时就有质疑,刘阶平在文末也提出过疑问。后来路大荒、孔家等研究者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以充足的论据论证这几篇鼓词当属伪作无疑。据此笔者认为《聊斋鼓词集》亦是伪作。
弹词是聊斋说唱传播中的又一重要门类,可能是受限于当时资料检索不易的缘故,关德栋、李万鹏在《聊斋志异说唱集》的前言中提到“演述聊斋故事的弹词,可见曲目最少”(9)关德栋、李万鹏.聊斋志异说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可与鼓词并作一类。其实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不少都刊登过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弹词小说(10)参全国报刊索引资料库。:
①聊斋弹词:狐嫁女 哈哈笑 《大世界》 1922年6月
②聊斋弹词:贾奉雉成仙 许舜屏 《金刚钻月刊》1933年创刊号
③聊斋弹词之一画皮 黄异庵 《锡报》 1938年9月
④杂俎:聊斋志异侠女篇弹词 檗子《小说月报》1917年第八卷第6期
⑤弹唱聊斋:瞳人语 起码说书《弹词画报》1941年第52期
⑥弹唱聊斋:画壁 起码说书《弹词画报》1941年第57期
⑦弹唱聊斋:种梨 起码说书 《弹词画报》1941年第63期
⑧弹唱聊斋:考城隍 起码说书 《弹词画报》1941年第47期
⑨弹唱聊斋:劳山道士 起码说书 《弹词画报》1941年第68期
⑩弹唱聊斋:长清僧 起码说书 《弹词画报》1941年第75期
这些篇目有些是一个故事分成很多部分在报刊杂志上连续刊登,有些是同一篇弹词在多个刊物上刊登,有些像《弹词画报》则是专门辟出一个栏目,请固定的作者对聊斋故事进行改编。以上这些篇目再加上《聊斋志异说唱集》中列举的《聊斋志异弹词》(沙河遗老)、《青梅配》(苍厓子)、《点点熙然》,篇目数量还是可观的,可供进一步研究。
结 语
综上对聊斋说唱逐渐形成的聊斋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与弹词等形式的论述,基本上可以看出从文人案头到勾栏瓦肆——《聊斋志异》传播的平民化趋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聊斋志异》的传播与接受大众化的倾向,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通过演绎形式的变革实现目标下沉,向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娱乐文学沿革的一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