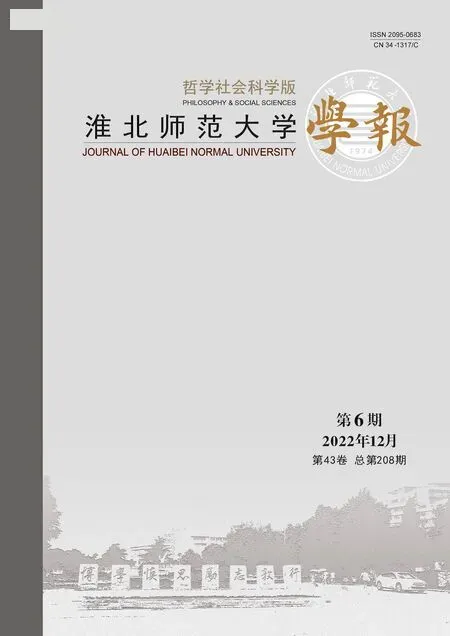能力知识的功能
崔治忠
(青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知识是人们认识自我和世界的产物,是指导人们开展生产实践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的重要依据。一直以来,知识论学家比较重视Knowing-That(简称KT)。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这种知识表达出来的,而且,我们的实践能力也是建立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1]自从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明确区分KT与Knowing-How(简称KH)之后,KH逐渐成为知识论学家关注的对象①徐向东将KT翻译为命题知识,将KH翻译为实践知识或能力知识;任会明将KT翻译为所知,将KH翻译为会知;郁振华将KT翻译为命题性知识,将KH翻译为能力之知。参见: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任会明.会知与呈现模式[J].哲学研究,2011(1):68-76;郁振华.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J].哲学研究,2010(10):70-78.本文遵从徐向东的译法,即将KT翻译为命题知识,将KH翻译为能力知识。。尤其是2001年贾森·斯坦利(JasonStanley)和提摩西·威廉姆森(TimothyWilliamson)反驳赖尔的区分以来,KH以及与KT的关系成为知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许多著名的当代知识论学家都参与了这场热烈而富有深度的学术探讨,例如,斯坦利、威廉姆森、约翰·本格森(JohnBengson)、马克·莫菲特(MarcA.Moffett)、尤里·凯斯(YuriCath)、邓肯·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亚当·卡特(AdamCarter)、泰德·波斯顿(TedPoston)、彼得·马基(PeterMarkie)、约书亚·霍布古德·库特(JoshuaHabgood-Coote)、凯瑟琳·郝蕾(KatherineHawley)等。我国学者徐向东、郁振华、任会明、黄敏、何朝安、楼巍等在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能力知识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对能力知识的定义、本质以及与命题知识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那么,学者们为什么关注KH?原因不仅在于KH与KT存在复杂关系,还因为KH具有重要功能。客观地说,学术界对KH功能的研究还比较少。下面,本文从认知例示、行动引导、技能衡量三个方面试述KH的功能,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吸引学者们对KH的功能进行深入探讨。
一、能力知识的认知例示功能
与KT一样,KH是知识。但不同于KT,KH与行动、能力存在紧密关系。赖尔将KH的本质理解为机智行动的能力或复杂倾向,马基认为一个人持有KH就意味着他拥有以行动回答如何做某事的能力,并且他对关于行动方法的第一人称命题提供命题性辩护[2]。有的反理智主义者认为,一个人持有KH,当且仅当,他具有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能力[3]。我国学者郁振华对赖尔所言的KH做了深入解读,认为KH是“用行动来表达的、体现了智力的能力之知”[4]。虽然KH与行动、能力有内在关联,但不能否认KH与KT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因为如此,理智主义试图证明KH就是一种KT。修正理智主义者凯斯认为一个人持有KH并不需要他知道做某事的方法,只需要持有关于做某事方法的真命题[5]。由此可见,持有KH意味着认知主体具有一定的认知地位。尽管KH依赖于主体对做某事方法的认知,但又不等于对该方法的认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KH的认知例示(instantiate)功能体现出来。
(一)能力知识与认知的关系
在具体分析KH的认知例示功能之前,需要先梳理KH与认知之间的关系。KH是Knowing-How的简称,而Knowing-How是knowing how to v的简称。KH的中文涵义是知道如何做某事,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被认为知道如何做某事就蕴含他知道做该事情的方法。例如,汉娜知道如何游泳意味着她知道游泳的方法。后来,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引入实践呈现模式,认为一个人知道如何做某事,当且仅当,w是他做该事情的方法,他知道“w是他做该事情的方法”,并且在实践呈现模式下持有“w是他做该事情的方法”[6]。显然,不管是知道做某事的方法还是知道自己做某事的方法,都是关于做某事方法的认知状态。虽然认知的种类和内容非常复杂,但与KH相关的认知都关涉做某事的方法。当然,做某事的方法有一般和具体之分。例如,自行车销售说明书中一般都有关于骑自行车的方法说明。但一个人总在具体的情景中骑自行车,他对骑自行车方法的理解不仅包括一般的方法,还包括在具体情景中对自己骑自行车方法的掌握。那么,有没有知道如何骑自行车但对骑自行车方法一窍不通的人?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骑自行车不同于成功地骑自行车,而成功地骑自行车不同于机智地骑自行车。赖尔认为,机智地做某事就是对KH的践行。而一个人要机智地做某事就必须掌握做该事情的方法,换句话说,不了解做某事方法的人不可能知道如何做该事情。
认知是人们对外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认识活动依赖的手段和工具不同,认知过程和结果也不一样。例如,感性认知不同于理性认知。就认知结果而言,有知识、信念、谬误之分。其中,谬误是人们批评和排斥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谬误或者与客观事实不符,或者与人们行之有效的系统观念不相容。需要说明的是,受认知能力、世俗偏见、外力干预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正确的认识可能被视为谬误,一些谬误可能被视为正确的认识。信念是认知主体相信事物是如此这般的状态,一般情况下,认知主体会对自己相信的对象提供一定程度的辩护。但相比于知识,信念的辩护强度弱得多,而且,信念的内容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凭借从祖辈那里沿袭下来的信念和通过习惯形成的信念处理绝大多数日常事物。因此,不能忽视信念对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不同于谬误和信念,知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认知结果的典范。一般认为最早对知识给出定义的是柏拉图,他在《泰阿泰德篇》(Theatetus)中认为知识是有理性辩护或解释的真信念[7]。从这一定义可以分析出知识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为真条件、信念条件和辩护条件。1963年,埃德蒙·盖梯尔(Edmond L.Gettier)通过两个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不能称之为知识的反例对传统知识定义发起挑战,迫使知识论学家或者完善传统知识定义或者提出新的知识定义[8]。
不管人们如何定义知识,知识需要满足的条件远高于信念。既然KH依赖于认知,那么,KH依赖于什么样的认知?显然,KH不可能依赖谬误。或许一个对如何做某事有错误认识的人基于偶然运气成功地做了该事情,但经过反复观察和比较之后人们不会将做该事情的KH归属于他。通常,一个人知道如何做某事蕴含他知道关于做该事情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知道关于做某事方法的人比不知道该方法的人更倾向于知道如何做该事情。但是,鲍勃学习驾驶模拟飞行器案例和查理学习更换电灯泡案例指出,一个人即使不知道做某事的方法也有可能知道如何做该事情。鲍勃由于偶然运气从骗子教练那里获得了碰巧正确的指导,查理由于偶然运气从一本充满错误信息的书上碰巧获得了正确信息。按照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的理解,鲍勃不知道驾驶模拟飞行器的方法,查理不知道更换电灯泡的方法。但是,他们都有意且成功地做了相应的事情。因此,鲍勃知道如何驾驶模拟飞行器,查理知道如何更换电灯泡。可见,KH并不需要认知主体必须知道关于做某事的方法,但要求他持有关于做某事方法的真命题。凯斯认为,KH的持有者可以不相信他持有的关于做某事方法的真命题[5]。但是,这一观点很难讲得通,因为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通常都是相信自己掌握做该事情方法的人。因此,持有KH至少需要认知主体掌握关于做某事方法的真信念。
(二)能力知识具有认知例示功能
KH的归属依赖于主体对做某事方法的认知,但不局限该认知。通常,人们不是将KH归属于只知道做相应事情方法或持有关于该方法真信念的人,而是归属于能够机智地做该事情的人。赖尔区分了理智和机智,理智表现为认知主体对事物属性和关系持有命题知识,而机智不仅表现为认知主体持有或思考命题知识,而且表现为他能够灵活熟练地运用相关命题知识。其中,对相关命题知识的灵活运用就是一种认知例示,即在实践活动中运用相关认知结果。例如,按照骑自行车的方法成功地骑自行车就是对该方法的认知例示[4]。一般来说,人们在骑自行车之前需要了解和掌握自行车的骑行方法,他成功地骑自行车的过程就是运用该方法的过程。概言之,一个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一定是能够机智地运用做该事情方法的人。这里的“能够”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现实意义上的能够或已经例示了的能够。反之,没有成功做过某事的人不能被认为知道如何做该事情,即使他掌握再多的关于做该事情方法的命题知识。可见,认知例示是KH的重要功能。
KH与KT存在紧密联系,既然KH有认知例示功能,那么,KT有没有该功能?如果没有,那么,原因是什么?要深入理解KH的认知例示功能,还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显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清楚,即KT没有认知例示功能。“纸上谈兵”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不能否认赵括掌握用兵的方法,但他缺乏的是机智运用该方法的能力和实践历练。实际上,赖尔也指出,一名士兵不可能通过死记硬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成为著名将军[9]20。同样,一名厨师也不能通过背诵菜谱成为烹调大师。人们不会要求知道“水的分子式是H2O”的人用氢气和氧气成功地合成出水来,也不会要求核理论物理学家必须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但是,一个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必须在现实当中成功做了该事情。例如,汉娜知道如何游泳就意味着她会游泳并成功地游过泳。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不可能被认为知道如何游泳。至于为何KH有而KT没有认知例示的功能,主要原因在于KH的归属除了满足认知和能力条件之外,还要满足实践条件。但是,KT的归属并不涉及实践条件,只需要认知保障和认知辩护。需要说明的是,认知例示功能揭示了KH与KT的差异和联系。就差异而言,KH的归属需要主体例示自己对做某事方法的认知,KT的归属不需要主体运用相关信念内容。就联系而言,KH和KT都蕴含对特定真命题的掌握,而且,高质量的KH本身就包含相应的KT。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KH以KT为前提。
(三)对潜在批评的回应
对于上述关于KH具有认知例示功能的观点,可能存在如下批评意见:第一种批评认为笔者把认知主体对做某事方法的理解与运用截然分离开来,从而与实际情况相背离。黑格尔批评康德脱离认识活动去分析认识能力,并把康德的做法称之为在正式下水游泳之前先要在岸上学会游泳。实际上,赖尔也反对把思考做某事的方法与运用做该事情的方法分割开来的做法,并认为对KH来说两者是同一个过程[9]18。第二种批评认为认知例示不是所有KH都具有的功能,因为一些KH的归属并不需要认知主体真正做过相应的事情。凯斯用保龄球案例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一个从来没有用保龄球砸过自己脚的成年人拥有用保龄球砸自己脚的能力,因此,他应该被认为知道如何用保龄球砸自己的脚[3]。实际上,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例如,一个从来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的驾驶员知道如何违反交通规则,一个从来没有用石头砸过别人家玻璃的人应该知道如何用石头砸别人家的玻璃。由此可见,认知例示不是KH必备的功能,至少不是所有KH具有的功能。第三种批评认为认知例示是KH归属的内在要求,不是KH的功能。例如,要将关于做某事的KH归属于一个人就需要他运用做该事情的方法并成功地做该事情。但是,一个人持有KH并不意味着他时刻在例示做某事的方法。
对于上述三种批评,可以作出如下回应:对于第一种批评,笔者认为思考做某事的方法不同于运用做某事的方法。在具体做某事的过程中,行为主体通常也是认知主体,他要思考做该事情的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完善该方法。与此同时,他要运用具体的方法做该事情。但是,思考命题知识和运用命题知识的共时性并不能掩盖两者的区别。人们通常在经过一定的理论学习之后才进行实践操作,这在技能培训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思考做某事的方法与运用该方法是同一件事,那么,技能培训中的理论学习就既没有必要也无可能。可见,批评者对区分思考和运用做某事方法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对于第二个批评,笔者认为即使再简单的行动,如果主体没有实际践行过,就不能认为他知道如何完成该行动。直观来看,用保龄球砸自己的脚是很简单的行动,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简单的是操作方法,不简单的是要承受该操作的后果。知道如何做某事不是指主体能够简单地按照一定方法做某事,而是指主体能够在整体考虑行动后果之后按照一定方法成功地做该事情。按照这一标准,人们认为的许多简单行动就不简单了。此外,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某事,那么,就无法认为他拥有做该事情的能力,不能因为做某事的方法比较简单就默认人们知道如何做该事情。或许有批评者继续指出,失去双臂的钢琴师虽然不能再弹钢琴,但他知道如何弹钢琴,这就说明认知例示并不是KH的功能。然而,人们之所以认为失去双臂的钢琴师知道如何弹钢琴,就是因为他曾经弹过钢琴,并且弹得很好。如果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他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弹钢琴。对于第三个批评,笔者认为,认知例示既是KH归属需要满足的要求,也是KH的功能。一个人被认为知道如何做某事就意味着他曾经或现在运用做该事情的方法成功地做过该事情。例如,一个需要修理管道的人愿意找知道如何修理管道的工人来帮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道如何修理管道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功地维修管道。可见,持有KH蕴含主体能够例示关于做某事方法的认知结果。
二、能力知识的行动引导功能
知道如何做某事不同于会做某事,也不同于成功地做某事。虽然KH与做某事的能力和行动有内在联系,但KH是一种知识[10]。不同于表述世界是如此这般或那般的KT,KH是关于如何做某事的知识。作为一种知识,KH包含认知内容;作为与行动密切相关的知识,KH包含能力内容和实践内容。KH包含的认知内容关涉做某事的方法,KH包含的能力内容表现为运用做某事方法的能力,KH包含的实践内容指的是主体运用该方法做某事的活动。一个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会做该事情的人,他之所以会做该事情,是因为他持有相关的KH。由此可见,KH具有行动引导功能。需要说明的是,KH的行动引导功能与认知例示功能密切相关,认知例示的过程通常也是KH引导行动的过程。
(一)能力知识与行动的关系
要深入掌握KH的行动引导功能,就需要分析KH与行动的关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区分行动,就有不同种类的行动。与KH有关的行动主要包括主动的行动、成功的行动、有意的行动等。因此,对KH与行动关系的分析主要表现为对KH与这三种行动关系的梳理。概言之,践行KH的行动一定是主体主动的行动,是具有很高成功概率的行动,是主体有意为之的行动。
首先,持有KH就意味着主体做相关事情的行动是主动的行动。与主动行动相对的是被动行动或消极的行动。所谓消极或被动的行动就是主体不能主观控制的行动,例如,肠胃的消化运动、血液的循环运动等。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消化食物,但不能认为他知道如何消化食物。因此,践行KH的行动一定是主动的行动。这一点对人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小猫小狗和智能机器的行动是不是主动行动,进一步来说,其他非人动物和智能机器是否持有KH?这些是深入分析KH与行动关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许多动物友好人士看来,小猫的撒娇、小狗的摇尾都是主动行动,但在笔者看来,主动行动是遵循行动意愿和方法的行动,小猫小狗的部分行动看起来遵循了一定的意愿和方法,但由于人与其他非人动物无法进行思想交流,人们还不能肯定其他动物的行动是主动行动。本着有疑不用的原则,笔者将其他动物的行动排除出主动行动的范围。虽然智能机器遵循严格设定的程序和方法,但由于自身没有行动的意愿,它们的行动也不能被称之为主动行动。既然非人动物和智能机器的行动不是主动行动,那么,非人动物和智能机器也就不持有KH。批评者可能认为笔者基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忽视了其他非人动物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但笔者认为,人们无法改变人类始终从自身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也无法让非人动物与人类平等交往,人类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是尊重和关爱非人动物的生存状态。
其次,持有KH就意味着主体做相关事情的行动是很有可能成功的行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关于做某事的KH归属于某一个人,不仅因为他会做该事情,更因为他能经常成功地做该事情。试想,一个执着于做某事但从未成功做该事情的人是否知道如何做该事情?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成功做某事是一个人持有KH的内在要求。但是,持有KH的人是否每次都能成功地做该事情呢?相比于前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鉴于归纳推理涉及概率问题,笔者认为持有KH的人能够以较高的概率成功地做相应事情。一个人做某事的行动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确保他能每次成功地做该事情。但相比于会做某事但不知道如何做该事情的人,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成功做该事情的成功率更高。当然,成功率高低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的成功率有高低之分,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位置做同一件事情的成功率也有高低差别。一般来说,持有做某事KH的人比不持有该KH的人更倾向于成功地做该事情,这也就是人们重视KH的重要原因。
最后,持有KH就意味着主体做相关事情的行动是有意为之的行动。“有意”不同于“有意图”,前者指的是遵循做某事的方法与原则,后者指的是拥有做某事的想法或愿望。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虽然能成功地做某事,但不能认为他知道如何做该事情。我们可以用基兰·塞提亚(Kieran Setiya)的拆除炸弹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该案例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人正在设法拆除炸弹,但面对令人困惑的复杂线路他不知所措,在报时器停止前他剪断了红色电线,炸弹被成功拆除了,但他不知道如何拆除定时炸弹[11]。显然,他之所以能成功拆除炸弹是因为他碰巧剪对了电线。与KT的归属需要排除发挥重要作用的偶然运气一样,KH的归属也要排除在实践环节发挥重要作用的偶然运气。为此,要将KH归属于某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能否成功地做某事,更要看他是否有意做该事情。拆炸弹的人有拆除炸弹的意图,但他拆除炸弹的行为不是有意的,因为他不知道拆除炸弹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做某事的行动越来越熟练,对做该事情方法与原则的遵循就内化为行动者特有的行为模式。从表面来看,熟练做某事的人似乎没有遵循什么原则和方法,但实质上他从来没有背离做该事情的方法和原则。这也就是“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人们的道理。
(二)能力知识具有行动引导功能
如上所述,KH与行动有紧密关系,一个人持有KH就意味着他能够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那么,关于做某事的KH与有意且成功地做该事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从逻辑角度而言,可能存在如下三种关系:一是KH是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前提条件,二是KH等同于有意且成功做某事,三是KH蕴含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第一种关系是就具体做某事的行动而言的,KH是一种知识,有意且成功做某事是一种行动,有意且成功的行动需要遵循一定的行动方法和原则,而KH就是引导主体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认知状态。对于熟练做某事的人来说,KH对行动的引导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KH对行动没有引导作用,只不过KH对行动的引导已经内化为他们的行动习惯。当人们熟悉的环境发生改变,KH对行动的引导作用就会显现出来。第二种关系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持有KH时非常有用,与KT一样,KH是一种内在的认知状态。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KH主要看他能否有意且成功地做该事情,如果他能够有意且成功地做该事情,那么,他就可以被认为持有做该事情的KH。反之则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等同于”表达的不是相等关系,而是一种表明关系,即有意且成功做某事表明主体持有相关KH。第三种关系反映了有意且成功做某事是KH归属的实践条件,除此之外,KH的归属还需要满足认知条件和能力条件。虽然实践条件不同于认知条件和能力条件,但三个条件都围绕做某事。其中,实践条件指的是主体曾经或现在有意且成功地做过某事,认知条件指的是主体掌握关于做某事方法的真信念,能力条件指的是主体能够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
虽然上述三种关系有内在差异,但都揭示了KH具有行动引导功能。具体来说,“KH是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前提条件”说明有意且成功的行动离不开对相关事物的认知;人们之所以将KH等同于有意且成功做某事,是因为KH是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持有做某事的KH,那么,他就能有意且成功地做该事情[12];“KH蕴含有意且成功做某事”说明持有KH为有意且成功做某事提供了认知条件和能力条件,其中,认知条件为主体有意且成功做该事情提供了方法支持,能力条件保证主体能够有意且成功地做该事情。可见,KH对主体有意且成功做某事发挥了引导作用[5]。既然KH具有行动引导功能,那么,KH是如何引导主体有意且成功地行动的?在笔者看来,KH的行动引导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KH为主体成功做某事提供了有效方法。如前所述,KH包含关于做某事方法的认知内容,该认知内容能够引导主体成功做该事情[13]。此外,持有KH的行动者能够机智地应对做某事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断完善做某事的方法,提高做某事的成功率。二是KH为主体有意做某事提供了能力保障。一个知道做某事方法的人不一定有做该事情的能力,但一个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一定有能力做该事情。KH包含的行动能力是KH引导行动的潜在因素,实际上,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主体运用一定方法做某事的能力。三是KH为主体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提供了实践指导。有了方法和能力还不能保证主体一定能够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要确保主体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还需要主体把行动方法与行动能力有机统一起来,并借助一定工具和环境。而持有KH的人能够运用行动方法和相应的工具有意且成功地做某事[13]。
(三)对潜在批评的回应
对于上述关于KH具有行动引导功能的观点,可能存在如下批评。第一种批评认为KH是对主体具有机智做某事能力的表征,它不是一种知识,也不具有引导行动的功能。具体来说,人们将KH归属于一个人不是赋予他一种认知状态,也不是给予他一种能力,而是对他具有机智行动能力的肯定。换句话说,人们把满足关于做某事认知条件、能力条件和实践条件的复杂状态或倾向称之为KH。这种复杂状态或倾向本身就是能够机智做某事的状态或倾向,并不需要KH引导。第二种批评认为践行KH的过程就是机智行动的过程,而且,机智行动本身就是遵循一定原则和方法的行动,因此,机智行动不需要KH引导,KH也没有引导行动的功能。例如,一个优秀的驾驶员知道如何开车,他开车的过程是自觉遵循和灵活运用开车方法的过程,他不会按照KH机械地开车。第三种批评认为笔者对KH行动引导功能的分析不正确,一般来说,引导行动的是行动原则和方法,不是能力和实践。把能力保障和实践指导作为KH引导行动的具体表现既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也不符合人们践行KH的实际情况。例如,管道修理工在维修管道的过程中,会熟练地按照修理方法和原则维修管道。如果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他会探索新的维修方法和原则并按照新方法和原则修理管道。在这一过程中,引导维修行动的是关于维修方法和原则的真信念或知识。因此,KH对机智行动的引导主要体现为方法引导。
对于上述潜在批评,可以作出如下回应。对于第一种批评,笔者认为KH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包含认知内容,还包含能力内容和实践内容。如果将知识严格限定为命题知识或理论知识,那么,KH就不是知识。但学术界普遍认为知识不仅包含命题知识,还包括技能知识、亲知知识、证言知识、自我知识等。因此,把KH视为知识是合理的。KH不是对主体具有机智行动能力的表征,而是对主体具有能够运用行动原则和方法机智行动的复杂状态或倾向的表征。这种复杂状态或倾向是遵循一定行动原则和方法的状态或倾向,而KH包含对行动原则和方法的认知内容,因此,可以认为KH对主体做某事的行动具有引导作用。实际上,第二种批评与第一种批评一样,都否定KH具有行动引导功能。只不过第一种批评通过取消KH的实际意义来否定KH的行动引导功能,第二种批评通过阐释“机智行动”的涵义来否定KH的行动引导功能。然而,机智行动不同于行动,引导机智行动不同于引导行动。毫无疑问,机智行动不用KT或KH来引导,因为机智行动本身是遵循一定原则和方法的行动。但是,笔者强调的是KH对行动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对机智行动的引导功能。一种行动要成为机智行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并将该原则和方法内化为实施该行动的特定模式。就做某事而言,KH的持有者遵循一定原则和方法的过程就是KH引导行动的过程。对于第三种批评,笔者认为KH不同于KT,KH对行动的引导不仅表现为行动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而且表现为KH的持有者能够借助主客观条件运用行动原则和方法。的确,KH对行动的引导不存在先思考行动原则和方法后运用该行动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也不存在主体按照KH行动的过程。KH对行动的引导功能主要表现为机智做某事的行动是遵循一定行动原则和方法的行动,是主体机智运用该原则和方法的行动,是主体有意且成功做某事的行动。
三、能力知识的技能衡量功能
能力知识除了具有认知例示功能和行动引导功能之外,还具有技能衡量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把技能与知道如何做某事联系起来。对于简单的事情来说,不存在有没有技能的问题。例如,开门、走路、吃饭、看电视等简单行动的技术含量不高。通常情况下,人们既不会关注一个人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也不会强调做这些事情的技能水平。但对复杂行动来说,人们不仅关注一个人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以及做这些事情的技能水平,而且通常把知道如何做这些事情等同于拥有做这些事情的技能[14]。
(一)能力知识与技能的关系
技能是通过一定方法或技术成功做某事的能力。与技能相关但又有区别的是做某事的能力和成功做某事的能力,就相关性而言,它们都是能力,而且都关涉做某事;就区别而言,技能关涉的行动包含复杂的步骤或环节,而且行动的成功率比较高。相比之下,做某事的能力和成功做某事的能力关涉的行动既可以包括复杂行动,也可以包括简单行动。从字面来看,做某事的能力就是指能够做但不一定成功地做某事的综合素质或复杂倾向,成功做某事的能力就是能够成功做某事的综合素质或复杂倾向。在有些情况下,技能等同于成功做某事的能力。例如,管道修理工具有的技能就是成功修理管道的能力,电脑维修人员具有的技能就是成功维修电脑的能力。或许有人会认为技能是能够以较高成功率做某事的复杂倾向或综合素质,而成功做某事的能力是百分之百成功做某事的复杂倾向或综合素质,因此,技能与成功做某事的能力不可能等同。但在笔者看来,具有做某事技能的人能够以高概率成功做该事情。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做某事的技能等同于成功做该事情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日益借助复杂的设备和手段开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相关操作技术和方法成为成功做某事的关键。与此同时,技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虽然技能是一种能力,但不是单纯的能力,而是运用一定技术和方法机智做某事的能力。因此,技能一方面包含认知内容,另一方面具有实践倾向。就前者而言,技能依赖于主体对行动方法、原则和手段的认知。例如,一个拥有维修电脑技能的人必然持有关于维修电脑方法和原则的真信念或知识。那么,有没有不了解或不掌握维修电脑方法和原则但持有维修电脑技能的人?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基于偶然运气成功做某事,但不能基于偶然运气机智做某事,而机智做某事蕴含主体具有做该事情的技能。与KH的归属一样,技能的形成和持有并不需要主体对做某事的方法和原则形成非盖梯尔化的有辩护的真信念,只需要对做某事的方法和原则形成真信念。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技术工人并不了解复杂设备的工作原理,但通过简单的流程化方法能够机智地操作该复杂设备,并拥有操作该设备的技能。当然,对从事设备研制和开发的工程师来说,仅仅掌握简单的操作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设备工作的原理。就技能具有实践倾向而言,一个人具有做某事的技能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做某事。这里的“能够”不是理论层面的逻辑可能性,而是指在现实层面已经成功做过该事情。
KH是一种知识,而技能是一种能力,因此,KH不同于技能。但两者存在紧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持有做某事的KH就意味着他拥有做该事情的技能。那么,作为一种知识的KH与作为一种能力的技能为什么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KH与技能具有共同的内容。虽然KH是一种知识,但它除了包含认知内容之外,还包括能力内容和实践内容。虽然技能是一种能力,但它是包含认知内容和实践内容的能力。就做某事而言,KH与技能都包含关于做该事情的认知内容、能力内容和实践内容。这是KH与技能存在紧密关系的重要原因。二是KH和技能都与机智行动有关。针对不同的事情,就有不一样的KH和技能。但不管何种KH和技能,都与机智行动有关。具体来说,一个人持有做某事的KH就意味着他能够机智地做该事情。同样,一个人拥有做某事的技能就意味着他能够机智地做该事情。三是KH与技能是表征主体同一种综合素质的两个指标。一个熟练做某事的人不仅拥有做该事情的技能,而且知道如何做该事情。做某事是行动,但熟练做某事是主体在拥有某种综合素质时的行动。人们可以用KH和技能来表征主体熟练做某事时的综合素质。只不过KH从知识层面进行表征,技能从能力层面进行表征。虽然表征的维度不同,关注点不一样,但表征对象是相同的。
(二)能力知识具有技能衡量功能
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用会不会做某事、能不能做某事、是否知道如何做某事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做该事情的技能。例如,如果一个人会修理管道或知道如何修理管道,那么,他就具有修理管道的技能。实际上,“会做某事”与“能做某事”具有相同的涵义,都在指称主体具有的同一种状态。因此,“会做某事”可以与“能做某事”相互替换。但是,“会做某事”不同于“知道如何做某事”,用它们来衡量做某事技能的效果也不一样。“会做某事”表达主体具有成功做某事的能力,而“知道如何做某事”不仅表达主体具有成功做某事的能力,而且表达主体具有机智做某事的能力。“机智做某事”有三层含义:一是按照一定方法和原则做某事,二是运用一定方法和原则成功做某事,三是灵活运用一定方法和原则做某事,并对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和弥补,进而不断提高做某事的成功率。如前所述,技能行动不仅是成功的行动,更是机智行动。“会做某事”能保证主体成功做某事,但无法保证主体机智地做某事。例如,一名象棋新手经过培训之后能够下棋或会下棋,但不会很快达到机智下棋的水平。因此,用会不会做某事或能不能做某事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该事情的技能就可能出现太过宽松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可能将一些不是技能的能力视为技能。例如,用会不会下棋来衡量一名棋手是否具有下棋技能就会认为下棋新手也具有下棋技能。显然,这与人们对下棋技能的理解有偏差。
既然“会做某事”或“能做某事”不能有效衡量技能的归属,那么,“知道如何做某事”能否有效衡量技能的归属?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做某事,那么,他一定具有做该事情的技能。例如,如果杰克知道如何维修管道,那么,他就具有维修管道的技能。或许有人会问,KH为什么能衡量技能?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持有KH蕴含主体能够机智地做某事,而机智地做某事就意味着主体具有做该事情的技能。二是持有KH的条件要高于具有相应技能的条件,因此,持有KH的主体一定具有做相应事情的技能。虽然KH和技能的归属都要满足认知条件、能力条件和实践条件,但KH的归属更关注主体对做某事方法的正确认知和灵活运用,而技能归属更强调主体具有熟练做某事的能力。具体来说,一个具有做某事技能的人可以不需要对做该事情的方法有深入的掌握,只需要他能按照正确的方法熟练地做该事情。但一个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人必须对做该事情的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并且能灵活运用该方法熟练地做该事情。三是KH的践行表现为主体机智地做某事,而技能的运用和发挥也表现为主体机智地做某事,因此,持有KH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另一个人做某事的行动来判断后者是否持有做该事情的技能。
(三)对潜在批评的回应
对于上述关于KH具有技能衡量功能的观点,可能存在如下批评。第一种批评认为持有KH并不蕴含主体能够机智地做某事。在理智主义看来,KH是一种特殊的KT,一个人持有KH并不蕴含他拥有机智做某事的能力,而是等同于知道做某事的方法,最多是在实践呈现模式下持有关于做该事情方法的知识。既然KH没有能力内容,也就不能用KH来衡量技能。第二种批评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技能最直接和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他能否机智地做某事,而不是用KH来衡量。例如,衡量一个人会不会维修管道,就看他能不能把坏了的管道修理好。如果能修好,就说明他拥有维修管道的技能。反之则否。第三种批评认为用KH衡量技能就会将一部分技能排除在外,因为KH归属的条件高于技能归属的条件。例如,一些业务熟练的电脑装配技术工人拥有做相关工作的技能,但他们可能对制造电脑的方法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解。如果用KH来衡量技能,这一类技能就会被排除在外。第四种批评认为KH是一种知识,技能是一种能力,按照异类不比的原则,KH无法衡量技能。退一步来说,即使可以用KH来衡量技能,但主体是否持有KH又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相比之下,衡量是否持有KH的难度不小于衡量是否持有技能的难度。第五种批评认为既然KH要通过技能行动来间接衡量技能,还不如用技能行动来直接衡量技能。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是经常用技能行动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技能。
对于上述批评,可以作出如下回应。对于第一种批评,笔者认为理智主义将KH等同于KT的作法已经受到广泛批评,而且,像斯坦利、威廉姆森、凯斯这样的理智主义者也将做某事的复杂倾向引入对KH本质的理解当中。总之,对KH本质的准确解释不能无视KH的能力因素。因此,第一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种批评和第五种批评都认为衡量技能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手段是技能行动而不是KH。的确,在实践场景当中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技能,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他能否机智地做某事。但在非实践场景当中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技能,就不能观察他能否机智地做某事。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是否持有做该事情的KH。或许有批评者继续指出,在非实践场景中如何准确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做某事的KH是一个困难问题。笔者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持有KH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满足KH归属的认知条件、能力条件和实践条件。概言之,就是通过理论测试和模拟操作看他是否了解做某事的方法以及观察他能否熟练地运用做某事的方法。在无法直接观察行动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可靠人士的证言知识和认知主体的理智德性来判断他是否持有做某事的KH。对于第三种批评,笔者认为KH只是衡量技能的一种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用KH衡量技能可以确保衡量的可靠性,有助于引导人们追求高质量的技能。如果要提高衡量技能的覆盖面,可以适当降低对做某事方法的认知要求。对于第四种批评,笔者认为衡量不同于比较,异类不比不同于异类不能衡量。况且,KH与技能存在共同之处,不能说两者完全不相干。的确,衡量KH归属的难度不小于衡量技能归属的难度,但这正说明用KH衡量技能可以保障衡量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能力知识具有认知例示功能、行动引导功能和技能衡量功能。认知例示功能是KH区别于KT的重要原因,也是KH作为实践性知识的重要体现;行动引导功能是KH与行动密切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KH连接KT与行动的重要桥梁;技能衡量功能是人们重视KH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评价他人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的对象,KH的功能也不一样。认知例示功能是KH对所有身份的人都普遍具有的功能,行动引导功能是KH对持有者具有的重要功能,技能衡量功能是检查者和委托者衡量一个人做某事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依据。虽然认知例示功能、行动引导功能和技能衡量功能各不相同,但三者存在内在联系,揭示了KH与KT、能力和技能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