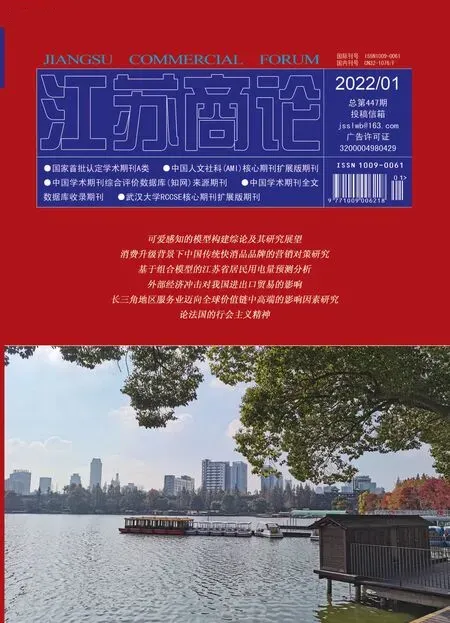论法国的行会主义精神
田珊珊,庞 杨
(东华大学,上海201620)
一、法国行会主义的概念
行会主义一词来源于行会。行会是一种行业互助组织,会员遵守一种共同的行业规范,并履行一定的行业职责,在行业内部形成生产者的团结,在国家内部形成同行企业间的团结。行会通常会限制学徒的数量以抑制不正当竞争。法国行会的职业道德由路易十四时期给予的职业特权培育而来,比如海员、矿工等职业。行会成员包括师傅、学徒、帮工,学徒通过一定的技能考试可以升为帮工,帮工通过一定的技能考试可以升为师傅。师傅和学徒,师傅和帮工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学徒必须听从师傅的教诲,认真向师傅学习技能。师傅也必须毫不保留地把职业技能教给学徒和帮工,并且为他们提供食宿和一定的补贴以供生活,监督产品质量,为整个行业发展把关。行会的设置还带有一定的宗教特色,设有宣誓职业,行会陪审员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行使他的道德职责和法律职责;行会管事会负责明确各个行会成员的职责,包括学徒、师傅的选拔和职业地位的维护等方面。不同的行业不断地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业加入行会组织中,同时也是为自己在等级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行会的作用在于它为每一个劳动者提供了一种特殊保护,使他们不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商品,而是一个有尊严的、在师傅的指导下传承职业传统的职业人。行业的繁荣比经济收入更加重要,这就使得行会成员不会因为任何经济利益而做违反行规的事情。
行会在建立之初承担着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是行会的主要职能,主要体现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监督、管理工商业活动。商品的交易和买卖具有一定的垄断性,限制自由竞争,不允许行会成员以外的人从事这一行业。1182年,法国屠夫行会被授予特许状,垄断买卖鲜活或死的牲畜①。除此之外,行会对产品的质量、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对质量低劣的产品当场销毁或处以罚金。行会对手工作坊的学徒和帮工数量也有限制,并且对商品价格和工资报酬进行严格的管理。这样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行业生产的质量和劳动者的利益,确保了行业发展的秩序。行会的社会职能体现在行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和救济上,确定工作条件,营造一种新的社团精神,在这个社团里,所有的社会阶层被团聚在一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注资的互助基金会使劳动者能够在遭遇不幸时得到行业力量的支持,也是行会加强行业归属感的原因。
行会主义在行会建立之初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繁荣,国家利益是首要利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通常放在第二位。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后,行业利益就成为首要利益,维护行业利益和传承职业精神仍是主要的职业文化。整个社会由各个分散的职业利益群体构成,履行行业职责和捍卫行业特权是这些群体最主要的行为特征,这就使他们得以区别于其他行业,占据自己的特殊地位,并为自己的职业地位感到骄傲。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的行会有公福尔(confrérie)、于行德(jurande)、吉尔德(gilde)、安斯(hanse)几种形式。公福尔是一种宗教、慈善组织,于行德、吉尔德、安斯是一种职业互助组织。在行会组织内部,也区分不同的行会成员,自由职业成员没有严格的从业规则,只需要在法律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行业职责。宣誓职业成员必须有皇家颁发的从业执照、行业学习、行业规范,晋升师傅的条件都有严格的规定。教规职业成员虽有一定的从业规范的限制,但比宣誓职业成员的自由度更大,从事职业的门槛较低。在14世纪前,只有教规职业成员,之后,才逐渐有了宣誓职业成员。
行会用公共纪律来约束行会成员,师傅掌控整个行会的发展方向并选举宣誓职业成员,整个行会的争议、争端都由宣誓职业成员来裁决,它是一种职业道德的奉行者。行会拥有一定的特权,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行会主义根据职业和社会地位分配权力,将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尽管有着互相的猜疑,但还是加强了行业团结。
二、法国行会主义的盛和衰
行会兴起于11世纪,高卢-罗马的行业协会和日耳曼的吉尔德组织是最初的原形。这两个组织同时带有宗教和慈善的色彩,为了保护其成员应对各种灾害,这个时期的社团组织职业性质不是十分明显,直到11世纪在卢瓦尔河-罗纳河地区产生的行会才开始有了职业色彩的萌芽。这个时期的行会主要是为伯爵、神职人员、国王服务的手工业者。吉尔德组织最初将大商人和小零售商组织起来建立一种职业虔诚和互助,早期主要集中在面包商、毡合工、成衣商。
从十三世纪开始,随着经济、政治的稳定,无论在发达城市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行会开始增多,并且严格按照行业制订的规范来组织。在法国,许多行业如皮货商、成衣商、旧货商人、建筑工人、工商业者、面包店老板、肉店老板等通过行会的建立得以形成。由于经济原因,为了控制生产,统治者对行会给予支持并且增加行会成员,统治者和行会师傅之间达成协议②。亨利二世在1581年立法推广行会,亨利四世1597年也同样鼓励行会的发展;黎色留和科尔伯特也竭力发展行会。一直到18世纪,宫廷给予行会重要支持,行会发展达到了巅峰。比如,普瓦捷在14世纪有18个行业组织,到了16世纪发展到25个,15世纪发展到42个。在巴黎,1672年,行会组织是60个,1691年发展到129个③。
行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达到了顶峰。路易十三统治时期的内战大大削弱了经济繁荣,物价上涨缓慢,迫切需要更加严谨地规范行业秩序。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使行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国王在这一时期给予行业更多的特权,使行业为国家服务。1560—1570年,商业保护主义盛行,手工业者通过规范行业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反对自由竞争出现的行业混乱。行会中的自由职业成员开始转向行会陪审员制度,传统的行会组织又重新恢复了活力。1597年,国王为了规范行业秩序,在巴黎、普罗旺斯、奥佛涅增加行会的数量。1661—1683年,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大力发展行会,使它服务于国家。他推行的主要政策就是出口法国的产品,建立贸易顺差,使法国产品名扬海内外。他提出将所有的职业都组织成行会,1691年巴黎的行会数量从60个增加到129个,在香槟地区、勃艮第地区、皮卡第地区、普瓦图-夏朗德地区、朗格多克地区也出现了行会数量增长的趋势。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为各个行业制订从业规则,这包括学徒的接收条件,对手工业制品的要求,雇用条件和解雇条件。为了重振老工业,政府重新整顿纺织行业,在很多地区建立了行会。通过这一时期行会的发展,法国劳动者逐渐形成一种行业归属感和公共精神。在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统治之后,行会精神得到了传承。1719年,箍桶匠行会重新更新并规范他们的行业规则,很多自由劳动者联合起来加入行会获得特权。从17世纪中叶开始,很多职业比如丝绸生产商、印刷工人、造纸者都以从事一种艺术,而不是以一种职业为荣。
尽管行会从13世纪到18世纪得到了繁荣发展,但从14世纪开始便遭遇了危机。准入条件的严格和控制使加入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内部晋升和外部招募受到了控制。从此,成为行会师傅的概率越来越小,并且只保留给行会师傅的儿子。从16世纪开始,持久性的大罢工开始出现,1539—1542年,里昂的打印工人和巴黎的打印工人举行罢工。这场行会的内部危机还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行会的自然衰落。从16世纪开始,行会便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从17世纪到18世纪,人口增长,城市发展迅速,工业劳动力增加,受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倾向于更加自由的经济模式,在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工作方式逐渐改变。在欧洲范围内,经济变革对行会组织提出了质疑,英国和荷兰都对行会提出了批判,认为它是阻碍机械化发展的桎梏。这一时期,启蒙运动思潮的崛起掀起了一场知识运动和道德运动,人们开始主张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自由。1791年,工作自由、商业自由、工业自由的法案得到推行,沙普利法提出司法上的个人主义:《职业群体、企业主、工人或学徒不能选举总统、秘书、工会,为公共利益制定法律法规》(article 1)。这是对行会的一种削弱,否定了行业利益(article 2)。同时,政府希望通过打压行会来加强国家的权威,使行业参与到竞争中去。1940年,行会得以复苏④。
尽管行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在旧制度之前它还是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⑤。大革命虽然废除了行会的发展,但这个传统仍然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得以保留。在法国工业化的历史里,行会主义始终成为一种现代化管理的工作方式。这显示了法国社会对行会传统的依恋。14世纪和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利益和收益成为此种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社会分工使得行业变得难以独立,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方式的自由而变得自由。然而,法国的劳动者并未完全被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他们倾向于保留他们的特权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政府对这种生产方式给予支持,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如圣戈班、雅宝信⑥。传统的生产和工作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不匹配,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法国人坚定的不接受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始终是行会模式占据主导,并排斥自由和竞争。
在沙普利法期间,行会的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互助会和工会先后填补了行会的空白,承担起了捍卫职业利益和加强职业团结的责任。这些职业社团以秘密的形式维护着职业化。如Henri Hatzfeld所说,“在行会被禁止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在很多时候都试图重新集合起来,这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控制产品价格,期待一个变革的行业组织,对互助和团结的渴望⑦”。1799—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第二共和国统治初期,很多的互助组织建立起来,承担了救助和反抗运动的双重职责。互助会的数量从1800年的60个增加到1815年的114个,先是在巴黎,后逐步在格勒诺贝尔、里昂、马赛等地建立。
三、法国行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形式
1791年,法国大革命彻底废除了行会,这意味着将整个社会划分成不同的职业群体的格局也被打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791年前的行会主义的精神还在当今社会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社会仍然由不同的行业群体组成,每个群体捍卫自身的职业特权并履行自身的职责,形成一种行业自治,建立了行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⑧。行会主义精神的延续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工会组织和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延续。
法国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行会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最好体现。120种制度和12000个附加制度将整个社会分成了拥有特权的不同的职业群体。每个职业,不管是从社会标准来看相对优越的职业或是相对卑贱的职业,都对自身职业群体所属的责任和特权保持警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如同参加行会一样,实现了在等级社会中使个人归属于某个职业群体,使群体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尊严在等级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作用。从行会萌芽阶段到社保制度正式建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行会并未因谢普利法的颁布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始终活跃在各项正式制度的安排中,体现了传统的现代化。
第一阶段:社保制度的行业化萌芽阶段
其实行业利益从17世纪起就受到国家的重视,开始在一些行业建立起特殊制度。从1673年开始,路易十四给予海上官员以及伤病和残疾的海员以特殊补贴。1709年,特殊福利扩展到商船海员及渔民。1790年,针对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制度建立,覆盖国家、大区、省、市的工作人员及医疗系统的职工,制度规定工作满30年后可以在50岁退休。1806、1812、1824年特殊制度的退休制度分别在法兰西银行、法国戏剧院、国家印刷厂建立。1894年法案在国家支持下建立了矿工社会互助制度和矿工退休制度,1850年雇主为铁路职工建立了医疗服务制度,1853年建立了铁路职工互助基金会,1855年建立了铁路职工退休制度,主要覆盖法国西部、北部和巴黎-奥尔良地区。1909年,铁路职工通过工人运动建立全国范围的退休制度。特殊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出于国家和企业主对一些行业的危险性和特殊性的考虑。除此之外,工人运动对提高原有福利水平和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⑨。
第二阶段:1830—1939行业互助基金会和社会保险模式
法国最早的行业互助始于中世纪的行会,同一行业的成员在危难时实施互济,是一种有限的、非正式的互助。1791年行会被废除后,互助会以新形式行会的身份出现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会员们交纳一定的分摊金,等到风险来临时享受应有的补贴。1848年二月革命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互助会因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然而1851年,政府出于加强国家统治和权威的考虑,解散了互助会,直到1852年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下才又得到承认。第二帝国时期互助会发展迅速,得到了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1898年国家还鼓励成立生育和教育互助会。1940年,在维希政府行会主义政策的影响下,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纷纷建立,行业团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行业为单位的互助传统奠定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格局和框架。
1910年,工人农民的退休保险制度(ROP),由雇主、雇员、国家共同合作,这项制度虽然最后没有被广泛运用,但却是以合作主义模式建立的第一项制度。1928—1930建立了由雇主、职员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险模式,这为1945年Pierre Laroque建立的社会保险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表明合作主义在法国经济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1945—1967社保制度正式建立和完善阶段
1945年8月由政府提出的建立社保制度的报告中,法国计划借鉴英国的社保模式,实现以普享、统一、均一为原则的全民保障。然而,社会保障法的撰写者也是社会保险的负责人Pierre Laroque却在社保制度建立阶段表现出与全民福利悖反、与行会主义趋同的改革理念。
1.通过职业团结来实现全民福利。在受到英国贝弗里奇模式的影响下,法国还是转而选择了以职业权决定保障权的路径,Pierre Laroque认为,职业权和公民权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工作者或即将成为工作者⑩。所以,以职业团结的形式来实现全民团结才是最为合适的。社保制定者认为职业社会是法国社会的重要属性,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公民社会。
2.Pierre Laroque在肯定职业权的基础上,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社保需求,使社保政策个性化,他认为社保制度对每个人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因为伤病、退休、生育等原因带来的损失也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制定不同的社保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弥补个人的损失⑪。每个个体是嵌入在自身职业体系里的,每个人因职业产生的各种风险都是不一样的,Pierre Laroque的社保理念本身就带有对行业化的倾向性。因此,碎片化的社保制度不单是工人运动的结果,社保制定者作为行会主义文化的执行者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Pierre Laroque在制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计划时,反对直接废除代表行业利益的特殊制度,主张以补充保险的形式在一般制度基础上延续之前的特殊利益,这本身就预示着改革的不彻底。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特殊制度于1946年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在社保制度中。1948年,非农领薪者制度和领薪农业者制度的建立与社保制度统一化的思想逐渐疏离,碎片化的加剧更加表明法国不可能脱离行会主义文化而建立一个贝弗里奇式的全民统一的社保模式。
1947年到1967年,社保制度的完善阶段其实也是将不同行业群体纳入一般制度内和建立与特殊制度性质相同的补充制度的过程。如1947年建立了官员补充退休制度(AGIRC);1952年建立了非领薪农业者的强制退休保险制度;1961年建立了非领薪农业者的强制医疗保险制度;1966年出台了非农领薪者的医疗生育制度;1966年建立了非领薪农业者工伤、职业病补偿制度。
第四阶段:1970—1978均一化改革阶段
即便是在以均一化为完善社保制度目标的改革阶段也不乏行业碎片化的政策。1971年旨在提高领薪农业者退休制度水平的法案出台,1972年建立了领薪农业者工伤保险制度,1978年司祭和教会成员的特别制度建立。为了消除各个职业社会群体福利水平的差异,社保改革者在这个时期推出了均一原则为目标的改革计划。1972年,商人、手工业者退休制度被纳入一般制度中。1973年,商人、手工业者的其他制度也被纳入一般制度中。1974年的法案将建立全法统一的社保制度提上日程,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生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保险⑫。然而,均一化的目的并没有就此达到,特殊制度的受益者拒绝降低他们的福利水平,甚至不惜提高分摊金缴费标准,改革对他们来说是徒劳的。非农领薪者和农业者,自由职业者和非领薪农业者保留了他们低分摊金和低补贴的特权。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将特殊利益纳入一般制度中,改革本身的方案也是缺乏组织性和系统性的。R.Delorme和C.André指出这项改革在保险项目和保障水平上都存在缺陷,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死亡险都被排除在外,并且补充保险不在被改革之列⑬。这些漏洞都使得消除福利水平差异的改革只能是隔靴搔痒。特殊利益群体的不妥协显示出行会主义文化的根深蒂固,改革方案本身的缺憾也表明法国还不具备达到均一化原则的文化基础。
1884年,法国的工人运动是被禁止的。在这期间,工人们建立起了秘密的互助组织和反抗组织,这些组织是建立工会和互助保险的基础⑭。工会集合了工人阶级群体,互助保险则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法国总工会于1895年建成,天主教工会联盟于1919年建成。在现代社会,工会代替行会扮演了保障行业利益,维护行业发展的角色。为了论证行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采用了访谈的形式来研究法国人对行会主义的态度和看法。在采访到的人中,所有人对行会主义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⑮。
1.认为自己的所得利益是正常的,心安理得的,“我父母觉得买的药得到报销是正常的,法国人习惯于国家为其提供各项保障。法国人有这样的情绪,他们希望自己是被救助的。”(私营业主)“我们应该一直比我们的上一代生活得好,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假期、娱乐,所有这些。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工作,我们的下一代有权利少工作并生活的比我们好。如果我们总是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生活,我们的孩子以后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对利益和福利的不断争取是行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法国社会则更多的是以行业的名义。
2.受访者对罢工的看法不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而是一种出于理性的行为,“我尊重这项权利,这是人人拥有的权利。当然,有人罢工的时候,另一些人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公共交通教师、清洁工的罢工。但是,人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原因的。”这位老师的心声也同时获得了一位学生的认同:“对于你们(外国人),地铁罢工看起来很恐怖,但我已经习惯了。当然,对于巴黎人来说,这是一种苦难,但也不要过分妖魔化它。巴黎公交公司的员工不停地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他们不是懒汉。当他们停止工作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另一位大学生对罢工等社会运动则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罢工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真正的职业劳动者。我认识一个地铁司机,他四十多岁,他挣的比最低工资的数额就多一点。他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生物钟被完全打乱了,工作条件也十分严峻。尽管有罢工,基本服务也得到了保证。”一位普通工人说:“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是很正常的,不然谁为他们做呢?”受访者对罢工者相对宽容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行会主义的一种赞同和默许,他们认为行业通过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维护行业特权是正当的。
正如巴黎公交公司的员工所说:“巴黎公交公司,人们并不重视它,只有当我们停止工作时我们才会得到重视。人们认为我们是受惠的,其实,我们的职业很艰辛。”这种在工作中缺乏认同感的感觉成为劳动者们抱怨的主要动机。根据2008年的一项l’Ifop调查,三分之二的劳动者认为不被承认是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根据另一项调查,(Observatoire Cegos“关于企业里的社会关系”)45%的法国人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承认。TNS Sofres的社会调查显示,不到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20年以来,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评价态势呈上升趋势。1986年,超过24%的人认为努力和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和奖励。2004年,超过37%的人这样认为。
工资低,某些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低,对个人努力的忽略是造成诸多劳动者认为自己工作没有得到认可的原因。法国人定义自己为“是某某人”而不是“做某某事”,也就是处于某个职业阶层的人,有职业归属感的人。在行会主义的保卫战中,利益的首位和职业地位的守卫同等重要。“行会主义会带来混乱、争议、对抗,但它同时是保障职业、社会群体社会融入的重要手段⑯”。
法国的行会主义在行会消失的时候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出现在劳动关系中,并且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以满足他们对行业地位和行业荣耀的追求。如同Jean-Pierre Ségal所说:“行会主义给人一种自私、忽略公共利益的感觉,但其实法国人并没有那么害怕变革,他们只是在要求一个配得上他们的荣耀的地位,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群体里的一员,满足他们对“伟大”和“荣誉”的追求⑰”。
四、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理性和感性的结合
法国行会的整体运作离不开现代化的因素,生产效率、技术革新、工业进步都是现代化的体现。现代化的工作理念和每个人对传统的依恋和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对行会主义精神的文化传统的秉承其实是达到技术革新、生产效率的助力器。
社会学家迪尔巴尔纳在对三个工厂进行民族志调研的研究中阐述了传统和现代的共融性。他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建立在对传统的道德意识的遵从基础上的:“在这三个国家中,个人融入集体完全不是出于想隶属于一个人人都融合在其中的群体的泛泛的感情,而是出于遵守规章,履行职责,尊重程序的责任感。现代性的虚幻在于认为处于责任感而服从自己意识的个人只属于自然和理智。但是,事实上是由制约道德意识的传统决定的,传统使人们的道德意识有所不同。美国人正直,尊重合同;荷兰人注重群体;法国人关心荣誉。责任感使一个民族群体固有传统的结果,人们出于这种责任感,在理智地构筑组织他们共同生活的机构时,表现得既‘现代’又‘传统’⑱。”法国的现代化的、高科技化的运作方式与法国传统观念意识上的责任是分不开的,这种责任感来源于对行会主义传统的恪守,对职业特权、职业荣誉感的绝对捍卫。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共同体”和“社会”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传统社会有着共同的语言、习俗、信仰、价值观和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并存,共同精神的意识的弱化,出于追求利益的目的对对方奴役、掠夺,双方产生对立或出于逐利的目的形成结盟。滕尼斯将人和人的关系解释为不同意志的驱使,“本质意志”将个人好恶、传统习俗、感性思维作为个人行动的准则,“选择意志”则将个人利益、目标实现、理智思维作为活动的思想动机⑲。社会变迁的发展被认为是由“共同体”到“社会”,由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过程。如此看来,现代社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传统的重量微乎其微。换言之,整个社会的运作,大到制度构建,小到个人行为,都应当完全遵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的理性法则,不考虑价值体系、道德意识等文化因素。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到其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者提出的二元分析模式⑳,似乎都将传统和现代视为两个完全割裂的对立面,认为情感价值和理性机制应当分属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使我们转变视角,认识到理性价值的消极影响并呼吁情感价值的回归,这也是对传统和现代并存、共融的最好证明。
社会学以及哲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也足以证明文化传统、个人情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越来越受到重视。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的社会学概念就是在提醒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特别是在以经济效率为着眼点的工具理性化的时代。韦伯对于以牺牲价值信念和风俗习惯为代价的纯粹的工具理性感到忧虑和失望,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步分化。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将国家的政治使命作为制约经济利益过度发展的手段,这一思路将民族文化、国民情感诉求纳入国家决策的体系之内。卢梭在批判现代性的思想中,认为公共意志不能凌驾于个人、各社会阶层的意志之上,应该重新将人置于整个社会秩序的中央。他还特别强调情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尼采在反现代性的理论中批判现代理性压迫自我,应该用个人意愿、激情取代对理性世界的适应。他还提出了在西方理性文明的统治下,个体不应该只是共性的、普遍的,而应该具有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特别的属性。因此,社保制度作为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产物,尽管已经考虑到了工业革命对人性压迫的危机,然而也需要更多地将民族文化和社会阶层的特殊性考虑进去,使社保制度不至于因机械性、同质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陷入现代化危机的困境中。
传统和现代两大力量成为传统学派和现代学派争论的焦点。现代学派认为启蒙运动带来的是对传统秩序、传统偏见、特殊主义的摈弃,现代秩序被认为是个人理性活动的结果,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枷锁,进入到普遍、统一的价值体系。现代学派的学者Jean-Fran?ois Billeter描述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由被监管的状态到自由的状态,是一种去除迷信,去除历史印记的过程......必须要谋划未来,摆脱历史和宗教的束缚,摆脱老旧习惯和老旧偏见的束缚㉑”。传统学派竭力守护文化特殊主义,赞颂真实、根源、土地和血脉。Fran?ois Julien提出:“人们来到世界上带着固有的、天赋的准则,带着不可避免的本能、天性,一种从出生开始就属于他自己的传统......他从来都只能是他的祖先所创造的他,他从来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㉒”。Edmund Burke担忧大革命使骑士精神消失,他认为幻想、想象的传统构建了有序的社会生活㉓。Hippolyte Taine也赞同传统拥有的重要价值:“宗教、国家、法律、习俗,所有道德生活的组成部分都会得到保留、振兴、这取决于新秩序的倾向㉔”。
两大学派的争论使传统和现代成为两个完全对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伴随着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复兴而发展的,传统和现代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融合和交融。社会学家迪尔巴尔纳关于美国、德国、法国的三个工厂的实证调研很好地反映了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工厂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即我们是现代的,同时又是传统的。三个国家在关于自由的定义中,17、18世纪的哲学家给出的观点是传统社会中民众对自由的看法和期待。洛克的观点是“自由就是财产权,个人的财产包括他的生命,他的自由和他的财富㉕。”由此可见,美国人的自由观就是自己的命运不由他人主宰,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使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威胁。康德的观点则是“每个人的决策是为了大家,大家的决策也是为了个人㉖”,德国人对自由的定义为参与共同决策的权力,公共意志的完全统一。法国人将自由看作是“不在任何人面前屈尊,不因为利益而迎合任何人㉗。”自由和“特权”“特殊”相关联,和“荣誉”“尊贵”相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在工厂的管理中,旧制度下的传统文化逻辑依然继续反映在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人工作的方式始终是捍卫自己的职业特权并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不低声下气地提供服务,在上级面前仍然保持自己的职业自主性,这些工作方式都是传统的“职业的荣誉感”的文化的延续㉘。在美国工厂里,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可享有特权,上级对下级的生产指标和效果进行规定和评价,也是契约精神的延续,是对劳动力,即自己的财产拥有自由的处置权,经过契约双方的书面承诺,劳动者也就是选择了如何处置自己的劳动力,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待遇、考核方式等,并会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㉙。在现代社会中,先进的生产设备、效率化的管理方式都是现代性的特征,然而,这并不妨碍传统浸入到现代中帮助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背景上中法交流应当更加关注职业间的相互交流,互相学习职业精神。法国的行会主义模式是法国从中世纪开始流传至今的模式,缔造了法兰西民族的职业传统,以行会的规章要求行业自身,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精神支撑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法国社会得以运作的保障。中国社会在营造优良职业风气的背景下,借鉴法国的做法注重职业精神的缔造和职业传统的传承,维护各职业阶层的利益和地位,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立足于劳动者对职业的热爱和坚守。从法国行会的发展看,中国社会要想实现“劳动的有尊严”的目标,除了提高工资,加强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关爱外,还需要从建立劳动者的行业归属感着手,使传统的行业信条和行业自律得以重新成为职业文化中主流的价值观。将之和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使行业团结转化为行业的尊严感和责任感,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
注释:
①G.Fagniez,Documents relatifsàl’hisoire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en France,Paris:Alphonse Picard et Fils,1898,Vol.I,p.174.
②Robert Castel,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Fayard,1995:228.
③Robert Castel,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Fayard,1995:159
④Yves Tinard,L’exception française,Maxima Paris,2001:240.
⑤Emile Coornaert,les corporations en France avant 1789,Gallimard,1941:161.
⑥Robert Castel,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Fayard,1995:126.
⑦Henri hatzfeld,du paupérismeàla sécuritésociale 1850-1940,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2004,p.58.
⑧Robert Castel,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Fayard,1995:117.
⑨Thierry Taurant.Les régimes spéciaux de sécuritésociale.Paris: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2000,p.11.
⑩Pierre Laroque.“Le plan fran?ais de sécuritésociale”.Revue fran?aise du travail,n 16,1999,pp.221.
⑪Pierre Laroque.“Le plan fran?ais de sécuritésociale”.Revue fran?aise du travail,n 16,1999,pp.639.
⑫Bruno Palier.Gouverner la sécuritésociale.Paris: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2002.p.116-117.
⑬R.Delorme,C.André.l’Etat et l’économie,un essai d’explication de l’évolution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en France,1870-1980.Paris:Seuil,1983.p.424.
⑭B.Gibaud,de la mutualitéàla sécuritésociale:conflits et convergences,Atelier.P.49.
⑮笔者于2018年5月对在沪的30名法国人做了深度访谈,主题为社保制度和劳动关系.
⑯Jobert,B et Muller,P,l’Etat en action.Politique publique et corporatisme,PUF,1987,p.23.
⑰Jean-Pierre Ségal,Efficaces ensemble.Un défi fran aise,Seuil,2009,p.66
⑱[法]菲利普·迪里巴尔纳.荣誉的逻辑[M].马国华,葛志强译.商务印书馆,2005:30.
⑲[德]斐迪南德·滕尼斯,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8.
⑳马克斯·舍勒的工商精神和形而上学精神的对立,亨利·梅因的契约和人身依附的对立,齐奥尔格·西美尔的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对立.
㉑Jean François Billeter,contre François Julien,Allia,2006:198,转引自Fabrice Bouthilon,Zeev Sternhell et les Anti-Lumières,Commentaire,2007(1).
㉒Jean François Billeter,contre François Julien,Allia,2006:198,转引自Zeev Sternhell,Les Anti-Lumières,211
㉓Edmund Burke,Réflexions sur la révolution de France(1790),Hachette,coll.《Pluriel》,1989,p.97sq.
㉔Hippolyte 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L’Ancien régime(1875),Robert Laffont,coll.《Bouquins》,1986,p.155sq.
㉕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ment,1690:87.
㉖E.Kant,métaphysique des moeurs,1796:598.
㉗Siyès,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1789:28.
㉘[法]菲利普·迪里巴尔纳,马国华,葛志强译.荣誉的逻辑[M].商务印书馆,2005:99-103.
㉙[法]菲利普·迪里巴尔纳,马国华,葛志强译.荣誉的逻辑[M].商务印书馆,2005:15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