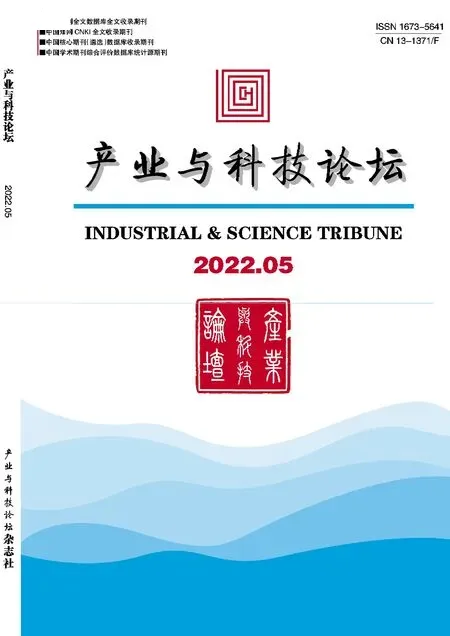文化间性视角下影视作品方言英译的不可译性研究
——以《新喜剧之王》为例
□黄惠宜 雷晴岚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融合与呈现。在跨文化语境下,影片译者需要注意片方的需求并考虑观众的观影效果与信息接受程度,其中不乏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化本身包含多元视角,电影字幕的翻语言转换由此会受到各种限制,从而产生不可译现象。聚焦于文化间性视角中的影片不可译现象,不仅有利于推动华语电影及文化在世界各文化中的传播,而且有助于文化间性理论在影片翻译领域的拓展应用。本文例子《新喜剧之王》中,存在较明显的方言文化特色,其字幕翻译具有相应的文化间性研究意义,因此该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文化间性
文化间性视角起源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受传统的西方哲学影响,主客体思维根深蒂固,交际理论长期受此影响而维持主体与客体的交际理念。而哈贝·马斯(1981)提出,人类在进行对话时应表现为一种双主体的平衡关系,以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取代传统的主客二分关系。此外,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把“文化间性”定义为“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可见,该理论与我国儒家思想倡导的“和而不同”理念不谋而合,都强调差异是沟通的前提,承认差异并相互尊重是交流的条件[1]。本文将结合文化间性理论剖析影视作品方言翻译的不可译性,以证明该理论对于影片翻译的适用度。
二、《新喜剧之王》中不可译现象
该影片延续周星驰导演一贯作风,聚焦于小人物的社会故事,讲述任劳任怨的临时演员如梦经历饱受质疑与磨炼的十余年,终于踏上最佳女主角颁奖台的故事。片中粤语配音诙谐有趣,再现名导演的现象级风范,无疑是观众追求的观影体验之一。于文化间性角度而言该影片具备区别于其他文化主体的主体化特点[2]。同时,此类特色文化内涵的参与加大了异语转换的难度,在一定条件下或可成为不可译问题。以下从文化间性角度出发,分析该影片部分方言台词的不可译性:
例1:粤语:杀你。
国语:成交。
英语:Deal.
“杀你”在粤语背景中是“成交”的意思,源自旧时广府商人在买卖时为避免同行得知价格,会在交易时做手势或暗语,而表示成交的手势就是以手作刀状在颈处比划,于是交易成功才有“杀你”的说法。译句之于影片角度确实有效传达原句意思,符合译语观众的基本观感需求。但从文化间性的角度出发,原句中蕴涵地方发展背景的方言台词在英译转换过程中或已失去交际主体的地位。原句自身的文化异质特性没有得到有效保留,仅原句意思得以传达到译语语境中,不免有所违背文化间性理论倡导的文化交际双主体平等交际的理念[3]。此外,由于影片的限制,译文难以达到与粤语原句在表层意思与内在文化要素上都完全匹配的高度,因此只能以失去原句文化内涵为代价,确保字面意思得以较完整传达,以保证剧情顺利推动。如此,粤语的文化内涵就被译语“拒之门外”,造成不可译现象。
例2:粤语/国语:咸鱼白菜
英语:plain rice
该例截自影片中背景音的粤语歌曲《分分钟需要你》。此处“咸鱼白菜”在原句语境中一般代指饮食寡淡,译句直接处理成‘plain rice’(白饭),即直接换成方便译入语观众理解的意象,从情节连贯角度而言,该译例确实达到基本传达期望。然而,从文化间性角度而言,“咸鱼白菜”这一文化意象显然未能跨越双语文化间的界限,造成译句中原句文化表象的缺失。表象是意义的载体,表象的缺失不免造成部分意义要素的缺失,其中当然包含文化内涵。地道译文固然符合观众的需求,但是以间性理论而言,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原片文化的主体参与地位。可见,原句中别具一格的文化形象有时难以在译入语中获得“新生命”,从而面临不可译难题。
例3:粤语:我忍你只四眼龟好耐啦。
国语:我忍你这四眼龟很久了。
英语:I've had enough of you.
该例句中“四眼龟”并不指四眼龟这种生物,而是取其比喻义。一方面引申指戴眼镜的人,且带有些许轻蔑调侃的含义;另一方面,龟这一形象在原句语境中存在一定的贬义,比如“缩头乌龟”等意象,代指遇事畏缩、怯于承担责任的人。译句则不考虑意象转换,直接用代词代替该文化意象,以达交际效果。以文化间性理论而言,这是原句的特色文化意象在译语中地位不均。原句该意象含有一定诙谐调侃的意味,其表达效果显然是代词所难以代替的,然而译句以代词替代处理,显然违背文化间性理念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双语文化的平等交际与和谐互通。
综上所述,以上例子均符合影片意思传达的基本要求,但句中的方言文化均难以移植到译语语境中,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可译现象[4]。从文化间性角度看来,译句由此失去原句的风格和文化蕴涵,体现英译过程中的双语文化交际地位不平衡。各例的英译既表现为文化间性视角中的不可译现象,同时也反映不可译现象中的文化间性理论。
三、不可译现象的原因
(一)表现形式限制。电影是一种完整表达特定内容的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方面,电影具有动态连贯性,所述故事情节是按预期安排发展的。由此翻译活动不免受到时间的限制,难以在相当有限的台词占时内传达所有原句的文化符号,就导致部分文化内容的缺失;另一方面,如果译者在荧幕中把原片冗杂的文化细节逐一解释,会造成字幕载体臃肿,影响观众的观感体验,甚至反而使观众无法有效理解台词,影响剧情表达的连贯性[5]。因此,影片特有的动态特点与观众观感会限制翻译行为,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可译现象。
(二)中英文化差异。电影是一种凝聚特定文化的声像艺术形式。影片中既定的文化背景及相关表达不只是单纯的形式,而是特定文化外显而成的载体,更是重要的语言文化意象。由此,看待中英双语差异,不应局限于语言载体的差异,关注双语文化的差异也同样重要。台词翻译涉及原片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再述,如果盲目消极处理,会造成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交际过程的地位不平衡,进而影响双语文化交际效果。因此,翻译活动需要兼顾双方语言及文化的平衡,既承认双方之间差异的存在,又相互尊重交际地位。由此可见,中英文化差异会增加翻译的难度,在翻译实践中会造成一定的不可译现象。
(三)方言文化特色。方言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承载形式,不仅有对话交流的作用,而且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群之于他们共同的生活与文化背景会产生独特的共鸣。影片《新喜剧之王》导演周星驰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在华语电影界可谓是脍炙人口,其特有的“无厘头”表达及方言背后的文化正是剧中人物形象和情节叙述饱满生动的一大助力器。可见方言文化与影片的喜剧效果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同时,方言又因其浓厚的地方特色与独特的共鸣感而难以移植到外语之中,经译语转换后可能失去原句的用意和文化底蕴,致使译入语观众难以完整体会到原片艺术情怀,从而影响影片现象级底蕴的传播。
四、解决措施
(一)采取意译。意译指不拘束于原句形式和表象的翻译,侧重原句意思的传达。在电影翻译中,意译方法往往采用在难以或无法保留原句表象或风格的情况中。根据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传达原句意思,并必要情况下放弃原句形式。出于对电影形式及画面的相关考虑,该方法比较适合用于处理不可译之处。但以文化间性角度,该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原语文化,难免造成文化交际地位不均的状况,因此要视具体情况而谨慎选择。
(二)适当加注。影片具有突出的观感要求,不同于书本等其他载体,有其动态性与观感需求。一般情况下影片放映难以暂停,观众也难以有足够多的时间琢磨相关大量注解,并且冗长注释会降低影片的美感,因此译者需要注意注解的长度。对于同一场面的较长台词中的文化承载词可适当添加注释,因为观众既有足够时间理解注释,又不至于影响剧情的推动。反之,如果是较短的台词场面,就比较不合适加注,因为该画面转换较快,观众或许无足够时间理解注释而影响观影体验。因此,电影翻译应该遵循“可观性”这一要求,无论是画面美观还是理解能力上都应充分考虑观众的观感体验,努力维护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名。
(三)增加宣传。适当推荐有兴趣了解更多文化细节的观众去接触和学习影片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而不能依赖在影片中补充过多的背景及文化信息。一来,电影本来就是一种动态的影视艺术方式,观众的观赏和信息都比较受限。再者,不可译问题之于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片方可以引导译语观众自行了解更多文化资讯,也可以根据具体剧情状况制定文化科普在线链接或小册子,以便观众在观影前后对影片的背景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五、结语
影视作品因其生动有趣,往往深入民心,如果方言文化的传播能充分利用影视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可谓如借东风。在这场“东风”中,字幕翻译俨然逃不开处理不可译问题这一难关。这就要求译者关注文化间性理论,既尊重双语间差异,又维护双语交际的双主体地位;既要有过硬的双语水平,又不乏相当的背景知识储备,才能在翻译实践中根据词汇、句子、语篇的差异之处而推敲出最佳的处理方式,才能使不可译现象朝可译可处理的大方向靠拢。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