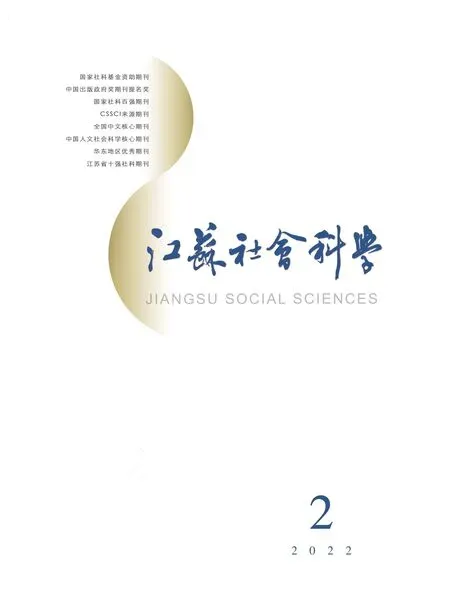皮尔士符号分类与演变理论之解读与修正
姜奕村
内容提要 皮尔士符号学始于其三元范畴理论,即将作为原初现象总和的“现象元”划分为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以此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他提出了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的新范畴列表和著名的三元符号理论。进而,根据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皮尔士将符号细分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三种类型,并指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遗憾的是,皮尔士对符号分类和转化的论述并不透彻。主要问题在于,他认为像似符号是第一性的,指示符号是第二性的,而这一观点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过程相违背。结合当今符号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本文拟系统梳理和解读皮尔士符号分类的理论推演过程,详细阐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背后的推理模式,力求对皮尔士的经典符号理论进行必要的反思和修正。
一、引言
作为符号学美国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与瑞士学者费迪南·德·索绪尔并称现代符号学之父。两位学者虽处相近历史时期,但因二人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路径殊异,而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分别为符号学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其中,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曾引领和推动了结构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的兴起和发展,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和对语言符号结构关系的分析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走向。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覆盖面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其影响力遍及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法学和文艺理论批评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的国际学界,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曾一度“鲜为人知”,以致需要其美国同胞、后辈学者莫里斯等人对其进行“再发现”。在我国学术界,皮尔士的理论也通常因被打上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烙印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误解和误读[1]丁尔苏:《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但实际上,在其一生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皮尔士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符号学理论[2]Innis,R.E.,Semiotics: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p.1.,而非“实用主义”哲学,其符号学理论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在当代主要体现在其与索绪尔符号学在理论内容方面的互补性上。我们知道,索绪尔的共时观和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选择将“系统关系”或“价值”,而不是将意指活动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这一选择导致了其理论学说过分注重符号系统的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的性质和意义。与建基于二元对立关系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同,皮尔士符号学以对符号现象的逻辑分析和分类为基础,并逐步发展出一套操作性极强的逻辑符号学分析路径,最终形成了其符号类型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因此可以说,从世界符号学理论发展的整体来看,皮尔士的符号类型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中在符号现象和意义研究方面的理论缺失,使二者形成了理论内容上的互补关系。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导致皮尔士符号学常常沦为研究索绪尔符号学的一个机械的参照物,也间接导致了国内符号学界对皮尔士符号学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鉴于此种情况,有必要对皮尔士符号学的理论核心,即符号分类与演变理论,以及其哲学基础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关键理论细节进行必要的反思和修正。
二、三元范畴理论及其应用
要了解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就要从他对现象的三元划分说起。“现象”一词的英文是“phenomenon”,为了与这一日常词汇相区分,皮尔士创造了一个英文术语“phaneron”(这里译为“现象元”),并赋予其特定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不同,皮尔士的“现象元”是原初现象的总和,它指“在任何意义上或以任何方式呈现于头脑中的所有事物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对应于任何真实的事物”[3]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284,p.5.71.。换句话说,“现象元”既可以是人们头脑中对于现实的反映,也可以是完全虚构的想法。这样一来,皮尔士将“一切可能被感知或被思考的东西”[4]Gorlee,D.,"Firstness,Secondness,Thirdness,and Cha(u)nciness",Semiotica,1987,65(1/2),p.45.全部纳入了其现象学分析的范围之内。进而,他对“现象元”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并根据其复杂的结构层级进行分类。皮尔士认为,“现象元”包含三类相互关联的存在形式,即:一级存在(firstness)、二级存在(secondness)和三级存在(thirdness),或者称作“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其中每一类存在范畴都分别反映了人类经验的一种模式,这便是皮尔士提出的三个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ies)。皮尔士对这三个普遍范畴的定义和具体阐述构成了他的“三元范畴理论”。根据皮尔士的定义,一级存在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潜在性,它具有“纯粹感觉的性质”[5]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284,p.5.71.,是物体本身的内在特征,因此是一元的、自我独立的存在,皮尔士称之为“感觉品质”(qualities of impression)。关于一级存在,皮尔士所举的例子是人们对花香的被动意识,这种意识不包含任何主观识别或分析评价,只是一种感觉的状态。与一级存在相比,二级存在是一个二元的、实际的、相对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个别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经验,并且涉及主体与被感知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被某人所感知的某一种花的香味就是一种二级存在,人们会将这种香味与具体的某一种花联系起来。可见,对二级存在现象的具体感知以及因此形成的经验会促使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现象与事物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比如从属关系、接续关系和因果关系等等。三级存在属于抽象的范畴,“它使具体的时、空经验获得新的形态”[1]丁尔苏:《符号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比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同一事物的感知效果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人们仍然使用同样的符号来表达、再现和传递这些效果。三级存在是一级存在和二级存在之间的“媒介”,即“作为现象元素的表现”[2]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5.66,pp.1.545-1.559,p.8.213.。需要强调的是,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之间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具体而言,二级存在中包含着一级存在,三级存在中又包含着二级存在。例如,作为三级存在的语言符号就同时包含着其他两种存在类型。
皮尔士的三元范畴理论构成了其整个符号学学说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这一理论原则的最初应用出现在《一个新范畴列表》[3]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5.66,pp.1.545-1.559,p.8.213.[4]Hoopes, J. (ed.),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p.23-33,p.23.一文中。在文章中,皮尔士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的新范畴列表:品质、关系和表现,这三个要素分别对应于三元范畴理论中的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是“现象元”在人类经验领域的具体体现。该范畴列表显示了皮尔士如何根据人类思想意识的复杂形式结构对经验进行分类。皮尔士指出,作为初始经验的“现象元”要么体现为一种品质;要么体现为一种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反应;要么体现为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中介。作为对内心思想的反映,品质具体体现为感觉,关系具体体现为事实,而表现具体体现为概念。丹麦学者Johansen认为,皮尔士对范畴的分析源自他对康德范畴理论的研究[5]Johansen,J.,Dialogic Semiosis: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66.。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列出了一个范畴表,其中包含四个大类,每一类又分为三个小类,从而构成十二个范畴。皮尔士论述范畴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康德的十二个范畴。正因如此,他将上述分类称为“新范畴列表”。皮尔士对这一范畴分类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他送给世界的礼物[6]Hoopes, J. (ed.),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p.23-33,p.23.,并称这是他“对哲学的唯一贡献”[7]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5.66,pp.1.545-1.559,p.8.213.。他因而主张用这个新的范畴分类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分类和康德的十二个范畴分类。这一新的范畴分类对其符号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三元符号理论与符号的分类和转化
如前所述,皮尔士对现象和人类经验的逻辑分析与范畴化研究为其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其最终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符号学理论范式,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元符号理论”,即将符号分为相互依存的三个基本要素:再现体(representamen)、指称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对于符号而言,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基本组成部分。实际上,符号三要素是皮尔士提出的三个范畴要素(品质、关系和表现)在符号领域的具体体现,当然,也是其三元范畴理论(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的又一次成功的应用。我们可以从三组术语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来理解和把握符号三要素的意义与内涵。在三元符号结构中,作为一级存在的品质具体体现为符号再现体的固有特点和属性,皮尔士将其称为“依据”(ground),即再现体的表意依据,这是符号表意的基础,是一元的;作为二级存在的关系包含表意“依据和关联”,即体现符号的表意依据以及再现体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展现了符号的二元性;作为三级存在的“表现”包含“依据、对象和解释项”,展现了符号的三元性[1]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在这三种逻辑对应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依据”一词值得关注。皮尔士指出,依据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它构成了一种品质或一般属性”[2]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根据皮尔士的解释,符号再现体并非从所有方面再现其指称对象,而是基于某一方面的依据[3]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作为一个连接再现体与指称对象的抽象品质,表意依据体现了符号所固有的品质和特点,即符号性或代表性。可见,虽然“依据”最终并未包含在三元符号结构的核心术语中,但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符号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再现体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即符号-对象关系。
围绕着表意依据所体现的不同品质特征,皮尔士进一步细分了符号-对象关系。他首先提出了两种基本关系:“品质可能具有特殊的顽强意志,这防止了它被剥离其指涉相关物。因此,存在着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所指的依据是可剥离的或是其内在品质。第二种关系所指的依据是不可剥离的或是其相对品质。”[4]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这里,区分两种关系的标准是连接再现体与指称对象的中介性品质是否可以脱离二者的指涉关系而独立存在,即这种品质是否是再现体及其指称对象所固有的。可脱离其指涉关系的中介性品质是再现体与其指称对象的内在品质。比如,像似性就属于内在品质。一张照片与所照人物本人的像似性品质是二者的内在品质特征,无论这张照片与其本人是否产生具体联系,这些品质都可以通过任意一方而被人们感知到。换言之,内在品质反映的是再现体及其指称对象共同的内在特征。与内在品质相对应的是相对品质,即,不可脱离其指涉关系的中介性品质。例如,邻近性就是相对品质。现实生活中,邻近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空间邻近性、逻辑邻近性和从属邻近性。空间邻近性指的是空间指示关系,逻辑邻近性指因果关系,从属邻近性指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出行的旅人看到远处升起的炊烟推断出前面有一户人家。做出这种推断的依据是旅人的生活常识:炊烟是由人们做饭产生的。这样,对于旅人而言,炊烟就成为这户人家的指示符号,而连接二者的中介性品质是邻近性,但这种邻近性品质无法脱离符号再现体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而独立存在,它并非二者的内在品质,因而是表意依据中的相对品质。皮尔士指出,相对品质或不可脱离性品质又包括两种情况:基于符号使用者所感知到的事实性品质和符号使用者所任意赋予的品质。前一种品质通过邻近性关系或因果关系表现出来,后一种品质通过规约关系表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皮尔士进一步指出,符号再现体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种:基于像似性的关系、基于邻近性的关系和基于规约性的关系[5]Johansen,J.,Dialogic Semiosis: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92.。根据这三种关系,皮尔士将符号分为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三种类型,他这样说道:
因此,有三种类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那些与其指称对象仅仅在某种品质上是一致的表现形式可以被称为像似符号。第二,那些与其指称对象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一种对应关系的表现形式可以被称为指示符号。第三,那些与其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依据是建立在一种外加特性基础上的表现形式,与一般符号相同,可以被称为规约符号。[6]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
由此可见,再现体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像似关系建立在它们共有的某种内在特征或品质之上;再现体和指称对象之间的指示关系建立在二者之间的邻近性之上;再现体和指称对象之间的表现关系建立在规约性的基础上,即,这种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在后来的著作中,皮尔士经常强调这种符号分类方法,他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符号分类”[7]Peirce,C.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8 vols.,Hartshorne C.,Weiss P.,and Burks A.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557,p.1.551,p.2.228,p.1.558,p.1.558,p.2.275.,我们在这里将其称为“符号-对象关系分类”。在以下这个经常被引用的论述中,皮尔士对这种符号分类做了进一步说明:
有三种符号类型在所有推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种是图式符号或像似符号,它表现出与话语主体之间的像似或类似;第二种是指示符号,它像指示代词或关系代词一样,硬将注意力引向想要呈现的具体对象而不去描述它;第三种是一般性名称或描述,或称规约符号,它通过名称与所指特征之间的概念关联或习惯性连接来指称其对象。[1]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369,pp.2.247-2.249,p.4.447,p.2.276.[2]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369,pp.2.247-2.249,p.4.447,p.2.276.
这里,皮尔士定义的第一种符号是像似符号,它与第一种符号-对象关系相呼应,通过共有的、像似的内在品质来表示其指称对象。皮尔士认为,像似符号“在表意上非常完美”,因为它将“解释者直接带到了表意所指的特征面前”,因而算得上是“卓越的数学符号”[3]Peirce, C. S., The New Elements of Mathematics by Charles S. Peirce, 4 vols., Carolyn Eisele (ed.), The Hague: Mouton,1976,4,p.242.。皮尔士认为,纯粹的像似符号指的是人们对可感知对象特征的直接认识,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而传达的并非确定的或真实的信息[4]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369,pp.2.247-2.249,p.4.447,p.2.276.。他指出,即使是一个想法,也不是纯粹的像似符号,除非它被解释为一种可能性[5]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1.369,pp.2.247-2.249,p.4.447,p.2.276.。换言之,纯粹的像似符号仅仅意味着“某物在那里”,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中并不包含交流过程。然而,作为某种表意品质的体现,一个实际的功能性符号不可能是纯粹的[6]Johansen,J.,Dialogic Semiosis: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相反,在实际情况下,一个具体的像似符号通常兼具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等特征。美国著名皮尔士研究学者Max Fisch对三种符号之关系的描述颇具借鉴性:
这些[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是符号化过程中的元素或方面,在不同符号化过程中,它们的相对显著性或重要性有很大不同。因此,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中最显著的元素或方面的名称来称呼它,或者用我们直接关注的元素或方面的名称来称呼它,却并不因此表明它不包含其他两种元素或方面。[7]Fisch,M.,"Peirce's general theory of signs",in Thomas Sebeok(ed.),Sight,Sound and Sense,pp.31-70,Bloomington&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44.
该论述表明,现实中的符号可以在不同语境中充当三种符号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而不是固定于某一类型。换言之,尽管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三者之间在内涵和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并非三种相互排斥的符号,相反,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包含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关于这一点,皮尔士有如下论述:“一个符号通常涉及所有三种表现方式;如果一个符号中的像似性元素占主导地位,那么称之为像似符号将符合大多数目的。”[8]Peirce, C. S., Manuscripts in the Houghton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as numbered in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Richard S.Robin(ed.),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67,491,p.3.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三种元素的主导地位如何确立。在这方面,皮尔士没有做出明确回答,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基本理论观点和原则做出推断。从三元符号理论中的各项关系不难看出,解释项在皮尔士符号理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皮尔士认为,符号因其使用者的解释而成立,没有使用者的解释,符号则不成其为符号,这里的解释就指解释项。事实上,这是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一观点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称一个符号为像似符号,并非因为其本质上就是纯粹的像似符号,而是因为我们从像似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同理,我们称一个符号为指示符号,并非因为其本质上就是纯粹的指示符号,而是因为我们从指示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一个符号为规约符号,并非因为其本质上就是纯粹的规约符号,而是因为我们从规约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交流目的和释意需求的推动下,符号处于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
从对“现象元”的划分到对符号分类和转化的论述,皮尔士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感知、区分和解释我们的经验世界,进而形成我们所生活世界的概念。这一过程表明,人类思想经验的三个存在范畴都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符号来中介和体现,而对这些符号的进一步区分又显示了事物间不同的关系结构。换言之,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每一个片段,无论多么简单,都必须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这种事物便是代表它的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具有成为其他事物符号的潜在能力,任何事物都是符号。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符号性本质。
四、问题聚焦与理论修正
以上便是皮尔士关于符号分类和转化的经典理论,它经常被后世学人所引用和讨论,在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研究领域都有一定影响。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一理论中似乎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皮尔士对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与规约符号的排序并不符合这三种符号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知道,对于这三种符号,皮尔士提供的排列顺序是: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从上文对皮尔士符号理论的解读和推演中可以得出,这种排列顺序的依据是三元范畴理论和三个范畴要素。皮尔士对这三种符号的定义是根据符号再现体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分别对应三个范畴要素中的品质、关系和表现。也就是说,皮尔士认为基于联想推理的像似符号体现的是事物的某种内在品质,属于第一性或者一级存在范畴;基于因果推理的指示符号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属于第二性或者二级存在范畴;而基于约定俗成的规约符号体现的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或表现,属于第三性或者三级存在范畴。由此可见,皮尔士对三种符号类型的排列方式反映的是它们所属的不同存在范畴,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符号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就会发现,这种排列顺序并不能反映符号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过程。换言之,皮尔士对符号分类和转化的论述其实并不透彻,而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很值得商榷。
鉴于规约符号属于第三性的观点已成学界共识,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前两种符号的排列顺序上,即究竟应该是像似符号在先还是指示符号在先。如前所述,皮尔士认为像似符号更为基础,属于第一性或者一级存在范畴[1]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第63页。,而指示符号属于第二性或者二级存在范畴[2]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第63页。。但是,当代越来越多的有关生物符号发生史的研究却证明皮尔士的观点是错误的。早在1981 年,符号学者Krampen 就指出,植物的符号行为全部都是指示性的,并且植物不能产生和传达像似符号[3]Krampen,M.,"Phytosemiotics",Semiotica,1981,3/4,pp.187-209.。不单是植物,这种情况在动物中也是如此。比如,有研究发现,猕猴的叫声可以指向其自身的年龄或者性别等生理特征[4]Ghazanfar, A., Turesson, H., and Maier J., "Vocal-tract Resonances as Indexical Cues in Rhesus Monkeys", Current Biology,2007,5,pp.425-430.;Leavens的实验证明,黑猩猩主用手的食指能够指向它想要让对方注意的物体,这种用手发出的指示符号是最简单的指示符号之一。而这一实验也进一步证明,产生和传达简单指示符号的能力既不局限于人类也不需要专门学习和训练[5]Leavens,D.,"Indexical and Referential Pointing in Chimpanze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1996,4,pp.346-353.。2013年,认知符号学家Zlatev等所做的婴儿与猩猩的对比实验进一步证明,猩猩可以理解指示符号,但却无法理解像似符号,并且,在符号理解方面,猩猩的能力要比婴儿差[1]Zlatev, J., Madsen, J., and Lenninger, E.,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Semiotic Vehicles by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Cognitive Development,2013,3,pp.312-329.。这些研究证明,指示符号及其推理模式是自然界生物的基本生存能力,指示符号是比像似符号更为普遍和原始的符号类型。
上述实证研究成果也在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界得到了积极回应。其中,中国香港学者、国际著名符号学家丁尔苏教授的理论观点就很具代表性。他指出: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指示符号先于其他种类。即便是尚未发明语言的原始人也一定会经常使用它们。我们不难想象,人类的祖先通过一定时期的观察,可以从眼前密布的乌云预测到即将发生的降雨,也能够从女人胸前的乳房推断出她们的性别。在这里,乌云充当了降雨的指示符号,乳房则成了女性的指示符号。应该指出,指示符号并非人类专利,自然界各种高、低级动物乃至生物都具有相同的能力。专食腐尸的秃鹫就能够通过哺乳动物的体态和动作判断它们是否已经死亡,老虎也可以通过嗅觉得知其他动物的存在。[2]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这里不仅强调了指示符号的原始性,而且揭示了其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在人类认知和交流过程中的基础性。与丁尔苏观点类似,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也从符号发生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并强调指示符号的出现先于其他符号类型:“从生物进化的序列来看,植物与动物最原始的符号活动,都是指示符号;从儿童成长的过程来看,婴儿的符号活动,从指示符开始,渐渐学会使用像似符;从指示词语的序列性来看,人的周围世界,以指示词语构成基本秩序。”[3]赵毅衡:《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进而,赵毅衡得出了以下结论:“人的符号意识的起点,是指示性。”上述研究均表明,在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指示符号比像似符号更为基础。换言之,后者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
上述例子证明,从符号的演变过程来看,在指示符号之后出现的符号类型是像似符号,而像似符号的形成是对指示符号模仿的结果。以下是丁尔苏对于像似符号及其推理模式的具体论述:
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具有由A推导出B的能力。这种释意能力又被应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形成所谓“像似符号”。具体地说,如果有人希望向另一个人提及某个物体,而该物体此时不在眼前,那么她就有动力制造出与该物体的某个部分大体相似的声音、图像、颜色等等,以此“诱导”听话人做出她所希望的推理,这个类似于该物体某个部分的声音、图像、颜色或结构就是像似符号。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实际是一个指示符号“像似化”(iconification)的过程,人类语言的发生和发展都源于此。认清这一过程可以避免符号分类中不必要的混乱。[4]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这里详述了像似符号的形成过程。由A 推导出B 的推理模式被皮尔士称为试推法(abduction),它包含产生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的两种推理模式。丁尔苏强调,像似符号背后的推理依据是多种多样的,像似不一定是视觉上的或者图像上的,也可以是任何感觉上的。赵毅衡也持相同观点。他举出了听觉、味觉和嗅觉等各个方面的例子:听觉上,舒伯特的《鳟鱼》在旋律上与鱼的跳跃像似,科萨科夫《蜜蜂飞舞》中的音符与蜜蜂嗡嗡的声音像似;味觉上,“素鸡”与肉的滋味口感像似;嗅觉上,香水与某种花卉的香味像似[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页。。由此可见,我们虽然可以将像似符号背后的思维统称为像似性推理,但其中所包含的推理依据却十分丰富多样。
在此基础上,丁尔苏还阐明了指示符号与像似符号在本质上的区别:指示符号是“对外部环境或自我身体认知的结果”,像似符号是“为了影响他人思想、情绪和行为而对这种认知结果的利用”,换言之,后者是对前者的模仿或仿制[1]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此外,这个区别还告诉我们,指示符号没有交流意图,而像似符号带有交流意图。可见,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在人类认知和交流中扮演着极其不同的角色。指示符号虽然不带有交流意图,但却是交流活动的认知基础。像似符号兼具认知和交流的属性,并直接参与交流活动。由此可知,成功的指示性推理无须借助于像似性推理,但成功的像似性推理却一定要借助于指示性推理。这样,二者的相互关系便明晰起来。交流意图的介入将导致指示符号的像似化。
德国学者Rudi Keller对符号的分类和演变过程有着独到的看法。在谈到上述三种符号类型的时候,Keller没有完全沿用皮尔士的经典术语,而是用“症状符”(symptom)一词来代替皮尔士的指示符号(index),他认为三者的排列顺序应是:症状符(symptom)、像似符(icon)和规约符(symbol)。显然,他也认为症状符,即指示符号的排列顺序应先于像似符号。Keller对指示符号与被像似化的指示符号之间的区别分析得十分透彻:
假设我和我的同伴正在听一个报告,如果我想向她暗示这个报告实在太乏味了,我可以朝着她的方向打一个稍带夸张的哈欠。这个哈欠必须略微不同于真实的哈欠,以保证它不被误解。假装的哈欠应该足够显著,使得接受者知道这是一次思想交流的企图,从而去寻找合理的解释。为此,假装的哈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哈欠”的假装。
2.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假装”的哈欠。
通过假装,症状变成了类象符号[像似符号]。它经历了一个类象化[像似化]的过程,其中的理由是:真实的哈欠可能是缺氧的症状,而假装的哈欠永远不可能是缺氧的症状。只有真实的症状才是症状,症状的效仿相似于症状,因而是症状的类象符号[像似符号]。[2]参见丁尔苏:《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这是一个通过将指示符号像似化来达到交流目的的典型例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们之所以能够在交流中成功区分真实哈欠和假装哈欠,是因为人们将这一判断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两种符号的熟练掌握。缺乏生活经验的幼童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区分,这也证明了皮尔士“符号因解释而成立”的基本观点。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指示符号向像似符号演变的例子还有很多。以雨天与彩虹为例,人们观察到,彩虹这种奇景会在雨天过后出现,但只是偶现,这是人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于是,每当雨天过后,人们会期待彩虹的出现。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雨天是彩虹的指示符号,因为雨天之后出现彩虹的概率很小。但是,反过来看,彩虹却可以是雨天的指示符号,因为每当彩虹出现,一定下过雨。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这种知识继续引申并运用在交流活动中,并出于对彩虹这种奇景的喜爱而将其与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发现,与雨天之后偶现的彩虹像似,世间的美好事物也往往无法轻易得到,而是要经历一番挫折磨难。这样一来,雨天与彩虹这样一对具有指示关系的符号就被像似化,“风雨之后见彩虹”便用来比喻人们通过克服挫折和磨难最终得到美好事物。
如前所述,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源于完全不同的推理模式:指示性推理和像似性推理。在语言尚未出现的人类早期交流活动中,这两种推理模式尤其活跃。丹麦学者Johansen 教授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在实际交流活动中,仅有像似性元素不足以构成认知和理解,因为“还需要有凸显所指对象的指示性元素”[3]Johansen,J.,Dialogic Semiosis: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96.。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借用Keller 教授在《语言符号理论》中的一个例子:“在树林中散步时,我想让同伴注意到有一只鸽子停在树枝上,但又不想惊跑它。我可以指着鸽子,模仿它的咕咕声。我的同伴会由此推断:‘啊哈,这家伙可能想让我看一只鸽子。’”[1]Keller,R.,A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0.在这个交流活动中,仅仅是对鸽子声音的模仿并不能让同伴意识到有一只鸽子正停在旁边的树枝上。实际的过程是这样的:同伴听到模仿的声音,认出所做的手势,并顺着手势看去才能发现树枝上的鸽子。对咕咕声的确认要靠像似性推理,而对手势的确认则要靠指示性推理,两种推理相结合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交流。即使在语言符号出现之后,人类也继续使用这两种推理方式,进而产生了转喻和隐喻。
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的演变方向都是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最成熟的符号类型,也可能是人类独有的符号类型。如前所述,规约符号对应的是符号-对象的第三种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惯例或者规约建立起来的。相比于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人们对规约符号的解读不依赖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从属、因果或者时空接续关系,也不需要在它们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像似性,而是“遵循所在社团在符号形式与指称对象之间所建立的习惯性对应”[2]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人类语言中的多数词语都属于规约符号的范畴,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并非因为它们与其所指对象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者某种时空上的联系,也并非因为它们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具有某些像似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语言社团里的所有人都在做这种词义连接。事实证明,规约符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总体过程来看,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是规约符号形成的基础。皮尔士也曾指出,规约符号由另外两种符号发展而来,他重点强调了像似符号向规约符号的转化[3]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2.302,p.2.222.。另外,他还补充道,规约符号总是包含着指示性成分和某种形式的像似性成分[4]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8 vols., Hartshorne C., Weiss P., and Burks A. W. (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66,p.2.302,p.2.222.[5]Peirce, C. S., The New Elements of Mathematics by Charles S. Peirce, 4 vols., Carolyn Eisele (ed.), The Hague: Mouton,1976,4,p.256.。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都会经历规约化的过程,进而演变为规约符号,成为相对稳定的人类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例如,不同的动物会发出不同的叫声,有些动物具有代表性的叫声,像犬吠和鸡鸣,会被用来代表发出这种声音的动物。这样,不同的叫声就成了这些动物的指示符号。进而,人们为了交流而模仿这些动物的声音,就产生了拟声词,也就是像似符号。这类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像似性联想也会因为不断的重复使用和“习惯成自然”而逐渐淡化直至彻底消失,最终由像似符号演变成约定俗成的规约符号,这便是符号的规约化过程或者称作词汇化过程。隐喻是一种典型的像似符号,在符号演变过程中,许多曾经活跃的隐喻表达会因为人们反复地、频繁地使用而被词汇化,最终成为规约符号。规约化或词汇化的过程会消除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原有联系,也就是说,当人们使用被规约化了的隐喻表达时,人们脑海中不再浮现像似性联想或想象。隐喻的创造有时非常偶然,也并非所有的隐喻都会被频繁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使用率很低的隐喻会逐渐被人们遗忘,而那些人们经常使用的隐喻则很可能因为反复地、频繁地使用而最终被语言社群规约化,变成普通词汇。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将这三种符号类型置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考查,就不难发现,为了满足认知和交流的需要,符号始终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在演变过程中,众多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最终会失去它们原有的解释基础以及先前建立的符号-对象关系,变成规约符号。相比于其他两种符号,规约符号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但是也并非不再变化。在有些情形之下,人们会故意将规约符号去规约化或者再次像似化,使其重新成为像似符号,以达到某种目的。例如,大多数汉字起初都是像似符号,在经历了规约化过程之后逐渐成为汉语语言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教幼儿园小朋友识字或者教授完全不懂汉语的外国友人学习汉字,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追溯汉字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像似关系,通过触发像似性联想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汉字最初的造字原理、更有效地掌握汉字。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语言领域,在艺术、文化等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艺术创作和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不断冲破规约性惯常思维的束缚,将生活中原有规约符号去规约化,从而在美学上创造新的意义和解释项。同理,文化创新也是如此。与规约符号的重新像似化相似,在某些情形下,规约符号和像似符号都可能重新转化为指示符号。由此可见,符号的演变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变化过程,它并不会终结于某种符号类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们对这三种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就不会停歇,而三种符号的相互转化和演变也将永不停歇。
五、结语
可以说,三元范畴理论是皮尔士符号学中最基本、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原则,无论是新范畴列表中的三个范畴要素还是著名的三元符号理论都由其推演而来。然而,在皮尔士使用三元范畴理论对符号-对象关系进行分类时却出现了问题。皮尔士没有认识到的是,虽然“品质”属于一级存在范畴,但以品质为基础推导而来的像似符号却不一定就是第一性的。相反,当代生物符号发生史的众多研究证明,基于某种“关系”的指示符号要比像似符号更为普遍和原始,指示性才是意指活动的第一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符号-对象关系分类中三项的先后顺序做出如下修正和调整:指示符号(第一性)、像似符号(第二性)和规约符号(第三性)。理论与实践均证明,这一排列顺序更符合符号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过程。实际上,相对于约定俗成的“表现”而言,品质和关系均属于不够稳定的符号依据。因此,与规约符号相比,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都是未充分发展的符号,或者说是“演进过程中”的符号。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确定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先后关系的时候需要考虑其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过程,而在确定规约符号与其他二者关系时就要容易得多。
上述问题的出现对于研究者而言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对于皮尔士的三元范畴理论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合理阐释和应用,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任何僵化的、机械性的理解和套用只能使理论陷入误区;第二,对于理论假设不能只顾单纯的逻辑推导,还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论证。这两点启示提醒我们以更加理性和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重要符号分类的再思考和再认识,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皮尔士对符号-对象关系进行分类和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确,符号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对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是我们时刻都在进行的意指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厘清符号类型关系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意指活动进行分析和解读。在这方面,皮尔士提出的“符号因解释而成立”的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符号使用者重新推向了意义研究的中心,对当今符号学和意义研究而言意义非凡。不仅如此,符号-对象关系分类和进一步细分的思路完全有可能为某一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上或方法上的新视角。例如,它可能为隐喻研究或者艺术学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这说明,作为皮尔士符号学中最基本的、最具生命力的符号分类,符号-对象关系分类在当今我国学术界仍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