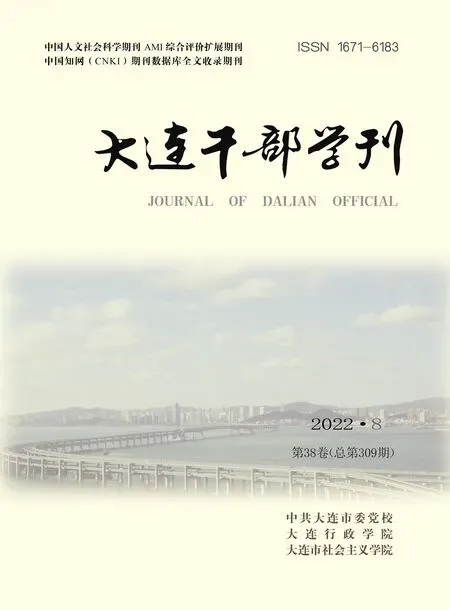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理论探索
范根平,王玲玲
(1.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深圳市坪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广东 深圳 518000)
回看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马克思并没有一开始就关注资本逻辑,这是因为青年马克思最初把目光投向法学和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整个思想轨迹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激励他不断走向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转折点。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理顺了国家、法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从社会现实走向“书房”,展开了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从这层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以法哲学批判为理论基础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原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和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本源性,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们把握他批判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提供了理论导引。
一、从“物质利益难题”到“经济学转向”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碰到了两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一是封建专制政府通过严苛且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极力扼杀出版自由;二是林木所有者借用反动政府的法令迫害劳苦大众。“马克思用这两件事为材料对地主政府发出特别强烈的控诉。政府在认真考虑当事区政府的情感后,决定启用自己的审查权力,并且审查越来越严格。马克思用尽了心思来与审查们周旋。”[1]以上两个问题究其根本属于“物质利益”问题,也是马克思遇到的“苦恼的疑问”。面对这些现实问题,青年马克思准备撰写政论文章予以回击,但他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还相当薄弱,于是开始全神贯注地沉浸于首批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2],并在此基础上广泛阅读前人的作品。
“物质利益难题”使马克思逐渐摆脱了世俗约束,开始从现实本身探寻现实政治和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曾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3]588马克思之所以受困于物质利益问题,主要源于他当时所接受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根本无法对物质利益纠纷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是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本身就把关涉物质利益问题的纷争引入“市民社会”的私欲战场,也就是把法、权利和物质利益的实在关系颠倒为虚幻的无法化解的理想性关系。从理论上看,物质利益和法哲学的关系是“现实实有”和“观念应有”的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无法通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化解,反而加剧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指出,任何利益都是现实的,都与人所生存的现实密切相关,同时强调利益问题并非青年黑格尔派“预指”的理性关系问题,而是无法超脱现实关系,即无法脱离“非人的、外在的物质”关系,换言之,利益问题直接指向与人相关的物质,指向人的私有财产。在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财产成了人的最高本质”[4],而要真正理解物质利益的本质,必须走向私有财产本质,即走向现实中的经济关系。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历程来看,马克思越是想解决物质利益引发的困惑,越是发觉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不足,也就越是激发了他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这一阶段,马克思深感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意识到物质利益对于社会关系的决定性意义,从而动摇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崇拜和信仰。与此同时,“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5]也就是说,物质利益问题一方面使马克思思想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他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正如恩格斯所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6]
基于《莱茵报》工作期间所遭遇的大量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出于对当局的愤怒和失望,马克思退出了《莱茵报》,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为了解决“物质利益难题”引发的“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3]591。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物质利益塑造的社会客观性关系,所以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法学著作,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等理论著作,逐渐深入社会实际,展开了对现实问题的批判。马克思对现实问题批判的逻辑表达体现了他从德国制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进路。显然,这一批判逻辑源于马克思对“时代错乱”的德国现实制度的理性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政治和法的批判不能单纯围绕德国的现实状况进行,因为从宗教批判走向现实批判、从神学批判走向政治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摈弃作为国家哲学的法哲学,如果仅仅从批判德国的现实入手,那么必定引发新的“时代错乱”。依循这样的思路,马克思把批判的矛盾直接指向黑格尔法哲学,并把黑格尔颠倒的体系重新置于历史的被告席和审判台上加以拷问,最终得出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制度代表了“时代错乱”,要使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成为可能,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也必须向这种制度所生成的官方哲学开火。
事实上,马克思并非在遇到“物质利益难题”之后直接转向了经济学研究,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在方法论上更加成熟以后才开始了对资本逻辑的系统解析。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清算,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国家体系的破绽,强调国家的理性是抽象性逻辑,人们意识到的仅是国家概念的制度,而非国家制度的概念。黑格尔把国家置于市民社会之上,制造二者的对立,使得国家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对立起来,由此把市民社会作为私人等级。马克思解开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谜团,明确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重要根基,并以此推断出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和法的重要论断。此后,马克思在回忆自己这一迂回之路时指出,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自己得出了重要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9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就是对自己曾经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的解答。
当然,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解答也是基于对市民社会这一“物质生活关系”的探究而最终出场的。对此,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7]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充分体现了犹太人的问题既是宗教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必须走向现实,深入到与犹太人紧密相关的物质生活的基本关系中。因此,马克思提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崭新路径——走向“人类社会”的历史之路。所以说,马克思思想转变始于物质利益难题。带着这个疑难之问,马克思开始了探秘历史唯物主义的艰难之旅。与此同时,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二、《巴黎手稿》对资本逻辑的初步剖析
为了探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马克思博览群书,在流亡巴黎期间撰写了一些手稿,后人将这些手稿进行整理出版,取名为《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打开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大门,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第一次相遇。马克思在《手稿》里面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引申出异化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地说,马克思试图用“异化”这一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他发现这种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摧残着人自身,这是一种“异化劳动”,即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对着工人自己。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冰冷的,人人都是遵循资本逻辑附着在资本生产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人与劳动产品上,更体现在劳动本身与工人、人和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在《手稿》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范畴,他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变化和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资本拥有劳动及其产品的所有权,资本家正是这种权利的所有者。正是通过这一过程,马克思的研究逐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并从生产、分工等角度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
资本逻辑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运作。对资本逻辑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更应上升到哲学层面。马克思的《手稿》正是基于经济学和哲学对资本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对资本逻辑展开了初步的批判。资本带来了人和物的关系的颠倒,将人视为手段而不再是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利润,一切都是为了生产,资本运作的内在过程就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具体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程。资本家是资本逻辑的“主动轮”,资本逻辑所要实现的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家利用手中资本的权力强迫工人劳动实现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是为了生计的劳动,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劳动,是“被迫”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生产商品、资本家和工人,并不断地生产这种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也体现在对货币的批判中。在赫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货币进行了批判,他将“货币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达,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交往异化和货币批判”[8]62。货币正如同一条纽带,把人同其他人、同自然界、同社会连接起来,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它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在需要和对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牵起了一条红线。货币看上去是万能的,它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是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金子的生动描述。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这些诗句,认为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形容的非常出色,货币的力量有多大,人的力量就有多大,“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9]245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货币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颠倒力。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其颠倒性的批判中,“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9]247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逻辑的初步剖析体现在他对资本的批判中。在他看来,资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资本家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另一方面,资本的支配权也在支配着资本家本身。因此,资本对劳动具有绝对的统治权,资本家运用这种支配权来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的积累能够扩大分工,反过来分工又能够增加资本的积累。当资本不断增加、不断积累,并分散在众人之中时,竞争便会逐渐浮出水面,而竞争的“出场”又会加速资本的聚集。据此来说,资本积累是资本本身内在的一种取向,资本通过竞争可以自由地选择资本的人格化代表、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资本通往的这条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这也是资本本身的增殖逻辑。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家为了资本、为了盈利无所不用其极,资本追求的永远都是利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眼中,整个世界都被经济规律所支配,人人都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环:人的生命是资本,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是人,国家就是负责生产的大工厂,在这个大环境下,生产和产品是至上的,工人的地位微乎其微。工人和资本家各有各的烦恼,工人的烦恼是生存问题,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烦恼是赢利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论工资提高与否,他们的结局始终都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9]121。由此可见,资本积累在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在危害着工人,资本的增殖是以工人的血汗和生命为代价的。一般来看,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工人的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实际却不然,因为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才能换取高额的工资。资本的积累带来工业数量的增多,工业数量的增多会带来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这就进一步带来了工人的增加,工人的增加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会导致生产过剩,最终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二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低的限度。因此,即使是处在财富不断增长、对工人而言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下,工人的结局依然十分悲惨,因为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要有资本的存在、只要受资本逻辑的控制,工人始终都是被奴役、被压迫的对象,谁也无法改变工人的命运与结局,工人始终贫困。即便社会达到最富裕的状态,大多数人也都会遭受痛苦。在国民经济学中,工人只是劳动的一种手段、工具甚至是劳动的动物,劳动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工人只是得到了自己劳动产品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了他只是作为工人(而不是作为人)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部分,得到了为繁衍工人(而不是繁衍人)所必须的部分。工人的境遇是悲惨的,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虽然劳动可以购买一切东西,但拥有劳动力的工人却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他们不仅无法购买一切东西,甚至还要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家阐发的观点得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9]123马克思看到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劳动目的的危害性,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从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来看,分工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在贫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工人越来越沦为劳动的机器。这样一来,工人与工人之间就会陷入激烈的竞争,为了让资本家看到自己的价值,工人使出浑身解数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无形之中也加入了生产过剩的大军,物极必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生产的衰落。因此,受到伤害的总是工人,“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9]124更进一步说,工人“生产”并造就了自己的贫困和毁灭,即使整个社会处于富裕的状态,工人依旧在不断地走向贫困。
三、《资本论》及系列手稿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解构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有言:“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0]8这里的抽象力就是辩证法,就是哲学思维,就是逻辑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坚持了“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这是运用“抽象力”分析问题的最典型体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11],实现了“三者一致”。对于辩证法,马克思也有深刻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22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充分说明了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和本质内涵,强调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把辩证法融入《资本论》,所以说《资本论》不是纯粹的经济著作,而是贯穿哲学思维的经济学哲学著作,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意义。同时,马克思强调,《资本论》研究的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抽象的共同体,这个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反映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马克思把“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0]10,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演进过程,它如同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十分独特的,这种方法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资本逻辑的研究立足于多重视角,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具体来说,马克思首先从商品—货币—资本的过程入手,层层展开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我们知道,作为《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面包含了货币、价值、资本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旨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和揭示资本逻辑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路体现在从货币—资本、交换—生产的转变,他在写作货币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逻辑学,“如果没有黑格尔的逻辑学,那么马克思便无法揭示货币的抽象化机制;同样,如果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无法破除货币的抽象化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8]49生产与交换是经济领域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人们生产出不同的商品用以交换来满足自己的不同需求,但当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货币的产生使商品交换更加方便,更加容易量化。对于商品的流通与交换而言,货币原本只是一种媒介、一种桥梁,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产生,货币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财富和资本的象征,被人们所追逐,于是人们生产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交换,更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货币、积累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财富和资本象征的货币就变成了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了。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际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12]货币的地位逐渐由媒介趋向于统治,而这背后隐藏的推手便是资本。确切地说,是受到了资本逻辑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与交换发生了颠倒,这种颠倒会造成生产与交换的对立并带来生产对交换的过度依赖。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们通过劳动和交换使货币具有了社会联系,人人通过货币与其他人保持着联系。从抽象的角度来看,维持这种联系的是某种不依赖于个人,不被个人操控,同时又操控人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受到资本逻辑的宰治。受制于资本逻辑,人与人的交往依赖于物,这种物的依赖性遮蔽了劳动中生产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将货币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达,他在“货币”这一章节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并在“资本”这一章节中对货币有了更加深刻的剖析。仅仅把货币作为货币去理解货币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两个概念。如果说对货币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交换关系的批判,那么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则是对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关系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与货币逻辑不同,只有在运用“使用价值”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资本逻辑。如果仅从简单层面来理解货币关系,那么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对立都无法看见,更无法对资本逻辑的本质进行批判。正是在深入理解、分析、透视货币与资本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要理解资本逻辑的属性就必须立足于资本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资本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出现一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以资本逻辑批判为视角对这种颠倒性做出了论证,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逻辑提供了科学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