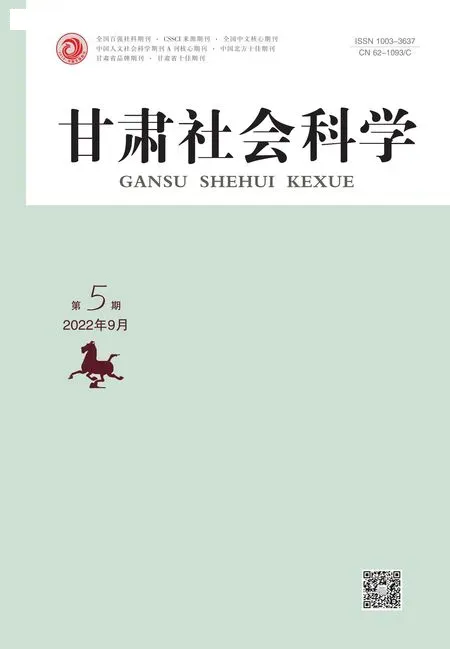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论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
苏 泉
(云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昆明 650500)
提要: 审美意象的共生与采借是不同民族进行艺术交流的重要途径,从民族志的角度看,借鉴兄弟民族的造型样式以延展本民族审美意象是实现民族美术发展的规律之一,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中“鹏”“狮”“署”图像的造型风格可生动诠释此类跨族际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这一历程发轫于东巴文化的原生土壤,是东巴图画象形文造型理念的延伸,并通过纳西族先民对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整合逐渐形成一种兼具古朴美感和表现性的意象造型风格,其中藏族民间绘画在造型、线条、设色、布局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显著。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历程既是东巴文化兼收并蓄艺术创造精神的呈现,也是藏彝走廊中多民族文化在美术领域交融共生的缩影。
一、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同类审美意象的相似造型
不同民族间审美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是实现民族艺术理念与表现风格更新衍变的重要途径。从载体形式说,跨族际的审美意象交融共生既可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抽象的表达,也可通过绘画加以具象呈现。从民族志的角度分析,绘画可作为民族生活历史记忆以及个体生命世界观审美叙事的表达路径,在表征不同民族某些相似审美经验的同时,还传递着彼此对于真、善、美等道德观念多元一体的认知标准。就此而言,不同民族的绘画艺术必定存在着某些可互为通约的审美意象,而这些意象又在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中成为彼此文化整合的表征。
造型表现是美术的重要功能,纳西族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同类造型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也体现在这一领域。故此,运用图像比较研究法,以纳西族东巴神话中颇具代表性的“鹏”“狮”“署”图像造型为例,试图说明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既一以贯之地延续了图画象形文字的传统,也兼容并蓄地吸收了以藏族民间绘画为代表的兄弟民族美术的元素,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意象造型风格。
东巴画的造型表现风格从形成到完备经过了漫长的衍进历程。“结合纳西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约在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纳西族社会中的原始巫教,因深受吐蕃本教的影响而形成东巴教,社会中已分化出专业的巫师东巴(类似汉族的‘史官’),由他们采集整理流传在民间的图画字,用以简单记事、通信、写卜书和经书,逐渐约定俗成而流行发展。”[1]就表现形式而言,图画象形文很可能就是东巴画最早的形态,其稚拙古朴的审美意象贯穿于东巴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并在与其他兄弟民族民间美术的交融共生中形成多样的造型风格。有研究指出:“东巴画以艺术语言反映了东巴文化所蕴含的宗教观、价值观。”[2]东巴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包括东巴文化中的神话、祖先、图腾,表现媒介包括木牌、纸本和布卷等多种类型,其造型样式十分丰富。然而,结合笔者的资料梳理及田野调研,至今在滇西北的丽江、香格里拉和川西南木里等纳西族、藏族杂居地区,两族民间绘画中依然存在着以“鹏”“狮”“署”为代表的同类神话图像交融共生的现象,且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基本肯定了这些图像在神话文本方面有相近的渊源并在造型方面有较高的相似度。以此为切入点,有利于说明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历程中多民族审美意象交融共生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藏族民间绘画是东巴画造型风格借鉴的一个主要来源,“藏族民间美术是土生土长的雪域藏族美术形态,它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以藏民族原始文化为主体,它自始至终同本土原始宗教文化、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具有悠久的历史性、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别于宫廷美术、贵族美术和寺院美术”[3]。藏族民间绘画就表现媒介而言大致包括岩画、壁画和唐卡这三种形式,兼有与东巴画相似的木牌、纸本和布卷等多种类型,神话造型同样种类繁多,然而由于具有成熟的绘画形式,各类造型的表现风格也相对统一。
东巴画中“鹏”“狮”“署”三类图像对应的审美意象是神鹏“休曲”“杜盘西庚”(白海螺狮子)和狮首“优玛”战神以及“署”,在藏族民间绘画中与此相对应的审美意象是“琼鸟”“威武伴神雪山白狮”[4]和“威尔玛”以及“卢”或“龙”,这些意象可作为案例加以对比探讨。
其一,对“鹏”图像审美意象相似性的比较。纳西族东巴画的神鹏“休曲”和藏族民间绘画的“琼鸟”在神话文本和造型样式方面有许多相似处。神话叙事方面,“休曲是东巴神话中的神鸟,属战神、保护神之列。休曲是藏语借词,意为‘雄鸡’,纳西语本身的称呼是‘斯普沃安盘’,意思也是雄鸡。在东巴经译本中,一般译为‘休曲’,或‘大鹏’、‘神鹏’、‘大鹏神鸟’”[5]354。另外,美国学者洛克曾把纳西族东巴经神话中的这一神鸟等同于印度神话中的迦卢荼(金翅鸟)Garuda①。“显然,东巴教和达巴教中的这个神鸟与本教里的金翅大鹏鸟是同源的文本。”[6]589藏族民间绘画中的“金翅大鹏鸟”确切应称为“琼”(或译为“穹”),从藏学研究领域的成果看,“琼鸟”图像意义非凡。研究表明,“另一个在青藏高原的岩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是琼鸟,仅次于牦牛,有些学者将此作为藏族先民崇拜的鸟或者神鸟,甚至将此作为藏族先民具有鸟图腾的证据,进而将其直接称为‘鸟图腾’岩画。在藏族古代文化中,各种各样的鸟出现在岩画、经文、故事中,唯有琼鸟的崇拜具有鸟图腾的几乎全部条件,可以称其为鸟图腾”[7]349。与“休曲”相同,藏学领域的研究表明“琼鸟”图像的起源与古印度的“Garuda”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印度,这个Garuda最早出现在婆罗门教的几个支派中,最后被佛教吸收,虽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同一神鸟出现在婆罗门教、佛教、苯教三个宗教传统中,说明了喜马拉雅山区这三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似乎有着共同起源的跨文化的神鸟在喜马拉雅各文化传统中均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7]357这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共源性现象,决定了无论是东巴画中的“休曲”,还是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琼鸟”,其审美意象之间存在着交融共生关系。
从造型样式方面看,东巴画中的“休曲”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琼鸟”图都存在“禽类”与“人形”两种类型。“禽类”造型中,东巴画的“休曲”多出现在东巴经书及木牌画中,其总体呈栖息状或飞翔状,头顶宝石,旁生双角,头两侧有耳,眼目圆睁,张口啼鸣,十分生动。类似造型的“琼鸟”在西藏的岩画中也较常见,呈现猛禽振翅欲飞的搏击形态。“人形”造型的“休曲”则同样多见,“不仅在《东巴舞谱》中专门记载有‘白海螺大鹏神鸟舞’,以再现他征服署神的场面,而且在《神路图》、《什罗画》等当中描绘有他高踞含依巴达神树之上擒拿署神之形象:双翅劲展,双目怒睁,铁喙叼署身,二爪攫署神之头与尾。与尤玛神相似,休曲之头亦为兽头,长有两角,其间画有如意珠宝。有时,额上绘一天目,以示耳聪目明”[5]356。在藏族民间绘画中,“人形”造型的“琼鸟”多见于唐卡及壁画中,“它的形象为长牛角的鸟首人身,鹰爪狮腿,马耳鹰翅,鸟眼猪鼻鸟喙,具备了各种凶禽猛兽的特征和威力”[8]。两相对比,便可以发现造型上存在的显著相似性。
其二,对“狮”图像审美意象相似性的比较。与“鹏”图像一样,纳西族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狮”也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渊源,在绘画中都具有“狮子”与“人狮”两类造型,在东巴经书及木牌、纸牌、卷轴画中较常见。“狮子”造型在东巴画中主要体现为“杜盘西庚”,是东巴神话中具有守护神职能的神兽,其造型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威武伴神雪山白狮”有相似之处。此外更具特点的就是“优玛”的奇特造型,“优玛是东巴神话中的战神、保护神。作为至尊神的辅佐,其主要作用是遵从至尊神之旨意,除鬼驱魔,匡扶正义。优玛又译作优麻”[5]316,在东巴图画象形文中其通常表现为狮首鹰身的奇异形象,而东巴卷轴画中则是“人狮”造型。
从“狮子”造型的表现风格看,“杜盘西庚”与“威武伴神雪山白狮”在绘画中都具有色如绿松石的鬃毛、健壮饱满的身形和洁白的毛色,可谓共生于两族民间绘画中的狮子图像,“人狮”造型图像则主要体现在“优玛”战神狮首人身、背生双翼的造型表现中。纳西学领域的研究对此已有较多论述,“据洛克考证,东巴教中的‘优麻’神也称为‘瓦麻’(Wua-ma),与藏族本教中的‘畏尔玛’(Wer-ma)神相同,相传Wer-ma神也有三百六十个,他们与东巴教中优麻神与端格神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样,也与Thugs-dkar有密切关系”[6]296,“无疑,纳西族的优玛信仰是藏族本教战神信仰的结果”[5]322。藏学领域研究也有类似的观点,“本教文献中描述的这种早期的威尔玛形象,在藏传佛教及本教的神灵造像中比较罕见,但在纳西族崇拜的wer ma神造像中体现的较为明显,本教文献提到的‘狮头猞猁耳’、‘忿怒面大象鼻’、‘水獭嘴巴虎獠牙’、‘水剑翅’竟都有完全的体现,尤其是神灵右手持的箭,下身围的虎皮围裙,更体现了wer ma的特征”[4]。藏族民间绘画中的“威尔玛”形象已不多见,但通过共源性的神话文本描述,可以推测东巴画中的“优麻”与藏族民间的“威尔玛”在审美意象方面也存在交融共生的关联。
其三,对“署”图像审美意象相似性的比较。“署是东巴神话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与至尊神等居住于十八层天界、鬼魔居住于地下界、人类居住于社会空间相对应,署所主宰的是大自然。”[5]342“不仅在形象上,而且在名称、种类、居所、等级制等方面与署相似的是藏族本教中的‘卢’(klu)。卢亦是一种人身蛇尾的神灵,据说与古老的蛇崇拜密切相关。”[5]348-349
从造型表现方面看,纳西族东巴画中“署”主要表现为人身蛇尾,或马头蛇尾、虎头蛇尾和牛头蛇尾等多样化造型。东巴画中“署美纳布”(署王之妻)形象为人身蛇尾的女子形象,二手抬至胸前,似合十状,以宝石、火焰、双蛇为头饰,身着披肩与飘带,这一造型就十分接近藏族民间绘画中的“龙”。“在唐卡中,通常龙的上半身为人形,下半身为缠绕的龙身,多半是白色身的,一头两手,双手呈合十祈求状,或供奉着珠宝,一条、三条或七条小蛇立在龙的头顶。”[9]“署”与“龙”的形象在两族民间绘画中也出现了交融共生。
综上所述,东巴画以“鹏”“狮”“署”为代表的造型与藏族民间绘画类似图像造型的相似是证明纳藏两族民间绘画存在跨族际交融共生审美意象的有力依据,也是两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例证。
二、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同类审美意象造型风格分析
通过介绍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相似的造型样式,不难发现两类绘画同类审美意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进一步就需要关注二者在表现风格中用线、设色和布局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从而体现东巴画造型风格衍进历程的特点。
“如果透过整个文化现象来观察我国民间美术,就不难发现民间美术与原始艺术在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上的相通之处。那些远古的原始经验、原始幻想越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已经悄然沉积在民间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10]由此观之,古拙质朴是我国民族民间绘画普遍存在的一种共性审美特征。一方面,尽管原始艺术思维是大多数东巴画绘制者创制古朴画风的重要灵感来源,然而图画与象形文“书画同源”的耦合特性才是东巴画形成此类风格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东巴画通过对以藏族民间绘画为代表的兄弟民族审美意象的交流整合所形成的意象造型风格是这一衍进历程的重要标志。
第一,以东巴画中的“鹏”图像为例。(1)造型方面,“禽类”造型体现在东巴图画象形文的字符中,主要以单线勾勒,总体呈现禽鸟形状。高耸的双角,头顶的硕大宝石,两耳突出,眼目圆睁,精神饱满,喙长而坚硬,正在张口啼鸣,为了凸显其威猛异常,有时甚至画出两对翅膀,并刻意夸大趾爪这些生动的细节。西藏岩画中“琼鸟”的“禽类”造型与之相类似,然而身形以色块涂抹。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二者的关联,然而由于两类图像存在的相同或近似的神话文本,可以推测,东巴画“鹏”图像的“禽类”审美意象可能就脱胎于与西藏岩画中“琼鸟”图像相类似的原始艺术,在后续衍进历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更多细节描绘的图画象形文符号。“人形”造型方面,两类图像交融共生现象更为明显。如上所述,东巴画“休曲”的造型样式明显相似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琼鸟”图像,然而风格不似后者的精致而工整,“休曲”头部与身体往往随意夸大,为了凸显其神力,上肢也被画的格外粗壮,双手攥拳紧握住盘绕于神树上的“署”,翅膀、尾羽及鬃毛也较少细部描绘,整体呈现一种稚拙生动的美感。“琼鸟”的“人形”造型虽同样呈现出头身的夸大,然而整体比例匀称,双手握住口衔之“龙”,动态相对和缓,对于鬃毛的飘动和双翅的舒展均有精到的刻画,呈现一种工致而灵动的美感。从造型风格而言,东巴画的“休曲”明显不同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琼鸟”,似乎更具有表现性。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东巴画中,“休曲”图像也会注入更多创作者的认识与想象。(2)用线方面,两类绘画线条形态也较为相近,且多以铁线或游丝描形式呈现,是画面中主要的造型手段。不同之处在于东巴画中的“休曲”因多用竹笔或硬毫毛笔绘制,所以线条流畅,变化明显,富于力量感,形象因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而藏族民间壁画及唐卡中,“琼鸟”多以精制的硬毫毛笔绘制,由于此类毛笔分类精细,所绘线条也更为工整优美,颇具装饰性,形象因而显得庄严肃穆。(3)设色方面,二者差异明显。东巴画多是平涂颜色,少有渲染,强调线条表现力。而藏族绘画在均匀平涂的基础上,运用渲染的技法,以色彩凸显立体感。(4)布局方面,两类图像也存在颇多相似处,东巴画中“休曲”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琼鸟”都可以立于主体形象的背光顶端,而东巴画中“休曲”有时也作为画面主体出现在中心位置,这大概与其在东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关。
第二,以东巴画中的“狮”图像为例。(1)造型方面,东巴画中“人狮”造型的战神“优玛”形象可能与藏族民间神话中“威尔玛”形象类似,这个造型在东巴经书及绘画中均有所体现。由于“威尔玛”形象可能已不多见于今天的藏族民间绘画,所以在探讨此类造型时,选择形态相近的“狮面空行母”作为替代比较的案例。与“休曲”的造型风格相同,“巴乌优玛”及其坐骑,躯干缩小,头手均被有意夸大,整体显得敦实,动态明显又充满力量感。“狮面空行母”总体比例匀称,结构相对准确,整体动态夸张,却轻盈柔和。(2)用线方面,两类绘画都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完成,却同样存在线条美感的差异。“巴乌优玛”以流畅有力的铁线为主,少有刻画。“狮面空行母”则以工整的游丝描表现,细节精致。(3)设色方面,前者多为平涂,单纯厚重,后者运用渲染,凸显装饰美感。总体表现方法相近,审美效果却大易其趣。(4)布局方面,“巴乌优玛”与“狮面空行母”图像都可以作为主体布置在画面中心,或作为配角出现在其他作品的四边,也体现出两类绘画在表现风格方面交融共生的关联性。
第三,以东巴画中的“署”图像为例。(1)造型方面,东巴画中“署”的造型样式与藏族民间绘画中的“龙”非常相似,存在交融共生关系。同为人身蛇尾的女性形象,而造型风格却差异明显。东巴画中的“署”,往往无严谨的比例结构,造型上同样夸张头手,躯体结实,下半身蛇尾粗壮,缠绕变化较多,富有力量感。藏族民间绘画中的“龙”,结构相对严谨,上半身多描绘为写实的女子形态,注重细节刻画,蛇尾的盘曲变化相对简单而流畅,呈现出一种优雅美感。(2)用线方面,二者也运用了勾线填色的技法。东巴画中的“署”以单线勾勒身形,线条相对生涩而粗犷。(3)设色方面,以平涂颜色为主,效果与前述案例相同。藏族民间绘画中的“龙”,以均匀而有力的游丝描为主,所呈现的工整细腻美感,渲染设色的风格也与前述几类相同。(4)布局方面,东巴画中的“署”有时与藏族神话中的“龙”一样,居于画面一隅作为衬托,有时又稍有不同,常作为画面主体出现在中心位置,体现了这一形象在东巴文化中的重要性。
根据对比可以发现,同一类造型,在藏族民间绘画中具有理性装饰美感,在东巴画中呈现为古朴稚拙美感。东巴画三类审美意象的造型特征显然保持着与东巴图画象形文造型风格的一致性,因此不同于其他民族同类审美意象。即便从摹仿论的角度出发,也应承认感性认识在调和与统一自然界杂多表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8世纪的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认为:“因此,艺术须摹仿自然,即表现自然呈现于感性认识的那种完善。这种完善当然带有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但是对于美学来说,这种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不是由理性认识分析出来的,而是由感性认识把它作为感性形象来感觉出来的。”[11]325尽管东巴画的造型理念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摹仿论范畴,然而前述分析却恰好证明,正是由于在采借其他民族造型样式的同时原生造型风格中注重感性认识的审美理念作用,才促使这些外来造型样式在东巴画中衍生出明显区别于原本造型风格的古拙审美意象。
如果要进一步探寻这种造型风格在现当代的美学价值,那么将其概括为一种具原始主义(原生态)倾向的审美意象当不为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就认为艺术形式应摹仿自然,而文艺正需要从自然中汲取原始的蛮野气息,“他认为这种气息才有诗意,因为第一,这里面才有巨大的活力和情感;其次,在原始情况之下,人也才可以毫无拘束地表现这种活力和情感;他的思维方式才是形象的而不是抽象的,语言也是如此”[11]297。显然,他倡导的纯粹审美趣味的回归是对东巴画稚拙古朴审美意象的一种诠释。如前所述,这得益于东巴画与东巴图画象形文造型理念的耦合。
关于东巴图画象形文的审美特点,著名艺术史家李霖灿先生早有说明:“麽些象形文字的经典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字——美!一种满纸鸟兽虫鱼洪荒太古之美。”[12]这种“洪荒太古”的美感,主要是来自东巴图画象形文的稚拙而感性的造型方式、遒劲流畅的线条美感和随性涂抹的各类鲜明色彩。创作者虽然没有接受专门的艺术训练,然而却能从自然中真诚地观察,进而提炼物象并表现其特征,不得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品质。前述分析的东巴画案例,似乎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东巴图画象形文这类“应物象形”的审美意蕴。
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大致有三方面特征:其一,衍进的起点是建立在图画象形文造型、用线乃至设色方面对古代原生审美传统的延续与回归。“古代的美感偏重于素朴的和谐的自由感,它是平静、轻松、单纯的愉悦。”[13]这些特质在东巴画“书画同源”的造型理念中得到了体现,并在后续与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所衍生的木牌画、经书和卷轴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中一以贯之。其二,衍进的过程主要是以神话文本的同源为前提,通过对以藏族民间绘画为代表的其他兄弟民族绘画造型样式与审美意象的整合采借,实现了表现风格的多样化。衍进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同类造型样式表现风格的延异,另一方面使得东巴画原有的单一造型风格形成多元一体的审美认同。其三,衍进的意义体现在东巴画造型理念的升华。东巴图画象形文诉诸感性的直观造型,彰显出一种夸张、强烈、率朴的力量之美,已具有意象造型的特征,在与外来美术造型样式的交融共生过程中其表现的形式与内容均得到扩展,形成了多种不依赖文字叙事而能独立观赏的形式,创作者的主观之“意”与事物的客观之“象”以纯粹绘画的形式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融合,使得美学价值在原有传统基础上得到提升。
纵观东巴画造型风格的整个衍进历程,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完善,其审美意蕴的主旨却始终古朴,这与东巴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密切相关。“文化传统不仅给艺术家提供了体现其创造力的载体,也决定了所能采取的形式,除非艺术家置身于传统当中,否则他就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表达自己。”[14]东巴画造型古朴审美意象的形成以东巴文化的理念为依托,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美学理念相呼应,有学者指出“在中西的比较中,中国之美的主型,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相对于印度之神的)人之(相对于西的悲和喜而来的)美”[15],可见中国的美学具有一种超脱世俗并兼顾现实的美学思维,在传统东巴画的造型风格中就体现为大多数不具备专业素养的创作者凭借感性认知与情感触动,通过朴素而简练的线条对自然物象的大胆表现与塑造,并且善于对外来绘画形式加以采借,扩充了表现技法,丰富了审美体验,使造型风格得以不断拓展。
三、东巴画造型风格在多元审美意象交融共生中衍进
就审美意象的构建层面而言,东巴画多样的观看与创作方式历时性地体现了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同时也是多元文化共时性交融共生的再创造,是对东巴图画象形文造型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东巴画的艺术风格、审美取向受到东巴文化的整体观照。”[2]造型风格与文化传统的一致性是认识这一历程的重要线索,实际上,诚如上文所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巴画多元一体造型风格的形成得益于纳西族及其先民立足原生造型传统,对藏族、汉族、白族、普米族等兄弟民族及其先民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这一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东巴画形成跨族际共生的审美意象。
纳西族先民为更好地传承东巴文化,以兼收并蓄的创新方式,积极采借外来的文化因素以充分适应本民族社会发展需求,遂形成多元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鹏”“狮”“署”图像就是其典型案例。因此,本文从时间、地缘、历史三方面因素着手,以东巴画与藏族民间绘画的交流线索为例,探讨东巴画造型风格在多元审美意象交融共生中的衍进历程。
其一,从时间因素而言,结合前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东巴画中部分神话造型受到藏族民间绘画影响,是一种文化整合的产物,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结合笔者的梳理归纳,公元前7世纪至8世纪,图画象形文的雏形及木牌画出现,进入东巴美术的初创期;公元8至13世纪,图画象形文及纸本美术的形成,并完善了东巴经书的形制,东巴美术由此进入发展阶段;公元12至17世纪,汉、藏文化在纳西族生活的地区交融碰撞,使东巴美术形成多样风格,体系趋于完善[16]。上述时间划分虽未必精确,然而重在阐述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是基于原生文化对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其二,就地缘因素而言,与西藏高原接壤的滇西北地区,具备藏族民间美术与东巴美术交流互动的天然优势,有许多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孔道延续至今。东巴文化研究学者戈阿干先生曾介绍:“1986年夏天,笔者沿着滇川藏‘茶马古道’西行,有机会在西藏亚东一带中印、中尼、中布交界地考察,发现在那儿的大山深林里,仍有很多如江南水乡似的沿江走道。事实上,不仅藏族人,也包括纳西人的经商者和朝佛者,自古就在这里自由进出了。”[17]山高谷深、河网密布的地缘环境,客观上促使纳西族和藏族先民依赖马帮商贸完成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这一过程中,藏族民间绘画的样式与技法极有可能就此传入金沙流域纳藏两族先民的生活区域,然而作为外来的民族美术,短期的文化交融不可能获得东巴画创作者们长久的审美认同,只有茶马古道上两族先民的长期交流合作,才可能实现东巴画对其他兄弟民族美术审美意象的吸纳整合。
其三,就历史因素而言,纳西族社会对以藏族为代表的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整合由来已久。“公元7世纪初,藏王(赞普)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势力扩展到滇西北地区,并于公元678年进入洱海北部地区。两年后又在今丽江县塔城与中甸县五境之间建造铁桥,置神川都督,又称吐蕃铁桥节度,‘收乌蛮于治下,白蛮贡赋’。”[18]公元783年(建中四年),唐与吐蕃划界,大渡河以南“磨些诸蛮”属吐蕃[19]。“唐代吐蕃本教流入纳西族地区的另一途径是公元8世纪吐蕃上层统治集团的‘扬佛灭本’。”[6]561由此可以认识到,至迟在公元7世纪末期,伴随吐蕃文化在滇西北以及洱海周边的影响,可能导致其民间美术与当地纳西先民的原生美术交流融合,这应是东巴画对于藏族先民绘画风格采借的开端,是未来两类民间绘画同类造型风格审美意象交融共生的前提。
另有研究表明,公元13世纪末以后,藏族先民的民间绘画对东巴画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直接,“元明以后,汉地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相继传入纳西族地区,纳西族绘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与汉、藏绘画艺术相结合,特别是唐卡对东巴画的影响最大,这个特点在纳西族卷轴画中大量出现”[20]。大致在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纳西族先民的统治阶层率先推动了藏族先民民间绘画技法及造型样式在纳西族先民生活区域的传播与影响,然而是否已普及民间并为东巴画创作者所认同尚难确定。
这些绘画与东巴画的广泛交融,则应是公元18世纪之后滇西北地区与西藏高原密切商贸交流的必然结果。有研究表明,“清朝将西藏也纳入势力范围,使得出入西藏高原的贸易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土司的统治以雍正时期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而宣告结束。但是丽江作为兴盛起来的贸易要塞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沿着贸易之路云南西北部藏族生活的地区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21]。清代丽江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势必进一步促进东巴画与其他兄弟民族民间绘画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并使之进入纳西族先民的日常生活,内地与边疆兴衰与共的历史规律对东巴画造型风格的衍进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 语
东巴美术的衍进史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深度,片面诠释其中某一类表现形式的稚拙造型风格会让其美学意义显得苍白而空泛。仅以东巴画为例,其造型就具有与东巴图画象形文“书画同源”的传统以及兼收其他兄弟民族绘画优长的风格特征,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由“应物象形”的单一文字符号,逐步衍进而成造型风格多样的审美意象。衍进的历程,除却对兄弟民族绘画风格的吸收,更重要的是保存并升华了本民族原生绘画中审美意象的美学意蕴。
东巴绘画与藏族先民民间绘画的交融可能早在公元7世纪以来便已逐渐开展,然而,从造型风格对比分析,同类审美意象的交融共生乃至衍进可能是孕育自元明清三代以降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之中。18世纪以后东巴画与藏族先民民间绘画的美术元素已逐步交融共生,是藏彝走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据。“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东巴画造型的衍进历程中,是推动东巴美术衍进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
东巴画来源于民间,它通过原生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象,其传承与发展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结果。当代美术工作者的重任,就是继续秉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宗旨,不断批判地继承与探索其中的美学意蕴,提炼其中的艺术元素,在现当代美术领域创作出更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美术作品,让观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其中的美学价值,感悟东巴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
注 释:
①关于洛克将“休曲”(或译“修曲”)等同于迦卢荼的观点,参见洛克:《论纳西人的“那伽”崇拜仪式——兼谈纳西宗教的历史背景和文字》,载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其注释①指出:“迦卢荼(金翅鸟)Garuda:印度神话中毗湿奴大神所骑之鸟。洛克把纳西族东巴经神话中的神鸟‘修曲’等同于此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