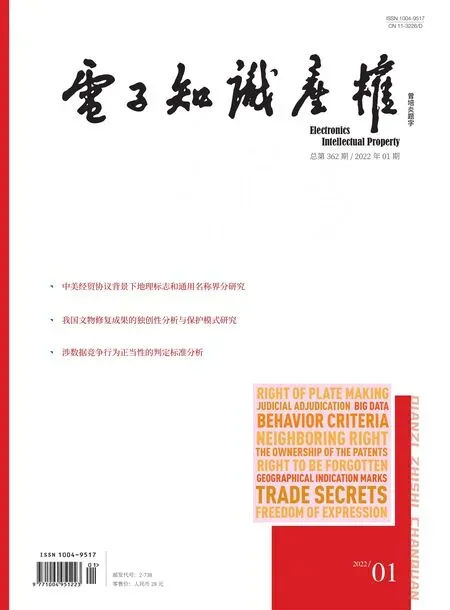必要性与可行性:“被遗忘权”制度的引入之辩
文 / 衲钦
一、引言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基于其强大的云存储能力,颠覆了人类社会固有的“遗忘是常态,记忆是例外”之精神规律,人们在不断产生新数据的同时,也被过去的“自己”所裹挟。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担忧,“被遗忘权”1. 在我国的理论界及实务界,“被遗忘权”在字面上虽有“权”的外观,但事实上并非我国一项独立法定权利。因此,文中在提及欧盟的“被遗忘权”时,即指该法定权利,而涉及我国的“被遗忘权”时,则意指“被遗忘权”所指代的一种利益。这一思想在欧盟被提出,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开始纷纷效仿或展开热烈研究。笔者综合分析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对于“被遗忘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研究“被遗忘权”之权利定位。即,“被遗忘权”属于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被遗忘权”应当纳入到我国的《民法典》中,还是单独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将其纳入其中等。这类研究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及出台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源,但相关争议点也随着该法的颁布而告一段落。二是研究“被遗忘权”权利内容,围绕其权利义务主体范围、适用案件类型、行使方式或程序等内容展开研究。但是,现有文献对于“被遗忘权”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却较少着墨。因此,本文以“被遗忘权”的产生背景及基本特征为出发点,辅之以现有法律制度、社会背景等因素的考量,着重分析“被遗忘权”意欲守护的价值是否拥有足够的分量去要求重构既有权利格局,充分探讨该制度构建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二、“被遗忘权”的形成背景与核心特征
“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对已合法公开在网络上,但不恰当、不相关、超出最初处理目的且继续保留会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要求数据控制者采取删除、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一项权利。”2. 杨立新、韩熙:《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24页。从权利外观来看,该权利是一种关于个人信息传播时间、方式及程度的自主决定权,是法律颠覆信息生命周期发展规律的一种纠偏机制。拟制“遗忘”似乎可以使信息正常新陈代谢,洗刷“数字刺青”,以实现对个人可识别信息的相对隐匿。由此来看,“被遗忘权”的产生具有强烈的时代属性,其权利性质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被遗忘权”的形成背景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因为广播电视具有即时性特征,随着节目播出结束后,一些信息在受众层面也就渐而泯灭,相当于一滴水坠入浩瀚汪洋中难以寻觅。而纸质媒体传播的信息虽然不会在受众层面即时湮灭,但由于纸质媒体之累积性,对其进行保存需要较大物理空间,受众能力有限,很难保存大量的纸质媒介。同时,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发布规模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传统媒体资源相对稀缺,责任方相对明确,可以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和行业自律等途径对不规范的媒体予以惩戒,使得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所以,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变相收集与整理并非易事。
在大数据时代,凭借网络的普及和云端备份、数据抓取等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人的一言一行均可被数字化,而数据一旦被生成,就能低成本、极速、跨地域的传输、复制和存储,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载体的物理局限性和传播内容易被“风化”的问题。人们可随时通过关键词“一键检索”等方式在海量数据中提取信息,其便利程度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但是,这种信息的全网存储以及高提取性,使得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透明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检索相关信息来了解、评价一个人,从而打破人们生活的宁静。尤其是在Web 2.0时代崛起后,每个网络用户都可以成为网络内容的创造者、发布者,这使得网络信息传播涉及主体众多,信息的发布源逐渐从传统的“中心化”跳转到“范中心化”,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产生的源点,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对责任主体之确定和责任范围之划定较传统媒体时代而言更难有效把握。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被遗忘”成为信息社会人群的迫切需求。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盟于《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1995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95/46/EC)中赋予公民在其个人信息不再需要时向相关机构提出“删除”的权利,以保护个人信息。这可以被认为是“被遗忘权”的最初形态。2012年,欧盟公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草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GDPR”),其中确定了“被遗忘权与删除权”条款(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o Erasure),3. COM/2012/011 f inal 2012/0011 (COD).规定信息主体有权向信息控制者主张删除相关个人信息,或阻止这些个人信息进一步传播。该条例最终于2016年4月14日通过,并于2018年5月正式生效,标志着“被遗忘权”已经被视作一种法律权利。2014年5月,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简称“CJEU”)对“谷歌西班牙案”(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v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4. 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 v. Agencia Esñ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alez ,C-131/12,2014.作出最终裁决,支持了原告“被遗忘权”的部分诉求。由于CJEU的这项判决结果将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家,所以也就标志着“被遗忘权”通过CJEU的最高司法权威在欧盟范围内得以重申。在本案中,CJEU认为当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因时过境迁而变得不充分、不相关或超出信息处理目的(Inadequate, irrelevant or no longer relevant,or excessive in the relation to the purpose of the processing)时,信息主体可向搜索引擎服务商提请删除索引相关信息的链接。
(二)“被遗忘权”的核心特征
“谷歌西班牙案”中,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ardia)的网站刊登了冈萨雷斯(Mario Costeja González)因欠债导致房屋被拍卖的公告,且该信息被谷歌搜索引擎编录,遂冈萨雷斯以相关信息与当前生活不相关、不必要、过时为由,向法院起诉了《先锋报》网站和谷歌公司。最终法院同意了原告的部分诉请,让谷歌公司断开相关信息的搜索链接,但却基于新闻自由之原因,并未要求《先锋报》报社删除相应新闻报道。纵观本案,并结合“被遗忘权”的基本概念,可大致归纳出“被遗忘权”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是“被遗忘”指向的对象是“合法流通的网络信息”。5. 梅夏英:《论被遗忘权的法理定位与保护范围之限定》,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16期,第49页。在“谷歌西班牙案”中,原告冈萨雷斯的房产拍卖信息被《先锋报》网站刊登,也正是基于这类信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以公开拍卖方式处理个人房产以偿还欠款,其传播方式并不具有违法性。如果该信息的使用存在侵权情形,信息主体可主张适用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等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而不适用“被遗忘权”的保护方式。
二是相关信息保留可能会导致信息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以数字检索技术蓬勃发展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使得一些在网络上休眠的陈年往事很容易被他人发掘,并经再次整合后用来评判“现在的我”。冈萨雷斯也正是基于对这一隐患的担忧,对多年前合法流通于互联网上的欠债、拍卖房产信息主张“遗忘”,以寻求个人“历史标签”遁隐于公众视线之外。
三是相关信息能够识别到特定个人。这个毋庸置疑,因为“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根本特征,若相关信息不能识别到特定主体,则不属于“个人信息”,只能算作广义上的“数据”或“信息”。另外,不具备“识别性”的信息或数据因无法“针对”到特定个人,因而也就不具备损害特定主体声誉之可能性。
四是“被遗忘权”所针对的是“不必要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个人信息。但具体何为“不必要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个人信息,欧盟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裁判尚且语焉不详。这种过于抽象的表达不但实践起来效率低,且极容易在这样宽松的语境下滋生“滥诉”行为。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的价值其实就是去处理那些“过时的、无用的或者脱语境的(Decontextualized)信息”。6. Mónica Correia,Guilhermina Rêgo&Rui Nunes. Gender Transition: Is There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Health Care Analysis,2021,29(4):291.这样的表述看似比“不必要、不相关的信息”更加明确一些,但是何为“无用的”“过时的”信息依然处于判断盲区,这些因素究竟以什么时间点进行观察以及“无用”是针对什么主体进行判断的?若对于信息主体来说某一信息已经不存在价值,但是这一信息会涉及其他主体的利益,甚至是社会公益时,对这一信息的保留或删除应该如何决断依然是困扰“裁判者”的难题。
五是为保证言论自由及公众知情权,“被遗忘权”行使的主要方式是删除、屏蔽搜索引擎提供的检索相关信息的链接,从而切断在海量数据中访问相关信息的通路,而非向搜索引擎服务商主张删除第三方所发布的原始信息。7. See Jennifer Daskal, Article: Speech Across Borders, 105 VA. L. REV.,2019:1618. 转引自Jessica Friesen. The impossibl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utgers Computer and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21,47(1):189.正如时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的薇薇安·雷丁(Viviane Reding)女士所述,“被遗忘权”并不是对原始信息的完全删除,而是“部分删除”。8. Viviane Reding: The EU Data Protection Reform 2012:Making Europe the Standard Setter for Modern Data Protection Rules in the Digital Age,http://www.doc88.com/p-9969691697299.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0月2日。这一特点在“谷歌西班牙案”中也有体现,CJEU的最终判决只要求搜索引擎服务商采取措施阻止通过“姓名”搜索来获取相应信息,而没有要求禁止通过其他词汇提取相关信息的行为。9.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dgment on “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 v. Agencia Esñ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alez ” C-131/12,2014:2.文中指出,“被遗忘权”只影响基于个人姓名进行搜索所获得的结果,而不要求把所有索引相关信息的链接全部删除。也就是说,使用其他搜索词,或者直接访问发布方的原始来源,仍然可以访问原始信息。因此,欧盟语境下的“被遗忘权”并非允许信息主体要求相关信息的“全部删除”。当然,“彻底删除”所有信息也是不现实的。
三、权利是否具有实施必要性——“被遗忘权”与相关权利对比
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若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已然能够涵摄“被遗忘权”所指利益的情况下,再行探讨移植一项新的制度,不免画蛇添足。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所欲移植的某一项制度与国内现有法律制度所保护的权益是否重合,以便从根本上探讨新制度引进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被遗忘权”与隐私权
隐私权是一种“事后”的消极权利主张,意图将已经被非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从公有领域“拉回”至私人领域。而“被遗忘权”是一种“事前”的积极权利主张,其权利对象是互联网已合法流通的涉及个人的信息,且这些信息往往因为时间久远与信息主体当下的实际情况不再相符,或因为原有语境脱离而产生了原意扭曲,从而导致信息主体的形象可能会被歪曲或误读。因此,“被遗忘权”的本意是对“已合法流通的信息”降低曝光度。
无论信息主体以何种形式将个人信息主动公布在信息网络空间,都会被认为放弃了隐私权。如果这时还用隐私权保护信息主体,反而是无意义的。若他人合法公布相关个人信息,也不应落入隐私权的规制范围,因为他人已履行了“合法”的注意义务。在“谷歌西班牙案”中,原告冈萨雷斯的房产拍卖信息被《先锋报》网站刊登,正是基于该信息的特殊性——以公开拍卖方式处理个人房产以偿还欠款,所以不属于个人隐私信息,且《先锋报》进行网页刊登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不能诉以侵犯隐私权。
(二)“被遗忘权”与名誉权
名誉权与“被遗忘权”的创设虽都以维护权利主体的社会评价为目标,但二者所针对的权利对象在本质属性上存在差别。名誉权所规制的是利用虚假信息损害权利主体社会评价的行为。而“被遗忘权”主要针对的是因时间流逝已无法准确反映出信息主体人格形象的客观、真实信息,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虚假”与“真实”的差别。若报刊、网络等媒体发布信息主体的不实消息,从而贬损信息主体名誉的,可依据《民法典》第1028条对失实内容主张更正、删除。而如果他人将信息主体的不良信用记录以合法的方式、途径披露于众,信息主体则无法通过主张名誉权寻求保护。
(三)“被遗忘权”与姓名权
姓名权侵权通常表现为干涉、盗用、冒用等形式侵犯特定人名的行为。而“被遗忘权”的权利对象为合法流通之个人信息,其具有“合法”外观,不属于姓名权的规制范围。如我国“任甲玉诉百度”案中,原告任甲玉就曾以百度的信息编录及其检索结果侵犯其名誉权、姓名权、被遗忘权为由,请求删除相应原始信息以维护其社会评价。而法院就以相关信息为合法发布的客观信息,不存在盗用或者冒用任甲玉的姓名为由,驳回了其“姓名权”主张。10.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书。
(四)“被遗忘权”与删除权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中,虽未引入“被遗忘权”制度,但“删除”作为一项权益保护路径早已有之。如《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二款,明确网络用户可针对自身的侵权信息主张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二款中,也都赋予了自然人对违法、违约行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以上几部法律关于“删除权”的规定,大部分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存在违法、侵权或违约行为。而“被遗忘权”并不以存在违法、侵权或违约行为为基础,如上文所述,其权利对象是“合法流通之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仅认为相关信息的存在不再必要等原因,就可通过主张“被遗忘权”来要求搜索引擎服务商删除、屏蔽获取相关信息的链接。这也是“被遗忘权”与我国“删除权”制度最大的不同。
(五)小结
综上可见,“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姓名权、名誉权和删除权间存在差异,所以其并不是以上三种权利的公约数。这样,“被遗忘权”看似具备了研究和探讨制度移植问题之必要性,但其实这种探讨还不够全面。虽然“删除权”与“被遗忘权”在权利内容上存在差别,但我国当前的“删除权”规定相较“被遗忘权”来说,更符合现今社会发展水平。
首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引入了“保证个人信息传播质量”的概念。即,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其中第47条,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的“删除权”之保护范围进行了扩展,除了对违法、侵权或违约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外,还允许信息主体主张撤回同意、删除处理目的已实现的信息,或保存期限已届满的信息等,给予了信息主体更加充分的保护,且该条款并非穷尽式列举了删除权的情形,随着新的权利类型产生还可以对该条款作补充性规定。虽然“删除权”条款的内容不及“被遗忘权”所涵摄的权益宽泛,但是这样保持克制与审慎的态度不但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也能够给予司法裁判者更明确的法律指引;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除了“删除权”的规定外,还加入了“修改权”等个人信息权。如该法第46条规定,“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使得信息主体有机会将个人信息恢复到正确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信息被不当重组,以致他人肆意描绘与控制信息主体“数字人格肖像”的行为。以上关于个人信息权的规定,对我国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个性化推荐服务、网络标签体系构建、网民画像模型之整合等提出了严格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信息的“脱语境”,使信息恢复到正确状态,这与“被遗忘权”所涵摄的法益相重合。而“被遗忘权”删除、屏蔽相关信息链接的手段不但无法保证信息发布质量、彻底隐匿相关信息,且会阻碍国内信息产业的发展,因为“被遗忘权”实现方式的特殊性,使得搜索关键词获取信息之精准度和相关度会大幅下降,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查找相关信息,且由于相关信息源并没有被彻底删除,人们还是能够获取到相关信息,不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会加剧信息的不对称。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11月1日才开始施行,还未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但是未来随着法律制度的落地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还可对现有条文进行修改或扩大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对已有类似制度的深入探索强于对未知制度的单纯引入,我国不应将完善制度的注意力放在“被遗忘权”上。
四、权利是否具有实现可行性——“被遗忘权”适用所面临的挑战
认可一种权利,引入一项权利,总是需要考虑社会的运作逻辑。现今,“被遗忘权”本土化面临着技术和处理成本等诸多问题。而法律制度的构建并非“单线”运动,其背后所隐藏的是网络时代多重利益的博弈。由此,从利益角度切入,于网络受众、产业及社会运行等层面讨论“被遗忘权”制度引进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为必要。所以,单独讨论“被遗忘权”制度构建之必要性是不全面的,还需要立足多重视阈探讨“被遗忘权”制度实施之可行性,比照、预设制度落地所产生的影响是否能与其所产生的效果间保持平衡。
(一)公共言论层面:影响公众言论自由权的行使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被遗忘权”基于对“合法流通信息”的调整,不可避免的会与言论自由权产生冲突。一方面,由于“被遗忘权”所针对的“不充分、不相关、超出信息处理目的”之信息对象的设定,具有一定模糊性。当无法对信息主体所请求“被遗忘”的信息进行定性时,信息控制者有可能为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作出断开相关链接的决定。如此一来,“被遗忘权”的适用语境就会不断延展,以致于一些年久、特征模糊的个人信息很容易落入到“被遗忘权”的规制范围,形成言论“黑洞”;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并非总是孤立存在的,有些个人信息会与其他主体的信息相叠加,构成彼此相互关联的“数据集”,此时若允许其中一方信息主体以“不相关、不必要、过时”为由,过于宽泛地限制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使,则易导致信息环境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11. “寒蝉效应”(Chilling eff ect)意指:人们因害怕遭到刑罚或面临高额赔偿,而不敢公开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戕害意见市场。所以,对该权利的行使不应优先于言论自由。12. Viviane Reding: The EU Data Protection Reform 2012:Making Europe the Standard Setter for Modern Data Protection Rules in the Digital Age,http://www.doc88.com/p-9969691697299.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0月2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虽然给予了信息主体修改信息以及撤回收集、使用信息之“同意”的权利。但是并未赋予信息主体“撤回”他人合法发布的、有关自己的、客观真实的信息。之所以不作如此规定,就是出于维护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的考虑。
(二)信息接收层面:损害公众知情权
在我国的“任甲玉诉百度”案中,1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书。“被遗忘权”请求人任甲玉曾在无锡陶氏教育机构做讲师,但这家机构的名声在外界颇受争议,而从百度搜索栏中输入搜索词“任甲玉”时,搜索结果中会出现“陶氏教育任甲玉”“无锡陶氏教育任甲玉”“陶氏任甲玉”等关联信息。任甲玉因担忧相关搜索结果会导致自己的社会评价降低,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百度公司删除相关搜索结果。本案两审法院均未支持任甲玉的诉求,不仅因为任甲玉未对相关权利主张之必要性及正当性进行充分论证,还因为其诉请涉及公众知情权。由于任甲玉依旧任职于教育行业,过往从业信息与其现任职业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能够成为相关群体借以参考的重要个人资信,也是作为教师诚实信用的重要体现。对该信息的保留既能确保公众言论自由,也可保障舆论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有学者主张“被遗忘权”是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进行规制,14. 闻荣芝、周龙杰:《被遗忘权在欧洲法上的创制及对我国启示》,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6页。但是涉公益与非涉公益信息间的界限如何进行划分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难题。正如“谷歌西班牙”案后,谷歌公司经审核对部分网民的“被遗忘权”主张予以回应之后,很多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无法被网民检索到。导致这些新闻媒体迫于生存危机转而起诉谷歌公司侵犯其新闻自由,使得谷歌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并于之后恢复了一些“被遗忘”的链接。可见,即便是欧盟境内对于“被遗忘权”制度的行使,也并未摸索出一套较为有效的平衡搜索引擎服务商、原始信息发布方与信息主体间关系的方法。若移除包含个人姓名、相关事迹报道的链接,会使得一些新闻媒体难以为继,其辛苦发布的消息会因为一些信息公众的请求而轻易被移除,使得其获取流量来源之通路被切断。同时,新闻媒体发布信息的质量也会有所下降,因为新闻媒体害怕相关个人信息经报道后面临“屏蔽”风险,所以尽量抹去新闻中有可能会涉及到的特定个人身份表征,这样当受众阅读新闻时会失去新闻意指的信息相对方,使得新闻可信度和明确度大大下降。
(三)社会秩序层面:不利于良性社会秩序的建立
在互联网时代,基于数字化信息流转的特点,信息主体一旦公开分享了个人信息,就有可能会失去对相关信息的控制。所以,减少个人信息数字化显露是数字时代的一种智慧,公民应懂得“自我审查”:知道哪些信息可以发布到网络上,哪些信息不能发布到网络上。15. Viktor Mayer-SchÖ 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3,148.而不能全然要求法律去保护他们的过失、不当行为与言论。16. 吴飞、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76页。信息主体自行公布于网络空间中的不当言论、不良事迹,若后续再企图适用“被遗忘权”对以上历史予以消除,这对搜索引擎服务商等主体而言,是一种额外的不当负担。而且这种不当负担所造成的人力、技术支出,搜索引擎服务商最后会通过其他途径或手段转嫁到网络用户本身,以挽回企业损失,这对于其他网络用户来说甚为不公。而对于那些由他人合法发布之个人信息,信息主体要求屏蔽相关信息获取方式应达到何种标准也是一个难题。只有明晰“被遗忘权”的规制范围,信息处理者才能知道自己行为的合法边界,从而有效防止信息主体依据“被遗忘权”过分行使诉讼权利。而我国当前依旧缺乏相对完善的信息保护体系,若此时贸然移植“被遗忘权”,可能会造成网络用户就任何自己“不满意”的信息主张“被遗忘”的乱象。
(四)权利运行层面:“被遗忘权”易被异化为一种“特权”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在信息世界淡化“历史身份”的手段,其受众群体大概率上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因为普通人的影响力具有局限性,对其合法公开的信息也仅限于小范围的查询,可能造成的影响极小。而对于名人来说,“被遗忘权”很可能会演化为一种工具,公众人物借此抹去不光彩的过去,蓄意“改写历史”。尤其是对于一些因犯重罪而被网络媒体合法曝光纰漏的人来说,舆论监督本身对其就是一种惩戒,不能因为成年犯罪人在具备行为认知的情况下犯罪,事后还去探讨对其可合法流通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要求给予这些犯罪人在犯罪后享有一切恢复到“风平浪静”的权利,这不仅是对社会安全、公众知情权的变相侵蚀,也是对被害人的变相“嘲讽”。正如CJEU在对“谷歌西班牙案”做出裁决两天后,谷歌就收到了一些个人信息删除请求,其中包括关于一位前政客不良行为的文章。另一些案件则涉及一名被控虐待儿童的男子,他寻求消除与他的犯罪有关的链接,以及一名医生寻求删除与负面评论有关的链接。17. John W. Knopf. Google Spain SL v. Agencia Esñ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108(3):508.而在韩国的“素媛案”中,犯罪分子赵斗淳在公众视野下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更是对再犯可能性极高之人所在生活区域人群的一种保障,对其应给予必要的社会监督。若允许这些人对合法流通的有关自己的信息(如居住区域、日常行踪轨迹等)进行屏蔽、删除,势必会引发民愤,激发公众更为强烈的好奇心,形成对信息主体的“人肉搜索”,导致信息主体更多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被暴露,从而出现“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18. “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 ect)意指:越是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使该事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五)技术应用层面:网络信息流动特性增加了“被遗忘权”实现难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网络空间彻底实现“被遗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空间的数据一旦生成就能低成本、无限制、跨地域传输、复制和存储。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之下,网络上的信息无处不在,很难有效做到信息的彻底删除。欧盟最高法院总顾问Maciej Szpunar曾指出,谷歌公司可就“被遗忘权”的行使限定在欧盟境内。19. Robin Langford: Right to be forgotten: Google wins court battle to keep it EU-only,https://www.netimperative.com/2019/09/24/right-to-be-forgotten-google-wins-court-battle-to-keep-it-eu-only/.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0月9日。即谷歌公司不必就全球范围内流转的欧盟公民之个人信息进行采取屏蔽或删除等措施。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若只要求搜索引擎公司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断开链接,则无异于“掩耳盗铃”。网民仍可通过使用VPN绕过境内搜索引擎对自己检索行为的限制,获取相关信息。亦或之后生成替代链接,供网络用户转发、分享,这种断开链接的方法仅是降低了在特定范围内用“姓名”直接检索结果的相关度而已。其次,搜索引擎服务商无法杜绝其他网络用户对相关数据内容的缓存,20. P.T.J.Wolters. The territorial effect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fter Google v CN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21,29(1):61.亦无法阻止他人将缓存内容进行二次传播。这种“删除”行为“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从这里删掉,却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21. Hannah L.Cook. Flagging the Middle Ground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Combating Old News with Search Engine Flags.Vand.J.Ent.&Tech.L,2017,20(1):13.由此来看,“被遗忘权”仅能保证信息被注意的可能性被削弱,而不能被消亡。这样就会造成为施行“被遗忘权”所投入的巨大成本与具体个案所带来成效之间严重不相匹配的结果,以致于“被遗忘权”之行使仅仅成为了一项缓解网民焦虑的“暧昧”举措。
(六)产业成长层面:抑制信息产业发展
“个人信息立法的宗旨应该是保持个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人格权保护之平衡。”22. 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即法律的功能不仅在于保护权利,还要兼顾人的行为自由。不能因为个人信息需要保护,而“一刀切”禁止所有个人信息的开发利用和自由流通。在信息开放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一个内在需求就是将尽可能多的信息汇总在一起,也正是依靠大量信息的不断“投喂”,大数据分析才得以变得更加精准和智能。若个人信息保护的过于严苛,不但阻碍信息流动,还会阻碍信息的二次利用,不利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如,“谷歌西班牙案”的判决结果直接导致谷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收到超过300万个链接删除请求,而微软公司也收到了超过89000个链接移除请求。23. See Jennifer Daskal, Article: Speech Across Borders, 105 VA. L. REV.,2019:1618. 转引自Jessica Friesen. The impossibl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utgers Computer and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21,47(1):178.2017年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即“PwC”)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500家美国公司中至少有68%的公司表示为履行GDPR数据合规义务预计将花费100万到1000万美元成本,另外有9%的公司预计将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24. PwC.Pulse Survey. US Companies ramping up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budgets. PwC,Inc,2017:2.在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若直接移植欧盟的“被遗忘权”,势必造成相关案件数量井喷式增长。这将会给搜索引擎服务商造成巨大的合规成本,25. John W. Knopf. Google Spain SL v. Agencia Esñ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108(3):508.严重影响初创信息科技企业的生长。同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需考虑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当前,我国信息产业还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转型期,26. 郑腾飞:《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三大结构性隐忧》,载《中国经贸导刊》2021年第5期,第52-53页。而这一发展时期少不了对大数据时代“信息”这一生产要素的整合与利用。若我国盲目引进欧盟的“被遗忘权”,任由信息主体对信息过分的控制,则会裹挟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演变成我国信息产业的“自我打压”。
五、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就是生产要素,信息安全及合理利用成为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被遗忘权”的提出,试图限制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对个人信息的过度保存和使用,竭力维护信息主体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其本身具备正当性基础。但是,在探讨“被遗忘权”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特定语境下权利实现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从“被遗忘权”的制度特点着手,对比“被遗忘权”与我国各项现有法定权利的差别,从而论述“被遗忘权”所涵摄的价值利益是否值得保护,是否具有翻新现有法律制度之必要性。之后,本文又从受众、产业以及社会发展等层面探讨了“被遗忘权”制度在我国是否具有实现之可行性。最终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结论皆为:我国目前不宜移植“被遗忘权”。若对我国“删除权”进行再一步的扩张,至“被遗忘权”的程度,则会使该权利演化成为信息主体恣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后悔药”,从而伤及其他信息相关方权益,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和利益冲突。所以,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应操之过急,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如何“更好实行”的研究上,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阶段性立法,待我国信息保护体系相对完善之时,再对信息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进行适当扩张也不失为一种好的保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