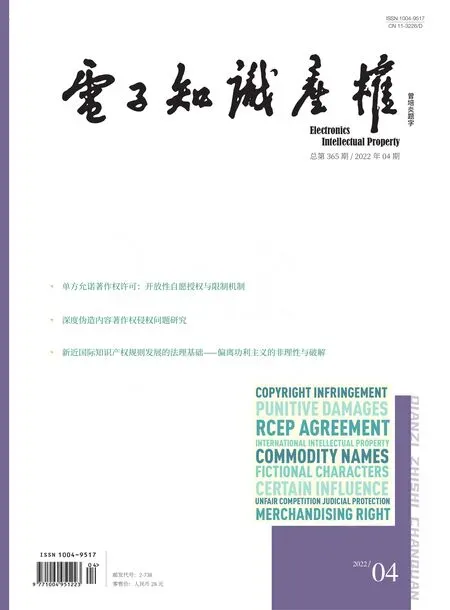新近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发展的法理基础
——偏离功利主义的非理性与破解
文 / 马忠法 谢迪扬
一、引言
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无限期中止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重心开始从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为核心的多边协议,向区域性协议、双边协议转移。伴随着逆全球化思潮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TRIPS-plus”条款不断涌现,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1参见杨健:《中美贸易战视域下知识产权保护“超TRIPS标准”发展趋势研究》,载《北方法学》2019年第6期,第94页。虽然不同经济体主导构建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都带有“TRIPS-plus”条款,但它们所呈现的“TRIPS-plus”的程度和方向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亚太各国在近年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RCEP),其知识产权章节的立法思路指向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进路,功利主义已经不足以解释两者背后蕴含的基本法理的区别。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其角色逐渐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倡导者。为了更好承担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大国责任,中国必须关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2本文所指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既包括专门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又包括多边、双边经贸协定中的知识产权章节。背后蕴含的法理基础,判断当下的规则发展趋势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方案,为今后引领制度变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此,本文首先介绍了“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两种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路径,并从知识产权的制度特点出发,论证了国际社会对功利主义的选择;其次指出国际知识产权的新近发展偏离了功利主义,不断趋近完满的所有权,即“财产权劳动理论”下的权利形态;再次,对国际知识产权趋近所有权的发展态势提出了理性的批判;最后,从调和“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之主次的角度,阐明破解之策。
二、知识产权的法理基础:传统与发展
知识产权的法理基础主要关注的是知识产权的正当性问题。自知识产权概念产生以来,有关正当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理论是两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一)财产权劳动理论
“财产权劳动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思想家洛克,他认为在劳动开始之前,世间财富为人类所共有;只要人使物品脱离自然状态,他的劳动就渗进了该物品,因而使该物品成为他的财产,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3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美国学者黑廷格发展了“财产权劳动理论”,将劳动者的权利限定于因其劳动实现价值增值的部分,而不是物品的全部价值;要求劳动者付出的努力与获取的价值形成一定的比例。4See 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89, 18(1): 37-42.虽然“财产权劳动理论”起初主要适用于有体物,但它完全可以作为知识产权的法理基础,因为没有哪种劳动可以独立于智力,所以智力劳动理所当然也是劳动的一种。5参见易继明:《评财产权劳动学说》,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99页。自启蒙时代至今,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观念,一直是许多人的深刻信仰。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了英国知识产权法的演进后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知识产权法的关注焦点仍旧在于评价某一特定对象所体现的劳动,6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 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208页。可见当时“财产权劳动学说”仍在知识产权正当性争论中扮演重要角色。7参见彭学龙:《知识产权:自然权利亦或法定之权》,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8期,第15页。即便是在当代,一些欧洲国家制定知识产权法时,依旧将“财产权劳动理论”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8参见何鹏:《知识产权立法的法理解释——从功利主义到实用主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第23页。
(二)功利主义理论
功利主义基于避苦趋乐的伦理原则,要求社会或政府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法学则是将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流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需要权衡功利,这是立法的宗旨,法律实施的基础,也是评判法律优劣的标准。9参见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功利主义对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1875年贝尔珀勋爵在英国国会上的著名发言为标志,他主张:“一个发明人对于其发明并不拥有自然的或者原始的一种垄断权……专利的存在只可能以公共效用为依据而获得保护。”10Patents for Inventions Bill, Hansard (Lords Chamber), volume 222, column 926, debated on Friday 26, February, 1875.此后,知识产权法越来越关注智力成果“背后的踪迹”,11S. Dentith. Political Economy, Fic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Practical Ide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Social History,1983(8): 186.即宏观经济价值,对国民生产总值或生产力的贡献,以及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作用。相比于“劳动财产权理论”,现代知识产权法更倾向于使用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话语和论证逻辑。12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 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功利主义认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由两方面构成:第一,知识产权能够激励人们更踊跃地投入创新事业,是授予创新者的奖励,从而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第二,知识产权过期之后,创新成果将流入公共领域,使社会公众普遍受益。如果知识产权带来的总体社会效益增益,大于限制知识传播造成的效益损失,那么知识产权作为一项公共制度就是正当的。13See Tom G. Palm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Non-Posnerian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Hamline Law Review, 1989,12(2): 262.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目的论、14目的论认为法的直接目的是产生并保护财产,最终目的是维持人类的生存,直接目的服务于最终目的。按照目的论的逻辑,之所以要通过法律制度创设并保护知识产权,是因为它可以使创新活动变得可持续,而创新事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利益论、15利益论认为利益平衡的状态即为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佳水平,知识产权法应致力于实现权利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等相关主体之间形成特定的利益平衡。参见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册),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实用主义16实用主义者认为,宏观的社会需求证成了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等证成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但都没有完全脱离功利主义。
(三)国际社会对功利主义的选择
上文已经提到,“财产权劳动理论”是基于有体物发展起来的,从该理论推导出的权利形态是各项权能均无瑕疵的、完满的所有权;虽然也能适用于知识产权,但无法解释知识产权与有体物所有权在权能上的差异。各国法律和判例不约而同地确立了知识产权期限性、条件性、地域性、可限制性和刑事救济谦抑性,这些特点都只有在功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才能得到解释。可见,在“财产权劳动理论”和功利主义之间,国际社会普遍选择了后者。17参见和育东:《从权利到功利:知识产权扩张的逻辑转换》,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5期,第10页。下文将分点详细阐述。
1. 知识产权期限性
在“财产权劳动理论”的视角下,知识产权与有体物所有权一样,无疑都是永久的。在1769年英国Millar案中,原告主张普通法上的复制权应独立于《安娜法案》,是一种永久的独占权,在当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18See Millar v. Taylor (1769) 4 Burr. 2303.但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知识产权应具有期限性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1774年的Donaldson案中,英国上议院判决,《安娜法案》中版权期限性的规定,已经取代了普通法中的永久复制权,因此只要该法案没有失效,版权就不再是永久性的权利。19See Donaldson v. Becket (1774) 2 Bro. P. C. 129.进入十九世纪后,在美国Wheaton案中,版权期限性的规定被类推适用于专利领域;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支持功利主义,认为制定法(包括版权法和专利法)是基于激励理论人为创设的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的成文化。20See Wheaton v. Peters, 33 U.S. 591 (1834).在当代,大部分知识产权都是一种期限性权利,也存在少数例外,比如允许无限续展的商标权、无期限的商业秘密权等。
2.知识产权条件性
“财产权劳动理论”并不支持对知识产权施加确权条件,认为只要付出了人的(智力)劳动,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对该智力成果主张权利。但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知识产权条件性逐渐得到推行,取代了“财产权劳动理论”主张的“额头流汗”标准,显著提高了获得知识产权的门槛,限缩了知识产权适格客体的范围。比如在美国Feist Publications Inc.案中,法官确立了版权的独创性标准,否认了电话号码簿的版权适格性,将“有劳动就有保护”的逻辑“拉下神坛”。21See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499 U.S. 340 (1991).同时,专利领域也发展出了实质审查制度,在新颖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创造性的标准,进一步限缩了专利适格客体的范围。就连长期以来坚持“专利乃发明者天赋人权”的法国《专利法》,也在1978年修订时增设了实质审查制度。22See Nobuhiro Nakayama. Industrial Property Law. Koubundou Publishers, 2000:32.仅凭发明者付出的劳动,无法支持其获得垄断性的专利权。
3.知识产权地域性
地域性是知识产权自产生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特性,“财产权劳动理论”不能为其提供解释,而功利主义却与其十分契合。因为在“财产权劳动理论”看来,知识产权是一种“精神所有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具有对世性,理应没有地域限制。23See L. Ray Patterson,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1624-1627.而功利主义认为,知识产权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为目的,人为创设的一种私权;它是由君主或政府授予公民的,为了追求本国或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因此它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君主领土或国家境内。知识产权的发展历史也印证了功利主义的观点。早在“财产权劳动理论”兴盛之前,欧洲已经存在由封建君主授予出版商“排他的出版所有权”的做法,这种权利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君主的领土;封建王朝衰落后,有的出版商基于“财产权劳动理论”,主张突破地域性的限制,但在实践中未获普遍成功。24参见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本体、主体与客体的重新认识——以财产所有权为比较研究对象》,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第3-7页。现实原因在于,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并不统一,是否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需要经过各国的国家审查、国家注册才能判断。25参见张乃根:《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知识产权制度对地域性的坚持,正是国际社会选择功利主义而非“财产权劳动理论”的表现。
4.知识产权可限制性
知识产权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限制性规定的发展也得益于功利主义理论。虽然“财产权劳动理论”也要求权利人对私人财产的占有不能侵害他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基于这一观点,许多国家的宪法授权国家在紧急情况下为公共利益目的,可以征收、征用公民的财产。但“财产权劳动理论”的标准过高,与现有知识产权限制性规定,包括非紧急情况下的强制许可制度等,并不十分契合。现行规定更多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总体福利,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公众之科学、文化需求的不当抑制。比如,按照“财产权劳动理论”的标准,社会公众只有在穷尽其他资源后,仍不能满足其科技、文化需要时,才能“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然而各国的“合理使用”规定显然没有提出如此苛刻的前置条件,正是功利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的结果。
5.知识产权刑事救济谦抑性
知识产权刑事救济制度也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其旨在众多能实现“激励目标”的手段中,选择对公众限制程度最小的手段,而不是追求极致的惩罚或震慑效果。从刑法条文上看,知识产权犯罪大多为目的犯和数额犯,极少出现行为犯和过失犯,比一般财产犯罪的规定更具谦抑性。比如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并没有目的上的限制,最高可判无期徒刑。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年)第二百六十四条。按“财产权劳动理论”的逻辑,侵犯著作权相当于盗窃“精神财产”,定罪量刑的标准应与盗窃罪看齐,但我国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制裁,只能建立在侵权人“以营利为目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基础上,且最高只能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年)第二百一十七条。显然与有形财产犯罪有差距。知识产权刑事救济更具谦抑性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侵权与否,并不如有形财产那般清晰,行为人的可预见性普遍较差,主观恶意也相对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如果民事侵权制度已经足以实现“激励目标”,就没有动用刑法的必要,这正是功利主义的思路。
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新近发展对功利主义的偏离28 本文所指的“偏离”,不是彻底放弃功利主义,也不是彻底废除了上文总结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征;而是从规则发展的趋势看,知识产权的基本权能不断趋近所有权,而所有权是“财产权劳动理论”下的权利形态。单凭功利主义无法清晰解释这种发展趋势,下文将详细说明。
知识产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权利体系,其制度特征、基本法理都不是静止的、永恒的。29参见马忠法、王全弟:《知识产权的历史成因、法定主义及其法律特征》,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67页。在各国初步完成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后,既得利益群体不满足于功利主义理论下附带种种限制的知识产权。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他们依旧高举“功利主义”的旗帜,但从改革的结果看,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趋势,越来越趋近于“财产权劳动理论”推导出的权利形态,即完满的所有权。
(一)知识产权保护期的延长
从总的趋势看,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试图排除国内法对知识产权保护期的决定权,并借助条约的约束力,使知识产权得到更长时间的保护。其中,版权领域的情况最为典型。1886年首次签署的《伯尔尼公约》并未规定统一的版权保护期,各缔约国可以自行确定保护年限。30Convention de Bern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1886), art. 2.1908年的柏林修订案增设了统一的版权期限,即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但允许各缔约国以国内法优先。31Acte de Berlin (1908), art. 7.法国一直倡导统一的保护期,认为可以促进跨国文化事业,其他缔约国虽然认识到统一的保护期将削弱“保护独立性原则”,但还是陆续采纳了统一期限。32参见【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领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郭寿康、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1948年的布鲁塞尔修正案强制规定,普通作品的最低保护期是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33Se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revised at Brussels on the 26th June 1948, article 7 (2).电影作品、摄影作品及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仍以各国国内法为准;34Se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revised at Brussels on the 26th June 1948, article 7 (3).并删除了柏林和巴黎文本的过渡性安排。以英国、瑞典、瑞士为代表的原先一直坚持较短保护期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显著让步。35Se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Documents de la Conference reunie a Bruxelles du 5 au 26 juin 1948. 1951:98, 201-202.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广播、电影等技术的发展,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关注新型版权的利益集团。在这一趋势下,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修正案进一步强制规定,电影作品的保护期至少为公开日或完成日之后的50年;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至少为完成日之后的25年。36Se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Revised at STOCKHOLM on July 14, 1967, article 7 (2), (3).这套版权期限性规定沿用至今,并被引入TRIPS协议。2016年签署的TPP陡然将所有类型的版权保护期延长至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70年。对普通作品而言,作者死后保护年限的增幅达40%;对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而言,保护期延长了近三倍。商标和专利领域也出现了类似趋势。TRIPS协议规定商标首次注册及每次续展获得的保护期不少于7年,而TPP知识产权章节将这一期限延长为10年。专利领域虽然没有直接延长保护期,但新近出台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出现了要求调整专利期的条款,是对专利保护期的变相延长。比如TPP知识产权章节规定,如专利局在审查期间出现了延迟,则须调整专利保护期以补偿权利人;37See TPP (2016), article 18.46.对上市许可程序导致的药品专利期不合理缩短,也须调整专利期作为补偿。38See TPP (2016), article 18.48.《中美经贸协议》也出现了此类变相延长药品专利期的规定。
(二)知识产权适格客体的扩张
在条件性方面,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适格客体的不断扩张。首先,商标的可注册范围不断扩大。最早的国际工业产权协定——《巴黎公约》并未对商标的可注册范围制定硬性要求,允许各缔约国由其国内法自行决定。39参见《巴黎公约》(1967年)第六条第一款。1988年,欧盟出台的《协调成员国商标立法第一号指令》明确要求成员国将字母、数字、商品外形及其包装纳入商标的可注册范围,使其正式扩张至立体商标。40参见《协调成员国商标立法第一号指令》(89/104/CEE)(1988年)第二条。目的在于实现商品、服务的自由流通,协调对市场运转有直接影响的有关条款,详见第三条。1994年出台的TRIPS协议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41缔约国普遍认识到TRIPS中的商标条款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并扩大国际经济失衡。See Luis Abugattas.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1991(22):371.没有正面回应立体商标、非视觉商标的可注册性问题,还允许缔约国将“视觉上可感知”作为商标注册的必备条件。42See TRIPS (1994), article 15.2016年,TPP知识产权章节明确排除了“视觉感知”这一注册条件的合法性,要求缔约国不得拒绝声音商标的注册,且应尽最大努力注册气味商标。43See TPP (2016), article 18.18.可见,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中,商标可注册客体规定的硬性程度越来越高,商标权的适格客体不断增多。
其次,可授予专利的客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巴黎公约》允许各缔约国在国内法中自行确定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范围。44参见《巴黎公约》(1979年)第一条,第四款。TRIPS协议则明确要求缔约国承认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但设置了获得专利的三项条件:一是具有新颖性,二是包含发明性步骤,三是可供工业应用。45See TRIPS (1994), article 27.TPP知识产权章节在TRIPS协议的基础上,新增了四项可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使用已知产品的新工序和源自于植物的发明;且要求缔约国必须承认前三种的任一种和第四种。目前工业界和学界还在激烈争论商业方法、计算机软件发明、基因技术发明等新型客体的可专利性。在未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可专利性客体范围很可能进一步扩大。
再次,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也呈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巴黎公约》并未将商业秘密作为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只笼统规定:“凡在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46《巴黎公约》(1979年)第十条之二,第二款。据此,TRIPS协议生成了未披露信息的保护制度,其保护范围有且仅有两大类,一是构成商业秘密的未披露信息,二是提交政府或政府机构的数据。2020年签署的《中美经贸协议》将保护范围扩大至“保密商务信息”,这个概念不但包括了商业秘密,还包括可能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流程、经营、作品风格、设备、物流信息、客户信息、库存、收入、利润等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4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2020年)第一章第二节脚注一。这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试图淡化商业秘密中“秘密性”这一构成要件,以扩大保护范围,正是对知识产权条件性的弱化。
此外,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开始出现“数据独占权”条款,意味着“额头流汗”标准的复辟。因为数据既不具有版权法上的独创性,又不具有专利法上的新颖性,其得到垄断性的独占权,仅仅是因为收集或获取数据的人对此付出了劳动。数据独占权首先出现于美国1984年的《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授予新药试验数据5年保护期,已知药品新特征的试验数据则拥有3年保护期;48See Sanjuan, Judit Rius. US and EU 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Test Data. www.cptech.org/publications/CPTech DPNo1TestData.pdf, 2006. Last visited on 2022-05-01.此后又于1987年被引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指令65/65/EEC》,正式成为一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49See Cook, Trevor M. The Protection of Regulatory Data in Pharmaceutical and Other Sectors. Sweet & Maxwell, 2000: 11-15.1994年,在美国的主张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设置了数据独占权条款;最后,TPP在沿用5年保护期的基础上,又将新农业化学品数据(本国首次上市)的保护期延长至10年,50See TPP(2016)article 18.47(1).生物药数据(本国首次上市)的保护期延长至8年。51See TPP(2016)article 18.51(1).
(三)部分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削弱
微观层面,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张力主要存在于商标领域。这首先体现于驰名商标条款,只要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即使尚未在请求保护国注册,也能获得保护,甚至保护程度更强,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直接突破。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驰名商标的保护程度逐年增强。《巴黎公约》规定的驰名商标仅限于商品商标,保护范围仅限于相同或类似商品;52参见《巴黎公约》(1979年)第六条之二。TRIPS协议新增了驰名服务商标,并将保护范围扩张至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53See TRIPS(1994)article 16 (2, 3).TPP进一步放宽了驰名商标的认定门槛,禁止缔约国将“已在本国或其他辖区内注册”、“列入驰名商标名单”或“已获得驰名商标认可”作为认定驰名商标的条件。54See TPP(2016)article 18.22 (1).
其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也体现了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削弱,因为一国商标主管机关在认定恶意时,已经为尚在域外的某项商标预设了一种排他权,可见该商标的效力超越了其注册地边境,延伸到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的国家境内。《巴黎公约》、TRIPS协议、TPP中,主管机关只有在认定驰名商标的前提下,才可以拒绝或驳回具有恶意或欺诈可能的商标申请。但RCEP对恶意商标注册的规制是独立于驰名商标的,因此缔约国可以在不能认定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打击恶意商标注册。可见,越来越宽泛的恶意商标打击范围,进一步松动了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约束。
宏观层面,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推动下,各国国内法对本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决定权不断限缩,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趋向统一,正是地域性削弱的宏观表现。55参见阮开欣:《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载《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第81页。上文已经阐述,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理论溯源可知,知识产权地域性源自封建君主所授特权的效力范围(即知识产权仅在其领土境内有效);而地域性的削弱意味着,国际社会越来越不认可知识产权是一种“被授予”的特权。在这种制度发展趋势背后,国际社会的“潜意识”似乎在向“财产权劳动理论”的逻辑靠拢。
(四)知识产权限制性规定和例外条款的弱化
文本相似的限制和例外条款经常在各项国际协定中反复出现。比如TRIPS协议第13条、第17条和第30条分别规定了针对版权、商标专有权和专利权的限制和例外;TPP、RCEP基本沿用了TRIPS的立法方式。但是新型知识产权纳入国际协定后,大多需要另行规定限制和例外条款。由于国际上知识产权既得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出现了弱化相关限制和例外条款的倾向,甚至将其完全“遗忘”在条约文本之外。比如TPP在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中设置了限制和例外条款,但在权利管理信息项下,立法者却忽略了这个问题;而基本同时期出台的RCEP,却在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项下均设置了限制和例外条款。56See RCEP (2020), chapter 11. article 16.可见,并不是因为权利管理信息不需要限制和例外条款,而是参与协定谈判的主体对限制和例外条款的需求和重视程度不同。
那么,TRIPS协议和TPP在总则部分规定的一般性限制和例外条款,是否可以弥补新型知识产权项下未设置类似条款的缺憾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相比于具体的限制和例外条款,一般性条款的示范效应较弱,法律适用较为困难。比如TRIPS协议没有在未披露信息项下规定限制和例外条款,间接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商业秘密制度建设时几乎没有考虑国家征用、强制披露、强制许可等限制和例外问题,无法满足实践需要。57参见李想:《基因信息领域中商业秘密壁垒的突破策略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20年第2期,第68页。《中美经贸协议》在利用“保密商务信息”的概念,大幅扩张了保护范围之后,依旧对限制和例外问题缄口不言,很可能也是TRIPS时期留下的“副作用”。
此外,TPP还试图约束安全例外的适用。一直以来,安全例外条款被誉为调解自由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平衡器”,为众多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所青睐。58参见何华:《知识产权保护的安全例外研究——由〈TRIPs协定〉第73条展开》,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819页。这类条款的立法范式,几乎都是授权于缔约国,允许其根据自己的判断,适当减免国际条约义务,以维护其根本安全利益。TRIPS协定将安全例外条款引入知识产权领域后,缔约国援用该条款可暂停知识产权保护义务,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也没有其他额外条件。然而TPP规定,当缔约国援用安全例外条款豁免条约义务后,即负有立即与其他缔约国磋商的义务,以调整TPP知识产权章节的内容。一般而言,暂时性的义务豁免并不会产生调整条款内容的必要,因此TPP意图调整的对象,很可能是知识产权章节附件中约定的保留和过渡期条款。换言之,援用安全例外的缔约国,可能将被迫撤回保留声明或缩短过渡期,这实质上构成了适用安全例外的额外条件。
(五)知识产权刑事制裁的强化
依照功利主义理论,知识产权刑事救济须更具谦抑性,以促进创新和公开为目标,而不是纯粹为了报复或震慑。然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逐渐淡化了这种谦抑性,专注于维护既有权利,其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刑事制裁力度与激励效果不成比例,很可能构成边沁所指的“过分之刑”和“昂贵之刑”。59过分之刑是指,通过更温和的手段即可达到同样效果,但却进行刑法干预;昂贵之刑是指,刑法干预后的正面效果小于负面效果。参见【英】杰里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页。
首先,刑事制裁范围明显扩大。在TRIPS协议框架下,大部分知识产权实施措施都采用了民事或行政程序,必须启用刑事制裁的仅有“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60TRIPS (1994), article 61.而TPP大肆扩张刑事制裁的适用范围,如侵犯载有加密节目的卫星信号或为此提供技术协助、为商业利益故意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或改变权利管理信息、未经授权复制电影、未经授权故意获取、盗用或欺诈性披露商业秘密等,都将被认定为犯罪。
其次,部分条款试图降低入刑门槛。比如,TRIPS规定的入刑条件之一是“具有商业规模”,并不支持对所有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无条件适用刑罚,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思想。但TPP规定,即便不是出于商业利益,但对权利持有人的市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影响的,也符合入刑条件。61See TPP (2016), article 18.77 (1) (b).显然,TPP试图架空“商业规模”的限制,扩大刑法打击范围。再如,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知识产权犯罪均为“数额犯”,即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在《中美经贸协议》中,侵犯商业秘密罪正在向“行为犯”靠拢,协议要求缔约方不得将“发生实际损失”作为启动刑事调查的前提。6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2020年)第一章第1.7条。
再次,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的严厉程度失当。比如商业秘密制度,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商业秘密拥有无限的保护期,其惠及公共领域的能力明显小于“以公开换保护”的专利,因此打击商业秘密侵权的严厉程度理应低于专利。然而TPP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刑门槛奇低,包括“与国内或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或服务相关”、“意图是对商业秘密的拥有者造成损害”、“受外国经济实体指示或为其利益或与其有关”等;63TPP (2016), article 18.78 (3).但在专利方面,TPP甚至没有强制要求各缔约国将侵犯专利规定为犯罪。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中美经贸协议》中,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构成要件、入刑门槛、权利人的举证要求均低于专利制度,对商业秘密侵权人的打击力度明显强于专利侵权人,这很难用功利主义加以解释。
根据比例原则,如果民事侵权赔偿制度已经能起到足够好的激励创新或激励公开的效果,那么大肆运用知识产权刑事制裁反而是对社会公众的不当约束,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违背。64参见姜涛:《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0页。虽然有观点认为,加强知识产权刑事规制有利于增加侵权成本,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从而促进创新和公开,因此是符合功利主义逻辑的。但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往往并不意味着创新能力越强,上述功利主义的证成逻辑过于草率,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
四、国际知识产权趋近所有权的理性批判
(一)违背国际主流意志的“暗度陈仓”
成功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明确的治理目标和清晰的治理意识。65参见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78-84页。然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总体发展趋势,似乎缺乏清晰的国际意志的主导。几乎所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都在序言或总则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国际治理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社会的总体福祉,这表明了国际主流意志对功利主义路径的支持和贯彻。但正如上文所述,具体条款所塑造的知识产权,正不断趋近完满的所有权,即“财产权劳动理论”下的权利形态,单凭功利主义无法清晰论证这种发展的合理性。可见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新近发展,很可能是一种违背国际主流意志的暗度陈仓。
从条约文本上看,TRIPS协议规定的三大目标:促进技术革新、转让、传播;促进创造者和使用者互利;促进社会、经济福利和权义平衡;完全体现了对功利主义的支持,对“知识产权乃天赋人权”等原理只字未提。TPP知识产权章节除了一字不差地沿用了TRIPS目的条款之外,还进一步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应“促进创新和创造力”、便利传播、“培养竞争、开放和有效率的市场”。66See TPP (2016), article 18.4.这些也全部都是功利主义的目标,全然不涉及“财产权劳动理论”。在《中美经贸协议》中,中国方面明确重申了功利主义的立场,表明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在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6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2020年)第一章第一节序言。但美国方面只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有意弱化了功利主义理论下保护知识产权所指向的终极目标,似乎保护知识产权本身就是终极目标。这偏离了功利主义,显露了向“财产权劳动理论”发展的倾向。
国际法是主权国家之间不同意志的妥协,因此国际条约所呈现的文本,是不同意志综合作用下胜出的国际主流意志的体现。68参见周银珍:《“历史合力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39页。如果国际主流意志确实希望更多地从“财产权劳动理论”出发,改革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那为什么不在序言或总则中明确表明这种意志?再者,同样都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为什么美国可以在《中美经贸协议》中显露向“财产权劳动理论”发展的意志,而在TPP中却不得不将其藏匿?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功利主义在WTO的164个成员的意志交锋中胜出了,在TPP的12个缔约国的意志交锋中也胜出了,在《中美经贸协议》中与“财产权劳动理论”平分秋色。可见,新兴知识产权多边协定中的趋向“财产权劳动理论”的条款,很可能是多边论坛的落败一方悄然植入的“小动作”;双边协定中的类似条款,是落败一方在采取“论坛转移”策略后的故技重施;69See Helfer, Laurence R. Regime Shifting: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New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aking.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29(1):1-4.国际社会须对此引起高度警惕。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偷换
上文已经谈到,部分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能,使其趋近所有权。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的重重监督下“登堂入室”,是因为支持者们为其编织了一件颇具迷惑性的“功利主义”的外衣,完成了从“激励创新和公开”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功利主义价值偷换。这种论证思路主要由以下几个观点构成:
首先,针对知识产权期限性和可限制性,有人基于功利主义目的论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期太短,限制太多,企业无法收回创新成本,使创新活动不能持续,最终损害社会福祉。比如药品研发企业一直声称自己“投资大、风险大、难度大、周期长”,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激励,药品创新事业将受到限制,可能危害人类健康。70参见程永顺、吴莉娟:《探索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其次,针对知识产权条件性,部分观点指出,企业投入研发成本获得的一些智力成果,虽然不构成知识产权,但具有重大商业价值,如果其他竞争者可以任意使用,将损害竞争公平性和商业伦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比如在药品试验数据的问题上,原研药企声称,仿制药企依赖其数据,在短时间内以极低成本上市销售,是对其数据的“不公平商业使用”。71See Bayer Inc. v. Canada, 155 F.T.R. 184 (1999).再次,针对知识产权地域性指出,由于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的全球性,以及商标抢注、专利侵权、作品抄袭等侵权行为的国际化,固守地域性将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最后,针对知识产权制裁谦抑性指出,因为知识产权侵权成本过低,预防、震慑未来侵权行为的效果不够理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所以需要增设惩罚性赔偿,并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制裁。72参见罗莉:《论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引进和实施》,载《法学》2014年第4期,第30页。
上述观点存在一个共性,它们都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并近乎盲目地坚信只有加强保护才能促进创新,保护程度与创新水平成正比。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促进社会整体利益。73参见宁立志:《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32页。即便没有知识产权,有天赋的个体也不会吝啬他的创造力,而给庸人再多的经济回报也无法使之成为天才。再者,智力创造需要利用前人的知识积累,过度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在“先创新者”和“后创新者”的利益平衡中偏袒前者,反而是对功利主义利益论的违背。74参见蒋舸:《著作权法与专利法中“惩罚性赔偿”之非惩罚性》,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81页。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上,保护知识产权只是一个中间目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目的在于利用创新促进人类福祉。在利益集团的反复游说下,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立法者似乎出现了终极目的和中间目的的混淆。极力追求保护知识产权这一中间目的,真的有利于实现“促进人类福祉”的终极目的吗?会不会反而对其造成阻碍?对这一根本问题,立法者们长期选择视而不见。
(三)与人类共同利益背道而驰
国际知识产权趋近所有权的规则发展态势,既没有得到国际主流意志的认可,缺乏程序正义;又无益于创新激励和智力成果的公开,缺乏实质正义;可见,这种趋近是非理性的。如果依照“财产权劳动理论”,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整个制度体系的终极目标,那么这种对保护强度的极致追求,可能将人类文明导向一个未知的困境,对人类共同利益造成潜在威胁。
一方面,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有可能阻碍后来者创新。在不具技术优势的国家,从无到有完成原始创新难度过大,而模仿创新相对而言投入少、风险低、较温和,是大多数企业的选择。但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模仿创新的合法路径,是这些国家技术进步迟缓、甚至停滞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通过双边自贸协定,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植入约旦(2001年)、摩洛哥(2004年)、多米尼加(2005年)等发展中国家。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完全没有因保护而腾飞。在《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统计的131个国家中,约旦位列81,摩洛哥位列75,多米尼加位列90,创新能力依旧十分落后。75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谁为创新出资(摘要版)》,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P020201209477114548116.pdf,第31页,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1日。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过度保护还可能消磨既得利益者的创新积极性。因为创造财富的不是创新本身,而是技术差距。对已经获得技术优势的企业而言,只要技术差距不被缩短,就能持续盈利。因此,与其将资金投入颇具风险的创新事业,不如加强政治、法律公关,提高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阻碍技术扩散。后者收益更稳定,更符合经济理性,正是现今许多实力雄厚的科技企业的做法。有研究指出,企业将患者支付药费的三分之二用于公关和营销,剩余部分还要扣除制药成本、经营管理等费用,投入研发的资金占比少之又少。76参见韩成芳:《药品专利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反思》,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第11期,第2页。此外,由于新颖性程度的高低不影响专利权的内容和期限,因此相比于高投入、高风险的“颠覆式创新”项目,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更加青睐重组现有技术,或进行微小改良,以“渐进式创新”达到变相延长专利保护期的目的。77参见【英】克里斯汀·格林哈尔希、马克·罗格:《创新、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刘劭君、李维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医药行业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推行超高保护标准的美国,医药创新能力不增反降,甚至不如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水平。78See Merrill Goozner. The $800 million pill: the truth behind the cost of new dru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31.研究表明,2017年美国批准的新药中,约有30%被认为“没有或只有少量额外益处(与原有药物相比)”;高价专利药有40%是原有药物专利过期后,其活性成分的重新配方。79See Phebe Hong, et al. Transformative models to promote prescription drug innovation and access: a landscape analysis. Yal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2020, 19(2): 59.已有研究者发问,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企业将原本用于申请专利、购买技术、侵权诉讼的费用投入研发,无法依赖现有技术优势而消除惰性,会不会更有利于人类创新事业?80See Clarence Lee Swartz. What Is Mutualism? http://www.panarchy.org/swartz/mutualism.5.html#patents. last visited on 2022-05-01.
如果说抑制创新潜力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尚属未知,那么知识产权过度保护造成的医药可及性问题已经切实摆在人类面前。为避免创新事业,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陷入无可挽救的境地,国际社会从现在开始就应正视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法理扭曲、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问题。
五、破解之策:“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的适用分野与调和
面对国际知识产权向所有权的非理性趋近,我们更不能非理性地横加批判;而应重拾理性,识别国际社会的真实需要,并据此审视各类知识产权的特点和立法目的,分别重塑其基本法理和价值取向。目前的知识产权客体主要可分为智力成果和工商标记两类,彼此差异较大;因此“财产权劳动理论”或功利主义的任一种,可能都无法成为整个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法理。根据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特点,确定“财产权劳动理论”和功利主义的主次,使其调和、共存,并反映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或有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知识产权章节、条款之中,或许是更好的思路。
(一)工商标记权:“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
工商标记权的法理基础应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辅之以功利主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工商标记权主要包括商标、地理标志81虽然地理标志不是一种私权,但它与商标权类似,并非作为一项智力成果而受到保护,其保护的是标志背后的商品声誉及商业价值,其中蕴含了当地人民的辛勤劳动。因此与商标同理,地理标志权的法理基础也应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保护强度应与商标看齐。等。以商标为例,虽然创造性是知识产权客体普遍具备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商标的创造性被“显著性”取代,标准明显低于专利和著作权。82参见周俊强:《知识、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基本概念的法理解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第43页。只要商标所标示的商品或服务能够与同类事物相区别,就能满足显著性的条件,不要求商标具备独创性或区别于现有图标的新颖性。可见,商标权并不意在保护商标本身所蕴含的智力成果,其目的在于保护商标所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声誉。因为商标的市场认可是经营者用其劳动换取的,未付出相应劳动的其他竞争者无权使用该商标。这是典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证逻辑。功利主义反而与商标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商标制度无意于激励公民创造各色各样的商标,而且商标必须附着在商品上使用,无须刻意激励公开,所以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激励创新与公开”的目标,与商标领域并不十分契合。
但功利主义在商标制度中并非毫无价值,它在保护公共领域、防止权利滥用、维护良性市场竞争等方面,具有无法被“财产权劳动理论”取代的独特作用。83参见冯晓青、李薇:《商标法中公共领域问题研究》,载《法学论坛》2021年第3期,第91页。在工商标记与智力成果的交界地带,往往需要功利主义来辅助框定前者的权利边界。比如实用艺术作品与立体商标的竞合情形,具有美感的部分应由著作权保护,其保护年限较短(25年),侵权打击范围较大(包括用于不相似的商品,甚至其他情形的复制);具有标示作用的部分(可能包括著作权过期后的美感部分),将落入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保护年限可以无限续展,侵权打击范围较小。专利与立体商标也存在客体竞合的可能性,前者保护功能性的部分,后者保护标示性的部分,两者的保护范围不能重合。此外,颜色商标、位置商标、著作权商标化、外观设计专利商标化等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都离不开功利主义的法理支持。
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功利主义为辅的基本法理基础,支持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在工商标记领域推行更为激进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挣脱功利主义理论下的地域性、可限制性、救济谦抑性等对制度发展的束缚。这意味着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可以进一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加强对恶意商标注册的打击,限制安全例外在商标领域的适用,提高侵犯商标权的惩罚力度等等。实践中,公认最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诸边知识产权协定——RCEP,也在TRIPS的基础上显著拔高了商标保护强度,几乎与TPP的保护水平看齐。RCEP商标制度的变革力度明显强于专利和著作权,且率先推出了独立于驰名商标的恶意商标打击制度。可见,国际社会已经深刻认识到工商标记与智力成果的区别,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的改革思路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国际共识。
(二)文化类智力成果权:“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的调和
智力成果可分为两类,一是文化类,其创造力集中体现为艺术性和美感,是能给人带来美学享受的作品,一般授予著作权等相关权利;二是科技类,其创造力主要体现为实用性和功能性,能切实提高物质生产效率或实现某种实用目的,一般通过专利、商业秘密、信息独占权等制度来保护。两类智力成果特点迥异,其法理基础需要分别讨论。
文化类智力成果权与功利主义的契合程度强于工商标记权,但弱于科技类智力成果权,更加适合“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相调和的法理基础。因为与工商标记相比,文化领域中激励创新、公开和传播的需要更为突出;与科技领域相比,文化类智力成果独占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较小,且较为可控。原因如下:首先,文化领域的表达多样性比科技领域更为丰富。虽然独占权限制了社会公众的部分表达自由,但仍有其他许多表达方式可供选择,不至于造成表达困难。然而在技术领域,在后创新者不太可能完全绕过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实现“空中楼阁”式的技术突破。其次,文化类智力成果的侵权可预见性强于科技类。在著作权纠纷中判断“实质性相似”时,需要法官以一般社会公众的视角对原作品和涉嫌侵权的作品加以比较,84普通观众测试法完全依赖一般社会公众的视角,而抽象测试法在分离出创新点之后,同样需要依赖一般公众的视角对创新点之间是否相似做出判断。参见白小莉:《如何判断著作权纠纷中的“实质性相似”》,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1531,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1日。说明普罗大众完全具备判断侵权与否的能力。但专利侵权判定须有专业技术的加持,甚至技术专家都有判断失误的可能。据统计,我国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中,被宣布全部或部分无效的比重接近50%。85参见董涛、贺辉:《中国专利质量报告——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实施情况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2期,第275页。与国家专利局相比,在后创新者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更为匮乏,判断侵权与否也就更加困难。再次,文化类智力成果较少涉及公众健康、人类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因此科技类智力成果需要的特殊制度安排,很可能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
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完善,首要关注点在于其能否满足社会的实际情感和要求。86See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3: 41.我们在抨击著作权过度保护时,也需要看到社会公众对原创者的崇拜与尊重,以及对抄袭、剽窃者的鄙夷和憎恶,完善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应当能与这种社会情感产生共鸣。因此可以预见,“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相调和的法理基础,将支持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适当提高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保护强度,并将具有同等保护强度的制度类推适用于新型作品或新型权利。比如RCEP在TRIPS的基础上新增了保护广播组织、保护载有加密节目之卫星信号、要求政府使用正版软件等规定,正是回应了这种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能忽视知识可及性、传播自由度等公共问题,须坚决抵制不合理的高强度著作权保护条款。比如TPP主张的大幅延长保护期、大肆运用刑事制裁等,国际社会尚且无法接受。
(三)科技类智力成果权:功利主义为主
科技类智力成果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巨大,其法理基础须坚守功利主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科技类智力成果权主要包括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87有观点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无期限的知识产权,与功利主义中促进知识公开的目标关系不大,因此更适合以财产权劳动理论为主的法理基础。但本文认为,商业秘密的法理基础仍须以功利主义为主。原因如下:第一,商业秘密与功利主义的另一目标——促进创新的关系密切;第二,商业秘密的权利内容具有实用性,属于一项智力成果,在分类上更接近专利权而非商标权;第三,部分以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关键技术,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因采取保护与限制兼顾的立法思路。等。当下国际社会的第一要务,乃是完成功利主义制度目标的拨乱反正,厘清“保护知识产权”与“激励创新与公开”的主次关系,将科技类智力成果的保护程度回调到一个真正能促进整体社会效益的水平。
然而最棘手的问题在于,现行科技类智力成果的产权制度究竟促进了还是抑制了整体社会效益,放眼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可靠的判断力。这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盛行有关。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保护私人财产、维护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控制在最小限度,因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88参见【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市场“不可知论”或许是一种无奈的社会现实;但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拥有了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工具,政府对市场的了解程度、监管能力依旧停留在几百年前的状态,甚至拒绝改进,显然是有问题的。私人部门作为被监管者,反而积极利用新型工具深度了解市场,并试图控制市场、干预政府决策。拥护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干预市场,通过削减政府开支使其蒙蔽双眼,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强度,而后者形成的垄断权正是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却能在西方社会屡获成功,并通过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植入发展中国家。可见,政府能力远低于私人部门,容易造成公共决策上的重大误判,使社会整体利益落空。
即便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任已经消磨殆尽,但由于没有出现更具影响力的理念,并且在既得利益者的修补和强化下,新自由主义已进入“超卖”(oversold)阶段,过去的利益结构和发展态势不太可能从内部突破。89See Boas, T. C., J. Gans-Morse, Neoliberalism. 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 Slog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44(2): 137-140.因此,尚未被新自由主义完全渗透的“外部世界”,或许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角色。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未来发展中,遏制科技类智力成果产权制度进一步向“财产权劳动理论”非理性趋近的重任,很可能需要由政治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传统范式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在充分了解市场之前,维持TRIPS时期的保护强度,既是对WTO多边谈判成本的尊重,又能较好控制制度变革的风险,可能是目前最理性的选择。实践中,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构建的RCEP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在“超TRIPS”条款横行的大环境下,RCEP提供的专利、未披露信息等科技类智力成果的保护强度,依旧基本与TRIPS持平;并首次将专利的实验目的例外引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在“保护”和“创新”之间明确选择了后者,表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创新事业本身的突出重视。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基本法理所呈现的偏离功利主义、趋近“财产权劳动理论”的发展态势,是一种由既得利益者隐秘推动的、违背国际主流意志的非理性嬗变,可能对人类创新事业,甚至对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害。对此,国际社会须引起高度警惕。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而言,一个健全的法理基础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求:一是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二是在最大程度上维持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三是基本符合国际社会通行的商业伦理与主流价值观。由于各类知识产权的特殊性,需要分别权衡其法理基础中“财产权劳动理论”与功利主义的主次,实现两者的调和与共存。未来,在不同法理基础的指导下,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各类知识产权将采取不同的发展进路。工商标记强保护、文化类智力成果适中保护、科技类智力成果兼顾保护与限制,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