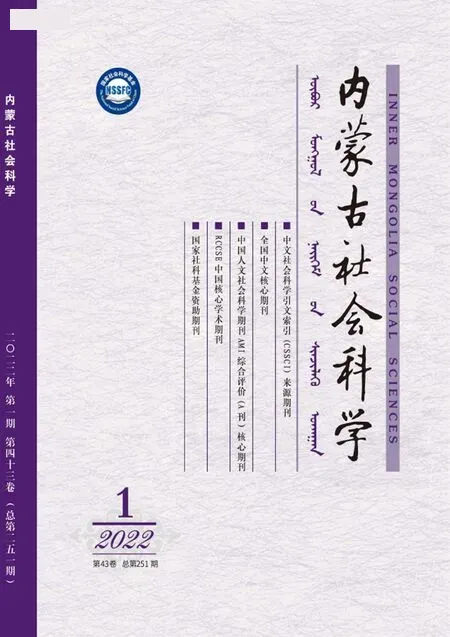治理生命:智能语言的结构主义叙事
徐亚清, 于 水
(1.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依据谱系学的视域,人工智能难以被界定为突兀出现的概念,而是内化于以智能语言为内核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某一直观技术现象。追溯其缘起,霍布斯以“力量和智慧”为代表的对于全能利维坦(leviathan)的论述[1](P.267)便包含着启蒙话语对待智能语言的看法,这是将生命存有的无风险福祉的希望寄托给利维坦的机械装置。在启蒙语境下,智能属于生命在对世俗生活世界的体验中所构筑的情境。由此形成的逻辑,应被解读为依靠智能语言治理生命的认知谱系。霍布斯以治理生命为主题的对人工智能的诠释,成为日后对智能语言的反思与转折的叙事难以绕开的对象。反思体现为以透视语言内核的方式阐释其认知方式的本真,这实质上是依靠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式的“遗产”与霍布斯“对话”的尝试。转折则体现为寻觅出离了技术加速的结构迷思之后的叙事可能性。为了寻找这一可能,福柯在其后期对马克思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即引入马克思对于治理生命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考。霍布斯、福柯、马克思构成了一条跨越时空的紧密联系的叙事主线。作为结构之场提出者的霍布斯、作为出离者的福柯和作为现实感持有者的马克思三者相融合,为透视智能语言谱系提供了认知入口。
一、霍布斯的“症候”:作为结构“褶皱”的智能
以结构主义作为对智能语言的叙事支撑,其目的在于构筑一种超越直观经验样态的认知谱系。既往一些论点以图灵式的人工智能的实证现象作为人工智能的语言起点,这种论点的内核几乎可以理解为“进化论”在晚近的遗产,它将技术现象的直观演进作为历史时空断裂式沿革的某一节点[2],但此论点所忽视的正是直观背后的语言本真。由语言序列进行追溯,便可以顺延得出追求精准、智能的现代性话语所构筑的启蒙的时空。实质上,20世纪后期在欧陆左翼中盛行的结构主义叙事,其主旨在于将启蒙学者奠基的、由自然科学的数理范式所塑造的结构体系,置于可以透视、反思的语言场中。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一方法在于解读观念之后的由语言序列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即“症候”。[3](P.14)谱系学式的回溯,是对以透视语言的方式把控霍布斯式的启蒙话语结构症候的尝试。
(一)全能与风险
细细考究启蒙认知的生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托马斯·霍布斯(Tomas Hobbes)是作为生命诉求智能语言起点式的叙事者显现在启蒙时空中。按照卡尔·施密特(Caarl Schmite)的说法,霍布斯提供了“笛卡尔机械装置”般的叙事。[4](P.49)实质上,启蒙并非某种固定化范式的概念,而只是意味着某种共通化的迈向世俗的认知,但认知本身不能遮盖世俗之场中的叙事张力。游历欧陆的霍布斯的做法,可以被理解为将笛卡尔、伽利略式的理性演绎式的语言注入了盎格鲁风格的经验之场中。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约翰·洛克(John Rock)便非常反感某种理性演绎的“赋权”,而更加强调自发经验所构成的认知结构,即对生命的“触觉”方面的体察。[5](P.93)因此,相比洛克,霍布斯进行了某种具有和解意义的说教。无论是个体生命的经验式体验,还是理性律令的体系构筑,均在霍布斯的叙事之场中共同成为其“症候”中的语言序列。
两种语言风格在智能叙事中所实现的相互和解,其原因正来自于霍布斯对于生命概念的执着。透视启蒙的内在逻辑样态可发现,将生命体验的视域仅定格于20世纪中期之后的晚近社会批判学者是失之偏颇的。世俗生命的在场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的共通主题,或者说按照福柯式风格的解读,生命在现代性认知的包裹下,第一次以语言的样态呈现在叙事之中,成为主宰叙事的某种语词,霍布斯便是这一做法的最早尝试者之一。霍布斯所要努力阐明的,其实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语言结构,生命在此结构中是在场的而非缺席的概念。对于霍布斯的叙事而言,生命应成为理解其结构的起点。唯有生命悬临于结构的叙事之上,其围绕智能语言的结构化叙事方能成为对启蒙体系的具有开辟意义的“症候”。霍布斯其实想要表达一种观念,那便是智能语言对于生命的体验来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霍布斯对智能语言的充分认可,缘起于他对全能生命状态的青睐,该逻辑可以从霍布斯论述的诸多细节中找到支撑。在他眼中,智能相等于生命的“代理人”[1](P.259)。透过霍布斯的文本可看出,智能的意义体现为生命在规避风险的世俗体验中所必须追寻的某种基本能力的载体,或者说是某种装置性的依托。依据“谱系学—现象学”的方法解读霍布斯的思考方式,那便是生命寻求智能的过程,实质上是存乎于万物之中的某种本真逻辑。为此,霍布斯对自然做出了一种深受笛卡尔启发却又不拒斥个体经验的阐释方式。在霍布斯看来,笛卡尔的“仔细追寻”风格的理性规则应在万物的运动式体验中得到体现[6](P.59),一切生命对于理性规则的遵守过程,实质上是实现个体体验与体系化逻辑相互印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体验对理性规则的明了,将使其获得某种无风险的“保全生命”状态。[1](P.327)
(二)装置与寄托
为此,霍布斯推演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逻辑,这一逻辑成为后世谱系学叙事无法回避且热衷探讨的基本对象,即对于机械装置的选择。在启蒙的时空中,机械装置被霍布斯赋予了厚望。这种装置意味着某种精准化、智能化的理性规则的显现,生命将借此实现对智能语言的皈依。透过生命选择合乎智能的机械装置的认知谱系可知,生命存有的设想在于通过对风险的本能逃逸,完成对合乎自身存有状态的理性规则的找寻任务,进而达到自明性的去蔽的显现状态。或者说,生命内在化地意识到,只有借助某种机械装置保护下的智能语言,才能为自身规避风险的、寻求福祉的体验提供全能庇护的可能性。不难看出,经验与演绎叙事在霍布斯的叙事之场“和解”之后,共同汇聚于对风险、生命与智能的阐释中,进而以利维坦机械装置的语言表述方式,奠定了智能认知谱系的叙事基础。
在为后世的福柯勾勒出所谓“智能抗拒风险”的生命景观的同时,霍布斯对于机械装置的浓厚兴趣和对生命世俗体验的说教式的语言症候,其实还揭示了另一种关键维度的逻辑勾连,即生命与智能语言之间的寄托关系。生命在选择智能语言庇护以需求复制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而并非洛克眼中的让渡。自我放弃是对驯服利维坦可能性的彻底否定,此概念强调生命要将自我全部托付给所要寻求的智能化的语言载体,换言之,是对包裹自我的利维坦给予全面信任。与洛克“不能观念到宇宙本身的位置”的想法不同[5](P.147),珍视笛卡尔的霍布斯表示,“来自人们的意志”和“来自自由”的统一方才是生命透视自我后获得的境界。[1](P.339)生命需意识到利维坦装置所代表的智能语言与福祉之间的合乎宇宙本真的关联。此关联在生命选择全能装置的、自我明晰存有本真逻辑的过程中便已被知晓,不应有放弃明了理性规则且逃避风险的“两全其美的”妄念。
从寄托利维坦的角度来看,霍布斯并不虚伪也毫不逃避。他眼中的生命进入利维坦的逻辑,正体现为在理性的明证中接受机械装置的裹挟。霍布斯认为,在风险中残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命不可能对使其自我明证的机械装置进行驯服性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因为正是利维坦使生命在对结构的归附中实现契合本真逻辑的存在状态。[1](P.327)或许相对于洛克,霍布斯的寄托观念对取舍有着非常决绝却更为坦诚的态度,他所勾勒的生命与机械装置的关系将裹挟看作是生命必须自我明证、坦然接受的过程,即生命听从利维坦结构,从而“避免监工残酷的惩罚”趋向与通往智能的逻辑相统一。既然生命必须依靠自己进入不进入便无法掌握的利维坦装置方能逃避风险、追求幸福之境,那么生命对残缺状态下无法透视的利维坦的态度应当是皈依,而不是批判和驯服。
(三)否定与保护
生命对利维坦的皈依,正是皈依智能语言接受治理的逻辑开端。在谱系学眼中,霍布斯无疑是对生命施展治理的一位启蒙之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世俗生活的叙事之场产生了浸润于生命的语言序列,这便是以治理为其逻辑的、面向生命的智能语言。按照福柯的解读,霍布斯将生命视作一种可以依托机械装置的方式、朝向被规定的全能境地进行认真操作的对象,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浸润于“身体的力量”中的结构。[7](P.191)福柯视野中以精准姿态规定并引导生命的结构内核,便是霍布斯维护的利维坦概念。这一概念曾长期在实证主义范式中被简单化地阐释为权力集合体维度,但单一层面的国家概念无疑是对霍布斯背后持久在场的机械装置的阉割化解读,从而使智能语言的缘起之场显得晦暗不明。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布斯的语言症候支撑起了追求世俗化、直观化智能技术成果的全部的启蒙认知体系。
治理生命的主题,正是在霍布斯围绕风险、生命与智能的利维坦教诲中产生的症候。但霍布斯眼中精致的语言说教无法阻止其后世的喋喋不休的争论,此争论的聚焦点在于对生命的否定与保护。霍布斯口中生命自我放弃的、进入机械装置的逻辑,却成为后世社会批判理论叙事无法释怀的对生命的否定性描述。按照罗伯特·埃斯波西托(Robert Esposito)对共同体的论述,利维坦其实意味着某种免疫(immunity)的内涵,为了实现对病痛般风险的祛除,生命必须接受“豁免灾害”的免疫治疗。[8](P.84)副作用般的否定性与生命在利维坦庇护下的自我生产相互捆绑已成为启蒙之场中生命存有的常态。但问题在于,生命接受免疫的方式是否一定是一种皈依的姿态?当20世纪后期社会批判叙事引出“理性成为暴君”的论述之时[9](P.17),其否认的正是霍布斯力求构筑的皈依性逻辑。
依据谱系学的观念,生命福祉是一个被智能语言进行强行规定的伪命题,这使得霍布斯在智能语言的认知谱系中逐渐声名狼藉,但以福柯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说的兴起与演化并不意味着洛克叙事的重新复兴。遵循福柯的逻辑,洛克所认真设想的反抗的情形或是使授权对象“解体”的命题毫无意义,因为以保护为名、对生命施以“惩罚”的结构不是可以从内部给以平衡、加以驯服的。[7](P.191)福柯的反思性叙事起点不是洛克,而是霍布斯。在福柯的眼中,霍布斯是“保护与否定相互捆绑”逻辑的诚实描述者,此逻辑为福柯所完全赞成,形塑了批判性叙事的起点。令人惊奇之处在于,通过对霍布斯的攻击,福柯居然与霍布斯达成了某种空前的一致性,那便是进入与自主无法在皈依利维坦的真实选择中真正兼得。从该角度看,福柯与霍布斯反而成为共在于智能语言谱系中的“好友”,这着实是一个颇为讽刺的局面。
二、福柯的遗产:生命权力的“出离”
以承认利维坦无法驯服的“另类友谊”为前提,福柯实质上是进入了霍布斯所开创的认知之场来解读其教诲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霍布斯式症候的维护者。越是侧重于以透视语言规范的方式阐释装置结构的无所不在,越是说明霍布斯“利维坦不可驯服”教诲的无可辩驳性。对于机械装置裹挟生命这一议题,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愿意承认,而在于是否愿意接受。从中可看出,霍布斯既代表了福柯在确立自己叙事之时所反对的一切,也为后者提供了某种叙事之元,即生命进入结构乃是启蒙之后世俗生活的本真样态。[10]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毕生致力于将范式结构视为“梦魇”的福柯获得了“反对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这一略带调侃性的称谓。[11](PP.14~15)在霍布斯教诲的影响下,福柯早已放下了所谓驯服的想法,其毕生为智能语言留下的遗产可谓承认结构不可驯服后的“出离”叙事。
(一)言说与他者
“出离”的本真思路可被归纳为承认结构之下的反抗性叙事,福柯力求反抗的乃是进入和接受结构作为生命本真体现的逻辑,承认霍布斯所述的生命进入利维坦装置的样态,却又将利维坦的语言能指与其对应的全能状态的所指加以分离。换言之,由霍布斯所开创的以利维坦为内核的结构主义叙事所描绘的智能只是一种进行中的语言。由于不愿接受保护与否定相互捆绑的霍布斯式教诲,智能语言与生命福祉的关联被谱系学加以切断,且以张力的方式呈现在启蒙的认知之场中。如果说在霍布斯眼中豁免机械装置达到全能的幸福之境是一种妄念,那么在后世的社会批判叙事中智能语言所规定的幸福本身便是一种虚妄之说。对于霍布斯的症候而言,福柯的论述更带有一种略带悲观的拷问,那便是与智能的语言规范的确立是否以“宰制”言说为前提。[12](P.41)
在承认生命已置身于利维坦装置这一真实境地的前提下,福柯试图将生命的存有样态从皈依利维坦以实现理性自明的语言规范中剥离出来,这一尝试可被理解为出离。所谓出离,是以将利维坦的渗透视作裹挟生命的现象为前提,进而思考生命的自我明证的历程与利维坦相互割裂的可能性。实质上,福柯接受霍布斯症候之时已接受了一个令自己非常痛苦的前提,那便是对生命遭遇的窘境的思考范围不能局限于探讨所谓独立体验的可能,更有甚者,生命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言说主体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按照福柯的理解,生命早已成为在语言结构渗透下被掏空的晦暗不明的概念,主体的概念在利维坦的裹挟之下显得不值一提。按照他的说法,言说意味着尝试以一种语言规范之外的“真实的、主动的、无限”[13](P.237)的方式,对结构掌控生命的具体样态进行内核化的拷问。
通过他者言说的出离方式,福柯力求寻觅一种可能,那便是存在不被智能语言裹挟的叙事。被誉为“法国尼采”的福柯期待一种直面生命本真内核的发声,以证明本真不需要通过理性语言的方式获得显现。按照他的那句为人熟知的诗句便是——“我无数次的打着灯笼,寻觅,在这正午时分”[12](P.43)。为此,福柯不止揭示了被利维坦用“保护”式语言消解的“另类”存有,他还从反向的角度再次阐明了为霍布斯所坚持的立场,用霍布斯的症候去反对霍布斯。此立场在于,创设智能语言谱系的利维坦装置以“规定”与自己相斥的他者为前提得以建构,即生命在进入利维坦之后必须接受放逐他者言说的可能性的教诲。在智能语言的全面裹挟下,他者言说的叙事只能苟延残喘,但不能由此忽视他者言说对于启蒙以来结构主义认知的某种前提。换言之,结构规定他者的原因在于对他者的重视乃至恐惧。
(二)范式与语言
终其一生,结构对他者进行定位的语言样态正是萦绕在福柯叙事之场中挥之不去的主题,这可以解释福柯为什么如此认真地思考范式背后的语言问题。在福柯的视域中,范式等同于利维坦装置结构对于启蒙以来现代性认知体系的话语输出,范式即是以利维坦为内核的结构语言本身。尽管利维坦是敌非友,但霍布斯的言论几乎像是魔咒一样,预言了利维坦对于通往世俗生活的现代生命的意义。该意义可以理解为,以范式的方式为世俗生命提供了渗透于存在之场的、自我宣称为通往智能之境的规定性的语言,按照福柯的理解便是规定他者之后的文明话语。进入利维坦等于对理性规则的文明话语的明证,进入之后对利维坦的皈依便体现为接受以智能语言序列为特质的范式。对于范式而言,福柯将其视作透视利维坦之时必须拆解的对象,但从未否认其作为语言本真的凸显乃是生命之场的基本现象。
上述逻辑便是福柯在对待智能语言之时持有的与托马斯·库恩(Tomas Kuhn)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不能由此否认福柯对范式语言的浓厚兴趣。众所周知,库恩试图揭示范式语言所指的认知本体的演进逻辑,按照库恩的说法便是聚焦于“应用范围和精确性”[14](P.24)。将智能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对应的尝试正是福柯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从遗留的文本来看,福柯对康吉莱姆的青睐和对库恩的反对见诸于其论述。思考范式对人类通往智能之境所给出的治疗方案,其前提不是将其视为本体,而是要透视其宣称可治疗生命的语言本身。福柯非常喜爱透视的谱系学方法,认为这样做可以真正理解霍布斯,即克服由利维坦教诲导致的眩晕感,使所谓全能的机械装置因范式的自我肢解而“现形”为语言。“语言只剩下语言”,成为福柯想要对智能认知谱系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换言之,以范式为核心在自我肢解之后将使利维坦被超验还原为可探讨、可反思的语言序列。从中也不难看出,库恩与福柯都应被视作霍布斯在认知谱系中的好友,但就立场而言,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更具有“诤友”特点,即以他者言说的主体姿态进入霍布斯的利维坦语言结构之中,怀抱着拆解后者的态度对霍布斯无可替代的地位进行了反对式的肯定。依据福柯的逻辑,库恩的论述除了复刻对霍布斯症候的记忆外毫无意义,其终究是以实证范式俘获康吉莱姆对语言结构的叙事,实质上却放弃了生命自我去蔽从而出离结构的可能。相反,唯有康吉莱姆的“标准并不存在”的观念才有可能构成一种出离结构的希望。[15](P.41)
(三)惩罚与治理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语言何以令人所信服,何以将自我与智能相挂钩?与霍布斯一样,福柯承认进入利维坦,或者说接受范式的渗透化“治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代性的本真现象。但这种接受并不意味着霍布斯所说的排他性的利维坦装置与生命自我明证等价挂钩,而是生命必须接受智能福祉“现形”后的光秃化,浸润于日常的强制性语言序列中。更为确切地说,生命作为一种被现代性所关注、所保护的对象,既在利维坦结构的诞生中得以凸显,又因为尊崇利维坦的范式而只能成为语言,这是作为“晚近事件”的人对其指涉的语言的开端之处便必须接受的宿命。福柯认为,利维坦的功绩不是让生命通过进入自身而获得明证,而是让生命在范式的关怀性治疗中放下对强制的惊恐,相信利维坦所教育的明证逻辑。然而,支撑生命自愿相信这一现象的力量仍是强制。
为了诠释智能语言的控制性,福柯找到了惩罚这一语言的坐标。在晚年的岁月中,这位与霍布斯对话的学者一直以惩罚为入口,去思考利维坦何以形塑智能认知谱系的主题。实质上,福柯所理解的惩罚不能仅被视为某种细节意义上的所谓监控机制,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库恩眼中的直观经验的论断。令晚年的福柯最为纠结的,仍然是霍布斯症候所揭示的生命对自我明证方式的认知之道。利维坦结构生成之后的惩罚序列的本真内核,是一种获得道德合法性的劝说式的语言遮蔽的控制力。依据福柯的逻辑,或许洛克的欺骗之术也来自于此。因为洛克对驯服结构的所谓“协定”的倡导,无外乎是授权给结构之后将享有福祉的劝说和在告知生命所谓不能离开结构的理由[16](P.211)。所以,相比霍布斯直截了当的“否定与保护”的论证,洛克更注重用某种合道德性的语言放逐惩罚的本真。
本真不会真正消失,而是在常态中缺席,在例外中在场。放逐之后所造成的只是惩罚在缺席中主导在场的逻辑。常态下的只是合乎尊崇利维坦装置的道德语言的治理,于是,福柯进而提出了治理术(art of government)一词。治理术的经验指涉,正是福柯后期不懈努力以探讨的所谓安全机制、领土控制与人口调节等浸润于日常的实践活动。这些在现代世俗生命看来习以为常的现象并非智能与道德的合体,其终究符合的是被道德语言维护的、惩罚悬临下的、“用智能的语言遮蔽被迫的真实境地”的这一逻辑,因而治理只是基于日常实践调教生命使之相信智能语言的活动。福柯认为,需研究的主题在于“治理的实践活动”背后受制于语言的“概念化”逻辑。[17](P.4)霍布斯眼中的通往智能福祉的利维坦笼罩下的日常,在福柯看来乃是以范式为认识论前提、以治理为坐标的治疗他者的绝望之巅。
三、马克思的可能:转折的生命现象学叙事
出离源自于智能结构治理下的他者言说的绝望,但绝望不会随着所谓出离叙事的确立而退场。相反,当直观经验被视为进入智能语言序列之后的配置对象时,现实感的晦暗不明反而成为利维坦挥之不去的原因。这其实是一个悖论,驱逐利维坦不等同于驱逐经验。如果说霍布斯的和解是以尊崇智能语言为核心,那么福柯在晚年力求开始的和解则是要以驱逐前者后的生命体验为核心,以缓和批判性与现实感的紧张关系。为此,福柯将视野转向了除尼采之外法国左翼叙事无法回避的另一个对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对治理术的阐释中,福柯便展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政治经济学这一原本被谱系学视作利维坦语言结构外化而成的实证范式的语言,反而被福柯找回。
(一)谱系与批判
对于福柯来说,转向政治经济学既是一个让谱系学面临背反式危机的抉择,又是保持对智能语言阐释的现实感不至于消失的唯一方法。终其一生,纠结于智能认知谱系的福柯无法割裂自己与马克思之间的藕断丝连,因而在其身后被冠以“尼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实质上,以福柯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在拒斥经验维度对谱系的“吞噬”之时,均无法抗拒马克思身上的某种魅力,因为马克思对于启蒙认知的超越性思考往往被反抗智能叙事的左翼学者视为某种批判性的缘起。这是马克思对后世“超越当下”认知的与霍布斯一样的“幽灵”般的影响。[18](P.4)对于治理术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谱系学叙事之场的坍塌性的可能,此种坍塌性正是来自于对利维坦结构的、与霍布斯纠缠不休的态度。
拆解性的叙事谱系,何以置身于利维坦所指的紧密调控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治理术现象之内?换言之,进入吸纳经验的利维坦之后,谱系学叙事却将一切的经验视为与实证范式勾连的语言要素而处置,利维坦作为批判的对象也将消失于叙事之场,这其实是福柯所不能承受的代价。利维坦一旦变得晦暗不明,认知谱系也将随之消失,这正是来自于福柯对霍布斯的某种变相认可的态度,即进入利维坦是不可避免的生命趋向。无论是否承认自我明证与进入利维坦在生命体验上的统一性,但现实感的消失无疑意味着认知的致盲。福柯所面临的实则是对利维坦的令人绝望的依赖,此绝望在于明知利维坦已被还原为语言,却无法将现实感从语言中拯救出来。故而敌意般的“居住”于利维坦的福柯,在放逐范式概念的同时早已将霍布斯已实现的和解重新撕裂。
与马克思和解,其实意味着找回被马克思以后左翼叙事的所谓“生产主义”的叙事。对于智能语言而言,围绕生产、分工等概念的经验要素反而是被欢迎的对象。福柯在对待治理术的问题上,逐渐表露出以生产拯救现实感的努力,但两种认知之场的撕扯同时也暴露无遗。按照福柯的阐释,治理术的语言逻辑需基于“生产成本和需求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加以论述。[17](P.33)从中不难看出,福柯一方面并未放弃让利维坦悬临下所有被尊奉的学科范式现形为语言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努力给予经验以不止步于语言的配置。或许在福柯看来,唯一的和解方式是让经验作为一种外化的直观现象显现于智能认知谱系中。毕竟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亲昵,所指的现实范畴在马克思所言“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被保留了下来[19](P.191),不至于沦为鲍德里亚口中“不可能存在之真”的幻象。
(二)结构与现实感
让福柯等人长期不敢完全拥抱马克思的原因正可被理解为对待智能语言的立场,他们无法厘清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可以被追随的“进入利维坦后将其拆解”的先驱、最青睐机械装置的启蒙之子。毕竟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描述并存于其文本之中。[19](P.191)如果从恩格斯的角度理解马克思,那么智能意味着是可以被认可的、进步化的认知方式。按照恩格斯的阐释,“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是需要被准确认知并成为行动基础的维度。[20](P.387)长期以来,以福柯为代表的左翼叙事对待智能语言的态度被几乎认作为“上层建筑的复仇”。[21](P.98)在福柯看来,进步叙事的建构与霍布斯所强调的理性自明如出一辙。于是,生产曾经被降格为霍布斯症候的勾结者,此后又因语言的唯一化而被福柯重新唤起,导致的终究是认知方法上的危机。
对于语言,马克思有着明确的界定方式。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他人存在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2](P.81)。在左翼叙事的眼中,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是以聚焦生产的叙事者的身份出现于社会批判之场的,对生产维度的青睐,被谱系学认为是重新将经验要素请回以尊奉范式的表现。左翼叙事担心的实质是马克思对利维坦采取的是表面批判实则维护的态度。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利维坦概念背后的认知错误实为“头足倒置”,但借助经验的叙事尝试在左翼叙事看来几乎等同于倒置之后又重新倒回,其分殊只是康德对经验的青睐与黑格尔尊奉本体之间的差异性而已。左翼叙事认为,马克思对“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兴趣表明,马克思本人是用经验重构本体,然而未能突破利维坦的认知体系。[21](P.56)这等于是用一只手拿起了另一只手表示要丢掉的东西,但结构作为认知的元叙事本身却并无改变。
若要探究马克思对于机械装置的态度,便需要关注1845年前后马克思社会批判叙事的逻辑演化。对于欧陆左翼叙事而言,以阿尔都塞所倡导的断裂论为代表的观点,即1845年后由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之场的论述,可以解释谱系学对马克思的态度。仿佛马克思代表了撕裂生命的自我明证与智能语言结构之间关系的叙事在确立自身论点之时所要反对的一切,但马克思自身的论点仿佛又使得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所担忧的逻辑难以自洽。马克思曾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他认为批判的超越意义应以现实感厚重的“地上”为前提,实现“从地上升到天上”。[23](P.30)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释的代表性的观点。此观点表明,将马克思等同于对机械装置加以维护的实证主义范式成员的论断强行驱逐了马克思本人从未放弃的批判性,且对马克思在认知方法上统合批判性立场与经验因素的努力视而不见。
(三)叙事与方法
基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可看出,谱系学对马克思的看法似乎只能是用自身的认知之场强行配置了属于马克思的语言,但放逐了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精髓所在,从而也导致了自身在撕裂了霍布斯用以和解的利维坦词汇之后难以寻找到现实感与批判性之间共融的桥梁。对于机器马克思曾表示,其应被视为“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真实境地的显现。[23](P.75)实质上与后世的福柯一样,马克思同样选择了一个逻辑前提,那便是透视的前提乃是进入,但进入之后所能观察到的并非只有语言。马克思与福柯的重要区别在于如何透视利维坦的方法,是将现实感还原于语言,还是透过语言看到现实感的可能性。很明显,福柯选择了前者,马克思选择的则是后者。在马克思眼中,语言的唯一化几乎等同于在智能语言的渗透下拒绝用眼睛直面机械装置,谱系学的透视将不复可能。
既然依据谱系学的逻辑,叙事的使命在于透视生命在智能认知谱系中存有的本真境地,那么从该角度看马克思并未违背谱系学的意愿,反而实质上承担起了福柯所要完成的命题。在霍布斯那里被认为是用生命的自我明证的基点统合了理性规则和世俗经验的利维坦装置,在马克思进入之后被接受的是重构的命运。马克思所做的重构的努力是一种对于认知方法的重新确立,而并非福柯所说的在“坚固无比”“严格而未经反思”的机械装置语言中的接受晦暗不明的宿命。[12](P.17)相反,一种全新的和解得以确立。此和解的关键其实不在于霍布斯想用某种基点支撑起结构的逻辑,而是使现实感终于不被结构所俘虏。因为现实感终于不再是霍布斯那里需要被结构引领从而获得明晰地位的对象,其自身成为叙事难以撼动的基础,因而柏林所说的马克思成功实现了“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样一个论断并不为过。[24](P.265)
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确立一个属于马克思的、阐释治理生命主题的生命现象学的叙事?在解决了所谓对马克思的“生产主义”的语言律令的怀疑之后,一切可以变得更加豁然开朗。或许也可以这么理解,欧陆左翼力求理解的马克思的所谓症候,应在于以脱离基点逻辑的方式让现实感不再受制于任何语言结构。基于马克思的逻辑,福柯将现实感化约为语言序列的排列游戏的论述是一种被福柯自己所讨厌的语言专断,那是因为放逐所有经验的叙事方式本身便形塑了一种结构。福柯与霍布斯的“好友”关系或许又有了新的一层意味,那便是双方都用各自认为合理的语言结构或是佐证进入自我明证的必须过程,或是以现实感的危机来反面印证利维坦的不可出离。马克思的到来更多的是一种方法上的拯救。脱离现实感的语言结构的位移早已令人生厌,马克思的作用或许正体现为回归和解之后的超越性的可能。
结语
将智能认知置于启蒙以来的思想史来进行总体考察,旨在表达一种反对单向的直观经验的进化论叙事的叙事立场,即对智能语言认知从实证范式中自我拯救出来,智能不等同于某种断裂性的“时代”。就认知谱系而言,智能在启蒙叙事中并未实现经验叙事所说的蜕变,而处于“一组或一系列数字符号”般的无限循环语言序列中[25],循环的起点来自于霍布斯所倡导的以治理生命为主题的利维坦概念。在此主题下可以形成的共识是,阐释启蒙以来的学者围绕智能语言所构成的叙事关系,其坐标不应只局限于直观性的智能词汇,而是来自于智能语言的机械装置内核。在利维坦渗透之下的、追求智能之境的范式化的认知成为悬临于启蒙学者叙事之场上方的挥之不去的语言症候。霍布斯、福柯与马克思在实质上均进入了以利维坦装置渗透下的世俗生命的存有之场中,也共同形塑了智能语言的认知谱系。霍布斯是语言结构的提出者,福柯是语言结构的反思者,马克思则代表着面向现实感进行转向这一谱系学反思尚未完成的命题。
其一,霍布斯为智能语言提供的难以回避的教诲在于,生命必须进入利维坦结构,治理则是生命必须接受的存在之场的本真现象。无论是将结构视为生命自我明证的标识,还是将结构指责为吞噬生命真实体验的怪物,进入之后接受治理成为无可辩驳的语言症候。生命被治理是霍布斯不同于洛克的核心逻辑,这一论断成为霍布斯对智能认知谱系的核心性贡献,其实质上帮助了生命从洛克的幻象中解脱出来,认识到所谓驯服结构无疑是一种生命的妄念。对于利维坦结构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依赖与掌控并行不悖的境地,这只是一些启蒙学者用语言勾勒的符号而已。在方法论上,霍布斯构筑了生命在世俗经验的获取中进入利维坦结构以获得自明的认知入口,依托智能语言的世俗样态实现了经验与演绎的和解。与之同时,霍布斯忠实地让智能语言渗透于生命的治理样态得以呈现,为反思提供了明晰的对象。以利维坦装置为内核,智能语言结构正式确立,此结构将生命语词作为其合法前提,开始了生命政治眼中的以“保护与否定”为特质的治理活动。
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说,福柯用反对霍布斯的方式达到了霍布斯当初力求维持的语言功效,即再一次承认了以利维坦结构为核心的智能语言对生命之场的渗透。在将利维坦视为叙事敌人的同时,福柯与霍布斯实质上在智能语言的叙事谱系中成了联合论战的好友。除了承认进入利维坦是世俗生命难以抗拒的本真现象之外,福柯对霍布斯语言功效的变相维护还具有一层讽刺性的原因,那便是出离叙事在逻辑上的不自洽。终其一生,无论是探讨疯癫、认识论还是治理术,福柯遵循的核心主线可以被概述为生命是否有可能遵循出离智能语言结构的他者逻辑进行言说,但随之导致的便是方法论的困境。霍布斯与福柯之间围绕智能认知谱系的叙事张力正是来自于结构与现实感在生命现象中的撕扯不清,当所有的经验被“现形”为语言加以放逐之后,作为世俗维度的利维坦也将成为不可认知的景观,出离的命题将因为现实感的消失而自动消解,与之消解的甚至还包括生命体验的可能性。撕裂表现为使经验不复可能,且使反思的演绎变得飘忽不定,这表明福柯有可能在不亲近马克思的前提下,亲自摧毁了自己力求构筑的出离的叙事。
其三,对于智能语言的认知谱系而言,霍布斯与福柯在认知方法上形成了“和解—撕裂”的关系,但马克思的“回归”预示了认知方法在重返和解中的超越性可能。谱系学的语言能指在自我执念的放逐实证之时也放逐了本该属于生命真实体验的全部的经验的要素,也就祛除了现实感的可能,这便使谱系学无法完成透视智能语言如何治理生命的命题。实质上,既然利维坦的语言能指无法转换为厚重的现实感基础上的智能之境,那么透视智能认知谱系之后思考生命存有之场的使命只能是将叙事交还给现实感本身,该逻辑应是晚年的福柯想要有所青睐但最终若即若离的对象。马克思的认知方法在福柯那里刚刚开始就变得飘忽不定,随之留给智能认知谱系的便是现实感自身的眩晕。对谱系学而言,难以克服的执念在于经验性的因素总是会被担忧为填充结构的语言要素,所以将属于生命的现实感解放出来显得尤为迫切,因为存在于智能语言的渗透之中的是生命体验的真实之境。也正是因为真实之境难以被叙事所放逐,因而马克思主义终究获得了重构智能语言认知谱系的可能性,这是生命政治叙事不敢完全承认却又无力辩驳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