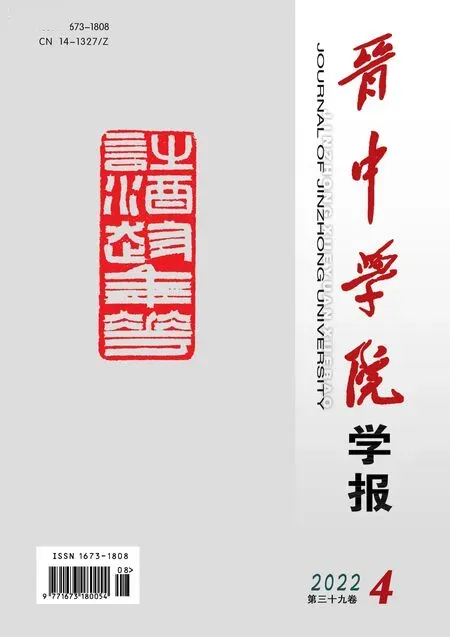论《铁木前传》次要人物及其成因
钟海林,柏雅萌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也是塑造人物的艺术。”[1]140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仅要给读者留下亹亹不置的故事内容,更要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家进行创作时,既遵循生活的逻辑,又不乏飞扬的个性。读者置身于小说这方平等开阔的天地中,既感受着人物的痛苦与欢欣,又照射出自己应然的模样。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铁木前传》是孙犁的代表作之一,在十七年文学中居于卓异地位。新时期以来,针对《铁木前传》学界涌现出一批具有学理价值的文章(1),尤其对人物形象的研究明晰透彻(2)。笔者经过梳理后发现,此类评论文章的视角多集中探讨满儿和九儿这两位神采斐然的女性,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一则,详细论述单个人物形象。二则,比较研究。满儿和九儿、满儿和其他女性、孙犁与其他作家(赵树理、沈从文、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三则,将小满和九儿归入女性群体(农村妇女、另类女性、先进女青年......)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对孙犁作品中“男性世界”和次要人物的观照如“蜻蜓点水”,即使偶见评论,也多穿插在以论述女性形象为主的文本中,或借助其反衬女性世界,或作为符码来阐明文章多义性。研究状况不平衡,既不利于描摹现实的总体风貌,也不利于囊括小说丰饶多义的主题意蕴。重读文本,笔者发现《铁木前传》中的次要人物具有潜在的探究空间,关注并阐释此类形象,对有效弥补研究缺口,把握孙犁小说中的人物世界,认知孙犁艺术风格,梳理孙犁与革命政治的关系颇有助益。
一、“不可小觑”的次要人物——杨卯儿
(一)“较早现身”
孙犁是一个敏感多思的作家,他在旖旎的水乡风光中氤氲着多姿的人物世界,尤以塑造女性形象见长。《铁木前传》中美丽聪慧的满儿和质朴稳重的九儿,历来被评论家和读者们津津乐道、默默涵泳,而次要人物(尤其是男性角色)则遭到忽视。现实人生是由形态各异的男女共同构建的,艺术与现实互为表里,相伴而生。若评论文章只观照某一性别,显然是不符合生活真实逻辑,且有损小说审美意蕴的。
人物的出场设置与作家的叙事动机、修辞意图密切相关。《铁木前传》中次要人物十分庞杂,杨卯儿就是其中一位。全书共二十章,孙犁安排他在第八章正式出场且共出现八次。杨卯儿较早出场,可尽快介入叙事,充当引出下文的契机,并使自我形象在接连发生的人事中不断被塑造、扩充、丰富。
孙犁在第十一章用插叙的方法对杨卯儿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刻画。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还运用暗示的语言,虽未正面描写杨卯儿,但读者在阅读与六儿相关的文字时会自觉地联想到卯儿。比如,六儿做生意“挣不下钱”却多得姑娘们喜爱的“小贩形象”,正好与后文副村长口中描绘的卯儿形象如出一辙。这两人之间似乎产生某种奇妙的暗合,甚至呈现出“新老赓续”的生命闭环。读者会自觉地发出“年轻的六儿是否会走上和杨卯儿相似人生道路”的深思。
卯儿还出现在六儿、满儿、四儿口中。比如,六儿手里拿着鹰在沙岗上行走,被锅灶看到后,他与四儿的问答颇有意味。面对锅灶的提问,四儿说,六儿“和杨卯儿为鸽子吵了架,仇大得不得了。经黎七儿把三个人拉到城里吃了一顿饭,两个人又成了好朋友,把鹰借给六儿了”。……“我还听到一个故事,杨卯儿现在成了黎大傻包子房的老主顾,每天晚上都要吃饱的。黎大傻的老婆对他说:卯儿哥,你只吃得好、穿得好,还不能算是完全翻了身,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可是你得请请我。这样,杨卯儿就在城里请了她一次。”[2]577两人的问答不仅突出了卯儿“游戏人生”的姿态,表达了锅灶和四儿惊讶、疑惑的态度,而且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为后文卯儿“出走”埋下伏笔。
(二)“意蕴复杂”
孙犁将自己美好的情感投射在小满儿身上,她与以往温厚淳朴的水生嫂们相比,呈现出别样风貌。小满不能被机械地定义为某种女性类别,也不能被粗略地划归到正面或反面人物阵营中。中国的文学长廊中能出现这样厚重开阔、复杂多义的人物形象,一部分得益于书中其他人物的对照烘托。杨卯儿就是其中一位。
“鸽子”这个意象在文中反复浮现。它是衔接人物关系的桥梁,卯儿因为“找鸽子”才遇见满儿,“鸽子”也隐喻着人对自由的憧憬。作者通过简笔勾勒,不仅刻画出卯儿爱慕女性的情态,也使满儿泼辣直率、深谙“女性法宝”的形象如在目前。孙犁选择在此处顿笔,没有继续展开二人的故事,而是笔锋一转,以插叙的形式引出干部和副村长这两个次要人物出场,并且在干部出场前,对卯儿的形象做出了简短的叙述。这样做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提示卯儿的身份信息,另一方面,对小说整体叙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叙事的突转,增加了文章的悬念,消减了审美的疲劳,是作者独运匠心的体现
首先,干部与卯儿经过了短暂的相处。卯儿先是把炕的“寒带”让给干部,二人又因水壶“漏与不漏”发生争执,最后干部离开。杨卯儿充满“乖戾气”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确需要改造。不过,他主动下“逐客令”的行为,是值得玩味的。普通村民对高级干部应该像黎大傻一样局促不安,充满敬畏,杨卯儿却与众人大相径庭。卯儿这样的态度是顺从本心、性情使然?是水壶的意义非同寻常?还是作者在此处想显露何种意识?孙犁再次顿笔,直接让干部去找副村长。珍惜水壶的缘由、干部和卯儿的故事都未延展,给读者留下遐思的空间。
其次,杨卯儿的形象由单薄变得丰满,由平面变得立体,得益于副村长对他出身历史的详细回忆。他俩年轻时一起做买卖,卯儿熟悉西山地理。“每年,他都是吃净赔光才肯回来的。他赔光,不是好吃懒做,也不是为非作歹,只是为了那么一股感情上的劲儿。”[2]560我们不该对杨卯儿身上的落后成分做过多苛责,而忽视了他对感情的执着和较强的工作能力。杨卯儿喜欢漂亮女人,刮风下雨都守在人家门口。今年他又遇到一位,蹲守时女人的丈夫正巧回家,把杨卯儿赶出来,卯儿和壶都翻下山去。头破了,水壶裂了。水壶是“女性幻想”的隐喻,卯儿对水壶的珍视一如他对女人的执着,水壶的裂缝一如他美好幻想的破碎。“爱情是一种自然而美好的人类情感。”[1]147杨卯儿“对感情的劲儿”是想引得异性关注,是正常的生命诉求。文中还提到卯儿觉得女人对他有意思,只是她男人不愿意。这虽包含自我安慰的成分,但能否做如下推想:这个女子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呢?这是那个时代妇女普遍的生存困境呢?
副村长和杨卯儿这对曾经一起做小生意的朋友,如今身份境遇如此悬殊,就像黎老东和傅老刚这对老朋友,阶级地位转变导致友谊破裂。孙犁的审美偏好使他在叙述时多呈现平缓淡雅的情调,不过度强调阶级分野,可一旦涉及道德评判和伦理审视时,孙犁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又让他踟蹰难决。一方面,他必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描写;另一方面,他又在思考,俯就时代伦理所做的价值判断、阶级划分是否合乎真实逻辑。孙犁的文化个性中有忧郁的气质,喜欢描摹破碎的美感。无论是家庭构建中角色的缺席、人际关系中彼此的嫌隙,还是具有象征性物品的裂缝,抑或是清朗俊逸氛围中流淌的孤独感,都给读者世事难以完满的遗憾和唏嘘。他每一处情感的倾吐,都是经过审慎考量后的呈现,从未逾越政治和革命的规范。那么,他缄默不语的背后想要映照何种幽深的光影?
至此,插叙结束,满儿和卯儿的故事继续展开,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通过相互映照,形象都更加鲜明。小满“惊艳式”地出场,使杨卯儿的“情感天平”偏移,他仔细打量着“一生中都未曾见过的美丽女子”,倾听着她的斥责,像宗教徒般接受天谴......杨卯儿是一个“痴情”的光棍儿,他长期处于情感压抑、求而不得的苦闷中,看见“美丽如花”的小满,必然会产生喜爱之情,但他并没有将爱慕延伸到生理层面,只是内心的愉悦和精神的倾慕。因此,我们不能把正常反应与个体德行强行勾连,也不该把他和好色之徒归为同类。况且,孙犁在文本中只是尽力地展现人物多重复杂的性格特征,“却并没有为之附加更多道德层面上的意义”。[3]
杨卯儿借给六儿的鸽子意外死亡,他要去找六儿的父亲黎老东说理,却没经住六儿的奉承,反倒帮六儿劝说黎老东不要生气。此处,孙犁设置了杨卯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我评价。他认为自己没有丢过脸,是个“正直”人;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是因为命里穷苦。杨卯儿虽然真心地帮助六儿劝解黎老东,但依然有缺点需要改正。他所谓的“正直”是定位不清;他“命里穷苦”是无力改变现状而产生的消极宿命论思想;他指出六儿的“荒唐”也是自己行为的折射。孙犁通过正侧面结合、他人和自我叙述融合的手法,意在还原杨卯儿“荒唐中有点可爱”的全貌。杨卯儿身上的缺陷没有让我们产生厌恶之情,反倒是集体中个人情绪无法自由言说的脆弱与渺小,为他濡染上悲剧的因子。读者在“忍俊不禁”中又不免“哀矜同情”。
二、“丰饶多姿”的次要人物群像
重读《铁木前传》,因发掘到杨卯儿形象的价值,由此延伸至对大壮、黎七、锅灶、四儿等一批男性形象的关注。这些男性角色组成的次要人物群像,搭建出与黎老东、傅老刚“老一辈”相对应的青年世界,反映出两代人在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上的某些差异。
作为“凝视者”的青年男子们。他们为眉眼灵动、容光焕发的小满所吸引,凝眸注视着她;却又为避嫌,不帮小满推碾,也不愿去小满家劝她改造,只是冷漠的“看客”。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构造本就有差异,男性力量强于女性,为女子提供必要的帮助实在是举手之劳,在文本中为何被演绎成“推推搡搡”的避嫌之势?作者安排这类青年出场,意在揭示传统乡村伦理仍然有巨大威慑力。此种语境下,人们必须归顺于秩序的要求,男女之间似乎只有一种相处模式,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也必须在同一轨道运行,否则就会遭到诟病。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是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巨大的路障。青年男女们在此间涉渡,因无力改变现状,就逐步衍生成“异化”的关系指向。假若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包容,精神世界更加自由,那么两性之间会有更多的坦诚相待和多元沟通。
作为青年团的典型代表四儿和锅灶。四儿追求自身进步,认真对待团里工作,尤其是关于“人生观”和“社会最能改造人”的论述,体现出他对主流意识的遵照和维护。锅灶,是作者的“代言人”。在叙事的过程中,“叙述者没有直接跳出来进行评判,而是把叙事干预的权力分化在各个人物角色身上,通过他们的言行来掌控叙事进程,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4]比如,“‘你认为我们一定打光棍儿吗?’锅灶说,‘据我看,那可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哩!’”[2]556“......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是我们走对了哩,还是他们走对了?”[2]578“红彤彤”的四儿们一定是光明的前途?“漫悠悠”的六儿们一定是阴暗的未来?孙犁借锅灶表达质疑,这是他逸出主流话语的试探,但究竟如何,孙犁一时无法作答。于是通过四儿的回答按住“轻佻”之流,回归时代大潮。四儿说,“人怎样才能觉悟呢,学习是重要的,个人经历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影响”。[2]579
作为“妻管严”的男性们。孙犁在整齐划一的革命年代,发现了被政治有所消隐的个人诉求和婚恋缺失,因此《铁木前传》中的男性角色常以“光棍儿”的形象出现,黎大傻和大壮是为数不多有妻子的男性。“光棍们”在残缺的家庭环境中感受不到温存;“大壮们”即使有妻子,在压抑的环境中也变得卑微懦弱,丝毫不见男子气概。黎大傻对刁蛮的妻子言听计从,不敢反抗。大壮的妻子因年长几岁,就在家中扮演着母亲和姐姐的角色。这类妇女,既没有传统女性温柔贤惠的品性,也没有另类女性勇敢无畏的风姿,她们看似拥有权威,实则连性别都成为“长辈身份”的脚注。丈夫们的屈服顺从是一种悲凉,妻子们的性别抹煞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孙犁塑造“光棍儿”和“妻管严”的形象,鲜明地反映出夫妻关系的异化,揭示出乡村畸形的生活空间,透射出他对现实深刻的体察和对忧虑克制的表述。孙犁把自己的情绪小心地安放在人物身上,通过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真诚地描绘了正常人性遭受倾轧的困境,也表达了对此种危害将会辐射到整个乡村的隐忧。
作为“出走者”的男性们。孙犁无意将人物拢聚在某种人生轨道中,也不对他们的选择强加干涉,而是遵循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让六儿、卯儿、黎七儿追随内心所求,坐上马车,扬鞭远行......黎七儿出身不好,没有土地,却认为凭能力也能过得滋润;卯儿作为“落后分子”却又性情恣意,喜欢闯荡的“游侠”生活;六儿虽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却充满童趣,勇敢地追求无拘无束的人生......“出走者们”是村里的另类,他们不安于现状,要走出沉滞,努力开辟新的生活天地。“出走”是背离传统的勇气,是个体冲破集体约束的尝试,也是传统重农抑商思想逐渐动摇的先兆。孙犁没有写出走后的结局,就像易卜生对“娜拉出走后结局如何”的回答那样,“他只是发问者,却不是作答者”。孙犁是一位清醒严谨的作家,他把填补结局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也在等待着历史的回复和时代的答案。
三、次要人物成因
孙犁怀着极大诚心和耐心描写他熟悉的乡村小景,关注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人事,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丰盈饱满,次要人物也同样个性鲜明。重读《铁木前传》发现其间弥漫着别一种悲凉忧郁的底色,人物或隐或现、或浓或淡地带有一种“茫茫然”的失落情绪。为何如此?
首先,孙犁受到民间传统、五四风潮和革命文化的多重滋养,本人就是极端的“矛盾体”。他真诚地汇入时代的主流,《铁木前传》的主题就是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也明确地表示自己遵循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时选择最熟悉的人事且赋予他们全部的感情。孙犁曾说《铁木前传》“......具备了真实的场景和真诚的激情”。[5]90但孙犁独特的性格气质和审美偏好又使他在《铁木前传》中呈现出旁逸时代的言说,这也让他遭到极大的厄运。他曾在《耕堂书衣文录》中写道:“此四五万千字小书,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之甚矣。”[6]41
其次,孙犁塑造的人物难以一言概之其善恶,他基本不会对人物进行伦理道德的指责,多诉诸体谅和尊重。孙犁安排与整个乡村秩序不协调的“另类人物”出逃,却又不点明结局,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特殊的人生选择和生命现象。人们自由意识逐步复苏,势必想冲破旧有体制中不合理的桎梏,奔向自由的田野。然而,社会没有为人的“逃逸”提供有效的途径,村民自己也缺乏文化自觉,所以卯儿、六儿、黎七的“出走”只是暂时的解脱,并不是真正廓清迷雾。当然,他们执着追求生命感觉、坚定走出滞塞环境的决心是值得肯定的。孙犁对现实人生有深刻的洞察,他知道“一体化”背景下“桃源消逝”已成定局,人们最终“无处逃遁”。然而,他对人道主义的坚守,让他不执着于苦难赘述,不刻意于人物“超克”困顿;他对诗意情怀的追求,让他给结局留白,在叙述中融入一抹暧昧混沌的色彩,增添一方迂回婉转的空间。孙犁因时时感喟世间渺小个体总被无常命运裹挟,会坠入无力摆脱、难以纾解的迷津中,所以他想把自己的宽厚和慰藉诉诸笔端,予弱小群体以安慰和关怀。正如他在一九八五年给某刊编辑写信所说,他认为作家要严肃认真,正心诚意,艺术创作应该“给人以安慰,鼓励,憧憬和希望”。[5]152
再次,孙犁或许无意间触及有关现代性的命题。从生活环境来看,童年虽战乱贫困,却有温暖的记忆,时代的前进反而使他流露出若隐若现失落苦恼的情绪。孙犁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提到,他写作的动因是进城后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苦恼”[5]90。这触及了“文明和道德的二律悖反”[7]命题。从人物塑造来看,孙犁没有对人物做出正反面划分,没有赞扬先进者,也没有贬低落后者,反而于隐微中透露出“政治先进者,人性上或有某种缺失;政治落后者,人性似乎更加完满”的观点。这体现了孙犁在大时代背景下对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之间分歧的辩证思考,增加了作品的时代感和厚重度。
最后,孙犁文本的芜杂多义、内心的无所安放,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境遇和生存状况。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知识分子的创作发生明显转向,农业合作化又将政治革命意识推向新的高度。特定的背景下,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必须转存于正确的表达空间中。现实社会是作家生活的真实世界,也是孕育艺术最坚实的土壤。无论处于何种语境都不该创作蹈空的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未必是难以相容和彼此对立的,革命的旨归也不会完全成为遮蔽作家自我意志抒发的“雾障”。相反,作家在不逾越限度和规定的情况下,对现实生活保留合理的怀疑,对人性人情之美不懈地追求,都会使文本充满多元和潜在的声音,留下源源不断的阐释空间。孙犁兢兢业业、小心捡束地耕耘着自己的“文学园地”,他通过“真事隐”的方式,把自我的心绪转寄在符合革命要求的土壤之中,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静待其孕育、伸展......
四、结语
孙犁擅长撷取乡村小景描摹平凡人情,营造舒纡气氛,传递恬淡心境。在浩浩荡荡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大潮中,《铁木前传》没有被湮没,时至今日,仍予读者以“常读常新”的审美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孙犁塑造出一系列性格迥异且善恶难辨的人物形象。他在主要人物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次要人物的描摹也内蕴着丰厚的心力。次要人物出场时间短、次数少,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释放他们的魅力,这考验了作家“排兵布阵”的能力。路遥曾说过,“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点点滴滴,多一些点点滴滴,就可能多一些丰满。”[8]17那些看似“东鳞西爪”零星散落于文章边角的叙述,在串联小说故事情节、丰赡文本叙事维度、发掘主要人物未触及的社会现实、弥补读者情感空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叙事意义,这些次要人物也“因其‘小’而‘众’更能反映社会动向与时代命运”。[9]孙犁于小切口中映射大时代,他在琐碎的生活褶皱中铺陈人物的情感波动和生命期待,在细微的动人瞬间中传达他们的命运抉择和人性美善。
注释
(1)参见: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 4 期;叶君《〈铁木前传〉:〈多义而敞开的“半部”杰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 期;潘艳慧《主流意识与个人诉求之间的矛盾叙事——论孙犁〈铁木前传〉的芜杂性》,《学术论坛》2004年第6 期;李展《小满儿论:迷茫的逃逸之路——重读孙犁的〈铁木前传〉》,《名作欣赏》2011年第6 期;郭宝亮《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1 期。
(2)参见:王宇《“空白之页”与“变异转型”——孙犁乡村女性叙事的复杂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期;杨亚林《论战争背景下孙犁的女性观》,《甘肃社会科学》2005 第3 期;余铮、蒋敏《美的化身与死的挣扎——论孙犁、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差异及根源》,《名作欣赏》2010年第17 期;李中华《论孙犁女性描写的深层情感隐秘》,《电影评介》2008年第 2 期;陈桐《孙犁小说农村青年女性群像研究》,《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 期;王正杰《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女性形象》,《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第3 期;滕金芳《赵树理和孙犁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塑造之比较》,《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3 期;胡学梅、余铮、蒋敏《孙犁与赵树理小说农村女性形象之比较》,《新闻天地》(下半月刊)2009年第 10 期;鲜晓丽《沈从文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比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2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