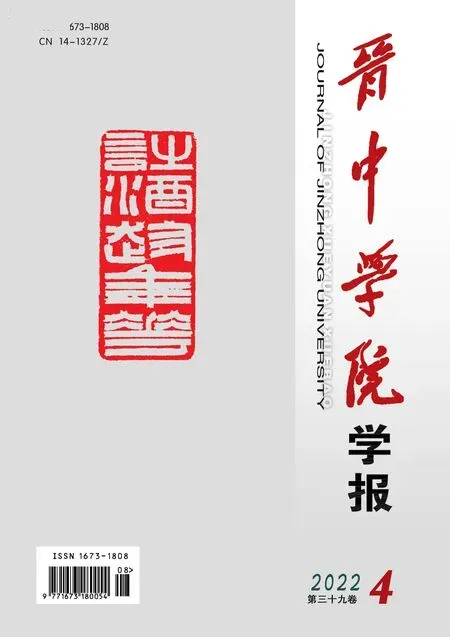太原风火流星传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钱永平
(晋中学院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山西 晋中 030619)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会进一步加强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以“延续和保持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民族基因,保留中华民族的记忆,珍惜优秀传统,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新文化”[1]。如何理解非遗传承?张紫晨指出:“传承活动是指上代文化与下代文化的接续性活动。即一种文化现象,在前进的时间流程里,被人们不断地延续着。......在这种延续性活动中,对上代来说,谓之传,对下代来说,谓之承。传是递,承是接。因此传承活动的公式为:传递—承接—再传递—再承接—多次传递(或传授)—多次承接(或接续),以至无穷。”[2]106可以看出,张紫晨将传承视为是文化的代际间动态延续过程,而不是形成的结果。这一定义适用于非遗,我们需要研究上代向下代“传递”,下代需要“承接”非遗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尤其是一些非遗项目需要当代人“承接”时,却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与成因,探讨破解其困境的路径。
山西太原晋阳风火流星有很高的艺术、民俗和体育健身价值,其表演令人拍手称赞。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后,风火流星才逐渐引起社会关注,但从非遗传承视角看仍后继乏人,其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一、风火流星的兴起与发展
风火流星源于民国初年,是传承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一带的一门融民间杂技与中华武术为一体的民间社火表演艺术,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表演者在一条长约1.6 米左右的绳两端拴上一个或多个用铁丝编成的拳头大小的笼子,里面装上燃烧的木炭,当表演者在夜间街头表演各种武术动作时,火花随挥舞的绳子四处飞溅,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人在火中,火随人转,极具观赏性。表演时用小锣鼓配乐,表演者根据不同的鼓乐变换动作,当多个表演者同时表演时,场面令观者叹为观止。
民国初年,太原人形意拳武术名家韩荣华和好友聂富喜、武吉光、武豹豹、武黑计等人一起创编了风火流星,在春节、元宵节期间,与踩高跷、舞狮子等社火节目一起表演,走在表演队伍最前面开路、打头阵,因此风火流星也被人们称为“开路将军”。[3]慢慢地,风火流星成为太原庙会和逢年过节集会表演必不可少的节目,练习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太原市晋源区东街郭家圪垛的村民几乎都能演练几下,直到现在,村里一些老人闲来无事时也能耍弄几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韩荣华将精力放到形意拳练习中,由他的好友聂富喜在每年正月“闹红火”时,组织武吉光、武豹豹、武黑计等人上街表演风火流星。聂富喜后将风火流星传给了他的三个侄子聂连富、聂鸿义、聂鸿寿以及邻居家的孩子,再由他们将风火流星传下来,现已传承五代人。但1976年发生的意外事故使风火流星中止了春节期间的表演,表演人员锐减,淡出百姓视野,成为少数人的业余爱好活动并继续传承,其间聂鸿寿还把风火流星传给了媳妇、孙女等。
2008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一批坚持传承风火流星的老艺人齐心协力,将风火流星成功申报为第二批非遗代表性项目,使其重新受到社会关注。在聂富喜、聂鸿寿、贾天仓、侯铁明(女)、孙梓朝这一脉传承人中,以贾天仓为首组建了风火流星表演团队,他们经常参加各类电视节目和博览会等场合的展演活动,完善并定名32 个风火流星表演动作。2019年8 月,贾天仓风火流星表演团队在太原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简称“二青会”)开幕式上精彩亮相,风火流星表演迎来了一次“高光时刻”。
从其发展中可以看出,太原风火流星表演者用扎实的武术功夫舞出绚丽火圈、火花,有着极强的观赏性和杂技惊险性,此前虽因意外事故使其传承人数变少,但现在时逢我国政府实施非遗保护的大好时机,作为非遗一跃而为太原特色文化,成为可在电视台综艺节目、博览会和大型开幕式上展示的民俗表演艺术。它体现了太原晋源地区民众优秀的文化创造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传承也面临诸多挑战。
二、太原风火流星传承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风火流星表演道具存在安全隐患
传承人表演风火流星时飞溅出的火花极容易将人烫伤。据传承人讲:“我们练习或表演时被木炭烫伤不足为奇,基本上每位艺人身上都有被炭火烫伤的疤痕。”这一安全隐患在风火流星过去一年一度的春节、元宵社火表演中暴露出来。1976年春节期间,风火流星传承人在太原市晋源区东街郭家圪垛城隍庙附近表演时,铁笼中的木炭火花飞溅到一名围观群众的衣服上,这位观众觉得很晦气,一直纠缠不清,要求赔偿,此事在村委会的协调下才最终解决,这场意外使风火流星传承人表演积极性严重受挫,自此退出当地春节元宵社火表演,主要在爱好风火流星的人中展开传承,传承人范围变小。
2008年,风火流星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后,受邀在电视台或博览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但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场合中是严禁使用炭火的,如何兼顾安全与表演效果,成为目前亟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难题。
(二)学习风火流星表演动作有难度
风火流星是由多名有扎实形意拳功夫的武术名家创造出来的,表演者都有一定的武术功底。1999年出生的传承人孙梓朝(1)九岁开始学习风火流星,他说:“我学习风火流星期间遇到最难的动作是‘口含双龙’,这个动作需要表演者用牙咬住绳子来舞动,刚开始练习时,绳子把嘴磨得红肿,甚至磨破皮,花了近一个月的练习才掌握了基本的技巧。而且,在风火流星铁笼里点上炭火时,温度会达到一千多摄氏度,学徒们在学习和练习风火流星时都很容易被炭火烫伤。”孙梓朝的父母曾一度觉得他练习风火流星会耽误学习,还有危险,因此激烈反对他学习风火流星。由此可以看出,练成风火流星不仅要冒着被烫伤的危险,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艰苦练习并且意志坚定才能坚持下去。
2015年至2016年间,风火流星传承人在太原王家峰小学、古城营小学、晋源二中开设过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风火流星课程,每周一次,每次时长约两小时,但传习效果都不理想。主因是学生大多是抱着好奇和玩一玩的心态去学习风火流星的,但练习风火流星堪比学武,想在娱乐玩耍中轻轻松松学成是不可能的,很多学生对风火流星的新鲜劲一过,就很难再认真投入了。
(三)风火流星传习方式与学校课堂教学为主的教育方式难以相容
笔者曾论证,非遗成熟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在人与生存环境密切互动的基础上,以身体为媒介,以技艺(能)、行为作为外在形态表现的高度复杂、熟练、杰出的经验性文化形式,这决定了口传心授是非遗的主要传承方式。[4]换言之,非遗作为一种以身体为载体的传统经验性文化,是传承人在师傅一边亲自示范,一边口传心授的基础上,通过长年日复一日地大量肢体练习和实践,将非遗转化为身体的肌肉感觉和记忆,并投射成实践经验,而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学习能力和表现力是最强的,这就决定了非遗代际传承最好从“娃娃”开始。可以看到,基于这种特性,当代优秀传承人都是在年纪较小时就接触并向前人学习非遗。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天仓就是十五岁左右开始学习风火流星的。
但当下青少年在学校接受教育,课业繁重,根本没有足够的练习时间。仍以孙梓朝为例,他用三年多时间学会风火流星的基本手法。2011年他因读初中住校,风火流星学习就此停滞三年,在此期间,他主要在周六日温习和巩固之前所学的风火流星动作,没有学习新的动作。直到2014年十五岁时他考上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后才又能天天练习风火流星。
从前文我们也可以看到,风火流星传承人曾在普通学校中开课,但传承人和学生一周只有2 小时面对面的学习时间,这对于需要身体介入反复练习并随时有师傅指点的风火流星是根本不够的。相关体育(武术)学校也没有专门的风火流星课程。加之很多人认为风火流星对个人发展没什么用,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学习风火流星的青少年自然少之又少。孙梓朝说当年和他一起练习的人有十来位,但很多人因学业和工作原因中途退出,目前只有三四位继续传习风火流星,其中只有他一名男性。
与之形成对比,目前太原市不少退休人员练习风火流星,以沙包代替炭火笼每天练习,强身健体,但因年纪和身体原因,很多高难度且精彩的风火流星动作是这些退休人员做不到并且也不能做的。从非遗视角看,这是风火流星表演动作的丢失,是代际传承水准下降的体现。
(四)风火流星的社会关注度低
近年来,传承人、政府文化部门、记者将风火流星视频上传到了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及微信公众号上,但视频播放量和文章阅读量并不高,根据发布时间早晚,目前播放量最高的是2022年5 月5日在新浪微博视频上一条题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风火流星,十几种动作变换,让人眼花缭乱”的视频,迄今有3.5 万次的播放量。多年来风火流星团队受邀参加地方电视台、网络电视台和央视总台的节目录制,一定程度上虽然扩大了风火流星的知名度,但社会关注度仍不高,据笔者在晋中学院的日常调查发现,很多在太原长大的大学生都没听说过风火流星,这是包括风火流星等很多表演类非遗项目面临的共性困境。
除上述问题外,随着太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从过去的庭院住进了小区的高楼,适合风火流星练习的空旷平坦场地越来越少,传承人目前和公园管理方申请选择在公园中比较空旷的地方练习,但如果使用装有燃烧的木炭笼子练习时,必须避免飞溅着的火花伤到公园里的游人。
三、窘境中的突围:风火流星传承困境解决路径
破解当下风火流星的传承困境,一个前提是传承人坚持练习,把老一辈传承人表演动作高水平地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在国家不断提倡非遗进校园的大背景下,坚持开展风火流星进校园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结合实际情况,研发出有传承效果的特色课程教学模式,借此发现那些喜欢并愿意学习风火流星的青少年。
风火流星生命力的本质在于面向观众的活态表演,春节元宵街头“闹红火”是风火流星传承人最为激动的“露脸”时刻。对此,结合当下社会发展实际,传承人不断争取更多表演机会,让风火流星面向更多的受众,激活发展动能,突破风火流星高水平传承赓续的小众化状态。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寻找风火流星炭火道具的替代方案。风火流星表演的魅力在于用武术套路挥舞绑有笼子的绳子,让笼子里的炭火借势飞舞,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是最危险的地方,为此,以贾天仓为代表的传承人一直在探索能替代炭火但又有火花飞溅效果的道具,已进行三次改进。第一次改进是针对手工制作的铁笼,由于窟窿很大,当在空中舞动时,木炭很容易飞溅出来,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容易被烫伤。2008年,贾天仓发现汽车空气滤清器的窟窿眼很小,可代替铁笼装上炭火,于是他将空气滤清器进行了改造并作为风火流星的表演道具。第二次改进是因为2010年风火流星团队参加上海世博会演出,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要求风火流星表演时不可以使用炭火,于是贾天仓将孩子们玩耍的跳跳球拆开,在里面装上了彩灯和电池,这样使得风火流星表演起来既安全又能产生灯火灿烂的效果[5]。第三次改进是在2019年二青会开幕式文体展演上,表演团队采用了LED 灯道具,虽然表演绚丽多彩,但缺少了火花飞溅的撼人视觉效果。迄今为止,这方面仍没有突破性进展,风火流星传承人们迫切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可替代炭火的新型表演道具,在降低表演危险性的同时还能形成如同使用炭火时火花不时飞舞的效果。
第二,进景区表演。风火流星有很多“绝技”表演,符合旅游的“新奇”特性。在当下,传承人与太原及周边景区管理方合作,在特定时期选择景区比较宽阔的场地,结合景区灯光秀等活动,在固定时间(以晚上表演最佳)进行专场演出是可行的,这能很好地吸引游客长时间停留在景区,促进消费,增加景区和传承人收入。同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以双方可以接受的形式,利用景区空置房屋建设风火流星展示馆,将风火流星的道具、服装、图片、影集、现场表演展示在大众面前,让人们通过参观风火流星博物馆,感受传统社火表演的魅力。
第三,积极参加各类展演,不断争取更多受众面广的舞台演艺机会。目前风火流星的传承人在政府支持下参与各类惠民演出,如黑龙江卫视的《一起传承吧》、央视频道的《2019 我要上春晚——〈火树银花庆丰年〉》、第三季《非常传奇》以及2020年春节特别节目《幸福节节高》的节目录制,这是当代弘扬风火流星的重要方式。新一代传承人应想方设法搭上最新信息传播载体,如将最具视觉吸引力的风火流星表演拍成短视频,让更多人在移动化、碎片化、视频化的媒体传播中注意到风火流星,为其表演创造更多机会。
最后,拓展和开创风火流星民俗生活应用场景。某种程度上,民俗是创造出来的并获得民众认可的文化活动。对于风火流星而言,“风火”是有民俗吉祥内涵的,通过反复宣传是可以获得民众认可的。对此,传承人可与太原市文化演出服务公司或庆典公司合作,运用现代会展思维、精心的活动策划,在各类日常重要仪式庆典场合进行庆祝性质的表演,一方面可增加演艺收入,另一方面能让更多市民认识、熟悉和了解风火流星。这也是风火流星生命力持续的地方民众基础。
注释
(1)孙梓朝,山西太原人,山西传媒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20 级学生,第五代风火流星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本文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提供人,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