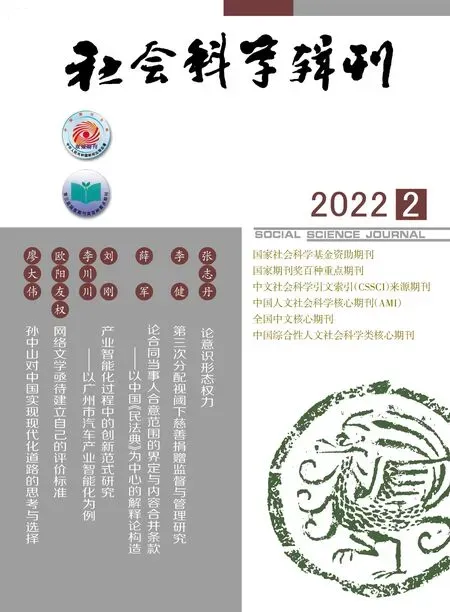近现代日本的“满洲风土”暨自然与社会文化调查书写评析
逄增玉
一
日本在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国策驱动下,在亚洲国家中较早进入“近代化”(现代化)的同时,也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1894年甲午战争后侵占了朝鲜和中国台湾作为海外殖民地,1905年日俄战争后又从沙俄手里夺取了东北旅顺、大连暨辽东湾,使之成为隶属于日本辖制的“关东州”。一直把“占领满洲”作为生命线和实现“大陆梦”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调查;甲午战争后,其政府机构、宗教团体、学校社团、学术团体和个人都加入了对中国及其边疆的调查探险等活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更是以学术调查的名义进行所谓学术考察和调查,不断出笼学术调查报告。从1906年开始,“满铁”建立规模庞大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还在沈阳、吉林、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事务所。1939年4月,调查部改组扩充,30年间收集的各种资料、书籍、档案、杂志、剪报、情报达到30余万件,并出版数千种资料汇编、论著和刊物。自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对我国东北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以资源、物产、农业、工业、商业、外国在华产业等经济类调查为主要内容,细致到对东北每一个地方的物产矿产资源、农作物类型、劳工乃至把头制度等,巨细无遗地进行极为广泛的调查,其中也涉及一定的文教、宗教和社会类事业以及与自然有关的文化。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满铁”的调查不断伸向华北和中国更广大地区。
此外还有清末建立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不断对中国各地进行旅行调查,出版了调查报告专题选本23种,其中包括《东三省铁道调查》(1928)、《满洲农家经济状况》(1929);专题论著13种,其中包括《对支文化论》。还有明治十四年(1881)开始的驻华使领馆对中国的分区调查,近现代日本的学者、官员、商人、军人、浪人的个人踏访,搜集汇编了大量的对中国各方面调查的资料情报。此外日本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对华信息情报收集与调查研究机构,如1924年在北京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其属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立的“东亚经济调查局”“东方文化学院”“东亚研究会”“中国通信社”等。1937年全面侵华后,又设立了“东亚研究所”“大东亚文化学会”“大东亚问题研究会”“日满支拓殖文化研究所”等官方、半官半民或民间调查机构,其中“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是日本官方成立的专门对东北地区进行调研并办有刊物的机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方面在国内继续进行各个机构和大学对东北的研究调查,出版和刊行各种有关东北历史、地理、自然、宗教、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研究著述、影像资料和调查报告(如日本京都大学对东北的多次所谓学术调查报告),一方面继续通过伪满政府各个部门(如伪满国务院、民生部社会司和教育司、文教部)、关东军、“满铁”调查部、“满铁”图书馆、“满铁”驻奉天哈尔滨和各地事务所、“弘报协会”“满映”“满洲事情案内所”“满洲日报社”“满日文化协会”“满洲国通信社”“满洲文化协会”“东亚文化协会”“行径满洲图书会社”“满洲铁道总局”“满铁”总务部庶务课“满洲文话会”“满洲帝国地方事情大系刊行会”、大同报社、盛京时报社、“满洲文化协会”“满日文化协会”“新京满洲学会”“新京大同学院”“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等,对我国东北甚至今朝鲜、蒙古国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综合调查和书写图录、影像摄制,构成为一整套帝国主义视野中的“满洲文化风情”,成为典型的殖民主义文化统治的表征。
如前所述,纪实性、科学性的对东北的风土调查、考察和记述早在甲午战争前后就已经开始进行,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对以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南部地区的占领和殖民化,“满铁”和有关方面更是加大调查书写和建档的步伐,属于广泛的人类学和文化学范畴的“风土”考察和记述的著述不断“发表”和出版。九一八事变后,更集中、大量地写作与发表有关“满洲风土”考察的记述,如“满洲日报社”编纂的《满洲风土记》(上中下),春山夫行的《满洲风物志》,千田万三的《满洲文化史点描》,田口稔的《满洲风土抄》《满洲风土》《满洲地方志考》,藤山一雄的《新满洲风土记》,真继义太郎《满蒙游记》,有富光门翻译的《满蒙探险四十年》,秋叶隆《满洲民族志》,平林芳胜《满蒙之文化》,川岛土路《满蒙风土记》,以及对东北或满蒙、满鲜民俗、民族志、宗教、音乐、风物、传说、美术、见闻、探险、建筑、古迹、物产、天候等各个方面的考察和调查著述。还有对东北的各种各类的图片和照片类图书,大都冠以“风物帖”“写真集”“写真帖”“写真大观”“写真年鉴”等名称。仅“满洲帝国国务院文库藏书目录”收藏的日本人撰写的关于东北、满蒙、满鲜的广义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书写的书籍,包括历史、文物、古迹、宗教、地理、游记、探险、考古、民族、习俗、礼制、文教、文艺、语言、文字、杂说、札记等,就达到数百种乃至上千种之多。如果把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和“关东州”出版的此类书籍加在一起,数量极其庞大。
这些冠以“风土”之名的文本中,多是以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视野和方法进行的著述,也有很多探险、漫游、生活体验性的旅游纪实和散文,与中国的“风土记”大都是文学性散文的性质有所不同。日本关东军出于殖民统治的目的,也资助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鄂伦春等原始通古斯民族进行人类学与社会学调查,出版有《驯鹿鄂伦春》等资料和书籍。还有不少日本本土的和伪满洲国境内的日文报纸杂志,也经常刊登若干有关东北社会文化的文章或者图片影画。设在大连的伪满文化机构“满洲文化协会”,还创办了《满蒙》杂志,专门刊载研究东北地理、社会、宗教、民俗、文化及广义的人类学等方面的调查或纪实性文章。
此外,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有很多日本的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东北自然和风土的文学性书写。正冈子规的句集《寒山落木》和诗集《金州杂诗》,国木田独步的诗歌《大连湾》,森鸥外的《和歌日记》,就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有关东北自然风土描写吟咏的作品。其后,从日本的大正时期到昭和初期,不少日本作家文士到东北观光旅行,写下了有关东北的纪行、诗与和歌。其中较多地描绘了东北风土且产生一定影响的,有田山花袋的《满鲜的行乐》、大町桂月的《满鲜游记》、沼波琼音的《满鲜风物记》、夏目漱石的《满韩各处》、迟冢丽水的《满鲜趣味之旅》、里见弓享的《满支一见》、与谢野宽的《满蒙游记》、尾上柴舟的《且行且歌》、西村真琴的《满鲜新观》、小杉放庵的《草画随笔》、长与善郎的《满支近顷》等,这些文本以纪行为主,也收有短歌和俳句。纯粹的歌集如川田顺的《鹊》、牧野英一的《灯》、岛木赤彦的《太虚集》等,也收有吟咏东北风土的作品。
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后不久,又开始了对东北的移民。随之在日本文人和开拓民中出现了所谓“满洲开拓文学”,其中报告文学作品有岛木健作的《满洲纪行》、德永直的《先遣队》、山田清三的《我的开拓手记》、菅野正人的《土地和战斗》;小说有打木村治的《制造光的人们》和《草席物语》、汤浅克卫的《先驱移民》和《青上衣》、和田傅的《年轻的土地》和《殉难》、荒木巍的《北满之花》和《百姓魂》、伊藤整的 《呼吸》、林房雄的《大陆的花嫁》、田村泰次郎的《猛男》、钎田研一的《镜泊湖》、福田清人的《日轮兵舍》和《松花江》等;诗歌有岛崎曙海的《地貌》、甲斐水棹子的《花灯》等。
总之,近现代日本从国家政府到社会机构和民间,对我国东北进行了规模浩大、内容繁多的自然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与书写,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表、图像和影像资料。这种调查书写与刊行的规模和数量,在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侵略、殖民或半殖民的列强中,日本堪称首屈一指。
二
近现代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的卷帙浩大、细致全面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的综合调查、书写与刊行,首先具有昭然若揭的政治帝国主义性质和目的,是为走向帝国主义的日本的“拓殖”,即进行侵略、占领和殖民的“国策”服务的。在伪满时期出版的日本人长与善郎撰写出版的《满支近顷》《满洲见学》以及其他日本人撰写的关于满洲社会文化综合调查的大量著述中,直接言说和表达东北或“满蒙”是日本帝国生命线的言论与观点所在多有,充分表现出近现代的日本,已经举国上下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和“拓殖”是实现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国策的基础。
其次,近现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综合调查与书写,除了为其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政治、国家目的服务的功能和性质外,从世界殖民主义历史来看,具有与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同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性质。欧洲最早内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如英、法等国,由于工业化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带来的对于劳动力、世界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必然性地导致帝国和殖民主义的崛起与世界性侵略扩张,而伴随着这一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军事、经济与政治的殖民主义扩张侵占的“恶”的历史进程出现的,就是以传教士、商人、探险者、旅行者、新闻记者、科学家等身份出现的对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殖民行为,其表现方式就是地理发现、地质勘探、资源调查、博物采集、地域命名、科学考察、文物考古、民俗风情采汇、宗教信仰摸查和传教以及国别地域文化的总览、纪实与文学书写等。这种总体性质上属于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的行为,大体上包含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并冠以文化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考察、言说和书写作为“他者”的非西方世界,建构了一系列、一整套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和话语谱系。在这套谱系中,西方代表着现代性文明及其价值,而非西方世界则被描述为原始、落后、野蛮和低于西方文明的“蛮荒之地”,其存在和被言说书写的状态“确证”了西方“优越先进”的文明价值和本质。简言之是西方“发现”了东方,因此西方及其文明的到来就是先进改造落后、文明改造野蛮的历史之善,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①转引自李扬:《文化与文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98页。另一种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科学、地理、博物、资源类考察与调查以及地理探险和发现等。但是,按照殖民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即使这种表面客观性、科学性的东西,其背后和内里也与帝国和殖民大扩张时代的霸权和强权存在一定联系,如被认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②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7页。,背后也有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影子,1859年达尔文历经20年完成的《物种起源》正式面世,极大地震撼和影响了整个西方与整个人类。但是,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长时期的考察、采集、观测和研究,是因为大英帝国遍布亚非拉的殖民地为其提供了便利和可能,达尔文很多时候是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动植物考察、分类、收集、研究,进而完成科学发现和建立理论的。达尔文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和殖民者,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在帝国和殖民主义鼎盛时代,西方列强国家的某些基于对非西方世界自然与社会考察而建构的客观性、科学性知识的背后,也有帝国的背景,就像殖民宗主国的人民大众也会或多或少地享受殖民地红利一样。而彼时欧洲国家的社会性更强的文学,即使是英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吉普林的印度森林动物小说、原籍波兰的英国作家康拉德的海外探险与猎奇性质的小说,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并非赤裸裸的帝国意识的宣扬,但他们某些作品仍然具有公开与潜隐的殖民主义背景、愿景和帝国意识。〔1〕
近现代走向帝国主义侵略道路的日本,虽然一再炮制各种意识形态说辞,声称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并非对亚洲诸国的侵略,而是为了“抗击英美”即把欧美老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亚洲,从而解放亚洲并把亚洲带向现代文明,但这是一种自我想象的“共同体”,是典型的虚伪意识形态。实质上,明治维新以后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其走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海外拓殖”、扩大生存空间、建立殖民地攫取广泛利益的道路与方式,完全是对西方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模仿和复制,甚至是更为亚洲化的拙劣的“模仿”——只是承续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一面,对西方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奠定社会基础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人权自由的一面,倒是完全缺失,所以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具有侵略性和野蛮性,这是历史昭彰的事实。
故此,近现代日本对东北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书写和刊行影像,同样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所有逻辑与套路、内容与装置,与西方早发和老牌帝国的殖民主义逻辑具有明显的同类性和同构性,即日本近现代对东北自然与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书写,也同样是以自认为“先进”“文明”“现代”的价值优越感和视域,将被调查考察之地视为原始落后的“他者”和需要被文明改造与征服的对象。这样的帝国和殖民的视域与意识形态,比较鲜明地表现在一些虚构性和文艺作品里。如1938年成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满映”独自或合作摄制的宣传“国策”的电影,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大陆三部曲”——《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以及《迎春花》和《苏州之夜》等,都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虚构为爱情故事电影,故事中的日本男性来到中国,在巧合或者误会中结识了中国女性,中国女性经过日本男性的救助、帮助而无一例外地被日本男性的魅力所征服,从而爱上日本男性。这种表面的战时异国男女的身体遭遇和浪漫爱情故事,其实只是一种艺术化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寓言和符号,象征和表达的是日本并非是侵略者而是“帮助者”和“解放者”,带领后者“迷途知返”即从误会、误解中觉醒,死心塌地地跟随“领导者”日本走向“美满”的“东亚共荣”。这种把殖民地文化和人民视为“过于女性化”和缺乏某种“男子气”和“阳刚气”的“本质”,把殖民侵略者和压迫者塑造、隐喻和叙述为“刚健的男子汉气概”〔2〕的逻辑和套路,在西方老牌帝国的文艺性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后起的帝国日本显然继承了这一殖民主义逻辑。
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东北书写中,如果说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之际的作品,由于日本尚未完全侵占东北而只是把大连、旅顺等局部地方占据为殖民地,故此这些作品或者歌颂日本帝国的“满洲进军”和攻击沙俄的“海外伟业”,或者把东北作为有待“拓殖”的充满价值和欲望的“外邦”之地与帝国视野下的“风景”,那么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占领东北、随着日本移民到来而出现的所谓“满洲开拓文学”里,那种帝国和殖民的逻辑依然存在且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方面,这些作品从日本人的立场和眼光出发,对中国东北的风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描写,其中特别对于东北的土地山河、平原草原的辽阔壮丽与四季景物,进行了充满赞叹、惊奇的描绘,因为在岛国日本看不到这样广袤的旷野平原和土地山河,看不到地平线的日出日落,他们为来到、据有了这样的自然与土地而惊叹和感叹,感叹的背后是对帝国海外“拓殖”由衷的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这片瀚海般阔大广袤土地与自然的书写中,也有意地强调其原始性、洪荒性和土著性,带有所谓的“处女地”性质,以及这里原住民的古老性、多样性和土著性,内里隐藏昭示的逻辑和话语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与中国联系的脆弱性、无关性或者非中国性,日本占领、移民和开垦这片土地山河的“拓荒”性与“合法”性——既然是多民族居住的、非中国的、原始性的土地,那么日本人前来拓殖和“拓荒”自然就是合法和合理的,甚至是把现代文明带进了这片土地。这样的话语逻辑在“满映”的“国策”电影《迎春花》中,还刻意强调东北历史上在渤海国时代与日本的联系和文化的同源性,也就是说,“满洲”与日本自古就是友邦和存在密切关系的,日本对东北的“北进”当然也不是侵略殖民而只是恢复历史的关系而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逻辑就这样被“名正言顺”和“去殖脱罪”了。
第三,那些更为卷帙浩繁的非虚构、纪实性的东北边疆地理、自然状况、物产资源、历史人文、风俗人情等“风土”调查书写,以及诸如“满映”摄制的自然风光片和科教片等电影,同样存在着客观性、知识性与殖民性的双重关系、视角和视域,总体上属于帝国视野下的“满洲风土”,这种在他者化的对象客体中被考察、调查和建构生产的知识,整体上都属于拥有殖民权利和红利的帝国的知识生产,是帝国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此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调查书写文献被纳入“帝国文库”,就标志着它们是日本帝国视域、权利和话语支配下的关于东北的知识生产,是帝国权利、殖民红利和为帝国服务的知识体系。①现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数百卷伪满洲国和满蒙史料文献,大多出于“满洲帝国国务院文库”。众所周知,伪满洲国并非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帝国,而是日本帝国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而且这些文库收录的史料文献大多数是日文而非中文,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其属于日本帝国的知识视域与体系。
当然,这种帝国野心和视域下的东北调查书写和帝国权利下的知识生产,由于日本对东北侵略占领和殖民统治有时间阶段的不同,因此这种帝国视域和权利的表现和症候存在一定差异。如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只是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即大连、旅顺据为海外领地“关东州”,因此这一时期对东北的社会文化和风土调查,还不是全面性和举国性的,而是以民间、企业和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官私一体的“满铁”的调查,是从“南满”铁路沿线开始的,次第扩大到东北、华北和整个中国。还有前述东亚同文书院,表面看是为了建立支那学即中国学,以学生的假期旅行调查的方式对中国展开调查,而为未来的全面侵略服务的“帝国目的”隐藏在学术和田野考察、民间调查的背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经把东北变成伪满洲国和实际的殖民地,因此调查考察的范围更为广大、内容更为细致,已经把日本“支那学”知识体系的所谓“客观性”和“学术性”目的与更加全面了解殖民地的一切、从而使其拓殖和统治稳固长久的政治性目的纠合在一起,因此,拥有了统治殖民地性质的伪满和“国运”基盘的胜利者、权利者心态,其调查书写的目的性同殖民性具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现代日本出现的侵占东北与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知识者和文化人中的“支那史”专家学者,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最早提出殖民东北与中国的设想和计划,不断著书立说或者参与“满铁”的调查中国计划,如著名中国史学者白鸟库吉早在1912年就发表《满洲问题和支那的将来》,提出了殖民东北和“满蒙”的思想,积极参与“满铁”的调查计划或为之出谋划策。20世纪20—40年代,各种以所谓史学知识证明东北不属于中国,日本“拓殖满洲”作为生命线进而领导“满洲”和东亚走向“文明”和“现代”的学说不断出现,东北研究成为日本的“支那学”或汉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满洲学”。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和全中国,提供了思想文化的“支持”,是近现代日本殖民主义重要的思想知识背景和毒源。
三
近现代日本除承续了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之外,其对东北的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书写,还带有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东亚殖民主义若干特点与症候。
由于同处东亚“一衣带水”的近邻环境和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了解和学习作为“文化上国”的中国历史文化即中国“事情”,并一定程度地模仿之,一直是日本关注和吸纳的重点。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力主和实践“脱亚入欧”国策并走向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但是在为了霸占东北而进行的大规模、长时间综合调查中,其汉学或“支那学”传统一直未曾断绝。帝国侵略扩张国策的支持,使得这样的调查考察具有西方老牌帝国未曾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参与调查考察书写者极为广泛和众多,调查考察和书写的内容极为广泛细致,几乎方方面面都被纳入考察调查和书写刊行之中。①日语的“中国事情”相当于中国状况、概况、国情等,至今很多日本高校都开设此课程。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几乎在日本都有不同的译本,从国会图书馆到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和较大的公立与私立图书馆,都有大量的收藏,阅读者众多,中国的《三国演义》和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历史纪实与虚构作品,甚至成为日本的畅销书和常销书,对孔孟老庄、先秦诸子和王阳明的学习研究,对中国的佛教以及禅宗流派有广泛的学习继承,已成为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常态。至今日本的汉学传统依然非常发达,日本讲谈社组织、由10位日本著名汉学家撰写的皇皇十卷《中国的历史》,201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受到学者和读者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甚至引起了一阵中国历史热,至今已经五次重版多次印刷。该书在规模、读者数量和社会影响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历史》。
虽然近现代日本承续了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与模式,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尽管近现代日本一改过去敬佩中国及其历史和文化的传统,瞧不起落后于日本现代化水平的中国并侵略之,不过在东北综合调查书写的文献资料里,他们暂时还没有流露出殖民宗主国对被其侵略或殖民国家历史与文化和文明的蔑视态度。大英帝国在统治印度殖民地期间,英帝国的官员和学者作家中就有若干人公开蔑视印度的历史与文化,如英国作家麦考来1835年致信印度总督的信中说:“欧洲任何一座好的图书馆的一架书,抵得上整个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文学,我还不知道有哪位东方学家能否认这一事实,我也还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东方学家敢于说,阿拉伯和印度诗歌可以和欧洲任何一国的伟大诗歌相比拟”②转引自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还有若干在印度的英国殖民官员也有这样的或明或隐的态度。〔3〕
自物质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宋朝被蒙古打垮,而日本侥幸得到所谓“神风”之助使出征日本的元军葬身大海之后,日本已经有蔑视中国的倾向,认为中国文化及其精髓被日本继承而中国成了“支那”。辜鸿铭以及部分持有与他同样立场的学者,也在很多文章文字里表达过日本是中国文化文明的继承者的认识〔4〕,抗战期间沦陷区北京的日本宣传官员奥田久司也曾公开认为,“中国观众的文化程度,比日本人低得很多”,所以他主张拍摄大众通俗电影以适应中国观众,目的是“对他们启蒙教育,即用糖果来吸引,同时给他们吃药”③〔日〕奥田久司:《大批京剧搬上银幕》,清远译,转引自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近现代日本众多的参与东北综合调查的单位与个人,不排除有对中国及其文明文化的蔑视者,但是就目前所见史料文献来看,还极少发现有像奥田久司那样公开表达对中国及其文明文化的蔑视言论。倒是有不少人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调查书写的根本目的是为帝国野心和国策服务,一方面仍然流露出对中国和东北历史文化博大浩瀚之感慨;一方面知道对作为“帝国生命线”的东北的调查书写是帝国背景和视域下的知识体系建构,是政治目的下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行为,一方面也有若干的汉学或“支那学”的传统和学术志趣。不仅如此,就像日本左翼学者冈田英树指出的伪满洲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存在一定的矛盾和裂痕、并非完全相同一样〔5〕,不论是日本国内还是来到东北的日本统治者和殖民者,对中国和东北的历史文化的认知评价也存在一定的相异之处,如“满映”拍摄的宣传“国策”的故事片《迎春花》,既有象征日本帝国的男性在东北得到中国女性青睐爱慕,以身体爱情叙事隐喻日本的“先进文明”的魅力,带领被开垦的“荒野满洲”走向“现代”的殖民“国策”宣传,也有东北即中国女性之美丽和魅力超过日本女性、日本男性主人公在东北的土地上受到教育、成长和成熟的“事情”。当然,这样的故事和叙事的根本目的还是为宣传所谓的“日满一家”“五族协和”共同建设“王道乐土”的殖民主义“国策”服务,为侵略占领制造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属于鲁迅所说的有利于殖民者对被殖民人民的“心的征服”〔6〕。不过,其中也多少流露出部分日本人对东北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博大性的认知,与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汉学传统对中华文明的亲和性认知存在一定联系。另外,日本和伪满政府在炮制“国是”和“国策”中,要求在被殖民的伪满“王道乐土”大力倡导中国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弘扬中国文化之精义精髓,这样的行为既有明显的愚昧人民效忠“满洲皇帝”和伪满政权、服从殖民统治的目的,客观上也有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并非完全蔑视和抛弃。因此在东北调查书写中少有文化殖民者的高傲和蔑视,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是近现代日本的东北调查书写所流露出的东亚殖民主义与西方老殖民主义文化殖民逻辑并不完全一致的原因。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原则,去关照考察近现代日本的东北调查书写史料文献,也不能不指出的是,刨除其文化殖民主义的总体性目的之外,那些大量冠以“满蒙风土”“满洲风土”“满鲜风土”称谓的史料文献,也一定程度地与日本思想和学术中重视“风土”即地域文化、民间文化、民俗风情文化研究的传统存在关联,日本本土的典籍书刊中,对于本国各地风土的调查书写也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另外,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东北书写,有些著名作家如森鸥外等并非右翼作家,只是受到日本帝国意识的影响,在日俄战争期间到过东北并在其作品里有所描写,还有像夏目漱石等作家,他们的中国和东北书写的动机、目的、程度,与日本发动侵略亚洲战争后,随着帝国侵略、拓殖的步伐而有目的有计划地书写中国和东北风土与风景的作家作品,也还存在区别和差异。应该说,日本的东北风土调查的殖民性与其传统的风土书写的非殖民性的关系,在这些史料文献中都混杂在一起,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学术甄别和分析。
与此相类,东北调查书写的大量史料文献,还存在着一定的方志性,即地域文化和乡邦文献的价值性,这些史料保留、遗存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属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畴暨社会文化范畴的民俗风土等内容,以及纯粹客观性和知识性的东西,包括科教类电影中的地方病调查与防治等内容,对认识和了解当时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文化、民俗与风情等方面状况具有一定的甚或是比较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它们既是帝国视野和目的下被收集整理和书写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史料,具有殖民主义目的性和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又是东北地域文化和历史存在的真实形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所以,改革开放后东北、内蒙古等地区开始重新重视和修撰各级各类史志方志之际,历史遗留下来的日本对我东北综合调查刊写文献仍然是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史。同时,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将伪满、“满铁”、日本各类侵华史料文献纳入重大出版项目和研究项目,各级各类出版社出版了规模宏大、卷帙浩繁的有关伪满、“满蒙”“满铁”的调查史料文献,也是看重其包含的地域乡邦文化史料及其价值,以及文化殖民主义的研究价值。可以说,近现代日本出于总体的侵略殖民目的进行的大规模的东北调查书写,是包含文化殖民性与乡邦、地方文献价值性的二元结构和关系的,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二元性问题,是几乎所有研究殖民地时期社会、生活、人民、文化等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好的问题。
对此,马克思对于19世纪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殖民地的分析和论述,实质提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殖民罪恶性和一定的现代文明价值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东方殖民地理论的分析模式和型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①参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8-863页。对于近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目的下的东北综合调查书写行为及其留下的史料文献,也应该以马克思的东方殖民地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揭示其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文化殖民主义大恶之下的某些超出其主观目的性的“小善”,正确对待文化殖民主义的负资产,予其以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与阐释。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