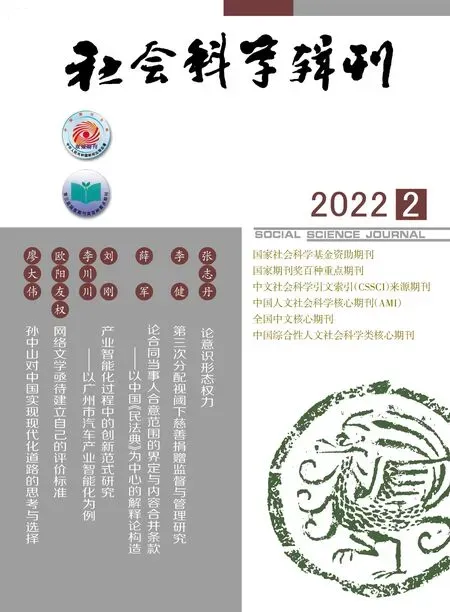论融资租赁的担保交易化及其限度
张家勇
融资租赁在二战后的发展引发租赁业的质变。租赁企业作为出租人,将承租人与出卖人通过融资租赁合同连接起来,同时发挥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在处理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时,融资租赁出租人是否承担普通出租人的义务,如物上瑕疵担保责任、租赁物维护义务以及租赁物风险负担,并享有普通出租人的权利,尤其是作为租赁物的完整所有权,涉及对这种新型交易形式的法律评价,不同的法律体系存在不同的做法。在美国,法院基于交易关系的实际内容,区分普通的租赁与担保交易而作不同处理。〔1〕在德国,融资租赁的法律属性是合同法上极具争议的话题。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先将其定位于使用租赁合同,随后则关注其有别于使用租赁的特殊性,近年来又呈现出回归倾向,强调使用租赁规定的可适用性。①Vgl.Staudinger/Stoffels(2018)BGB Leasing,Rn 65-69.我国《民法典》延续了原《合同法》将“融资租赁合同”有名化的做法,但在相当程度上将融资租赁功能化,或者说担保交易化,使融资租赁合同在规范实质上发生“转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型效果,引发相关规范理解与适用上的特殊问题。最典型者,如融资租赁不同类型的规范意义、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条件与限度以及合同失败情形融资租赁担保性的维持等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本文拟以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为中心,尝试对前述问题作出回应。
一、融资租赁的典型交易结构及其偏离
融资租赁通过将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进行类型结合,形成独特的交易结构:出租人应承租人的要求购买租赁物供后者使用、收益,承租人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向出租人返还价款本金并支付合理利润,在经济上有信贷融资的特点;但是,承租人并不直接获得出租人的融资,而只是享有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故在法律上只表现出融物的特征。①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权与应付租金将体现为企业资产与负债。因使用权的价值与租金大体相当,故而,在完全摊销情形下,租赁物的使用权价值与所有权也趋于一致,从而引发税法上的特别问题。也就是说,融资租赁交易在会计、税务与法律上的处理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关于融资租赁适用的会计准则,参见任立华、柏亮:《融资租赁法律风险防范指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第139-140页。通过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以及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的彼此关联,融资租赁的融资与融物双重特征在法律形式上呈现出不同强度的结合。
(一)融资租赁的典型权、义配置
对于融资租赁来说,融资反映的是交易的经济实质,而租赁则是其借用的法律形式。融资的经济实质在何种范围或程度上影响到租赁形式的规范效果,涉及普通租赁与担保性融资租赁的界分,是融资租赁在不同立法模式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借用租赁形式,融资租赁出租人需在法律形式上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如果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或者出卖人并未向出租人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则不能成立有效的融资租赁关系(《民法典》第737条),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其实际交易内容确定,一般为借贷关系。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但是,融资租赁情形的买卖合同通常由承租人以出租人名义进行磋商后缔结,出租人原则上只负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价款支付义务,标的物由出卖人直接交付给承租人,且出租人依买卖合同享有的拒绝受领权(《民法典》第740条)、索赔权(《民法典》第741条)等救济性权利也都由承租人单独享有和行使(《民法典》第739条),出租人仅有协助义务。承租人不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且出租人不得未经承租人同意,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民法典》第744条)。因此,与融资租赁相关的买卖合同具有典型的赋权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性质。由于出租人并不享有买卖合同中其作为买受人的实质性权利,买卖合同产生的权利移转效果实际存在于出卖人和承租人之间,融资租赁合同的“融资功能”也由此体现。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出卖人虽然参与了该合同的履行过程,即向承租人交付约定的租赁物,但其本身并非合同的当事人。③相反观点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出卖人。参见王利明:《合同法分则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5-306页。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负担的主要义务是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民法典》第748条),并不负担普通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民法典》第747条)、维修义务(《民法典》第750条)以及租赁物致害责任(《民法典》第749条),也不负担租赁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民法典》第751条)。租金的确定并不参照租赁市场的一般租金水平,而是根据租赁物的大部分或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民法典》第746条)。融资租赁期满后所有权的归属通常是区分融资租赁和普通租赁的参考因素之一,即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归属承租人,或者承租人只需支付象征性价款的合同,通常可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但是,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归属更多与成本摊销有关,对于融资租赁的交易性质并不发生决定性影响④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拒绝将购买选择权约款本身作为认定担保交易的必要条件。参见R.C.C.Cuming,“True Leases and Security Leases under Canadian 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y Acts,”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7,no.3(February 1983),p.269。,融资租赁也因此再次反映出“融资功能”的中心地位。
据此可见,在典型交易情形,尽管融资租赁在经济效果上兼具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但在法律架构上,其融物功能完全附属于融资功能。融资租赁法律规制的核心,更多在于确认融资租赁出租人原则上不承担除容忍使用义务外的其他普通出租人的义务,以及除存在法定或约定理由外,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的义务(《民法典》第751-752条)。融资关涉对出租人利益的保护,而融物则涉及承租人利益的实现。鉴于融资租赁同时具有融物而非单纯融资的特征,其并不适用借款合同的相关限制规定,如利率限制(《民法典》第680条第1款)、禁止利息预先扣除(《民法典》第670条)。正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融资功能的中心地位,它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担保交易形态。
(二)具体交易偏离典型构造的效果
在融资租赁交易实践中,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可能偏离前述典型结构。具体表现为融物功能在两个相反方向的变化:
一是融物功能名义化。在典型融资租赁情形(直租)下,融资租赁呈现三方结构,承租人通过融资租赁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收益。与之不同,在售后回租情形下,出卖人与承租人融为一体,融物彻底名义化,即:尽管同样存在租赁物所有权的变动,但在出卖前,承租人已经取得标的物的使用、收益,售后回租只是改变了承租人使用、收益的身份。与直租不同,回租并没有产生普通意义上的融物效果,仅发挥承租人自有之物的融资效用。此时,出租人实际变成贷款人,从信贷管制和税收征收的角度看,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都偏离了融资租赁典型的功能定位,并产生不同于典型交易的法律效果。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表现出单纯的融资担保交易结构,不发生典型融资租赁情形下与买卖合同有关的问题,如标的物迟延交付、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等。不过,这种偏离仍不影响融资租赁的性质界定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赁解释》)第2条。,属于被法律承认的规避行为。
二是融物功能实质化。融资租赁出租人之所以不承担普通出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负担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主要是因为标的物种类、品质、性能等的确定,完全服务于承租人的意志和需要,出租人只关注标的物价值对融资安全的影响。因此,排除融资租赁出租人除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占有、使用义务外的其他义务,与这种交易的客观目的相符。但是,如果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选择租赁物,或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租赁物的确定就不再仅反映承租人的选择自由和利益,而是取决于出租人给定的选择对象,此时,就没有理由仍将与租赁物相关的索赔风险或瑕疵损害加诸承租人。从融资租赁合同的角度看,若出租人干预租赁物选择,出卖人实际上就处于出租人的代理人地位,如同承租人是从出租人那里直接取得租赁物一样,厂商租赁通常就属于此类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出租人与出卖人在利益关系上应作一体评价,出卖人在买卖合同中违约将直接影响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这种类型的融资租赁类似于分期付款形式的所有权保留买卖,担保交易特征也相似。
与之不同,如果当事人在计算租金时并未对租赁物价值作全额摊销,例如留有超过10%的余值,在租期结束时,承租人可以选择续租、退租或留购,且出租人承担设备维修、保养等专门服务甚至设备过时的风险〔2〕,这种交易形式属于普通的租赁还是担保性融资租赁就不无疑问。界分的关键在于,通过合同权利、义务配置,承租人是否有义务确保出租人获得与其购置租赁物的投入及合理利润相当的收入。就此并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考虑因素,如合同约定的租期与租赁物预期使用寿命相当、租期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承租人,或者承租人仅需支付象征性价格而取得所有权、承租人负有以固定价格留购的义务、约定出租人在承租人违约时可以转售租赁物且承租人应补足差额等,均属表明交易之担保性的因素。②在美国,如果留购价格是动产账面价格的10%-25%,动产余值被认为是重要的,该种交易应认为属于真正的租赁。不过,单纯免除出租人对租赁物适用性和适销性,或者将损失风险全部转移给承租人的约定并不足以否定真正租赁的存在。参见R.C.C.Cuming,“True Leases and Security Leases under Canadian 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y Acts,”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7,no.3(February 1983),pp.274,285。相反,如果合同中存在承租人期中退租的约定,尤其是约定承租人在租期届满时应返还租赁物,而租赁物仍然存在可观的经济寿命,则反映出普通租赁的特征。〔3〕我国《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银保监发〔2020〕22号)第5条明确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可以经营租赁业务,因此,如何界分普通租赁和担保性融资租赁必然成为处理相关租赁纠纷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应当注意,不能仅仅依据当事人所使用的合同名称,或者出租人是否具有融资租赁企业身份而对相关合同加以归类或定性。也就是说,对于前述融资性租赁交易形式,不能被当然地认定为担保性交易。
(三)小结
基于融资租赁的典型交易结构,《〈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将其作为担保交易对待。但是,实践中,融资租赁存在多种交易形式,且融资租赁企业通常同时从事普通的租赁业务与担保性融资租赁业务。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具体合同权利、义务配置所反映的交易目的决定了交易类型归属,但类型归属反过来又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比如,租金加速到期条款在融资租赁中属于被法律承认的惩罚性救济措施(《民法典》第752条第2句第一分句),但在普通租赁合同中则属于不被允许的惩罚措施。〔4〕因此,在立法将融资租赁限定为担保交易的情况下,评估当事人具体交易中融资与融物功能的具体结合形态,须对其妥当定性并赋予相应法律效果。
二、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及其限度
普通租赁和担保性融资租赁的关键性差异是,普通租赁的出租人享有完全所有权,而担保性融资租赁出租人的所有权则属于担保性所有权,与其他担保物权一样为价值权,在承租人不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时,仅享有就标的物变价并依法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第1款)。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不仅引发出租人法律地位的变化,而且也在规范整体上引发体系效应。
(一)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规范基础
融资租赁所有权担保权化的直接效果是,当承租人不支付租金时,出租人可以就租赁物价值优先受偿,且租赁物的变价效果亦归属于承租人。也即,将租赁物作为经济上归属于承租人之物予以变价并清偿其债务。由于该担保性所有权的担保对象是租期内承租人对出租人所负租金债务,因此,租赁期满时租赁物所有权的归属状态并不反映出租人所有权的担保功能。
《民法典》第752条第2句第一分句规定,承租人在催告后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此即融资租赁承租人租金债务加速到期之规定。加速到期并不解决租金债权的实现问题,因此,和其他迟延支付租金的情形一样,出租人仍面临如何实现租金债权的问题,但《民法典》并未提供超出通常合同救济措施外的特别救济。《〈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第1款赋予出租人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规定将租赁物变价并以所得价款支付租金的权利,使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
一旦完成这样的转化,面对出租人租金债权的救济需求,合同履行效果维续的规范适用前提就不再必要了。《〈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第2款规定,在出租人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情形下,若承租人主张租赁物价值超过其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时,人民法院仍应确定该租赁物的价值。该解释规定并未表明确定租赁物价值的目的,其规范效果只能依《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规定确定,即出租人就超额部分对承租人有返还义务。〔5〕若非如此,此种价值确定即属徒劳之举。不过,既然将融资租赁承租人所有权完全担保权化,此种价值清算即属当然,何须承租人主张?其中的规范逻辑令人费解。
必须看到,《〈民法典〉担保解释》与《民法典》在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的价值清算效果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规定,若当事人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且承租人已支付大部分租金,出租人因承租人欠付租金而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时,出租人负有价值清算及超额部分返还义务。就文义而论,“大部分租金”至少是全部租金的50%以上。将出租人的超额价值返还义务限于“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能够避免承租人因违约而获取租赁物的升值利益,因此,这种规定在经济激励上是可取的。在相反情形下,也即当事人约定租赁期满所有权归出租人,或者承租人欠付大部分租金时,出租人解除合同后是否仍应承担相同的价值清算及返还义务,《民法典》并无明文。①《民法典》第758条第2款规定的是租赁期满承租人不能返还时的残值补偿,而非如同条第1款那样以合同解除为适用条件,所以无法以之作为合同解除效果的规范依据。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合同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898页。因合同解除后的价值清算及超额返还义务系不同于合同解除通常效果的特别效果,故而,在没有特别规定时,就应当遵循一般规定,当事人并无就租赁物价值作特别清算的必要,这与对《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规定作反对解释的结果一致。如此看来,《〈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第2款统一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的价值清算效果,将《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的特别效果一般化,是在所谓功能主义理念指引下对《民法典》规定的“突破性”扩张解释,据此完成了《民法典》并未反映的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的完全担保权化。
(二)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辐射效应
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后,其将作为担保权益产生相应的效果,由此引发的法律适用问题,兹择其要者分述如次。
1.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登记
出租人所有权登记作为完善出租人权利的措施,其一方面能够保障出租人以租赁物价值确保债权实现的担保目的,另一方面有助于排除第三人的善意取得。从反面看,出租人租赁物所有权登记也有助于标示承租人的资产情况,避免与之交易的第三人对其资产状况产生误判,减少交易风险。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法上对于一年期以上长期租赁不论是否构成担保交易,均强制要求所有权登记的做法〔6〕,正是寄意于此。
我国《民法典》第745条规定,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规定赋予出租人所有权以登记能力,使原“融资租赁解释”第9条第2项有关通过抵押登记实现出租人权利保障的规避措施不再必要;同时,对于不以登记为所有权公示方式的标的物而言,该规定也具有特殊规范意义,即借由所有权登记彰显担保权益。同时,本规定另外产生两项否定性效果:其一,明确融资租赁出租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是“所有权”,因此,知识产权等“权利”不得成为融资租赁的标的。其二,出租人所有权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因不动产所有权变动须“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民法典》第209条第1款),故登记对抗不适用于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故而,不动产亦不得为融资租赁的标的。据此可知,《民法典》规定的融资租赁标的仅限于动产。②反对者或认为,尽管《民法典》第745条规定了出租人所有权的登记对抗效果,但也只能认为其系就动产融资租赁所作的规定,无法推出融资租赁标的不能为不动产的结论。但是,因不动产所有权登记为不动产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民法典》第216条),因此,无从产生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效果。一方面因动产担保情形承认功能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因不动产情形坚持形式主义的立场,会造成《民法典》体系内的价值冲突,显非妥当。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所有权登记为所有权归属的证明,若将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则此时的所有权登记实际为担保权益登记。相应地,出租人所有权登记也并非所有权归属登记,而系担保权益完善登记,即完善出租人所有权的担保效果。③此处借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0条关于通过登记“完善担保权益”(to perfect security interest)的表述。在我国《民法典》上,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在法律形式上自出卖人取得,其无需登记(特殊动产除外);但是,在该所有权功能化为担保权益的情况下,其取得在实质上只能归于承租人,并遵循一般动产抵押的相同变动规则(《民法典》第403条),从而有登记对抗需要。此时,登记并非担保权益取得要件,而是其对抗第三人的要件,故为担保权益的“完善”而非“取得”问题。该种登记是否与普通的所有权归属相符,反而无关紧要。〔7〕出租人所有权登记与其他担保权益登记,主要是抵押登记,形成顺位关系〔8〕,不会发生“他物权限制所有权”的问题,应按照《民法典》第414条第1款第1项确定权利顺位,同时亦有第404、416及456条等规定的适用问题。如果当事人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或者承租人以固定价格留购,也不发生实质上的所有权变动,仅发生出租人配合涂销原所有权登记的义务,与动产抵押登记之涂销相似。
2.融资租赁出租人的取回权
出租人取回权是基于其所有权人身份而享有的将租赁物从承租人处收回由自己控制的权利。取回权是实现所有权人对自有之物的控制权能,旨在避免因受他人控制而遭受不利。最典型者在占有标的物的债务人破产时,所有权人可自破产管理人处取回标的物(《企业破产法》第38条)。在融资租赁情形下,如果出租人所有权被担保权化,在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将不得行使取回权,而只能与其他有担保权的债权人一样主张破产别除权。如果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满所有权归属出租人,前述结果将与这种约定矛盾。为避免形式上的矛盾,在出租人主张取回租赁物时,宜依照担保权益归属清算方式,令出租人同时承担价值清算义务。
与破产时所有权的取回权不同,在所有权保留情形下,出卖人在买受人违反约定时亦得取回标的物(《民法典》第642条)。融资租赁出租人虽然享有类似于保留所有权出卖人的法律地位,但《民法典》并未赋予出租人同样的取回权。除非当事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有此等救济措施的约定,否则,出租人不享有取回权。不过,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目的是迫使买受人及时做出补救(回赎),但因“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4条将《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第二分句的规定解释为担保权实现规定,取回权就变成只能通过协商实现的权利,其实践价值遭到极大贬损。有鉴于此,在融资租赁情形并无类推适用该规定的必要。①融资租赁实践中存在与“取回权”具有相似功能的“锁机”措施,即出租人利用技术手段将租赁物“锁定”,致使承租人无法正常使用租赁物。这种措施通过剥夺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而对其产生心理施压,从而发挥促使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担保功能。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1240页。
3.与动产抵押权的有限统合
在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情况下,其与同样不以占有为权利内容的动产抵押权具有相似性,从而存在统合的可能性,尤其在登记对抗规则、优先顺位规则、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以及破产别除权等方面都表现出统合的必要性。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是否能够统合值得讨论。
一是担保人处分限制规则。在动产抵押情形下,抵押人有权转让抵押财产,抵押权不受影响,但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抵押人以转让所得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民法典》第406条)。但是,在融资租赁情形中,若承租人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的,出租人可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民法典》第753条),表明作为担保提供人的承租人对租赁物无处分权。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承租人的处分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也侵害了出租人的所有权,使得合同目的落空,故而出租人在此种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②这种理解立基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与功能主义的制度构造不符。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1262页。从《〈民法典〉担保解释》采行的功能主义视角看,这显然属于形式主义的理解思路,说服力有限。作不同处理的考虑或许在于,因动产租赁物位置易变、物理存在不稳定,其自由转让可能危及出租人的担保权益,所以应予限制。③此系学者批评《民法典》第406条抵押物自由转让规定指出的理由。参见汤文平:《法学实证主义:〈民法典〉物权编丛议》,《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民法典》颁行后,也有学者主张对第406条作限制解释,使之仅限于不动产。参见刘家安:《〈民法典〉抵押物转让规则的体系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不同观点参见常鹏鹏:《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约定的法律效果》,《中外法学》2021年第3期。因二者的担保功能运作机制趋同,若在动产抵押情形允许自由处分而在动产融资租赁情形禁止处分,就会发生评价矛盾,也与功能主义的担保制度解释构造有违。因此,将二者加以统合应属妥当,且统合的方向应当是对《民法典》第406条作限缩解释,将动产抵押排除于该规则之外。
二是购置款优先规则的有限适用。购置款优先权(PMSI)是《民法典》新引入的担保规则,只要动产价款债权人在标的物交付十日内办理了抵押登记,其抵押权就优先于抵押人在先设定的与该标的物有关的除留置权外的其他担保物权(《民法典》第416条),不论在先设定的是浮动抵押还是固定担保。该规则本来旨在消除在先浮动担保因其所担保债权扩张而对潜在债权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我国《民法典》通过扩张该规则的适用范围而引入更多的政策考量,即以限制在先担保权人利益的方式提高债务人的融资机会和融资成本。〔9〕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担保的正是出租人为承租人利益购置动产所发生的债权,因此,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16条规定,《〈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7条对此予以确认。不过,如前所述,售后回租并不产生普通意义上的融物效果,仅发挥承租人自有之物的融资效用,所以,售后回租情形的融资并不具有为承租人新购资产的效果,出租人的债权不应享有新购资产价款债权的超级优先权。不论是承租人在先设定的浮动担保还是固定担保,其与售后回租形式设定的出租人所有权均应按照《民法典》第414条之规定确定优先顺序。《〈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7条并未关注融资租赁的具体形式而作一般类推适用,显非适当。实践中,融资租赁企业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80%以上为售后回租形式,使融资租赁变为准银行信贷,企业面临极大经营风险。〔10〕若对售后回租形式的融资租赁进一步类推适用购置款优先规则,无疑将极大助推这种融资租赁形式,难谓妥适。
(三)小结
尽管《民法典》并未明确将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完全担保权化,但出于消灭隐形担保的目的,《〈民法典〉担保解释》基于融资租赁典型交易结构将其完全担保交易化,完成了《民法典》并未完成的制度变迁目标。但是,具体融资租赁交易形态对融资与融物两项功能的体现存在程度差异,《〈民法典〉担保解释》在完成制度变迁的同时,尚未结合融资租赁具体交易形态作必要细分,对于售后回租形式融资租赁,尤需特别处理。
三、合同失败情形下融资租赁担保性的维持与排除
在合同无效或被解除的失败情形下,会产生为履行合同而作出的给付发生恢复原状的问题。就融资租赁合同而言,在出租人所有权担保权化的情况下,因担保效果内嵌于融资租赁合同中,在合同失败时,租赁物上预定的担保效力是否仍能维持不无疑问。
(一)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时租赁物担保效果的维持
《民法典》第760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时,租赁物的归属依照当事人的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租赁物归出租人,但因承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的,出租人可以主张租赁物归承租人并由其给予合理补偿。自形式逻辑以观,融资租赁系借用租赁形式而实现融资担保目的,形式意义上的租赁物所有权始终归出租人,不论融资租赁合同有效与否都是如此,仅在合同有效时,租赁物所有权可依当事人约定而转归承租人(《民法典》第757条)。当然,此种归属效果并非强制,若当事人约定合同无效时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自当依约定处理。①实践中,当事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通常仅就租赁期满租赁物归属进行约定,鲜有就合同无效时租赁物的归属进行约定的情况,因此,依约定确定合同无效时租赁物归属的规则实用价值有限。不过,融资租赁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仅在发挥融资担保功能,在合同无效时,前述形式意义上的所有权是否仍应维持其担保性所有权属性,须予辨明。
首先,《民法典》第760条关于租赁物所有权归属确定规则适用于融资租赁典型交易即直租形式。租赁物所有权与购买价款(融资)具有对价性,享有租赁物所有权者须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故而,若融资租赁合同系因可归责于出租人的原因而无效,将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租赁物贬值或意外灭失风险也由其承担,这样的结果与无效引致原因的责任效果相一致。当然,若标的物升值,出租人也将因此而获利。不过,标的物本系由出租人付款而获得,其享有升值利益对其他人并无不公,故无需特别考虑。若合同系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而无效,如果仍将租赁物归于出租人,在租赁物贬值或毁灭时,承租人的地位将反而优于合同有效时的地位,显非妥当。反之,将租赁物归属于承租人,前述问题亦可避免。但是,在租赁物升值时,承租人实际上基于出租人的付出而取得升值利益,与其应就合同无效负责的法律评价并不协调,通过赋予出租人选择权的方式改变租赁物所有权归属,则可消除此问题。可见,《民法典》第760条将租赁物所有权原则上归于出租人,例外归于承租人的处理原则有其合理性。①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租赁物所有权归属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时标的物发生流转的可能性较低,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不过,前述结论仅从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双方角度观察,并未将其他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承租人的债权人,纳入考虑。就此须补充说明两点:一则,未登记的出租人所有权是否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自出卖人而非承租人,所以,在出卖人已完成交付和权利移转后,出租人即享有完全所有权,不论是否登记,其均可基于物权排他性而具有对世效力。②需注意者,《民法典》第745条有关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登记不同于第225条关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登记,本文这里是指前者而非后者。据此,依《民法典》第760条确定的所有权归属就不在第745条的适用范围内。二则,当租赁物所有权依第760条归承租人,但已依第745条完成出租人所有权登记时,该登记是否仍可发生担保权益登记对抗的效果?答案应为肯定,此时,出租人的地位与合同有效时的地位相同。若非如此,出租人将只能择一请求返还租赁物或主张损害赔偿,因前者可能不利于出租人,而后者将出租人地位弱化为单纯的债权人地位,故两者都不能充分保护出租人的利益。相反,若此时仍维持出租人所有权登记的保护效力,出租人的法律地位将得到改善。此种做法源于融资租赁交易本身的特性,并不违背《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第2、3句确认的担保从属性,对承租人的其他债权人亦非不公,因为后者不应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而获得更优地位。
其次,《民法典》第760条不适用于售后回租形式的融资租赁合同。在售后回租情形下,若因出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租赁物所有权转让本身无效,自不发生出租人取得所有权问题。若因承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虽然无效,但当事人设定担保权的意思仍应尊重(同直租),从而,出租人所有权登记仍应发挥担保权益登记的对抗效果,以确保出租人融资债权的实现。由此,在售后回租情形下,《民法典》第760条无适用余地。
(二)融资租赁合同解除时租赁物担保效果的维持
融资租赁合同存在多重解除事由,包括因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而解除(《民法典》第754条第1项)、因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民法典》第754条第2、3项)、因出租人迟延付租而解除(《民法典》第752条第2句第二分句)以及因出租人原因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而解除(《融资租赁解释》第6条)等。在因买卖合同失败或租赁物毁损、灭失等情形解除合同时,不会发生出租人主张租赁物上的担保权益的问题,故与租赁物担保效果有关者仅为后两种解除情形,分别对应出租人解除权和承租人解除权,兹分别说明。
1.承租人欠付租金时出租人解除合同的效果
在出租人因承租人违约而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情形下,《〈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第2款规定,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承租人抗辩或反诉主张返还租赁物价值超过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也就是说,出租人在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时,应当对租赁物进行价值清算,并将超过欠付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租赁物价值返还给承租人。这类似于让与担保的归属清算方式,实际上将《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的法律效果扩张为出租人解除合同时的一般效果。③参见本文第“二(一)”部分所述。
但是,上述扩张解释引发如下问题:既然出租人在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时都必须履行价值清算义务并返还超额价值,《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为何还要规定“当事人约定租期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且“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的适用前提呢?结合《民法典》第746条及第758条第2款规定可知,不论租赁期满租赁物归属如何,在将融资租赁完全担保交易化的情况下,出租人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时,均应有价值清算问题,只不过清算的复杂程度因归属不同而存有差异而已。实际上,前述第二项限制具有明显的利益衡量特征:如果当事人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且承租人已支付了大部分租金,此时,租赁物所有权的实质利益应归承租人,在确保出租人担保利益的前提下,出租人返还超额价值自属正当。相反,如果承租人仅支付少量租金或根本未支付租金,仍然使其享有租赁物超额价值,有以出租人受损为代价使承租人获利之嫌,此时唯有剥夺承租人的超额价值返还请求权,方能彰显前述限制规定的积极价值。相应地,在《民法典》第758条规定的相反情形下,出租人可以主张普通租赁的解除效果,以放弃预期租金收益为代价而享有租赁物升值利益。当然,其也可以要求承租人支付未付租金,并就租赁物价值担保债权实现。
可见,《〈民法典〉担保解释》的扩张解释虽然更加彻底地贯彻了融资租赁担保化的功能主义立场,规范效果明确,但难以取得《民法典》规定解释构造下最佳价值协调的效果。
2.出租人违约时承租人解除合同的效果
对出租人违约致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形,《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相关效果作专门规定。在没有特别规定时,应当适用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定。不过,因存在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分际,租赁物所有权归属应有不同。依形式主义的规范逻辑,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物归出租人;依功能主义的规范逻辑,租赁物归承租人。若租赁物归承租人,其虽然得享有租赁物升值利益,但亦需承担贬值损失,且租赁物上仍有出租人的担保权益,结果对其并非总是有利。若租赁物归出租人,承租人仅需承担普通租赁情形承租人的租金支付义务,虽不享有租赁物升值利益,但总体于其有利。既然合同解除原因在于出租人干扰融资租赁目的的实现,且形式主义规范逻辑更有利于保护承租人利益,因此,在承租人因出租人违约而解除合同时,融资租赁担保功能应予否定。
(三)小结
在融资租赁合同因出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或者因出租人违约而被解除时,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融资租赁担保功能应予否定;在融资租赁合同因承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或者因承租人违约而被解除时,融资租赁的担保功能仍应维持。
四、结论
融资租赁将融资功能与融物功能结合,在法律构造上使融物功能从属于融资功能,从而为融资租赁担保交易化提供了条件。但是,现实的融资租赁交易在融资功能与融物功能的结合及偏重程度上存在差异,《民法典》第735条所界定的融资租赁能够容纳更多样态的交易形式,将这种交易形式一体担保交易化,可能发生对本来复杂的交易形式作过于简单化处理的危险。因此,《民法典》并没有对融资租赁作这样的一体处理,而是为不同交易需求预留了更多的规制可能性。但是,《〈民法典〉担保解释》则将融资租赁彻底担保交易化,所在处理模式上更为简单明了,却丧失了应对融资租赁交易复杂性的制度灵活性,在规范适用上所引发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审慎评估。
融资租赁法律规制的核心在于,法律规制时须评估融资功能的经济实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融物功能对使用租赁形式的借用效果,具体反映为普通租赁与担保交易的界分和规范效果的确定。普通租赁与担保交易的界分应结合具体交易内容,综合多种考虑因素作个别认定,租金的构成或融资成本的摊销方式、租赁物相关经济利益及损害风险的承担、租赁期限与租赁物经济使用期是否相当、租赁期满租赁物所有权的归属以及承租人留购权或购买义务之有无及行使或履行条件等,均属具体交易属性界定的考虑因素。就此而论,融资性经营租赁和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所引发的法律规制问题值得特别关注。按照《〈民法典〉担保解释》的处理进路,一旦将具体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也就同时确定了其担保交易的属性,从这个角度看,前述交易属性界定意义重大。
对于担保性融资租赁而言,出租人所有权在功能上转化为担保性所有权,从而能够在担保效果上与动产抵押进行规范效果的统合。但是,《民法典》在具体规范上并未明确反映出规范统合的方向和内容,在进行解释适用时应特别留意标的物处分限制规则和购置款优先权规则的具体适用或统合方向。对融资租赁合同失败的情形,现有的规范也并不完整,仅在因承租人原因致合同无效或者因承租人违约而致融资租赁合同解除时,融资租赁的担保功能才需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