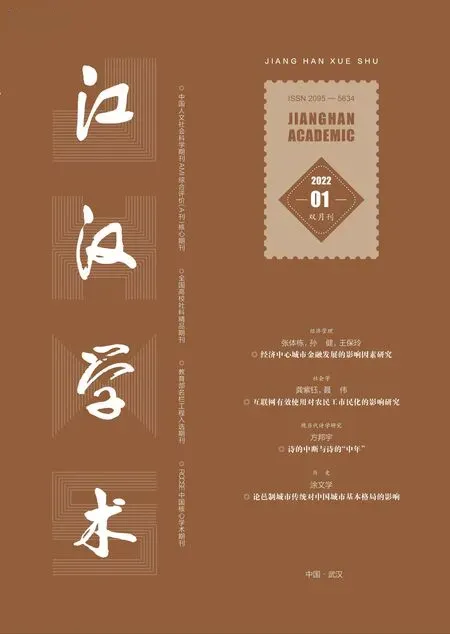论邑制城市传统对中国城市基本格局的影响
涂文学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中心,武汉430056)
关鍵词:城市起源;城;邑;邑制城市;城市发展
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上古城市的兴起
中国的城市至少有五千余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亦即距今五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河套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巴蜀等地区出现了许多可以称得上城市的大型聚落,典型者如距今约五千三百年的郑州北郊邙岭的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市遗址,距今约五千三百年的浙江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四千六百年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市遗址,距今约四千五百六十年的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城市遗址,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河南淮阳县平粮台中原龙山文化中期城市遗址,距今约四千四百年的河南登封县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城市遗址等等。迄至本世纪初,考古发现了64座早期城市遗址,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24座,河套地区23座,长江中下游地区11座,巴蜀地区6座。
人类从分散居住的村居聚落到集中聚居的城市聚落,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政治统治和军事斗争的必然产物。首先,这些城市大都在原有乡村聚落基础上演进而来,即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古城遗址内都有较丰厚的村落文化遗存;章丘城子崖遗址清晰地显示出从村落到城市演进之过渡痕迹:“山东历城的龙山镇,有保存得相当好的板筑围墙的残存;这墙的时代当属于龙山文化……在这里我们知道龙山文化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村落周围建筑防御用的围墙。”[1]湖南灃县城头山周围分布着二百多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聚落遗址;石家河古城周围也分布着许多村落遗址,表明石家河古城是在聚落群发展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当然,城市起源与乡村聚落之间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的观点并非定论,有学者认为,“这些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龙山时代的城邑相对于前此的中心聚落来说都是易地另建,与文献中‘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的记载相吻合,反映的则是从中心聚落到城邑的发展过程中的非连贯性”[2]49。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亦认为邑制城市并不是从农业聚落直接过渡而来的,而是国家出现后因为政治军事需要人工建设的结果,“都市作为开拓者的基地出现,从这点来看是人工建设的都市,不能认为是由古代的农业聚落自然形成的”[3]4。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古代从分散的乡村聚落到集中的城市聚落,“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成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决定性的变化”。[4]上述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我们不作评论。不过在乡村聚落与城市聚落之间存在着过渡环节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城邑的产生,并不是在那些充满和谐气氛的生态聚落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从原始村落到早期城邑,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便是环壕聚落。”[5]12-13聚落范围内开挖封闭环状的壕沟用以安全防卫。从开敞散漫的村居到有沟壕环绕的集中封闭的聚居再到城墙合围的城市聚落,这便是上古国人居住方式从村落到城市演变进化的三部曲。
其次,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上古城市起源提供了经济支持。平粮台城市遗址中存在着的陶器作坊、炼铜作坊以及宰杀大牲畜进行祭奠的遗迹,显现出上古中原地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有相当发展;“江汉为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区系之一,实际也是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区域,为稻作农业的主要的起源地。石家河古城也就是稻作农业不断发展的结果。江汉地区原始农业经济和原始宗教的发展可集中表现在其早期聚落的扩展与演变方面。聚落不断扩展的结果便即早期古城的出现。”[6]同样,长江三角洲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也是良渚古城赖以生存并壮大的经济基础,此地河湖纵横,“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这种江湖甚多,物产丰饶的自然地理条件,正是产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则是这一发展的高峰和最后阶段”[7]。苏秉琦先生更以诗一般的笔调这样描述上古良渚的城乡生态:“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也就扎住了。把良渚比喻成首都,也有道理。”[5]105
复次,上古城市功能具有鲜明的政治军事性质。“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文字、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8]这些早期城市一般都由夯土城垣或石砌城垣,并辅之以壕沟而合围成的方形或矩形聚落,城市内部分布着宗教和宫殿建筑、居住区、墓葬区等,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子崖、平粮台、王城岗“这三个有坚固墙体的区域,以及内部小而具防护性的生活空间,则更似要塞堡垒一样的权力中心”[9]。研究表明,上古城市很有可能就是黄帝、有虞、少昊、三苗、禹夏及其他部族首领的都城所在地,郑州西山古城可能是有熊国国都,“黄帝都有熊,是有熊国君,因此把西山古城称为‘黄帝城’是无可非议的”[10]。淮阳平粮台古城一说为太昊氏族都城,一说为有虞氏部族之城址;而登封王城岗应是“禹都阳城”之所在。《国语·周语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鲧所建之阳城被禹立为夏朝都城。《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世本》及《汲冢书》皆云“禹都阳城”。因之,《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发掘报告云:“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的发现和城址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探索夏代文化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两座龙山文化二期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的地望十分吻合。我们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龙山文化城址可能就是夏代城址,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城址。”[11]章丘城子崖古城大约应为东夷少昊族裔谭人所筑,如董作宾即指出其为谭国都城遗址[12]。石家河古城面积120万平方米,城内有巨大的宫殿或宗庙大型建筑,“这座史前巨城之大,让人目瞪口呆”。研究者认为“应为九黎、三苗首领所居地,即为三苗国都”[6]。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二百九十多万平方米,有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是良渚古国——“成鸠氏之国”亦即天皇氏之国的国都。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及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二、“天下有土,分地建国,置都立邑”:先秦时期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时间行进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出现,由此开始所谓“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关于夏代的城市起源,历史传说与考古发掘相映证,如上所述有所谓“鲧作城郭”和“禹都阳城”。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的城市遗址,学界推测其为夏朝晚期都城斟鄩的可能性地点之一,另外发现可能是夏朝都城之所在的还有河南巩县稍柴遗址等。“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时代并没有发现汉字。夏王朝的都城是考古学逐步弄清楚的几个大城市中的哪一个,目前还没有定论。……商朝以前的时代是有考古学上已探明的‘大国’的。然而,哪一城市才是‘大国’夏王朝的首都,目前决定性的材料还不充足,有待进一步研究。”[13]商王朝统治范围东自济水,西至陕西,北起易州,南到江汉,其统治中心主要在河南中原一带,已经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有偃师商朝、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方国城邑有山西夏县东下冯城址、山西垣曲商城城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等。当然商代方国城邑远不止这些,“甲骨文记商代方国五十多个,方伯名四十来个。……陈梦家曾指出,卜辞中有许多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商王的都邑,另一类是商的族邦之邑。这里所谓族邦之邑,可以考虑为商代的‘二级城市’”[14]。周人灭商后,西周统治的核心区域为陕西关中一带,西周重要的都城遗迹有周原岐邑、西安丰镐及河南洛邑等。丰、镐二京先后为文王、武王所建,《诗·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丰、镐二京为一个都城的两个区域,为西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周末年,因戎人入侵,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丰镐遂废。洛邑大致位于河南洛阳洛河北岸,涧水与瀍水之间,为周公所建。由于迄今为止洛邑遗址并未被考古发现,故其究竟是一城还是双城,具体地点何在,于今人仍然是谜一般存在。[2]63-64西周除都城外还有大量的诸侯国城邑,“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西周的封国都有自己的统治据点,也就是说,无不建城立国,西周初年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筑城数量当以数百计。”[15]58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扰,诸侯蜂起,出于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需要,诸侯们纷纷立国筑城,“千丈之城、万丈之邑相望”(《战国策·赵策三》),衍成先秦时期又一个建城高峰。“据说《春秋》《左传》《国语》中的城邑地名有1016个,从方志等文献中可找出近六百个城邑,因此,推论春秋城邑在一千以上。战国时筑城更多,春秋战国合计当在两千以上。战国时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已成为真正的城市。”[15]63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城邑遗址共有315座,其中主要诸侯列国的都城遗址基本被发掘,共有14座,如洛阳东周王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陕西凤翔秦都雍城遗址(秦早期)、临潼秦都栎阳城址(秦中期)以及咸阳秦国及秦王朝都城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河北邯郸赵国故城遗址、山西夏县魏都安邑城址、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遗址、河北平山中山国灵寿都城遗址、湖北江陵楚国都城郢城遗址以及安徽寿县楚国寿春都城遗址等;较大诸侯国的别都或临时性都城、一般诸侯国都城、战国时期重镇大邑等约100座,如山西襄汾晋国都城之一的赵家古城、河南上蔡蔡国故城、湖北宜城楚皇城、江苏扬州吴越邗、广陵城等;较小诸侯国或附庸国的都城以及列国的一般城邑、军事城堡等约201座,如内蒙奈曼旗沙巴营子、河北怀安赵城、山西闻喜大马古城、河南商水扶苏城、山东滕州滕城、湖北孝感草店坊城、湖南汨罗古罗城、江西樟树筑卫城、江苏武进淹城、浙江湖州吴越菰城等等。[2]84-124
先秦城市除“城”的称呼外,还有“邑”的称呼。许慎《说文》对“邑”字的解释是:“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凡邑之属皆从邑。”这实际上蕴含着两方面意义:其一,“邑”“城”同义。“‘邑’字是一个会意字,‘邑’字上部口形是城邑或居域之象形,下部从卪,像人跽坐形,就是两膝跪地,臀部放在腿上,整个字的字义为人聚会、聚居之所。”[16]由于邑即城,先秦时人便将筑城称为“作邑”,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逸周书·作雒解》亦云:周公东征告捷,“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礼记·祭法》云:“天下有土,分地建国,置都立邑。”《国语·楚语上》云:“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勤。……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王制》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大戴礼记·千乘》云:“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史记·春申君列传》云:“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自为都邑。”所以,商周时期的都城便直称“ⅹ邑”,如《诗经》说商都为商邑:“翼翼商邑,四方之极。”(《诗经·商颂·殷武》)周代早期都城称岐邑,周公营建的成周故址称洛邑,又称新邑、新大邑、洛师邑等。自周至汉,作为城市的邑和里与作为乡村的野和庐相对应,成为两种不同的居住方式。《汉书·食货志上》云:“在野曰庐,在邑与里。……春,全民毕出在野,夕冬则毕入于邑。”《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由是可见“邑”“城”同义。其二,“邑”“国”通称。许慎释邑,开宗明义即谓“邑,国也”。清人段玉裁注云:“邑,国也。郑庄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敝邑。古国邑通称,《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尚书》曰‘西邑夏’、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周代封国多从邑(卪)部。“比如:‘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斄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鄯,鄯善西域国也。从邑、从善,善亦声。’”[16]据统计这类字共有70个,也就是说有70个名称从邑(卪)部的诸侯国,如鄯、邰、邠、豳、扈、酆、鄏、鄻、邙、鄩、郗、鄆、邶、邘、邵、鄍、鄐、鄇、邲、卻、邢、郇、鄋、鄦、鄎、郹、鄧、鄒、鄾、郢、鄖、鄘、那、邴、邿、郯、郚、酅、酁、鄑、郜、鄄、鄶、邧、郔、郠、鄅、郰、郕、酄、鄣、邗、鄫、郭、郳、郱等。
三、“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先秦邑制城市若干特点
由“邑”之上述两层意义,我们得以一窥先秦邑制城市诸多特点。
(一)城市国家体制
与古希腊一样,中国古代也是城邦国家,城邑即为国家,国家就是城邑。“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策·赵惠文王三十年》)“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存千二百国。”(《后汉书·郡国志序》“注”引《帝王世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论述中国古代都市国家起源时,对《战国策》和《后汉书》上述文字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根据中国的古代记载,中国在古时有万国。这里所说的‘国’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邑’,而将其称为‘国’,表示它们互相独立,是不属于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从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的数量既然被称为‘万’,其面积就必然很小。继万国之后,记载又说其城虽大,不过三百丈,人虽众,不过三千家。假如一丈相当于三米,那三百丈就是九百米,如果城郭是正方形的,那一边的长度是二百二十余米。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那人口不过一万五千人。不过,太古的数据是否真的一直保留到形成这样记录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怀疑的。后来都市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甚一日,独立国家的数量逐渐减少,于是当时的形势被投射到过去,才有了周的初年有一千八百国,殷的初年有三千国,而在之前有万国这种计算吧。”[17]65这里,宫崎市定就提到了“国”和“邑”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从国家的性质来看,中国古代是城市国家;从城市的性质来看,中国古代是“邑制城市”。对此,另一位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更有明确论述。斯波义信认为,中国的城市制度以秦朝为界,可以分为“邑制城市”和“郡县城市”两个时期。“四千多年中国都市史在时间上可以整齐地划分为二,前半部分为邑制都市时期,后半部分为县制都市时期。”[3]3
先秦城市国家体制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如宫崎市定所说,个体城市(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城市即一个国家,商、周王朝与方国、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采邑之间往往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藩属关系。“将商、周、春秋、战国的聚落史称为‘都市国家时代’,或许能更清楚地了解实际情况。也就是说,聚落之间的关系是点和点的关系,点支配面的领导国家当时还没有出现。”[3]12这种点对点的城市国家形态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宫崎市定即认为从都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源于“春秋五霸”争雄时期:“五霸出生于异民族,因而与周系统的民族必定有很多不同,特别在政治组织上,它们虽然受到中原都市国家文化的影响,但其发展的方向却并不是都市国家,而是有着很强的领土国家的倾向。”[17]75
其二,城市国家体制下的邑制城市具有强烈的等级色彩,首先是在城邑的规模上中央王朝都城与一般方国城邑有严格的规定,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说法,“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即天子王城方九里,诸侯的国都、公的城邑方七里,侯伯的城邑方五里。另《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东征后“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郑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反映到城邑的建设规模上,如商代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城垣围起的范围就达2平方公里至3平方公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城邑总面积达到10―30平方公里,而盘龙城遗址城址面积仅7万平方米,垣曲古城城址面积仅13万平方米。周代周原遗址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丰镐遗址总面积达十几平方公里,而曲阜鲁国都邑和琉璃河燕都的面积都仅在5平方公里左右。台北学者认为,商周王朝与方国城邑之间的这种规模等差,“表现出区域性方国与中原王朝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悬殊,反映了商周时期王权最终确立、存在着共主支配下的等级城邑制的历史事实”[2]77。
其次是城邑建筑亦等级森严,诚如《左传·桓公二年》所云:“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如城墙,《左传·隐公元年》云:“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杜预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定,王城城墙高七丈,诸侯城墙高五丈,大夫城墙高三丈。城邑道路宽度,“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即王城宽九,诸侯宽七,大夫宽五(周代一轨为八尺)。王城、诸侯都城和大夫城邑的宫室的建筑也必须合乎等级礼制规范:“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周礼·考工记》)宗庙建筑也有相应等级规定,《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按照规定,‘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意谓诸侯不得为天子立庙,大夫不得为诸侯立庙,否则便是越轨行为。”[18]
由此可见,城市国家体制下的夏商周的城市正是一个王权、王朝控制的大小不同的等级体系。香港学者薛凤旋将夏代城市分为四级聚落体系:“二里头文化或夏代的核心地区……优良的农业条件使这一地区人口兴旺,支撑了高密度的聚落以及一个四级聚落体系。”薛凤旋还指出,“商代沿袭了夏代的空间发展规律,以一个四级聚落体系来管理广袤的领土”[19]。王权控制下的先秦城市因其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模和形制,斯波义信指出:“把夏、商的聚落方式用图来表示的话,就可以变成大邑——族邑——小邑,或是王邑——族邑——属邑的关系。”[19]
其三,城市是统治者为卫君守民所筑造,是政治中心而非工商业城市,是“王公的堡垒”而非市民自治家园。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在中国,是否为官吏的驻所是城市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而且城市也是依照官吏的等级来分类的。”[20]265“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20]220与古希腊城邦国家相比,中国商周城市国家有诸多差异。一是先秦城市是王朝都城,方国和诸侯都邑、大夫采邑等各级政治中心城市及军事堡垒,而古希腊城市则是商业中心。“战国以前的城市,是在分封的不断扩展中相继出现的,其作用既然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亦即不是工商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结果。”[21]344而古希腊城市无论是克里特、迈锡尼,还是雅典,其城市都起源于商业并向海外拓展。“在城市历史的初期,欧洲如一潭死水,野蛮纷争的原始居民生活其间。靠近欧洲所出现的城市的最早迹象是在克里特——希腊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在这里长浆船用于运送重要的贸易物品,特别是橄榄油和锡(后者被用来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在来自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和思想的滋养之下,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在这里萌芽了。”[22]29政治城市与商业城市的性质不同,使得二者在市政设施、居民构成乃至城市精神诸方面都大相径庭。大抵而言,先秦城市市政建筑以宫庙为中心,而市政广场、神庙和商业贸易场所则是古希腊城市里的重要建筑;这种为经济、为艺术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远比商周时代的中国人为政治、为权力较智伐谋和武力厮杀更具人性化和个性化。二是先秦城市国家是一种“共主支配下的等级城邑制”,无论是商代的方国城邑,还是周代的诸侯都邑,每一个城市并非一个独立的城市个体(春秋战国时期另当别论),其在血缘宗法、权力统属乃至城市规划建设方面都必须严格等差,合乎礼法。而古希腊城邦则相互独立,相互竞争,“与过去的模式相同,希腊仍是一个众多小城邦组成的群岛之邦,这些小国以城市中心和周边的腹地为核心。各个城市(或城邦)之间竞争激烈,不仅表现在常规的战争上,也体现在对国外市场、熟练劳动力、艺术的争夺上,甚至是运动竞技上的较量”。个体城市的独立和城市间相互竞争孕育了古希腊人城市共同体意识,这恰是先秦国人所不具备的。“在这种竞争精神驱动下,希腊人创造了包含艺术、雕刻和戏剧在内的高度个性化的思想文化,显示了当今西方城市的典型与特征。希腊人孕育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城市意识,这种意识同数百年后的城市居民产生共鸣。”[22]31-32三是先秦城市为各级统治者所筑制,所占据,所主导,无论天子所居之王城,还是诸侯所居之都邑,抑或卿大夫所居之采邑无不如此。先秦城市的居民包括王公贵胄以及士农工商,在这个居民构成中,王公贵胄居于社会上层,主导着国家乃至城市的一切;士——读书人或为官僚、谋士或为农耕,“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管子·大匡》),大都是政治和权力的依附者。先秦诸子百家尽管学说纷纭,思想驳杂,但主张大一统、维护君权专制和封建等级制,为君主和朝廷治国驭民提供思想理念和出谋划策是所有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共同特点。主张集权专制、刑名法术的法家自不待言,宣扬民贵君轻和讲究无为而治的儒道二派在国家和城市治理理念、路径上舍民治而崇官治,其学说的实质仍然是官本民末的专制主义。如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完全排除庶人——普遍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这与古希腊哲人倡导民主政治,申张公民权利的观念大异其趣。“不像其他地方的哲学家关注神学和自然界,希腊的思想家思考的是公民个人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捍卫公民集体(Koinonia)的健全。亚里士多德评述说,公民就像船甲板上的水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船行中船只保存完好’。在雅典产生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理念——如立法者梭伦所言——公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22]32与古希腊城市工商业阶层相对独立并成为社会主流群体不同,先秦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官营工商业,工商阶层也是国家政治机器的一分子,“有许多氏族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专业氏族;或者较小的家族是工商业者。根据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应享受国人的待遇,居住城内,受到保护。事实上,周代的工商业生产已被正式纳入行政系统,算是政府的一部分,即‘工商食官’之制”[23]15。四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出现如古希腊城邦的城市自治和“市民社会”,产生民主甚至共和制度。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城市共同体”和“城市市民”都有特定的含义,城市共同体包括防御设施、市场、自己的法庭、团体性格、城市和市民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等等;市民并非泛指城市居民,而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就政治意义而言,市民包括享有特定政治权利的所有国民(Staatsburger)”[20]262。韦伯认为这种城市共同体只在西方存在,“然而在西方以外,从来没有过以一个自治团体(Gemeindeverband)形式存在的城市”[20]265。具体到中国先秦及古代中国城市,马克斯·韦伯亦颇为武断地指出:“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市民’与‘城市共同体’的概念。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自治’只是个职业团体及村落的特色,而非城市的。”[20]220中国古代城市未能如古希腊城邦那样独立自治,建立起市民主导的“城市共同体”,根源仍在于邑制城市政治中心、军事堡垒和农业型聚落的基本功能所致。“城既然只能由统治阶级来建,并且是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的,则古代城市自然是一个政治中心,是整个统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实施统治的发号施令的中枢或首脑。这样的城市,当然就不能使之自由发展。……等级不同的城市,驻扎着等级不同的统治者,即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及为其服务的大小臣工直至抱关击柝。《荀子》说:‘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城市就是这些人的驻在地。这样的城市,只能紧密地结合在封建统治体系的结构之中,而不能脱离这个体系作离心的发展,亦即向自治的和独立的方向发展。”[21]344
(二)农业城市属性
古代都市基本上是一种农业城市,“大邑也好,族邑也好,小邑也好,在城外都没有人们定居的村落(散布的村落),农民或者居住在城里,至少也会居住在城的周围……从其人口构成来说或可称之为‘农耕市民都市’(马克斯·韦伯语)”[3]7。对于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居住在城邑,先秦及汉代史籍不乏记载,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五谷毕入,民皆居宅。”《汉书·食货志上》云:“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庄子·让王篇》说颜回在城内城外都有农田产业,宁愿务农,也不愿意出仕:“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赵冈认为:“周人是以耕稼起家的民族,擅长农业生产,想来他们在征服殷商以后不会立即放弃农业生产。周王室派出执行武装殖民任务的氏族,其中有些成员在到达辖区后仍会坚持从事农业生产。周代城市中注定了会有相当数目的农民,他们是国人身份,要住在城内,受城池保护,同时从公家领到一郭内或附郭之土地,从事耕作。”[23]16赵冈、张继海都曾以《史记》史料为例,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居民构成中农业居民的存在。“《史记》卷82《田单列传》:‘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数年不下。’莒和即墨何以能坚持数年之久呢?除了城防坚固,有粮食储备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两座城市中有相当面积的农田,可以生产自救。……既墨和莒都是齐地有名的城市,但城中都是农民。”[24]赵冈谈到齐国都城居民成份时,认为农民占有相当比例:“《国语·齐语》中说齐国都城共分为二十一乡。乡是当时城中的行政区划。据记载,这二十一乡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六’。士是政府的行政人员,占城市居民七分之五,似乎太多。很可能此处是士与农并为一类,与工商相区别。”[23]40
古代“农业城市”并非中国独有,欧州、中东同样有过存在。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上,城市与农业的关系绝非清楚而单纯的。曾经有过(现在也还有)‘农业城市’(Ackerburgerstadte)的存在,这样的城市是个市场中心及典型市区行业的所在地,因此与一般村落截然不同。”他认为这类城市一般存在于中小城市中,大城市类似情形则鲜见。“西洋古代的‘市民’实际上是‘农耕市民’。”[20]204-205
先秦时期城市乡村化乃是由当时农业经济占居主导地位、农民比例居绝大多数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农民城居、农田阡陌与手工作坊杂处,城市形成早期的中国城市呈现出的是城乡不分、城乡一体的场景,所以傅筑夫干脆就说“战国以前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些有围墙的农村”[21]345。
由于城市政治军事和农业性特征,中国古代城市虽然也有商业、市场和手工业,如商朝的都市“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为了供给这些大都市的庞大人口以及王室贵族的豪华生活,帝国需要通过一个聚落系统在广大的领土幅员内有效地开发、组织各种资源,管理所涉及的双向物流”。这就是说,先秦城市虽然也有商业、市场和手工业,但这都是因统治者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先秦城市本质上不是经济性的工商业城市,而是一种非生产的消费型城市。“所谓‘君侯城市’指的是,城市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宫廷及其他大家计的购买力维生,此种城市类型相似于另外一些城市,定居在那儿的工匠及其商人的经济机会主要也得看城里大消费者——即‘坐食者’(Rentner)——的购买力而定。”[20]201
(三)防御与祭祀功能
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乔尔·科特金指出,城市是神圣、安全、繁忙之地,正是这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早期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所谓“神圣之地”,“宗教设施,如庙宇、教堂、清真寺和金字塔,长期以来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它们向人们宣示,这些城市也是神圣之地,直接与掌控这个世界命运的神祗之力相连”。所谓“安全的需求”,“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的过程中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很多城市最初或是作为逃避游牧民族的掠夺,或是逃离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守法纪现象的避难之地而形成的”[22]5-6。与古希腊和中东城市一样,早期中国城市同样重视安全和宗教,具有军事防御和宗教祭祀功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兵戎是当时国家两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国家——王朝权力中心城市里最突出的地标性建筑物——城墙和宗庙,即是这两件大事的物化形式。
由于国家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城池和奴隶常常兵戎相见,于是城市的防御功能凸显。早期城市大都高筑城垣,商代城邑除殷墟外都是有城垣的城邑,两周时期的王朝都城虽然没有城垣,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都普遍筑有城垣。关于城墙的功能作用,历来有多种说法,有防洪说,如长江中下游和成都平原古城;有防洪与军事防御双重功能说;有宗教和礼仪象征说,如三星堆;有君民划分功能说,如辉县孟庄、襄汾陶寺、天门石家河、余杭莫角山、凉成老虎山、黄陂盘龙城等[25]。但城墙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军事防御。史籍记载表明,人类筑城的原初动因就是为了卫君守民,如《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左传·襄公七年》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穀梁传·隐公七年》云:“城为保民为之也。”《易·坎卦》云:“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诗·大雅·板》云:“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孟子·梁惠王下》云:“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为也。”《墨子·七患》云:“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管子·权修》云:“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明人孙永泽对城市卫国安邦、捍官保民的历史及作用更有总结性概述:“人君者……设为城郭沟池以守其国,以保其民人,传记谓其制自黄帝始。历代建国,必有高城深隍,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卫捍百官万姓,其所系甚重,其为功不小。”(孙永泽著《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九)先秦的城邑无论是否有城墙存在,都与人们的“安全需要”有关。有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王朝都城如殷墟、丰镐及洛邑未筑城垣,乃是因为王朝统治权力强大,城市无安全之虞,恰好从反面印证城墙的防御功能。“三代都邑城垣或有或无,尤其是西周时代的三处王朝都邑均未发现城垣,应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和王权的确立,三代王朝都在王畿的周边地带设置了许多可直接控制或有友好关系的诸侯方国,这些方国成为拱卫王畿地区的屏障和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重要支柱。同时,与前此的龙山时代相比,这一时期战争的性质和形式也有所变化,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三代王朝为核心的政治军事联盟与叛服无常的周边邦国部族之间,也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而在王畿及邻近的周边地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减弱。国势的强盛和以周边诸侯方国为屏障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种王朝都邑与诸侯方国都邑筑城自卫这种被动保守的防御手段成为不必要。”[2]82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攻城略地,城市防御功能凸显,人民安全需要急迫,于是各国纷纷广筑城池,是为中国古代又一次筑城高峰。“因为列国战争激烈,故墟重建,旧墙修葺,小城扩大,卑邑作城,大城邻近复有小城,所谓‘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于是造成‘连城数十’的景观。”[26]
如果说,城垣在三代城邑中并非普遍存在,那么宗庙是先秦都邑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墨子·明鬼篇》)二里头三期4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三代宫庙之雏型;殷墟遗址中东北部有占地面积颇大的宗庙宫殿基址;周朝先祖古公亶父营建周人都邑时,首先建设的便是宗庙,《诗经·大雅·緜》云: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古公亶父筑城之前先建宗庙,反映了宗庙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在城市建筑格局中的中心位置,而且在维系宗族——王朝统治的先定性、合法性象征意义。夏商周三代都是宫庙一体,人神共处,但以庙为主,“寝不逾庙”:“君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礼记·曲礼下》)所以,“先秦宫室在宫庙一体的总格局下,宫寝与宗庙的地位并非等重,作为维护王权神圣性的宗法制度的载体,宗庙是宫殿宗庙区乃至整个都城的核心之所在”[2]80。三代王朝对宗庙的这种极端看重,既是出于古代社会人们对不可知的神灵的某种神秘感和敬畏心,更是王朝统治者企图藉此获得“天命神授”合法性和祖先庇佑其宗法统治万世一系的长久承续。也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宗法制特征,先秦城市“神圣之地”以宗庙为主的建筑及敬天法祖的祭祀礼仪与古希腊和中东、印度有明显不同。如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中的所谓‘内城’中居支配地位。在这片内城的城墙之中,神庙与王室的宫殿和显贵的宅邸比邻而立。这种布局让整个城区充满着一种神祗庇护下的安全感”。再如印度,“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也是把标志性的宗教建筑安置在城市中心,这两个城市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境内。它们与其保持贸易联系的苏美尔相类似,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主要的信仰似乎集中于‘生育女神’,这是与中东的丰产崇拜相同的重要特征”。宗教建筑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以及对于神灵的崇拜,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城市文明具有契合共通之处。然而神权在王朝政治统治中扮演的角色及崇拜、供奉、祭祀何方神圣,中国三代显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大体而言,中国是王权统治而并非神权统治,尽管“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但国王——王权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三代敬天,法祖,与古希腊、埃及及印度的诸神崇拜亦颇违异。所以,乔尔·科特金对“神圣的起源”与早期城市文明关系格局中这种“中国特色”有精彩论述:
在中国,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商代的统治者将神庙置于城市空间的中心。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天行道”的原则。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22]6-11
总之,夏商乃至西周的城市,奠定了中国城市的一些基本格局,并对后世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的范例。公元前2世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22]18更进一步言之,先秦邑制城市那种非自治的官僚制的传统,直启秦汉以后郡县制城市体制格局,诚如斯波义信所论述,“它没有朝着成为古代民主制转变为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孕育地的方向发展,而是转向了成为古典官僚制温床的方向”。由秦至清延续二千余年的郡县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郡县城市,其城市功能之政治军事而非工商经济中心、城市市政体系之官僚管治而非市民自治的基本特质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实际上正是‘县’制从最底层支撑了这种官僚制并使其发挥机能,这种特点在现今中国都市制度中还清晰可见”[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