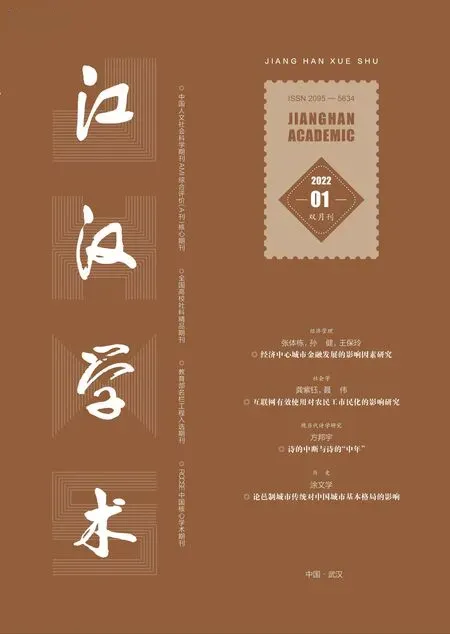走向“少数”之“普遍”
——拉维科维奇的希伯来语诗歌生成论
蔡 玮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达莉娅·拉维科维奇(Dahlia Ravikovitch 1936—2005),被认为是以色列建国后最重要的希伯来语女诗人①。幼年缺失父爱,青少年时期的叛逆个性造成与周遭环境疏离,以及成年后情感与婚姻的坎坷经历,都成为拉维科维奇后来诗歌创作的重要精神背景。在国防军完成兵役后,她进入希伯来大学学习文学,后当过记者与教师。她所经历的多次中东战争促使她积极投身和平运动,并留下大量富于批判性的作品。她一生出版了8部诗集、3部短篇小说集、8部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了大量英语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虽尚未广泛进入汉语读者视野,拉维科维奇的诗歌地位却已然被奠定。其诗作在以色列拥有广泛读者,且获包括“比亚利克奖”(1987)、“以色列奖”(1998)、“总理奖”(2005)等多种奖项。以色列文学最高奖“以色列奖”的颁奖辞概括了她的诗学品格:“她的诗一方面是有关‘丧失’‘不可能之爱’和‘存在的绝望挣扎’的个体见证,一方面是普遍真理和普遍经验的表达。其作品的特质表现在:丰富精致的诗歌语言,通过融进日常习语而形成复杂的语言织体,个人的抗议之声结合了集体的声音……这使她成为我们时代卓越的希伯来语诗人。”②
拉维科维奇诗集《低空盘旋》(Hovering at a Low Altitude)[1]的两位英译者曾获美国笔会翻译奖,在成书过程中他们与拉维科维奇本人充分协商,从诗人全部创作里选取160首优秀诗歌结集而成,无论从整体的代表性还是译文出色程度上,都不亚于她的第一本英译诗集《火的衣裳》(Dress of Fire,1978)。而《火的衣裳》以其突出成就已被布鲁姆收入《西方正典》经典文学书目(中译为《火装》)[2]。
结合德勒兹与加塔利③提出的“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理论和“生成”(becoming)理论,我们发现,无论在其诗歌的先锋姿态、僭越品格、反抗父权传统方面,还是在后期的批判强权与反抗暴力方面,拉维科维奇一直都站在少数立场并为生成一个“少数派”(minority)去创作。我们从中可感受到她在反抗传统权威获得女性权力的同时去“生成—女人”,突破既有文学格局“生成—女性作家”,到走出自我的民族身份和作家身份“生成—巴勒斯坦平民”的“生成—他异性”的写作轨迹。其个体书写和集体叙事、内在隐匿性与表达的集体装配互为交织起来的逃逸线路,凸显了诗人的当下意识和积极回应少数集群声音的伦理承担。
一、生成—女人:克分子与分子的政治
拉维科维奇、阿米亥和扎赫被认为是以色列建国一代的三位杰出代表,但在作为男性专有舞台的希伯来诗歌传统中,女性文学的谱系几乎不存在[3]。一方面,因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历史,希伯来语逐渐失去日常交际功能并主要用于宗教祈祷和经典文本研习,成为了男性专有语言。而担负家庭生活责任的犹太女性在父权文化传统下长期被排斥在犹太经典教育门外,失去了掌握希伯来语的机会,更遑论用以阅读和写作。她们使用的是流亡期间创立的作为“妈妈语言”的意第绪语。该语言和女性身份一样,被认为是属于家庭日常的、琐屑的、情感的东西。另一方面,部分女性虽然在20世纪初接受了犹太启蒙思想的影响,通过教育开始掌握希伯来语,但还是很难创作出符合男性文学批评标准的文学作品。犹太复国运动话语里的男性中心色彩更为浓郁,男性诗人常自拟时代先知,承负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批判者的使命,女性作家被认为游离于战争、集体友爱和英雄主义等民族性经验外,从而被边缘化[4]。
拉维科维奇的第一部诗集《一只橙子的爱》(1959)就使用了“纯粹典雅的《圣经》式希伯来语,夹杂《密西拿》《密德拉西》中的短语,讲究节奏韵律,追求对仗工巧”[5],不同于以色列建国后同代年轻诗人们因逆反建国前历史进步的大叙事风格而注重自由体形式、散文化风格、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社会图景的总体写作趋势,其典雅甚至古奥的诗歌语言与各种犹太典籍甚至仪式咒语形成丰富的互文肌理,使得诗歌既充满神秘主题与精神暗示,又具有回环往复的韵律感与歌谣意味。对作为男性创作专属领域的古典诗歌来说,拉维科维奇的这种古雅之风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僭越性质,毕竟未曾有女性作家能够基于女性的细腻情感创作出具有如此经典特质的诗歌作品。就希伯来女性诗歌而论,“拉维科维奇比她之前的任何一位女诗人都更广泛地闯入了男性正典的领域,破坏它的根基”[6],因此不管是对于民族历史、文学传统的等级制度,还是对于建国后的文化心理和文学风格趋势而言,她在最初的创作中就“敢于是一个例外”[6],敢于走上一条不合时宜的反叛路线。在多数语言的少数运用中,颠覆语词内部的权力关系,在支配性的男性辖域内实施“生成—女人”的解域化政治运动。
德勒兹认为,“所有的生成都是弱势性的,都经历着一种生成—女人”[7]412,所有的生成皆始于和经由生成女人,因为正是女性让人类向新的可能性敞开,代表着不被“男性那理想化的理性、力量、支配性和活力所定义的”[8]生命的多样可能。白种以色列男性建构了二元对立的多数框架,并以此衡量、分类与规范非白种人、非西方人、女性和儿童,而他们最先窃取的是女孩的肉体以制造可对立的有机体。如同《机械玩偶》,女性的身体是被剥夺而又重新组装起来的有机玩偶,在一晚偶发的“逃逸事件”中自我瓦解并走向自身的“生成”,可是这一失控事件立马被“去事件”化,被重新编入坚固冷酷而宏大的二元系统的“多数”之中:
那个夜晚我是一个机械玩偶,
向右转向左转、向所有方向转。
我摔了一脸,摔成碎片,
他 们 熟 练 地 将 我 修 补 齐 整。[1]63(李 以亮译)④
失控的玩偶一旦展露其个体性,展露其“向所有方向”旋转的自由和本真,立马便碰壁摔跤,被作为一个需要“修补”的疯癫者或病人。在“多数”主体的目光期待和调教下,女孩以失去其感性、活泼的丰富身体样态为代价,成为一名符合“多数”要求的“理想女性”——“举止考究而顺从”“舞步得体而标准”,被编进“克分子”⑤网络组织,被剥夺自身原始的“身体”和“生成”。然而这个舞池上的感性失控事件偶然释放出的“女性粒子”并不具有渗透能力,很快便又更深地落入她想逃避的辖域组织中,沦为“与猫狗做伴”的家庭宠物。因此,被剥夺了自身“生成”的女性首先“必然要实施一种克分子的政治,其目的就是重新赢得她们自身的有机体、历史和主体性”[7]390。虽然不存在“生成—男人”⑥,但女人的生成是在“一种彻头彻尾的男人的生成—女人之中”[7]413,因为生成之中的主体始终是一个克分子实体(molar entity)。
女性作家同样如此。拉维科维奇那些独具女性特质和鲜明风格的诗歌,使得女性文学开始从希伯来文学传统里的边缘地位挤入文学地图,赢得“我们作为女性作家……”的表述主体。《牛蛙》是诗人为女性诗歌在希伯来文学传统版图上争得一席之地的非凡之作:
灿烂星空是一个无底的海。
在这样一个夜晚,很易看清
“绝望的泥沼”究竟有多深。
在一群牛蛙中间,在小池塘
有一枝黄色百合花,离群索居。[1]111
不是去抓住克分子宏观树形组织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获得安全感,而是直视进暗夜星空的深渊,勇敢面对一种无身份无根基的恐惧,将深渊的边缘折叠进池塘的内部,隔离出属于水百合自身的湖心荒岛。诗中,象征男权力量的牛蛙围困了池塘中心一朵精致的水百合,“为女性在希伯来诗歌领域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视觉隐喻”[9]。诗歌交织着源自经文典籍或传统诗歌的互文音响。副题标明献给希伯来前辈女诗人丽娅·戈登伯格(Leah Goldberg)(且有意仿照戈氏风格),还呼应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著名的短诗《我是无名之辈》。打破时空界域,诗人将自己和戈登伯格、狄金森,集聚为一个新的机器配置,试图冲破男性传统诗歌版图的辖域边界,在文学史单一的男声合唱中,植入一个迥异的女声表述,掀起解辖域化的生成运动来改变诗歌版图的权力格局。狄金森诗笔下的青蛙是被诗人轻蔑的:“做个,显要人物,好不无聊!/像个青蛙,向仰慕的泥沼——/在整个的六月,把个人的姓名/聒噪——何等招摇!”[10]拉维科维奇呼应了狄金森,将那些活跃在一种“共名”状态下作为预言者的男性诗人,化身为喧闹沼泽里的牛蛙,直斥“他们太瞎”。在他们笔端运作的是超编码机器和树形同质逻辑;他们将女性划归到大自然和母性领域,赞美她们的伟大奉献,并将女性书写从民族体验和主流书写中排挤出去。如以色列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在《水池》中将女性隐喻为水池,被作为男性的大树所穿透、保护,而水池成了森林欲望的镜子,是男性用以施展权力的对象[9]。自然世界作为男性诗人创作的纹理空间,成为他们专属的诗歌世界,《牛蛙》则揭开了“水池”这个浪漫主义的虚幻面纱,揭示了被喧闹和泥沼充斥的真实面目,击碎它作为男性欲望之镜的幻象,将残酷而混乱的现实导入现代希伯来语诗歌,从而激活了一股解域和解码之流。
生成—女人的分子性运动伴随着克分子实体的主体意识。然而局限在于此主体意味着始终处于与二元性机器的关联中,要么耗竭分子性来源要么中止那股变化之流从而导致生成的失败,因此要超越这种克分子的政治,“构想出一种分子性女人的政治,它潜入到克分子的对抗之中,穿越于它们之下,之间”[7]390。这种分子的潜入在拉维科维奇的诗中还常常与“欲望”主题相结合。诗人早期代表作《一只橙子的爱》呈现了欲望的这种侵入式的在克分子主体内部进行解辖域化的力量,揭示了欲望机器的生产性:
一只橙子确会
以生命和肢体爱,
爱那个吃下它的人,
那个剥开它的人。
……
然后,它侵入他
皮肤下的肉。[1]49
希腊神话里的“金苹果”(橙子)⑦指涉欲望非人的和无界限的属性,它引发了十年的战争,最终以伪装的形式(作为战利品的木马)侵入欲望主体(特洛伊)内部制造了毁灭。在诗中,欲望对象和欲望主体在这只无器官的植物体(橙子)中交汇,经过侵吞和被侵吞的运动,植物体成了“强力得以流通的地方,是权利、能量、生产得以发生的地方”[11]。而被侵吞者和被侵袭者也在这个邻近场所中变得不可区辨,在共同释放的爱欲粒子中“生成—女性”。这既是女性个体全新的生成性感知,又是欲望机器自身运作的效应,是超越了克分子主体的集体装配的表达。欲望的僭越性力量、少数者的呼喊,就这样出现在拉维科维奇以极其典雅而富有韵律——在传统专用以表达崇高理想——的诗歌语言中。
二、生成—他者:对集群共同体的回应
拉维科维奇后期的创作笔触更多地向着这个世界的处境打开,向着少数群体的未知和可能的遭遇打开,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及其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尤其反对战争暴力对人性的毁坏和对生命的摧残。诗人亲历了男权社会中的全部压抑、苦闷和挣扎,她对受压迫、受损害而没有权力的少数人群,尤其是被民族主义所侵害的外部与他者,抱有天然的亲和感,并将与他者相遇,向着他者打开自身的生成过程之新异感受写进诗歌。这是对“少数集群”之呼唤给予的回应,并“在”少数之中“为”少数呼喊和歌唱的伦理承担。在一次访谈中她说:“如果我不能感受到自己的压抑,我也不能体会到那些被压迫者的眼泪。”[1]253这种敏锐的感触力,也意味着抒情主体在向“集群多元体”(pack multiplicities)⑧的生成过程中,在无规定的身份认同中,不断增添着新的可能性。
在德勒兹看来,女性、孩子、动物或分子等“少数派”总是有剩余的成分可逃离其自身被既有的理性秩序所形式化与有机化的多数界域,从而开辟出面向未来的全新道路。“生成”不是去获得某种固定形式,而是达到一种不可区辨的邻近区域,“其中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再也不可区分”[12]2。这区域属于一个尚未被规定的到来中的少数集群,由于并非事先存在亦不能预见,由于突如其来攫住当下而总是独异、鲜活。它的恒久敞开具有对尼采所谓的“太过人性”的批判力量,也包括诗人对处于弱势方过度同情所导致的目盲,未意识到这种同情之根源可能来自树立“人性”陈规的多数群体。因此诗人的自我对抗自我批判就是一种呼应“少数集群”的“生成—他者”。
《低空盘旋》一诗描写了一个无辜的牧羊女被多数界域中的男性残忍杀害的事件。叙述者“我”,一个多数界域中的女性,在安全的位置(盘旋在现实上空)看到了整个暴力过程,然而字句间隙渗入从“我”分裂而来的牧羊女的他者目光,以反讽那种“我不在这里”“我未曾看到任何东西”的非少数立场:
我不在这里。
我在荒凉的山峦的上方
在遥远的东边。
没有详细描述的必要。
只需简单地投掷,盘旋在上方
以风的速度旋转。
可以找个逃避的借口并说服自己: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1]175
对于无辜牧羊女的受难,诗人在此感同身受,并且交织着自责、无奈和没有一个“旁观者”可以免责的复杂情感,而诗人、读者,无论来自哪个民族,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漠然的方式参与了侵害事件。对苦难的无视和冷漠,对真相拷问良心的逃避,对大地、对集群、对当下此地的逃离,这种低空盘旋的姿态与国家社会和超编码机器,构成了同谋关系,组建了“共振装置”(apparatuses of resonance),他们携手将暴力和灾难投掷在无权者和弱势的少数群体身上。此时诗人经由异国牧羊女的眼睛将背叛的笔触转向自身,将辖域化的作家领地解辖域化,因为“生成—他者”“先于”并且“外在于”一个诗人的主体身份。事实上,在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误认为我们充分参与了是非判断和社会公义的声张,未曾意识到这也无非只是在现实上空“简单地投掷”,而依旧并且继续麻木于发生在身边的人们的不幸,麻木于那些践踏他者和未知的排异性暴力。“写诗是不够的”,牧羊女警醒着我们。第一人称的冷峻叙述,也是诗人对自己早期诗歌追求唯美效果、为了形式精致而舍弃意义,常借想象异域旅行以远离当下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思,也是对同时代诗人逃避当下文化与政治问题的伦理谴责[13]。写作是微观政治的运作,是发现并回应那些总是在总体化之线下变化着的逃离着的生成之流。德勒兹的文学本体论差异指出:“文学‘是’什么,差异于文学所呈现的生成的权力或力量”[7]105,作为后者,文学有其探索自身的方向:创造并呈现不能被理智所把握的新异感受(sensation)。
《死于大火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如此触目惊心,更是让人对“当下”的“直接感受”难有任何回避的可能:
大火一把将他攫住。
——这里没有任何隐喻——
……
上帝!它们在燃烧!他叫喊。
这是他在自我保护时能做的一切。
他的肉在屋子的木板间燃烧,
木板是助长火势的第一步。
他已经没有意识。
大火燃烧着他的肉体,
对未来的感觉,
他对家人的记忆麻木了。
他已经失去与童年的任何联系,
他并没有要求复仇、救赎,
或者看见第二天的黎明。
他只是想让燃烧停止。[1]217
一句句诗行展开了在时间中绵延的苦难本身,它在意识还未到来的时候一点点啃噬生命,作为过去式的反思或将来时的想象,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冷峻、坚实的诗句映射出某种利器的寒光渗透进灼烈的身体之不可承受的承受本身,诗人逐渐生成为燃烧着的阿拉伯人,而燃烧者生成为女诗人自身。“生成的行为是一种捕获、占有、增殖,但绝不是复制或模仿。”[14]13占有和增殖意味着将异在于民族界域和多数作家的新型感知经由生成为阿拉伯人的“个体间身体”(集群)而生产出来,这并非独特的个人感受,而是在生成中抹掉了自己,传达出集体的杂音(并非异口同声),具有直接性的政治批判力量。集群外在于既有秩序,但它内部并非一个封闭的同质群体,而是在时间中向着未知开放而变化多样的感觉组块。少数集群不指涉被男人所建构和规定的女人,也不指涉被以色列人所定义的阿拉伯人,而是尚不存在的民族,那些“即将到来的人民”[7]494。
这种非个体书写的“集体表述装置”(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理论是德勒兹论卡夫卡时提出的,装置代替传统的“系统”“结构”“形式”等概念强调其中的异质性、开放性和生产性;而集体表述意味着一个非主体、非个人的诗歌表达方式,且不能将感觉诉诸作者个体经验或其才华禀赋,而是一种力量之实验性运转中集群的多样生成。诗歌《变形记》,如同弗兰西斯·培根三联画作中的“无器官身体”,回应了卡夫卡从一种生命形式向全然他性的多样生命关系去生成的诗歌实验,呈现从猫的“毁形”走向“变形”的“暴力”、“无形体”和“他者”的生成之“疯癫”症状:
那猫发脾气了。他用尾巴鞭打自己。
开始,他用右爪抓左爪,
然后伸出爪子,刺进他的眼睛;
他同样掘进自己的另一只眼睛。
浑身被血浸透时,这只猫感觉最好。
他撕碎右边的大腿肉,
当然,把左边那只,也猛拽出来。
很快,他的身体变成一团肉泥。
他绝不是一只非理性的猫。
他屠戮自己,却没有痛苦,
因为他一生渴望变为一只狗,
牧羊犬或狼犬,都是一样的。
猫的疯狂撕扯,失控自戕,如卡夫卡作品中的所有暴力,关联于已发生的或将临的灾异事件,也关联于存在之基的丧失和内在最深的虚无。然而疯狂和失控的自毁最终却并未被虚无所摧毁,某种力量将它交还给这个既是逝去的又是全新的世界,这不可见的力量在“交还”与“变形”的过程中得以可见。这一具不再能分辨爪、眼睛和大腿的混沌之肉,如同撕碎了的、封闭的孤独“自我”之幻觉,撕裂了一只孤傲高冷的猫的生命形式。这一具无器官身体,这一团轻盈的“肉泥”并未垮掉,而是被某种细弱之物所托举,某种变形之力、转换之力、不可摧毁的剩余之“肉”。器官组织的自我摧毁,其暴力属于分子性的暴力介入,它区别于多数所施与的克分子暴力,在其最深处有着来自外部的温柔与爱。那变形之力,如同暗夜尽头经由疯狂而显现的生命微光,却并非“非理性”,而是出自转化为拥抱一个全新世界的“狗”的恒久“渴望”,进入未知世界并与之共同生成的多样生命形式和多样社会关系之可能。这种生命形式超越了善恶,超越了左与右以及在此对立基础上划界的层级组织和封闭系统,也超越了权力纷争或民族仇恨,如同超越了牧羊犬与狼犬之对立的“犬群”——到来中的尚不存在的“少数集群”。这种到来的生命形式,由此也具有了批判性力量,以及对超越民族层面的暴力的批判。正是这样的诗歌实验,在无意义、无逻辑、无理智甚至无可感知的悖谬中,语言掏空自身向外翻转,融解于自我屠戮最为表层的动作之流动中,激发我们向他者和未知敞开,迎接直接性的新异感觉和新的思想图像的生产。
三、少数文学:“临界自由”上的原生艺术
德勒兹以卡夫卡的写作为例提到少数文学的三个特征:“语言的解辖域化;个体与政治直接性的关联;表述的集体装配。”[14]18其中“少数”并不特指某种弱势状态或某类弱势群体,不关乎数量,少数文学也并不指向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而是“被称为伟大的(或已建构的)文学中心内部的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性条件”[14]18。因此,“少数文学”并非与“多数”(major)对立,而是在多数内部凿出外在于多数设定的二元对立框架的生产性权力,是一种“生成—少数”(becomingminor),尤其是全新的感知类型的生成创造。
如同卡夫卡为德国语言制造了一条逃亡路线,拉维科维奇也让希伯来语“在极端冷静和有力的呼喊中发出呼喊……将语言缓慢而渐进地带进荒地。为了呼喊而使用句法,给予呼喊一个句法”[14]26。比如《众水的咆哮》:“不,我淹死在海洋里,/那里有一个男人爱我/没有留给我一粒指甲壳。”[1]95如果说,在卡夫卡那里文学是随着鼹鼠的死亡开始的,鼹鼠那“向着温柔的怜悯而直直伸出来的可怜的小红爪子”[12]2,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拉维科维奇的诗歌是随着女性的枯竭和死亡而开始的,而诗歌创造就成了一个“生成—鸟儿”的事件。《像拉结一样》如此展现了哀悼与阵痛的生成瞬间:
像拉结那样死去
当灵魂如鸟儿颤抖,
要冲破藩篱。
在帐篷后面,在忧虑和恐惧里,
雅各和约瑟说起她,
不寒而栗。
生命中的每一天
在她内心深处
都像一个想要出生的婴儿。[1]156
死亡所带来的是克分子同一自我的枯竭与丧失,“像拉结那样死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在死亡的废墟之上,才回复一个“强度世界”“差异世界”,才给予了舞蹈和创造的条件,让新感知和新世界的到来成为可能。诗句呈现的精神孕育和创造的生成时刻给予的强度感受,超越了个体体验,指向普遍的激情过剩和生命之流的不息运动,指向一种“生成—孩子”或“生成—鸟儿”的迭奏旋律——敏锐、直接和天真无邪的直接感受,“临界自由”上的原生艺术(art brut)⑨。
拉维科维奇的英译者加纳·柯隆菲尔德(Chana Kronfeld)却认为,德勒兹意义上的少数文学写作所限于的英、法、德等多数语言排除了希伯来语文学等少数(已然经典化)之外的真正少数,于是在《现代主义的边缘》中他批评德勒兹的少数文学概念排除了国际文学潮流里非主流语言实践中的现代主义少数派。此外,少数文学被称为伟大文学传统的革新条件,依旧是一种本质论成就的术语,使得“少数文学中历史性的、文化的和语言的多样化形式再次变得不可见”[15]。但事实上这种批评忽视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将希伯来语、汉语等文学实践都纳入某同一性框架下来自我定位成其中的少数派,恰恰抹去了德勒兹他们倡导多元体中心的努力,同时也暴露了非主流语言文学对欧美文学中心地位的认可,以及渴望得到他们承认的内在焦虑。柯隆菲尔德指出,少数文学必须具有革命性与创造性的力量,但他没有认识到德勒兹的本体论区分,其本质基础恰恰就在创造性潜力与现实效应相互叠加(差异)于之上的强力线或生成线(差异)本身,并非传统形而上学所界定的能够被不同方式模仿的客观形式或共相,或者奠基于某种普遍我思之创造性主体(同一)。
已然正典化的卡夫卡、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特质在当下或已失去创新品格,然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少数文学”的内核不是某种审美特质,而是“生成”,是特定环境中被压迫意识的一种斗争性的功效性文学实践,其中的强力线,在重新当下化时可被一再激活和重新占有,即使环境变更,卡夫卡式的僭越、创造和生命强力的生成,将不断经由差异化的实践过程而回归。这并非某同一物的回归,回归本身即存在,是一种生成的肯定,是差异自身“生成—同一”的差异化重复。少数文学作为生产文学之“群众多元体”的“集群多元体”,是性质的变革与风格的创造于不断重复的绵延中向着未来恒久开放的潜在多元体(存在层面)。然而在具体的已然实现出来的群众多元体(存在者层面)中,需要在相对的、暂时的秩序中心和界域(territory)内谈论作为存在者的少数文学个体的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实践。就如同德勒兹非常谨慎地谈论“卡夫卡(对于中欧而言)和麦尔维尔(对于美国而言)”[12]4,我们也是在“对于以色列而言”的“多数”界域内谈论拉维科维奇的少数文学实践如何从内部隔离出一座“荒岛”,并将之归于对文学“潜在多元体”而言的普遍性“少数”。这种具体的语言实践与普遍之间绝非模仿和表象关系,对于以色列而言的拉维科维奇与对于中欧而言的卡夫卡间,也不存在诗学元素方面相似或差异性关系的理想性基准,但在各自的逃逸书写中对“生成的强度”之“感受”却朝向同一个“强力”的“少数集群多元体”。德勒兹的生成论诗学和拉维科维奇的诗歌实践所给出的全新视野的文学和理论模式,得以“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文学及其批评话语”[16],重新审视和理解具体文学实践与普遍文学生命之间的关系。
一个扎根现实当下而非沉浸在幻想中的作家从他的所见所闻中返回的时候,如同一个归家的醉鬼,伴随着眼膜充血,然而“那是双心灵的眼睛”[17],过于沉重的事件使他精疲力竭然而被给予“生成”的身体并非病人,却是“自身与世界的医生”[12]3。拉维科维奇“恶劣的健康状况和生活风格,都未能阻止她卷入巴勒斯坦问题。她经常参与游行或讲演活动,反对对待妇女和儿童的非人道行为。作为深受读者爱戴的非官方桂冠诗人,她替以色列民众发出了强有力的抗议之声”[1]252。
四、结 语
爱或者痛的经验是主体沉浸于时间中的动态过程,所占据的当下时间结构因为瞬间过后即闭合,无法被语言把握也容易被遗忘。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总是那些静态化的或被语言普遍化的东西。拉维科维奇的诗歌抗拒着这种“回忆”式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无论是对自己早期浪漫主义和追求唯美倾向的反思,还是对各种理想主义谎言本质的揭露,拉维科维奇都在批判那种逃避现实的胆怯。苦难或事件是与真实当下的相遇,是主体没有能够幸免、不可承受但必须要去承受的绝望境遇。它是拒绝对象化的,而语言的复述总是试图再现“抗拒被再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诗人被剥夺了写诗的“语言”。然而诗歌只能是对“沉默”、对“无言”的打破,是在沉默尽头的述说。必须经常去,“去到他站立的地方”[1]55,他——她的父亲,已逝的、双重意义上的那个父亲。因此,必须写诗,必须经常写,即便他一次次不在,总要经常去。每一次都经由不同的道路,每一首诗都有其特殊的语境和氛围,但每一次都是重复的“爱的作为”,都是对不被救赎灵魂的痛惜和哀悼,以及从爱的渊源流淌而出的、对那些无辜受难者的关怀。然而渊源处的那个“父”不被看见,也不说出任何东西。那追寻者仍然确信:他曾在那里,并且将总在那里。诗歌占据的时间总是那个不在的“现在”,一条空洞的时间线,如一条毁灭之线横贯诗节,如一条没影线掏空语言,然而它重获的是词语表层的厚度,是“富于表达力的活生生的质料”。这活生生的资料被装进了漂流瓶,携带着作为诗人的全部使命,前往它迫切想要前往的地方,“他”站立的地方,是关于死亡的那一个“谜”,也是一次相遇的可能性,一次便是全部的与他者的相遇。如同在回应策兰那封《瓶中信》,拉维科维奇写道:
不过,那里有一个被扔进水里的瓶子,
希望
有一只手掌会抓住它,有一只眼睛会看
到它,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惊讶地说起它:
我发现了一个瓶子。[1]216
注释:
①英译者提到,不少人甚至认为她是希伯来历史上最重要的女诗人,参见Chana Bloch和Chana Kronfeld的文章“Dahlia Ravikovitch:An Introduction”,出自Prooftexts,2008年第28卷,第15页。
②引自以色列《国土报》Grin Sagi的新闻报道,1998年3月6日。转引自Chana Bloch和Chana Kronfeld的文 章“Dahlia Ravikovitch:An Introduction”,出 自Prooftexts,2008年第28卷,第16页。
③为方便起见,以下涉及两人合作的内容暂时先归属德勒兹名下。
④征得同意,本文译诗均采用诗人译者李以亮的译稿。
⑤克分子(molar)与分子(molecular)对应于多数组织与少数运作,前者基于“树—根”结构的二元性宏大集合体,基于严格的层次结构和总体化模式,不为灵活性和偶然性留下余地;分子性基础则是微观政治的变化的量子流形式,其中“始终有某物在流动和逃逸,它避开了二元性的组织,避开了共振的装置和超编码的机器:那些被归属于‘风俗的演变’的事物,年轻人,女人,疯人,等等“,见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
⑥男人是强势的,而“所有的生成都是一种生成—弱势”,见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⑦英译注提到“橙子(orange)”,希伯来语字面意义乃金苹果。参见Dahlia Ravikovitch,Hovering at a Low Altitude,第49页。
⑧作为强度的“分子多元体”,相对于“克分子多元体”的“群众多元体”(crowd multiplicities)而言。《千高原》中的第二座高原(第35-52页)区分了这两种多元体:“集群多元体”是不规则的,游牧的,与生成、分子性,容贯性平面,强度、不可编码、块茎等概念相关;“群众多元体”从属于“一”并且具有可数元素与有序关联,与克分子性、数量、广延、组织化、树形等相关。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共同运作于同一个配置(机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