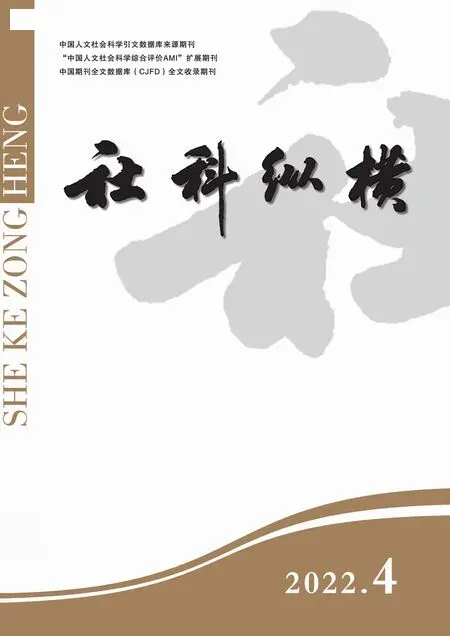孟子对孔子“政者正也”的理论推进
解晓燕 张会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266580)
孔子首提“政者正也”,开启了君主的一己之正与天下政通一体圆融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政者正也”,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同样主张“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将治国理政的政治责任集中于政治领导者,反复劝诫政治领导者强化自我修养;也将政治的终极目的归为道德教化,认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在此基础上,孟子对“政者正也”的思想引申与发展,从仁与礼、王与霸、德与位三个维度总结出内圣之道、外王之道及君臣之道上的“正”之阐述,引申出上承天意、下符民意、更合心性的“正治”理论体系。
一、仁与礼:孟子论“正治”的内圣之道
“政者正也”并非孔子对“政治”的辞典式定义,但集中体现孔子对政治活动本质的认识。在孔子看来,“正”是指领导者德行之正,政治的要点就在于执政者发挥其道德表率的作用。孟子论“正”的一大发展在于突破早期儒家容礼之学的范畴,打开个体心性哲学之门对“正”的主体性进行深入挖掘,使得君子之“正”不再只是由外向内安顿的以礼正身的过程,更成为由内向外扩充的存心养性之路。
孔子一生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制度,认为礼乐传统经夏、商、周三代损益相继,到周代呈繁盛之态,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此基础上,孔子谈“政者正也”之“正”大半属于以外在礼制规范要求君子涵养威仪之论,可归于早期儒家容礼之学的范畴。《论语》中提及“正”字24次,共计16则。除个别如“正唯弟子不能学也”的介词使用外,其他悉数是对君主、卿相、士大夫等为政主体的规训直言,其丰富内涵主要在于以等级名位规定下的礼制对一己之身进行严格的自我驯化,打造“事上也敬”与“临其民以庄”的身体魅力。具体视之,孔子论及“正”的相关语段涉及身姿之正、衣冠之正、容貌之正及颜色之正等多个方面。如《论语》强调君子站坐间的身姿要端正,合乎礼制。对此,《乡党》篇载“席不正,不坐”,《论语注疏》解曰“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如此之类是礼之正”[1],另载“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与此同时,《论语》指明君子在国君前的行与立要添一份敬重感,如《乡党》篇写明“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等。另如,《泰伯》篇载曾子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指出君子的容貌、脸色、语气皆要庄重合礼,才可使他人敬重与信任,终可使得“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尧曰》篇则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强调位居人前的君子要衣冠端正,目不斜视,眼神坚定。在衣冠体貌之外,孔子虽未以“正”言之,但始终要求君子的行止要践履“礼”的规范以达到正身之目标。
春秋时期礼乐逐渐沦为僵化的形式而不复有内在的生命,孔子也曾一度感慨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试图重新为日益僵化的礼制贯注新的精神基础。《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答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另一处有言“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学而》篇也言“礼之用,和为贵”。俭、戚、敬、和等明确表示外在礼乐需要扎根于一种本源性的内在情感。对儒家思想体系而言,孔子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援仁入礼、以仁释礼,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评,“儒家继承了礼乐传统而同时企图从内部改造这个传统,赋予礼乐以崭新的哲学涵义……仁义之说乃是突破礼乐传统而出”[2]。然而,作为社会性规范的礼与作为主体性规范的仁两者如何融通,孔子言之未深。论及礼,他承继并整理旧的礼乐经典,但未能指明“克己复礼”的内在自觉到底源于何处;论及仁,他多从具体表现随宜而言,如孝、悌、忠、恕,也没有指明仁的根据由何而来。由此,在孔子的理论中,“政者正也”的“正身”尚存在“正出于二”的困境,呈现为以礼正外在与以仁正内在的二元隔阂,仁与礼的融通显然需要进一步推进。
孟子对孔子论“正”的发展即在于尝试打通仁与礼以及社会性之身与主体性之身①的隔阂,使得君子“正己”不再是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的两层皮。孟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子已明显不同,诸侯各国进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烦琐的礼制大多名不副实,周礼进一步衰落。处此背景下,孟子的理论对以礼制规范由外往内安顿的正身重视度不高,甚至对孔子以礼制为要义的正名之论都未曾提及②。孟子对孔子“正身”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在于将仁、礼与“心”结合。在孔子那里,以心论仁尚未出现,“仁”作为其频繁提及的良善情感未能扎根于“心”,这使得“仁”缺少落实于普遍个体的情感着力点③。而孟子承子思而来,以私淑孔子自居,他自觉地继承孔子关于“仁”的睿识,发展出“仁心”之说。《孟子》中“心”出现117次之多④,将“仁”与不忍人之心直接对接,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另一处孟子在关于四端的论述中,将不忍人之心表述为恻隐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犹其有四体。(《孟子·公孙丑上》)
《告子上》篇表述稍有不同,但意义相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⑤。这其中,孟子强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凸显仁、义、礼、智的心之本源与各具差异的情感实质。在论及仁、义、礼、智四者关系时,对比孔子的仁礼并重,孟子关于仁与礼的论述可谓大异其趣。在孟子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仁是所有一切之大本大源的情感,是人心向善的最初动因,根源于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义、礼与智位于仁之后,与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相比,作为义之端的“羞恶之心”、作为礼之端的“恭敬之心”、作为智之端的“是非之心”皆处于后置位置,需要先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一更根本的衡量标准,解答因何羞恶、因何恭敬以及因何是非认定的问题⑥。从大本大源之意出发,孟子口中的“仁”有时也有囊括四心的统合性内涵,此所谓“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政者正也”的“一己之正”与“天下政通”皆渊源于仁,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与这一过程同步,孟子对“礼”进行了“内向化”的重新阐释。在孟子之前,“礼”主要是作为一种国家的基本制度,即作为“礼制”来被定义的。然而,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得礼的制度性理解越发名存实亡。孟子之“礼”在传统的外在制度内涵上大幅萎缩,反而向内收敛为根植于心的一种观念或者情感,曰“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或“恭敬之心,礼也”⑦。换言之,孟子之“礼”成为一种表象,它的本则深藏在人的内心感应之中,表达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对人、对事所表示出的尊重。礼之用必须出自诚心的敬意,“致敬尽礼”(《孟子·尽心上》)实为一体。《孟子》中有“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的说法,指出礼若落实不到日常,需要反求诸己,扪心自问是否心意诚敬⑧。“礼”也不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孤立存在。以恭敬之心为端绪的“礼”,后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与“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为前者所统摄。礼以仁作为存在的根据,礼所诚敬之对象在于“仁心”与“仁政”,崇仁心、尊仁政的“敬”就成为礼的情感实质,即仁本礼用。礼演化为一种君子“以仁存心”之后衍生的恭敬、辞让之观念,复而再转化为约束君子的外在德行规范。
由是观之,孟子对仁与礼的统一,尤其基于仁的先在性及本源性进行的新“礼”改造,突破了封建旧礼的桎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给予了“礼”以崭新的情感实质与哲学内涵。孟子的理论努力完善了孔子言而未尽的仁礼关系论,他主张存心养性,由内往外扩充式地以仁正心进而正身,这其中就囊括了“礼”的全新理解。此“礼”逐步脱离尊容礼、正威仪的制度内涵,蜕化为尊仁敬道的观念与德行,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有诸内而形诸外”的思考模式,解决了孔子悬而未决的“正出于二”的逻辑困难,完成了“政者正也”的本源内求化过程,使得政治运作与为政者的主体品性联系更为紧密⑨。而自另一方面来讲,孟子论礼的新旧之别,代表着战国中晚期“政”的合法性论证正在发生质的转变。礼乐原本是代表着三代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集中表现,但在孟子看来,本于仁的德行之礼较之于旧有的规范之礼处于更高的位置,甚而两者矛盾时,孟子主张“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这实质上确立出王道之于霸道、道统之于政统的超越性位置,开启了先秦时期论“正”与“政”的新篇章。
二、王与霸:孟子论“正治”的外王之道
孟子将孔子“正出于二”的仁礼并重转化为仁本礼用,对“正”的把握更明确地收紧为对“仁”的内在皈依,“正”治之“正”的主体本源被根植于“仁心”之上。孟子基于此以正为政、以正导政,在为政者的内在心性与外在政治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依孟子之见,“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仁心与仁政是一体贯通的,天赋本然的良心善性是实现王道仁政的人性根据,以仁政平治天下乃是恻隐之心自君主内心逐步推至“政”的客观化过程,或言之,“政在经验生活中的达致具体就展现在仁的伦理向度中”[3]。为政之道的关键之处在于君主对恻隐本心的自觉与发现,进而面向黎民百姓的存养与践行。由此,建立在统治者天赋本然的良心善性基础上的仁政成为一种君民忧乐与共的人性化政治。
如果说孟子论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赋予了孔子的“政者正也”以本心本体,孟子论君王的“不忍人之政”则将内在的君主心正与外在的政通人和实现了逻辑整合,赋予了“政者正也”更明确的民本指向。孟子将此种人性化的民本政治称之为“王道”,曰: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看来,儒家的内圣之学是存养本心之学,其存养的恻隐之心转化为外王之道则显现为民本之学。“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若君主将自己的不忍之心运用于民之疾苦上,则为不忍人之政,此种不忍之政就是仁政,是王道。王者因民而王,君主为民信任与追随的缘由在于其与民忧乐与共,欲民之所欲,恶民之所恶,由此关心民生,制民以恒产。这种共情恰恰肇因于王者自觉挺立、扩充其内心隐微之处的“不忍人之心”这一端绪,此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这里,“政”成为统治者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实现过程,由此,“政者正也”之“正”在指涉修己正身的内圣之道外,也拥有了直指政治权力正当性的第二重含义,即政治权力的实行过程必须符合“保民”“安民”的“外王”之道。
孔子论“政者正也”,基本不包含对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深入探究。《论语》中与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孔子的“正名”之说。《论语·子路》篇记载卫国国君卫灵公去世,流放在外的其子蒯聩与继承君位的其孙辄父子二人争夺国君之位,作为父亲的蒯聩成为流放在外的臣下,身为儿子的庄公却是身居上位的国君。基于父子争国的特定史实,孔子提出为政之要在于“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与此同时,他却难在各有劣迹的父子二人中点明谁更有资格成为一国之君,此事甚至成为后世争讼的一桩疑案⑩。事实上,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中,孔子虽倡导复古,强调因袭传统之“名”,却也隐隐生发出摆脱血缘正统论,寻求“以实正名”,以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自觉,只不过这种自觉尚是潜在的、隐匿的,未与保民、安民产生切近的关联。孔子的理论中存在大量关于养民与重民的阐述,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即便如此,民本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仍是蜷缩的。孔子曾言“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未就此引申,进一步点明若上位者残暴不仁,君子在“事上也敬”与“养民也惠”之间如何果断抉择。君子“行己也恭”的内在之诚指向等级礼制还是仁心仁政?这样的矛盾还没有赤裸裸地袒露于孔子的经验视野中,由此道统与政统、王道与霸道的区分尚隐没在其字里行间,这也是孔孟二人关于“霸”以及管仲态度不一甚至立场相对的原因所在。
孔子对“相桓公、霸诸侯”的管仲评价比较复杂,但无可争议的是他评管仲以仁:“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论语》中,仁人低于圣人、高于君子,配享仁人称呼的仅六人: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以及管仲[4]。管仲九合诸侯,匡扶周室,维护了周室的存续,这对于“吾从周”的孔子来说是天下要紧的大事大功,在此意义上,孔子认为管仲之作为可比肩极少数的古圣先哲。原本依孔子之见,礼乐征伐的政治大权应该出自周天子,此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诸侯若越俎代庖,便反映天下无道,不合于孔子的理想。管仲辅佐的齐桓公乃一介诸侯,竟做起“一匡天下”的大业,这在孔子正名主义的严格解释下是离经叛道的,其所作为不是其所当为。但由孔子对管仲相桓公一事的评价看,诸侯操持大权若用以尊王攘夷、回护周礼,孔子不惟不非议,更称许不已。此处,孔子评管仲以“仁”不是由保民安民而论,而是从周礼存续的结果出发默许了管仲违礼行权的霸道11○。
战国礼坏乐崩的情景更加严重,各个强国均主张兼并,“霸诸侯”成为君主们心心念念的政治目标,征伐频仍,时局动荡。处此背景下的孟子在王道与霸道之间划下了清晰的分割线,与孔子站在相对的立场上批判管仲。在孟子看来,“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孟子·公孙丑上》),“霸”是缺乏政治正当性的纯暴力统治方式12○。孟子不认可霸道,认为“一匡天下”必须以王道行之,霸道绝对不可取,在他看来“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一匡天下的政治征伐必须祭出民心所向的“正”之大旗。如孟子与齐宣王谈及伐燕时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一国如行暴政、虐其民,另一国对待虐民之国加以征讨是正当的,因为“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以民意为衡量标准,孟子赞成征伐虐民之国,诛杀国君以“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同样以民意为衡量标准,孟子反对嗜杀,反对为争地而战,为争城而伐,为国君的私利而杀人,他始终强调的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征伐天下、称霸诸侯不足称道。孟子借曾西之口言道,“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管仲只是依靠齐桓公的信任专齐国之政,也只是顺齐国之强成就了本就属于齐国的霸业,所谓霸业也不过“功烈如彼其卑也”,这种评价恰恰是因为管仲止步于霸道,没有能向前多走一步贯彻王道。
由是观之,孔子言“正”与孟子言“正”的含义指向不同,两人对于“政”也生发出理解上的演化。因为孔子“正出于二”的标准设定,管仲才可在其评价体系中拥有“如其仁”的极高评价。孟子则将“正”的价值基础定位于仁,主体本源根植于恻隐之心,其理解的“政”自然也摒弃了孔子的多向理解,聚焦于“不忍人之政”,着力寻求保民与安民。基于此种民贵君轻的认知,孟子对统治及征伐的合法性作出了独到的“正”治阐释。可以说,孟子对王道与霸道的区分以及王道高于霸道的论说,在王纲失序、君与民日益分离乃至对立的情况下,将君与民重新联系在一起,并以保民安民的责任为突破口开启了统治者的“名之自觉”[5]。对此,萧公权曾评价道,孟子的养民之论深切著明,为先秦仅见。在这一点上,孟子甚至多次重申西周以来“天民合一”[6]的思想,借助天的权威拔高民的位置,指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依孟子之见,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天与人归”。就政治权位而言,“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只是天不再是会表达情绪的人格神,“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13○。由此,天成为虚悬的至高主体,民升为天意反应的载体,权力的合法性虽由天与,实赖人归,人之所归就是民心所向14○。在孟子看来,无论是禅让、世继甚至是征伐,都可能是正当的权位转移方式——“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但前提在于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论述至此,孟子关于“正治”大致完成了一体圆融的体系建构。孟子延续《礼记·中庸》之论,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诚”作为人心深处一种真实无妄的状态,成了天道与人道的内在连接,因“诚”之故,天道不需要任何的媒介就可以直接地落到人(或曰“劳心者”)的内在道德生命中,而主体通过内在的心性就可以领悟天,此所谓“尽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而在“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的论述中,不言之天摒除了人格化的特征,民(或曰“劳力者”)成为天放置于外在人世间的代言群体。由此,孟子形成了以天为“正治”的超越性根据、以仁为“正治”的主体性本源、以民为“正治”的实践性落脚的逻辑整合,开拓出上承天意、下符民意、更合心性的“正治”理论体系。
三、德与位:孟子论“正治”的君臣之道
儒家主张“德位合一”,但在实际的政治中德与位多数时期并不统一,发展到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德与位甚至呈现出各据两极的趋势,道统与政统趋向二元分立。若以政统言,王侯本应为主体,君尊臣卑,但现实中的君主多为私欲与野心所蒙蔽,居高位而无德;而以道统言,原本固定在封建关系中各司其职的“士”因动荡的局势成为以道自任的“游士”,他们在摆脱封建身份羁绊的同时,获得了对天下正道探索的自由,进而逐步从居高无德的强权者手中接过了道义话语权。在此前提下,德与位相待而成成为孟子论及君臣关系时的理想之境,他寄托于“贤君”与“贤士”双方的自觉努力,为孔子的“政者正也”增加了君臣“相责以善”的新内涵,开拓出以德“正”位的新面相。
孟子从道统的超越性视角来审视现实的政治权力,其对君臣关系的定位超越了以往儒者主流的“君尊臣卑”的范畴。在孟子看来,虽然以政统言君高于臣,但以道统言,君主绝对不可屈盛德之士为臣,而应将贤士“举而加诸上位”,时时以一种无确定之规的师徒之礼尊而养之。
孟子主张君主“恭俭礼下”,尤其要以师徒之礼尊贤养贤。就尊贤而言,他曾有“不召之臣”的阐发。原本为人臣者有义务服从君主之召,甚而臣子闻君之召应唯恐不及,否则与礼不合,是为不敬。孔子就有“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的明确态度。孟子挑战这种传统礼制观念15○,《孟子·公孙丑下》曾载齐宣王召孟子前往朝堂,意欲请教治国之道,但孟子托病不朝。孟子认为“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若君主的德性不如臣民,他应该屈尊降贵、亲自登门,敬贤人如师,虚心请教。针对不召之臣,孟子友人景丑曾直斥其非,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景丑所持有的观点就是基于君尊臣卑的政统而发。但在孟子看来,敬作为礼的情感实质,呈现出层次之别,他辩解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依孟子之见,君主虽居高位,但就辅世长民一事恰居于下位,其“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孟子·万章下》)。不召之臣作为君待贤之“礼”,背后所体现的“敬”正是君主对仁政之道的尊崇。朱熹认为此处“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7],即以爵与位为衡量标准的敬是“敬之小者”,以道与德为衡量标准的敬是“敬之大者”。
孟子不排斥君主“养贤”,只是主张“养”应该是君主尊重贤者道德人格的延伸,是“尊而养之”的自然之举。《孟子》文本中屡次提及尧待舜之道,认为那才是“悦贤能养”的典范。为君者的尧“以不得舜为己忧”,他看重舜的贤能,就给予其充足的生活资料,“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孟子·万章下》),而后舜又被尧“举而加诸上位”,委任以重要的政治职位来发挥其才干,甚至于到“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最终成就流传千古的尊贤佳话。另一处,《孟子·离娄上》中曾载:“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孟子·离娄上》)此处君对臣的“三有礼”,首先强调君主“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即君主敬重贤臣的道德志向,听从其所持的治国之言,以民生为重,施仁政于天下;其次要求君主体恤为臣者的生活艰难,预先免除臣子的后顾之忧。
“三有礼”在重要性的排序上是不可颠倒的,如果抽离人格尊重,君主仅仅表达对臣子的物质体恤,恰恰可能成为孟子所言的“非礼之礼”(《孟子·离娄下》)。孟子与万章的一段对话,恰说明君主对有德之士仅以富养之是不可取的非礼之举:
曰:“君餽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餽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彶。’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孟子·万章下》)
缪公欲以物养贤者子思,但未能以师生之“礼”向子思学习仁政之道,其屡次赠送食物就变了质,成为一种亵渎君子道德人格的“无礼”表现,甚至在子思眼中已经形同豢养犬马。孟子认为君对贤士之礼的“养”必须以在切实行动上尊重其贤能才具与道德人格作为关键前提。此种情形在孟子身上也曾发生。齐宣王不尊其道,孟子致为臣而归,王欲挽留之,便通过时子传话,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义愤之下辞而不受16○。
孟子主张为臣者应以道辅君,“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甚至将为臣者的进谏推向一种必然的道德要求,拓展出儒家“正治”理念中重要的“他正”维度,使得“谏正”(即批评政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气节与血性所在。
事实上,孔子对“以德谏位”也有相应阐述,但囿于礼制的规范,其表述相当克制。在臣事君的行为要求上,孔子希望臣子事君,“敬其事而后食”(《论语·卫灵公》),认识到事君“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做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时时劝诫,强调为臣者勇于正君之不正。不过,孔子认为臣子选择“犯之”的时机很重要,应“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论语·子张》),其背后暗含之意是君主对臣子未能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时,后者可选择闭口不谏,孔子赞宁武子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便是此意。甚而再退一步,孔子支持“有道则见”的入世原则,也不反对“无道则隐”的避世行为,他视蘧伯玉为君子,正是因为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总体而言,孔子对君主仍保持着较高的敬意,他在“德”与“位”发生矛盾时,选择以温和的“以德谏位”方式处理,局限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其中君尊臣卑的礼制约束仍时时可见。
不同于孔子的克制,孟子对“以仁为本”之新礼的改造突破了封建旧礼的约束,他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依孟子之见,敢于“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上的真正的恭与敬。反之,无原则地迎合君上的私情己欲,可称之为“贼”。另一处,孟子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认为臣子立身朝堂之上但君主不行仁政,是臣子劝谏的职责未尽,可称之为“耻”。孟子甚至认为“长君之恶”“逢君之恶”不仅不是臣子对君主应有的礼节,而是“罪”(《孟子·告子下》),是对君上最大的不恭不敬。“贼”字、“耻”字、“罪”字的使用,实际上已经将“谏”与为臣者的职责进行了紧密的道德捆绑,臣子不应只是君主命令的执行工具,而必须具备抨击暴政的独立人格,应“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上》)。在奔走列国宣扬仁义的途中,孟子常拿着儒家的这个人臣伦理去拷问尸位素餐的官员,例如,孟子曾对自己的学生乐正子话带讥讽,“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孟子·离娄上》),认为乐正子只是从饮食起居上侍奉君主是不应该的,学古之道的终极目的应在于以道侍君。
孟子所倡导的谏诤,尚属为臣者作为“有言责者”的外在行为标准,其最终目的在于由言而心、由外而内的“格君心之非”、触君主本心。《孟子·离娄上》曾言:“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是对孔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同义表述。具体到君主,孟子认为在心与政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孟子言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公孙丑上》),另一处相似的表达讲“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生于其心者与作于其心者即为君主的私欲,君主以其私欲吞噬不忍之心就是孟子所言的“放心”,若君主与民忧乐与共的心之本源被吞噬,落实到政事之上便会威胁到百姓生活甚至生命。孟子以君师自居,又以好辩扬名,其终身所求就在于通过谏诤的方式匡正君主的非正之心,使君主在自身的世俗欲望中实现善端的觉醒,回归到仁义之心上来。如此,这段话中的“一正君而国定”的“正”强调的就并非孔子所说的君主自正,而是“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结果17○。
如果“格君心之非”是贤臣“正君”的核心目标,谏诤就成为可选择的手段之一。若将孟子的逻辑再向前延伸,处于道义一方的“大人”寻求“格君心之非”这一最终目的,其外在的形式手段可能就不拘泥于“以德谏位”。在此之上,孟子继承先贤“以德谏位”的传统,并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如《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伊尹流放太甲的事,因太子太甲不顺义理,作为辅臣的伊尹将太甲流放于桐邑,公孙丑的疑问在于“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但在孟子看来,伊尹“放”太甲于桐,是“格君心之非”的正当之举,“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伊尹作为孟子所列的“圣之任者”,是朱熹所谓“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7],其品行之高使得他有资格以放逐为手段求格君心。另一处,孟子曾向齐宣王直言,“贵戚之卿”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即“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告子上》)。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的激进之言,也曾申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暴君放伐论,这两处的阐发中,孟子部分扬弃了周公、孔子等先贤的乐观态度,更深切地意识到个别政治上位者的幽暗人性难以改过迁善18○,但若是将其君臣相责以善的以德正位引申为“人民革命”思想仍存在过度解读之嫌疑。孟子所言的以德正位实际上仍延续着孔子关于“道假势以行”的明确要求,一方面他对易位之举做了贵戚之卿的身份限定,同时更明确指出人臣不得动辄就言易位,“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下》)。
综上所论,孟子对君臣之道的论述无不体现出其对“道”的皈依立场和以道之“正”治位之“不正”的理论旨趣。此处,孟子尽管与孔子一样推崇“政者正也”,但他赋予贤士以道为依归的道德使命与政治自觉,士以“道”为依据考察君主行为,不断“正其不正”。换言之,“正”的部分责任从君主之位转向贤士之德,从君主自正位移到贤士对君主的“他正”上。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孟子也讲过“其身正天下归之”“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但其前提已经加入了“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的批评谏正,相对孔子而言,“孟子的政治观已经不是狭义的美德政治,而是偏重于士大夫立场的批评政治”[8]。
注释:
①诚如杨儒宾所论,正威仪最大的底色在于它是以社会共同体规范的身份(即礼)展现出来的伦理,虽然在君子个体上表现出来,但它仍然只是社会性身体的意义,缺乏内在主体性的真实内涵。参见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湾中央研究院,1997:40-41。
②孔子对正的理解中“正名”占据重要位置,他借齐国蒯聩与辄之间君臣父子关系的错位凸显礼制的重要性。《孟子》中“名”出现10次,分别表“名字”“名目”“名誉”之义,与礼制相去甚远。
③《论语》提及心6次,只1次与仁有所关联,即《雍也篇》载孔子评价颜回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但也并非以心论仁。
④《孟子》中心另有3次用于人名,不计入内。
⑤梁涛从孟子思想发展的历程解读四端之说的两处不同,他认为《告子上》中所载孟子与告子辩论时,其四端说尚未完全形成,甚而与告子的辩论加深了孟子对四端的思考,但彼时其表达仍有不准确之处。后来他到齐国与齐宣王会面时再提四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说法。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5-310。
⑥梁涛认为孟子之礼是对礼内涵的缩小,以辞让之心推广的礼只能表现为进退之间的礼仪形式,而不能再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笔者认为仁本礼用应该理解为权力的合法性论证的转向。
⑦《孟子》中辞让出现2次,恭出现11次,敬出现39次。恭敬与辞让并不完全相同。就恭敬而言,在貌为恭,在心为敬,朱熹讲“恭者,敬之发于外者也;敬者,恭之主于中者也”正是此意。辞让则指不敢径自接受而有所谦让。两者的共性在于将他者放在更高的优先地位上。在这几个词中论及礼的情感实质,“敬”确实更具代表性。
⑧《论语》曾提到“修己以敬”“居处恭,执事敬”,但论述的是君子之所为,未如孟子这样直接将“恭敬之心”与“礼”画上等号。关于论语中的敬可以参见陈立胜.“修己以敬”:儒家修身传统的“孔子时刻”[J].学术研究,2020(8):30-37。
⑨有学者认为孟子的理论体系中存在两种礼,一种是规范之礼,一种是德行之礼,参见刘旻娇.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J].哲学研究,2020(4):70-79。
⑩后人对孔子这段话出现“纠名正分、以名正名”与“循名责实、以实正名”两种解读,前者主张以父子之道正君臣伦理,如朱熹引胡氏曰:“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主张以父子伦理正君臣之道,由此该公子郢继任君位。参见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2。后者主张以君臣之道正父子伦理,如吴林伯曰:“有实而后有名,名缘实而生,故曰名附实也……孔子答子路之问,特征其中政治之名”。参见吴林伯.论语发微[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51。
11○金耀基认为孔子评管仲以仁是因为管仲的民本思想,笔者持不同意见。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法律出版社,2008:50.另可参见谭延庚.论孔子称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视野下的分析[J].管子学刊,2016(3):20-26。
12○《论语》仅围绕管仲提及“霸”1次,孔子并未如孟子一样揭示王霸之别,他提及“霸”没有贬损之意,甚至称许齐桓公“正而不谲”,赞许管仲“如其仁”,与此同时,孔子也提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似乎隐喻由霸至王是一个阶段性的量变过程。孟子则明辨王与霸的不同在质不在量,在本性不在过程。孔子与孟子对于“霸”的理解已经发生转变,这也代表着两人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基点发生了位移。关于孔子论“霸”的历史背景可参见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0-81。
13○夏世华认为“天不言”是孟子重要的理论改造,他祛除了天的人格神特征。不言之天若被确立为最高权位授予主体,必须要为之配备一个能辅助传达命令的实际权位授予主体。于是孟子才能主张“天与之”即是“民与之”,将后者作为传达天授予权位命令的辅助原则。参见夏世华.孟子对早期儒家禅让学说的反思与重构[J].2020(5):135-143。
14○孟子有时过于强调民意,反而在言语中忽略天意。如齐宣王认为伐燕顺利,不是齐国之力所能为,必有天助,想以天意为借口进一步夺取燕国,他探寻孟子的看法,曰“不取,必有天殃”,孟子直接规避了天的问题,回答道“取之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
15○孟子在现实上下等级的礼制规范与君主好善而忘势的君臣新礼之间多有平衡,以缓和两种“礼”之间的冲突。他也承认礼制规定臣对君命之召要积极服从,但同时又有不服从君王之召的情况,辩解之论大约有二,其一,他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孟子敬王也,这种敬就是礼。再退一步,他认为”市井之臣”和“草莽之臣”都算作庶人,庶人“不敢见于诸侯,礼也”。另可参见方旭东.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J].文史哲,2010(2):40-49。
16○鲁缪公、齐宣王虽不用贤士之道但仍欲尊其人,甚至有意以物质财富的赠予来保持一种友人关系。孟子显然反对与君主之间生发出非师非臣的“友”之状态,他指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这种模糊的“友”渗透着君主的物质供养,士因德而自持的尊贵便可能畏缩混沌,进而在君主面前恶化为“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的境况(《孔丛子·居卫》)。
17○孟子对“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论断,与他对为臣者的理想人格——“大人”——的道德想象相关。《孟子》中“大人”出现12次,大体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意涵指向。一种是指类似君主这样的位高之人,如“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上》),其中的“大人”就是位高权重者。第二种指具圣人品性的辅君贤臣。孟子认为大人者养其大体、从其大体,即以心之官钳制耳目之官,以良心本心充盈整个生命,居仁由义,不沉溺于食色利欲。
18○关于孟子的幽暗意识可参见晏玉荣.性善论、寡欲观以及义利之争——论孟子的幽暗意识[J].道德与文明,2017(5):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