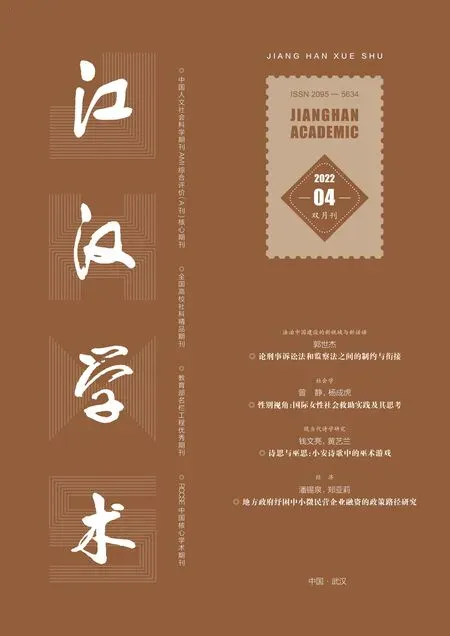从需要视角看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
——与无意志论者商榷
刘清平
(武汉传媒学院 电影与电视学院,武汉 430205)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围绕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激进意志论者主张不受因果制约的“自由意志”是构成道德责任的先决条件,无意志论者主张道德责任的根基是与自然因果机制一致的自由或理性。笔者以往有关自由意志的文章已经剖析过激进意志论理论卷入的深度悖论,为避免重复,这篇文章将聚焦在无意志论的观点上,围绕苏德超、宋尚玮、田昶奇、尹孟杰等学者的论述展开讨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坚持自然主义、反对激进意志论的观点,就否定了源自需要而与自然因果机制一致、作为道德责任乃至人生在世根基的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
一、无意志论的理论漏洞
从某个角度看,两大阵营的名称有点戏剧化色彩:激进意志论的观点原本来自西方的“自由意志论”,可大概由于主张把“自由意志”与因果机制割裂而呈现出脱离自然的特征,所以名之为“激进”。与之对照,无意志论者干脆否定了意志的存在,如苏德超指出:“意志并非本来就有,而是哲学家为了解决哲学问题(特别是道德和自由问题)构想出来的,这些哲学家的构想并不成功。”[1]尹孟杰也主张:“精神状态只是物理过程的副产品。由于物理过程不受人类的控制,因此自由意志并不存在。”[2]这样,除了面对激进意志论者的反驳外,无意志论者还要面对许多间接承认了意志存在的理论的挑战,其中不仅包括长期坚持“知情意”三分架构的西方主流哲学,而且包括虽然也不怎么愿意使用“意志”一词,却仍然不得不对“需要”“(内)驱力”“动机”“激励”这些与“认知”和“情绪”有别的心理现象做出解释的现代心理学,甚至还包括了承认自由存在的无意志论观点自身:要是意志(自由意志)不存在的话,与自然因果一致的自由(现实自由即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又是怎么可能的呢?它凭什么叫作“自由”呢?
应当承认,无意志论者的某些见解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它明确否认不受因果制约的“自由意志”的确是众多西方哲学家由于陷进二元对立架构“构想”出来的一种不仅“不成功”,而且“莫须有”的幻觉(严格说来是个“幻念”);其次,现实中的确存在与自然因果一致的自由,并且构成了每个人每天都在追求的人生目标[3]。不过,无意志论者在否定加了引号的、不受自然因果制约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一并否定了不加引号的与自然因果保持着两位一体关系的自由意志时,却出现了严重的理论漏洞,一笔勾销了这种将自由意志作为人们达成与自然因果一致的现实自由的动机源头的重要作用[4]。
从这个角度反思无意志论观点,或许可以说,在主张“无意志”这一点上,它被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架构带进沟里了。因为它把自由意志这种人们从事一切行为的动机源头与因果链条这种大千世界的变化机制嵌入到不共戴天的矛盾冲突中。这导致了两个荒唐的结果:首先是把所有承认“自由意志”的学说(包括激进意志论)都变成了缺乏定论的不知所云——毕竟,离开了确定性的因果必然,面对完全不确定的随机偶然,哪个学说还能“有定论”或“有所云”呢?其次是把无意志论的观点逼到了连自由意志自身也给虚无掉了的理论窘境:它原本在肯定自然因果的基础上完全能够如实肯定自由意志,却由于这个架构的误导,在肯定自然因果的同时否定了自由意志,把自己称为“无意志论”。
然而,我们在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反思性的问题:难道人生在世不可能形成某种与自然因果一致的自由意志吗?要是答案是否定的,人们与自然因果一致的现实自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现实自由难道能够离开人们的自觉行为及其动机源头,单靠自然本身的因果机制从天上掉下来吗?对此更接地气的回答似乎是:我们与其在“有了自然因果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坚持难以成立的“无意志”主张,不如从自然本身的因果机制中寻找能让人们达成与自然因果一致的现实自由的动机源头——亦即与自然因果一致、不加引号的自由意志,并且因此从无意志论者的立场转到有意志论者的立场上。
二、意志源于需要的因果机制
值得肯定的是,无意志论者虽然否认了意志的存在,却没有拒绝对它下定义,从而为围绕它的存在问题展开对话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概念基础。如苏德超指出,“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意志,它是行为的发动者”,是某种“意图”“当下的想要”;“意志,大约是指心意(意)的取向(志)”[1]。他此后还做出了一系列承认“我们”都有“心意的取向”的清晰表述:“我们希望”“我们倾向于”“我们的愿望”等。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已经包含着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当然可以给某个自己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下定义,但从逻辑上说,他理应在界定后就论证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存在,而不是反复给出这个东西真实存在的证据。不幸的是,这似乎正是无意志论观点陷入的结局:要是人们(包括无意志论者)都将“意图”“当下的想要”“心意的取向”作为自己从事各种“行为的发动者”,岂不就证明了意志是真实存在的么?
现代心理学在研究“行为发动者”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可以作为意志存在的自然主义证明,这些成果彰显了从自然生物体(包括人)的“需要”中产生的“驱力”如何推动它们从事各种活动(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国内一本普通心理学教材曾指出:“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例如,血液中水分的缺乏,会产生喝水的需要;血糖成分下降,会产生饥饿求食的需要……。”[5]国外有教材也主张:生物体的“生理需要产生了驱力,而驱力这种紧张而迫切的激励状态会迫使生物体做出满足相关需要的行为”[6]340。毋庸讳言,这些论述的自然主义倾向是相当彻底的,因为它们甚至没有用“意图”“当下的想要”这类更适用于人的哲学术语,而是运用了“需要”“驱力”“激励”“满足”等日常术语,指认了自然生物体从事各种活动的“发动者”。有鉴于此,倘若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人们也有这类与其他自然生物体相似的因素,构成了行为发动者形成“意图”“当下的想要”的自然基础,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否认与自然因果一致的意志的存在了。换言之,恰恰是人们那些能够产生驱力的需要,为他们的意志奠定了一个扎根于因果链条的自然基础,使之能与自然因果机制保持完全一致,因为这种从需要到意志的联结和转换本身就是自然因果链条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现代心理学的这些成果,从日常语义的绵延角度可以指出,人们的各种需要一旦进入了自觉心理,就会通过内在因果机制转变成“想要(will)”,作为心理动机(驱力)驱使人们从事行为,满足需要,维系存在,以致我们的确可以像马斯洛①那样宣布:“当我们谈到人的需要时,我们讨论的是他们生活的本质。”[7]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元价值学视角出发,把人的需要以及由之而来的“价值”区分成道德、实利、认知、信仰、炫美五个领域,如实描述它们是如何按照人性逻辑对人的存在发挥动机源泉的决定性作用的,并提出了“需要是人生哲学的原初起点”的命题[8]。
应当指出的是,或许出于不愿承认不受自然因果制约的“自由意志”的考虑,当前的心理学教材很少使用“意志”一词。例如,《津巴多普通心理学》几乎没有提到“意志”,还把“需要”“驱力 ”“ 激 励 ”“ 动 机 ”“ 本 能 ”“ 欲 望 ”等 问 题 放 在 了偏重于“认知”的“感觉和感知”“学习”“记忆”“思维和智能”等章节后讨论,甚至在同一章里也放在了“情绪”部分之后[6]319-358。不过,这种拒绝在表述中运用“意志”一词的做法,同样不足以否定意志的存在。毋宁说,考虑到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知、情、意”三分架构(如康德区分人类心灵中“欲求的机能”与“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9]),这本教材在讨论了“认知”和“情绪”后,还是不得不拿出一定的篇幅讨论“需要”“ 驱 力 ”“ 激 励 ”“ 动 机 ”“ 本 能 ”“ 欲 望 ”等 心 理 因素,可以说正是以“‘有意’不用‘意志’二字”的方式,指认了“意志”与“认知”和“情绪”三足鼎立的存在。
进一步看,《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以及其他心理学教材讨论“知、情、意”的这种先后次序,还体现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对这门从西方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自然科学的负面影响: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人是“理性的动物”,更看重“我思故我在”的一面,他们总是把认知因素放在首位,却相对忽视了被视为“感性”的情感(情绪)和意志,结果掉进了一个逻辑陷阱而不自察。既然“需要”“驱力”“激励”“动机”“本能”“欲望”这些意志因素构成了人们从事一切行为的动力源泉,以致缺失了这些动力源泉,人们甚至不会“想要”从事“感觉和感知”“学习”“记忆”“思维和智能”等行为活动,那么,离开前者考察后者,不是会让后者变成无源之水吗?
有意思的是,无意志论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这种忽视源头却偏重水流的错误。例如,田昶奇在得出“道德责任的根据不在自由意志而在理性”的结论时[10],似乎没有想到一个追根溯源的问题:倘若按照注重理性的斯宾诺莎的见解,意欲或冲动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从中必然产生那些倾向于维系人的存在的东西,人们则因此被决定着从事种种行为”[11]107,或者按照同样注重理性的康德的见解,“生命就是一个存在者按照欲求能力的规律展开行动的能力”[12],我们在把“理性”视为道德责任的根据时,是不是应当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东西促使人们运用理性能力从事“理性”认知行为的呢?毕竟,反思一下自己运用理性能力从事“理性”认知的人生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理性”自身,而是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求知欲”这种以认知的正确性作为欲求对象的需要—想要—意志[13],以及笔者通过批判维特根斯坦哲学发现的“求晰欲”,即这种以认知的明晰性作为欲求对象的需要—想要—意志[14-15]。失去了这些认知需要(认知维度上的自由意志)作为动机源头,理性认知就将沦为无源之水,既无法构成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也不可能成为道德责任的所谓根据。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们有了指向理性认知的需要—想要—意志,他们才会形成理性能力并且从事理性认知的行为,从而拥有理性认知。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彰显理性认知对于道德责任的重要意义,都抹杀不了理性认知本身也是源于特定的需要—想要—意志的简单事实。
综上所述,意志对于人生在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源于自然因果机制的驱动力—需要的心理表现,它是人们从事一切自觉行为的唯一动机源头。
三、意志本身的自由特征
倘若我们无法否定意志,那是不是还有可能否定意志的自由特征,据此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呢?笔者认为,倘若像西方主流哲学那样把自由与因果链条置于二元对立之中,我们当然有理由否定这个意思上的“自由意志”,因为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东西一样,任何意志都是处于因果链条中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与因果机制势不两立的“自由意志”。可是,倘若打破了这个二元对立架构,承认了自由与因果机制的两位一体,我们很容易看出:意志在它所处的因果链条中本身就有自由的特征,并构成了人们在现实中从事所有以“自由”为目标的行为活动的唯一动力源泉。
奇怪的是,尽管无意志论者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的“意志”做出了清晰的概念界定,却几乎没有对现实存在的“自由”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虽然尹孟杰指出,“自由体现在我们的行为具有物理与心理的双重性质:人类行为既在物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范围内被物理规律支配,也在心理学和社会学范围内具有自发性”[2],但她却没有解释,何以这样的双重性质就体现了自由?如果撇开了自由与自然(物理规律)的一致不谈,“自由”的独特处是不是在于“自发”?这里的“自发”是指心理“不自觉”呢,还是康德说的“无因而生”的纯粹“偶然”?从她接下来的话看,“苏德超或许赞同的是一种与因果律相容的自由,通过‘随机数发生器’表明:我们即使无意志,也可以拥有自由感……基于我所处的环境以及实际能力,我只能去快餐店或者在家做饭,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火星吃面包。这种二选一的自由,正是‘随机数发生器’带给我们的自由感”[2],答案似乎偏向于随机偶然意思上的“自发”。但撇开其中不经意地运用了“随心所欲”这个成语,潜在指认了意志(意欲)与自由的密不可分不谈,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还流露出了主张自由在于必然(物理规律或因果律)与偶然(随机数发生器)统一的自发意向,结果不得不面对一道难题: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必然与偶然统一的自然无机物,是不是也能在“无意志”的状态下,诉诸随机数发生器化“偶然”为“自由”的神奇效应,享有与人类似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感”,并且因此承担“道德责任”呢?我们是不是有理由为了将自然主义的立场贯彻到底,就把人们的道德责任也追溯到这些无机物的自然因果机制那里呢?不幸的是,这样的追根溯源等于取消了无意志论者也承认道德责任真实存在的问题。
其实,一旦我们把“自由”理解成“由乎自己”的“随意任性”“从心所欲”,就能发现意志本身直接具有自由的特征,自由意志也可以说是分析性的同义反复。换句话说,自由不仅与人们的意欲(想要—意志)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而且直接包含了想要—意志的内在特征:人们的想要—意志总是推动人们在行为中将它们付诸实施,由此弥补自己的缺失,维系自己的存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这恰恰意味着“随意任性”“从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自由”。说穿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自由感”“自由的愉悦”,不是什么“随机数发生器”带给人们的,而是人们把意志付诸实施后由于满足了需要所达成的“心满意足(满意)”的情感状态。就此而言,由乎自己、从心所欲的意志在本性上就是自由的,并且构成了“人人生来自由”的唯一动机源头。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无意志论者没有给出“自由”的清晰定义,但正如对“随心所欲”的运用所表明的那样,只要谈到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他们也很难否认一个事实:人们只有基于由乎自己的、从心所欲的自由意志,才能达成由乎自己的、从心所欲的现实自由。例如,苏德超在反驳笔者时指出,“不是对人性逻辑的遵守造成了我们的自由,而是自由让我们选择了人性逻辑”[16]。田昶奇也主张,“行动者必须把理由看作充分的,然后根据充分的理由来选择,再根据选择来行动”[10]。不过,一旦这样承认了自由与选择的关联,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意图”“当下的想要”这些意志因素,单靠自然因果机制或随机数发生器去解释人们的自由选择了,因为人们显然是凭借自己对无法兼得的“可欲”目标的权衡比较,才做出这样的自由选择。诚然,无可否认,按照自由与因果的两位一体,人们的任何自由选择都是植根于因果链条中的;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因果链条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人们的“意图”“当下的想要”展开的,并构成了它们与各种“无意志”的东西植根于因果链条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否定自由意志而单靠因果链条,就不可能正确解释人们的自由选择。
拿田昶奇谈到的那个虚拟例子来说:“一个正常人类出于‘我感到饿’这个理由而抢劫包子店时,作为原因的理由已经与‘包子能让我饱’‘包子就在包子店里’‘我可以通过抢劫获得包子’等一系列理由处于推论关系中,而‘我可以通过抢劫获得包子’是不道德的理由,因此这个人认可了这个不道德的理由,进而引起相关的行动而承担道德责任。”[10]一方面,在这个人做出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的自由选择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能够诉诸理由推论关系加以描述的因果链条;但另一方面,这些因果链条恰恰是以“我感到饿”的需要—想要—自由意志为起点的。由于我自觉意识到由于营养缺失生成的指向食品的“需要”,所以产生了“想要”找东西吃的“意图”,并在发现了“包子就在包子店里”(以及自己没有钱)的事实后,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意志,在“两难困境”下做出了由乎自己的自决选择——不是认为“我应当通过打工赚钱买包子”,而是认为“我可以通过抢劫获得包子”,结果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到如此清晰的证据,对于无意志论者非要把上述理由推论关系或自然因果链条说成是“无意志”的立论,我们或许只能这样解释:与其说他们否定的是现实中人们真实拥有的与因果机制两位一体的自由意志,不如说他们否定的是激进意志论在二元对立架构中幻想出来的与因果机制不共戴天的“自由意志”。
为了加强论证,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事件。按照2018 年的纪录片《徒手攀登》的记述,主人公亚历克斯·霍诺德在大脑构造和家庭环境等多种因果链条的决定性影响下,从小形成了“想要”攀岩的随意任性。可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非但没有扼杀他的自由意志,反倒还使这种随意任性强大到了面对死亡的威胁依然坚定不移的地步,推动他“决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徒手征服难度最高的酋长岩的人,却拒绝了“本可以不这么做”的开放性选择(他或许觉得这种开放性选择会让自己变成意志薄弱之人)。进一步看,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这个“意图”或“愿景”的实现寄托在激进意志论者主张的“随机偶然碰运气”或是无意志论者看重的“随机数发生器”上②,而是通过数十次带绳攀登的尝试,了解每个风险因素及其因果关联,反复思索自己理应在因果链条中承担的各项人伦责任,并采取种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朋友在场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以及自己的失误对朋友的不利影响。正是由于以这种与因果机制一致的方式将自由意志付诸实施,他才没有因为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缘故,随机偶然地给自己以及朋友带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后果,而是从心所欲地完成了创纪录的壮举。在成功登顶后,他充分享受到了表面上看不动声色、实际上是心潮澎湃的强烈体验,以致我们手心冒汗地盯着屏幕上的登顶场面时,也会设身处地地分享到他由于实现了自由意志所感受到(而非“随机数发生器”带来)的巨大“自由感”。
在这个案例中,考虑到自由意志、因果链条和自主责任保持着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缺少了任何一个因素都难以解释另外两个因素,我们还有什么必要钻进二元对立的牛角尖里,徒劳地琢磨下面这些纯属幻觉的“哲理”问题呢?霍诺德置身其中的因果链条,是不是剥夺了他想要攀岩的自由意志,以致设定他的意志存在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攀登过程涉及的那些因果链条,是不是注定了像俄狄浦斯的必然命运那样,会毁灭他在现实中的行为自由,只有借助随机数发生器化“偶然”为“自由”的神奇效应,他才能碰巧成功登顶③?与其说,我们是凭借因果链条否定他有自由意志,只从他是因果链条上最容易改变的环节入手,来说明他承担的种种责任;倒不如说,我们更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事件不仅有力地反驳了主张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不共戴天的激进意志论,而且也有力地反驳了宣称人们能以无意志的方式达成与自然因果一致的现实自由的无意志论。事实上,只要我们不是沉溺在西方哲学家精心发明的某些莫名其妙的晦涩术语中,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类似的真实事件上,或许更容易走出这个西方主流学界凭空构想的扑朔迷离的理论迷宫。无论如何,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摆在那里的基本事实,而非哲学大师们设想出来的玄妙架构。
站在激进意志论者立场上的牛尧这样反驳无意志论者:“虽然我们没有对意志的直接观测证据,但是我们有间接证据——例如,我们通过内省而发现的意志作用。”[17]尹孟杰针锋相对地指出,“通过内省或者体验得到的间接证据却无法证明行动者体验到的就是意志而非认知或者情感”[2]。不过,假如不仅刚才分析的抢包子者的选择或霍诺德的行为,而且无意志论者谈到的“意图”“当下的想要”“我们的愿望”“随心所欲”等都不足以作为意志存在的“间接证据”,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仅缺乏有效的直接经验证据证明认知或者情感的存在,而且通过内省体验得到的间接证据也无法证明行动者体验到的就是认知或者情感。因此,人的自由不仅是无意志的,而且是无认知和无情感的,剩下来的只有因果律与随机数发生器的统一。可是,一旦这样将自然主义的立场贯彻到底,自由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这里看,无意志论者未能给自由下个清晰定义的深层原因或许在于,这样的定义势必会通过语义分析的途径,迫使他们承认意志的存在及其自由属性,因为“由乎自己的从心所欲”已经分析性地包含着对与自然因果机制一致的需要—想要—意志的指认了。不管怎样,无意志论者在肯定了与自然因果一致的现实自由后,依然拒绝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只会让自己的立论沦为无源之水。要是连自由意志这个动机源头都不承认,怎么可能说清楚人们对自由的现实追求呢?
四、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
从文本看,无意志论者主要是围绕道德责任的根据问题,否定了与自然因果二元对立的“自由意志”的存在。但考虑到笔者在回应苏德超和田昶奇的文章里,已经论证了自由意志对于人们承担道德责任的必不可少,所以这里想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论证自由意志对于人们维系自身存在的必不可少。
自由意志之所以对于人的存在不可或缺,根本原因在于它作为“需要—想要”内在包含了那根因果链条:只是在人的“存在(有)”出现“缺失(无或没有)”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形成需要—想要—自由意志作为动机源头推动人们从事随意任性的行为,以求弥补缺失,满足需要,维系存在。换言之,只要人的存在有了缺失,人们就会生成需要—想要—自由意志,并且哪些方面的存在有了缺失,就会生成哪些方面的需要—想要—自由意志。倘若这些需要—想要—自由意志得到了实现,人的存在就得到了维系,并且哪些方面的需要—想要—自由意志得到了实现,人在哪些方面的存在就得到了维系。举例来说,人们揭示事实真相、获得真理知识,就能满足求知欲达成认知领域的自由存在;人们创作或欣赏了艺术作品,就能满足炫美心达成炫美领域的自由存在。
从这里看,人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以需要—想要—自由意志作为动机源头展开的悖论性动态过程:人的存在出现了缺失,才会生成“需要—想要”弥补这些缺失的自由意志,并通过将自由意志付诸实施的途径,满足人的需要,弥补人的缺失,维系人的存在。就此而言,人生在世的所有悖论都植根于“我需故我在”的悖论:只有生成了弥补缺失的需要,我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因此,没有了需要—想要—自由意志,也就不会有人的存在;或者说,人一旦不再有所需要—想要了,也就不再作为人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同苏德超所说,“‘意志’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词”[1],不过,人们在日常言谈中如此自然而频繁地说出这个词,与其说是在谈论某种压根不存在、只是哲学家凭空构想的抽象幻念,不如说是在谈论自己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须臾无法离开的那个动机源头。也只有这样理解自由意志对于人们维系存在的必不可少,我们才能理解自由意志对于人们达成现实自由、承担道德责任的必不可少。
首先,从“我需故我在”的视角看,人的整体存在可以说是由自由与不自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当人们从心所欲地实现了某些自由意志的时候,就在这些方面拥有了自由的存在,反之则在这些方面拥有了不自由的存在。所以,否定了自由意志对维系人们存在的必要意义,我们就无从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达成连无意志论也没有否定的与因果机制一致的自由,却竭力避免同样是与因果机制一致的不自由了。事实上,无意志论者除了语焉不详地谈到了人们与自然因果一致的自由状态外,几乎没有怎么谈到人们与自然因果一致的不自由状态,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否定了自由意志,结果没法回答人们在与自然因果一致的前提下怎么也会陷入不自由的难题。人的这种不自由状态不是由于与自然因果不一致造成的(当然更不是由于随机数发生器突然失灵造成的),而是在与自然因果一致的同样前提下,由于自由意志遭受挫折失败造成的,所以尽管它与人的自由状态截然相反,却可以得到同样合乎理性的解释。
其次,无意志论者强调的道德责任问题属于人的人伦存在,重点在于防止不可接受的伦理之恶:谁要是伤害了其他人,侵犯了其他人的权益,却没有承担道德责任,就会破坏人伦关系。对此笔者看法与无意志论者没有差异,区别仅仅在于,在笔者看来,人们在伦理领域从事的所有行为,无论包含怎样的因果链条机制,都是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才应当承担自己的人伦行为给其他人以及自己带来的后果责任,由此维系道德领域的正常秩序。否则的话,倘若按照无意志论者的见解,我们无须诉诸自由意志,单凭人们行为的因果机制就能找到道德责任的根据,就很难解释一个问题:某个包含了同样因果机制的行为,为什么张三觉得值得赞赏,李四觉得应受谴责?如前所述,笔者正是据此对田昶奇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对于“我感到饿”—“包子能让我饱”—“包子就在包子店里”—“我可以通过抢劫获得包子”的因果链条机制和理性推论关系,“我”觉得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却觉得是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呢?除非无意志论者能够回答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否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道德责任来说,与因果机制两位一体的自由意志构成了必不可少的根据。
最后,“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里的“必然”二字,同时兼有“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认知意思和“不可或缺或不可抗拒(无法改变)”的非认知意思。在日常言谈和哲学语境里,两种语义往往纠结在一起,也给我们揭开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之谜增加了难度:有可能否定自由意志的必然,是哪一种意思上的必然呢?事实表明,只有人们抗拒不了坏的必然性(厄运或噩运),才会否定人们的自由意志,并且也不是在“使其变成无”的意思上,而仅仅是在“使其遭受失败”的意思上否定自由意志,所以往往造成悲剧或崇高的后果。相比之下,人们抗拒不了好的必然性,非但不会否定自由意志,反倒还能促成自由意志的实现。至于认知意思上的必然性,笔者一直认为与自由意志保持着两位一体的关系,所以不会在任何意思上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
不过,笔者此前还是按照国内外的流行见解,把认知意思上的“必然”和“偶然”理解成事实的两种特征或状态(必然规律或偶然属性),并据此肯定了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两位一体。但在批判性地解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后[18],笔者发现,它们与其说是事实的两种特征或状态,不如说是人们对事实的认知的两种特征或状态。当人们以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确定性方式认知某个事实时,就会说它是“必然”的;当人们以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不确定方式认知某个事实时,则会说它是“偶然”的。能够支持这个见解的关键证据是:对于掷硬币、大树倒下、量子运动等现象,倘若人们拥有了足够的能力和信息,就能以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方式揭示它们的因果链条和变化趋势,从而把原本的偶然现象变成必然的。事实上,我们不仅能在这个意思上理解斯宾诺莎的主张:“说某个东西是偶然的,仅仅表示我们的知识有缺陷……对它的存在不能明确肯定”[11]32-33,而且还能在这个意思上理解康德倡导的很少有人说明其机制的“哥白尼式革命”[19]——“人为自然立法”的实质,就是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把对象本不具有、只是认知包含的“确定性”结构加到对象上,仿佛自然物遵循着某种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规律(法,law)”似的[20]。
由此考察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会得出一个更有力的结论:如果说认知意义上的必然和偶然只是认知的两种特定状态,就更不可能存在“必然只会否定自由意志,偶然才能促成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架构了。首先,人们对事实拥有的任何必然性暨确定性的认知,非但不会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反倒还体现了求知欲以及这种自由意志的成功实现(亦即意味着他们达成了从心所欲的认知自由),并有助于指导他们成功地实现道德、实利、信仰和炫美方面的自由意志;其次,人们对事实拥有的任何偶然性暨不确定的认知(如有关粒子的不确定认知),反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求知欲这种自由意志的挫折失败(亦即意味着他们未能满足求知欲而陷入了认知不自由)。
就此而言,当我们在认知意思上说“自由意志‘必然’存在”的时候,其实是指我们能以确定性的方式指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及其意义。所以,这样的“必然”当然也不会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了。相比之下,当激进意志论者断言“自由意志”与“必然”不共戴天、只是“偶然”的时候,仅仅意味着它对自由意志只有不确定的认知,并因此陷入了逻辑矛盾。它的这个断言也是以确定性的方式指认了“自由意志”一定是与“必然”不共戴天、一定只是“偶然”的“必然”特征。因为假如真像它断言的那样,“自由意志”与“必然”完全不共戴天、纯属“偶然”的话,它对于“自由意志”是无话可说的——或者说任何确定性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它说出的每一句确定性话语都在逻辑上否定了这个断言。在这方面,量子力学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它虽然承认人们对粒子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但要是它的全部认知都是随机偶然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了;相反,作为一门科学,它首先是由确定性的认知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有关粒子的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认知,如同“‘测不准’—定律”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就此而言,笔者此前的见解依然成立:“只要承认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我们对意志自由以及现实自由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清晰确定的言说,就像我们对于纯粹偶然的现象不可能形成任何清晰确定的言说一样。”[3]
综上所述,无意志论的观点难以成立,不仅在于它通过否定了自由意志而否定了道德责任的根据,而且还在于它否定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其中也包括了这场对话的存在根据,因为各位参与者都是基于好奇心这种自由意志参与到对话中的。从某种意思上说,笔者之所以否定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强调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避免这类说不通的逻辑矛盾。
注释:
① 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引用西方译著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有所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② 不难看出,激进意志论和无意志论的观点虽然相冲突,有一点又是相通的,都把自由归结为随机偶然了;区别主要在于,激进意志论者认为随机偶然的自由是与因果必然“不相容”的,无意志论者则认为随机偶然的自由是与因果必然“相容”的。
③ 请注意下面这个被二元对立架构遮蔽了的事实:在攀登过程中,假如真有一阵难以预测的山风以随机数发生器的偶然方式吹了过来,霍诺德或许就会跌落悬崖、粉身碎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