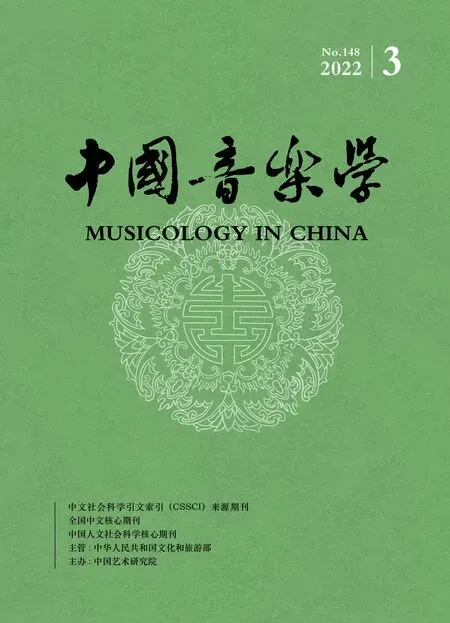后基督教时代的巴赫诠释—论汉斯·布鲁门伯格的《马太受难曲》
□毕 琨
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凭借他的著作《隐喻学的范式》(1960)、《新时代的合法性》(1966)、《哥白尼世界的起源》(1975)与《神话研究》(1979),布鲁门伯格提出了以“隐喻”(Metapher)作为哲学语言的基本要素、恢复那种形成于古希腊时代的对理论的“好奇心”和以神话减轻脆弱的现代性人类的内心负担等观点。作为与于尔根·哈贝马斯齐名的德国哲学家,布鲁门伯格的晚期著作《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于1988年由法兰克福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由于浸润在德语原作中的神学、解释学、音乐史学与音乐哲学相交融的特点,造成了读者接受上的困难:它的英译本直到2021年才面世,而中国音乐学界至今尚未有学者发表与之相关的论文。
作为布鲁门伯格的唯一一部以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马太受难曲》延续并深化了《神话研究》中的议题,即如何在具有压迫感的现代性中坚持自我,找到一种审美化的自我和解的方向。它探讨了如下问题:对于不再是基督徒,却又从接受史的角度回顾基督教的读者,基督教的陈述还具有什么意义。尽管布鲁门伯格长期的辩论对象雅各布·陶布斯(Jacob Taubes)和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在与布鲁门伯格的探讨中批评了他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的新异教含义,但是,布鲁门伯格的《马太受难曲》还是受到了神学家们的认可,因为它能够激发新教和天主教神学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在《马太受难曲》中布鲁门伯格将音乐解释学与神学相结合,为后基督教时代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与路径,为远离神性的现代性的人找到了存在的美学性依据。①胡继华:《神话与启蒙的共生之环—略论布鲁门伯格及其〈神话研究〉》,《书屋》2014年第10期。对于布鲁门伯格来说,一种来自于E.T.A霍夫曼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是可以被接受的—即音乐变得不再是宗教性的,它本身就是宗教。②〔德〕卡尔·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6页。虽然巴赫本人认为,音乐可以服务于宗教礼仪,但是,巴赫作品的伟大之处却在于,允许宗教的本质从宗教礼仪转移到音乐本身。①〔德〕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一、崭新的接受视域
在《马太受难曲》中,布鲁门伯格强调了那种包含着视觉与听觉能力的视域概念(Horizontbegriff)—它涉及对过往历史痕迹的触及以及对未来的隐喻性的接近。②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p.7.意欲获得这种视域能力的人,必须与他所生存范围之内的人与事打交道,或者说,他要将自己置于一个可以理解的位置。③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7.在此,视域(Horizont)是一个背景,它的作用就在于让一切表面的事物都在它的衬托下脱颖而出并发挥作用。于是,所有的事件和形象就矗立在它们的视域之前。布鲁门伯格也指出,深度性(Hintergr ü ndigkeit)并不一定就有感受的价值,与此相对的表面化(Vordergr ü ndigkeit)也不代表会褫夺感受的资格。因为感受的片面性是一切感受的宿命,这要求人们对缺席的、尚未知觉到的知识要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因为它们也许不会永远缺席。④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8.在这样的意识设定中,需要提及以马太福音为依据的受难曲的听众,以及那些为了不错过巴赫作品,而必须在巴赫作品面前出现的现代性的人。然而在他们的视域之中,巴赫教区的图像和寓言、神圣的历史与讲演、格言与赞美诗都消失了。巴赫逝世已经两个多世纪,关于巴赫的一切不可能如历史评论家所写的那样被准确地理解。
对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否曾经存在过的怀疑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可能让《马太受难曲》的晚期听众没有机会识别出谁在被歌唱以及谁在被安慰,有可能让《马太受难曲》当下的听众成为被其传统所遗弃的现代性的人。但是通过对接受视域的调整,还可能为基督受难曲赋予新的意义、经验和考量的立场。⑤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9.在此放弃美学的吸引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太受难曲》的后基督时代的听众是不会被历史的真实性这个过时的问题所感动的。在音乐中存在的只是神圣的自我意识的传递,它不言而喻,不可重复,以此来呈现给每一个隐含的巴赫听众。⑥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10.当现代性的人不去考虑语词的规范等级之时,就意味着音调、充盈的受难曲的自我鸣响将超越所有的内容。⑦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15.
对于现代性的人而言,历史中的神学术语上帝的 “启示”(Ofenbarung)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早已陷入了不可察觉的境地,对《马太受难曲》的聆听却可以抵消这种不可察觉性。被《马太受难曲》感动的人也许会做出让步,他们也许会承认,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上帝,保罗、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的上帝会被过度地伤害,但即使没有这种让步,人们依然能够领会受难曲。通过聆听受难曲,耶稣的受难与濒死才被直接地呈现出来。在受难曲中音乐是那种支配文本构成和语词意义的东西。
二、作为“绝对音乐”的《马太受难曲》
巴赫的基督受难音乐让现代性的人有权不去理会马太福音传统的不可更改性,巴赫音乐的再发现是19世纪音乐史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巴赫的音乐从先前的外在目的中抽离出来,被赋予了审美的自律性。它是 “绝对音乐的精粹样板”“绝对音乐”的“范式”,是“复杂结构和强烈表现力的完美结合”。⑧〔德〕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第236页。在此,语词被音乐同质化了,以至于没有任何逻辑可以反对它。⑨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48.音乐独立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它在语词中是无法获得的。即使一位福音传道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关注语词,也无法将许多异质性的语词聚拢在一起—巴赫以音乐的方式介入福音书,以音乐确保文本的统一性。⑩〔德〕伯伦贝格:《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布鲁门贝格的〈马太受难曲〉与尼采》,载《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田立年、吴增定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中,音乐并不是语词的伴随物,相反,音乐使得语词只能通过声音的方式让人听到。在这部作品中语词通过音乐让自己获得了鲜活的隐喻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历史批评之前,音乐成为文本的救赎—在这部作品中审美经验是那种让宗教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①Josef Wohlmuth, Hans Blumenbergs Interpretation der Matthäuspassion Bachs, Verk ü ndigung und Forschung 58. Jg., Heft 1, 2013, p. 70.
巴赫对素材的加工是一种提炼浓缩的过程,借以纯粹的音乐的力量—借以一种“诸元素组合的游戏”②Georg Knepler, Geschichte als Weg zum Musikverständnis: zur Theorie, Methode und Geschichte der Musikgeschichtsschreibung, Leipzig: Reclam, 1977, p.95.—或者说,通过自足的音符象征而孕育出更有力的生命。布鲁门伯格认为,通过音乐巴赫将耶稣的代替世人遭受痛苦的行为,直观化或审美化了。巴赫凭借声音让听众与沉痛的情景保持着距离—当听众有机会疏离恐怖的状况之时,感性化或者说审美化就有机会获得成功—这是对现代性的悲苦现实的一种超越。③胡继华:《对现实性的审美超越—布鲁门伯格解读〈马太受难曲〉》,《基督教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具有美学性的中心意义。在Eli Eli中,今天的听众听到了绝望的呼唤。《马太受难曲》中的这声呼喊就是音乐的不协和音,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听觉上的不协和,也让我们领悟到了它是怎样被转化成艺术的。而一旦这声叫喊被转化成艺术,那不协和的经验就被扬弃,与此同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就被转化成了愉悦的体验,这让《马太受难曲》的听者得到解压式的释放。④〔德〕伯伦贝格:《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布鲁门贝格的〈马太受难曲〉与尼采》,第138页。《马太受难曲》中的戏剧性的场景捕捉到了作为悲剧高潮的受难事件,那后基督教的听众可以体验到颤栗以及感到随之而转化出来的快感—在德意志美学中,悲剧(Trauerspiel)一词是由“悲苦”(Trauer)与“游戏”(Spiel)相结合构成的,在戏剧层面游戏性得以强化。⑤〔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基督受难音乐短暂地给予人一个幸福的免除罪责的空间,这个空间具有不可追问性,它意味着原始宗教生活世界的一种最终的形象化。⑥Hans Blumenbergs Interpretation der Matthäuspassion Bachs, p.78.在对巴赫的受难曲的聆听中,听众被带回到仪式性的层面,由此能够实现一种非概念性的操作,这个操作打碎了理论化的主题。音乐占据着神学与形而上学缺少的东西,占据着一种对拉丁语语词Passion的双关语的感受能力。⑦Nicola Zambon, Wie ein erloschener Stern,der nachleuchtet. Marginalien zu Hans Blumenbergs Matthäuspassion, in: Permanentes Provisorium: Hans Blumenbergs Umwege, hrsg. von Michael Heidgen,Paderborn: Fink, 2015, p.208.从字面意义上讲,Passion一方面意味着痛苦与死亡,另一方面意味着人类的激情,意味着将上帝和人推向更高的境界。痛苦与激情意味着审美偏好:人的生命自身的动态过程就是在快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这种相反的两极之间摇摆的过程。它们之所以给人的感受以美的形式,就在于它们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之中。在艺术家的作品内激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构造的力量。⑧Wie ein erloschener Stern, der nachleuchtet.Marginalien zu Hans Blumenbergs Matthäuspassion, p.208.
对音乐的亲和力和良好的趣味是现代性的人参与像受难曲这样的事件的唯一合理条件。⑨Wie ein erloschener Stern, der nachleuchtet.Marginalien zu Hans Blumenbergs Matthäuspassion, p.212.在这里审美观念并不意味着严肃性的降低,只有通过审美的刺激,受难的故事才能在情绪上得到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上帝的分量。音乐与那种涉及讽喻与神话、隐喻与图像的敏感性相关,简而言之是与非概念性相关。⑩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45.康德希望看到宗教的拟人化被克服,以支持对理性的纯粹信仰。与康德不同,布鲁门伯格认为基督教的上帝需要中介性的工具才能成为现实。这些载体就是隐喻、符号、图像,它们并不幼稚,是克服概念性的预制形式,是独立的、有价值的非概念性形式。只有在人能够与非概念性打交道的情况下,受难的故事才是可行的。为此,他们就需要一种与神学的僵化教条和形而上学的严密系统相对立的音乐,因为音乐是概念以及类型单一性的对立物。这正如尼采强调的那样,真正重要的不是语词本身,而是一系列语词的语气、力度、调置、节奏—一切无法用文字书写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由于音乐具有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它成为解放记忆、深刻体验的绝佳工具,简而言之,音乐是非概念性理解的绝佳工具,它完全可以打破教条的统一性和僵化性。在《马太受难曲》中仪式感的优先性先于陈述,在仪式中的人们不必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做的只是让仪式圆满宏伟地实现,没有人在传道人的宣叙调中询问“圣餐”和耶稣的话“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外表上看布鲁门伯格的《马太受难曲》是文本缩影、轶事和短篇小说的集合,充满了离题、交叉、迂回—但这一切只是发生在表面上。更确切地说,它们以变奏、插入句和重复的形式排列在一个共同的文本中, 以对比的方式推进主题化的主要动机。布鲁门伯格的《马太受难曲》就像一首反向进行的声部一样,抵消了古代语词的合唱和神圣的书写,以此再现了巴赫受难音乐二重合唱队所保持的尘世小调和天堂大调之间的张力。《马太受难曲》的音乐可以打破教条的统一性和僵化—布鲁门伯格也接受了恩斯特·布洛赫的音乐哲学—当耶稣说“你们中的一个人会背叛我”,教徒们在最剧烈的快板中不安地互相喊道:“主啊,是我吗?”在经过一段绝妙的休止之后,教徒们唱起了合唱“是我,我应该赎罪”,《马太受难曲》的再次鸣响强化了一种主体化的倾向。①Ernst Bloch, Geist der Utopie, Münche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Dunker & Humblot, 1918, p.103.古老福音圣歌的谐音形式伴随着野性的、锯齿形的、分裂的节奏对位,那狭义上的沉默和封闭的形式类型像是被突破了。②Ernst Bloch, Geist der Utopie,p.104.在这里受到训练的声音渴望将自己转移到更丰富更坚固的乐器的色调上,以此作为管弦乐队中最高、最具表现力的部分。
音乐不是一种认知,也不是实际知识的创造。受难音乐让聆听者与他无法忍受的事物保持审美距离,这意味着适宜的限制在一种表现上帝之无限性的形式性上。这让人想起埃米勒·米歇尔·乔朗向人类的眼泪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致敬,并将他的形而上学的反思浓缩为一句话:“音乐使我大胆地面对上帝”。③Hans Blumenberg, Matthäuspassion, p. 109.结尾合唱的双向角度使人几乎难以忘却《马太受难曲》,让人相信这位托马斯乐长不会白白地让歌唱发生,让人在聆听这部作品之时无法否认它孕育了上帝。依据受难曲上帝必定存在,否则这整个作品就是一个撕裂的幻觉。如此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夜以继日地寻找上帝的证明却忘记了真实存在的东西。
三、聆听的意义
今天的听众有一种秘密的特权,即摆脱了教条式的知识,而这种教条式知识总是在问题被提出之前就知道答案。④Wie ein erloschener Stern, der nachleuchtet.Marginalien zu Hans Blumenbergs Matthäuspassion, p.219.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不仅创造了最高程度的教义的确定性,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反对确定性的对立面的状态。现代性的受难曲的听众正好处于后者的位置,那就是在确定性的丧失中得到收获。结合这样的场景通过对音乐的纯粹的体验,受难将再次变得有意义。
音乐对于理解基督受难是不可或缺的,它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概念相异,通过音乐受难变成了听众的聆听体验。声音揭示了痛苦的具体性,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被遗弃的人类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音乐至少可以实现同情与共鸣,这就如同合唱团在《马太受难曲》结束时唱到的那样:“我们含泪坐下,对墓穴中的你呼唤。”⑤Nicola Zambon, »Wir setzen uns mit Tränen nieder«- Hans Blumenberg als Hörer der Matthäuspassion,in: Das Heilige (in)der Moderne, hrsg. von Hector Canal,Maik Neumann, Hans-Joachim Schott, transcript, 2013, p.50.
布鲁门伯格《马太受难曲》的核心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性分析,这种分析只能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巴赫的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基督受难音乐为布鲁门伯格提供了一个生活世界式的契机,通过音乐的造型性的力量去表达宗教思想所不能表达的东西。《马太受难曲》的宗教感染性所基于的神学前提,不仅对巴赫的同时代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域中本身就是固有的,但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难以接近了。⑥Nicola Zambon, »Wir setzen uns mit Tränen nieder«-Hans Blumenberg als Hörer der Matthäuspassion,p.43.在圣经—基督教的受难故事中,一个被他的创造物过分怨恨的上帝,他的牺牲是对难以理解的赎罪的激烈要求。这是一个遥远的甚至是奇怪的想法,再也无法与现代性的人的生活世界中熟悉的任何事物联系起来。对于处于现代性中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信仰的前提已经丢失,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唤起这种意象之意义的视域也丢失了。处于现代性中的人会发问:“今天还有谁相信这位上帝为我们的罪孽而牺牲了自己?”①Nicola Zambon, »Wir setzen uns mit Tränen nieder«-Hans Blumenberg als Hörer der Matthäuspassion,p.46.这就是现代世界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出现的鸿沟。尽管存在种种困境,根据布鲁门伯格的说法,现代听众仍然可以接受失落的异己上帝作为自己的上帝,尽管距离遥远,尽管只是在音乐演出的持续时间内。布鲁门伯格认为,即使信仰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观念,这种虚无主义却并不意味着这位死去的、被埋葬的、几乎被遗忘的上帝对人无话可说。巴赫的生活共同体与现代听众遥不可及的距离,恰恰使我们能够摆脱教条知识的严密性。《马太受难曲》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关于上帝的谈话都可以是隐喻性的,这创造了一种接受的自由。
结语
布鲁门伯格与阿多诺的观点达成一致:从教条式的秩序中释放出来的是巴赫音乐强大的美感,它具有一种纪念碑的性质。②Iris Hermann, Musik, Text und Schmerz in Johann Sebastian Bachs Matthäuspassion, Zeitschrift f ü 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H. 36, 2006, p.31.因为它引发了对一个世界的体验,这个世界不能或不再能够以实质性的方式呈现给主体。通过充满着想象的回溯,上帝将再次变得可以考量和可以言说,这正如《马太受难曲》所显示的那样。关于基督受难充满想象力的富于变化的回溯不是柏拉图式的确定性的提升,也不是关于复活的确定性表达,而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在后基督教听众的视域中充满力量的表达。后基督教听众通过对不确定性的追溯可以开启新的确定性。布鲁门伯格将《马太受难曲》的音乐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中—这旨在建立一种听众结构,使得在后基督教的视域中对基督受难的理解与言说成为可能,即使这一切只是发生在慰藉性的聆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