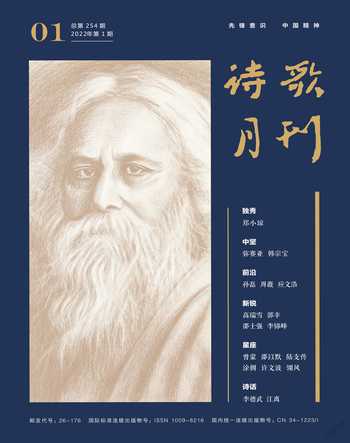空心潭(组诗)
空心潭
在这里能悬空的
必定是飞鸟。飞鸟是过客,我也是过客
跋涉与穿越者,此时有着最短暂的交汇
我们并未借机言谈,我仅能
在某个黑夜唤住自己
和自己大声交谈。
空心潭若是空的,尘世便也是空的
静止,你所能
行走,你也所能
但这些虚妄的影子,必有所不能
边上一棵半朽的古树恰巧也加入了讨论
确切地说,也在两面巨大的镜子里被发现
我们生活在镜子里
致落叶
好吧,就这样败退
拖曳起盛年时绵密的心事
戴上来时的盔,来时的甲
在最后一场山风之后
山呼海啸般退去
假使还有一段惊泣鬼神的爱情
在燥热午夜
引燃了无名烽火
那么,请将它的魂魄带走
在某一年春天
请仍将干干净净地来
访柳如是墓
与她继续唱和的春水
又暖。我绕过西城,绕过了一首好词
去寻她。终究无处可寻
那一副艳骨,也曾瘦
瘦比黄花。和收不得的一世风流
今安于了一抔净土:
“莫道无归处,莫道旧时飞絮,莫道人去夜偏长”
三百年的光阴里
红和绿,肥了的江南,或者句子
已皆成虚空。但除非你爱
爱绛云,也爱红豆
除非你在晚明的山河里
料定如是多妩媚
吃茶
立冬以后,风雨住进山中
湿冷,虚寒
原本要问季节借来的枯枝和干草退还给火种
也闻不见炊烟,竹篱笆扎紧的茶园里
有人点燃一首诗
有人削尖一个词语
杯中的茶叶开始返青,裹挟泉水
走咽喉要道,直达心肺
而昨夜,夜已深
河东街经过老城,有酒客提灯
药引
裹着廉价的茶水,日子从那天起
一一作别。我嗑开一枚南瓜的种子
五月,又一次在腹中种下
禪坐在兴福寺里
我磕过头的神还在。他们最先看见空心潭上
有鸟鸣经过,有如钟声从肺腑上划过
不用再开口。山峰间的涡流
通往山下就成了一池静水
有如眼睛凿开了身体
能写意流出来的都不是泪
这一年,红豆树在小城花开
这是红豆与红豆树之间将有的重逢
是生活里预先埋下的肿胀
转过了那些长巷子,我仍然深信
儿时的单纯。打住,或者奔腾
快四十年了,有时我只是被灯火虚晃了一下
那天我也独坐在七弦河的民居下
足足半日。这是对江南的茫然。有如身体里
每一条河流生病时自己为自己开具了药引
暮春
水开始饱满
枪膛微微发热
去云端,或者是柴草上好像都一样
吃了姑娘的亏
腰疼
小把小把的光阴被抄送
陷入故乡和流放地
我再一次被摊平
等食桃子的肉
和皮
秋风辞
雁阵高飞,他们退耕还林
为往事奔波的人
强说过一个愁字,恰关进了小牢笼
我的故乡:江南
吞下秋天的是我的喉咙
和我的舌
渴!百里之外,长江茫茫
百步之内,大幕沉沉
一夜西风乍起!是谁早于天空
取出大把荒草和心事
枯荷
白昼还在生长
看似无所谓要带走什么
那就跪下来
在池塘,保持长久的姿势
不经意的美
是被支起来的,善良的疼痛的部位
最后缺了渔歌
和夕阳,把飞白留给冰冷的风景
诗友来访
在小小的圆里保持着
我们的谈话
是整个夏天茂盛的一部分
肯定是坐上了另一个轴,或者
是台风扑倒的原因
无数个通往过去的窗口
渐渐明亮
幻想症
我们翻出来
幼稚病
我们翻出来
而对于岁月的封锁
你魔性的笑声比我总要高明一些
许文波,1970年代生,居虞山下,江苏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潮》等刊物,著有诗集《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