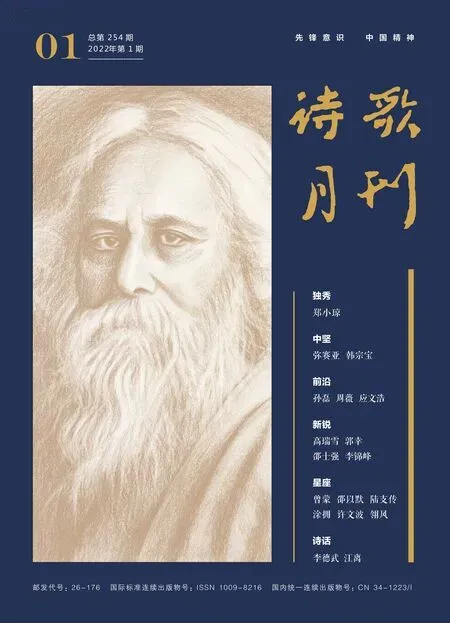“当我唱完了那首歌谣,群星皆已熄灭”
郑小琼
从天河搬到白云,生活的节奏因为疫情而改变。以前双休日,我都会到工业区转转,比如东莞、惠州、佛山、深圳等地。疫情期间,无法外出,在双休日写小说,抽半天时间爬白云山。沿山道行走,在山里转上三四个小时。山中的一草一木、一溪一涧、一崖一石……为了弄清楚白云山的树木、花草,我用“形色”软件了解这些植物,它能分辨照片中植物的名字、习性、价值……还有历代诗人是不是写过与这株植物有关的诗歌。几个月时间,我认识的植物越来越多,记住了很多有关植物的诗歌。这些在路上朴素得无人关注的花草,不仅有美丽的名字,还有很多诗人为它们写过诗。我越来越感兴趣,并重新认识古典诗歌的意义,特别是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诗人,他们为路边的花草写下的诗歌,如果不是刻意地搜索,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诗人存在,在新诗的创作上,似乎很少关注具体的花草、山水。在白云山中散步,面对自然的山水,一些句子与念头突然涌上来,我边走边在手机上记下。
“当我唱完了那首歌谣,群星皆已熄灭”,这是我从黄婆洞水库朝黄道婆像走的途中写下的句子。我沿梅花谷一直走到聆泉,聆泉很小,水很清澈,附近村民背着壶、扛着桶在接山泉水。山道竹林茂盛,山谷幽深,只剩一线天。我抬头望了望天空,一团像老虎样的白云正飘过,我在手机上写下“老虎抱雪走过天空”。回到家,我把这些句子整理好,放在一个文件夹。为了记住在山中认识的植物以及与它们有关的诗歌,我会写下一段小感受。
打工诗歌以现代工业化为背景,十几年前,我阅读了一些工业革命的文章与书籍,包括经济学的书籍。其时,我在工厂的车间装配一种塑胶制品,那家公司的制品大量出口,出口的地方很多,从富裕的国家到不发达的国家都有,而价格与质量完全不一样。当时工友们关心的是订单的单价,好不好做,做哪个工资高些。至于它们出口到哪里,大家从来不关心。我却常常会问一些看来很幼稚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把质量差的出口到穷国家,质量好的一定要出口到富裕的国家。后来偶然读到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的一些文章,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1800年以前,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社会中,人均收入会有所波动,时好时坏,但却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即使到1813年,大部分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他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好”。而在工业革命后到现在,全球最富国家与非洲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有40倍之多,这在工业革命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行业便是纺织,当我站在黄道婆像前面,她是中国纺织业史上的先驱人物,想起工业革命,想起写过的打工诗歌。在工厂那段时间,我用中国传统咏物诗的方式写车间里的机器,车间的图纸、螺丝、车刀等都成为我诗歌中的意象,我在工业物象间寻找诗意。
在白云山里行走,在认识那些植物的过程中,古人写诗,万物皆可入诗,在打工诗歌中如何将工业名词入诗,如何将人类自身智慧创造出来的事物变成诗歌中的意象与传统,拓展打工诗歌内部的文学性与美学传统。我开始思考人类与机器、人与人类自己创造之物如何共处,让工业名词焕发出一种古老的诗意。有机地将工业名词与自然意象融合,让工业器物与诗意表达之间产生巧妙的平衡。工业名词像一把尖锐的“语言之刀”剖开生活的铁器,闪烁语言之光,照亮人类精神与内心的幽暗处,解剖人类面对工业的孤独、迷茫、伤害、创造。从重新认识自然开始,在我的诗歌中,人类与机器、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的不再是过去诗歌中表达的紧张与冷漠,它们之间和谐共存,如何让诗歌散发着工业机器般的节奏,密集的工业意象相互撞击,彼此制约,犹若工业齿轮般啮合,表达工业词语野蛮的生命力与工业自身的律动。
有一天,跟一个不写诗的朋友聊到现代诗歌,他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写现代诗的诗人会不会把自己的诗歌给牙牙学语的儿童读,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他又说,为什么家长教刚学说话的孩童都是教他们背诵古诗,很少有人教现代诗,其实对孩童来说,无论是古诗古文,或者现代诗歌,在他们心里没有多少区别。他的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我问过一些诗人朋友,都没有回答。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教大国,“诗教”这个词出自《礼记》,无论是从“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种记录古人日常劳动生活的民间歌谣发展起来的“国风”,还是“投足以歌八阕”这种“功成作乐”的传统发展起来的“雅乐”,抑或从远古举行的大型祭祀发展起来的“颂”,或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现代诗歌似乎与中国诗教传统开始断裂。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为了便于阅读与记忆,我写了一批不超过一百二十个字、十行以内的小诗。在写这批小诗之前,我读了一些有关禅的文章、日本的俳句、魏晋的玄学等方面的书籍,试图将三者融入新诗之中,写了七八十首短诗,算是一种探索。对于新诗的探索,许多同行们都身行力践,比如现代禅诗、九行以内、八行、六节、汉俳等都有人探索过,用禅思来打通“古典”与“现代”看起来似乎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废名、周梦蝶、洛夫、孔孚等前辈诗人在这条道路上有一定成就,我写了几十首之后,暂时搁浅了这种探索,觉得功力太浅。十年的工厂生活与七八年工业区的交流经验,现实主义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修禅在于修心,而我的心尚不能静。
我不停地在白云山的山道上转来转去,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面对白云山四时不同的风景,面对满眼青山,不同形状的石头,不同种类的树木,山中溪流、水塘、寺庙、古墓、悬崖、山洞……从认识的植物中重新认识中国的古典诗歌,我开始写这些诗歌。在诗歌的形式与结构上做一些有意思的探索,早些年,我寫过一本叙事风格比较强的《玫瑰庄园》,写了八十首二十四行诗歌,六节四行体例。后来出版了一本《纯白》的十二行诗集,四行三节的结构。中间还断断续续写了不少十四行诗歌,我最早的十四行诗采用莎士比亚体,四四四二的形式,后来写的多为彼特拉克体的四四三三形式,这些十四行诗收录在我的诗集《行旅》中。《行旅》中的十四行诗主要写我在异国的感受。在白云山中行走,我想以田园山水为背景写一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我还是想在形式上做些探索,我采用的是五行三节,一共十五行,在这些诗歌中,我进行了更严苛的要求,力求每行长度一样。
中国新诗百年,一代又一代诗人在进行各种探索,从发轫期闻一多先生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格律诗,到九叶派、朦胧诗、口语诗,大家从不同的维度对新诗进行有益的探索。我觉得新诗的探索应该注重如何“在变化中找回传统”。中国的诗歌史是一部不断在复古与革新交替的探索史,比如在唐代陈子昂等人提出“在革新中有复古,在复古中求革新”的主张孕育了唐诗的高峰。
我把这组诗歌命名为“俗世与孤灯”,它隐喻我写这些诗歌时的状态,在最现代化的广州城的白云山间行走,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诗意。每天挤着地铁上下班,回到斗室,青灯黄卷,推窗望外,是地铁、高速公路、汽车、高大的楼群、拥挤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十分熟悉这些场景,它们不断在我的诗歌中出现,我写过很多表达俗世的诗歌,我喜欢诗歌中充满人间的烟火味与俗世的争吵,它们是机器的声音、订单、图纸、塑胶、铁片、车刀……也是资本、商品、利润、GDP、跨国公司、网络,这些我熟悉的生活。当疫情不断改变着我曾经的生活节奏与习惯,我从热闹的工业区转身折进白云山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生活好像从俗世转向孤灯下,这些诗歌正是这种心境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