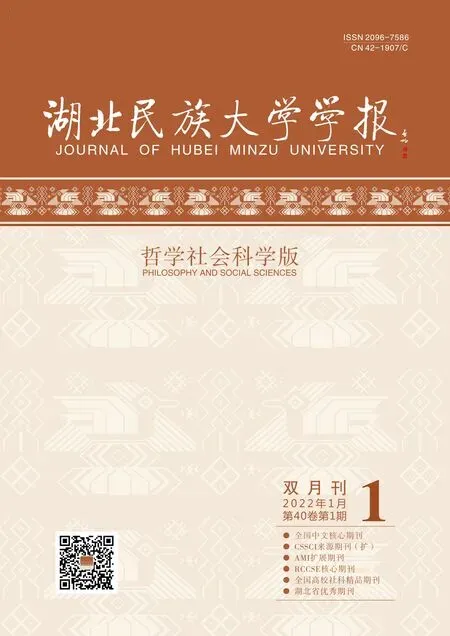爨僰军与元朝的西南边疆治理
张述友 王世丽
爨僰军又名“寸白军”,为大理国时期的常备军,元代被降格为云南乡兵,活动区域从云南扩大至西南地区。关于爨僰军问题的研究,民国时期夏光南先生关注较早,《元代滇之寸白军》对军队缘起、性质、人员构成、战斗力进行了概述性讨论;方国瑜先生有所发展,提出爨僰军的乡兵性质;此后张增祺、段玉明、张锡禄等就以上问题继续讨论。(1)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17-124页;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96页;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62页;段玉明:《大理国军事制度考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张锡禄:《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77-279页。但除夏光南先生之外,未再有专篇讨论爨僰军系列问题,甚至连爨僰军的整个活动轨迹也未曾梳理清楚。本文试图通过整合支离破碎的史料,探究爨僰军在元代的活动轨迹及最终历史命运,整体把握爨僰军在元代西南边疆治理中的作用。
一、大蒙古国时期爨僰军与西南统治的确立
1253年,蒙哥汗为实现“斡腹南宋”,命皇弟忽必烈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取云南,结束了大理国割据云南的历史,迎来蒙古统治云南的时代。但蒙古军忙于辗转全国各地征战,无暇顾及云南的军政统治,只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征战云南未降附地,扶持羸弱的大理段氏辅助执掌云南成为忽必烈的最佳选择,其中就包括仍有强大战斗力的爨僰军。大蒙古国至元初,段氏率领爨僰军先后追随蒙古大军远距离征战南宋广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平定云南境内舍利畏叛乱,征战云贵未降部,打破了爨僰军只活动于云南的界限,成为活跃西南地区的一支军事力量,协助元朝确立了西南的统治。
(一)配合统一战略
爨僰军追随兀良合台远距离征战南宋广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1258年,兀良合台率蒙古军三千,爨僰军一万,从滇东沿宋代以来广南西路横山寨买马道,一路势如破竹攻破今广西田东县、南宁市、贵港市、象州县、桂林市等地,又挥师北上,连破今湖南沅陵县、怀化市、长沙市,大小战役十三次,共斩杀宋兵四十余万。(2)《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81-2982页。翌年,兀良合台率大军在今湖北武汉与忽必烈胜利会师,部分爨僰军则继续征战于荆湖北路今桑植、沅陵等地,“爨僰……再从济江攻鄂东北”(3)姚燧:《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师中书右丞相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1册,第678页。就是例证之一。此次系列征战,爨僰军在人数上是蒙古军的三倍之多,一路长驱直入南宋统治腹地广南西路、荆湖北路及荆湖南路,可谓是披荆斩棘、骁勇善战,顺利完成了从西南包抄南宋的任务。1261年,时人详议官王恽拟定《宣谕大理及合剌章俾还本土手诏》,“嘉汝等(爨僰军)远自云南,导从先锋,转战千里,直渡鄂渚,以达于此,勤已至矣。今者俾尔各还本土,以遂厥性,优赐各有差”(4)王恽:《宣谕大理及合剌章俾还本土手诏》,《秋涧集》卷6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1册,第27页。,朝廷下令赏赐征战湖南、湖北的爨僰军,令其陆续返回云南原籍。但部分爨僰军官兵就地解甲归田,落籍于今湘鄂一带,即今湖南白族的由来,使得桑植县成为湖南白族聚居地,为桑植县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平定社会动荡势力
信苴日(段实)率爨僰军平定声势浩大、波及云南全省的舍利畏起事。1264年,舍利畏集结滇东三十七部及楚雄、姚安、昆明等三十万兵力,攻入昆明等地。(5)李源道:《大理崇圣寺碑铭并序》,刘景毛、文明元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93《金石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云南宗王不花(6)李治安:《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思想战线》1990年第3期。两次密集调遣爨僰军“率众进讨”舍利畏,激战过后,才得以收复今昆明、楚雄、玉溪、曲靖、宣威等地,使滇东爨部重新归附。信苴日因平定舍利畏起事有功,被朝廷赐予“金银、衣服、鞍勒、兵器”(7)《元史》卷166《信苴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0页。。1274年,舍利畏再次起事,信苴日用计将舍利畏“枭首于市”,舍利畏起事终因舍利畏被杀彻底平定,元朝又赏赐信苴日“金一锭及金织纹衣”(8)《元史》卷166《信苴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1页。。与蒙古军相比,信苴日及其领导的爨僰军更加了解云南的局势及舍利畏军队的特点,这是能够平定舍利畏起事的重要原因。舍利畏起事波及云南多个区域,给蒙古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信苴日及其领导的爨僰军维护了蒙古在云南的继续统治。
(三)征讨未降诸部
大理段氏率领爨僰军多次征战“远近啸聚,大为民梗”的未降附者。(9)王恽:《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秋涧集》卷5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0册,第669页。信苴日与信苴福亲率“爨僰军二万为前锋”,协助蒙古军征战尚未归降的云南诸部。如1276年,平定摆夷、和泥等未降附部落;1277年,平定永昌之西的腾越、蒲、骠、阿昌、金齿等未降部落;1280年,平定贵州八番、罗氏鬼国的叛乱;1283年,平定施州子童及会川诸夷的叛乱;1287年,平定维摩蛮未降部落。(10)佚名:《招捕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元史》卷210《外夷三》、卷11《世祖八》、卷133《脱力世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56、223、3229页;倪辂辑,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0-351页。
总之,自1258—1287年间,爨僰军耗时三十年完成对西南的征战,维系了西南边疆的大一统,西南疆域得以充盈,开辟了面向中南半岛的战略前沿,云南战略纵深得以保障。据《元史·地理志》载云南四至:“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11)《元史》卷6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7页。,当时云南行省的范围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及今缅甸北部、越南西北部、老挝和泰国北部。爨僰军对元朝西南疆域的确立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二、元代初期爨僰军的屯田守土
蒙古军平定云南之际就开始着手云南屯田事宜。1267年,皇子忽哥赤委派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劝农官负责屯田,并疏通滇池水域,得到良田万顷(12)《元史》卷167《张立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5-3916页。,为后续云南大规模屯田奠定基础。只是此时屯田类型均为民屯,直到1283年爨僰军军民合屯才开始军屯,并于1291年完成。
(一)屯田分布中的军事考量
为了清晰地了解元代爨僰军九处屯田情况,本文以《元史·兵三·屯田》为基础,结合《经世大典·屯田篇》所载,来说明元代爨僰军屯田分布情形,见表1。(13)大理金齿等处宣尉司都元帅府军民屯仅载有军民田总数,此处按户取均值。另外,云南军田、民田数计量单位均为“双”。大理、中庆等地“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乌撒路“诸夷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本文采用一双五亩计算。详见李京撰,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8、100页。

表1 元代爨僰军屯田
据表1,元代爨僰军军屯户数共3332户,民屯户数共15 184户,若每户按4.5人计算(14)据《元史·世祖本纪》载,1290年全国共13 196 206户,58 834 711口,得出每户约4.5口。,爨僰军军屯共14 994人,民屯共68 328人。1276年云南共128万余人(15)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46页。,那么元代爨僰军九处屯田人数约占云南行省总人数的6.5%,屯田人口规模较小。另外,爨僰军军田面积约60 907亩(16)由表1可知爨僰军屯每户18亩,又知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屯户数302,军田亩数补为5436亩,同理乌撒宣慰司军屯总户数为200,军田亩数补为3600亩。,民田面积约269 154亩(17)因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民屯户数165,民田亩数补为2970亩。,元代云南行省见于记载的屯田共有483 335亩(18)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那么元代爨僰军军田耕地面积约占云南行省屯田面积的13%,爨僰军民田耕地面积约占云南行省屯田面积的56%,所以,爨僰军军民合屯、军屯屯田共约占云南行省屯田耕地面积的69%。由此可见,虽然爨僰军军民屯田人数较少,但是规模较大,在云南行省中占有重要分量。
爨僰军九处屯田具有严密的层级性军事布防考量,军屯是民屯的重要军事支撑。鹤庆路、威楚路、中庆路是与内地“路”无异的行政建制,直属云南行省管辖,属于元朝统治的滇中腹心区。乌撒宣慰司、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民万户府、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位于边疆宣慰司靠近内地的交通咽喉,属于滇东、滇东南交通咽喉区。武定路虽是“路”的建制,但受罗婺土司影响,长期游离于中央王朝管控之外,直到元朝设武定路,才正式纳入王朝的管控,并设五处站赤,但仍面临罗婺土司的困扰,只能“制兵屯旅以控扼之”(19)《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58页。。武定路缺乏民屯条件,军屯才能保障昆明经武定、西昌至四川驿道的畅通,属于交通咽喉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处于西南和缅国、暹罗域外接壤的边疆地区,是元朝在西南开疆扩土设立的军事开拓前沿区,征缅行省的设置就是具体体现。所以,爨僰军九处屯田的分布由靠近内地腹心区、交通咽喉区、军事开拓前沿区三部分构成,体现了元朝治理西南的理念——由中心向前沿延伸的层级性军事防御体系。爨僰军屯田事业虽是经济行为,但严密的军事布防意义不容忽视。
(二)军屯形制的典型示范作用
爨僰军九处屯田处在元初云南经济恢复与发展阶段,军民合屯分别由前期民屯、后期军屯构成。云南大理金齿等处宣尉司都元帅府,威楚路、中庆路、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爨僰军屯田之际,都存在“漏籍户”现象,不利于云南行省的赋税征收。其中滇中与大理地区是云南诸王、段氏、贵族和豪户隐占漏籍最多的地区。于是云南行省令“所属州县拘刷漏籍人户开耕”(20)《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7页。,重新编户进行民屯。通过对漏籍户的清理,使“已籍者勿动,新附者籍之”(21)《元史》卷12《世祖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6页。。爨僰军前期民屯的主要目的在于收取赋税,获取对云南财富的积累与占有。
爨僰军民屯为军屯奠定了基础,军屯于两年后才逐步推进。军屯之初主要是为了“以供军储”(22)《元史》卷15《世祖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1页。,如武定路因“云南戍军粮饷不足”开军屯。但“至于云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23)《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58页。。可知,元朝统治者意识到云南不适合大规模屯田,所以有些地区仅军屯于咽喉要道,达到控制一方的目的。另外,爨僰军已基本完成征战任务,陆续接到屯田耕种的新任务。但爨僰军作为协助蒙古军征战西南的重要军事力量,不可能完全放弃军事职能,一旦发生战事,屯田人员又可迅速穿上戎装变成士兵。云南行省清理民屯户籍时,也清定了爨僰军籍,有效地掌握与控制爨僰军的规模。同时爨僰军九处屯田均以“户”为单位,这表明从事军屯的并非军人个体,而是军户携带家属屯田,更具有稳定性。爨僰军屯田初期未出现大规模人户逃匿的现象,除云南行省管理森严之外,以“户”为单位的屯田方式也发挥了稳定军屯的作用。元初爨僰军军民屯田的方式,改变了蒙古军西南边疆“务食于敌”、以战养战的军需供应传统,逐渐向军民屯田“以备军储”的方式转变。爨僰军屯田既妥善安置了军队人员,又解决了军粮供应,实现开源节流,最终达到分而治之。所以,爨僰军军屯形制具有军屯与民屯相结合、寓兵于农、以户为单位的典型示范作用。爨僰军九处屯田是元朝积极经营开发云南的重要体现,为明代诸卫错布于州县,屯田遍列于原野奠定了基础。
三、元代中后期爨僰军由守土军户向普通民众的演变
爨僰军屯田守土为元朝西南边疆的稳固与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但随着元中后期爨僰军军籍的松弛,导致屯田事宜出现诸多问题,由守土军户向普通民众转变的必要条件一旦满足,由兵到民似乎就成为必然。
(一)固定军籍的松弛
元初,云南行省以强制性的方式组织爨僰军屯田事宜,行省“命于所辖州县”进行屯田。(24)《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5页。世祖年间,爨僰军屯田对闲荒田地的开发亦颇有成效,增加了耕地面积,解决了部分无地军户、民户对土地的需求。如威楚路军民屯田“一十五户官给荒田六十双”(25)《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6页。。爨僰军屯田地区曾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王惠任威楚屯田大使时“增粮万石”;延祐年间,乌蒙乌撒屯田“府中储积多如山,陂池种鱼无暵乾,几闻舂硙响林际,仍为蓏蔬流圃间”;曲靖地“野无荒闲,人皆力耕,地富饶”,仁德府“川原平衍,皆可耕稼”(26)李源道:《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刘景毛、文明元等:《新纂云南通志》卷93《金石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陈旅:《题蒙泉吏隐图》,《安雅堂集》卷3,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第407册,第87页;李贤:《明一统志》卷8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3册,第828、835页。。同时,元朝统治者的赋税征收也并非无节制,有时也会适当减免,如1293年“免云南屯田军逋租万石”(27)《元史》卷17《世祖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3页。。爨僰军户的屯田守土为西南边疆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期屯田不均,成为爨僰军军民合屯面临的严重问题。爨僰军与正规军之间、爨僰军各地之间屯田面积差别较大。由表1可知,爨僰军军屯户数共3332户,军田占有耕地面积约61 204亩,按每户4.5人计算,则每人仅有4亩耕地,与正规军每人50亩相比(28)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相差甚远。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屯每户4亩,而其他八处军屯每户都在20亩左右,各地间的屯田亩数悬殊较大,使得农业发展极不平衡,正如“其军站户,富者至有田亩连阡陌,家资累巨万,丁队列什伍;贫者日求生活有储无甔石,田无置锥者”(29)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0册,第443-444页。。元朝后期经营不善,屯田入不敷出,使得屯田最终走向衰败,“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30)《元史》卷19《成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3页。,反映了军户逃亡的现象。就不难理解到1308年,元朝“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驰……可兴者兴,可废者废,各具籍以闻”(31)《元史》卷22《武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05页。。当云南行省强制组织实施屯田逐渐力不从心时,军户的守土固疆之计就面临土崩瓦解。云南屯田事业趋于荒废,爨僰军屯田也走向废弛,预示着爨僰军由军向民转化条件的到来。
(二)由军到民的转变
1291年以后,有关爨僰军的记载不再直接现于史书。爨僰军作为曾经驰骋西南、屯田守土的一支强有力军队,不可能就此销声匿迹。那么,爨僰军的最终历史命运如何?通过对其前期的发展轨迹及明清以来曾经屯戍地的历史遗迹,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实现了由军到民的转变。
首先,爨僰军已经具备由军到民转变的一些条件。国家层面,爨僰军屯田之初,国家给予荒田、种子、耕牛等方面的支持,为爨僰军顺利屯田提供了必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但中后期屯田经营不善,“且无贴户之助,岁久多贫乏不堪”(32)《元史》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17页。,趋于荒废,爨僰军户不再隶属于军籍,从而获得农民的自由身份。群体层面,参与屯田的爨僰军主要由征战西南返回云南者和就地签为爨僰军军户者这两部分构成。返籍的爨僰军征战三十余年,被安置于各屯戍地,迅速归田授业,将其人身关系固定在土地上。元代就地签为爨僰军屯田的情况较为普遍,1290年就有大理金齿等处宣尉司都元帅府以及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鹤庆路。他们的耕地除“官给田”外,多为军民自有且得到部分开垦的“己业田”,说明就地签为爨僰军的屯户被行省就地编户,他们的生活似乎未有大的改变。所以,作为乡兵的爨僰军,能够较快地融入屯戍地,具有由军变民的天然优势。个人层面,爨僰军屯田之初是以户为单位,不存在家人两地异居的情况,稳定性强。因此,爨僰军缺乏返回原籍地的动力,并且大多已经习惯屯戍地的生活,甚至就地签发的爨僰军则由当地居民补充而来,世代为农,屯戍地与居住地从未发生改变,有聚则为军、散则为民的特征。
其次,元代爨僰军曾经的屯戍地给后世留下诸多历史痕迹与地名。明末清初成书的《肇域志》载永昌府“又有爨僰军千户所,亦在城内,后为右千户所,军营俱明初废”(3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8《云南六》,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184页。。由表1可知永昌府为大理金齿等处爨僰军的屯田地之一,元末永昌府爨僰军军营已经荒废,明初彻底废除,原因无非是爨僰军军籍人数严重不足,明廷已无重新整合的必要。显然,除了逃亡之外,大部分爨僰军应当实现了由军到民的转变。另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河西县地图标有“寸白乡”地名(34)董枢修、罗云禧等:乾隆《河西县志》卷1《图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24年,第39-40页。,元代河西县属临安路治地通海管辖,爨僰军曾在此屯田。此“寸白乡”当为元代爨僰军后代的聚居地,由兵变民才保留下来屯田的历史痕迹与地名,一直到今天通海县河西镇仍有“寸村”的地名。
因此,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爨僰军屯田之后就鲜现于史书了。除了部分逃亡之外,大部分爨僰军实现了从屯戍军户到普通民众、从部族军到编户齐民的演变历程,爨僰军不再以一个单独的军事个体活跃于历史舞台,而是演变为普通民众隐蔽于世,毕竟官方对民户干扰相对较少,使得他们有了重建家园的机会。
四、爨僰军在西南边疆治理中的运用效果
通过爨僰军的军事征战与屯田守土,可知爨僰军是维系元朝西南边疆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爨僰军的军事征战与屯田守土,既是元朝统治者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措施,又是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方式。元朝在西南边疆治理中充分发挥了爨僰军的军事优势及社会力量的协调整合能力,开拓与巩固了元朝在西南边疆乃至全国的大一统局面。
(一)军事优势的凸显
元朝对爨僰军在西南边疆治理中的运用是成功的,彰显了爨僰军的军事优势。第一,表现在爨僰军的兵权问题。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将爨僰军的领导权交给降元的大理国旧主段兴智,段氏对爨僰军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如1256年段兴智与信苴福领导爨僰军二万人追随兀良合台征战西南各地。(35)《元史》卷166《信苴日》,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0页。自1270年,云南宗王加强统治,爨僰军的领导权开始发生变化,朝廷任命蒙古人爱鲁“兼管爨僰军”(36)《元史》卷122《爱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12页。,一直持续到1276年云南行省正式建立,爨僰军的领导权再次出现新的变化,调兵权由云南宗王收归云南行省,但仍由段氏直接掌管。如1276年,元朝发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率蒙古军,大理路总管信苴日率爨僰军,征战今保山以西地区,遇有紧急军情,信苴日要向忽都驰报。(37)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刘景毛、文明元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92《金石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224页。1278年,云南行省“签爨僰人一万为军”(38)《元史》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17页。,可知云南行省也掌握着增签爨僰军的权力。1283年,云南行省令脱力世官以蒙古军、爨僰军等攻打子童,脱力世官受兼管爨僰军的爱鲁领导,调兵权仍归云南行省。爨僰军的调兵权经历了大理段氏直接领导、云南宗王命达鲁花赤兼管、云南行省节制三个阶段,元朝统治者可谓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最终将其领导权从大理段氏、云南宗王平稳过渡到云南行省,从而步入正轨,归入云南行省所统辖的军队,强化了行省对爨僰军的管控。第二,元朝统治者充分发挥了爨僰军独特的作战优势。元朝充分掌握了爨僰军的作战特点,“然其人与中原不同,若赴别地出征,必致逃匿,宜令就各所居一方未降处用之”(39)《元史》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17页。,爨僰军的优势为适应征战西南边疆,若派往全国其他区域则容易出现士兵逃亡的现象。爨僰军还有征讨交趾、缅甸的优势。1269年,安南不按时纳贡,张庭珍出使曰:“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其中“云南之兵”即包括爨僰军,与交趾距离较近,有利于快速调兵遣将,距离优势成为元朝劝降交趾的谈判筹码,第二年交趾恢复纳贡。(40)《元史》卷167《张庭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20页。1290年交趾又不纳贡,张立道出使交趾曰:“汝所恃者,山海之险、瘴疠之恶耳。且云南与岭南之人,习俗同而技力等,今发而用之……汝复能抗哉?”(41)《元史》卷167《张立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8页。云南爨僰军与广西俍兵均为西南土著,能够较好地应对瘴疠,且拥有与交趾相似的习俗、技力优势,交趾以示臣服。元朝充分发挥了爨僰军在西南地区能够适应瘴疠,习俗、技力与交趾缅甸等国相近的作战优势,达到了扬长补短的效果。
(二)社会力量的协调整合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协调丽江摩娑蛮、大理段氏总管之间及西南各主要社会力量、地方军之间的关系。第一,元朝统治者先后有选择性地拉拢丽江摩娑蛮、大理总管段氏,并斩杀大理国宰相高氏。忽必烈初入云南,丽江摩娑蛮最先成为蒙古军的向导,一时间摩娑蛮成为忽必烈提拔重用的对象,但摩娑蛮主要生活在丽江地区,且实力相对弱小,无法满足蒙古军统领云南的宏愿。随着征战云南进程的推进,兀良合台“诛其臣高祥,以段兴智主国事”(42)《元史》卷166《信苴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0页。,段氏与高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只因“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43)《元史》卷4《世祖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9页。,高氏拥兵自重,难以节制,段氏实力微弱却仍有较大影响力,于是让其执掌爨僰军。之后,元朝统治者深受其对段氏认知的影响,不断加深对云南各种力量的协调。大理段氏率领爨僰军不断协助蒙古军征战各地,进一步得到元朝的肯定。信苴福死时,元宪宗曾吊唁“受命以来,朝夕惕励,赖尔维勤,用征不庭”(44)倪辂辑,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2页。,仅段氏还被元廷“录功赐金银、衣服、鞍勒、兵器”“复赐金一锭及金织纹衣”“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等。(45)《元史》卷166《信苴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0-3911页。段氏总管与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相始终,同亡于明。只是随着元中后期爨僰军屯田于云南各地,大理段氏逐渐丧失对爨僰军的管理权,这也是元朝对爨僰军的分而治之之策,从而统合了云南各种力量。
第二,元朝组织蒙古军、探马赤军与爨僰军、摩些军、罗罗军、和泥军、徭兵等地方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以支援元朝的内外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云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1256年爨僰军追随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军征战交趾,1259年爨僰军随兀良合台、阿术率领的蒙古军征战西南各地,1277年爨僰军与蒙古军、摩些军出征缅甸,1278年云南行省签发爨僰军、罗罗军、和泥军协作平定未降附者,1284年蒙古军、探马赤军征战滇西等地,1287年爨僰军与蒙古军、农土富民兵协作出兵维摩蛮。蒲蛮军“在澜沧江以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肢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46)《元史》卷210《外夷三》、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57、2517页;李京:《云南志略辑校》,王叔武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6页。。马可波罗评价云南地方军“其人骑马用长骑(镫)之法,与法兰西人同”(47)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A.J.H.Charignon)注,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6页。。总之,元朝统治者不断协调整合西南各种类型的军队及社会力量,使其屡建奇功。
第三,爨僰军与蒙古军、探马赤军、畏兀儿、新附军、汉军、渐丁军、回回军等共同镇戍及屯田于云南各地。镇戍方面,如1278年,云南行省增加渐丁军、爨僰军、落落军(即罗罗军)、和泥军的充军数量,参与镇戍及后续的征战(48)《元史》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17页。;1284年之前云南行省曾派汉军、新附军三千人镇守金齿,当年又新增蒙古军、探马赤军两千人增派到金齿及大小车里,以应对“其地民户刚狠”,爨僰军亦军屯于金齿地(49)《元史》卷99《兵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43页。;1285年,元朝派遣一千户畏兀儿镇戍云南(50)《元史》卷13《世祖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0页。。屯田方面,1286年朝廷“赦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51)《元史》卷14《世祖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8页。,可知蒙古军曾参与云南的屯田之中;1293年汉军一千人建立梁千户翼军屯,第二年分出七百人在今昭通屯田(52)《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7页。,1318年又征调畏兀儿及新附军五千人屯戍于今昭通(53)《元史》卷10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8页。;1303年遣回云南的回回军一万四千人去各处屯田戍防(54)《元史》卷21《成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页。。其中军民合屯并重,是元朝在边疆地区特有的屯田模式,也是元朝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战略性政策,通过民屯人口与军队的协作,改善西南边疆的防卫环境,增加军粮供应。总之,对爨僰军而言,不论是与蒙古军等诸军的共同镇戍还是各种屯田模式,既达到了“控扼蛮夷腹心之地”,戍守一方的目的,也达到了“仰给军食”“以资军饷”的目的,客观上巩固了西南边防,推动了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明代西南边疆大规模的屯田发展提供了经验。但元朝统治者对爨僰军的运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爨僰军的领导权虽时受云南宗王、云南行省节制,但仍由大理段氏直接掌管,使得爨僰军成为段氏与云南行省相抗衡的力量,客观上弱化了元朝的西南边疆治理。再者,应注意爨僰军始终是为元朝及大理段氏服务的,随着元廷对爨僰军的密集征调,虽说自给自足,但“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出界后,许以劫掠,收夺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辈”(55)向达:《蛮书校注》卷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页。,百姓苦不堪言。此外,元世祖年间把爨僰军屯种者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虽然短期内解决了军粮、兵源等问题,但是不能长久维持,最终导致屯田废弛。
综上所述,爨僰军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大蒙古国时期参与征战云南、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平定云南、贵州等地的叛乱及未降附者,辅助元朝确立了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元朝初期参与云南各地的军民合屯,既满足了层级性军事防御体系又具有屯田的典型示范作用;元朝中后期随着固定军籍的松弛,爨僰军最终实现了由守土军户向普通民众的演变。元朝在治理西南边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爨僰军的军事优势与社会力量的协调整合能力。因此,整体而言,元朝对爨僰军的运用是成功的。元代全国的乡兵除了西南的爨僰军之外,还有辽东的乣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及福建的畲军等(56)《元史》卷98《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9页。,活跃于东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参与全国的统一战争、平定叛乱,而屯田事宜,最后鲜见于史书。笔者通过爨僰军最终命运的走向,推断辽东的乣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及福建的畲军可能也经历了从守土军士到普通民众的演变,以此回应学界关于元代全国乡兵的历史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