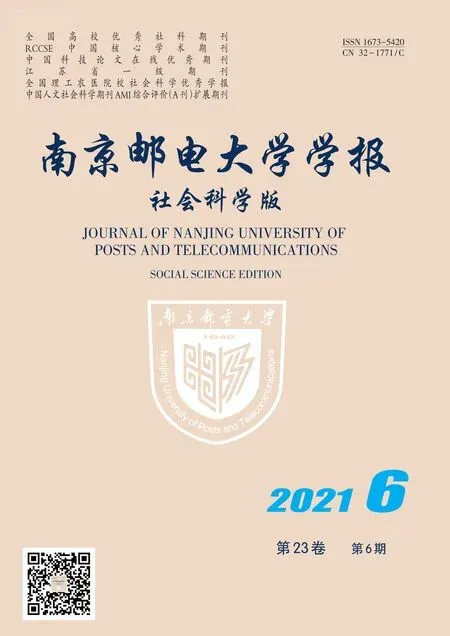“以邮就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述论
黄 鹏,朱奎泽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抗日战争胜利已逾70年,抗战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鲜为学者关注,军事邮递(简称军邮)就是其中之一。军邮是在备战或作战时期,为适应战地环境、便利军事单位和官兵使用、供应作战需要而特予组织的邮递服务[1]431。军邮不仅保障了作战必需的通信联络,还维持了军事区域同后方的联系。它是辅助抗战的重要手段,其功能的发挥对战役保障、战争指挥有直接影响,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学界对军邮的研究整体较为薄弱,有对苏区军邮的研究,有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的考察,有人侧重考察云南、湖南的军邮运作,还有人重点阐释军邮体系与职能。(1)参见苏全有《对民国军邮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95-105;赖晨《论中央苏区的军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0-64;安国基《抗战军邮史》,中国台北:“交通部邮政总局”,1976;袁风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邮简介》,《民国档案》,1990(2):123-125;李曙光《千军万马方寸间——中国军邮研究》,北京:长城出版社,2015;伍佩佩《抗战时期云南军邮述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76-78;申艳艳《国脉所系、滇邮风采——抗战时期云南邮政研究》,云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小用、廖发堂《试析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8-102;范守平《探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军邮》,《中国邮史·湖南》,2011(1):29-35;吴明《从第九战区档案看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湘潭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曾潍嘉、宋祖顺《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军邮体系与职能》,《军事历史》,2015(5):38-46等。此外,对军邮的研究在中国邮政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2)参见晏星《中华邮政发展史》,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叶美兰《中国邮政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等。已有研究与军邮的历史地位及重要影响极不相称,对军邮的组织结构、军邮的业务特征、军邮与抗战之间的关系等鲜有论及。本研究主要关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邮事业,拟运用所发掘的军邮相关档案资料,考察中国近代军邮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业务开展,揭示军邮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丰富抗日战争史和中国邮政史的研究。
一、中国军邮溯源沿革
中国军邮的原始形态与传统驿传制度一脉相承,它是为适应国家军事与行政的需要而设立的,是战争与统治权的产物。中国传统驿政虽无军邮之名,却有军邮之实[2],负有近代军邮的使命[3]31-32。旧式驿政只传公文,不传私信。近代军邮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官兵服务[4]184-185,它不仅是战时的通讯网,也是安定军心,旺盛士气的精神武器[5]。驿站有固定处所,采取接力传递的方式,而近代军邮则随军行动。
中国军邮的设置因袭着传统邮驿的特点,同时借鉴了西方军邮的经验。近代军邮组织创始于德国,因其军邮组织完备与管理方法妥善,战区邮件寄递绝少贻误[6]27-28,为各国树立典范。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不断开办军邮,军行所至,军邮随之[3]35-36。中国近代军邮制度主要仿自欧日,结合中国实际,逐步补充、修订,渐趋完善。
中国近代军邮发轫较晚,始创于民国初期。1913年,蒙疆不靖,是时政府派兵镇压,为便利军讯,“交通部”与“参谋本部”商订《军事邮递章程》,其中包括《军事邮递所办法》及《普通邮局办理邮务办法》,共计36条。1914年2月,事件平定,军队撤回[1]。此次军邮开办虽规模较小、作用甚微,但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军邮的先河,成为中华邮政试办军邮的起点。
中国近代军邮萌芽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当时日军炮轰上海附近各地,大场、真茹、南翔一带邮政业务被迫停顿,上海邮工得到了当局的许可,主动参加服务,组建了“战地邮局”[7]。此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中国被迫抗战的局势,积极充实国防,开始扩建军事交通,筹划军邮,并派遣军事交通考察团赴欧美考查,搜集军邮资料。鉴于军邮的重要性,“交通部”部长俞飞鹏赴欧考查后,遂着手筹备,积极储训人员、购置器材、拟订规章。1934年1月,南京军事交通研究所创立,设置邮政系[3]44,用以培植军邮干部。学员毕业后进入江西星子海会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交通队继续受训。学员在受训期间,工作实习重于理论检讨,因此能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1935年冬,国民政府军队在京杭国道举行为期一周的操练,演习攻防、检讨武力,并借此机会演习军邮,于东西两军配设军邮局所,时称“临时邮局”,负责办理相关部队邮递业务,随军移动,以附近普通邮局为承转局。此次演练向军队宣传了军邮的概念,开启了近代军邮组织先声。1936年春,军事委员会与邮政总局洽商拟订《军邮规则》,并再度进行为期3个月的演习。两广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湘汉一带驻军众多,调动频繁,为试验新规及增加工作人员经验起见,同时为避免发生误会,遂以“临时邮务”名义代替军邮机构,乘机演习。1936年6月,组织临时邮务督察处,负责指挥监督;7月将人员集中至长沙、南昌两地开始工作;8月设临时邮局,随军推进广东,并以每师配一临时邮局为原则;9月中旬事定,“临时邮局”亦告结束[5]。
为更好地筹备与推动军邮工作的开展,国民政府制定多种军邮规章,详细规定了军邮人员的培训、军事机密的保守、军邮所需交通工具的提供、军邮人员的待遇及纪律等,以保障军邮有效运行。1936年春,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第二组主持筹备军邮事宜,拟定多种规章。全面抗战爆发后,后方勤务部先修订《军邮暂行规则》,嗣后增订《军邮视察规程》及《处理公用军事邮件暂行办法》。1938年2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后方勤务会议,颁行《军邮免费汇兑处理办法》。1938年8月底,第二届军邮会议在汉口召开,将原有军邮规章详加修正。第三届军邮会议于1939年10月中旬在重庆召开,决定将“军邮业务局”改称“军邮局”,“军邮业务员”改为“军邮员”,“军邮传递员”改称为“军邮联络员”[8]162,陆续增订规章数种,以适应业务需要。截至1941年年底,军邮规章计有《军邮规程》《军邮联络员处理邮件汇兑办法》《军邮视察规则》《军邮员办事规则》《军邮免费汇兑规则》《空军免费汇款规则》《前方与军事机关及部队官兵集团汇款办法》《军事通讯储蓄规则》《前方各军事机关及部队请发特种代表信箱办法》《军邮档案处理办法》《军邮派出所规则》《军邮联络站规则》《各部队军邮官佐训练办法》《抗战时期前线作战官兵交寄家书优待办法》《各军事机关及部队交通运输工具免费汇款规则》共15种[9]。以上各项规则、办法均是依据《军邮章程》[10]的相关规定订定,对各军邮机构及人员的职责及运行规范详加界定。比如《各部队军邮官佐训练办法》按照《军邮章程》的相关准则,要求各部队军邮官佐为娴习军邮工作,需在各军邮总视察段驻地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每处调训官佐以20~30名为限,其训练科目及时间分配为:邮政概论、军邮概论、邮政法规、军邮法规、部队军邮官佐处理邮件汇兑办法分别为10小时,邮局及军邮局实习22小时[11]。军邮人员受训内容的70%为专业训练,30%为思想训练,目的在于使军邮人员与部队人员一元化[12]。至此,军邮组织已成为作战部队的固定机构。
军邮事务归军事委员会办理,分由“交通部”邮政总局及“后方勤务部”经办及督察,选调原储训军邮人员,分调各战区,配设军邮局所及联络站等随军工作。军邮人员遂参加各军事机关实际工作。之后战局逆转,日军深入,政府西迁,战争持久,战区扩大,军邮设施迭经调整,规模广大,功效卓著。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军邮机构陆续撤销,办理军邮人员则予复员。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管理机构与网络建构
(一)军邮管理机构
军邮管理机构是专门负责管理军邮行政事务,但并不直接处理业务的组织,分为最高管理机构与分支管理机构。前者综管全国军邮事务,后者为各战区军邮管理局,负责推动区域性军邮设施建设。抗战期间,邮政总局主管军邮,各军邮派出所及军邮联络站归属军邮局管理,各军邮局隶属军邮视察分段管理,各分段归军邮总视察段管理,各总段及各军邮收集所归隶属的主管邮区邮政管理局管理。邮政总局指挥各邮区管理局总段,以及总段内各兼办军邮局所、军事邮件直封局和军邮汇兑储备局,军邮业务视情况分归相关军邮总段或视察分段管理,若战事情形特殊,可以越级请示或由临区管辖。在军邮监督方面,各军邮局派出所、联络站受配设部队主官的监督节制,军邮总段、分段及收集所受相关战区司令长官或其次级军事长官的监督节制,全国军邮业务受“军政部”(后为“国防部”)及“后方勤务部”(后为“后方勤务及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督察。当时,在“后方勤务部”下设有军邮督察处,处长由邮政总局视察长兼副处长,全体人员亦由总局视察室人员兼任。1944年冬,该处缩编为一科,全科人员仍由军邮总视察室调用。军邮局实际上属于纯技术业务部门,军方并未对其有主动或实质上的监督与指挥[13]。
(二)军邮网络建构
抗战期间军邮区域极为广阔,且随战事演变不断调整。全面抗战之初,先是按照各战区交通状况及军事需要,指定前方若干邮区办理军邮事务,划分军邮总视察段,简称总段。1937年8月中旬开设10个总段,分为5大干线:一是平绥及同蒲线,设有万全、阳曲2个总视察段,辖北平邮区及山西邮区各一部分,归山西邮政管理局管辖;二是平汉线,设有清苑、石家庄2个总视察段,辖北平邮区的大部分,归山西邮政管理局管辖;三是津浦线,分设沧县、济南、铜山3个总视察段,包括河北、山东及江苏等邮区,沧县、济南段归山东邮政管理局管辖,铜山段归江苏邮政管理局管辖;四是京沪、京杭线,包括上海、江苏及浙江3个邮区辖地,设有吴县及杭县2个总视察段,分属江苏、浙江管理局管辖;五是陇海线,设有郑县总视察段,在河南邮区辖境内,归河南管理局管辖[8]163。其后随军事局势演变,历经调整。万全总段于1937年8月底并入阳曲总段。清苑及石家庄总段分别于1937年9月下旬及10月中旬撤销,合组为开封总段,11月下旬复并入郑县总段。沧县总段于1937年10月下旬并入济南总段。吴县总段因京沪线沦陷,于1937年12月初撤销,所有人员撤入皖南、赣北。1938年1月初,另组赣皖总段,杭县总段在杭州失陷后,改称浙江东段。徐州会战前,济南总段人员因战事撤入豫东,济南总段于1938年改组为豫东总段,郑县总段同时改称豫西总段。阳曲总段人员撤入陕西,1938年3月改组为晋陕总段,并在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另组安徽总段。武汉会战前,安徽总段一部分人员于1938年7月转移至湖北,改组鄂皖总段,湖北长江以南另组鄂南总段。武汉会战后,豫东、鄂东、鄂南总段撤销,于1938年11月底在湘鄂边境开设湘鄂总段。铜山总段人员则绕道上海、香港入粤组建广东总段。豫西总段因并豫东总段于1938年10月中断,称河南总段。1938年12月,于粤西及桂南另组桂粤总段。截至1938年年底,全国共有浙江、河南、晋陕、皖赣、鄂皖、湘鄂、广东、桂粤等8个总视察段。1939年2月,黔川境内开辟黔川总段,主管黔、川两省各公路沿线汽车邮运督遵事宜,又将车巡范围扩至黔桂、湘黔、黔滇、川陕、滇缅各路。因作战部队进入敌人后方鲁、苏、皖、冀等省,游击战规模扩大,遂抽调军邮人员随军深入鲁苏、鄂皖边区,原有鄂皖总段改称湖北总段。至此,全国共有12个军邮总段[9]。
军邮督察处于1939年6月成立,军邮总视察段由原依地名命名改为依数序命名,称为第1至第12 军邮总视察段[14]688-689。其中,第10军邮总视察段因环境特殊无法开展工作,于1942年2月撤销,该总段工作由第11军邮总视察段于1942年12月2日接手。由于越南形势吃紧,1940年11月,在黔、滇两省公路以南地区成立第13军邮总视察段。1942年2月,远征军进入缅甸,随军的军邮局推进至缅甸,归第13总段指挥。1942年5月,军邮局随军进入印度,成立直属驻印军邮总视察段;1944年9月,改升为印缅军邮总视察段,旋改称第20军邮总视察段;1945年9月,该段因远征军回国而撤销[4]196。1942年至抗战胜利各军邮总视察段相关概况详见表1。

表1 邮政总局现曾办军邮人员详情表及各军邮总视察段驻地一览表(1942—1945年)
总之,抗战期间军邮网络逐步构建,覆盖区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苏、浙、皖、赣、豫、陕、晋、冀、绥、闽、鄂、湘、粤、桂、黔、滇、川17个省份及印度、缅甸、越南3个国家。此外,在每个总段内又按驻军及交通情形划分军邮视察分段,以便指挥查视军邮事务,至抗战胜利时共有90段[3]55。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业务开展及特征
(一)军邮业务的开展
军邮业务或工作机构,指直接配设于各级部队或设在交通要卫处理军邮相关业务的机构,可分为收投、承转、收集及辅助机构四类。军邮收投机构设于战地,是最主要的军邮业务机构之一。前方师以上的部队配设军邮局,以便各部队军邮局联络,或供附近及往来当地各军事单位使用。随军行动的,称为行动或随军军邮局;不随军行动的,则称为从地或驻地军邮局。无论随军与非随军,均须依战地情形随时转移其驻地。军邮承转由指定地点的普通邮局负责。军邮收集机构专司往来前、后方军事邮件的收集批转。由于部队调动频繁,流动性较大,为保证机密,军事邮件多不书写番号及地址,只书写代号或信箱号码等,普通邮局无法知悉。军邮收集所负责搜集此项资料,并据以批转前、后方来往邮件,便利递送。军邮辅助机构由相关军事单位自行派遣人员组设,具有代办性质,负责汇收本部队官兵交寄的邮件,转送军邮局,并从军邮局领取寄交本部队官兵的邮件,携回分发。按照国民政府军邮规定,营本部及其以上单位应各指派官佐1人充任军邮联络员,办理汇转工作,也可于其部队内设置军邮联络站,以军邮联络员充任站长[8]162。此外,还设有军邮档案保管处,该处既非指挥机构,亦非执行机构,而仅可称为军邮辅助机构,主要职责是集中保管上述各级军邮机关所有档案,使其不至散失,便于检查[2]181。
(二)军邮的业务特征
国民政府办理军邮的主旨是便利前方作战部队的通讯。军邮是邮政的一支,但其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盖军、普两邮,无须辨明其关系。毋使以军邮涉入普邮,致荒本务,毋使普邮貌袭军邮,有损军邮之实,且毋使军邮勉循普邮,以减军邮效用。”[15]军邮虽然在业务种类、办事手续以及所用规章等方面与普通邮政相同,但是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具有以下特征[16]。
第一,军邮的军事服务性。军邮既传递公用军事文件,也供战士私用,主要目的在于维系将士社会关系,使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与后方社会交往并未完全断绝,以纾其念”;慰劳将士辛勤,“后方赍寄慰劳物品,以至前线,使将士奋兴”[15];传递书报,供给将士精神食粮;汇寄饷款,赡给将士家室。因军邮具有明显的军事服务性,故将士用军邮寄发邮件,可特别享受减费或完全免费的待遇。如抗战部队设有军邮局的,每一官兵每月可领军邮邮票一枚,专门用于寄发平信家书,其价值约等于原应贴付平信邮资的10%。军邮小额汇款免收汇费,大额汇款统一采取低费率,规定同一邮区内收1%,区外收2%,并拟定官兵集团汇款办法,对于兑付军汇予以手续上及期限上的便利。公用军事邮件,仅纳单挂号邮资,而按快递寄递称为“军快”邮件。私用军事邮件,贴用军邮优待邮票,官兵家书加盖“征书”戳记后,即便没有邮路也予设法投递;军人家书经相关部队证实加盖“军人家书”戳记后,可以享受免费航寄。收寄官兵零星个人包裹,以5公斤为限,一律按小包寄递,收费则照小包资例折半优待。
第二,军邮处务与业务的特殊性。一是军邮处务具有军事优先权。军事邮件可比普通邮件提前封发、运递。二是军邮业务在办理时间上具有周期性与集中性。由于军队起、息、操、课均有规定时间,受此影响,军邮业务办理具有周期性。如军队在每月的指定日期发放薪饷,故军邮开放汇票业务一般在部队发饷后的一周以内。又如,为促成官兵养成节俭风气,军邮业务局以通讯方式办理军邮存款。再如,士兵唯有在周日休息时才能写家信,故当日及次日收寄信件比平时要多。三是军邮业务办理内容具有独特性。军邮所办业务按规定与普通邮政所办业务无异,但因战地环境所限,以及为优待官兵起见,军邮未开办保险邮件、储金寿险以及保价保值邮件等业务,主营业务即为办理官兵通信及汇兑事务。
第三,军邮局所的可移动性。军邮局是战时的邮递组织,以军队为服务对象,须“以邮就军”,随军移动,使部队官兵随时随地可以用邮,故军邮业务局设备简单且便于移动。
此外,军邮与普邮在业务上联系密切,因此军邮组织须与普通邮政保持密切的联络。军邮的职能一方面是便利战争区域军事邮件的寄递,另一方面是办理战争区域与后方往来邮件的接转。为保证此两项职能的顺利执行,均须依赖于普通邮政的协助[6]44。
因此,军邮以便利前方作战部队通讯为设立主旨,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在特殊环境中开展工作,具有以邮就军的特性。军邮业务局须适应环境、认清对象、发挥特效,给予部队官兵通讯的便利。
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作用评析
军邮是为满足作战部队的通信需要,维持军事区域内及军事区域与后方各地间的邮递通信联络。此种联络,关系军事甚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强有力地保障抗战胜利。
中国军邮于1937年下半年草创,翌年渐见规模。1940年业务扩展,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军邮即予结束。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计有会战21次,重要战斗1 117次,小战斗38 931次。中国军邮局所配设于所有陆军作战部队,军邮局所必须随军参与所有战斗[17]1。
中国军邮机构于1937年创办,当年支出25 000元,未有收入。自1938至1945年,中国军邮机构整体收入153 030 389元,支出850 176 790元,整体亏损697 146 401元[17]337。但自全面抗战以来随军的军邮处所设立甚多,专为军队服务,功效尤著。历次会战以后,各地军邮总视察段及军邮局所随战局的开展普遍增设,每师部以上单位皆配设军邮局及军邮派出所,每团部以下单位配设军邮联络站,设置军邮机构508所,兼办军邮的邮政局所还有近2 000个[18]307。军邮人员亦呈增长态势,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调派军邮人员共2 052人。在抗战动乱的环境中,1938—1944年军事邮件的平均投寄率在80%以上[13],足以说明军邮对维系战时通讯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军邮是部队官兵与亲人联系的纽带。正所谓“邮电事业为传达消息之主要工具,对于军事及国防方面关系尤为严重”[19]5。抗战时期,战争前线消息传递的灵通对各部队步伐的调整,以及后方与前线的沟通均至关重要。消息稍有隔阂,谣诼繁兴,既影响前方将士士气,也扰乱后方民众人心,对战事进展极为不利。将士在前方作战生死未卜,后方家中“幼子娇妻,倚门悬望”。前方将士一旦不能得悉家中状况,难免朝朝在念,暮暮追思,势必影响其作战勇气与决心[6]25。军邮不仅缩短了家庭与战场的距离,“为军寄命,以旅作家”[12],给予将士精神上莫大的慰藉,而且是在心理上操持战争胜负的枢纽,直接关系战事的成败。
第二,展现了中国军邮人员的热血风采。
所有军邮人员均为邮政事业中的中坚基层干部,且均为三十岁以内的青壮年。他们大部分离妻别子、放弃安适生活,活跃在各战区,投入军邮事业,与前线作战官兵同甘共苦,抱着满腔的抗日热情,置生死于度外。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他们还能帮助军队做一些军事上的布施。军邮业务人员身赴抗战最前线,记录战况消息;利用职务便利,运送政工宣传品;发挥侦探和尖兵的作用,获得军事情报。一般军事谍报员的教育水准较低,由于后方汉奸的充斥,军邮业务员最适宜充任情报任务[20]。与谍报员相比,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丰富的地理常识,对各地风俗较为熟悉,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不易引起后方奸细的注意,便于施行反间谍的工作。战时传递信息较平时风险更大,由于陆路运输遭到战争的破坏,多数邮运均依靠步班邮路完成,广大邮工奔走于前、后方之间,肩挑背负、来往传递、风雨无阻,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任务。据统计,抗战期间交通部门因公伤亡人数人员中,邮政部门伤亡仅次于铁路、公路部门,死亡165人,受伤155人,共伤亡320人[21]109。若没有广大邮政员工的努力工作,军令、政令的畅达便无从谈起,也必将直接影响抗战后方的稳定。
中国近代军邮的筹设,既传承了传统邮驿的特点,又借鉴了德日等国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抗战实际,不断进行调整,日趋完善。通过对军邮发展沿革、管理机制、业务特性、网络建构、传递作用等方面的考察,发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因军而兴、以军筹设、为军服务等以邮就军的特性。不容否认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系统依然存在诸多局限,如国民政府在财力、物力、人力、军队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军邮系统难以高效地适应抗战局势的复杂变化,制约军邮作用的全面施展。但从整体上看,全面抗战期间,军邮除维持军事通信,还努力抢运邮件、组织秘密邮路、沟通与后方游击区间的邮运,各项业务粲然可观,对于便利军讯、鼓励士气、安定民心、协助作战均功不可没,为整个抗战史上的光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