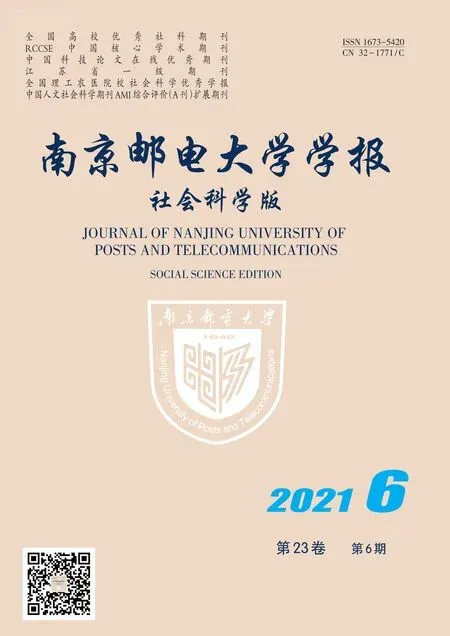中国审美设计的意匠法式研究
陆姗姗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引 言
中国传统造物实践,是形式与功能的合体,这种合体是文与质、美与善的统一,并由此形成了真的磨砺、善的陶冶、美的感化的统一风格。其中,造物“适人设计”是主体对客体的享受,是一种有间隔而非功利的“观照体验”,也是一种由“先验自我”到“生命自我”的审美感受,囊括了感官的愉悦、生理的满足并上升到了审美性设计的高度。该审美性设计是“后实践的”,以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为根基,是适人性设计的最高表达形式。人们通过对这种审美性设计的形式、法则、创造手法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审美程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器物的造物创意。
总体而言,皇家造物常常折射出权势阶层的文化取向、价值体认、审美旨趣,而民间生活器物、生产用具,则透溢出社会弱势阶层的价值尺度、审美趣味。由于不同阶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权益分配清晰明确,官作与民具的使用范围、流通领域、传扬渠道差异显著。而出自文化阶层审美意识的设计意匠法式,则充当了官作与民具的中介。
通常,器物的设计思想、创意尺度,除特殊的御制、官用形式外,大都属于官民不分的通例设计,基本不触及等级观念和审美情状。由于在对器物的占有方式、审美方式以及涉及审美内容的形态、择材、工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官作与民具显示出不同的设计特征。官作造物设计与民用器物设计皆属于中国传统造物设计范畴,代表了中国设计传统的主流,二者的审美创造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审美情趣。
一、传统官式设计的审美特性与造物缺失
官作的设计传统是强力占用社会大量资源、物质材料、工匠资本的产物,其典雅纯正、合乎规范的造物风格与设计行为,是当时社会雅文化与科技水准的体现[1]。官式造物从器型看,具有讲究礼制、造型谨严、设色精致等优点,外观上拥有民具无法比拟的优势,器物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长久的稳定;从制作工艺上看,其科技含量高、工序复杂,能在图像学层面体现出制作的精良和缜密。
官作造物虽已成为中国设计史上的“典范式样”,但多半官作设计作品的传承时效较短,品类样款较少,传播地域也相对窄狭(除了硬木作家具与皇家服式款样)。这种不足是令人深省的,除了皇权政治与经济原因外,最核心的是其对资源的侵占、较少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上的狭隘。材料罕见、工艺复杂、造型奇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优秀技艺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造物具有标准法式,但官作造物显然难以浸透传统造物体系。
设计制造标准要以公平公正的造物交换体系为前提。器物如果不被大众普遍使用和流通,就违背了其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属性,成为了特种商品,无法展现其大众性、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官作器物明显存在这一问题。从造物的使用、认知到审美,官具不承担流通的职能与任务,这大大束缚了工匠的创新能力和创作自由,导致其无法实现新的艺术作品创造[2]。这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官作器物的设计创意与表现,使其难以在中国设计传统中立足,而那些经典案例的意匠法式,无一例外,都兼具传承与普及价值。
从设计学来看,官作造物对后世器物的造型装饰、功能形态、工艺延展的影响极为有限,它主要是民具造物模仿的对象,并未被列入创新之列。对民间及文人的生产与生活影响微乎其微。
通过以上几点,能够发现官作器物未能成为中国设计传统体系的“意匠法式”的原因。因此,我们未将其加入中国传统设计经典案例之列。
二、“意象论”之文人造物取度
审美意象是在直接审美感兴中产生的,是对审美自然的真实反映。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精神是“意象说”[3]。从魏晋士子到宋代文人介入绘画,由文人创造的“意象论”不仅创造了独有的审美意匠体例,也推翻了传统以视觉感知为主的鉴赏模式。此类艺术作品的典型特点是真性情和真意气的释放、生命意识的觉醒及对生命安顿方式的探寻[4]。这一特点对中国画的形成、繁荣、传承起了重要作用。文人们倡导的书画理论与实践,影响了国人造物设计的意匠法式,被广泛应用到装饰题材之中,对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忠于自然真实进行摹写还是遵从内心进行创造性表现,一直是“意象论”的分歧所在。魏晋时期文人生命意识觉醒,再加上战乱频繁、官场失意,导致他们纷纷遁世入隐,以饮酒吟诗、喝茶品茗、著书立说、雅集山水的方式逃避现实,借此描绘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此时,文人士子将绘画品评拔高到具有传道意义的程度,“意象论”则确立了象征手法和写意传达的途径,是中国古代视觉艺术中最具影响、最有承传价值的“意匠法式”。
宗炳的《画山水序》与谢赫“六法”在传统绘画的理论技巧、生命反思、意义寄托上高度一致。在宋代审美风尚发生转换,美学境界上由对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对逸品、韵味的追寻,对美学本体论的建构、审美社会功能的强化以及人生境界的推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的瓷器色泽温润、典雅精致、简远舒朗,达到了超逸之境。同时,明式家具追求人与自然的合一,布局上追求“天圆地方”(特别是圈椅,上圆下方)的形式美感,充分显现出文人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风范,使居住场所与众不同、超凡脱俗。可以说,中国书画独创的“意匠法式”,对中国传统造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适人性设计而言,“意象论”的意匠法式建构出器物造美手法三大定式:借形寓意的比兴暗喻手法,合形入意的象征表意手法,化形立意的创意表现手法[1]。总之,先秦至宋“意象论”的核心范畴成为“韵”的法式意匠,其对中国传统造物的审美创意与表现,是所有艺术理论与审美观念都无法企及的,并且影响范围也超出了官作、民具体系,成为中国社会审美的最高范式。因此,研究“意象论” 法式意匠可以更好地探寻中国传统设计中关于“形式美”的法则与取度。
三、民具设计是中国传统设计审美意匠的主体
民具的创意表现与官作造物、文人造物相比较,具有更加多元化的审美倾向。一方面它深受两者审美情趣的浸染;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自身的审美趣味。尤其是后者,不仅造就了影响中国传统审美性设计的主体形式,而且构建出具有承传性、统合性、普惠性的意匠法式。
民具设计在资源占有、工艺技术、文化内涵上,与官具、文人设计相比优势全无。然而在实用功能上,民具的优势突出。其通常选择性价比高的材料、工艺、色彩,以材质简易、造型简洁、装饰简单、色彩朴素的实用原则为主导,与社会主体人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最易达成传统造物流传远与普及广的目标。
民具设计意匠法式中的自创部分,往往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利益辨别、意愿取度、价值评判的真实反映。如,“夫妻恩爱”“多子多福”等吉祥图式与官作造物虽有相通之处,但在选材范围、色彩抉择、工艺加工、造型式样、创意设计上却大相径庭。
民具设计具有朴素自然、情态生动、灵活多变的艺术旨趣,不拘一格、变化巧妙、奔放自由的构成方法,同时还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的表现风格。
一般而言,民具审美的“俗”是设计的源泉,官作审美的“雅”是设计的参照与取向。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及民具审美设计的意匠法式,往往指的是制作优良的民间器物,那种粗鄙浅薄、庸常低次的审美趣味一般创造出的都是柔媚甜腻、平庸浅俗之作[5]。优秀的民间造物是民具审美设计 “意匠法式”的重要部分,其构成了中国传统设计审美意匠的主体。
民具造物,小至油灯糖人,大至牛车水碓,处处彰显出“贵在实用、重在内容、文质统一”的中国式器物造型的审美趣味。民具从设计到使用皆在民间范围,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民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更能传达出造物者的个性。不拘一格、奔放自由的构图方式,在民具器物平面的纹饰构图与立体器型的结构中充分彰显。
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的表现风格传达出民间器物审美多元的应用之势,民具对不同材料的使用以及极强的应变能力,造就了无穷尽的崭新之物,草鞋箩筐、桥墩斗拱……每一种器物的样式都传播地域极广、流传时间极长、影响极深,成为特定时空范围的“意匠法式”。民具的意匠法式生命力极强,随着各种条件变动不断衍生出新的形式与内容,传达出民具设计在装饰手法、工艺技术、造型表现等环节中的独特理念,进而有利于其设计理念的创新与承传。
四、意匠法式的建构六法
(一)官具“金子塔”式价值准则
官作创意造物的评判主要遵循功能完备、价值巨大、审美怡情的标准,目的是维系贵族集团的价值取向。“官作设计意匠”的器物设计,受益对象是少数贵族,他们拥有社会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工匠资源,在技艺、审美上也拥有绝对话语权。同一阶级内部也因等级的差异,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评价机制。在古代,按品级对中国官员使用物品的大小、数量、设色等进行不同的设计,在使用上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官本位”金子塔式价值标准的“用器制度”,很明显被继承了下来。
(二)官具设计“取势”构成方式
不管是平面还是立体的设计创造,官具造物的构图、纹饰、造型、结构都显现出一个“势”字,并以围棋布局、书画留白的布势格局为主,这也成为官作设计“取势”的重要构成方式。围棋布局,大势若立,龙盘虎卧,自有满盘皆活、大气磅礴之势。书画则或傍山取势,小景点睛,外取叠云之雾,幽深于山峦沟壑,自有青玄高远、灵空飘逸之势。
“取势”之风传及造器,自然使民间画师无法企及,这是官作设计创意的意匠法式的核心所在。如北宋汝窑的双贯耳瓶,便是此类设计的佳作:器物土质细润,坯体如胴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直径较长,腹部扁圆,颈部两侧对称贴有竖直的管状贯耳,均匀协调,光泽沉稳,油润自然,烘托出庙堂正气,使整个器物巧夺天工、妙趣天成。
官式设计的“取势”构成在元青花和明清家具造型立意上尤为显著。如明式家具的官帽椅、扶手圈椅、宽大案几等,造型凛然大气,曲直有度,气势如虹。这种“取势”就是堂皇正气、超凡脱俗、高古雅逸的趣味之体现。同时,这类官作设计的“取势”构成方式,是中国传统设计少有的亮点,在当代设计中,尤需领略传承其中的造美之“势”。
(三)官式设计文人式造型手法
文人作为文化生产与传承的主体,是雅文化的主要代表。文人造物手法常常被官式设计模仿,并大量体现在官作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中,同时,也出现在大量官员使用的日常器物中。
官作的器物,器型和纹饰讲究威严端庄,寓意吉祥。设计题材展现的是“皇家势气”,希冀的是“海天祥瑞”;上乘天命、下扶天下,绘的是“天下为公”,求的是“昌隆鸿运”。即便衙役小吏、寒窗白衣,也希望能够宦途得意、百福具臻,因此,他们使用的器物常常与贵族阶层接近,用具常常表意“玉洁冰清”“高风亮节”。这都与民间造物模式不同,显示出使用者的特殊身份与地位。
科举入仕的文人,他们的地位虽然得到提升,但仍需要依靠整个阶层共同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通过与世袭贵族区分,显明品德高古、闲情隐士的风度;通过与白衣寒士保持距离,彰显洒脱自由、心向天下的士族情怀。而不论是展示文化修养还是自我抒情,他们在器物装饰、造型等方面都表现出忧郁的,却又象征“善”的观念。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具有审美性的自由生活,政治意义上不乏脱离世俗的洒脱,其中壶中天地的闲隐、乐天安命、悠游闲适,明显有“高尚其事”的心态。
这种玄涩的文人式造型、描绘手法,构建出宋代至近代中国官式文人造型意匠法式。具体而言就是器物素雅的纹饰与设色简洁的装饰风格,轻盈洒脱的器型与洁净的审美感受。这种文人的意匠法式,影响了800余年的官作器物审美设计。很多著名的古代设计案例,都是这类意匠法式的代表作,如北宋官窑、南宋素髹漆器、明式家具、清代镶嵌屏风等。
(四)民具评判的价值标准
对造物审美价值的总体评价往往体现于人对自然的有目的的改造。这通常体现为“贵在实用、重在内容、文质统一”的民具评判标准。实用性功能是中国造物的本质所在,故谓之为“根”;适人性是其内容所在,故谓之为“本”;内容与外在形式统一、经久耐用、功能良好,故谓之为“果”。这几个方面相互牵引、浑然统一,形成了器物的完满形象。可以说,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就是无可置疑的好器物。
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与当代的“实用至上”的工具性价值不同,其更加强调朴素的实际功用,并统辖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如操持的便捷、适人性和延续性等,这是民具造物的重要取向。效能,专指器物的“以物克物”的实用功能。好用,指的是器物的适人性功能(省力顺心、养眼简易)。耐用,指的是器物质量的牢靠。民具设计和使用常常表现为造物者、使用者、拥有者为同一人,并且成本便宜、省工省时、性价比高,其中“称心遂意”是其审美造物中最看重的,但往往也制约了创造上的自由发挥。
总体来看,民具设计对器物中“华而不实”“名不副实”“徒负虚名”的取向一般弃而不用,这也是其造物的重要原则。
(五)民间设计“饱满式”的构图设计
多数民间美术和工艺制作式样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饱满式”构图,由此显示出造型与构图的“多”与色彩的艳俗。从视觉上看,只要是器物表面的区域,就堆砌并充斥着民间图式,而这种构成法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饱满式”构图。
以民间青花为例,文人器物的青花往往是主物的摹写与大面积虚空,由此达到“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的效果。而民具的设计往往是图案布满瓶身,给人以团结喜庆、繁花锦簇的感觉。小到玩具,大到农具,均表现出共有的法式。“饱满式”和“团簇形”共同构建了民间设计饱和式构图方法,成为中国传统设计中最重要的意匠法式之一,也成为民间传统工艺在审美性设计方面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民间图式的“饱满式”,通常有“中心开花,四周填空”“折枝盘转,满幅贯通”“星斗满天,花草满园”三种方式,具有饱满大气、敦实生动的特征,与官作纹饰的拘泥扭捏、孱弱病态完全不同。
民具造型的“团簇形”通常有“构架围空,构件填虚”“坨捏塑形,轮廓外溢”两种构成方式,透溢出结构严谨、妙趣横生的特征,与官具的死板僵直、气息奄奄形成对立。
(六) 民间设计的“自由度”手法
在民间器物造型与彩绘的艺术表达中,自然的工艺、天然的材料、恬淡的心境是其审美创作的主要动力。可以说,民间器物的美是“被救助的美”[6],工匠与画师大都没有专业基础,一般就是对自然进行即兴式描绘,创作天马行空,表现出质朴的审美风格。
民间造物的创意之法,其“自由度”是官式、文人无法拥有的。民间艺人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创作原料也取之自然,整个制作散发出自由的气息,给人带来生理的舒适与心理的愉悦。正因为如此,民具成为超越时空局限的“写意创作”。
同时,民间设色打破了专业色彩法则,经常运用互补色并突破色彩禁忌,对中国传统官作设色、文人设色及西洋油画等标准设色法则进行拆卸性的对抗,并因此形成了民间艺术特有的设色模式。其设色极具视觉张力,显示出健康之美、朴素之美。如蓝印花布、泥塑、风筝等经常用色无畏,制造出审美奇观。
结 语
中国古代造物的演变,总体是以民具造物为牵引,散发出朴素之美和乡土旨趣,为当代设计奠定了创作基础,并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补充。官作与文人造物虽雅致标准、完满圆全,却并未成为中国造物的主流,其造型装饰、功能形态、工艺传承的不足也非常突出。在探究古代审美意匠法式中,值得重视民具设计的主导作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