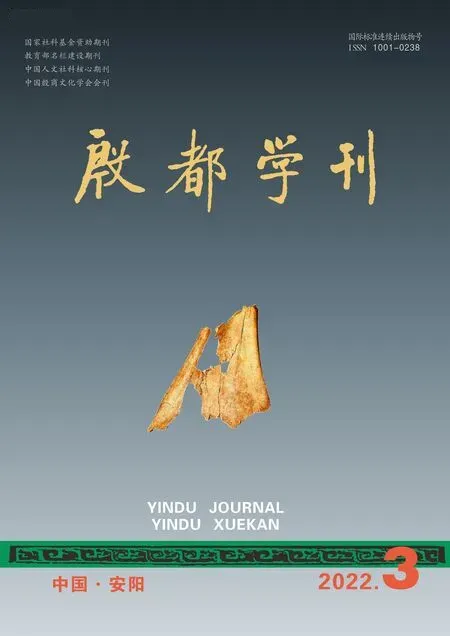释迦牟尼时代的国家与宗教礼仪
刘欣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正值北印度的数十个农业部落世系向地域性国家转换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里的早期国家和世界各地一样,需要建立为巩固国家机器而设置的宗教礼仪,以便开疆扩土,征服周边国家。同时,国家的形成意味着原有社会体系的解体,因此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铁质农具的普遍使用和水稻农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促使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难免给社会带来急剧的变化。农业开发向森林沼泽夺取土地,迫使失去生计的猎人和渔民加入劳动力集约的稻作农业经济,成为最底层的劳动者。同时对自己状况不满的村民、野人受城市生活的诱惑进城找出路,加入各种新生行业。这时印度的西北门户,亦即位于今巴基斯坦的呾叉始罗城(Taxila)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是来自西亚、中亚、南亚的有志之士荟萃之所,为政界、商界、医药、科学等行业造就大量人才。成就学业后,学子回到恒河中下游的大城市,成为新生的国家机器和城市经济的栋梁。城市中文字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有文化的思想家对婆罗门教的宇宙观和宗教礼仪提出质疑甚至反对。婆罗门知识分子也致力于对宗教思想和礼仪的改革,企图力挽狂澜,在新的国家体制中保住婆罗门教的主流地位。
一、生机勃勃的新生国家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恒河流域的城市和国家是工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铁矿开采和冶铁业造成铁质工具和农具的普及使用,因而促使恒河中下游平原沼泽地的开发。稻作农业的普及又带来大量的剩余财富和行业进一步分工。一个个商品交换中心在河流、道路的交口出现,城市于是崛起。但是这个时期的城市不是围绕宫殿、神庙而有计划地建设,因此既没有辉煌的建筑群也没有很好的市政规划。商人和手工业行会各自划分地盘,分别管理自己的成员并组织贸易和生产。各个城市都有钱庄行会发行本地的货币。各城的货币都是银质的长方形银版,形状不规则,但是重量有本城钱庄打上的印记来担保,史称“打印钱”。各个城市的打印钱的重量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互换率,商人带着本城的银币到别的城市做生意,可以到当地的钱庄换成当地的银币。恒河中下游的各个城市和地处西北的呾叉始罗组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和贸易体系。呾叉始罗是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枢纽,印度城市通过那里进口马、葡萄酒,出口棉织品、铜器、宝石等等。城市一方面热热闹闹,一方面乱糟糟。同时,城市是财富聚集的地方,也是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原有的世系社会的上层集团即刹帝利已经分裂成很多支系氏族集团分散在各地。他们的政权机构由氏族成员集体组成,称为Gana Sangha,意为“众人的集合体”。释迦牟尼出生的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释迦族就是这样一个氏族共和国。这种氏族共和国的政体有本族的成年男子构成,规模不是很大。释迦共和国的成员大概不超过一千人。(1)早期巴利文佛经多次用500位罗耆开会决定国家大事。500人显然是个套话,但是也能反映政体的大致规模。同时在恒河平原有数个这样的氏族集合体组成了强大的跋耆共和国联盟(Vrijji Confederacy),参政者达数千人或至上万人,(2)在吠舍哩城举行的大会有7707罗耆,当然也是套话。可以估计少于一万成年男性公民。在繁华的吠舍厘(Vasali)建立集会和商议国家大事的中心,也就是联盟的都城。这种集团统治的国家里产生了释迦牟尼和大雄这样的思想家,也就倾向于依靠这些新生的意识形态来维护新生国家政体的合法性。
同时,吠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两大世系家族即太阳系和月亮系已经分崩离析,而不属于这些吠陀贵族的乱世英雄代之以起,以强权政治和军事征服起家建立君主国。以太阳系的家族史为主题材的史诗《罗摩衍那》的中心脉络是憍萨罗国(Koshala)的国王十车王的长子罗摩被流放,历经险情,终于回到都城阿约底。罗摩的继位,象征着以长子继承制为国家权力传承原则的君主制的胜利。但是,到了佛所生活的年代,虽然憍萨罗国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国,憍萨罗国的王室早已不是太阳系的君主。同时,释迦族倒自称是太阳系的后代,但是释迦族的国家并不是君主制。憍萨罗国王波斯匿为了提高王室的社会等级,向释迦族求婚。也就是说,远古的太阳族虽然向君主制演化,但是并没有产生统治一个地域国家的真正的王统,而是分解为释迦族这样的小政体。月亮族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更清楚地表现远古世系传承制的分解。摩诃婆罗多大战是在吠陀时期月亮系的两个支系中展开, 即以般都五子为一方,俱卢百子为另一方为争夺水草牧地而发生的战争。地点是在恒河上游和雅木纳河之间。般都五子被迫出走流放,回来后双方各自纠集盟军,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结果是俱卢百子全体阵亡。取得胜利的般都五子,连同他们的猎犬,一同登上喜马拉雅山,升到天堂。也就是说,月亮族还没有来得及向王权发展,没有建立长子继承制,就已经瓦解。到了佛的时代,俱卢族仍盘踞在河间地,是一个刹帝利贵族的寡头集团(Gana-sangha) 建立的政体,但远不如恒河中下游的跋耆共和国强大。印度古代两大史诗的故事情节成型,就是两大世系时代的终结。
在吠陀时期与世系家族首领相互依存的婆罗门祭司失去了原有的靠山和稳定的生计,必须在新的动荡的社会内外求发展、找出路。释迦和跋耆这样的刹帝利共和或寡头政体造就了佛和大雄这样的思想家,有了新的意识形态,不需要婆罗门祭祀为他们求天命。同时新生的君主国靠强权起家,需要的就是在臣民眼中的合法性。婆罗门的祭祀仪式也就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为巩固新兴的王权而服务。但是,吠陀时期的宗教仪式是在印度河上游和雅木纳河之间的平原形成的。那时的吠陀社会主要从事牧业,以世系为组织原则的部落之间经常为水草牧地的分配发生纠纷,造成战争与迁徙。祭祀的目的主要是祈求我方战争的胜利,方式是宰杀牛羊、燃烧黄油,取悦神的欢心,得到神的支持。神还喜欢一种称为“索麻”的兴奋剂,要在祭坛上反复浇这种饮料。祭司和主祭人当然也要喝这种饮料以求与神的结合的精神境界。由于战争各方祭祀的是同一群神灵,难免竞相宰杀更多的牺牲,乞求神灵支持已方而不是敌方。这样一来祭祀的规模越来越大,祭司部落的人们不可能吃掉所有的肉食,实际上很多的牛羊就这样烧掉了。
吠陀时期的超自然神灵分两大类:狄瓦(Deva) 和阿修罗 (Ashura),这两类神灵在印欧语系社会进入南亚之前产生。公元前二千纪在中亚草原的印欧语系游牧部落祭祀各种天神。其中狄瓦类天神英武好战,阿修罗纯净和平。崇拜阿修罗或称阿胡罗(Ahura)为最高神明的一派形成祆教,迁入伊朗高原,成为波斯文化的传统宗教。而进入南亚的一派以崇拜狄瓦天神为主,在战神因陀罗的旗帜下驾驶双轮马车进入南亚。在南亚西北地区形成的吠陀宗教祭祀礼仪并不排除阿修罗是天神,经常把阿修罗与各位天神相提并论。(3)例如吠陀颂诗编号Part 1, VIII 20.17: divāh āsurasya vedhāsah, 上天的仆人。Vedic Hymns, translated by Max Müler, vol. 32 of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1,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9. p. 401, 405.特别是在祭祀火神阿格尼(Agni)的时候,阿修罗经常与阿格尼同时出现在颂诗中,阿修罗以掌握幻术著称。“阿修罗术”成为幻术或奇迹的代词。(4)例如吠陀颂诗编号 Part 2, III 3.4, p. 316, 320; V 10. 2, p. 389, 390. Vedic Hymns, translated by Hermann Oldenberg, vol. 46 of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7,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9.但是到了农业发展、城市崛起的时代,这一套祭祀规则已经行不通了。首先牧场变成农田,不可能蓄养大量牲畜。少量的牲畜有新的用途,马要拉车,牛要耕地,社会不可能提供大量的祭祀牺牲。新兴的国家需要税收来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并保护生产的发展。同时,新的社会统治集团虽然不属于吠陀时期的望族,但仍然是印欧语系文化圈的世系,仍然向往吠陀时期贵族集团的威望,愿意请婆罗门通过祭祀把这种古老的威望带到他们的王冠上。他们统治下的臣民,却不尽是印欧语系文化的人口。各地的土著各有自己的宗教和神明,用各自的方言与神交流。如何治理这些化外的人口,使他们不仅向国家纳税,而且对统治集团的文化心悦诚服,是婆罗门祭祀要帮助统治集团解决的难题。
二、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
建立新型国家的主角是公元前二千纪中期进入的印欧语系部落衍生出来的氏族。它们已经以世系组织的方式吸收很多当地的非印欧语系社会。世系血统是社会组织的理论原则,实际的社会文化的扩展往往是通过婚姻联盟来完成的。这里的发展主题是印欧语系文化内部的王权的长子继承制。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吠陀社会的主要氏族与非印欧语系的氏族结盟,加强本族的力量。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摩诃婆罗多》史诗的主角一方,班都五子与雅达瓦族结盟,使雅达瓦族足智多谋的克里希纳加盟成为英雄阿周那的战车驭手,实际上就是他的军师。克里希纳帮助阿周那劫持自己的妹妹,实际上是用联姻巩固两族的联盟。雅达瓦族原本不是吠陀社会的成员,而是在德干高原西北部一带游猎的部落。他们的代表物质文化是“黑红陶”,不同于北方平原的吠陀社会的彩绘灰陶的物质文化。克里希纳的肤色很黑,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黑色”。也就是说,当时游唱摩诃婆罗多大战故事的诗人也指出克里希纳与吠陀世系的俱卢族在外貌上的不同。然而这个外来的肤色黧黑的克里希纳不仅成为班都一方的军师和道德上的中流砥柱,而且在中古时期变成印度教的大神。《罗摩衍那》史诗的情节也说明吠陀社会与化外民族交往结合的过程。罗摩在流放中为了与罗刹族的战争,与猴子部落结盟。这里罗刹并不是鬼类,猴子也并不是猴子,都是化外集团。这些新加入吠陀世系的首领们学会说吠陀梵语,遵照吠陀社会的祭祀礼仪,也就进入社会主流。
在农业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代,婆罗门教通过祭祀建立的种姓体系是吸收化外民族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机制。吠陀社会的祭祀仪式,首先把本世系的人分为两大类。“罗耆尼亚”意为“辉煌者”,武艺高强,保护本部落的牲畜群,抢夺别人的牛羊。这些人在婆罗门的支持下演变成社会的统治集团,称为“刹帝利”。普通社会成员是大多数,是社会的生产者,称为“吠舍”。婆罗门是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与神沟通者,人数不多。到了这个时期也有些人认识到吠陀祭祀对社会无益,宁愿遁入山林,带领学生,过修行的生活。前面已经提到,刹帝利王族体系在佛的时代已经分崩离析,家族成为地主,与吠舍家族一样从事农业经济。但是刹帝利和吠舍并没有放弃世系称号。农业劳动,特别是稻作农业,是很艰苦的劳动,这些农业家族必须增加劳动人手。“首陀罗”种姓于是产生了。“首陀罗”意为“小人物”,是在家族世系以外的人。在种姓原则上,首陀罗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都源于一个始祖。婆罗门出于始祖的嘴,刹帝利出于他的臂,吠舍来自腿,首陀罗来自脚。这样四个种姓构成一个封闭的等级制。但是在宗教礼仪上,首陀罗与前三者的待遇完全不同。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的男孩子长成少年时要接受成年仪式,成为种姓的正式成员。但是首陀罗的子弟没有这个仪式,也就是说他们与世系没有关系。他们有可能是吠陀社会的落魄者,失去家族关系。也有可能是化外民族加入主流社会来谋生的个体或群体。在稻作农业经济里,少数首陀罗是奴隶,多数是雇工和集体租种土地的佃农。首陀罗农民有自己的家族,也有自己的神明,就是说,在主流社会内有自己的天地。还有些来自没有家族背景的人到新兴的城市里寻找机会。有些有才能有机遇的人成为医生、书记,或加入手工业、商业行会,也有些运气不好的人只能从事清扫一类低级劳动,形成种性体系之外的贱民社会。
与此同时,很多非印欧语系的社会长期生活在主流社会以外。南亚地区地形复杂,生态多样,新兴的地域国家位于开垦出来的沿河流的平原和平原与山林交界的要地。农业是主要的资源,但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也需要从周围的山林获得铜矿、铁矿、木材、石材、燃料,以及各种植物、动物产品。渔人、猎人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城里人和村里人,到矿上干活,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往往受到鄙视。他们崇拜自己的神灵,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有机会的时候,也劫持商队、抢劫民户。那些在城里乡下谋生的首陀罗和贱民也有不堪压迫剥削,逃离文明社会,重操打鱼狩猎、打家劫舍的旧业。从统治集团到市民、农民离不开这些野人的服务,对他们的骚扰也是又恨又怕,把他们看作非人类的造物,说的是无法理解的语言,崇拜的是鬼类的神灵。众多的化外社会各有名称,当时的南亚文明社会把他们基本分为三大类,一是“夜叉”(Yakha),一是“蛇龙”(Naga),一是“罗刹”(Rakhsa)。夜叉是生活在山林水泽里的人群,与文明社会相对友好,交往很多。蛇龙部落以眼镜蛇为图腾,首领和偶像都戴由五条眼镜蛇头组成的王冠。他们也在文明社会周围活动。罗刹的名声差一些,活动的地区离文明社会较远。罗摩这样的王子被流放到深山老林,才与罗刹国交锋。这个罗刹国是与吠陀社会演变而来的文明社会文化迥异的政体。由于交往极少,没有了解,双方敌意很深。罗刹社会的人偶尔出现在文明社会里,但往往被视为鬼类,不足挂齿。总体来说,吠陀社会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既有合作、融合,也有冲突与战争。对于新生的国家政体来说,如何在宗教礼仪上确定与他们的关系,以决定对付他们的政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正是因为主流农业、工商业社会与山林水泽的人民交往,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一直很密切。在国家兴起的时代,遁入山林的婆罗门在森林深处建寒舍,带领弟子研讨哲理,与飞禽走兽共处,对自然界的活动观察仔细,悟出一切生灵都渡过转世轮回的生命周转圈的心得。转世轮回的观念最初在《奥义书》中讨论,在佛的时代除了彻底唯物主义派外,各个新生教派都把它当作宇宙万物运转的基本规则。印度的梵语宗教文学充满以动物为题材的故事情节。罗摩在流放中,在与罗刹国战争时,不仅与猴子王国交往,还与森林里的各种动物交谈、交往。在这个宇宙中,人和动物没有清楚的界线。在礼乐具备、谈吐优雅的文明社会之外,生活着各种可以言喻或不可言喻的异族,还有各种飞禽走兽,说出的话人也不懂。化外社会和动物界的生灵与人的亲疏不同,但是如果相信人和一切生灵都在转世轮回的生命圈里的话,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甚至文明人的生命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没有本质区别。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时,悟出这个道理,并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创造了佛教的宇宙观,亦即印度产生的所有宗教派别的宇宙观。在佛的世界里,各种不同语言、发式、装束的化外社会,各种进入文明社会和在社会周围活动的生灵——象、虎、鹿、猴、鸟——为主流社会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这个宇宙观的指导下,释迦牟尼向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传播他的思想,生活在山林水泽的人民觉得佛的教导很有道理,即在一个贫富急剧分化的社会里,人生的苦难都来自欲望,因为欲望使得人们造下孽,于是托生到低级的造物,做牛做马,过着更为悲惨的生活。他们生活周围的动物世界和他们精神世界的各种神灵给他们丰富的题材来发挥这种思想。在佛涅般后的几百年里,出现了一大批“佛本生故事”(Jatakas),讲的是释迦牟尼出生在今生之前,曾托生为各种人物和动物,做了很多积功德的事迹。现存的五百多个佛本生故事中,至少一半以上是以动物为题材的。在这些故事里,佛的前生曾经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猴王,雄伟奇特的六牙白象。很多故事的动物角色不是佛,但是很有灵性,能说会道,和人没有区别。我们现在看来是童话、神话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他们所熟悉的世界里曾经发生、仍然在发生的事情。人们听不懂鸟语、兽鸣,但也听不懂其他部族的语言,所以很可以想象鸟有鸟语,兽有兽语,只是与自己社会的语言不同,大家都是这个大千世界的生灵。
从印欧语系文化沿袭的宇宙观带来的是印欧大草原的世界,这时与热带雨林的世界相遇。始建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公元前二世纪初)的桑奇佛塔和巽迦王朝(公元前一世纪初)的巴鲁特佛塔的石雕艺术和铭文展现了以佛本生故事为题材的这个大千世界。早期佛教不仅反对杀生祭祀,也没有什么礼仪。佛和他的大弟子云游四方,口头传播思想。佛圆寂后,弟子信徒建佛塔,保存他的遗骨,即“舍利”。之后佛的著名弟子的舍利也都建塔保存。直到公元前后,佛教的僧团都没有固定的寺院资产。佛塔于是成为僧团集合、礼拜的中心。桑奇佛塔是礼拜佛教的阿育王支持所建,不仅有阿育王的饬令为证,而且有展现阿育王礼佛的画面。巴鲁特佛塔建造时,巽迦王朝对佛教不热心,只有王室的女眷和王子有捐赠。因此,巴鲁特佛塔更能体现当地人民和途经商人等的民间信徒的思想。佛塔周围是石柱雕成的门廊和围栏,铺满石雕艺术,并刻有捐赠者的名字。两处佛教圣地都没有佛像。早期佛教不把佛当成神,而是进入涅般境界的导师。菩提树、佛脚印等是佛的象征。同时,很多夜叉像出现在佛塔周围,男女都有,女性为多。这些夜叉像既是偶像,又是佛的崇拜者。巴鲁特佛塔对偶像和故事题材的画面多有铭文记载,我们可以利用艺术和文字来讨论佛塔表现的宇宙观。
巴鲁特佛塔建设有记录的资助人,即佛教所说的供养人,有136人。其中58人为男性俗人,36女性俗人,25僧人,16比丘尼,有4个记载巽迦王室的捐赠。(5)Bharhut Inscrip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i, edited by H. Lüders, revised by E. Waldsehmidt and M.A. Mehendale, published by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76. p.1-2.这里女性占相当于男性供养人的62%;其中41人为僧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名字来看,供养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人的名字带着Naga,说明来自崇拜蛇的文化,有的带着 Yakha 的字样,说明与夜叉崇拜文化认同。有一类名字含有“野生灵”(Bhuta) 的字样,有可能是指比夜叉和蛇部落更为外围的社会的总称。当然还有认同婆罗门教的神明因陀罗和太阳神米特洛的。捐赠者还说明自己的家乡:城镇、村庄、山林、营地。(6)Bharhut Inscrip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i, edited by H. Lüders, revised by E. Waldsehmidt and M.A. Mehendale, published by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76. p.45.他们资助雕刻的艺术品多在佛塔的石围栏上。围栏由大石柱分为几段,大石柱上是突出的立像,石栏和石柱交叉处多为表现佛本生故事的浮雕,石栏上多为动物植物构成的装饰纹。总之,佛塔周围一人多高的石栏以众多的艺术品和捐赠铭文变现了佛教信仰者的社会组成,他们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的宇宙观。
首先来看供养人的形象。 在围栏的一端,也就是佛塔入口的大门一侧,一位王者骑在一头大象上,双手恭敬地端着盛装佛遗骨的盒子,率领骑在象和马上的随从。(7)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编号:107-141。图片来自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IIS) photograph archives at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这位王者的形象很可能表现巽迦王室成员对佛的供养。(8)出资雕刻这幅图面的并不是王室,而是位来自Vedisa的女性, Chapadeva, 是Revatimita的夫人。这对夫妇的身份无从得知,但显然不是等闲之辈。Bharhut Inscriptions,A 34, p.25.巽迦王朝的先辈是孔雀王朝的婆罗门宰相,但佛教文献一般不把巽迦族当作佛的支持者。从巴鲁特的铭文和这幅雕像来看这些婆罗门君主虽然不大力提倡佛教,但还是有所表示。不过君主在这个佛教社会里并不占领导地位,他们的形象并不比其他主要供养人更为高大。有名有姓的供养人里有僧人也有俗人,俗人往往以夫妇的形象出现,向佛虔敬致意。(9)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编号:268, 269。佛时代的最富有慷慨的供养人,王舍城的孤独长者的形象没有出现,但是他的事迹出现在一幅圆形浮雕画上。(10)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编号:156。画面上是用金币铺垫的园林的地面,表现孤独长者为佛教僧团购买祗园精舍的情节。精舍的主人要价很高,索要的金币必须铺遍整个园林的地。这些慷慨的供养人多为大商人,佛教文献经常提到的居士、长者。
在围栏的栏柱上,有数十个与真人高度相当的浮雕像,多是有名有姓的夜叉和半神(Devata)。这些人像代表受佛的启蒙皈依的夜叉等化外部落首领,在佛经中多有记载。但是在巴鲁特佛塔建筑上,他们的形象已经成为偶像,也就是信众礼拜的对象,是敬信的供养人捐赠的礼品。其中一位双手合掌礼拜的夜叉名为苏其洛摩,意思是刺猬头。(11)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编号:144。巴利文佛经记载他与佛的一番对话:
苏其洛摩:修行者,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答不出来,我要么打倒你的头脑,要么劈裂你的心,要么一脚把你踢进恒河。
佛:我还没见过宇宙中任何的造物,不管是天神、妖怪、梵天,还是世上的任何生灵,不管是修行者还是婆罗门,不管是人还是神,能够打倒我的头脑,能够劈裂我的心,还是能一脚把我踢进恒河。不管怎么说,你就问吧。(12)Sutta Nipata, II.5, quoted in Robert DeCaroli, Haunting the Buddha, Indian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苏其洛摩是一个外貌粗野,桀骜不驯的首领,传说是在迦雅亦即佛觉悟的圣地一带的森林里出没的夜叉。(13)Sutta Nipata, II.5, quoted in Robert DeCaroli, Haunting the Buddha, Indian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3.而释迦牟尼成功地说服他皈依佛教,不仅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且带领部落入教,所以成为佛教社会中的传奇人物,甚至是礼拜的偶像。这些围绕佛塔致敬的夜叉和半神大多有名有姓,很可能是部落首领加入佛教后被神化了。例如称为“丽人”(Sudasana) 的女子像很可能是记载中的印度东部昌巴城的女首领。(14)印度博物馆,编号:43。夜叉神遍布印度各地,他们的神像到处都有,在巴鲁特佛塔周围,他们虽然文化语言不同,围绕佛塔庄严礼拜,是各地佛教社会效法的典范。
蛇神也是印度大地处处皆是的民间神明。蛇王的王冠由五条眼镜蛇组成,下级蛇神的头上眼镜蛇数目递减,四个、三个、两个不等。巴鲁特佛塔围栏上刻有数个蛇神崇拜的画面。有一幅画面则是蛇王埃罗巴塔率众蛇神礼拜菩提树的场景。(15)印度博物馆,编号:265。几个世纪以后,埃罗巴塔在梵文化的佛教经典中出现,成为佛教神殿中的护宝神之一。(16)The Mahavastu, translated by J. J. Jones,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56, reprinted 1978, p. 380-301, quoted in Decaroli, Haunting the Buddha, p. 74.在梵文佛典中,埃罗巴塔传说来自西北的呾叉始罗,而在巴鲁特佛塔上,他更像是蛇图腾部落的帮主,带领下级首领来参拜佛。这些带着蛇冠的人,也是国家主流社会以外的集团,接受佛教的领导,加入佛教社会,他们的首领也就被神化,成为佛教神殿里的成员。
巴鲁特佛塔围栏石柱像之一是一位波斯王室装束风格的武士。他头上束着飘带,腰挎长剑,右手持一枝带叶的葡萄。(17)印度博物馆,编号:A24798。这座雕像没有姓名,但是其波斯风格是毫无疑义的。在佛教世界里,他可能是阿修罗的代表。阿修罗原是印欧语系的神明,在印度的吠陀时期是狄瓦诸天神的对手,同时是伊朗语系的最高神群。佛教文献通常把阿修罗当作既非人、又非动物的造物,也就是说,比文明人低一等、比动物高一等的异域人。在释迦牟尼生活的公元前五世纪,印度西北部包括最大都市呾叉始罗是波斯阿赫梅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此后被希腊人占领,但波斯的祆教文化仍然盛行,不少祆教信奉者仍然生活在印度。这位祆教人物在这个佛教圣地的神态虽不是顶礼膜拜,但仍然是很彬彬有礼,很尊崇。阿修罗是来自异域的人,但不是没有教化的野人。
在各个雕像群的底部,总是有一些长相丑陋的小矮人肩负重担,表情很吃力。(18)印度博物馆,编号:109。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苦受难。他们是谁呢?佛教世界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生存空间呢?有学者把他们归在夜叉类,但是他们在巴鲁特佛塔以及其它佛教建筑上的地位远不及那些已经神化的夜叉。这些是失去家族部落的支持、在动荡残酷的文明社会中求生路的小人物。他们是佛教宇宙中世间的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但在宗教圣地还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世间之上,还有一个天神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居民主要是吠陀时代的神明,也有些从民俗宗教加入的神。释迦牟尼的教导是靠个人的修行得到解脱,不需要神力的解救。但是他并不否认吠陀神明的存在,而是把他们并入到佛教的宇宙里。佛圆寂后流传的佛本生故事中,吠陀神因陀罗改名萨可(Saka)或萨可罗(Sakra) ,经常参与世间的纠纷。在佛教的信徒看来,吠陀神也是尊重佛的。贝鲁特佛塔围栏上有诸多体现众神向佛礼拜的场面。其中有众神殿庆祝佛削发的仪式。圣坛上是释迦牟尼头上剃下的发卷,天神有的合掌致敬,有的观望楼下的歌舞表演。表演者是世间的夜叉、半神,如前面提到的丽人。舞者为女性,奏乐者为男性,能辨认出的乐器有箜篌和鼓。(19)印度博物馆,编号:182。这些乐器显然不是吠陀时代就有的,而是通过呾叉始罗从波斯人或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但是这些舞者乐者则是印度各地民间传奇人物演变的半神半仙。
在这个佛教宇宙里,却没有佛的形象。人们礼拜的对象或者是象征佛得道的菩提树,或者是一双脚印、发卷。同时,佛经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在以佛本生故事为题材的画面上。在这些故事里,佛的前生是智慧无私的造物, 例如猴群首领以自己的身体搭桥供猴群度过深涧。(20)印度博物馆,编号:35。在这些童话故事般的画面上,猴子、象、鸟、松鼠、鱼、蛇虎、豺、人、各种人首鸟身、人首兽身的造物,以及各种天神、地鬼在行动,在对话,似乎生活在同一个境界,没有语言和物质的障碍。在这个宇宙中,人、神、动物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他们之间的身份都是可以转化的。佛的前生当过各种动物,大家的前生都可能当过动物。杀生很可能杀掉自己亲人托生的动物。积了足够的功德可能转生为天神,但是在天宫享乐,把功德花掉了,还是要回到地上来。这个宇宙的各个层次都是相通的,但是有等级,佛教信徒都愿意托生为天神或人,不愿做畜牲或阿修罗,也就是比人低、比动物高的外域人。只有佛本人脱离了这个轮回的宇宙,所以不再是有形象的造物。
三、五花八门的新生教派
佛教的这种宇宙观是从当时印度社会的现实状况中产生的,释迦牟尼用清晰的逻辑阐述出来,崇信者的社会集团用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思考加以补充。释迦牟尼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也面临财富的急剧增长、阶级分化、频繁的战争、疾病、灾害, 以及生活在文明社会周边的渔猎社会对新生国家的挑战,迫使他们思考国家产生的原因和走向。现在我们知道的宗教派别,除了耆那教有文献流传,都没有本派的传世记载,只是通过佛教文献的记录知道,释迦牟尼在成道前六年修行时,曾经尝试过各种教派的思想,反驳他们的理论,我们只能从《长阿含经》记载的反驳中窥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总体来说,都基于吠陀后期《奥义书》发起的宇宙空间和时间的循环概念。但是,在这个大循环的宇宙中,人生以及各种生灵是否有生死轮回,意见不一,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到严格的转世规则不等。顺世派 Lokayata 的创始人传说名为Carvaka,是彻底唯物主义派别,他们认为一切生物的灵魂和机体都是同一不可分别的,因此生命是不能从一个造物转到另一个造物的。以此推论,天、人、动物、鬼是不可能共享一个世界的。这个派别在印度史上长期流传,但是它没有什么宗教礼仪,对统治者巩固国家政权没有用处,对寻求解脱的大众也没有吸引力,是局限在少数思想家之间的哲学派别。阿耆毘派( Ajivika )则属于另一个极端。在阿耆毘派的宇宙里,不仅一切生物都要转世轮回,而且一切生物的命运都是前生注定的,不可能由个体的作为来改变。转世的道路程序也是定好的,因为宇宙已经划分成各种领域,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也都有固定的路线。(21)《长阿含经》,英译本 T.W. Rhys Davids,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Pali Text Society, 1899, reprint 1977,p.71.阿耆毘派有相当的追随者,也曾得到一些统治者的支持,但是极其严格的修行对大众的吸引力不大,所以也没有形成宗教传统流传下来。
当时能与佛教一较高低的只有耆那教。耆那教的创始人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出生的环境也类似,在跋耆共和国的都城吠舍厘附近,也是一个反婆罗门正统和君主制的政治环境。耆那教的宇宙观和教旨与佛教看起来很接近,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耆那教的宇宙也是从生到死大循环,各种生灵都经历转世轮回。同时耆那教的无害主义比佛教要严格得多,包括小到虫蚁的一切生物:“禁止杀害一切生灵,禁止摧残、虐待、折磨、驱赶一切生灵。切记这个道理,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这是导师的教训。”(22)Jain Sutras, translated from Prakrit by Hermann Jac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 reprint 1980, p.38-39.因此,信徒要十分小心,不仅要时时避免踩死虫蚁,还要戴上口罩,避免无意中吸入虫蚁。这样一来,不仅渔人、猎人不可能信仰,农民也不可能加入,因为耕种土地不能不杀虫。耆那教也有僧团,僧人以化缘为生,但是对接受的食物有严格的要求。僧尼都不得在其他宗教的任何场合领取食物。在沙门和婆罗门云集的场合,不管是婆罗门教的马祭、因陀罗盛典,还是夜叉、蛇神部落的活动,都要回避。(23)Jain Sutras, translated from Prakrit by Hermann Jac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 reprint 1980, p.92-93.这种规则与我们在巴鲁特佛塔的围栏艺术上看到的包容万象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宗教实践使得耆那教在商人社会里扎根,跟着商人追随商机而前往商业发达的地区,在印度经久不衰,也曾经得到某些君主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团结少数民族,举行巩固国家政权的礼仪。
四、婆罗门教的困境与改革
婆罗门是旧的世系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世系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掌握与神交流的特权。早在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婆罗门教文化追随印欧语系的吠陀社会向恒河平原迁徙的时候,很多婆罗门知识分子认识到大量宰牲来祭神已经不适应农业社会的发展。有的遁入森林发展学术,他们的思考和讨论记录在《奥义书》。同时正统的婆罗门祭祀仍然用自己家族掌握的知识和社会地位跻身新生国家的统治集团,为新的统治者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当时世系分化成种姓,曾经为一方霸主的武士世系已经分崩离析,自称来自这些贵族世系的家族也都各立门户,经营农业。在失去世系组织的时代,婆罗门祭司为出身微贱的国王们求得天命,就要用祭祀把新的霸主吸收到世系神话的体系中。
吠陀后期的婆罗门教经典《百路梵书》是对吠陀祭祀仪式的注解,同时也是在进入农业社会的情况下,对祭祀仪式的修正。婆罗门主持的王祭是为君主加冕的仪式,在宰牲之后,婆罗门宣布君主得到天命,而他们自己则在索麻神的保护下“这个人,就是你们(俱卢族和般查拉族,月亮族的两大世系)的君主,我们(婆罗门)的君主就是索麻(月亮)神。”(24)最初的听众,是月亮世系的这两大家族,以后的王祭场合,祭司可以换其他部落的名称,或简单称之‘人民’。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894,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1979, part III,V3,12,p.72.于是,婆罗门不仅把君主纳入婆罗门教的体系,而且把自己驾驭在君主之上。马祭是为君主制定疆域,君主和婆罗门祭司挑选一匹好马,在举行仪式以后,由一位大将追随其后,在征服的领地漫游,随时接受不甘心受这位君主统治的人的挑战。一年以后,人马回到君主的驻地,宰杀马以祭神。这个仪式在印度历史上长期为君主制服务,只是真马换成假马,成为形式。还有一种主要为王权服务的仪式称为“庆功酒宴”(Vajapeya),其中主要一项活动是马车竞赛。马车竞赛是吠陀社会古老的风俗,是武士们之间的比武活动。君主主持这个赛事,表现与武士世系的连续,他们和天神的亲密关系,因为赛车的缘起是狄瓦天神之间的竞赛。举行了“庆功酒宴”,君主就不仅是“王”(Raja),而是 “皇帝”(samraja)。(25)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79, part V. 1. 1. 14, p.4.
《百路梵书》在描述这些祭祀活动时,屡屡提到狄瓦天神和阿修罗同源于一个始祖,并在出生后就不断竞争。狄瓦天神和阿修罗是中亚印欧语系社会分裂出的两大支系。崇信阿呼罗为神明、狄瓦为鬼类的一派入主伊朗高原,发展为祆教,而崇信狄瓦为天神的一派在印度发展为婆罗门教。到了吠陀时期的牧人转变成农民的时候,阿修罗还是无处不在,可见当时很有一些祆教尊崇者生活在印度。他们有些可能是在吠陀人入主南亚前后到印度定居,长期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有些可能是后来的移民,特别是在波斯帝国统治西北部包括呾叉始罗时期,商人使团很多来往。巴鲁特佛塔围栏上向佛礼拜的阿修罗(图8)看起来就是波斯贵族。婆罗门祭司抱怨阿修罗骚扰他们的祭祀,(26)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79, part I, I. 1. 16 ff., p.8 ff.可能是符合真情的,因为祆教反对杀生祭祀。婆罗门说阿修罗善于搞魔术,(27)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79, part II. 4. 5. p.362.这也符合其他文献对祆教的记载。婆罗门说阿修罗不会说话,因为天神把他们的语音抢走了。(28)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79, part II, III. 2. 1. 22.这正是反映这两支印欧语系社会的语言分化,已经不能相通了。更为根本性的文化区别是,阿修罗的葬礼不同于狄瓦天神的崇信者。婆罗门教实行火化,燃尽的遗骨入土为安。但是,阿修罗的信仰者是要把遗体与土地分开的。(29)Satapatha-Brahma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us Egge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79, part V, XIII 8. 2. 1, p. 430.这点也基本符合祆教经典对葬礼的规定,只是婆罗门的记述没有那么详细。(30)The Zend-Avest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ames Darmeste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80, Fargard V - p. 72 ff.看来,阿修罗不仅是天神的对手,也是婆罗门的不可轻视的竞争者。
给婆罗门祭祀造成困扰的还有罗刹。罗刹虽然有时与阿修罗相提并论,但显然没有阿修罗显要,因为罗刹没有根,也就是没有世系可寻。(31)Satapatha Brahmana, Part II, III. 1. 3. 13, p.16.这些罗刹很可能是印度当地的土著,他们并不像阿修罗那样顽固,只要接受吠陀祭祀,是可能加入婆罗门教的种姓体系的。(32)Satapatha Brahmana,part II, III. 2. 1. 40. p. 35.《奥义书》中记载的一位名为“真情”的男孩,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何人,因为他的诚实而被接受为婆罗门学生。(33)The Upanishads,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Max Ml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reprint Motilal Banarsidass,Delhi,1981,Part,I,IV 4,p.60-61.这个男孩大约也是一个吠陀世系以外的人。婆罗门教这个时期通过宗教祭祀礼仪接纳化外的人口,只是这种接纳限于个别人,而不是部落整体。
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比吠陀时期更加丰富。宰牲、赛车、祭祀等活动都伴有音乐。弦乐器维纳vina在各种祭祀场合都要演奏。马祭时奏乐的场合很多,优秀的乐手成为大师。(34)Satapatha Brahmana, Part Satapatha Brahmana, Part V, VIII 4. 3. 3., p.362-363.祭祀的场合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是喜庆活动。巴鲁特佛塔围栏画面上天神奏乐舞蹈(图10)反映的就是婆罗门教宗教礼仪的这种发展。同时,吠陀梵文已经过时,婆罗门学者帕尼尼制定梵文标准语法,为古典梵语文学亦即婆罗门教的正统地位打下基础。婆罗门教的祭祀礼仪在为新生的王权服务的过程中,吸收中亚、西亚的文化,也在形式上趋于完美,发展成宫廷的宗教礼仪。同时,随着各种游牧、渔猎社会进入主流农业社会,他们的音乐、舞蹈传统也加入以狄瓦天神名义举行的喜庆活动。正是婆罗门教礼仪活动向音乐、舞蹈的发展使得狄瓦天神的信仰传到不同语言文化的民间,因而也被佛教的礼拜礼仪采纳。
五、释迦牟尼挑战婆罗门教的宇宙观
释迦牟尼精确阐述的转世轮回的观念把天上地上的各种造物包容到一个宇宙,坚决驳斥婆罗门教杀生祭祀的合理性。从文化上,释迦牟尼与婆罗门正统划清界限,不用吠陀梵文说法,而是用俗语说法。他所用的方言,大概不是他出生的喜马拉雅山麓的方言,而是在他四处修行,得道后云游说法,积各地听众和辩论对手的口音,而形成的能为印度北方大多数信众和反对派听懂的口语,从而奠定巴利文佛经的语言规范,为佛教经典的文字化打下基础。释迦牟尼和梵文语法家帕尼尼大约是同时代人,都属于印欧语系的文化。帕尼尼为经典梵文的发展制定规则,释迦牟尼倡导的俗语并不是没有严格语法规则的口语,而是语言规则不同于经典梵文的巴利语。
释迦牟尼之所以能够把举止粗野、相貌鄙陋的化外民族改造成文明社会的成员,是因为他所率领的出家人组成的僧团用严格的礼仪来建立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早期僧团居无定所,只是在雨季暂住供养人提供的临时居所,或者在沿路的山洞避雨修行。当时其他教派的修行者大多完全不修边幅,甚至赤身裸体,表示与自然界的彻底结合。释迦牟尼本人当过这种修行者,但认为这是失败的生活方式,不可能通过这种毫无意义的苦行悟道。同时,要为一个不断壮大的僧团建立一个管理制度,需要一个过程。从最早的巴利文《律经》来看,释迦牟尼本人亲自因势利导,建立了一套生活管理制度,为僧人的修行创造健康的环境。
佛教僧团这套礼仪的建立,也得力于当时著名的医生耆婆(Jivaka)的指导。耆婆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他出生在摩揭陀国的都城王舍城,母亲是当地的名妓,为了生计把刚出生的儿子抛弃到街上。一位王子路过围观的人群,发现这个还活着的婴儿,收养他,命名耆婆,意思是“活着”。耆婆长大成人,得知自己的身世,决心学一门技能,安身立命。他前往呾叉始罗求学医术,学成后回到王舍城,报答养父之恩,在恒河中下游一带行医。(35)Vinaya Texts, translated from Pali to English by T.W. 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2,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4, part II, viii 1-35, p. 171-194.耆婆是释迦牟尼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佛教僧团的保健医生。当时僧人在天冷的时候没有衣服,拣火葬墓地死人的衣服来穿。死者家属可能也把死者的衣服捐赠作为功德。有一次,佛患病,耆婆为他诊治以后,恳请佛接受干净的、新的袈裟,并允许僧人接受供养人赠送的新布或衣物。(36)Vinaya Texts, translated from Pali to English by T.W. 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2,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4, part II,viii 31-35, p. 191-195.于是佛规定僧人可以接受新的、干净的衣物。有一年王舍城传染病流行,许多病人无处投医,听说佛教僧团收养病人,并有耆婆诊治。他们于是前往僧团驻地,假装皈依受戒,治愈后又脱离僧团,反成俗人。耆婆发现这种行为之后,气愤不已,规劝释迦牟尼不得度这种患传染病的假信徒入僧团。(37)Vinaya Texts, translated from Pali to English by T.W. 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2,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4, part II,Part I, I 39. 1-7, p.191-194.这一方面当然是剔除假冒伪劣的皈依者,也是保护僧团的卫生环境,避免传染病流行。在耆婆的指导下,释迦牟尼为僧团规定了一整套卫生制度,包括在驻地建浴室,锻炼活动的场地,并规定僧人要每天刷牙。(38)Vinaya Texts, translated from Pali to English by T.W. 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2,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74, Part III, V 14; V 31, p. 103ff; 147ff.正因为这套制度经过律经的整理成为佛门弟子必须尊崇的宗教礼仪,佛教僧人的生活虽然很简朴,但是大多长寿。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有争议,但他无疑活到七十余岁,这在公元前五世纪的热带地区不能不说是奇迹。
佛教僧团这种健康的生活制度为统治集团的反叛者和社会的失落者提供人生的归宿。最早的比丘、比丘尼有不少人写下诗歌表达自己对佛的教导的领会和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慨。从这些诗歌来看,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有王子、公主,有婆罗门弟子,也有贱民,还普通人家的子女。僧团是化外社会有志之士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好几个佛门大弟子随母姓,说明来自婆罗门教以外母系社会。著名的目健连和舍利弗就是从母姓的。(39)Psalm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II, Psalms of the Brethren, translated by Mrs. Rhys Davids,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13, reprint 1980, p. 340.这些比丘的母亲,以至于母系家族,也就加入佛教社会。不管出身高贵还是低贱,对他们在僧团的地位高下没有影响。比丘尼的诗歌里多有提到得到人身的解放,包括摆脱了兴奋剂 āsava。这些毒品具体是什么很难确认,但是服用兴奋饮料看来很普遍。吠陀祭祀中婆罗门祭司把索麻酒献给神,自己也要喝,以求达到与神的沟通。到了国家城市兴起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新的兴奋性饮料。加入佛门的妇女,有些就是为了摆脱毒品,过健康的生活。例如舍卫城的一位婆罗门出身的比丘尼 Sakulā 的诗歌就以“我摆脱了一切有毒的药物, 我冷静、清醒,看到了涅般境界”的诗句结尾。(40)Psalm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I, Psalms of the Sisters, translated by Mrs. Rhys Davids,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09, reprint 1980, p. 61.佛门的宗教纪律与婆罗门教的疯狂祭祀活动公开地分庭抗礼。
六、孔雀帝国阿育王对婆罗门教的改造
公元前五世纪新生国家兴起的时期,婆罗门教以祭祀为君主请天命,是政治上的当权派。佛教则是在野派的首领,团结归化主流社会以外的部族,收容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以及社会剧烈变化造成的失落者,建立国家领土内的慈善机构,并用严格的宗教规则管理来自社会各层次的僧尼,实际上缓和了政治、社会矛盾,扶助了新生国家的诞生和发育。在佛圆寂一百余年后,以摩揭陀为基地的孔雀王朝统一印度大部,君主制国家成为印度历史上最持久、最稳定的政治体制。但是,婆罗门教在印度的主导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佛所出身的释迦共和国和大雄出身的跋耆共和国联盟被帝国扩张吞没,但是佛教和耆那教都在继续发展。佛门弟子把释迦牟尼的教训编写成书,四处建造佛塔集合礼拜,通过雕刻艺术重述、诠释、补充佛的教导。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是著名的佛教支持者。他本人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同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努力用释迦牟尼的胸怀团结广大领土上多民族、多文化传统的臣民。他统治时期发出的敕令向全国各地发放,用当地语言刻写在石柱上。阿育王在他的敕令中,总是称“婆罗门和沙门”,把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在野派的修行者相提并论为文明社会的精英。同时他严禁杀生祭祀以及相关的喜庆活动。(41)Inscriptions of Asoka, new edition, by E. Hultzsch, Delhi: 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69, First Rock edict, p. 51.阿育王禁止杀生祭祀是促使婆罗门教礼仪及教义改造的重要举措。婆罗门仍然是帝王的参谋和教师爷,但是杀生祭祀的宗教礼仪失去光彩,泥塑的牛马替代真正的牺牲,以至于婆罗门种姓中也形成素食主义的风气。但是阿育王并没有严禁婆罗门教祭祀礼仪上的喜庆活动。我们在布鲁特佛塔上看到,夜叉、蛇神部落进入主流社会,实际上增加了音乐舞蹈,发展成民间的宗教活动,在佛教礼拜的光环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