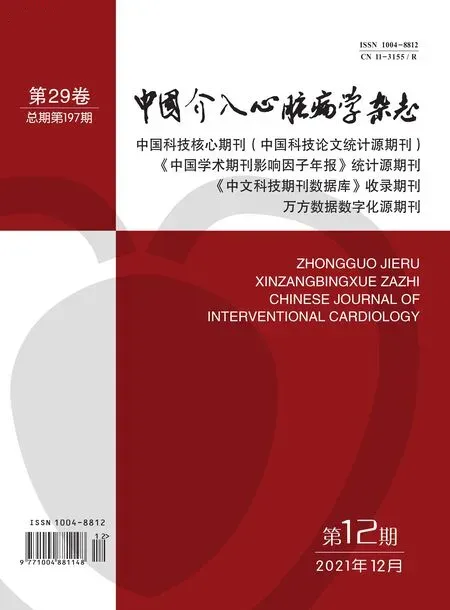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中瓣周漏同期介入封堵1 例
张蔚菁 潘文志 管丽华 张晓春 张源 张蕾 陈莎莎 李明飞 周达新 葛均波
1 临床资料
患者 女,78岁,因“反复活动后胸闷气促1年”于2020年4月23日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患者近1年来反复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无胸痛、晕厥等症状。既往无高血压病、糖尿病病史。入院查体:脉搏78次/分,血压130/81 mmHg(1 mmHg=0.133 kPa),呼吸18次/分;两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界无扩大,心率78次/分,律齐,主动脉瓣听诊区可闻及3/6级收缩期喷射样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入院常规经胸超声心动图示:主动脉瓣膜及瓣环明显增厚伴重度狭窄,瓣叶形态显示欠清,二叶式主动脉瓣不除外,无主动脉瓣反流,升主动脉增宽为39 mm,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68%。主动脉根部CT血管造影示:二叶式主动脉瓣,瓣叶增厚明显不均匀,可见多发斑点团片结节状钙化,瓣环见粗大钙化,左冠状动脉瓣和无冠状动脉瓣交界处巨大团块状钙化,瓣环长短径24.5 mm×21.3 mm,瓣环面积391 mm²,周长71 mm,瓣环开放面积67 mm²,主动脉窦宽28.8 mm×29.7 mm×31.5 mm,瓣下左心室流出道见条片状钙化,左心室流出道管径24.4 mm×19.1 mm,面积352 mm²,升主动脉窦管交界处管径28.6 mm×25.5 mm,瓣上40 mm处升主动脉管径36.8 mm×35.5 mm,左冠状动脉开口距瓣环8.9 mm,右冠状动脉开口距瓣环10.7 mm(图1)。入院诊断:重度钙化性主动脉瓣狭窄,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

图1 术前主动脉根部CT 血管造影情况,左冠状动脉瓣和无冠状动脉瓣交界可见巨大团块状钙化 A.主动脉瓣环(瓣环见粗大钙化,瓣环长短径24.5 mm×21.3 mm,瓣环面积391 mm2,周长71 mm);B.瓣上结构;C.右冠状动脉开口距离瓣环高度;D.左冠状动脉开口距离瓣环高度;E.左冠状动脉瓣和无冠状动脉瓣交界巨大团块状钙化
患者美国胸外科医师学会(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评分4.8%。于2020年4月24日静脉复合麻醉下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穿刺左侧桡动脉监测血压,穿刺左侧锁骨下静脉,置入6 F鞘管,植入临时起搏器导线至右心室。穿刺左侧股动脉,置入6 F鞘管。穿刺右侧股动脉,预置2把ProGlide动脉缝合装置后穿刺置入9 F鞘管。进入Lunderquist导丝,退出6 F动脉鞘管,将Gore18 F导管鞘套件缓慢推进至升主动脉。使用6 F AL1造影导管、直头超滑导丝进入左心室,后将导管沿超滑导丝送入左心室,交换为6 F猪尾导管,测量左心室内压力及主动脉压力分别为181/7 mmHg和120/49 mmHg。送入塑形后的Lunderquist导丝,选择18 mm×40 mm的Z-med球囊在180次/分右心室起搏下于主动脉瓣处扩张1次,结合术前主动脉瓣CT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测量的瓣环直径大小,选择23 mm的VENUS-A主动脉瓣膜(杭州启明TAV23)。经Lunderquist加硬导丝送入装备好瓣膜的导管输送系统至主动脉瓣环处,于猪尾导管和主动脉根部造影协助下打开并释放瓣膜支架,复查主动脉根部造影提示人工瓣膜位置合适(深度4 mm),冠状动脉开口未受影响,中度偏多主动脉瓣反流(图2A)。复查TEE提示二尖瓣开闭不受影响,人工主动脉瓣膜工作良好,中度偏多瓣周漏,轻微瓣中反流(图3A)。
遂予Z-med主动脉瓣球囊(20 mm×40 mm)在180次/分右心室起搏下于主动脉瓣处扩张1次,复查主动脉根部造影提示中度偏多主动脉瓣周漏,且无冠状窦处可见钙化团块挤压瓣环,遂未再予以22 mm球囊再次后扩张(图2B)。TEE提示人工主动脉瓣工作良好,重度瓣周漏,无明显瓣中反流(图3B)。复测左心室内压力和主动脉压力分别是105/17 mmHg和89/33 mmHg。
考虑到患者瓣周漏的出现是由于瓣周钙化负荷重,特别是左冠状动脉瓣和无冠状动脉瓣交界处巨大团块状钙化斑块造成人工瓣膜贴壁不良,遂决定进一步施行经导管瓣周漏介入封堵术。在AL2导管指引下,超滑导丝通过瓣周漏进入左心室,换入Superstiff导丝至左心室后送入6 F COOK抗折鞘管,后沿抗折鞘管送入10 mm PDA-PLUG封堵器(上海形状记忆合金),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和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指引下在9至12点钟方向处封堵,复查主动脉根部造影提示瓣周漏减少为中重度(图2C),复测左心室和主动脉压力分别是107/18 mmHg、103/38 mmHg。
再次在AL2导管指引下送入超滑导丝通过残余瓣周漏至左心室,换入Superstiff导丝至左心室后送入6 F COOK抗折鞘管,后沿抗折鞘管送入12 mm PDA-PLUG封堵器(上海形状记忆合金),在DSA和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指引下在6至9点钟方向处封堵。复查主动脉根部造影提示瓣周漏减少为轻度(图2D),TEE提示瓣周漏减少为轻度(图3C),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提示轻度瓣周漏、2枚封堵器位置良好(图3D),复测左心室和主动脉压力分别是120/13 mmHg、114/53 mmHg。遂退出鞘管,使用预先留置的ProGlide动脉缝合装置缝合18 F鞘管处动脉穿刺点,保留起搏器导线,余穿刺点加压包扎。术中用肝素4000 U,测得激活全血凝固时间267 s,碘克沙醇300 ml。术后抗生素应用3 d;口服阿司匹林100 mg、每日1次与氯吡格雷75 mg、每日1次拟治疗6个月,其后长期给予阿司匹林100 mg、每日1次。

图2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术后及瓣周漏处理后主动脉根部造影 A. TAVR 术后即刻主动脉根部造影;B.球囊再扩张术后主动脉根部造影;C. 10 mm PLUG 介入封堵后主动脉根部造影;D. 12 mm PLUG 介入封堵后主动脉根部造影

图3 TAVR 术后及瓣周漏处理后TEE 检查 A. TAVR 术后即刻TEE 主动脉根部长轴切面;B. 球囊再扩张术后TEE,左侧为主动脉根部长轴切面,右侧为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C. 10 mm PLUG 和12 mm PLUG 介入封堵后TEE,左侧为主动脉根部长轴切面,右侧为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D.12 mm PLUG 介入封堵术中和术后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
患者术后无活动后胸闷气促再发,无心律失常、肾功能受损、溶血等并发症出现。NYHA心功能上升至Ⅰ级。2020年5月28日随访经胸超声心动图示:人工主动脉瓣轻度瓣周漏,二尖瓣后叶瓣环钙化伴轻度反流,升主动脉增宽,LVEF 59%。
2 讨论
TAVR是心血管疾病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自2019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发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PARTNER3研究[1]结果以来,TAVR正向全人群患者迈进。但根据多项研究结果显示,TAVR术后的中重度瓣周漏发生率高达9%~21%[2]。PARTNER研究Sapien3瓣膜公布的1年期随访结果[3]:重度瓣周漏的发生率为0,中度瓣周漏的发生率为2.7%,而中度瓣周漏的出现与患者1年的死亡率相关。故TAVR术后瓣周漏问题需重视。
造成TAVR术后瓣周漏的原因主要有瓣周钙化严重导致人工瓣膜贴壁不良、人工瓣膜尺寸选择与自身瓣环大小不匹配、人工瓣膜置入过深或过浅等多种原因。依据目前的技术手段,应对TAVR术后瓣周漏主要有球囊后扩张、瓣中瓣置入、经导管瓣周漏封堵等措施[4]。其中球囊后扩张术是大多数术后瓣周漏的处理方式,而对于瓣膜置入过深或过浅的情况,可以采取瓣中瓣的方式。对于上述方法无法解决或不适合解决、特别是瓣周钙化严重造成人工瓣膜贴壁不良导致的瓣周漏,介入封堵是优先选择,国外已有多例相关报道。根据Waterbury等[5]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共纳入18例TAVR术后重度瓣周漏的患者,同期施行封堵术,手术成功率为78%(瓣周漏从中重度降至轻度及以下)。近期也有国内报道了对TAVR术后瓣周漏尝试封堵,但由于出现罕见的输送器嵌顿事件,尝试通过提拉技术拔出嵌顿的输送器,最终导致瓣膜脱出而未成功的案例[6]。本文报道的是国内采用介入封堵措施同期治疗TAVR术后中重度瓣周漏并且取得良好效果的病例,证明了其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TAVR术后瓣周漏的评估环节,主动脉根部造影和TEE两种方式各有其局限性。主动脉根部造影受体位的影响,有时不能很好地区分瓣周漏和瓣中反流,并且在瓣周漏直径测量时受到瓣周漏位置的影响。TEE则面临测量结果受操作者主观影响大的问题[4]。在本例患者测量过程中将二者结果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近期国内报道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式,探究了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在TAVR术中监测的意义,指出纳入的54例因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而行TAVR术的患者,术中共发生36例少至中量瓣周漏,最终均由三维超声心动图明确瓣周漏位置及大小[7]。在本例报道中,利用实时三维重建技术提高了瓣周漏位置判断和流量大小测量的准确性,为2枚封堵器放置位置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证明了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在TAVR术后瓣周漏介入治疗中的价值,值得推广。
对于TAVR术后瓣周漏的转归及其机制的研究国内外文献报道缺乏一致性。根据PARTNER研究结果,在术后2年的随访中,22.4%的患者瓣周漏较前进展,46.2%维持不变,31.5%的患者较前减轻[3]。而来自Webb等[8]、Muñoz-Garcia等[9]、Ussia等[10]的单中心研究结果则显示TAVR术后瓣周漏在随访的1年中没有明显变化。造成上述不同转归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020年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11],在其纳入的93例接受自膨胀瓣膜的TAVR术后患者中,共有63例患者出现瓣周漏,其中中度和重度瓣周漏的患者有21例(22.6%),而1年期的随访结果显示,有2例患者从轻度瓣周漏发展为中度瓣周漏,却有25例患者瓣周漏较术后即刻时减少,其中就包括前述21例术后中重度瓣周漏患者中的9例,瓣周漏减少至少1个等级。并且,该研究发现,瓣周钙化负荷在造成转归的不同上起到关键作用,瓣周钙化较轻的患者瓣周漏好转的可能性较钙化评分高的患者大。本例患者也从正面验证了对于瓣周钙化负荷重所造成的TAVR术中中重度瓣周漏患者,同期行经导管瓣周漏介入封堵术是可行的,同时也是必要的。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