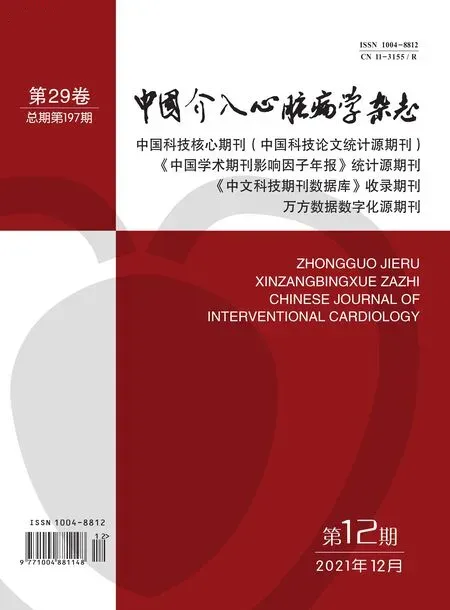左心耳封堵术致左心耳冠状动脉瘘1 例
王学文 钟建利 田伟 张勇华 苏晞
1 临床资料
患者 女,76岁。因“胸闷、气促12年,胸痛伴心慌4年,心慌加重1个月”于2020年7月入住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现病史:患者2008年开始间断发作胸闷、气促,偶伴双下肢水肿,未积极治疗。4年前开始间断出现胸骨后闷痛不适,伴有心慌,于2017年4月19日到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住院诊治,入院诊断为:心律失常,心房颤动(房颤)。动态心电图示:房颤伴缓慢心室率(最慢心率42次/分)。冠状动脉造影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图A~C)。2017年4月24日行左心耳封堵术(图D~E,采用波士顿科学公司33 mm WatchmanTM封堵器),术后患者未诉不适。出院后坚持服用抗凝药物(利伐沙班15 mg,服用3个月后停用,未服用华法林)。2020年6月患者无明显诱因再发胸闷,憋气,伴有心慌,为行系统治疗,于2020年7月17日就诊于本院。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0年,最高血压180/100 mmHg(1 mmHg=0.133 kPa),平素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治疗;有脑梗死病史,未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否认糖尿病病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查体未见阳性体征。
治疗过程:患者2017年4月住院治疗过程中,心电图提示房颤,F波低平。超声心动图示:双心房扩大(左心房内径4.9 cm,右心房内径4.8 cm),二尖瓣轻度关闭不全,左心室射血分数56%。根据CHA2DS2-VASC评分:高血压病史1分;年龄73岁,1分;有脑梗死病史,2分;女性,1分;总分5分,属于卒中高风险,需要积极抗凝。HAS-BLED评分:高血压病史,1分;脑梗死病史,1分;年龄73岁,1分;总分3分,属于出血高风险,抗凝治疗需要评估获益风险。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示:左心耳内未见血栓形成,二、三尖瓣轻度反流。患者及家属不愿意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电生理专家评估后认为:患者年纪较大,左心房扩大,心电图F波低平,考虑房颤持续时间较长,射频消融手术成功率较低;患者卒中风险高,但患者不愿意长期抗凝治疗;根据中国指南及共识推荐[1],CHA2DS2-VASC评分≥2分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若不适合长期口服抗凝药,在服用华法林国际标准化比值达标基础上仍发生卒中、栓塞事件或HAS-BLED评分≥3分可选择左心耳封堵治疗,降低卒中风险,同时可减少抗凝时间。经商议后家属同意左心耳封堵术。2020年7月入院后超声心动图示:双心房扩大(左心房内径5.1 cm,右心房内径4.7 cm),升主动脉明显增宽,二、三尖瓣轻-中度反流,室间隔增厚,心律不齐,左心室射血分数56%。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示:左心耳封堵术后,左心耳内未见血栓形成,二、三尖瓣轻-中度反流。头颅CT示:双侧基底节区、双侧半卵圆中心、双侧放射冠区、双侧额叶腔隙性脑梗死,陈旧性病灶可能。检验结果示:凝血功能,肝功能,甲状腺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及D-二聚体、超敏C反应蛋白、地高辛浓度、肌钙蛋白I未见异常;随机血糖8.59 mmol/L,糖化血红蛋白7.6%,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1139 pg/ml;总胆固醇5.61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6 mmol/L,三酰甘油2.23 mmol/L。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阴性。心电图示:房颤伴快速心室反应(心率122次/分),右束支传导阻滞,室性早搏。动态心电图示:房颤,室性早搏全程13 308次。2020年7月20日冠状动脉造影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回旋支左心耳瘘(图F~G);考虑患者左心耳封堵术后出现左回旋支-左心耳瘘。遂于2020年7月22日行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示(图H~I):左回旋支近段发出两支细小分支,其一支血管于左房耳前壁向上走行进入左心房体、耳交界处内侧,汇入口径约2.2 mm;另见一支血管向左绕左房耳迂曲走行汇入左房耳左侧壁,汇入口径约2 mm;左房耳可见封堵器影,封堵器形态好。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示:左心房与左心耳间细束血流信号交通,分流束宽约0.2 cm,封堵器肩部高出约0.8 cm。左心耳左侧壁可见细束连续性血流信号汇入左心耳内,考虑为小冠状动脉瘘可能。药物治疗方面未给予特殊治疗。既往文献未见类似并发症报道。
2 讨论

图1 A~C. 2017 年4 月21 日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回旋支血管正常,未见血管瘘;D~E. 2017 年4 月24 日左心耳封堵术;F~G. 2020 年7 月20 日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左回旋支左心耳瘘;H~I. 2020 年7 月22 日行冠状动脉CT 血管造影示,左回旋支近段发出两支细小分支,其一支血管于左房耳前壁向上走行进入左心房体、耳交界处内侧,汇入口径约2.2 mm;另见一支血管向左绕左房耳迂曲走行汇入左房耳左侧壁,汇入口径约2 mm;左心耳可见封堵器影,封堵器形态好
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血栓栓塞是房颤患者致死或致残的主要原因。房颤患者卒中的发生风险较一般患者高出5倍,且随年龄的增加而迅速增加[2]。研究表明,房颤患者发生卒中的主要原因是左心耳血栓的形成和脱落,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高达 90% 的血栓来源于左心耳[3]。因此,左心耳封堵术得到运用和发展,通过封闭左心耳,隔绝左心耳血栓来源已经成为预防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血栓栓塞的新方法,可有效地预防卒中的发生[4]。随着左心耳封堵术的应用和发展,越来越多手术相关并发症出现。常见并发症包括以下几种[5-6]:心包积液与心脏压塞、空气栓塞和血栓栓塞、器械栓塞、器械表面血栓、血管损伤、残余分流等;更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封堵器脱落[7]、猝死等。心包积液与心脏压塞是左心耳封堵术中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目前临床研究最为多见的并发症。多数并发症经过常规处理可以得到解决,预后尚可。严重并发症例如封堵器脱落甚至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处理。本例患者左心耳封堵术后3年复查心脏造影检查,发现左心耳与左回旋支之间存在交通,且冠状动脉有大量血流到左心耳内。此类左心耳封堵术后并发症在既往文献中未见相关报道。瘘管形成病因尚不清楚,根据患者既往造影检查结果对比,考虑左回旋支与左心耳之间的瘘管形成,与左心耳封堵器置入相关,可能因左心耳封堵器上的金属梁穿破左心耳刺入左回旋支,经过缓慢组织重塑,从而形成瘘道。经过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及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也同样证实存在冠状动脉与左心耳之间的分流存在。大量冠状动脉血经左回旋支瘘道流入左心房,可能与患者胸闷不适症状相关。根据该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无法明确具体分流血管的入口,因此,介入封堵治疗无法进行。该患者症状不典型,治疗方面选择了继续观察,维持既往药物治疗方案;未建议患者积极外科治疗。
每一种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种技术的完善,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的进步上,对于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的认识和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本例并发症既往未见类似报道,具体病因仍需要临床进一步观察,必要时行动物实验,进行相关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