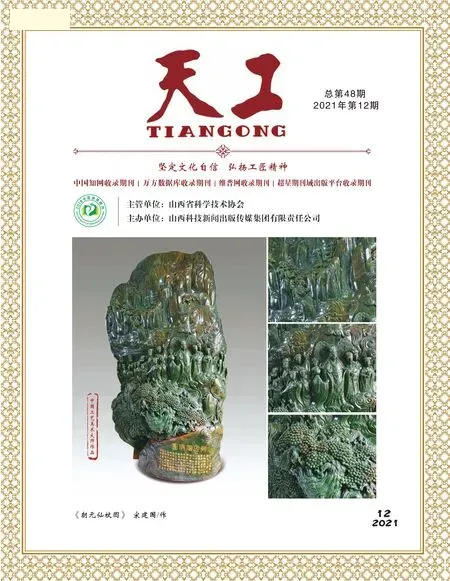多元文化交汇下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造型
陈晓萍 王庆兰
泉州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一、引言
泉州开元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唐垂拱二年,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有着皇家寺庙的规格。在开元寺中,现存宋代大雄宝殿的妙音鸟斗拱和甘露戒坛的飞天伎乐斗拱①根据《鑑湖张氏族谱》记载,“十四世张仕逊,字法参,官主簿三余,以木雕游寺观,所治皆绝品,如泉州开元寺飞天”。张仕逊所处年代距今约760年,由此可见,张仕逊在南宋开元寺重建时参与设计和雕刻了飞天。而根据2014年11月7日在《东南早报》发表的《开元寺木雕七百多岁》一文,可了解到开元寺在明末又进行重塑,一般在重塑的过程中,工匠们会尊重前代的造型,给予仿制恢复。,造型精妙,兼具实用价值和美观价值。
大雄宝殿被称为“百柱殿”,柱头上装饰着二十四尊妙音鸟——由十二尊老鹰翅膀的大型妙音鸟和十二尊蝙蝠翅膀的小型妙音鸟组成,其造型与印度神话中“迦陵频伽”近似,都是人身鸟翼。妙音鸟们头戴宝冠,袒胸露臂,脸庞端严,神态优雅,项挂缨珞,臂束钏镯,背上两翼舒张,妙音鸟有的手持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如琵琶、洞箫、三弦等,有的手持文房四宝,还有的手持五香斋果,皆侍奉在五方佛前(如图1)。甘露戒坛斗拱处的飞天伎乐在造型上更偏向中国传统的飞天艺术形象,从造型上来看,其完全是人的形象姿势。与妙音鸟相比,飞天伎乐以飞扬的飘带代替了翅膀,大多赤裸着上身,也有部分身着小件背心,有的手持“南音北管”乐器在空中表演大型的乐舞,还有的手持托盘供奉宝物于佛前(如图2)。

图1 大雄宝殿 妙音鸟(宋代)

图2 甘露戒坛 飞天伎乐(宋代)
纵览中国飞天艺术,开元寺宋代“飞天”造型算是独树一帜。那么,为什么在泉州会存在着造型如此独特的“飞天”呢?
泉州处在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区域,促使该区域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1]闽南多元的文化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这也造就了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的独特艺术形象。①在中国,“飞天”指的是在佛教艺术中供养的天人,礼佛、奉献、飞舞的天人。本文中的“飞天”指代有两种,一种是佛教中“乾闼婆”和“紧那罗”两神的衍变;另一种是人首鸟身的妙音鸟,“妙音鸟”梵语译为“迦陵频伽”,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而存在。飞天伎乐和妙音鸟因功能和造型有很强的联系,为了叙述方便,下文统称为“飞天”。
二、中原文明对开元寺宋代“飞天”造型的影响
中原文化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它发源于河洛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中原文化在我国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在闽南文化中,中原文化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原文化传入闽南,主要靠的是人口的迁移流动。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地区的宗教思想、文化、工艺技术、风俗习惯等就开始持续不断地传入闽南地区。总而言之,中原文化对闽南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中原文化在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的艺术造型和审美理念中,占据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一)“飞天”的性别
泉州开元寺宋代的“飞天”脸庞端圆、高鼻通额、两耳肥厚,“飞天”的这种造像手法与当时泉州佛像造像的手法一脉相承。不管是大雄宝殿的妙音鸟,还是甘露戒坛的飞天伎乐,身躯和上肢都做了几何的概括,这两者的形象都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性别倾向,能感受到“飞天”在造型上既有男性的阳刚又透露出女性的细腻。
开元寺“飞天”这种没有性别之分的造型,是中国佛教艺术中非常典型的中性化的艺术形象。在中国佛教艺术中,这种中性化艺术造型的产生是中原文化中审美取向的展现。中原文化中,人们对美的追求是十分含蓄、隐晦与内敛的,讲求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而外域的“飞天”在造型上不仅性别特征明显,男女形体有着极大的区别,而且对其生殖器的表现丝毫不避讳,这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格格不入。开元寺宋代“飞天”在造型上对性别进行了模糊处理,中和了阴柔与阳刚两种审美特征,是中国人对神的形象的一种理想化展现,是佛教艺术在中国衍变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美学思想观念的展现,传达出中国人含蓄内敛、中和的审美追求。
(二)“飞天”手持“南音北管”
泉州开元寺宋代的“飞天”手持“南音北管”演奏的主要乐器,其中大雄宝殿的妙音鸟手持南音的南琶、洞箫、三弦、拍板等乐器,而甘露戒坛的飞天伎乐则手持北管的壳仔弦、北管笙、北琵琶、双清、单皮鼓、提弦、大吹等乐器。
南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古乐,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北管,曾是中原古韵,最开始流行于江淮一带,现有“天子传音”的嘉名——泉港北管艺人世代传说唐明皇游江南到闽南,亲听北管演奏,并御赐一面小铜锣助兴,北管艺人自豪地称作“天子传音”,并世代传为佳话。[2]“飞天”手持南音北管,既是对中原传统音乐文化的记载,也是对中原文化的展现。而“飞天”手持乐器,同样证明了泉州南音北管悠久的历史,特别是“飞天”所持的曲首琵琶,形制与唐代琵琶十分接近,“飞天”头部向后仰成135°钝角,而另一件乐器拍板(旧称檀板),与《韩熙载夜宴图》所绘乐器一致(如图3)。

图3 甘露戒坛 手持曲首琵琶的飞天伎乐(宋代)
“礼失而求诸野”,南音北管在中原地区难觅踪迹,却在闽南地区不断流传,成为闽南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化,内化为闽南人独特的地域文化。
(三)在开元寺“飞天”的审美取向上,折射出了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最初是指自然界,“人”指的是人类活动,“合一”代表两者的关系。[2]其指的是人类的各种活动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也就是天道,才能获得成功。按照民间的传说,开元寺大雄宝殿斗拱处的二十四尊妙音鸟,代表着中华文化中的二十四个节气,两种拥有着不同翅膀的妙音鸟,分别象征着白天和黑夜,这种说法表现了当地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人们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
三、海洋文化对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的影响
闽南地处中国东南部的东海之滨,宋元时期,闽南的泉州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主力地区,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海洋文化带给当地人开阔的眼界、包容的胸襟以及开明的思想,同时多元文化的传入、融合,也为闽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丰富且坚实的土壤。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不断发展的活力源泉,也对开元寺宋代“飞天”的艺术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飞天”作为斗拱的样式
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飞天”最与众不同的是,开元寺“飞天”并非出现在建筑屋脊之上,而是作为建筑承重的斗拱,兼具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飞天”头顶的宝冠顺势与梁相结合,身体贴合柱身,下身屈膝的造型,仿佛随时会蹬离柱面腾空而起。“飞天”斗拱这种设计意识与印度文明早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古希腊站立的、以头承重的石质女郎柱,到中国于空中横出的、以头托拱的木质妙音鸟的演变过程,其中的文脉(包括对人体的热爱)源自古希腊,经古印度的融合过渡,在中国得到发展。”[3]现在的印度建筑中仍然可以见到以承重形象出现的飞天状构件,泉州“飞天”斗拱造型与阿旃陀第1窟门柱上的“飞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图4),这也间接说明了泉州宋代飞天形象很可能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

图4 印度阿旃陀第1窟门柱(部分)
(二)“飞天”皮肤的颜色
泉州开元寺“飞天”的肤色是深棕色,而中国其他地区的“飞天”大部分都拥有白皙的肤色。泉州开元寺“飞天”这种深棕色的皮肤,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其直接受到印度艺术文化的影响。在印度壁画中,人物的肤色大多都是较为深的棕黄色。这两点都说明了海洋文化对泉州宋代“飞天”造型的影响。
四、闽越文化对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的影响
闽南文化可以说是一部迁徙文化史,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在闽南。历史上记录得最早的一次往闽南地区的迁移是在战国时期,当时越国被楚国所灭,亡国后的越国贵族和平民向闽南地区迁移。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迁移,越文化和闽文化相结合,最后形成了闽越文化。越人好巫术,信奉鬼神的习俗对闽越文化中的民间信仰有着深刻的影响。闽南当地人信仰神佛的出发点,是借用信仰来满足信仰者功利的愿望。其信仰的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实用、功利和世俗的意味。开元寺宋代“飞天”手持的不同器物——南音北管、文房四宝以及五香瓜果,这些都是当地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被当地人供奉给佛,求佛满足他们的心愿。除此之外,闽越文化对开元寺宋代“飞天”的艺术形象产生的影响还反映在以下三点。
(一)“飞天”的蝙蝠翅
开元寺大雄宝殿有十二只妙音鸟长着蝙蝠翅膀,这种形象在中国“飞天”文化中,是天下无双、绝无仅有的。在闽南地区,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蝙蝠纹样被广泛应用在当地传统建筑的装饰上,如门窗、墙面等。在闽南民俗文化中,对“口彩”十分讲究和重视,蝙蝠本身就有着“遍福”的好“口彩”,在寓意上又有吉祥、如意、福气的含义,满足了闽南人内心功利的价值需求,所以闽南人尤为喜爱使用蝙蝠纹样作为传统建筑、家具等的装饰,这也是闽南地区建筑装饰的一大特点,展现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5 印度阿旃陀第17窟顶部壁画天人(局部)
蝙蝠翅膀的妙音鸟,虽然属于宗教造像,但其形象的设计与闽南民俗文化息息相关。蝙蝠妙音鸟满足了人们祈福求满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流露出闽南文化中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不愧是我国“飞天”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飞天”世俗化的色彩
开元寺“飞天”斗拱色彩的运用,具有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闽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多是深色调,深蓝色的海洋、深绿色的山、棕色的土壤等,闽南一年四季如春,红花绿叶,触目所及的是艳丽的色调。环境造就了闽南人的色彩喜好——“闽南地区用色喜用红色、金色和黑色,按当地人的俗语云:红喜气、黑大方、金富贵。以红色作底子象征着喜气,金银色从质地和视觉上都能感觉到财富的重要性”[4]。闽南人生活中常见的红砖古厝、金苍绣、古眠床、永春漆篮等,都体现了这种喜好。开元寺木雕彩绘“飞天”多采用金色、红色、蓝绿、黑色这些颜色进行装饰,这种色调,一方面是使整个大殿的色调和谐,另一方面显露出了闽南人用色的偏好,也是闽南“重商求利”风气的一种展现。
(三)泉州开元寺宋代“飞天”展现了当地杰出的民间工艺——惠安木雕
开元寺“飞天”造像是惠安木雕细腻精湛的雕刻工艺的展现,其在整体形态动作上浑厚典雅,在细微之处也不失精致生动,如“飞天”的耳朵上的花朵耳饰、宝冠上的飘逸的冠带、冠带上的花朵装饰等。
惠安木雕是闽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源远流长,直到现在还焕发着勃勃生机。一位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对惠安木雕有这样的评价:“实在很难想象,这些走出穷乡僻壤的民间艺匠,当他们还带着传统的躯壳前行时,能迅速地完成对外来文化的剔选与消化,并融化于自己的艺术筋骨中,在一个有限的宗教空间,成功进行了多元文化空前融合的艺术实践。”[5]闽南的多元文化从来都不是惠安木雕发展的阻力,倒不如说惠安木雕是在保持传统精髓中,在汲取多元文化精华中永葆青春活力。开元寺宋代“飞天”作为一件杰出的惠安木雕工艺作品,充分显示了宋代惠安木雕工匠精湛的技艺和聪明智慧。
五、结语
站在多元文化的视域下,诠释开元寺宋代“飞天”的艺术形象,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多元文化正是开元寺“飞天”艺术形象折射出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含义。开元寺“飞天”也正是因为受到了闽南地域独有的多元文化的熏陶,才能以这样独具一格的造型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成为中国“飞天”艺术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色彩。
——开元寺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