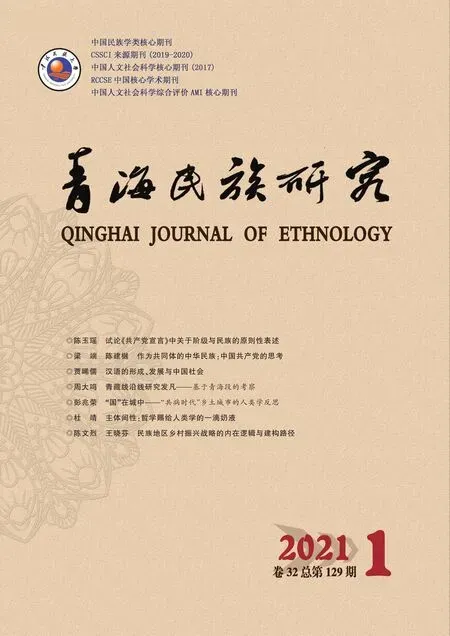“国” 在城中
——“共病时代”乡土城市的人类学反思
彭兆荣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以城市为中心。 具体而言,城市成为疫情的暴发地、传播地、重灾区。 即使到现在,人们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案和举措,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共病时代”,①城市的疫情形势、城市的防疫功能、城市的未来形制等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性问题。 人们也将从世界上不同的城市类型中找到那些重要的、值得传承和发扬的文明因子。
众所周知,中西方的城市形态、贯彻理念和建设模型迥异。 西方的城市(代表性的欧洲城市建制)最重要的原型为“城邦”(city-state),形态和形势上都有“话语强权”(Acropolis)的意思,acro 是至高点,权威;polis 是城邦,与“政治”(politics)同源。 也就是说,西方的“政治”与“城市”存在着发生意义上的关联。 因此,城市成了一种政治话语,海洋拓殖、战争冒险、 商业贸易成了西方城市文明的代表类型,特别拉丁系城邦制。 以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城邦为例,因希腊的土地贫瘠,几乎没有大河流,广泛的灌溉也不可能,粮食生产能力极其有限。 所以,以战争掠夺、商业贸易来换取粮食成为城邦国家最重要的事务。[1]
中国的城市原型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农本之正(政)”成为国家社稷最为重要的政治话语,也构成了“国家-城郭”(“国”有“城”的意思)的基本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守土持家,安居乐业等乡土特征都贯彻在了城市建制之中。 也就是说,我国城市思想、智慧、理念、设计、营建所遵循的是“乡土性”,故笔者称之为“乡土城市”。 这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述《禹贡》中就已奠定的基型。 “中邦”即中国,语义上也有古代希腊的“城邦”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彩色。 但是由于“中国”以农业为背景,与土地形成一种“捆绑关系”,建构“中邦-五服-贡献”的稳定形制。 “贡”为提供贡品;“服”就是提供服务,即贡献粮食。 《尚书·禹贡》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意思是说五百里王城的一百里区域,提供整捆连穗带桔的粮食;二百里以内缴纳的禾穗,秸杆不需要;三百里以内缴纳去了秸芒的穗;四百里以内缴纳带壳的谷粒;五百里以内缴纳去了壳的米粒。[2]这也是最早的“服役”“纳税”和“地租”的原始关系。 其中“甸服”中的“甸”确指王田,泛指天下粮仓。 “畿”也从“田”,指王城四周的地区,故有“京畿”之称。 也就是说,古代的王城以田地为基础而营建,以田畴为范式而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乡土城市。
我们简单地对中西方的城市进行“知识考古”,主要是面对共病时代的城市趋向有一个基本根脉的把握。 当然,也包含着一种批评,即我国的现代城市形制明显以西方的城市模式为样本,很大程度上丢弃了我国传统乡土城市的特点,而我国传统的乡土城市中已经羼入了“防”的功能,包括防御、防范和防疫功能。 因此,我们需要从我国传统的城建形制中重拾那些有价值的“城防性”因子和因素。 这对我国未来的城市发展或将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与提示。
一、城国(郭)的乡土形制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因子和因素完整地呈现在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之中——从宇宙观、价值观到具体的城防功能。 从价值认知看,在“天圆地方”的发生性原理中,地为“方”,“方正”视为“天下法式”。 “国(囗)”之形制为方正,体现了“地方”的基型;从文明的形态看,中式的城郭建制以农田为样本,城郭以“田畴”为基础,这种建筑理念和形制早在周代就已成雏形;从设计建造看,“城”与“郭”互为整体,古代的王城为“内城-外城”的统合。 “城”与“郭”的功能不同,“城”为“卫君”的宫城,“郭”是“守民”的郭城。 古都洛阳城遗址即按照这样的形制修建的[3];从城防的角度看,城郭设计层次分明、区隔开放的建制既传承了传统农耕文明,又符合严格的等级制度。 而且具有明显的防范与疏通的功能性。我国古代也把城市说成“城池”,主要指古代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后泛指城市、城郭。
中国古代的城乡在发轫期具有自己的特点:整体性。 表象上,城乡在形制上存在明显差异,即“城”的方形结构,而“乡”则是更接近于自然旷野的状态。 但是,在性质上却是协作性的,明显的特征是“重土形方”。 这个特点也生动地反映在城郭的建制中,比如“街坊”之“坊”。 自古以来,“神圣”之分,“神”指天王,“圣”指地王,“圣王”即从“土”。 《说文解字》:“圣,汝颍之间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于省吾认为“圣”与“田”“垦”有关。[4]所以,古代的“帝王”其实都是“地王”,比如陶,实为土。 尧帝“陶唐氏”。尧、舜、神农等先祖皆为重土之“王”。
然而,话说到此仍不完整,农耕文明决定了国以农为本,帝王“重土”本为常理。 但我国古代的“重土”之王还需要附加一个条件:建国。 所谓“国”在古代曾经指王城。 也就是说, 为王者, 需要建一个“国”。 以古代的政治形制,圣王也往往是城王,城郭即城国——古代的“王城”形制,“国(囗)”同构。 《周礼》在“考工记”“春官宗伯第三”“秋官司寇第五”等章之开言皆有“惟王建国”之句。 所谓“建国”,就是建立城郭。 也就是说,无城郭者无以称王,其中潜匿着这样一条线索:社稷重农,圣王从土,圣需王城,城乃国之肇基。 这不仅揭示了我国传统的城乡关系不是对峙性的, 而是互为一体的, 也表明 “王”与“城”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国古代的城郭的乡土性与西方的城市、城邦皆存在差异。 因此,有学者把我国古代的城市叫作“城邑”是有依据的。 比如李学勤就认为:“中国的早期城邑,作为政治、宗教、文化和权力的中心是十分显著的,而商品集散功能并不突出,为此可称之为城邑国家或都邑国家文明。 ”[5]众所周知,西方的城乡关系是对峙性的,我国不是,是连缀性的。 城郭与城邑同中有异。 关于“城邑”(基本上是以宗族分支和传承为原则)和“城郭”(基本上以王城的建筑形制为原则),这里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城郭与城邑的一致性,前者主要强调形制,后者主要突出宗族关系。 众所周知,“家国天下”为中式理念,“家国”也表明“国”之“家”性。 即使是王,也以家为世系;第二,二者是不一致的,城郭在古代曾经是按照王城的理念设计营造,就是说,“惟王”方可“建国(城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邑曰筑,都曰城。 ”所以,城邑既可以指王城,也可以一般的城市,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第三,城邑的行政格局,殷商时期,除了“城-邑”外,还有“邑-鄙”的建制。 陈梦家认为,商代的“邑”与“鄙”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行政制度,“鄙”的基本意思是“县”的构成单位。 《周礼·遂人》:“以五百家为鄙、五鄙为县。 ”
邑的本义是众人聚集之地。 《释名·释周国》云:“邑,……邑人聚会之称也。 ”所以,“邑”也是城乡聚集、汇集之所,指城郭及其周边的居民和区域。 《周礼·地官·小司徒》“四井为邑,邑方三里。 ”“邑”的形制事实上与原始部落存在关联。[6]邑又与郊联通,《尔雅》:“邑外谓之郊。 ” 也就是说, 不论 “邑”为“国”、为“乡”,都衍生于农作,与农耕、季节相互配合。 吕思勉说:“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人做领袖。 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 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塾。 当大家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 出去的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 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 ”[7]
此外, 中国又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农业国家,虽然城乡一体,却是等级区隔严格。 城邑也是按照尊卑等级建造的,这与“封建”的意思相一致。 《说文解字》:“邑,国也。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如上所述,“城”之“护君”与“郭”之“守民”,既区隔,又连缀。 城邑的区隔又以方型营建, 形成了完整的城防体系,这也包括了在疾病发生的时候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之原则。[8]此说在初时是根据不同的疾病分别治疗,发展到后来也包括根据不同疾病的分科情况,以及分隔治疗。
概而言之,我国古代的城郭、城邑、邑鄙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之上,以“城-郊-野”为范,在严格封建等级伦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防御和防范建制,包括分科、分区隔离的诊治功能。
二、城建的农耕形貌
总体上说,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的城郭类型与农业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史前的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农耕与水利灌溉相互关联。 有些城市遗迹表明,城内修建的水塘、排水沟、居住区、祭坛、制陶作坊以及水稻田和灌溉系统。[9]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距今约5300~4300 年之间的良渚遗址,既是古代的城郭遗址,又是古代长江中下游稻作文明的产物,其水利灌溉、石制家具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良渚遗址2019 入选为世界遗产名录。
这也表明了我国的古代的“乡土性”早已融入到了城郭、城邑的建制之中,甚至城郭以农田为模型。 具体地说,城郭的营建以井田秩序和格局为样本。 《考工记》有详细的记录:
匠人为沟洫,耜广为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10]
这说明王城的经营乃国家大事,“国”之营建与经营,以井田之制为据。 疏云:“井田之法,畎纵遂横,沟纵洫横,浍纵自然川横。 其夫间纵者,分夫间之界耳。 无遂,其遂注沟,沟注入洫,洫注入浍,浍注自然入川。[11]
古代的王城以“方”为基型,以“田”为样板的设计理念一直成为后世城郭建制的模型。 《周礼·地官》:“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 ”就是说,城中为住宅用地,城外郭内场圃可种植瓜果蔬菜,近郊和远郊地区为各种性质的农田和草地,主要用于生产粮食,饲养牲畜。 城郊外围还有林区,可供应木材,还可调节气候,保持水土。[12]
“方田”的样式与城郭的“街坊”形制也存在关联,成为我国城郭空间格局的具体表现——既是住宅的基本格局,也是住户之间的关系格局。 虽然“街坊”的城市营建传统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方(坊)”的基本形制也在变化。 西方学者施坚雅提出所谓“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个特征,其中就包括“坊市分隔制度消失,而以更自由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所取代。[13]这样的判断值得商榷。 “坊”以“土”为建材,自然会在历史的岁月中坍塌,这与西方的石质建材不同,但“坊墙的倒塌”并不意味着“街坊形制”的消失,更不意味的“坊制的崩溃”。[14]我们仍可以在很多现代城市中瞥见“方(坊)”的原始形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城郭,特别是王城,是帝王、天子栖息居住的地方,也是帝王政治的物质建筑的权力化象征。 比如畿,指古代王都所领辖的方千里地面,后指京城所管辖的地区。 《说文解字》释:“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则曰畿也。”而《禹贡》中的所谓“甸服”,意思是古制称离王城五百里的区域, 也就是王畿外方五百里至千里之间的地区,即京城附近的地方。 这两个字皆从“田”,不仅表示城郭的形貌为方田,也说明京畿也是国家的粮仓(甸)。
《尚书·多方》中有诰令:“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 ”王国治田曰畋。 而“贡服”其实就是纳税。 劳动人民通过田赋的方式“纳税”,“税”即以“禾”“兑”之,这决定了封建统治“苛政”的“横暴权力”性质。相反,乡土社会的却是“自治”的。 这也构成了我国城乡的重要特点,[15]即两套管理体系相互配合。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城郭、城邑建制虽然经过了不同时代的变迁, 出现了区域之间的差异,但城建以乡土为背景,以井田为样板的农耕形制一直未变,成为中华民族城建传统的重要范式。
三、城邑建制中的农时节律
如果说,我国古代的城郭的空间形制与农业的形态具有同质性的话,那么,时间制度也与“农时”历法相契合。 我国古代的朝代更替通常会以新的帝年和纪历来“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开篇“夏纪”之首句为“禹都阳城”,即“夏纪”以“禹都阳城”开始。说明古代的王朝以都城所在为纪录的开章。 接下来的是“《纪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这其实涉及到中国的宇宙观,即从空间和时间开始。 王城都邑也就成为历代王朝开始的象征,无论是续用旧都,还是迁居新城,大都有新的“纪年”“帝号”“皇历”。 这也是为什么《纪年》伊始即言都城。
无论是“时”“年”“号”“历”无不关涉我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 “天时”与“地利”是配合的,“天”管“时”,“地”产“利”。 “利”从“禾”,说的农时作物。 也就是说,我国的传统城市与农耕文明的节律相配合。 具体而言,农耕文明将天时、地利、人和的认知关系反映到节律和时节中,那些与“天时”有关的时令也会反映到城邑建设中。 《尚书·尧典》: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时”与“日”有关。 文字上,“时(時)”、属“日族”,诸如旦、早、晨、旭、晓、朝、暮、晚、昏、明、暗等涉及到时间的文字必以“日”表示,其本义为太阳运行的节奏、季节。《说文解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管子·山权数》:“时者,所以记岁也。”农耕文明的根本就在于与四季(四时)节气相配合,围绕天时而进行各种农事活动,无“天时”农耕文明便无依据。 既然我国“城在农中”,当然,亦秉承农时节律。
比如我国古代城郭中实行的“更”制就很独特。“更”的本义一般认为是更改,又引申指轮换、交替,还可指重新。 “更”是基本形制与“天时”保持一致,也与“农时”保持一致。 古代城郭和宫廷中的值夜,分为五个班次,按时更换,故又引申指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 “更”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时间分制的独特性,也是配合农耕历法和纪时的特别形制;“更”制既是经历、重复,又是变化、更改。 《玉篇》:“更,历也,复也。 ”古代的所谓“三老五更”强调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 其实,所谓“知更者”不啻为“农耕者”。 我国的“历”的典型代表就是农历。
古代记录“时间”的形制一般称为“历”。 通常有两种:歴、曆。时可通用,但侧重不同。“歴”侧重于经历,强调时光流逝。 《说文》:“歴,过也。 ”“曆”从日,与日有关,据“时”而纪,强调纪历。 《说文》释曆:“历象。 ”“曆”的本义指“纪时法”,历本、历法、历书等皆以其为本。 《易·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农耕田作不仅遵守天时之历,也与城郭建设存在关联,其中包括修建的时间规定。 比如《月令》中有关于城郭和宫室修建时间的记述如下:“孟春之月”,②“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 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这些规矩原本只是根据时节和农事的关系而进行的“天时”安排。
不言而喻,“流动性”也是对“时”的一种实践。相对而言,城市的流动性更大,乡村的流动性较小。城市的流动性、移动性、商业性等特性经常是作为乡土社会的对立面出现的。 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的商业性活动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在强调这一点时需要“特别加注”: 即农耕文明在商业贸易方面无法与海洋文明相比况,却未必不发达——流动性并非说明“发达”的唯一理由。 封建社会的城郭建制从来就不缺乏流动。 《史记·货殖列传》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只是,中国的城邑的流动性、流通性、商业性总是与农业的发展相互印证。 特别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商贸活动也会快速成长,交流也越来越显得重要。 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市”,即商业交易活动。[16]《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之也。 市有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流动性”与农时存在关系,这与西方城市有着重要的不同。
“天时”与“天象”是相互配合的,就像时间与空间相互配合一样。 “王”曰“天子”,建造和居住也包含着“天象”的因素,从古代的营造学而论,王城如此,民居亦然。 比如中国传统的建筑学有一套完整的相宅术,无论是阳宅和阴宅之“相(象)”都必须符合天象,同时在此基础上的天文历法。 比如确立“四方”之象,与天象星宿必有关系。 古人把二十八宿看作神灵,在古代的形象图上,把东方七宿连缀起来,形成龙的形状,南方七宿形状为朱鸟,西方七宿的形状为虎,而北方七宿则为龟。 《三辅黄图》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17]这涉及到了中国的营建方位体系:“当方位选择得到认同, 方位体系便形成了, 这个传统一般不易发生改变。 建房、建城、筑墓,都会以认同的方位体系为依据,这样的体系可以代代相传。 《周礼》开章所说要辨别方位,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18]
概而言之,我国传统的城市建制的特色非常明确、明显,反映在中式的宇宙观,特别是时空制度之中,“天时地利人和”不啻为圭臬。 同时,城郭配合农耕文明中的时节。 这也是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文化遗产。
二语报纸专栏评论写作互动元话语使用考察 ……………………………………………………… 鞠玉梅(4.37)
四、亮起红灯的城市
此次新冠疫情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城市为重灾区。 纽约、巴黎、柏林、马德里、罗马、伦敦、莫斯科等皆没能幸免。 这促使我们对“城市话语”的重新反思和反省,特别是西方城市和城市形制。 如上所述,现代的西方国家体性与古代的城市(城邦)存在着基因的关联。 在城市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城市”是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乡村是“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城市是中心(country),乡村是边缘(countryside)。从这个层面来说,城市疫情的问题也是历史和政治问题。 其中有一个重要形制背景:西方传统的城乡是“对峙”性的,以往这种政治权力格局更多只是体现的政治和管理方面,而此次疫情则扩大到了疾病的传播方面。
其实,西方的学者早已注意到了现代城市危机中的“被遮蔽”的情形,并为之敲打了警钟,《没有郊区的城市》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以美国的城市为例,把美国城市的经验教训归纳了24 点, 其中列出了美国一些著名和重要的城市人口变化数据,以说明这些城市已经进入到了“非弹性”③的“极限点”,属于“没有郊区的城市”形态。[19]虽然这只代表西方学者中的部分观点,但作者提供的材料和数据是可信的。 这些材料和数据表明,美国的城市发展处于危机之中。 此次疫情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正是纽约。
相比较而言,世界上的城市都有其共性,但中国的城市传统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 除了上述所强调的城乡关系与西方的城乡关系的差异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式的城乡关系不是“对峙”的,而是“连缀”的,这也反映在了城防方面。 《礼记·礼运》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城墙之于城的关系无疑有一个不言而喻的解释:防御和防范。 有人认为城墙起源于环壕聚落,属于部落社会, 与农耕时代初期对土地资源的争夺有关;有人认为城墙的出现是聚落社会向城邑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 有人认为城墙的出现是防洪的需要;还有人认为城墙具有宗教性质;更有人认为城墙是为了区隔财富和人群的等。[20]上述观点,除了宗教性功能有些特殊外,其余都含有“防范”的功能,无论是防敌、防匪、防洪、防盗、防疫、防秽,还是防僭越。也就是说,我国古代的城邑形制中既是隔(独立的)又有疏(交流的),“城邑”二字可为注解。
值得一说的是,我国的城乡协同还包括“城镇-乡镇”关系:“镇”既可与城连缀,又与乡相连。 “镇”的本义为“镇压”。《说文解字》:“镇,博压也。从金真声。 ”《周礼·大宗伯》:“王执镇圭” 意指威镇四方。《周礼·考工记·玉人》:“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子代天巡牧镇守。 可见“镇”的原始意象是以特殊的城郭营建工具用于“镇守”“镇定”“坐镇”等,以维护安全。 《广雅》:“镇,安也。 ”“镇”原来就是负责防卫的军事建制, 后来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连缀单位。 笔者以为,中国的“城-镇-乡”是依照“城-郊-野”的形制认知逐渐形成的。 这种形制的防范性,无论是御敌、防匪、防灾、防疫都接受过历史的考验。
相比较西方国家“没有郊区的城市”,我国“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功能上,“郊”是城乡的中介,紧急的时候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无论是御敌、抗洪还是防疫。 礼仪上,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国家大事的“戎”在于保家卫国;“祀”则是作为礼仪之邦的祭祀。 “郊(祭)礼”是古代帝王最重要的国家礼仪:即帝王祭祀天地之地。 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郊谓大祀,祀为群祀。 特别是祭天,中国古代君王举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年中某些重要的时日,君王带领三公九卿等诸大臣依据礼法于国都郊外祭祀上天,感恩上苍,为百姓和国家祈福的一种祭祀活动。 管理上,“郊”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连接城乡之间的区域,而是组成了“家国天下”体系的区域与行政划分。
概而言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和灾害频发的国家。 所以,传统的城市建制已然将城防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乡土性背景也精巧地融汇在了城防的建制之中。 近代以降,特别是当代的城镇化发展,有模仿西方的城市建制的趋向,需要警惕,同时也嘱我辈将自己优秀的城市遗产传承下去。
五、结 语
现代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快速移动和流动,这成了此次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冠疫情的“无形宿主”。 世界各国制止疫情传播的最常见方式是“禁止移动”——特别是停止、限制“人的流动”,诸如封城封国、停航停运、停工停课、限制社交、居家隔离等成了最通用的手段。[21]而疫情的主要发生地正是城市,这警示我们,当我们热衷于讨论现代化城市的诸多优点时,却大多忽略了“现代性”与“城市病疫”的关系。 所以,城市的疫情防范也将成为后疫情时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快速地对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建设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加速中国特色“乡土城市”的建设。 其中包括重要的几个方面:第一,突出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城乡特色,创立“乡土城市”的建制;第二,恢复和建设城市中的类似于“井田”式的空间格局,保证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分隔-交流渠道,特别在疫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进入分区隔离状态;第三,恢复和强化“城-郊-野”的传统,以保证在防疫上的缓冲区域和通道,化密为疏;第四,恢复和强化传统乡村的“自然村”形制,以保证在疫情时期仍然可能“各自为阵”地进行生产,不至于让生产完全停滞。
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城市重灾现象已经将共病时代的城市防疫问题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中国的传统城市建设与营造也或将从单纯的城市遗产上升到有助于保护人民生命的高度。 如果说“中医” 对此次我国疫情的防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中邦”式城建智慧或也可以在共病时代起到相应的作用。
注释:
①“共病时代”是美国学者芭芭拉·特纳森-霍洛威茨 凯瑟琳·鲍尔斯合著的书名《共病时代: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的惊人联系》,三联书店2017 年版。
②农历年分十二月份,即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月、腊月。 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 每三个月为一季,即孟、仲、季。 所以,孟春即指正月,依此类推。
③城市的“弹性”和“非弹性”被认为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生命力的重要依据。 城市弹性大指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有很多空地可以用来开发建设,城市政治和立法则以拓展空间为目标。这类城市被称为“弹性城市”。反之,城市的建设密度已经超出平均水平的传统城市,而这些城市因为各种原因处于无法拓展其发展空间的为“非弹性城市”。见[美]戴维·鲁斯克《没有郊区的城市》,王英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