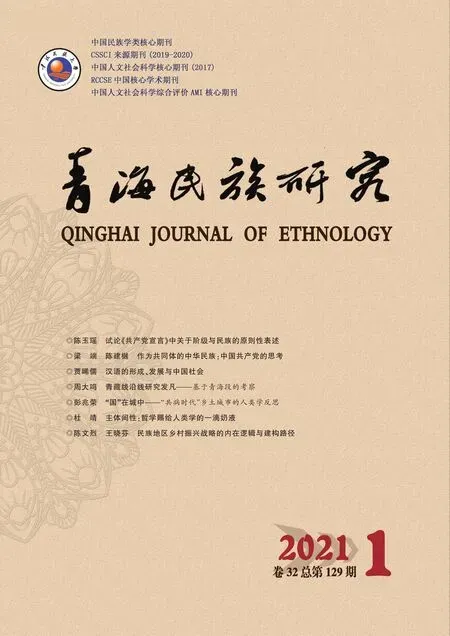象征符号与文化调适: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发辫研究
完麻加 吉毛措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一、研究视角与问题的提出
身体作为自然之物, 本身没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但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时空中,身体及其头发、手等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寓意, 并成为表达身份归属、政治认同、权利等级和族群边界的符号。 西方学界对身体的隐喻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挖掘,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和《疯癫与文明》[2]等著作,将犯罪的惩罚与规训、精神病学、医学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结合起来,从“身体”的角度观察世界。 最先揭示头发的象征意义的是人类学家利奇,他在《头发之无意识的意义》中认为“剪发象征着阉割、性分离”[3];在《巫术之发》中从社会仪式的角度分析了头发的象征意义,认为剪发象征着 一 种 社 会 地 位 的 转 变[4]。 后 来 霍 皮 克(C.R.Hallpike)提出了不同于利奇的观点,认为“发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象征, 长发象征着置身于社会之外,而剪发则象征着生活在社会之特定纪律的统治之下”[5]。 威廉森(Margaret Holmes Williamson)对伯华特人的发型的探讨和奥贝塞克对斯里兰卡女性修行者发型和头发分析等成果也从象征或解释的层面分析了头发与发型的意义[6]。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头发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研究。 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文化中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毋敢毁伤”的礼俗,这是体现“孝行”的重要方式;而且华夏居民认为蛮夷戎狄与自己的发式不同,将此作为区别“文明”与“野蛮”、“我族”与“他族”的文化标志。 清朝入关后,不同的发式象征着国民身份的不同归属[7];在清末民初,剪辫不仅被赋予坚定革命立场、 舍弃旧习俗社会含义,而且还是民族主义建构的主要路径[8]。 有学者发现,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头发样式象征意义不同,“留辫子象征保守,剪辫子象征革命;短发、平头象征汉奸头;长辫子和短发象征因时而变的审美趣味;阴阳头和光头象征惩罚罪人”[9];而且“在同一族群之内,同一象征(头发)可能因男女不同、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区别;也有可能对社会和个人有不同的意义;也可能对不同的人(如性别、职业)有不同的意义。”[10]也就是说,这种生物的身体空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象征符号的“多义性”。 虽然国内学界刚刚开始探讨和阐释头发等身体空间的象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藏族文化是中国一体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藏族从性别角色、社会地位、僧俗身份、人生礼仪等层面对头发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 此方面的研究最早有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在甘南夏河调查撰写的《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和《藏民妇女》[11],近年来刘军君[12]和 看本加[13]等人对藏族 关于 头 发 的 文 化 进 行了比较深入的发掘。 但除了上述成果,对此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且多数停留在“怎么来的”和“什么样的”等静态方面,缺乏对头发的象征意义及发式变迁过程的动态研究。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佛教传入吐蕃后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 产生了丰富的象征符号和意义体系,如宁玛派俄巴①的身体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尤其是他们的发辫作为群体外显的文化特征被不断再生产。 然而,与此相关的学术命题仍未被学界广泛关注。 鉴于此,本文以宁玛派俄巴的发辫作为切入点,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俄巴发辫的象征意义及变迁, 以期能揭示宁玛派俄巴在历史中社会角色的构建过程。
二、“俄拉”及其历史变迁
佛教僧人入寺后举行弃世为僧、消除烦恼和错误习气的“剃度”仪式,此项“通过仪式”象征身份的转变和再生。 佛教经典教义认为,头发象征人间无数的烦恼、恶习和贪、嗔、痴“三毒”,僧人消除恶心、烦恼和“三毒”方能专心修佛。 据史籍记载,在释迦牟尼时期,印度出现了许多其他教派,而释迦牟尼为了区别佛教与其他教派,从外表上剃头表现佛教徒的身份。 因此,僧人剃度是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宗教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表征。 佛教传入吐蕃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过程,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才具备了佛、法、僧三宝。 当时出家为僧的“七觉士”也按印度佛教传统举行了剃度仪轨,表明自己“身心向佛”。 但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僧团“俄巴”却是“身披白衣蓄发”,与学习显宗的“身披袈裟剃发”的出家僧人之间有一定的差别。
“俄巴”即密咒师,在史料中这一群体早期的记载非常有限,笔者在《宁玛派密咒师的起源与发展》[14]一文中做了初步梳理。 到了后弘期,由于各教派间的互动,民间俄巴对自身文化做了调适,包括在身体空间、宗教服饰和宗教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再造,尤其是他们的“俄拉”最具代表性。 俄拉是藏语,其中俄指俄巴,即宁玛派密咒师;拉指拉巴,具发辫之意。 俄拉即宁玛派俄巴的发辫或密发,藏语中对俄拉还有“托觉合”“托凑”“托祖”“强洛”等称呼。 托觉合、托凑、托祖指头发合拢后,置于头顶盘发成髻;强洛指对头发不造作、自然垂落于后背,不仅指宁玛派中修炼密宗的俄巴,也指其他教派中以居士身份修习密宗之人。 宁玛派俄巴群体以蓄发和举行灌顶仪式而转换他们的身份。 俄拉是宁玛派密咒师的身份标志,具有区分群体认同的功能。
密咒师蓄发的最初起源和发髻盘式在《佛教密宗法器简论》 中有记载:“按佛祖释迦牟尼佛的教义,虽为表达自己的佛法比外道蓄发者的法更为殊胜,以及体现弃世离俗的思想而剃去头发、削掉胡子。 但出现了安扎巴德法王和喀什米尔的达瓦桑波等俄巴。 为了他们的份额和需要,在新、旧密中赞许英雄不剪头发为装饰。 蓄发盘在头上象征法我无别,发辫向右缠起代表男勇士,向左缠起代表女英雄。 蓄发盘在头上的方式有束发、束一半和发髻竖立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把所有的头发系在头上,且发尾不外露而成小圆体;第二种是把头发的一半系在头上,一半垂落在后背;第三种是把头发自然垂落,从头顶取出三、五股头发结成一团后成圆状并系在头顶。”[15]该记载说明追随释迦牟尼佛者应剃度,但为了在家修行者即俄巴的需要而允许不剪头发,也规定了盘发的三种样式。 这对佛教中允许“蓄发”提供了历史依据。 然而,密宗的许多仪式仪轨在经典和历史中很难得到考证,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质疑过其权威性和正统性。 因此,追随旧密者以掘藏、故事、神话等方式编织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不仅把俄巴蓄发的历史文化追溯到印度,而且为藏地居家俄巴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宁玛派文献中对“俄拉”起源的记载非常有限,这些文献表明在吐蕃时期赞普等上层贵族就有蓄发、盘发的传统,而且苯教神职人员也可能需要蓄发。 上层贵族蓄发盘发的传统见于《白史》,据记载:“松赞干布以红绢缠头,是波斯风尚。 又言,阿里拉达克处,直至现在传为法王之后裔,彼等遇新年等节令,则其所着衣物,谓是往者之服饰,称赞夏的红帽,其顶细长,上角有一阿弥陀佛像用红绢缠绕,绢端前面交错。”[16]这一记载也得到了敦煌壁画中赞普画像的证实,“第159 窟的壁画上有赞普像,画中赞普站在一块垫子上,……赞普头戴的红色高帽像是用红布之类的缠起来的,有红色缎带,帽檐下缠有白布,白布下面的头发齐耳跟打成发结”[17]。 这些材料证明,吐蕃时期已有赞普把头发打成发结,并用红布等缠于头顶的传统。 这与宁玛派俄巴蓄发,并用红、 黑布缠绕于头顶的传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苯教中也有蓄发成髻的传统,尤其作为修密者一定要蓄密发。 据传成书于公元8 世纪的《扎巴林扎》中载:“为了表彰苯教徒,身披虎衣,发髻盘头。 ”在《苯教源流弘扬明灯》中亦载:“晚年,芭敦巴勒却想出家为僧,于是就找到苯教高僧绰仓珠拉。 当他向绰仓珠拉表明自己的意愿。 当绰仓剃发时,在芭敦的每根头发上显现忿怒神。 故称,若你出家,将会侵犯威尔玛神灵。 你还以俗家居士身份弘扬教法吧! ”[18]引文中的芭敦巴勒是生活于十一世纪中期的一位苯教密宗师。 因此可知,至少在十一世纪,苯教传统也认为修密者需蓄发受灌顶,且认为头发象征本尊神。 目前,佛苯两教中蓄发受灌顶传统的来源尚无定论,也无法考证。 但从零散的史料分析,佛教在吐蕃立足前,吐蕃上层社会和斯巴苯教传统中就有蓄发或盘发成髻的发式, 象征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具有神圣或世俗层面的不同隐喻。
佛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白衣蓄发类俄巴群体得到了发展,他们对发辫赋予了佛教化的解释。 如我们从史料记载和现存的壁画、唐卡等图像媒介来看,宁玛派中的掘藏师和大成就者等重要历史人物可结发成髻。 他们成髻的方式一般有头发系在头上,且发尾不表露在外而形成小圆体式的发髻或一半系在头顶一半垂落在后背以及头发垂落与后背,在头顶取出三、五股头发结成一团后成发髻等三种。 这三种发髻方式与《佛教密宗法器简论》所载内容一致。 俄巴从藏传佛教旧密的观念出发,解释发辫是佛教文化中的“四自然”的具体表现。 自然就是保持原型,不造作。 那么头发作为四自然之一,应保持原型,不造作。 也就是说头发保持自然散落与后脑而不成发髻。 随着社会和宗教的发展和变迁,出现了头发盘绕在头顶以及没有束发、束一半或发髻竖立头顶等成髻方式。 其中普通俄巴只把发辫盘在头顶,而掘藏师、大成就者等著名人物才享有头顶盘发成髻的权利, 以示殊胜的身份和地位。笔者调查的一位堪布说:“按传统来讲,俄巴的俄拉是自然散落的,不应像现在这样缠绕在头顶,也没有发辫按顺时针缠绕代表智慧和逆势针缠绕代表方便的解释。 托觉的历史传统可能比较悠久,是用俄拉缠住金刚或经书后牢固的放置在自己的头顶。 当然,只有大成就者或著名的掘藏师才有资格成髻为托觉。普通俄巴把发辫缠绕于头顶的传统是后期再造的。这是由于居家类俄巴平时从事生产劳动, 为了方便才把俄拉缠绕在头上, 并用红色或黑色的布袋来保护它。 ”②这是宁玛派精英从自身角度对俄拉及其变化做出的解释。 但从历史上各教派互动关系来看,制度化宗教占主导地位以后, 试图整合和改造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民间宗教或信仰; 而底层的民间信仰又尽力靠拢制度化宗教,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 宁玛派俄巴在民间为信众举行驱邪避灾、招福招财等仪式,在民间扮演人神之间的中介, 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传承者。 宁玛派俄巴与其他教派僧人具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其“俄拉”作为身体空间的文化标识,有别于剃头为僧的文化传统。 所以,宁玛派俄巴的俄拉从最初披散的状态改为缠绕在头顶, 尤其用俄拉缠住佛像、经书等后置于头顶,是俄巴主动向其他教派靠拢努力将自身正统化的一种策略。
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民间的宁玛派俄巴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转变, 他们对俄巴的蓄发及盘发等也进行了文化重构。 近代宁玛派著名人物杜炯·久智叶西多杰提倡头发扎于后脑,并经常梳洗发辫,“俄巴无力打理密发,那么在上师前接受灌顶后,不可剪发但可经常梳洗,且要使发辫干净、 整洁。 这是掘藏师杜炯久智叶西多杰的传统”[19]。除他之外,德关钦则扎西贝觉(1910-1991)、敏珠林赤钦德关钦则扎西(1930-2008)等宁玛派著名人物也把俄拉扎于后脑。 这些重要人物的新发式对民间普通俄巴的蓄发、盘发带来的很大影响,尤其对年轻俄巴来说, 他们乐于接受头发扎于后脑的艺术家形象。 我们在俄巴聚集区调查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俄巴不再把俄拉缠于头顶, 而像女性或艺术家一样把俄拉扎在后脑,并经常梳洗,显得非常时尚。这种新的蓄发方式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
三、蓄发仪式与象征意义
俄拉对宁玛派俄巴来说是最神圣的象征符号,也是确定身份的重要标志。 一位俗人想成为俄巴,需蓄发、受灌顶。 因此,蓄发仪式是俄巴转换身份仪式过程,是世俗的身体空间过渡到神圣的身体空间的“阈限”阶段。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特别希望能亲身观察蓄发仪式,也跟多位报道者嘱托过此事,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如愿。 因此,我们只能结合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阐述宁玛派俄巴的蓄发仪式过程及其意义。
当有人想加入俄巴群体时, 首先要寻找师傅,在师前学习宁玛派基本经典教义,并开始蓄发。 当因缘时机成熟时,师傅请一名金刚上师为弟子举行灌顶仪式。 举行仪式时,首先受灌顶者需清洗头发上的污垢。 接下来供奉曼扎,供奉上师,并向上师宣誓自己一心修密,严守戒律的决心。 上师讲述旧密的殊胜之处及需恪守戒律的重要性。 同时,上师祈祷本尊神护佑他的求佛之路,也委托本尊神等神灵在其不守戒律、对佛法的不尊时给予严惩;其次,上师向受灌顶者赐予加持之水,让他的身心语得到神灵的加持;最后,依次进行外部宝瓶之灌顶、内部智慧之灌顶、密部殊事之灌顶和甚密语言之灌顶等四灌顶。 受灌顶者接受的是各自本尊神的无上灌顶,而本尊神以受灌顶者的五行八卦等为依据进行选定。 因此,每个人的无上灌顶又因各自修行的本尊神不同而有所区别。 灌顶仪式对俄拉赋予了神圣的寓意,是俄巴文化中的“四自然”之一。 自然之头发为发辫、自然之容器为颅碗、自然之衣着为白色、自然之心地为质朴。 头发作为四自然之一,必须保持原型,不造作。 “四自然”是宁玛派“本源清净”“自然圆成”等核心哲学思想的外化。
俄巴接受灌顶仪式后,俄巴的每一个头发上有无数位本尊神以及空行母等密宗神灵。 他们将头发盘绕于头顶,象征敬仰神灵,象征自己与本尊神灵无别。 《密宗服饰与法器》中说“头顶缠发表示佛我无别”[20],《发辫简论英雄之吼》也载“娘氏之子卓卫贡宝向迦湿弥罗释迦室利表明在他跟前剃头出家。班智达说,你按此身份传法更为殊胜。 可他强烈要求剃头,并准备剪发时,剪刀被折断而未能剃发。 班智达又说, 你的每根头发上显现无数位本尊神,不能剪发”[21]。这些记载都表明俄巴的密发象征着本尊和各种忿怒神。 修密者要敬仰和呵护发辫,绝不能玷污和污秽。 有研究指出:“(俄拉)的象征意义说是礼敬宁玛派上师,并说五十八股辫子象征五十八尊愤怒神, 发辫四周蓬松的头发代表无数空行母,乌黑的发辫是佛的法身, 发辫上的饰物是佛的报身,发辫的每一根头发则象征佛的化身。”[22]有研究还指出:“密咒师开始蓄发时需要经过上师或活佛诵咒加持灌顶,发辫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神圣的,终生不得剪断。 除非在拜见上师、活佛或堪布时才可取下发辫,表示朝拜和尊敬。 ”[23]笔者在调查时所有报道人也强调,接受灌顶后俄拉上有无数位空行母。 剪断头发相当于杀害了无数位金刚萨埵,此罪孽是无法忏悔的。 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都表明,俄巴在上师前接受灌顶、蓄俄拉后再不可剪短,也不能在公共场合随意拆散。 他们只能在拜见活佛、堪布以及举行特殊法事仪轨时才能取下俄拉并缠于脖上。 18世纪热贡地区的仁增华丹扎西说“无发辫的俄巴为不伦不类者。 ”[24]仁增南卡嘉措也说“出家为僧者需剃头,修行密法者需蓄发。”[25]在我们调查时,许多地区的俄巴都认为灌顶蓄发对俄巴来说非常重要和神圣, 象征着本尊和空行母等诸佛与自己无二无别;如果不接受灌顶,不蓄发留辫则视为不合格的俄巴,且经常轻视和排斥此类俄巴。 以上论述表明,俄巴的发辫有不同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神圣的象征意义。 因此,我们才能在藏族聚居区看到常年蓄发的俄巴。 从世俗的角度审视“俄拉”,可能有人会视为肮脏、危险或异类。 但对俄巴来说,“俄拉”象征和表达着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是社会情感的交流媒体。
总之,发辫是俄巴的身份标志,蓄发后不许剪发。 这一传统在宁玛派教义中有神圣的象征,在不同的时空中从未改变。 “不同的人类群体和同一族群内的不同个体,以人的自然产物(头发)为材料,建构不同的文化象征,为的是彰显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意义。 ”[26]借助象征可以使个体、群体或社会组织融合在一起,并使人们顺从和忠诚,同时也激起对敌人的愤怒和厌恶感。 俄拉作为俄巴共有的一种象征符号, 为俄巴赋予了一种神圣性而脱离世俗生活。 这是确定他们身份的文化符号,也是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象征符号。 但是,前文指出,发辫的成髻盘发方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变迁。 众所周知,符号的象征意义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其原有的意义。 有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人们遗忘,有时人们又重新选取被遗忘的象征符号,但却给它赋予与原始意义不同的解释。 从“俄拉”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俄巴继承俄拉的原始意义还是丢弃,或者选择性的重构新的意义系统,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做出抉择。
四、 结 论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文化的传承者。 他们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在闲暇或特定的时间内才举行仪式活动。 当村民们遇到红白喜丧而受邀时, 为信众举行各类仪式活动,帮民众排忧解难, 所以在民间具有广泛的信众基础。 这类现象在恪守戒律、系统学习藏传佛教经典思想的僧侣眼中视为“不正统”或“另类”。 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宁玛派俄巴文化中不同于其他教派的部分被改造,努力向佛教教义思想靠拢,试图将自己正统化。 白衣蓄发作为宁玛派俄巴显示自己的象征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不断地改造,也赋予了新的文化意蕴。 宁玛派俄巴的俄拉是与宁玛派信仰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象征符号,具有神圣的文化内涵。 对俄巴来说是确立身份标志的符号,也是一种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象征符号。 在历史上,作为个体的身体经常成为争夺政治、权利、身份的焦点,从而成了具有社会性的身体。 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各教派间的互动深刻影响了彼此的文化传统。 俄拉作为俄巴外在的象征符号,在被其他教派所排斥的背景下, 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传统文化,对继承了吐蕃贵族和苯教传统的俄拉也进行了佛教化的解释。 随着社会的发展,俄巴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年轻一代的俄巴把头发扎在脑后,打扮成具有“艺术家”特征的形象,这是时代给身体空间留下的烙印。
注释:
①宁玛派俄巴的主要特征是娶妻成家、扶老养儿,平时参加生产劳动。 在特定时间或休闲时举行法事活动,或在民众邀请时到百姓家中去念经做法事。 俄巴在民间还称“阿巴”“俄巴”“俄华”“宦”“宦爹”“唤”“奔”“本”“本本子”“本布子”“棒棒子”“阿弥”“吾坚巴”等等。
②诺布堪布,笔者于2014 年4 月8 日访谈。 该引用为访谈内容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