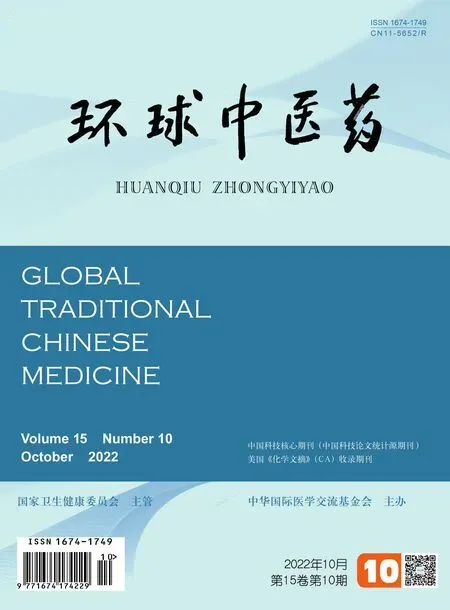基于“平正轻灵”浅析花类药调理脾胃枢机之妙用
范乙林 何聪 王晓素
脾胃者中州之府也,其主枢机。《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临证指南医案·不食》载“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皆强调了中土脾胃的重要性。脾胃升降协调,枢纽司之有度,则四象斡旋,五脏安和。吴鞠通《温病条辨》有言“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结合历代医家的临证经验,可以发现“平正轻灵”的辨治法度在脾胃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花类药多性味平和,芳香灵动,与脾胃之性甚为贴合,以其调理脾胃枢机常有妙用。故将之经验总结,以飨同道。
1 脾胃枢机健运有常是五脏安和的关键
脾胃者谓之五脏中枢之机要。“枢”者枢纽,“机”者气机。脾胃作为人体之“枢机”,可联系上下,沟通表里,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肩负着荣养五脏,调节周身气机,维护五脏安和的重要职责,诚如《素问·经脉别论篇》所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脾胃“枢纽”司者有度,生理功能运行正常,则后天之气充足,五脏六腑秉脾胃之气不断充养,生命活动得以继续。即有《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所言:“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旺,则能食而肥。”
脾胃居中央以溉四傍。“中气为升降之源,脾胃为升降之枢轴”,脾气升发,则肝气得以升发,肾水随之上济;胃气下降,则肺气能够肃降,心火随之下交[1]。路志正教授[2]亦提出“持中央,运四旁”。如肝与脾胃之病关系密切,肝与脾胃土木相乘相侮,互为制约,临证常见肝气郁结或肝阳上亢,克制脾土,使脾胃功能失调。“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金匮要略》),临证之小柴胡汤即治肝实脾之典型方剂。又如肺主气,主宣发肃降,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揭示了肺与胃经脉络属关系,依“肺胃相关”之理,临证治疗肺病可用运化脾胃为手段,常有培土生金之法。
《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载:“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更是体现了临证顾护脾胃之气的重要性。脾胃枢机受损,机体气血无以化生,则难以维系五脏六腑的正常生理功能,故而临证应时刻谨记脾胃枢机健运有常为五脏冲和、气血和调之关键。
2 “平正”是协调脾胃枢机的基本理法观
“平正”二字可从“脾胃衡平之态”“五脏冲和之态”“循法达变之治”三个方面论述。
2.1 中焦非平不安,治需顾护脾胃衡平
脾胃衡平是指在治疗脾胃病时应注重顾护脾胃枢机的衡平状态,正如《温病条辨》中所言:“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脾胃是人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篇》)。两者同居中焦,共为后天之本,承担“中央土以灌四傍”的职责。脾胃之气充盛,纳运功能平和,食饮谷物得以源源不断地化生为水谷精微,人体气血津液得以生化有源,五脏得以安和。
然脾与胃虽俱为中州之土,其职能亦有差别,“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临证指南医案》)。脾土升清,主司运化,水谷之精微得以布散;胃土降浊,主司受纳,水谷之糟粕得以下传。脾之升有赖于胃之降,胃之降亦有赖于脾之升,两者既相辅相成,亦相反相成,集对立统一、互根互用于一体,共同完成充养全身的任务。
故调理脾胃需顾及二者之间平衡稳态,契合其升降相适、阴阳相成、寒温相宜、纳运相成、燥湿相济、虚实相允的特性,临证不可一味单纯补脾胃,应以达到阴阳平秘、寒热平调、虚实平允、气血平和的“以平为期”之态为目的[3],诚如吴鞠通所云:“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使阴阳两不相奸为要。”
2.2 四象皆有脾气,调脾胃兼及五脏冲和
五脏冲和是指在以调补脾胃为中心的基础上,亦需兼及五脏功能的冲和平稳。所谓冲和,即为脏腑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共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
脾胃居五脏六腑的中心,为中枢之官,心肝肺肾生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脾胃水谷之气的充养,而脾胃作为“升降之枢”职能的体现,亦有赖于心肺肝肾升降浮沉的中和调平,乃有《景岳全书》所载:“然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胃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
治五脏以调脾胃[4],是调脾胃以安五脏的补充,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故在脾胃病的诊疗上,要注意把控脾胃与其他脏腑的主次与平衡关系。例如:脾胃的升降有序离不开肝之疏泄,《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土得木而达。”若肝气失疏,郁而横逆,犯及中焦,是导致脾胃枢机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临证治法选择上需体现“醒胃必先制肝,治肝可以安胃”的原则。脾胃的升降和畅亦有赖于肺之宣肃和谐,肺居至高,为五脏六腑之华盖,上者下行,肺气肃降有常利于胃气的通降有节[5];脾之升清依靠肺气之宣发[6],“上焦如雾”,才得以布散水谷精微于全身,诚如喻嘉言所云:“凡脏腑经络之气,皆肺气所宣。”
2.3 谨记三因制宜,临证宜循法达变
循法达变是指在临证治疗脾胃病时需要循法守度,达变就新的中正之道。循法守度是指在调理脾胃的过程中,需遵循《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之法,在明确探求与把握脾胃疾病病机的同时,做到守法守方,此即中医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的精髓所在[7];然而疾病的发生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需根据“天时、地利、人和”角度综合调治,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而宜三因制宜出发适当调整用药,才可奏效甚捷。治病如行军打仗,“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寤言二·迁都建藩议》)。医者需要站在至高点全盘把控疾病演变过程,做到知己知彼,病虽千万,然理相同,正奇结合论治疗效方可显著。
3 “轻灵”是调理中州的独特方药观
3.1 用药需轻清和缓
“轻”即轻清、和缓。用药轻清,一来药量常不大,药味常不多,但用药精当,直达病所,既能发挥治疗作用,又不会留邪伤正。如防风、升麻、柴胡之属稍许用药即可达到升举清阳之功,清阳得升,浊阴得降,升降相宜,带动全身气血运行,谓“四两拨千斤”。二来用药柔和轻清,不过用重镇、滋腻之品,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常用药多为轻清之品,如人参、茯苓、薏苡仁、麦冬、半夏、石斛、陈皮、桔梗、生姜等[8]。
用药和缓,指常用甘淡中庸之品缓图之,不急功近利,其用药看似平淡,实有长者风范。如钱乙治疗小儿疾病,用药常以丸、散剂,药性缓和而起沉疴,小儿稚阴稚阳,非缓和之药无以护其娇嫩脏腑。脾胃之病亦有同理,其中土已伤,若药石峻猛,再添负累,治病必然事倍功半。海派名医丁甘仁,其创建的丁氏学术流派在江南医界颇有影响,丁氏宗法张仲景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用药轻灵,以轻去实,所用药物药性大多平和,除阴阳偏颇之甚者鲜用附子、干姜、黄连、黄柏等大寒、大热之品,热则灼阴,寒则败胃,均为脾胃增添负担,两不相宜[9]。
3.2 组方宜灵活变通
“灵”指灵巧用事,遵古而不泥古[10]。不拘于古方、古法或某一经验方药,临证圆机活法,灵活变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伤寒论》之经方往往除记载本经正治外,还着重论述类证、变证、坏症等,比如桂枝汤证兼有咳喘,可加厚朴、杏子;太阳病,但桂枝汤不解者,配合针刺风池、风府可助药力等。皆证明临证变通之重要。
现在,传统中医学与西医学不断交流汇通,让如今传统医学的“灵”不仅包括灵活变通、不拘古方。医者可以借助科技手段进一步加深对疾病的认知,例如上皮内瘤变、肠上皮化生等“望闻问切”不能发现的危险因素可以被早发现、早治疗,组方不只局限于中药,在完善相关检查的基础上,必要时中西药联合或相继使用亦可互相增效。不拘中西之别,不碍门派之见,圆机活法,择其善者而用,为如今传统医学组方之“灵”。
4 花类药平正轻灵,在调和脾胃枢机中多有妙用
脾以运为健,胃以通为补,脾主升,胃主降,脾喜甘温刚燥,胃喜甘凉柔润。用药时,升降润燥寒热均需兼顾,故曰“治中焦如衡”,以下从“平调气机之周流”“平衡中焦之寒热”“平和戊己之润燥”详述花类药调理脾胃之妙用。
4.1 平调气机之周流
平衡气机,一者调理脾胃本身之升降,使脾胃升降有序;二者使肝肺气机左升右降正常,龙虎回环井然有序[11]。花类药可通过升清降浊、疏肝理气、宣降肺气以平调气机之周流。
葛花和旋覆花是具有升清降浊之法的主要花类药[12]。葛花可升发清阳,醒脾和胃,每遇清气不升之飧泻、肠风均可适用。高濂的《遵生八笺》卷十一讲述解酲汤:“外解肌肉,内清阳明,令上下内外,分消其患,使胃中秽为芳变,浊为清化,泰然和矣。”“诸花皆升,旋覆独降”,旋覆花降气除满,如张仲景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坚、噫气不除所用旋覆代赭汤,应用颇广。《神农本草经》言其:“主结气胁下满,惊悸,除中上二焦结闭之疾。去五脏间寒热,皆咸润降下之功。”临证见胃通降失司,在上有嗳气呃逆,在中则脘腹胀满,在下则大便秘结,此时旋覆花皆可用之。葛花、旋覆花两者相伍,一升一降,升发脾之清阳,清化胃之秽浊,使脾胃恢复“中焦如沤”的生理状态。比之升麻、柴胡,大腹皮、厚朴等升降清浊药物,葛花、旋覆花药性和缓不燥烈,无劫阴之弊。
“人身左升属肝,右降属肺,当两和气血使升降得宜”(《临证指南医案》),肝与肺一升一降,两经交接于肺中,如“龙虎回环”之势[11],脾胃之升降随之并调。
肝主生发,肝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机调畅通达,肝气左升则助脾气同升。玫瑰花、绿萼梅为疏肝解郁常用花类药。玫瑰花味甘辛,性微温,归肝经,可疏肝解郁以增行气,又可芳香醒脾以助纳运。如《食物本草》所言:“玫瑰花利肺脾,有益肝胆,可辟邪恶之气,气芳香而味甘美,令人神爽。”绿萼梅酸涩而平,入肝胃经,疏肝理气,和胃生津,善治疗肝胃气机郁滞所致的胁肋胀痛、脘闷嗳气、纳食不香,以及痰气交阻所致的梅核气等病症。故而针对脾胃虚弱者兼有肝气郁滞,此时需疏肝解郁,又忌刚燥伤胃。玫瑰花、绿萼梅药性和而不猛,疏肝解郁而无刚燥之弊[12],对于老年患者或者是脾胃虚弱者更为适合。
肺为华盖,其体清虚,其用宣降,其主治节。肺主宣降功能正常则可调节一身之气和液的运行,肺气右降则胃气同降。款冬花是降肺气的常用药物,《神农本草经》载其“味辛,温。主咳逆,上气,善喘,喉痹,诸惊痫,寒热邪气”,现代药理学发现款冬花含有挥发油类、酚酸类等活性成分,有润肺下气、止咳化痰的功效[13]。此外,又有洋金花、扶桑花、昙花、白兰花入肺经,亦可用于肃降肺气。
4.2 平衡中焦之寒热
中焦胃腑多血多气,不耐寒热,易被邪侵,病久多从热化。如肝气郁结,化火化热,横逆犯胃而肝胃郁热,又如湿邪侵犯中焦,湿性黏腻,郁久化火而脾胃湿热。花类药虽有苦寒泻热之功,然其柔和轻灵又不致苦寒太多而伤胃,故临床得到广泛应用。黄花地丁、金银花为常用药物。
黄花地丁,又名蒲公英,其功专阳明,泻湿热而不损脾土,比之山栀、黄连苦寒泻火更具平和轻灵之效。诚如《本草新编》曰:“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惜世人不知用之,阳明之火,每至燎原,用白虎汤以泻之,以免太伤胃气。盖胃中之火盛,由于胃中土衰也,泻火而土愈衰矣……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土,可以久服长服而无碍。”金银花,别名忍冬、鸳鸯藤。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止痢,可治阳明热盛之便秘、痤疮、口腔溃疡等症。其苦寒且不易败胃,代茶饮尤为合适,被誉为“世界四大保健品之一”[14]。《本草纲目拾遗》载其:“气味芬芳甘甜,可宽中开胃,清热解毒,代茶饮尤能散暑。”
“阳道实,阴道虚”(《素问·太阴阳明论篇》),脾脏属阴易阳损,多病从寒化,胃腑属阳易阴伤,多病从热化。临床常见脾胃寒热同病,然治中焦如衡,清热祛寒均不得太过,花类药清泻实热,柔和轻灵,不致苦寒太过,解胃腑郁热常可用之。
4.3 平和戊己之润燥
脾为太阴脾土,喜燥恶湿,胃为阳明燥土,喜润恶燥。故脾脏易受六淫湿邪困阻。花类药质地轻清,辛以发散,长于宣化、燥化湿邪,使受困脾脏恢复其功。其用可从“宣化悦脾”“健脾化湿”分述。
宣化悦脾即使用轻清、芳香之品宣散透散湿邪使脾气得清的方法。厚朴花为厚朴的干燥花蕾,辛温苦燥,《饮片新参》曰“宽中理气。治胸闷,化脾胃湿浊”。厚朴花可芳香化湿,理气宽中,其行气化湿力似厚朴缓,对脾胃湿阻气滞所致胸腹胀满疼痛、脘闷不舒甚好,对老年患者及脾胃虚弱者尤为适用。与厚朴相比,厚朴花作用偏于中上焦,而厚朴偏中下焦[15],因此其宣化功用更为突出。豆蔻花为白豆蔻之花,味辛性平,作用平和,可开胃理气,止呕除痞,长于宣化之功,用之醒脾悦脾常有佳效。正如《饮中新参》所载:“开胃理气,止呕,宽闷胀。”
脾主运化,脾脏本虚,则“脾气散精”之功受损,影响其“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能,机体水液的输布异常,导致内湿生成。加之脾脏虚弱,则更易感受外淫湿邪,最终内外湿邪合而困脾。此时脾气得健则湿邪自除。白扁豆花为健脾化湿常用药物,其解暑化湿,健脾和中,无温燥伤津之弊[12],《四川中药志》曰其“和胃健脾,清热除湿”,对于脾虚湿困之呕逆、吐泻,食少久泄均可适用。如《本草便读》言:“扁豆花赤者入血分而宣瘀,白者入气分而行气,凡花皆散,故可清暑散邪,以治夏月泄痢等证也。”
脾胃燥湿相济,互根互用。“燥郁不能行水而又夹湿,湿郁不能布精而又化燥”[16],如若脾胃任一方受病,则可见到燥与湿兼夹出现,此时尤需平衡,祛湿需顾护胃阴,润燥亦兼顾脾运,花类药质清力缓,不致燥湿太过而伤胃阴,为平和戊己润燥之良药。
5 结语
脾胃作为人体枢纽,居中央以溉四傍,脾胃枢机运化失常,五脏运转枢纽失司,四象不得斡旋。脾胃升降有序,则五脏安和,即使四象阴阳略有偏颇,亦可随中土升降调节和合有序。然治脾胃如衡,非平不安,遣方用药需“平正轻灵”,使脾胃之体各适其性,阴阳两不相奸。花类药轻清灵动,一可调理气机,使脾胃清浊得分,龙虎回环有序;二可平衡寒热,使胃腑郁热得去,脾阳正气不虚;三可协调润燥,使脾脏湿浊得化,胃腑阴液不伤。临证治疗脾胃病以求阴阳衡平,虚实平允,气血合和,花类药以其平正和缓、轻清灵动与脾胃之性十分相合,临床应用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