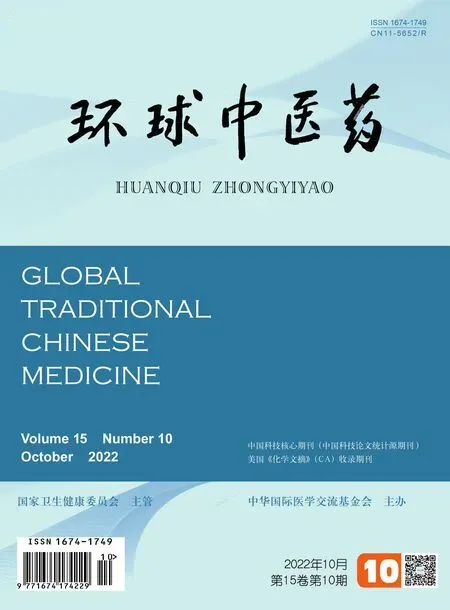从《小儿药证直诀》浅谈钱乙用“毒”之略
方枫琪 黄钢花
《小儿药证直诀》[1]集中体现了钱乙的学术思想,其对后世儿科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钱乙基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在用药方面精炼轻灵,消补兼施,寒温并投,用药忌香燥刚烈,力求柔润[2]。但品读深究可发现该书在用药中不乏使用有毒中药,这与小儿发病急、传变迅速息息相关。《类经》曰:“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张冰[3]等通过对古籍的梳理发现,随朝代演变“识毒”愈发深入,毒性中药的临床应用也愈加广泛。毒性中药大多作用迅猛,对沉疴旧疾、疑难杂症有着效专力宏的作用特点。有毒中药如同一把双刃剑,合理用之,效如桴鼓;随意用之,如当杀人。砷剂结合西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能更好地诱导分化,已得到国际认可[4]。然而,近年来随着中药不良反应事件的涌现[5]及现代药理学的快速发展,临床应用上谈“毒”色变,毒性中药的使用受到极大的阻碍。本文从剂型、服药方法、用法、配伍关系、用量等方面,浅析《小儿药证直诀》中有毒中药的使用,学习钱乙用“毒”思想,并搜索古今相关文献,对毒性药物的研究进展进行整理,以期在临床上更好地“识毒—用毒—防毒”。
1 中药毒性定义
关于中药毒性说法源远流长,西汉以前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冢宰》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东汉时代,《神农本草经》开始按有无毒性将中药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强调了药物偏性。南北朝刘宋时代雷敩撰写的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强调了有毒中药的炮制,中药毒性也开始了“识毒—减毒”漫长经验积累过程,但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性,对中药毒性的认知仅能停留在宏观层面。直到现代,随着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动力学等技术发展,对中药毒性的认识进入微观分子层面。现代药理学认为药物毒性是药物能够产生对人体造成损伤和危害作用的表现,一般这种毒性具有剂量依赖性。
综上,中药“毒性”有广义与狭义的说法,广义“毒性”同时概括了药物的偏性及纠偏作用,即包括药物的安全特征及不良反应;而狭义的“毒性”概念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毒性”,即引起机体功能障碍、病理变化及死亡的内涵。本文根据《中国药典》第一卷内记载的83种毒性中药饮片进行分类[6],发现《小儿药证直诀》中有毒中药共21种,其中有大毒2种、有毒15种、有小毒4种。有大毒中药为巴豆(5次)、巴豆霜(4次),有毒中药为朱砂(17次)、轻粉(12次)、雄黄(10次)、全蝎(10次)、制天南星(10次)、半夏(8次)、白附子(6次)、牵牛子(5次)、蟾蜍(4次)、硫磺(2次)、附子(2次)、甘遂(1次)、苦楝皮(1次),有小毒中药为苦杏仁(5次)、鹤虱(2次)、贯众(1次)、川楝子(1次)。
2 用“毒”以攻邪去实
《小儿药证直诀》中含有毒中药方剂接近一半以上,主要用于治疗疳积、咳嗽痰盛喘急、惊痫等小儿急重症。《温病条辨·解儿难》曰:“邪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小儿有着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病理特点,钱乙本着“急着治其标”的原则,常使用有毒峻猛之药以攻邪祛实,往往能起到重剂起沉疴的疗效。
2.1 脾胃虚衰,诸邪内生,当以上下分消,消积豁痰
钱乙认为小儿吐泻、慢惊、疳积、虫痛等脾胃病,或因脾虚而致,或日久致脾虚,皆能因“脾胃虚衰……诸邪遂生”,脾胃运化失司,痰湿内生,诸邪壅滞。治疗上“可以散药治之,使上下分消其气,则愈也”。钱乙不乏使用轻粉、巴豆、半夏等有毒中药。其一,轻粉,味辛,性寒,《本草纲目》中认为“轻粉,轻飞灵变,化纯阴为燥烈,其性走而不守,善劫痰涎,消积滞”。钱乙善用白饼子丸、麝香丸、铁粉丸等,用于乳食不消、郁久化热及痰热壅盛类病,乃取其祛痰消积,逐水通便之效。其二,巴豆,味辛,性大热,与轻粉一寒一热,互为补充。钱乙善用白饼子丸、安虫丸、珍珠丸等,用于脾胃素虚,寒积内生、痰热壅盛类病,乃取巴豆峻下冷积。其三,半夏,味辛,性温,钱乙善用白饼子丸、金箔丸、藿香散等,用于治疗小儿吐泻、慢惊、痰热壅盛类病,乃取其燥湿化痰,消积止呕之效。这三味有毒中药,在主治上均具有消积、豁痰功效,均可清下共施,上下分消;在功效上三者均为猛药,在消积豁痰方面具有其他中药不可比拟的疗效。但三者均具有一定毒性。有研究表明按0.58 g/kg轻粉每日给药,轻粉的组织蓄积量会逐渐增多,以肝肾组织明显,但给药1个月未出现中毒症状及主要脏器病理变化[7]。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半夏具有良好的止吐和抗消化性溃疡作用、镇咳平喘作用等,但亦具有肝脏、胃肠、心脏、肾脏等常见器官毒性[8]。
综上,笔者认为一方面现今关于半夏的毒理药理研究已日趋完善,临床上使用率亦高,但需关注的是,临床超剂量使用半夏的情况普遍存在,若长期使用可能出现器官毒性蓄积。有研究表明单次给予较高剂量的半夏酸水渗漉液可造成小鼠急性肝损伤,毒性出现早、持续时间长,且呈明显的时毒、量毒关系[9]。另一方面,关于巴豆、轻粉的毒理学及毒代动力学的基础研究几乎无报道,在药物用量安全性上仍属于盲区,临床上使用率低。著名中医临床家叶橘泉先生[10]曾言:“只要辨证、炮制妥当,在危急关头下,有毒的巴豆正是治病的利器。”另外,钱乙认为“脾主困”,主张运脾以醒脾,丁香、木香、麝香等芳香走窜辛散之品也多合而用之。
2.2 小儿急惊,心肝两旺,当以清热熄风,豁痰开窍
钱乙认为“小儿急惊者,本因热生于心……盖热盛则生风,风属肝,此阳盛阴虚也……热痰客于心胃”,其具有“风、热、痰、闭”的特点,病位以心肝二脏为主,病性以实为主。对此钱乙不乏使用朱砂、雄黄、全蝎等有毒中药。其一,朱砂用以治疗小儿一切急惊风,如大青膏、五色丸、安神丸等,乃取其清心镇惊安神之效,《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朱砂性凉体重,能养精神、安魂魄、镇惊悸、熄肝风。其二,雄黄用以治疗小儿急慢惊,如牛黄膏、牛黄丸、抱龙丸等,乃取其燥湿祛痰、可化肝风之效。《本草择要纲目》云:“雄黄入肝经气分,故肝风肝气,惊痫痰涎,头痛眩晕,暑疟泄痢积聚诸病,用之有殊功,又能化血为水。”其三,全蝎用以治疗小儿急慢惊,乃取其熄风镇痉,攻毒散结之效。《本草经疏》曰:“蝎禀火金之气以生……入足厥阴经,诸风掉眩,木属肝,风客是经,非辛温走散之性,则不能祛风逐邪,兼引诸风药入达病所也。”这三种有毒中药,分别具有清心热、祛肝风、祛顽痰的作用,三者常可相须为用,共奏清热熄风,豁痰开窍之效。但三者均具有一定细胞毒性。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朱砂具有镇静催眠、抗焦虑、抗恐惧等药理作用,同时具有肝肾毒性、神经毒性、遗传毒性[11]。有研究表明单次大剂量口服朱砂,不会出现明显毒性反应,但反复给药会造成毒性蓄积[12]。雄黄具有抗病毒、抗炎、抗结核、外伤皮肤、防止冠心病、心绞痛、抗白血病作用,同时有致突变、致癌、致畸、生殖毒性等毒副作用[13]。
综上,以上三种有毒中药分别可解急惊风之“风、热、痰”,现代药理学表明朱砂和全蝎可从不同途径发挥抗惊厥作用。樊永平总结国内外研究认为蝎毒是抗癫痫的主要有效部位,可明显降低海马神经元兴奋性,抑制动物癫痫敏感性和防止海马硬化的形成,对癫痫发作时的神经细胞同步放电及放电的传播有较强的抑制作用[14]。但关于雄黄抗惊厥方面的研究仍未见报道,其机制仍有待研究。另外,钱乙在治疗急惊时还擅长使用牛黄、麝香、冰片等中药。其中,牛黄清心豁痰开窍、凉肝熄风,冰片、麝香芳香开窍,以解急惊风之“闭”,现仍为治疗小儿急惊常用中药。
2.3 中病即止,攻补兼施
从《小儿药证直诀·中卷》医案中的药物运用,不难窥见钱乙在运用此类药物时常常中病即止,扶正祛邪兼备,且严格把握病机,抓准时机给药,故常常能起沉疴,病去体安。如钱乙在治疗婴儿惊痫时使用大青膏(内含朱砂)时,曰“盖儿至小,易虚易实,多即生热,止一服而已”,体现其“中病即止”思想;在治疗严重吐泻病时,先后使用使君子丸、石膏汤、水银硫磺二物并生姜水调下,以先缓补脾、后退热、最后温胃益脾,病即愈;在治疗肺炎喘嗽重症时,先予褊银丸(内含巴豆)下之以先下痰散积,后补脾肺等等,体现其攻补兼施思想。
2.4 用量精当,讲究个体化
考虑小儿脏腑柔弱,钱乙在用量上采用计量单位联合形态大小度量,且讲究个体化用量,说明钱乙在当时已意识到儿童用药用量需根据患儿年龄、体质壮实情况考量。参考韩美仙[15]古今药物剂量考究,《小儿药证直诀》中常出现计量单位换算关系依次为:1两=10钱=100分=30 g;常用形态单位由小到大依次为麻子大<粟米大<绿豆大<桐子大<皂子大<鸡头大。这类含有毒中药方剂中形态多以麻子大、粟米大、绿豆大为主,用量上除了粉红丸中天南星用到120 g,余用量多以分、钱计量。
药物的毒副性一般与剂量相关,钱乙用药轻灵,使用峻药严格把控用量。所以,虽使用峻药,但往往能病去体安。笔者认为,一方面,使用有毒中药的关键是把握好“量—效—毒”平衡。邸莎[16]认为临床上应坚持“以效择量、以毒限量、效毒权衡”的原则,从病、势、证、症、方、药、人等方面出发,以达“效—毒”平衡。另一方面,钱乙虽采用计量单位联合形态大小形式对剂量进行描述,但因丸剂制备需加入辅料,且根据原料药物性质不同,其制成丸剂大小不一。因此,药物剂量的精确估量较难。查阅文献,现已有关于《伤寒论》方药实物称重研究[17],笔者认为对《小儿药证直诀》中丸散剂复现进行药物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研究意义。
综上,钱乙所用常见有毒中药多数具有效专力宏特点,与小儿病理生理特点息息相关。后代小儿医也多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含有毒中药方剂载方136首,亦多运用于惊痫、痰喘、吐泻等脾胃、心肝病症[18]。现代临床应用上,有研究表明,含以上有毒中药的中成药,如小儿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一捻金等在降高热、镇惊、豁痰止喘等疗效确切,但其在用量用法、安全性评估仍有待进一步完善[19]。2018年《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20]中取消了经典名方制剂处方中有毒药味的限制及在急症、危重症方面的应用限制,但规定经典名方制剂申请人均需系统、深入地开展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因此,如何使得有毒中药在相对安全情况下发挥强大药效,仍是这部分有毒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重点。
3 用毒需防毒去毒
3.1 炮制以减毒增效
《小儿药证直诀》中常用炮制手段有水飞法、药物七情相畏法(姜制、胆汁制、曲制)、火制(烧、炮、炒、焙)、霜制等。传统工艺炮制对有毒中药减毒增效具有不容小觑作用。现代研究表明水飞朱砂可降低有害物质游离金属和可溶性金属的含量,降低其毒性[21]。水飞雄黄可降低游离砷水平,增加可溶性硫水平[22]。
郁红礼[23]等发现白矾浸泡或生姜加白矾共煮的方法炮制能显著降低天南星科 4 种有毒中药(掌叶南星、半夏、天南星、白附子)中毒性成分凝集素蛋白的含量。巴豆祛油制霜能降低脂肪油含量,降低毒性,缓和其泻下作用,增强其行水、消积聚的功效[24]。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炮制方法被挖掘。有研究表明冻杀干燥法加工全蝎可以有效地防止其活性蛋白质因加热而变性失活和被水溶解而造成的损失,显著地提高其蛋白含量和抗肿瘤活性[25]。采用高能球磨法制备纳米雄黄生品,并采用酸水炮制工艺得到的雄黄颗粒能够降低后期高能球磨接触时As2O3的产生,从而降低毒性[26]。
3.2 制剂以缓其“毒”性
《小儿药证直诀》中含有毒中药的方剂多为丸剂,居一半以上,散剂次之,汤剂最少。其中丸剂和散剂可较好缓解毒性,使药物发挥作用更温和。
3.2.1 大毒者须用丸 丸剂具有很好的缓解毒性作用,《苏沈良方》提出“大毒者须用丸”。笔者认为丸剂在减毒中具有以下优点。其一,丸者缓也。丸剂可延缓有毒物质在体内的吸收,减少毒副反应。其二,丸剂多可在常温下制备而成,现代研究已证明朱砂、轻粉、雄黄、水银等经火烧后可生成有毒物质。其三,丸剂在制作过程中常可加入辅料制之。辅料能影响药物制剂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及患者的依从性,甚至会造成不良反应,同时其对缓控释制剂、靶向制剂等的作用更为显著[27]。《小儿药证直诀》中含毒药方剂中常使用的辅料有蜜、面糊、姜汁、胆汁。蜂蜜味甘,性平,具有补中、润燥、解毒、矫味之效,为古代丸剂制作的常用辅料。面是用小麦、大麦、荞麦等磨粉而成,面糊可助药物定型,同时使药丸迟化,延缓毒性药物成分的释放[28]。姜汁、胆汁作均可相杀半夏、天南星,以减轻中药毒副作用。
3.2.2 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 散剂具有制作简便、便于携带、起效快、药物间相互作用少等特点,相较于汤剂来说,其不需要经过高温水煮,含挥发油、不耐热、贵重、难溶、毒性较烈的中药尤其适合制成散剂[29],且作用发挥快,便于婴幼儿服用,尤适合急病用之。同时,从《小儿药证直诀》中散剂使用方式、制散方法、制散粒径、每次服药量、煮散加水量、煎煮时间及煮后药液剩余量、服药时间、服药温度、药物溶媒等方面[30],可看出钱乙使用散剂十分讲究散剂制备、用量及服用方法,使散剂起到增效减毒作用。
3.3 特殊饮品以化其“毒”性
《小儿药证直诀》中方剂使用时多采用与某种饮品共服的用法,薄荷汤、米饮用之最多。其中,薄荷汤在肺系、心肝、脾胃病症中均有使用。其一,薄荷汤辛凉宣透,可引药上行,在治疗肺系病症时可加强透热疏风之效;其二,薄荷为“小儿惊风、风热家引经之药”(《证类本草》),在治疗心肝病症时可加强清热凉肝、熄风解痉之效;其三,薄荷有辟秽解毒作用,口感佳,有助于小儿丸剂、散剂的服用。米饮是用上等大米熬稀饭时,锅面上凝聚的一层粥油,其性味甘平,在治疗脾胃病症中常常使用,有健脾和胃、调和药性之效,可化诸药之毒[31]。
综上,从钱乙有毒中药使用中可窥出其中医特色“减毒”思想,无论从中药炮制、制剂制备还是同服特殊饮品来看,都是中药减毒增效的好办法。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借助药物安全评估规范化流程,具有更适用于儿童的剂量、剂型、配伍、口感佳等特点的中药复合剂具有较大潜在开发价值。
4 小结
《小儿药证直诀》记载方剂中,接近一半使用了有毒中药。钱乙认为小儿脏腑未全,形气未充,对于攻伐性药物多使用谨慎,但由于小儿发病急,传变迅速,钱乙在小儿急惊风、疳积、肺炎喘嗽等出现急危症时,多利用有毒中药效专力宏的特性,或上下分消、豁痰消积,或清热熄风、豁痰开窍。从《小儿药证直诀·中卷》医案篇可窥见疗效显著,且在用药中钱乙多注重药物使用时机,用量精当,攻补结合,中病即止,小儿多能病愈体安。同时,运用峻药时巧妙利用丸散剂、辅料、服药方法、配伍关系等减毒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及发展。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钱乙在有毒中药用药上受隋唐“服饵”盛行[32]及科学技术水平影响,仍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中药作用机制、毒副作用、新的炮制工艺、剂型被发现,但大部分有毒中药的毒代动力学研究仍匮乏,毒性指标存在多样化、不统一情况,缺乏可靠的不良反应临床报告分析,没有一套完整规范化的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等问题,仍亟待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