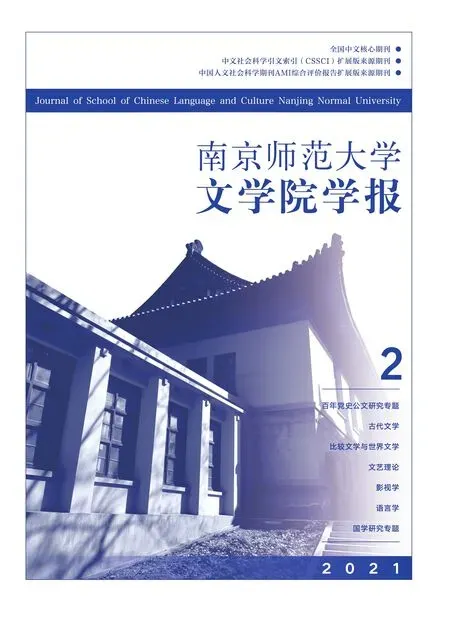试论古代建阳书坊的营销模式
宋文文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宋代刻书相当普遍,官刻、家刻、坊刻三大体系均已形成,全国刻书地点非常多,中心地则主要有浙江、汴京、四川、福建等。作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其所刻之书(以下简称建本)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各种典籍非常齐备,发行的范围也非常宽广,供科考用的场屋类书籍更是百倍于经史。建本确是我国古代刻售书规模最大、品种最多、影响最广的版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建阳书商的经销能力要强于其他刻书中心。
一、瞄准读者市场,确定出书定位
建本以坊刻为主,坊刻本在制作上,不会像官刻那样不惜工本,也不如家刻注重声誉。坊刻主要面对中下层民众的喜好与需求。自宋代雕版印刷业开始普及之时,不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其刊刻的书籍基本以文人士大夫的需求及审美品味为主,市场的书籍销售定位也是以这些人为主,而庞大的中下层民众几乎被忽略的。两宋时期,浙江杭州亦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所刻之书籍史称“浙刻本”,浙刻本制作精良,校雠细致,刊行成本较高。从知见的浙刻本数量及种类上看,官刻本为多,尤其是地方官刻本最多,各地区知府及太守在任职中刊行过大量书籍,内容基本为已故族人、乡贤等著作。其次才是坊刻本,多以诗词歌赋、佛经等迎合文人雅士之审美品味的书籍为主。故在印刷的质量以及刻印书籍的品味上,要求自然较高。
与较为复杂精美的建本相比,浙刻本的版面更显得简单朴素,不像建本那样广告宣传意味浓厚。这与建本的发行方式相关。受利润驱使,建阳书坊主们十分关注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自己的刻书范围,力求在竞争中保持不败之势。因此,书坊业飞速发展,其发展势头很快超过官刻与家刻,致使官刻、家刻渐淹没于众多的民间刻书之中。从书籍的种类及内容上看,除经史类书籍外,建阳书坊主还把目光投到了市民阶层所需的工具书及通俗物的刊行上,这些书籍往往价位低廉、通俗易懂,大大满足了购买力低下的中下层民众的需求与喜好。
在知见的元代刻书目录中,经籍史类的建本约有372种(经部111种、史部54种、子部115种、集部92种)。[1](P224)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籍数量不及宋代数量多,反倒是通俗类书籍数量更多。立足广大中下层群众是建阳坊刻业长期赖以生存之本,其广大的市场需求为坊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明代中期以后,建阳书坊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无论是书坊数量还是刻本数量都比明前期多出好几倍,吴世灯在《福建历代刻书述略》中称,嘉靖后建阳刻书有705种,若算上嘉靖之前,竟达到1000种以上。各地的书坊大多以通俗文学为刊刻对象,而建本在刻书内容上较前期相比,通俗文学及小说类书籍大量刊刻,并占据建阳书坊的半壁江山。至此不难看出,建本从出现之始,便将市场上长期被忽视的中下层民众定为其主要的销售群体。此外,从知见的建本书籍中可以看出,其字体多为颜体字,为节约成本,版面大多较紧凑,牌记装饰亦较为精致,以吸引读者眼球、作广告宣传之用。
杭州、建阳虽皆为古代两个有代表性的刻书中心地区,二者所定位的销售群体不同,浙刻本基本以正经正史及古今之人的诗词类书籍为主,质量较高,刊印过程中,往往不计成本,非以营利为目的。
杭州在五代时期便是吴越的王城,南宋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于临安。这一时期北方的官宦、地主、商贾等广大老百姓纷纷南来,使得此地人口剧增,浙江成为全国最富裕地区之一。苏轼曾在《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中言:“伏望圣慈深念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胜数。”[2](P916-917)杭州不仅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又历来文风兴盛,不论是官宦还是老百姓都十分重视教育,因此,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读书人。北宋时期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家都在浙江一带从事政务,他们闲暇之余也经常参与文学活动。杭州本地也有一些著名的诗人、词人的活动,如林逋、周邦彦等,都显示出杭州人文氛围的浓厚。在此背景下,可以想见其地书籍流通的状况自然会偏向文人雅士,所以刊刻的书籍定位基本以文人为主,对中下层民众的喜好是不怎么关注。加之宋代朝廷对版印书籍的严苛管理,杭州作为其都会城市,在书籍的刊行及流通上,自然不能“自由”发展,其刊行主流必然以朝廷及少数文人士大夫品味为主,传统文人所不屑的通俗类读物多不在其刊行之列。
相较于全国繁荣的中心城市杭州来说,“偏远”的位置给建阳坊刻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建阳处于闽北,在福建西北部一带,约有90%为丘陵或山地,间有狭窄河谷。但建阳虽偏于荒远之地,但交通却有优势,它位于密集的水路网络交通的枢纽,客观上为书籍的转运流通创造了巨大的条件。同时,相对于中心城市杭州等地而言,建阳远离政治中心意识形态的严苛把控,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也在客观上促使了建阳书坊业的自由发展,建阳书商们可以根据图书市场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营销方式,寻找适合自己的营销策略。于是,向来被其他刻书中心所忽略的平民读者群,成为建阳书商的主要市场定位,其所刊刻的书籍主要针对广大民众及科举监生。
二、刻书选题广泛,重点范围集中
建阳书坊主们凭借多年的发行经验及敏锐的商业头脑,总能紧跟市场需求、瞄准形势确定自己的刻印选题。刊刻种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医学用书、生活方面等工具类书。元代政府重视医药书籍,故关于医药方面的书籍不仅出自官刻,很多书坊也争相刊刻医书。叶德辉称:“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3](P114)元代医药方面的建本近三十种,比宋代品种增长百分之三十。如建阳余氏西园精舍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金成己撰《伤寒论注解》十卷、《图解》一卷、建安高氏日新堂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宋陈师文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图经本草药性总论》等。
建阳坊肆除了着眼于医药类用书,还刊刻了大量的日用类书,建阳每家书坊几乎都有一、二种类书刻本。《事林广记》、《翰墨全书》、《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日用类书籍被多次翻刻。甚至考亭学派的人物刘应李也刊行了《翰墨全书》,并在书中言:“书坊之书,遍行天下。凡平日交际应用之书,悉以启札名,其亦文体之变乎?”
二是小说戏曲等书籍。宋代已经盛行讲史、说神鬼报应和妖魔鬼怪故事,建阳书坊刊刻了大量通俗笔记小说,如《山海经图》、《龙城录》、《挥录》、《括异记》、《四朝闻见录》等七种;通俗话本小说有《三国志》、《开元天宝遗事》、《宣和遗事》等三种;[1](P160)还有平话小说盛行,麻沙等书坊出版过《武王伐纣》、《乐毅代齐》、《前后汉》、《五代史》、《大宋宣和遗事》等书。[4](P297-298)元人喜欢写曲,散曲更多。元代北人散曲和民间通俗文学的评话小说也在建阳书坊刊行。建阳书坊刊有《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等,而民间唱本小说、平话小说也非常流行,较著名的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三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三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统称“元至治刊平话五种”,也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5](P40-41)明代通俗文学发展空前,相关品种数量极多,“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后至明末建本小说杂书,更如夏夜繁星,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6](P378)
三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类书。科举类用书是历朝历代文人士子最常用、使用量最大的一类书籍,科举鼎盛之时,数量庞大的科考之子为建阳书坊提供了广阔且稳定的销售市场,销售应试书籍成为书坊的重要经济来源。
南宋初期,建宁府约有四千多人参加州试,而至淳熙十三年(1186),就有近一万人参加应试,[7](P4598)因此,科举使用之书需求应该是很大的。这些需求通常包含四书五经、小学、史评、总集等书。如《四书》,就印有集注、大全、精义、会解、讲义、说苑、图解、梦关醒意、拙学素言、披云新说、天台御览等多种名目,《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建阳坊刻著录的《论学绳尺》,此内容是有关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1卷,所录之文分为10卷,甲集12首,乙集至癸集一共16首。每两首立为1格,共78格。每题先标出处,再说大体意思,而缀加评语,又附上典故,分注该文之下。
此外,还有场屋应试用的策论文章。建阳书坊主们为迎合文人学子需要,在此方面做的非常突出。而场屋内外所用的程文策论更为畅销之书,一经刊出,必被学子抢购。《宝庆堂宋本书录》称:“用意严慎,当为能文之士所篇,未可与南宋建阳坊本出于书贾杂钞者”;叶廷珪刊刻的《海录碎事》、祝穆编撰《事文类聚》,《四库全书总目》则分别称:“盖随笔记录,不免编次偶疏,然其简而有要,终较他本为善也”;[8](P1147)“独是书所载必举全文,故前贤遗佚之篇,间有藉以足征者。……是亦其体裁之一善,在宋代类书之中,固犹为可资检阅者矣。”[8](P1149)总之,场屋之书只要编法得当,对士子科举考试还是有所帮助的。此类书籍为参考的士子提供了极大便捷,因为儒家经典卷帙浩繁,若从头至尾进行通读复习,需要耗费上大量的时间,故宋代就出现了应对科考之类的应试参考书籍。至明代,随着科考形式发展愈发的程序化,科考类参考书籍的功能自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建阳书坊中所刊刻的科举考试类的书籍数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三、质量优劣共存,不同书商互补
建阳书商皆围绕营利目的,形成一定的趋同性,将书籍定位在广大中下层民众读者,也有一部分书商则专刊刻品味高、质量好的带有一定学术性的书籍,而这些书商则补充了长久以来对“最下”建本认知的一些不足。
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及藏书家对建本的评价不高,其原因大多源于建本所用之刻书原料价廉,内容上校雠不精及广大的中下层读者群体等因素。叶梦得曾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9](P116)明代藏书家郎瑛指出:“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获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获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0](P664)由于建阳书坊众多,竞争激烈、印量庞大,而书坊主们为了谋取更大利益,不仅常以求节工省费、价廉易售为其主要的经营手段,在刊刻的书籍品种上,也以市场上最畅销的通俗读物为其主要的刻印内容。尽管建本有争议性,但建本中也不乏善本,即使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代善本中,仍以建本最多。
宋代建阳书坊主刘之问,他是麻沙人。其在庆元间出版颜师古注本《汉书》,不仅采用了宋祁的十六家校本,还用了其他十四家校本参考,又采用刘敞、刘攽、刘奉世三人刊误,内容精确,为宋代善本,明南监本、汲古阁本皆以此为底本。[11](P115)
建阳刻书大家中,当属余仁仲万卷堂刻书最好、最有名气。早在12世纪,余仁仲所刻的经书已经博得一片赞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评论其所刻经书:“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余仁仲所刻《春秋穀梁传》:“此本其字画端谨,楮墨精妙,为当时初印佳本。”[12](P83)南宋建阳黄善夫家刻,以刊印精美而著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最早刻本,便是出自黄善夫之手。由于在苏诗的“五注”、“八注”、“十注”基础上,“搜索诸家之释”编撰而成,此书最大特点是分类编次和汇注百家,后人称此书为“王注”、“百家注”。此书刚一出版,便遭到“闽中书肆遂争先镌雕,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期于广销射利,故同时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于文字,初无所更订也。”[13]
明代建阳慎独斋刘弘毅,刻书与大多建阳书坊主不同,其所刊基本为经史书籍,卷帙浩繁,校勘精良。因其刻书质量好,当地官府都请其刊书,明正德年间建阳知县区玉刻《山堂群书考索》,就让刘弘毅监督,“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14](P272-273)明代学者高濂曾说:“国初慎独斋细字,似亦精美。”[2](P220)清叶德辉言:“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雠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2](P268)明代建阳坊刻基本以盈利为首要,成本低、印量多、销量快是其惯用经营之道,故鲜有佳评,而刘弘毅在当时充满书贾味的刻书中心还能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尊崇自己的信仰理念,也算是为其开辟出另外一番经营之道。虽然短期内,不会像其他一些建阳书商可以收到可观的利润,但对于大多文人学子来说,刘弘毅所刻之书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故可以为众多藏书家所收藏,代代相传,为人们所珍视。
四、营销模式前卫,集中批发并行
建本的营销模式主要体现在集中销售和批发销售两个方面。
1.集中销售
景泰《建阳县志》中载:“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崇化两坊,更被称为“图书之府”。 传统的古代书籍贩售方式,一般以坐店为主,即刻印书籍的地方或书肆,建阳的书坊乡—麻沙、崇化基本便是此种坐店式集中的售卖方式。实际上就是集中的书市,刻书都集中在这两个书市上,
建阳的崇化与麻沙两地相距很近,书坊之间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但竞争也尤为激烈,两地书坊所刻书在内容上、形式上有很多共同地方,故两地都习惯在自家刊刻的书籍上铭刻地名,以示差别。如麻沙所刻书籍称“麻沙本”,崇化坊肆刻印之书则称作“崇化本”。著名的刻书世家余氏、刘氏、熊氏等皆出自这两地。《建川刘氏宗谱》载,刘氏先祖刘翱自西安迁居麻沙,其有四子,分别为晓、暐、晔、噪,分为元、亨、利、贞四房,其中元房、利房居麻沙,大部分以刻书为业,贞房在宋末时期,随刘君佐迁居崇化,并以刻书为业。[15](P197)《谭阳熊氏宗谱》记载,建阳熊氏分为东、西二族,熊氏刻书中又以西族书林让房一族中刻书者最多。二族祖先唐代熊秘原本是居住在崇泰里樟埠地区,十三世熊祖荣从崇泰里入赘到崇化里书林,其被称为熊氏书林始祖。
据《中国印刷史》所列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的书坊牌号有37家,其中刘氏书坊9家和虞氏书坊3家在麻沙,余氏书坊6家、蔡氏书坊2家、陈八郎家、建阳龙山堂、建安万卷堂、建溪三峰蔡梦弼和建安钱塘王朋甫等书坊均在崇化。由此得出:在南宋时期,至少有22家在麻沙、崇化两坊;其次,余、刘两姓书坊至少有15家,占麻沙、崇化两坊绝大多数。宋代的书肆以麻沙为中心,而离它较近的崇化、水南、崇川、钱塘等地都在出版书籍,但由于麻沙的交通方便,故这里又是书籍的集散地。因此宋元时期的建本,均被称为“麻沙本”。 此外,笔者通过查询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目录可知,今见的建本基本以麻沙本居多,如麻沙刻本《九经白文》、唐杜甫撰《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外集一卷(1919年上海文瑞楼据《古逸丛书》本影印)、《老子道德经》宋麻沙本(中华民国二十年故宫博物院影印)等。
宋代建阳刻书家族中,以刘氏、余氏最多,元至明亦是如此。其两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设在麻沙、崇化。至明代,几乎全部书坊都迁到建阳。
由于建阳书坊刻书多,书籍的销售和买卖构成了书坊的商业化模式。书籍的生产与销售基本都会在一个地方。大部分早期书坊主几乎都居住在建阳县的麻沙镇或周边地区。在后来的南宋后期和元代,书坊铺在崇化里的书林镇随处可见。
2.批发销售
明嘉靖《建阳县志》曾记录:“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各商贩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16](卷之三P6)每个月有六天专门出售书籍的集市,在同时期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商纷纷前来批货。由此可见此地商品书籍之丰富。查慎行《建溪棹歌词十二章》说:“西江沽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 书籍售卖虽有固定设铺的书店,有的是需要长途贩运,主要解决较远地区读者的需要。
刻印者兼营销售,刻书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是书商聚集之地。建本以价廉著称,杂书利润更高,而且品种向来丰富,各地书籍品种之间也需要调剂,所以才能吸引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来此批发。康熙年间《建阳县志》记载:“是日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建阳地区有水陆两路可以通向全国各地,书船是深入江南水乡图书流动供应的因地制宜的售卖方式,其规模比挑担售书方式要大很多。建本图书外销,有水陆两路,水路用木筏,沿建溪到下游,陆路向西,可以到江西,再北上到全国各地方。[17](P87)建阳刻本还利用分水关路远销海外,“麻阳溪和从武夷山南下的崇阳溪在建阳濯锦桥下汇合流向南平,称闽江,部分建本顺流而下经闽江转福州、泉州等港口转运至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8](P132)北宋时,高丽以三千两银向泉商徐戬订造了经版三千片[19](P72),南宋淳祐元年(1241),日本僧人回国时,带走了祝穆的《方舆胜览》、朱熹的《论孟精义》等在内的数千本中华典籍[20](P347)。
五、结语
闽北僻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成为相对闭塞但又自成体系的社会区域。在这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其名下的文化产业之刻书业却可以独霸书市数百余年之久,与建阳书坊主前卫的经营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建阳书商总是可以随着图书市场需求变化而变化,但不变的是其出书的群体定位——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建本最早打破传统,面向下层民众出版小说、戏曲等通俗廉价读物。因此,传统对通俗书籍的成见及对民间刻本的轻视而以偏概全,多数人对建本更存有全盘否定的评论,是有失公允的。
建本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建阳书坊主为了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保持领先,获得更大利益,皆或多或少采取过一些粗制滥造、压缩成本等手段。建阳坊刻业在满足商业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文化普及与知识传播的责任。尽管坊刻以营利为目的,但建本图书中也不乏善本。
建阳坊刻业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生产出与市场定位相适应的书籍产品,并随市场变化而随时做出调整,而且在销售模式上,也是在立足于本土的广大读者群的基础上,运用其便捷的水上交通,将“价廉”的书籍运输到全国各地。无论在生产或者销售上,其经营模式较同期的其他刻书中心相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广大的市场需求自然为建阳坊刻业提供了长期的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致使数百年间,建本图书营销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