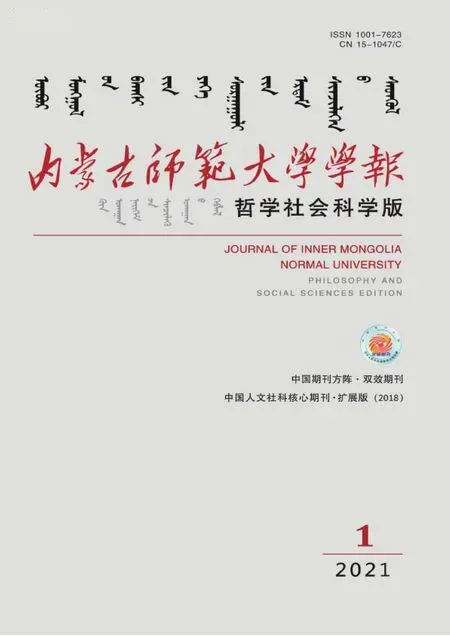辨 与 变
——《文心雕龙·辨骚》篇主旨探微
李金秋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辨骚》篇位列《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之末,是结篇,也是“文之枢纽”与“论文叙笔”的节点。从语法角度来看,五篇的篇名均是述宾结构。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下同),释义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原”“征”“宗”作为述宾结构的述语,其义皆属于本正源清,故要追根溯源;从感情色彩来讲,“道”“圣”“经”是根基,不可撼动,唯有遵循方可行。而后两篇——《正纬》《辨骚》含义则发生了改变,即:“酌乎纬”“变乎骚”,“正”“辨”二字则含有去粗取精、正本清源的意义了。作为转折篇之一的《辨骚》,“骚”有何变化,刘勰要辨析“骚”的哪些部分呢?根据刘勰“原始以表末”的为文之法,我们先来解读“骚”之所指。
一、“骚”的内涵解读
本篇中的“骚”是指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非单指《离骚》一篇。这一观点,各学家已然达成共识。如范文澜注曰:“《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中,《离骚》最为重,后人因以《骚》名其全书。”[1]48《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小序:“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2]133徐师曾《文体明辨·楚辞》[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4]、许文雨《文论讲疏》[5]皆认同此观点。
而别有发声的是纪昀,他是从“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的角度认定:“离骚乃楚辞之一篇,统名楚辞为骚,相沿之误也。”[6]54对此,李详在其《文心雕龙补注》中反驳纪昀之论:“详案:《周中孚郑堂礼记》云:《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又云作词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汉书·迁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皆举首篇以统其全书,据此,彦和亦统全书而言,纪氏殆未审也。”[6]54李详的批驳言辞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纪昀的立论之基予以反驳,“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即说《离骚》有诗教之内容,既有依经立义之旨,怎能偏以浮艳之根论之?二是从古人习作命名的惯称入手,指出纪昀之论不够审慎和严谨。
除了李详所述两点外,笔者以为从《辨骚》篇内也可看到论证:“《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7]22,《九辩》是楚大夫宋玉所作的长篇抒情诗。“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屈、宋逸步,莫之能追。”[7]22-24屈、宋即指屈原、宋玉(宋玉的成就虽不能与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承继者)。又有《时序》篇可以佐证:“爰自汉室,迨自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响,于是乎在。”[7]252意思是说,自汉武帝后的百余年文学史中,辞赋家的创作虽有变化,但创作的大趋向仍是效仿屈原和楚辞的。可见《楚辞》“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明确了辞赋之作“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因此说,刘勰的《辨骚》篇是总就《楚辞》而言的,而屈原之《离骚》作为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发挥了代表的作用,因此用以指代《楚辞》而已。
二、各家对屈原和“骚”(楚辞)的评价
在刘勰之前的文人对屈原和楚辞的品评态度有两种:一是扬,二是抑。因此也形成了崇骚派和抑骚派两大阵营。
扬之者的代表人物上至君王——汉武帝、淮南王,因“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离骚》可与《国风》《小雅》堪美,能做到“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其文辞的光芒如同日月般熠熠夺目。对这一观点有着深刻认识和阐发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道:“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8]2482这段话是从史学的角度给予屈原和其辞赋的论语,“文约、辞微”“志洁、行廉”,太史公更看重的是屈原“志洁”“行廉”的品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志向决定其辞作的思想力量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并提出这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认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由怨生矣。”[8]2482“怨生”道出了屈原《离骚》是“为情而文”,是言“离忧”的悲壮、激昂之情,是郁结于中而不得不发的自我宣泄的创作心理。这种发愤著书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之者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王逸。他接受淮南王刘安对《离骚》的评语: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认为是符合风雅传统的。王逸对屈原及其楚辞的评价是在和班固的论争之中建立起来的,集中在《楚辞章句序》[9]一文里。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这是对屈原以赤诚之心、皎洁之志报效国家,以“踵武前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心态的描写,也是王逸所认可和赞美的。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9]。
王逸肯定了屈原辞作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刘勰的认识与王逸是相通的。
抑骚派的代表是扬雄和班固。扬雄是从他自己的处世立身之道——隐德知命观来审视屈原其人。在他的凭吊屈原的辞作《反离骚》[10]中可见一斑:
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懿神龙之渊潜,埙庆云而将举,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所处……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
在《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中亦有记载: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10]
扬雄认同屈原的文采斐然,甚至超过了司马相如;他同情屈原被放逐的不幸,但对屈原坚贞不屈、投江赴死的行为表示不可取。在他看来,人生在世,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顺境时一展才能,不顺时则像龙蛇般潜藏起来,等待时机云起而腾飞;一切的遭遇皆是命中注定的,因此要做一个认清形势、辨明吉凶、全身进退的智者,而不能像屈原那样坚持己见以致以身殉国。扬雄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与屈原慷慨赴义的殉国精神是各自的人生选择,皆由其性情使然。
班固指摘屈原也是承继了扬雄的部分观点,列出三点不满处:一是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二是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三是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
第一处中的“露”“扬”二字指责屈原不能做到《大雅》所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明智之器”[9]卷1,是屈原的性格缺陷。第二处和第三处不满可归为一点:即屈赋所言“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显然《离骚》于此是不符合儒家敦厚精神的。故得出他的评判之语: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对屈赋并非一味批判,亦有其高扬之态:一是赞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二是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弘博丽雅”是对屈原辞作的总体评语,并指出屈原是后世辞赋家之祖师,可见班固对屈原及其辞赋是认可的,故称其为“妙才”。
综合崇骚派和抑骚派的观点,我们看到两派在对“文”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一是认可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艺术风格:雄奇瑰丽;二是屈赋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为辞赋宗,名垂罔极。不同点是在“志”的理解上,司马迁认为屈辞的精神是激昂向上的,王逸阐释《离骚》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之义,是儒家的中和之美。扬雄和班固是不满于屈骚中的激昂之志,班固指出《离骚》中部分内容是不符合风雅传统的。
笔者以为,两派的观点各有失全面。在《离骚》这篇长诗中既有司马迁所说的“忠怨之情”,也有追求“两美必其合”的唯美求女之义[11]150。屈原的美政思想与高洁品质在现实中饱受摧残,于是在回归神话中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自己的精神和谐,《离骚》正是诗人屈原追求精神自由的壮美宣泄。
通过梳理文学史上这段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论争,除了要让读者明晰文论本真之外,最主要的是了解刘勰在对前贤评析屈辞中所持的观点及立场,刘勰的判断又如何。
三、刘勰《辨骚》篇“辨”的内容与“变”之真义
(一)刘勰所需“辨”的内容
在《辨骚》篇中,“辨”主要体现在:
一是列举前人对《离骚》的不同评价,明析各家抑扬、褒贬之说的正确与否。
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之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6]20。
刘勰是推崇屈原和《离骚》的,但是他对汉代这场关于屈原及其辞赋的大讨论中各家的观点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没有做到“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所以得出的论断是不切实际的,是信口谈论而已。显然,刘勰不认同前贤对《离骚》的评价。那么,刘勰的“不认同”恰当与否呢?我们通过梳理刘勰在全书中评价屈原及《离骚》的语句后再加以甄别。《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其体系结构的系统性、完备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某一问题时需结合见于各篇的论述,综合起来进行探讨。在分析刘勰眼中的屈原及《离骚》这一问题时即是如此。
首先,刘勰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内容上是取镕经义,是符合儒家经典的习作。
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7]22。(《辨骚》)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7]74。(《杂文》)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7]26。(《明诗》)
在刘勰看来,楚辞是受到儒家诗三百浸泽的遗世佳作,有着诗者兴观群怨之内核,继承和延续了前朝和同时代的文风,是为情而造文的楚地之绝唱。
其次,刘勰认为楚辞在表现形式上是自铸伟辞,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7]22!(《辨骚》)
观其艳说,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7]254。(《时序》)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7]176。(《定势》)
《说文解字》:“奇,异也。” 本义是独特、殊异,后引申为出人意料、美妙。 刘勰以“奇文”“奇意”来言楚辞的与众不同,即“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12]。这是符合儒家风雅的绝美范文,是刘勰极为看重的。并具体分析楚辞诸多篇章予以佐证: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怅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7]22。(《辨骚》)
楚辞篇篇文意、辞采斐然,刘勰于各篇中用精取弘、道其精髓,充满着对其挚爱与敬佩之情。有着这样艺术魅力的楚辞,也正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才人有着“惊才风逸,壮志烟高”的情怀,才能写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惊采绝艳、无与伦比之作。
二是提出“四同四异”说。
“四同四异”说,是刘勰以儒家经典为量尺,通过比较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儒家经典后得出的。所谓“四同”,是指:“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的典诰之体,“讥桀、纣,伤羿、浇”的规讽之旨,“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的比兴之义,“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怨之辞,是同于《风》《雅》的,因此“四同”是对屈原辞赋的肯定。而“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表现在:“托云龙,说迂怪”的诡异之辞,“康回倾地,夷羿蔽日”的谲怪之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之自适”的狷狭之志,“士女杂坐,乱而不分”的荒淫之意。“四异”则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7]258(《时序》)造成的,是“风杂于战国”的结果。刘勰归总屈辞的“异”即是不同于以往的诗文创作,是一种新的、变化的创作形式,创发出新生的契机,这是刘勰见识的过人之处。
纵观“四同四异”说和汉代的崇骚派和抑骚派的观点,我们看到,刘勰是综合了两派观点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非是后者对前者的全面否定,只是刘勰结合《离骚》等系列楚辞文本,论述得更加具体,比前者更丰赡了一些。因此说,刘勰的“不认同”恰恰是针对前贤们各执一端,未能全方位地看待屈原及其辞作的影响和成就而表态的。
三是明辨后人学习楚辞的偏颇。
在学习楚辞上,六朝时文人追崇丽靡之词、注重藻饰、强调形式技巧、空尚浮泛,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多篇章中多有论及:
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7]24。(《辨骚》)
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7]14!(《宗经》)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7]178。(《定势》)
辞人爱奇,言贵浮诡[7]290。(《序志》)
汉代虽已有效仿楚辞的辞赋之作,但非文坛主流,辞赋之作不过是文人闲暇消遣而已,属于扬雄所称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因此,在两汉时期,楚辞是无法撼动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砥柱——经学的至高地位的。到了六朝时期,因为时人争相模仿《离骚》写作成为文场的流行。南朝文人裴子野撰文《雕虫论》予以批驳,文中描述了当时文风:“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宋书·谢灵运传论》亦有此论:“源其风流,同祖风骚。”可见,楚辞在当时的地位已然飙升。刘勰看到,后人在对楚辞的学习和模仿中,各取一二而不能得其要,尤其是陷入雕缛成体的漩涡,偏离了方向,造成文风的败浊、文坛的流弊,这样发展的后果势必会影响到群言之祖——儒家经典的至尊地位。因此,对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再认识已经变得亟需和迫切了,刘勰与汉代诸家对《离骚》的认识自然是不同的,亦是由“时序使然”。
(二)“变”之真义
刘勰辨析屈原和楚辞在两汉的论争和他给屈赋的评价与定位,其主旨是为了探求文变之道,以匡正世风。他看到了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由质逐文:
圣文雅丽 越世高谈 远近渐变 去圣久远
衔华佩实→文胜其质→体势浸弱→文体解散
↓ ↓ ↓ ↓
春秋时期→战国时代→两汉时期→六朝时代
显然,刘勰是推崇圣人文章的雅丽兼备,行文要做到质与文二者相得益彰,而非顾此失彼,即出现质胜文或文胜质的状况。而六朝的文坛却恰恰出现了“文胜”的审美导向——繁缛雕饰、艳风旖旎,“俗盛雅衰”的局面已经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雅俗观在审美体系的健全下产生了新变,不再仅以政教标准评价诗与乐,文人们以艺术为媒介超越礼法,追求通脱,彰显生命永恒的价值。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12]而这种偏离了儒家诗教传统的、一味的“通脱,华丽,壮大”之流弊,是刘勰“执笔搦翰,乃始论文”的驱动力。
于是,刘勰循其源头——确定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艳逸之端(这也是世人所认定的),纪昀评语:“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刘勰在对楚辞进行一番由里及外的剖析后,我们看到,刘勰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框定在儒家经典和辞赋之间,是上承《风》《雅》、下启辞赋的桥梁,即“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7]22(《辨骚》)。刘勰认为 《离骚》辉煌的艺术成就是基于“去圣未远”(即:《离骚》亦是依经成文)这一主要原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如何在正统(儒家经典)和新锐(楚辞之风)这二者间寻求一种平衡呢?刘勰提出“倚雅颂,驭楚篇”的创作准则。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7]24。
《雅》《颂》用以指代儒家经典,这是拯救时文弊端的良药。在刘勰眼中,经书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7]24,是“极文章之骨髓者”[7]10(《宗经》)。所以,儒家经典是所有文学范式的根本和准则,是“贞”和“实”;从楚辞中可汲取的是写作技巧,是“奇”与“华”,如奇伟的想象、华丽的辞藻,用以增添文章的情致。“倚《雅》《颂》、驭楚篇”是要做到“执正以驭奇”,即是以“倚雅颂之‘正’来驭楚篇之‘奇’,是要得的;失雅颂之 ‘正’来追逐楚篇之‘奇’,就要不得,虽说楚篇本身的‘奇’基本上并未离开风雅之‘正’(但也是‘风雅之博徒’了),可是再向前走一步,这‘奇’就是偏离正统的邪门了。”[13]140显然,“倚《雅》《颂》、驭楚篇”是解决“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7]178(《定势》)、穿凿取新、追新逐奇等问题的最佳途径了。
刘勰正是通过对屈辞的辨析与定位,借此对当时的文坛流弊予以规范,同时也对魏晋时期的文学进行了反思。诗教是自古以来教化百姓的重要途径,通过诗教可以达到“以正性情”的目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指出:“服膺诗教者”对屈赋采取“訾而绌之”的态度:“《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则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之。”[14]鲁迅先生这一论述表明了世人对屈原及“骚”之裁决上的“两难”的文学态度。
余论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主言志是言志派的创作旨归,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离骚》则以其奇思纵意、独具个性的语言与恢弘博大的构思,启迪后世的缘情表达,成为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鼻祖。因此,把两种不同的文学范式进行比较是有失偏颇的,诚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讲,“《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举以方经“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15]。也正是后世对《离骚》学习和模仿的不当,影响到屈骚的文学价值和时人对其的认知,使其成为汉赋“辞人丽淫而繁句”[7]264(《物色》)之弊的祖师了。从宗经的立场出发(刘勰对屈辞“四同”“四异”的评定亦是以依经立义为标准),刘勰绝不会将经书和《离骚》相提并论的,因为经书是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发脉,是毋庸置疑和不能受到任何危害的。
刘勰《辨骚》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未囿于一端去判定屈骚的诗教功能与文学功能,而是认为屈骚是二者兼备的典范,因此设定《辨骚》篇的位置是有深远意义的。“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上承《诗经》,下开汉赋的关键。如果没有它,中国文学就失去了发展的媒介,是很难突破风雅的枷锁,创发新生的契机,所以他把《辨骚》列在卷首。看成是他‘文学本原论’的重要环节。”[16]这是符合刘勰《辨骚》篇主旨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