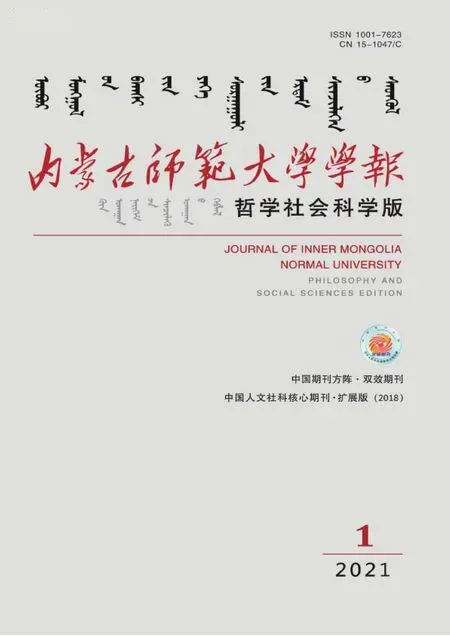平淮西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田恩铭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9)
唐代战事与文学的关系是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对唐代的战争文学做了粗略的勾勒,主要针对的是直面战争的文学作品。王福栋《唐代战争诗研究》则拓展研究视野,对于战争诗与战争过程的关系有所梳理,有所侧重地探讨了战争诗中的功名意识、女性形象、历史想象。近年来,相关的研究选题中,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是研究较为集中的重要议题。胡可先对于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宏阔而深入的剖析[1]136-140。吕蔚以安史之乱与唐诗的关系分析战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2]130-132。
唐代“平淮西”战事发生于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因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死后,吴元济擅自称留后,唐宪宗发兵征讨,直到李愬雪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而结束。关于平淮西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胡可先概述了元和削藩与文人创作的关系[3]136-140。彭万隆《元和削藩与元和诗歌》将元和时期讨伐藩镇的战事活动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颇具学术眼光[4]130-233。陈尚君《大唐王朝的第200年》亦在勾稽平淮西相关的史事中提出新见[5]。关于平淮西战事的文学书写,笔者曾有《“平淮西”与元和士人的文学书写》,侧重分析战事之过程与文学书写之风貌[6]132-156。实际上,唐代战事的前前后后存在着知识精英阶层关于战与非战的论争,存在文人参与军旅的激情书写,存在战事结束后的盖棺论定,更回荡着战事过后的文学余响。这些方面均与文学经典的生成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平淮西”的前前后后与八篇经典有关,其中包括四首(组)诗、四篇文。四首(组)诗是白居易《琵琶行》、刘禹锡《平蔡州》、元稹《连昌宫词》、李商隐《韩碑》。四篇文是吴武陵《遗吴元济书》、韩愈《平淮西碑》、段文昌《平淮西碑》、柳宗元《平淮夷雅》。此外,柳宗元《古东门行》、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及韩愈的战地短歌系列及联句诗均堪称名作,裴度、杨巨源、王建、姚合、鲍溶亦有诗作纪事。元和之后,白居易、刘禹锡、王建等人与裴度交游活动中依然会追忆战事之图景,有诸多诗篇传世。这些诗篇构成合唱之效果,乃是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之袅袅余音。
一、《遗吴元济书》:吴武陵对战事的关注
宋祁、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中,吴武陵以文学家身份立传,列入《文艺传》之内。宋祁、欧阳修一改《旧唐书》史臣立传之宗旨,对于《旧唐书》列入《文苑传》的人物进行大规模调整,其中变动最大的是中唐阶段。吴武陵能被收入《文艺传》之内,这是对其文学家身份的认可。宋祁、欧阳修认可吴武陵文学家身份的主要依据是吴武陵所写的四封书信。四封书信中,较为重要的是《遗吴元济书》《上韩舍人行军书》,这两封书信均与平淮西战事有着密切的关联。
淮西地区是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一个战事多发地,皆因节度使更换而引起。平淮西战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如王永兴所论:“讨伐淮西吴元济之战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之前为第一阶段;此后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为第二阶段。”[7]46淮西长期为吴氏家族所据,而“自为留后”是藩镇所遵循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并非唐朝所情愿为之,却又时常默许之。吴元济之父吴少阳,任淮西节度使。本来,淮西节度使是吴少阳之兄吴少诚。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吴少诚卒,弟少阳自为留后,朝廷也就予以默认。同是吴姓,吴少阳很欣赏吴武陵。据《新唐书》本传载:“淮西吴少阳闻其才,遣客郑平邀之,将待以宾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阳子元济叛,武陵遗以书,自称东吴王孙,曰……元济得书不悟。”看来,吴武陵的这封信没起到《与陈伯之书》的作用。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匿丧,自总兵柄,朝廷遣使吊祭,拒而不纳。十月,下《招谕蔡州诏》,《全唐文》作《晓谕淮西制》,中有“擅自继袭,肆行寇掠。将士等迫于受制,非是本心,遂令此军,若坠渊谷”之句,以严绶取代吴元济,宣示招降之意。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因“纳于忠顺之途”不成,朝廷下《讨吴元济制》并立即出兵征讨。据此时间节点,吴武陵劝降书当作于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下《招谕蔡州诏》之后,或《讨吴元济制》之后。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年(815年),吴武陵尚在永州,与柳宗元经常聚会,于僻地寻找风景,该文撰写时间或许应更晚一些[8]136。
这封劝降书被全文采摭入《新唐书》,毫无疑问,当是吴武陵被列入《文艺传》的代表作。《遗吴元济书》行文立论颇具大局意识,从国家大义出发,以“智”“仁”“孝”“明”论定其反叛之举乃是“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败俗”。这封信出语果断,立意明确,直截了当,反复申说反叛的严重性。柳宗元称其“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9]1978,诚非虚誉。而“兴西汉之文章”则蕴含有古文之精义。文章依时、势、地三端而论吴元济之不合时宜:“时”则从德宗开始,讲述藩镇势力分布之情形,得出战事一起,淮西必败的结论;“势”则集中于唐宪宗之声望,“今天子英武任贤,同符太宗,宽仁厚物,有玄宗之度”[10]7385。反叛的结果是骨肉分离、家破人亡;以领地而言,“三州至狭也,万国至广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10]7385。基于此,若战事一起终会落得个“尸不得裹,宗不得祀”的下场。
吴元济确实有过动摇,但我们无法确认吴武陵这封书信是否发挥了推动作用。战争仍然在进行中,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被委以重任,踏上征途,韩愈为行军司马,吴武陵有《上韩舍人行军书》。据《新唐书》本传云:“会裴度东讨,而韩愈为司马,武陵劝愈为度谋……武陵之奇谲类如此。”[11]5790-5791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度使持节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等使,以太子右庶子韩愈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八月发赴行营。吴武陵上书韩愈献计献策应该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吴武陵这封信的主旨则可以“诚使诸侯以严暴,吾以宽厚收之;诸侯以杀戮,吾以礼义怀之;彼有所短,吾见其长;彼有所乏,吾施其余,则事何不济?功何不成?”概而言之,采取怀柔之策,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最好。吴武陵曾经在柳宗元的山水小品中作为其旅伴出现过。元和十二年(817年),已经告别永州的吴武陵还有《遗孟简书》,书信中为迁转到柳州的柳宗元叫屈,云:“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10]7386此时的柳宗元已在柳州任上,本人也时刻关注着战事的进展,战事刚刚定局便有《平淮夷雅表》上呈,从中能够见出渴望改变境遇的迫切程度。
在《旧唐书》文本建构的基础上,《新唐书》常常采摭文章入传以重构文本。柳宗元、吴武陵的传记便具有代表性,柳宗元的传记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以采摭文章入传而完成的,吴武陵的传记则是另一种情况。《旧唐书》并没有专门为吴武陵立传,而是在吴汝纳传记中简要叙及,云:“武陵进士登第,有史学,与刘轲并以史才直史馆。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赃贬潘州司户卒。”[12]4500《新唐书》为之立传,列入《文艺传》中,被采摭的文字便包括与平淮西相关的两篇文字,其中《遗吴元济书》全文采摭入史,而《上韩舍人行军书》则采摭部分内容,因与柳宗元相关,《遗孟简书》《与裴度书》均采摭入传。在《新唐书》史臣看来,吴武陵的文学家身份因上述文本而确立,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对于文学与政事关系的重视程度。从唐宪宗下《讨吴元济制》到吴武陵《遗吴元济书》,其中包括武元衡遇刺,这是平淮西战事提速的一个节点。再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吴武陵《与韩舍人行军书》,构成了一个属于吴武陵所关注的独立阶段。吴武陵的文章是直面战事的文本,无论是与吴元济对话,还是与韩愈对话,他认为劝降书所发生的作用即便不能直接结束战事,也会对于战局的进程发生影响,他或许高估了自家书信的作用。简而言之,吴武陵之所以被北宋史家列入《文艺传》之中,主要是认定《遗吴元济书》《上韩舍人行军书》等文本为直面战事的文学经典,故而才会采摭文本入传而被经典化。
二、白居易《琵琶行》与武元衡之死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间接原因是武元衡被刺事件。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武元衡遇害,裴度亦重伤。可以想象的场景:这一时节天亮的有些晚,武元衡刚刚走出居于靖安坊的宅子,便遭到刺客的迎头一击。或许揣在怀里的奏章还带着体温,或许有些内容还在打腹稿,或许吟诗的雅兴刚要被一触而发,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便停止了思考。武元衡之死引发朝廷震恐,历来主和的萧俛、钱徽等人便再次发声,而唐宪宗和裴度则征讨之意已定[13]314-321。白居易本是太子官,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宫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武元衡之死干卿何事,他却上书要求尽快抓捕刺客,于是,遭到本当言事者的忌恨。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写有《赏花》及《新井》诗,被认为“甚伤名教”。据白居易《与杨虞卿书》 ,他认为自己是因言获罪,进言的原因则是因“平淮西”导致武元衡之死,“素恶居易者”则借他事以陷之。《旧唐书》《新唐书》对于这件事均有所叙述。据《旧唐书》本传:“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12]4344-4345《新唐书》所叙与《旧唐书》一致,只是在重构中发生了叙事角度的变化。如本传所云:“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坠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11]4302武元衡遇刺发生之前,白居易就屡屡上言,言平淮西之事,相关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李师道出钱为魏徵孙赎故第之事,另一件是派中人吐突承璀率师讨王承宗之事。如果将这些结合起来考察,则不难得出结论,即白居易是征讨淮西的支持者阵营中的一员,这一点与韩愈的立场是一致的。元和十年(815年)七月,白居易最终被以不孝的罪名先贬为江州刺史,王涯认为白居易不宜治郡,再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与师皋书》中叙及此事,仍难以遏制愤激之情。
《琵琶行》是如何炼成的?其中必定有武元衡事件的影子。元和十一年(816年),白居易已在江州任上,有一次在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水上传来琵琶声。这不是普通的琵琶声,而是“铮铮然有京都声”,这是江州与长安所建立的音乐和文学的空间。白居易以强烈的主题意识,叙述与琵琶女从相识到共鸣的过程。先是听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乃是因地域之关系而选择见面,这是琵琶女第一次弹琵琶;“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之后第二次弹琵琶展示的主要是技艺;因技艺引出彼此追忆身世之后,琵琶女第三次弹琵琶则建立在彼此相知的基础上,带来“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特殊效果。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对话在琵琶声中徘徊不已。其中曲江宴饮、雁塔登临历历在目,留下的还有富有血腥画面的武元衡遇刺。白居易的听琵琶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是琵琶女激发出来的,循音而见人,听音而知人,知人而思己。琵琶女声名的时过境迁唤起白居易强烈的自我比较意识。陈寅恪引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同相识”诗句时认为:“则既专为此长安古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14]49细读《琵琶行》,构成七个层面:江州的风物环境与长安的国际都市景象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难听的本地俗曲俚音与阳春白雪的琵琶声构成又一个比较的层面,流落江州“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与长安当红的自己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居于长安曲江宴饮的白居易与身处江州的自己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知晓琵琶女身世的白居易与仅仅听音的白居易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琵琶女的当红与白居易的长安生活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琵琶女的流落江州与白居易的贬谪江州构成一个比较的层面。外媒的触动往往会拨响诗人的心弦,因平淮西而导致武元衡被刺,白居易就此贬谪江州,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元素,白居易的命运因此发生改变,上述比较层面均与此相关。正是琵琶女的出现将京城与江州联系在一起,令白乐天思及被贬的情境,于是,琵琶女、琵琶将江州与长安连接起来,江州与长安将琵琶女与白居易联系起来。实际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地位并不对等,而是来自京都的琵琶声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文学经典的动人之处就在于间接文本的特质,事在诗中却并没有直说,而是仅仅作为背景,蕴含于作者、琵琶女的追忆之中若隐若现,所起的作用便是激发出白居易的贬谪情结。
《琵琶行》中并无直指平淮西战事的诗句,白居易虽然以地域之对比暗含追忆旧事,关于帝京却无一言,“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起笔与琵琶女将当年的受宠与“老大嫁作商人妇”加以对比,白居易截断众流,没有叙述自己贬谪江州的原因。施补华《岘傭说诗》便认为白居易这段自叙“又嫌繁冗”,其实繁冗的叙述中才能写出同病相怜之意,叹谪居之沦落,“辞帝京”之原因隐括其中,意到笔随而令人浑然不觉。不过,白居易隐而不发还是有原因的,此次贬谪的直接原因是不孝,尽管理由牵强却难以辩解,一旦写在纸上还会无端增加政敌;而间接原因则是武元衡遇刺后的越职上书,此事更无法以诗笔言之,还会增加因言获罪的可能性。于是,与《长恨歌》中用“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样,白居易直接叙述身居江州的“迁谪意”,言意不言事是一种缘自潜意识的自觉选择。
武元衡之死对平淮西战事的走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唐宪宗、裴度下定决心,持续一年的平淮西战事正式提速。当此际,贬谪在外的刘禹锡、柳宗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古东门行》《代靖安佳人怨》等诗作。这些抒情文本仅仅是平淮西进程中的一个前奏。这个前奏指向的究竟是一战到底还是中途退却?可以说,因坚持平淮西导致武元衡被刺杀,而武元衡之死影响到本不相干的白居易,这件事促动他勇敢地越职上书,因之被触怒的谏臣们另辟蹊径寻找贬斥白居易的机会。他们从白居易的诗作中找到可攻击的要点,白居易猝不及防地被击中,只好离开长安,奔赴心目中那遥不可及的江州。江州地僻方知长安米贵的缘由。因琵琶女的介入由人及己,琵琶声中倾听入神的白居易想必是在平淮西战事的刀光剑影中体味着“青衫湿”的内涵。就文学接受史而言,无论是在中唐,还是在后世,《琵琶行》均是以平淮西为特殊创作背景的文学经典,只是武元衡之死仅仅是平淮西第一阶段的一个轩然大波,白居易因此被贬,复因此遇到已在京城过气的琵琶女,两人聚于江州,沦落中互诉身世而产生共鸣,遂而生成被称为“叙情长篇”的抒情文本,在后世的阅读过程中因性别、身世之对话而产生极佳的接受效果,进而渐次经典化,成为千年来传颂不衰的文学经典。《琵琶行》的经典化既与“平淮西”有关,又与文学文本的抒情传统关联甚深,背景因素对于作者固然重要,而文本一经形成便入读者的期待视野,文本阅读的影响因素自然也就不止一端。
三、韩愈的战地短歌、联句与战事之进程
裴度的二赴淮西意味着战事的第二阶段开始。元和十年(815年)五月,裴度为淮西行营宣慰使,赴蔡州行营“宣谕诸军”,杨巨源《送裴中丞出使》一诗纪其事。裴度宣慰归来后力主淮西可取,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劝宪宗当机立断。六月三日,裴度受重伤,六月二十五日,裴度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宪宗强力支持裴度,接受其建议,并为之扫清障碍。元和十二年(817年),李愬赴淮西,战事格局发生变化。六月四日,吴元济乞降,但已经无法掌控局势。七月,裴度为宣慰使,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随之奔赴淮西。王建有《东征行》一诗纪其事。
与裴度一起奔赴淮西,韩愈以武将身份参与其中,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诗作,其人堪称是行程叙事的战地记者。我们不妨以裴度并督战作为线索,将韩诗与战事之过程结合起来读读。现存的诗作,韩愈写给马总的最早,是在出发的前一年,马总已经任刑部侍郎。《酬马侍郎寄酒》:“一壶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无诗酒,其如月色何。”刘禹锡在元和十二年(817年)与马总唱酬往来,有《酬马大夫以愚献通草茇葜酒感通拔二字因而寄别之作》《酬马大夫登洭口戍见寄》等诗作。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赠刑部马侍郎》:“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15]1033一年之隔,身份之变化让两人迅速进入角色。韩愈这一时期的诗作堪称平淮西的战事实录。《过鸿沟》云:“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方世举评曰:“此诗虽咏楚、汉事,实为伐蔡之举,时宰有谏阻者,几败公事也。视为咏古则非。”[15]1034奉和、酬赠甚至联句均与平淮西战事紧密相关,如《送张侍郎》:“司徒东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两府元臣今转密,一方逋寇不难平。”写自信平蔡必胜之决心。行至女几山,裴度有诗作,如今仅存“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韩愈和之,充满壮志豪情,《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云:“旗穿晓日云霞杂,仙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15]1036依然展望胜利后的图景。到达郾城有《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诗云:“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期。幕中无事惟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宿西界有《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烧烟火宿天兵。不关破贼须归奏,自趁新年贺太平。”至襄城则有《同李二十八夜宿襄城》:“周楚仍连接,川原乍屈盘。云垂天不暖,尘涨雪犹乾。印绶归台室,旌旗别将坛。欲知迎候盛,骑火万星攒。”有《过襄城》:“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远来迎。”有《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荒山野水照斜晖,啄雪寒鸦趁始飞。夜宿驿亭愁不睡,幸来相就盖征衣。”如果选定一个点,郾城的联句会是首选。《晚秋郾城夜会联句》是李正封和韩愈共同创作的一首五言叙事长诗。这在与平淮西相关的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李正封引题,韩愈主导叙事的节奏,“平生耻论兵,末暮不轻诺。徒然感恩义,谁复论勋爵”。如方世举所论,这首诗先是由引子引出平淮西战事之议题,然后一分为二,至“且待献俘囚,终当返耕获”是实写,写蔡州平定之前的旧事;而后是虚写,“皆悬拟歼贼、奏凯、振旅、饮至诸事”[13]1064。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创作的这些文本与此前的战事诗风格不同,善于抓住战事进程中的细节直抒胸臆,在唐代战事诗中可谓别开生面。
雪夜平蔡州,马总任留后,而韩愈等人还京,韩愈有《酬别留后侍郎》:“为文无出相如右,谋帅难居郤縠先。归去雪销溱洧动,西来旌旆拂晴天。”[15]1066韩愈以实录之笔法写其所闻所见,蔡州平定,难以掩饰兴奋。自淮西归京,一路上展望的是盛世之追忆,如过连昌宫有《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云:“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过桃林有《桃林夜贺晋公》,诗云:“西来骑火照山红,夜宿桃林腊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时重叠赏元功。”有《次硖石》:“数日方离雪,今朝又出山。试凭高处望,隐约见潼关。”至潼关有《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又有《次潼关上都统相公》:“暂辞堂印执兵权,尽管诸军破贼年。冠盖相望催入相,待将功德格皇天。”奏凯后一路欢歌,这是韩愈的诗化言说。鲍溶有《蔡平喜遇河阳马判官宽话别》、姚合有《送萧正字往蔡州贺裴相淮西平》,这两首诗是表达“雄鸡一唱天下白”喜悦之情绝好的见证。接下来便是刻石立碑、论功行赏,战后的余事依然会生成新的文学文本,这是韩愈平生写得最为畅快的系列作品,这些文本却在传播的路径中未曾经历广泛传播的经典化进程。
四、《平淮西碑》:功名之争与文学经典的同题叙事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二十八日,唐宪宗下《平吴元济德音》,第二天下《诛吴元济敕》,十一月一日吴元济被斩于独柳树,刘禹锡有《城西行》纪其事。十一月末,裴度、韩愈等人自蔡州回京,十二月十六日到长安。功成名就之后便会迎来谁上功劳簿及所占份额的争夺。平淮西的胜利的确鼓舞人心,这样的成就必然要树碑立传。根据《旧唐书·韩愈传》,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二月,韩愈受诏撰写《平淮西碑》,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云:“以收复淮西,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16]2882这个任务落到韩愈的手上,韩愈从构思到完成共70日,元和十三年(818年)三月二十五日撰成,自谓“经涉旬月,不敢措手”。
那么,韩愈《平淮西碑》是如何记述“刬刮群奸,扫洒疆土”的呢?《资治通鉴》对征讨平淮西战事进程的叙述,与段文昌《平淮西碑》近乎一致。关于雪夜入蔡州,韩愈《平淮西碑》叙述过于简单,仅仅将平蔡州列于裴度的部署之中,作为战事的重要环节,没有被突出之意。云: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合战亦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17]1518-1519。
因时局的变化,李愬一方的抗争,韩愈《平淮西碑》被磨去,重写的任务落到作为战事局外人的段文昌身上。这不仅仅是从局内人到局外人的变化,作者与裴度关系远近的变化,而且是文本从古文到骈文的变化。段文昌一变韩愈之叙事格局,所撰《平淮西碑》将平蔡州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云:
将决其机,以安海内。复命丞相裴度,拥淮、蔡之节,抚将帅之臣。分邓禹之麾旆,盛窦宪之幕府,四牡业业,于藩于宣。先是光颜、重允、公武,戎旅同心,垒垣齐列,常蛇之势,首尾相从。胡骑之雄,纷纭纵击;逐余孽如鸟雀,猎残寇似狐狸。干矛如林,行次于洄曲。丞相之来也,群帅之志气逾厉,统制之号令益明,势如雷霆,功在漏刻。贼乃悉其精骑,以备洄曲之师。唐随帅李愬,新总伤痍之军,稍励奔北之气,城孤援绝,地逼势危,而能养貔虎之威,未尝矍视,屈鸷鸟之势,不使露形。是以收文城栅而降吴秀琳,下兴桥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众以留之或谓蓄患,不利吾军。愬诚明在躬,秉信不挠,爰命释缚,授之亲兵。祐感慨之心,出于九死。纵横之计,果效六奇。粤十月既望,阴凝雪飞,天地尽闭。乃遣其将史旻、仇良辅留镇文城,备其侵轶;命李祐领突骑三千以为乡导;自领中权三千,与监军使李诚义继进,又遣其将田进诚领马步三千,以殿其后。郊云晦冥,寒可堕指;一夕卷旆,凌晨破关。铺敦淮濆,仍执丑虏。虽魏军得田畴为导,潜出卢龙;邓艾得田章先登,长驱绵竹。用奇制胜,与古为俦[15]1572-1573。
韩愈《平淮西碑》叙述李愬雪夜入蔡州一事过于简略,仅仅不到40字。段文昌《平淮西碑》以骈体行文用近三百字渲染此事,将李愬定谋略之过程和盘托出。毫无疑问,平蔡州是平淮西的重头戏,更是震慑藩镇的关键环节,韩愈、段文昌就平蔡州本身用字差别不大,而是在如何谋篇上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李愬调兵遣将的过程于平淮西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不当忽略的。战事结束,韩愈受诏撰《平淮西碑》,撰写的主导思想恐怕不是韩愈所能决定的。黄楼就认为:“平淮西后,宪宗君相恐李愬等居功难抑,对其有所戒心,《平淮西碑》体现了宪宗君相抑制李愬等武臣的策略。”[18]87而《平淮西碑》被磨则是因为淮西局面发生变化,唐宪宗为协调文武关系而不得已为之[18]87-88。若果真如此,《平淮西碑》就不仅仅是一篇为平淮西盖棺论定的文字,而是卷入时政的媒介。宪宗为调节文武之矛盾而磨碑,给予韩愈的打击是双重的。韩愈是战事的亲历者,文体文风改革的推动者,磨碑事件虽属将帅功绩之争夺,对于韩愈而言,一方面否定了其战事参与人的权威话语权,另一方面则否定了其作为执笔者的文学变革意图。
韩愈《平淮西碑》撰成,刘禹锡、柳宗元颇有微词。一方面认为并非平情叙述,对于李愬平蔡州的作用有所弱化;另一方面遣词用语不够雅致。这里还要述及柳宗元《平淮夷雅》和刘禹锡《平蔡州》,一组文与一组诗构成了对应关系,是外放者对于战事的另一种总结。或许是旁观者清,不会夹杂私情,韩愈写裴度必然有自己的情怀,而刘、柳虽然认可裴度,却不会从个人立场出发,而是根据自家从战事的进程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判断。柳宗元《平淮夷雅》成,有《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献平淮夷雅表》,柳《雅》《皇武》写裴度,《方城》写李愬。战事结束后的诗作中,当以刘禹锡《平蔡州》为经典之作。《平蔡州》计有三首:第一首先写李愬雪夜入蔡州,再写裴度来镇抚之事,落笔于讴歌宪宗时代;第二首借助老人之口言说太平之可贵;第三首则转向“天子受贺登高楼”,极言一个战事胜利而四海晏清的连锁反应。就与平淮西相关的诗作而言,刘禹锡《平蔡州》堪称经典之作。翁方纲《石洲诗话》认为:“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19]427刘禹锡对于自己的诗作亦颇为欣赏,如对于第二首的解读,无论是首联写“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还是尾联“因以记淮西平之年”,均蕴含自得之意[20]426。
《平淮西碑》的经典化进程在晚唐便已开始,北宋时期渐次形成定论,主要围绕战事叙述的客观性、今古文之争的合法性而展开。平淮西战事结束,便进入总结阶段,需要树碑立传,为平淮西撰写碑文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韩愈的头上。韩愈正在兴头上,古文家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平淮西碑》树立,又被磨平,再被树立的时候,韩愈早已离开尘世。又过了半个世纪,同为河南人的李商隐有《韩碑》一诗,为唐人《平淮西碑》之争盖棺论定。李商隐《韩碑》一诗以叙事之笔推崇韩愈《平淮西碑》,全诗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裴度为中心叙述平淮西的过程,李愬等人被认定为其爪牙;第二部分写韩愈撰《平淮西碑》之始末及韩碑被磨一事;第三部分是称颂“公之斯文”,有“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之句。《韩碑》重在立论,论点出而主题成,主题成而文字显,文字显而情感真。入宋以来,对于《平淮西碑》有褒有贬,褒者多而贬者少。褒者不出李义山评论之两端:一端立于家国情怀,一端立于文章之法式。韩碑、段碑孰优孰劣,于接受史中尘埃落定。因争功韩愈《平淮西碑》被磨而有段文昌《平淮西碑》立,再有李商隐《韩碑》,三篇经典文本的生成经历由战事而文学,由文学而政事,最终回到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韩碑,落脚点依然回到韩碑,只是已经由中唐而入晚唐。就文本生成的语境而言,韩愈《平淮西碑》是平淮西战事结束后生成的文本,因争功而段文昌有《平淮西碑》,韩、段碑之优劣又引出李商隐《韩碑》,从文到诗,构成了文本经典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五、《连昌宫词》:平淮西落幕后的余响
一座唐玄宗、杨玉环未曾到过的宫殿,为何成为元稹的关注点?元稹的想象力并不强,却以坐落在河南宜阳县的连昌宫作为李、杨的栖居地,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连昌宫词》借助老人之口完成了对李、杨故事的再造过程。这首诗完成于元和十二年(817年)末或元和十三年(818年),就在本年或前一年,平淮西尘埃落定,吴元济伏法,淄青等地归顺,战事结束便意味着一个区域和平生活的到来。元稹在平淮西结束的背景下,以“努力庙谟休用兵”来表达自己对于战事的论评。
《连昌宫词》是以“平淮西”为触媒形成的文本,可分为两个独立的叙事单元。诗作开篇就引出“宫边老翁”,以老者的叙述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这个叙事单元包含3个部分:第一部分渲染安史之乱前的盛世镜像。这部分内容以“上皇”与“太真”的奢靡生活为中心,琵琶、念奴、李谟、吹管、擫笛构成一组意象群;百官队仗、杨氏诸姨构成一个对举盛况展示,意味着一个盛世的巅峰状态。这个巅峰状态在公元755年戛然而止。于是,连昌宫之图景为之一变:“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第二部分的这四句诗点到为止,并没有像杜甫那样刻意描画安史之乱的万象,而是一带而过。第三部分透过老者的叙述展示了连昌宫人去楼空渐为废墟的凄凉景象。这部分内容也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集中写“两京定后”连昌宫的命运,无人顾及而宫门久闭。二是因“去年敕使因斫竹”,老者终于有机会带人一览残境,这座无人打理的宫殿早已是“荆榛栉比”“尘埋粉壁”,今昔对比令人潸然泪下。连昌宫的未来呢?“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第二个叙事单元则是作者的独立思考过程。这个过程先由一问一答引出:“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这是作者发出的质问。问罢老翁就要回答:“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21]705-706上述诗句将开元、天宝一分为二,世风为之一变。问答之后,引入作者对于当下的思考:“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元稹所以写《连昌宫词》,与连昌宫的地理位置相关,这里正是平淮西的战地周边区域,战地如今终于恢复平静了,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未来就需要“努力庙谟休用兵”。元稹在创作《连昌宫词》的过程中,采取了将战事“并置”的写法,以连昌宫为关键词联结起来,“安史之乱”与“平淮西”被放在同一个层面书写。这里存在叙事的偏向,元稹并没有直面战争,而是隐没战场及战事本身,以连昌宫的今昔之变烘托出和平与战时、战后的区别,主要侧重于描写“安史之乱”的影响来突出战争的残酷性,“卒章显其志”,结尾以“平淮西”战事的胜利发出渴望“休兵”的议论。实际上,整首诗是以“平淮西”触发的感想,元稹是将历史语境落在连昌宫的空间之内,进而贯穿于整首诗的叙事进程中。
以“安史之乱”为书写背景,《连昌宫词》的比较对象是《长恨歌》。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从校书郎贬盩厔尉,仙游寺在盩厔,王质夫、陈鸿家在此,三人一起去仙游寺,有感于李、杨故事。据陈鸿《长恨歌传》,“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22]758。歌成,使陈鸿为《长恨歌传》。为什么要写呢?《长恨歌传》有所透露,云:“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22]758宋人笔记中多有称赞《连昌宫词》者,如洪迈《容斋随笔》“古行宫诗”条云:“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23]161而后专列“连昌宫词”条以比较《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优劣,云: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荡,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23]161。
洪迈将两篇作品加以比较,以能否“监戒规讽”为前提,暗含的便是以“安史之乱”与“平淮西”并置。宋人张邦基、明人胡震亨皆以“箴讽”立论。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为微之之作过白乐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19]171。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文云:“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著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讽;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贺裳《载酒园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的论说与之相类。宋人潘淳《潘子真诗话》则将《津阳门诗》《长恨歌》《连昌宫词》放在一起比较,认为“稹之叙事,远过二子”。诸家评论的着眼点均是乐府诗的讽喻功能,言说史事则由过去指向当下。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连昌宫词》胜于《长恨歌》:“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23]245算是为数不多的从文学风格上得出结论的。两篇作品写作时间不同,一篇元和元年(806年),一篇元和十二年(817年),《长恨歌》乃是白居易早年之作品,《连昌宫词》乃是元稹中期之作品。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是元稹受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14]63,所蕴含的讽喻之意或与所处语境有关,认为《连昌宫词》末章与萧俛、段文昌“消兵”之说有关系。这两篇诗作的创作时间,一在《胡旋女》之前,一在《胡旋女》之后,从时间维度上构成了不同的观察点。在新乐府运动的背景下,凸显了元、白乐府诗创作的特殊性,即融入以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形成的创作群体之中,文学创作之讽喻意义彼时被凸显的乃是趋同之风尚。
如果要分析元稹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变化,可将元和初期《胡旋女》《柘枝舞》等作品与《连昌宫词》比对。《胡旋女》讽喻之意或来自李绅原作,此乃唱和活动之通例。不过,结合两人关于安史之乱的诗文,因思世乱而抗拒胡音之用意始终未变。元、白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在创造的文本中关注个体当下的生活,又将政事与文学结合。元、白刻意讽喻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元和时期,此后稍有涉及,故而未能衔接上以安史之乱背景下的述往事为主题之书写过程。《长恨歌》《胡旋女》《连昌宫词》均涉及李、杨故事,立意不同,所描述的故事图景亦不同。白居易《长恨歌》以叙事而落在叙情一端,《胡旋女》乃是因乐舞之域外而突出文化之纯粹性,蕴有胡音乱华之意。《连昌宫词》则从今昔对比入手,以李、杨纵情欢娱场面铺排与乱后之荒凉形成两幅不同的画面,强化期盼消兵之愿望。元稹《连昌宫词》是因平淮西胜利有所触动生成的文本,反对战事、追求和平乃是书写的主题,今昔对比是写作手法,这也是《连昌宫词》堪称经典的必备条件。如此说来,平淮西便是元稹创作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使得元稹将连昌宫作为选择的地理空间,将安史之乱作为时间节点,将平淮西之功成作为立论的一个基点,两者结合则侧重于战事与民生之关联性,这是我们阅读《连昌宫词》不可忽略的前提。
余论:从平淮西相关联的文学创作看战事与文学的关系
所谓“元和中兴”是以平淮西为前提的,一场关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战事引来文士阶层的广泛关注,自战事起至立碑封赏均有诗文纪事,其中便经历了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一方面,战事为文学经典的生成创造了书写主题,因而诸多文学文本应时而生;另一方面,文学经典依战事的进程而形成了独立的阅读空间,而后才因多种元素的介入而被经典化。以平淮西为中心生成有不同文体的经典文本,形成合唱之效果,围绕战前、战时、战后的历史图景,书信、诏令、碑文、诗歌、表奏均有不凡之作。
就平淮西战事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战事与文学相互刺激形成新的话语场域,自中唐至北宋,文学家、史家均空前重视文学与政事的关系。因此,一旦战事发生,因之发生关联者就会诉诸笔端,创作相关的文学文本。以平淮西为中心的文学书写而言,跨文体叙事的特殊意义可以成为考察战事与文学的切入视角。平淮西之过程与文学经典的生成以诏令、书信、碑文、诗作、表等多种文体文本形成合唱的声音。经典文本与政局、古文运动、文武关系均建立联系,文学书写呈现一个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典范。
第二,从创作的作品来看,以平淮西为中心构成了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间接文本更易于被经典化,经典化进程受到传播过程中传播语境、传播者、媒介、信息、受众等多个因素影响,传播效果自然不同。所谓直接文本就是直写其事的文本,如《遗吴元济书》《平蔡州》《平淮西碑》《平淮夷雅》《韩碑》及韩愈的战地短歌及联句之作,上述作品与平淮西紧密相连;间接文本则是以平淮西作为一个源头而产生的文本,作者并不是战事的见证者,而是因事成文,如《琵琶行》《连昌宫词》等文学经典之作。
第三,战事提供了“事”,亦有文人因之生“事”,所创作的这些文学文本便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文体自身的特点,或侧重一端。叙事或者抒情的文本均与议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叙事、抒情与议论相结合是文本经典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突出特征。
大浪淘沙,经过千年以来读者的筛选取舍,《琵琶行》《平蔡州》《连昌宫词》《韩碑》《平淮西碑》在起起伏伏中被经典化,成为围绕平淮西战事前前后后的追忆性文本。这些文本生成于战事的不同阶段,因传讽至今而经典化。涂炭生民的硝烟早已散去,想象的空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史家的笔下,而是弥漫于诗笔的罅隙间。